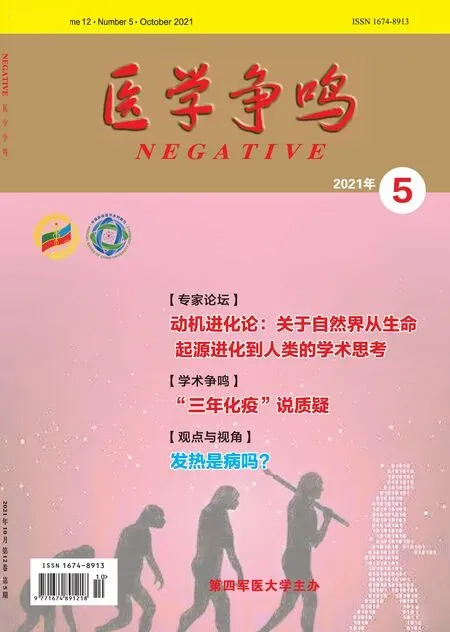动机进化论:关于自然界从生命起源进化到人类的学术思考
张成岗(北京中医药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北京 102488)
在迄今为止原因仍然未知的情况下,地球从36亿年前逐渐开启了生命起源与进化的漫长历程。最初从微生物开始,历经藻类、植物、动物等过程,及至20万~200万年前开始出现人类,逐渐形成了目前仍在快速发展中的人类社会[1-2]。在达尔文进化论中,基于大量科学观察所形成的《物种起源》以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认识,构成了人类对自然界在生命现象方面的主要认知体系[3-4]。然而,从动物进化到人类,如果仍然使用“弱肉强食”的方式来看待人类社会的话,显然既不人道、更违伦理,即人类社会不应该存在动物世界那样纯粹的“优胜劣汰”之丛林法则,而是应该形成能够显著促进人体身心健康与人类社会和平发展的理论与实践,让人类这样的“万物之灵”尽可能减少诸如病毒疫情、慢病顽疾、焦虑抑郁、恐怖袭击、难民危机、战争阴云等事件的威胁,在短暂的百年岁月中,拥有阳光心态和文明理念,实现健康长寿、颐养天年的目标。显然,回答这个问题充满巨大挑战。然而,随着近年来生命科学领域研究的新发展,使得从“物质和意识”以及“心理和精神”等复杂关系的角度进行深入剖析该问题提供了可能,对于从“被动适应与主动进化”的角度重新理解“人是什么”、“什么是人”以及“什么是真正的人”等问题提供新思路。
1 对于人类和人类存在意义与价值的持续追问推动着人类发展
对于“人是什么”以及“什么是人”的研究与思考,几乎贯穿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所有过程,并最终将在科学与哲学的层面得以充分体现。随着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科技进步,人们在物质层面上已空前丰富,健康水平和人均寿命也显著提升。然而,由于人类社会的复杂性,不同国家的发展历史和文化过程与文明现状各不相同,导致即便是在21世纪的今天,世界各国的发展也并不均衡,有的相对富裕,有的则相对贫穷。即便是在发展较快的国家中,也仍然存在大量慢病顽疾、焦虑抑郁以及病毒疫情等现实问题;而在发展相对较慢的国家中,恐怖袭击、难民危机、战争阴云等事件也让民众缺乏安全感和幸福感。因此,人生究竟是幸福的、还是痛苦的,或者说应该是幸福的、还是痛苦的,该问题一直贯穿着作为个体的人的一生以及群体意义上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需要从“人是什么”以及“什么是人”这样的关于“人的本质”的角度进行深刻剖析。
就“人”本身作为一种特殊的“高级动物”而言,在无异常情况和病变的状态下,正常人的自然寿命通常是100年左右,自精卵结合开始,分别经历胎儿、婴幼儿、青少年、中年以及老年等阶段后寿终正寝。其中,惟有在受精卵的胚胎发育时期和胎儿形成阶段,母亲通过子宫和脐带为胎儿提供发育所需要的全部营养物质并带走代谢废物,确保胎儿处于最理想的发育环境中,胎儿无需关心自身的“衣、食、住、行”。当历经十月怀胎、胎儿呱呱落地之后,婴儿就开始了“吃、喝、拉、撒、睡”与“衣、食、住、行”等充满刚性需求的一生,并从幼儿园等环境开始学习知识,逐渐走上认识自我、认知世界和发展思想的人生道路。
在人的刚性需求过程中,与动物相同的“吃、喝、拉、撒、睡”是每天的“必修课”,是决定肉体存在的关键,其中以“吃”为第一需求,而“衣、住、行”则是必须在满足这些“必修课”之后的需求,毕竟动物的“意识”有限,既难以关心、亦无能力去解决其自身的“衣、食、住、行”等问题,这是动物与人的基本区别。当然,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则是人类具有系统完善的语言能力和知识体系,能够通过复杂的思维过程和科学研究,形成人类独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且人类知识还一直处于快速、甚至加速发展的状态。尤其重要的是,作为拥有复杂意识与情感意志和精神信仰的人类,对于人类和人类存在意义与价值的追问,则是动物所不能、可能也并不需要、而且也没有能力达到的。只有通过努力去理解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并实现更高的目标和追求、尤其是精神追求而不只是物质需求,人生才会更有意义,才能避免和动物一样,只满足于日常的基本生理需求。
2 饥饿与摄食动机可能是肠道菌群驱动下人体被动应答的表现
在对于事关人体生存的第一需求即“饥饿与摄食”及其背后的动机进行深入研究的过程中,所获得的新发现为深入理解关于“人的本质”这一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近年来受到国内外大量报道肠道菌群与人体慢病密切相关的启发,笔者所在实验室以自身甘当“小白鼠”,完成体验式观察进而开展广泛科学研究,最终发现并证明“饥饿源于菌群”,即迫使人体每天必须进行“一日三餐”摄食的饥饿感来源于肠道菌群,后者是在胎儿出生后被自然界“主动接种”到胃肠道、并形成与人体相伴终生的共生微生物群体[5]。虽然医学界公认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机体通过免疫反应防止肠道菌群进入人体而避免感染性疾病的发生,然而,通常并未意识到自然界在“设计”人体的过程中,会通过使用肠道菌群而不是人体本身来启动摄食所必须的饥饿感[6]。这种“自然”设计理念对于动物而言在理论上也具有普适性,即自然界很可能也是使用“肠道菌群”以“万有菌力”的方式来迫使动物和人体产生饥饿感而被动摄食,一方面用来满足动物和人体的营养需求,另一方面用来满足肠道菌群的营养需求[7]。由此提出“菌心进化论”[8],并证明通过靶向肠道菌群向其提供人体不吸收的植物多糖和膳食纤维等食物“喂饱菌群”,即可显著减少并消除饥饿感,人体使用自身库存糖原和库存脂肪提供能量,只饮水不摄食,正常作息7~14 d,体质量可生理性下降5~10 kg,肥胖相关慢病症状可显著改善[5,9-22],从而形成“菌心说”学说,认为肠道菌群是迫使人体摄食所必须的饥饿感之“信号源”,是人体摄食的中心、重心与核心,而使用诸如柔性辟谷等技术通过靶向调控肠道菌群,即可调控人体饥饿感,使得人们能够从每天必须“按时吃饭”的摄食行为调整为“按需吃饭”,在饮食上更自由,身体上更健康[7,23]。
在发现“饥饿源于菌群”的基础上,参考计算机的工作模式对人体结构与功能进行理解,可将人体以“一分为三”的方式定义为“肉体、菌脑、人脑”,其中“肉体”由人类第一基因组DNA系统(operating system 1,OS/1)所控制、“菌脑”由人类第二基因组DNA系统(operating system 2,OS/2)即微生物基因组DNA系统所控制,相应地“人脑”则由人类“第三”系统即音像符号语言系统(operating system 3,OS/3)所控制。“肉体”作为运动载体即“肉体主动”为“菌脑”和“人脑”提供平台,后两者则是“菌脑主吃、人脑主思”的关系[24]。于是,在以“饥饿感”为代表的“摄食”这一基本的、首要的、事关人体存活的食物需求和生存动机方面,可被理解为是由“菌脑”引导、“人脑”应答、“肉体”执行的完整过程。除此之外的“衣、住、行”则是人体生理需求,而思想、精神、意志、信仰等作为“人脑”的功能并通过“精神追求”予以展现。
3 人脑使用音像符号进行逻辑分析表现出思维判断而发展动机
如前所述,一旦将人体对摄食的直接记忆归因于由携带非人类基因组DNA遗传密码的人体共生微生物,尤其是肠道菌群所构成的“菌脑”所承载,就能够比较合理地解释“人天生下来就会摄食、而不需要学习”这样的“本能”行为。从基于“饥饿源于菌群”的“菌心说”学说而言,肠道菌群在人体内胃肠道中繁殖其自身后代的压力,以通过生物化学反应分解和破坏胃肠道黏膜而引发轻度炎症反应,通过胃肠道神经系统以及迷走神经和神经内分泌机制向大脑以信号上行方式进行传递,被大脑解读为饥饿感,表现为人体每天必需通过摄食活动以保护和防止肠道菌群对人体胃肠道的分解破坏,从而形成人体摄食行为的“内在压力”和“内生动力”。而且出生在不同地域的人群,其体内通常是从当地生活环境接种相应微生物群体进入胃肠道,形成终生共生的肠道菌群即“菌脑”,承载了所在地域环境的“菌脑”之食物记忆,表现为“一方水土养一方菌、一方菌群养一方人”的饮食生态链,从而为“摄食无需学习”这样的本能行为提供了相对合理的科学解释,即人们通过拥有肠道菌群而直接获得源于肠道菌群对于食物记忆能力的饥饿与摄食信号(相当于“获得性遗传”)。有什么样的肠道菌群就有什么样的摄食信号,相应的肠道菌群能够帮助宿主处理相应的食物,否则就容易出现由于所摄入的食物与肠道菌群不匹配而导致过敏、呕吐、腹泻、便秘等问题[25-26]。
就“人”本身而言,学习记忆是终生都需要进行的过程,也是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然而,此前学术界对人类的摄食行为是否需要学习和记忆的相关研究并不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上世纪20年代俄国科学家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实验,通过建立声音刺激信号和动物摄食行为之间的关联性,可观察到动物胃肠道的消化液分泌行为,这也是实验心理学的代表性研究。长期以来,由于学术界(生理学、神经科学、心理学以及精神科学等)基于一般性的现象观察而形成“大脑摄食中枢”控制摄食行为这样的惯常思维性认识,而且通常认为胃排空、低血糖、饥饿相关基因的表达等是“饥饿感”的原因,加之一百多年之前,在发现条件反射这种现象的时候,人们对于肠道菌群的认识和理解还远远没有达到现在这样的广度和深度,因此,关于“摄食”动机与行为的相关知识,目前仍然处于相对停滞、局限于“大脑摄食中枢”调控人体和动物摄食行为的认知程度,却难以合理解释为什么“越吃越胖、越胖越吃”,也难以提出科学有效的防止贪吃多占、烟酒依赖甚至毒品成瘾等严重的“人被食物所控制”即“人为物役”现象。现在看起来,很有可能是由肠道菌群所构成的“菌脑”从饥饿与摄食的信号源角度,在影响甚至调控了“人脑”对于以食物为代表的碳源需求的正确判断与合理决策。
显然,人和动物的行为,虽然看似是受大脑和神经系统指挥,可似乎更像是受“动机”所控制的。以“摄食”为例,“条件反射”作为一个典型的摄食行为,既与心理学密切相关,同时又与神经科学密切相关。虽然“大脑摄食中枢”控制人和动物的摄食行为是不争的事实,且拥有大量科学证据支持;然而,关于人和动物“摄食”行为的原始动机又是什么呢?是何种因素驱动了这种摄食行为的产生呢?已知骆驼在沙漠中可以连续数周无需摄食而正常生活,冬眠动物如黑熊等也可以连续数月无需摄食而正常存活,诸如此类现象的存在,说明“摄食”行为对于少数动物来说,并非必须的,而是可调控的,只不过不同动物对于“饥饿”的调节和忍耐能力是不一样的。就事关人和动物肉体生死存亡的“摄食”行为而言,以人为例,不摄食就会饥饿、如果连续数日不摄食的话,就会由于饥饿而导致营养不良甚至死亡,从而形成了人类对于饥饿具有天生恐惧感,且所表现的生活常识为一个人不吃饭是不可想象的。正是由于“饥饿”现象对于人们的内心和精神而言,具有强大的挑战性,因此,有人通过“绝食”或“断食”或“禁食”来锻炼自己的意志,提高毅力,甚至与宗教信仰密切相关[27-28]。然而,通过近年来的研究,笔者实验室提出并反证“饥饿源于菌群”之后,从而形成了“肠道菌群(菌脑)向人体赋予饥饿感”这样的新认识[22,29],并且可以通过靶向肠道菌群调控(减少甚至消除)人体饥饿感,让人体的饥饿感与摄食行为变得科学、可控之后,就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和重新认识人体“摄食”的动机、过程、机制和意义了。
在“由肠道菌群微生态所构成的‘菌脑’可能是人体对于物质记忆的物质基础”中[30],深入讨论了人体对于以食物和饥饿感为代表的、通过胃肠道和呼吸道与人体接触的物质记忆可能源于人体共生微生物菌群DNA遗传指令复制其后代所驱动,通过生物化学反应来实现,从而为揭示“物质需求”记忆的“物质基础”即“菌脑”提供了新思路。相应地,就人脑而言,其所需能源主要(99%)来源于葡萄糖,神经细胞并不像肠道菌群那样在胃肠道中直接与作为生物化学反应底物的食物(碳源)通过直接接触或肠道菌群复制后代的方式形成对于特定底物(食物)的“直接记忆”,那么,人脑中主要记忆的是什么内容呢?这些内容又是怎样被人脑所记忆的呢?这也正是神经科学领域近几十年乃至近一百年来正在深入研究并期望得到答案的几个问题,同时也是国际“脑科学计划”以及我国脑科学计划的重点与难点所在[31]。
虽然目前尚难以回答“人脑是如何进行记忆的”这个复杂问题,但有三点内容应该是明确的:第一,人脑肯定不会像肠道菌群那样通过复制自身后代的方式进行“物质记忆”,否则神经元一旦和种类繁多、庞杂多样的底物(如食物)直接接触的话,就会引起多种异常反应,尤其是免疫反应。众所周知,成年动物脑内除个别区域如海马和嗅球的少数神经元可以分裂之外,绝大多数神经元是不分裂的,反过来提示人脑记忆应该不是依靠神经元分裂这种方式来实现的。第二,既然人脑的能量来源主要是葡萄糖,而神经元内部有大量突触小泡,神经细胞之间的连接也是通过大量突触来联系的,说明人脑记忆应该依赖于脑内庞杂的突触联系。由轴突、树突以及其间相互交叉连接所构成的国际神经科学领域研究热点如“人脑连接组学计划[32-33]”以及Rao等[34]于2019年提出的“化学连接组”等,应该是脑内记忆的物质基础。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地方,即人脑具备对语言、音像等符号的抽象记忆、逻辑判断及思考分析能力,即人脑所“记忆”的“对象”应该是“符号”及其逻辑,并且主要以人类语言、音频、视频等特定符号的有序排列来表征,这一点也是我们此前所说的“人脑受‘OS/3’控制而工作”的原因,是基于OS/1对人体的生理控制以及OS/2对人体共生微生物尤其是肠道菌群的“菌脑”控制所延伸出来的平行概念,有助于对上述过程进行理解。
由此可见,人脑在本质上是“符号记忆体”与“逻辑判断器”,通常从婴儿时期(半岁)开始受到环境中各种各样的信号刺激,如与父母的互动、自发爬行锻炼,一岁左右开始学习说话,三岁左右上幼儿园再到上学后开始学习各类知识,实际上都是在给“人脑”这个学习主体持续输入各种“符号”素材,表现为“学习和记忆”的过程,通过该“人脑”进行分析判断和逻辑推理等,以便形成该“人脑”对外界环境以及自身认识的综合记忆和思维判断,并通过思想、精神、意志、信仰等表现出来。
4 动机进化论分别包括被动的物质需求进化和主动的精神追求进化
不论是动物还是人类,摄食都被认为是一种本能活动,是天生就会的行为,而并非后天习得,然而惟有人类必须通过大量学习前人的知识,才能够不断地发展人类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因此,人类的学习行为不妨可以被理解为知识层面“主动进化”的表现。如果一个人不去主动学习科学技术文化知识的话,那么,思想和认知上就会停滞不前甚至退步,这是不言而喻的,而这一点在动物界是不存在的,因为动物幼崽只需要通过学习掌握捕食技巧、确保其能够在野外生存、不被饿死,保证该物种的正常繁衍、基因遗传即可。既然已知“饥饿源于菌群”,说明动物和人体的“被动摄食”行为很可能是被自然界通过“菌脑”或称“万有菌力”所控制的过程[30],即摄食能力并不一定需要人和动物自身去主动学习来获得,而是在出生后自然界将主导饥饿感与摄食行为的肠道菌群“主动接种”到人和动物的胃肠道,即可直接赋予人和动物的被动摄食能力(同时表现为宿主与共生微生物的协同进化),详细讨论可参考“菌心进化论”[8]。在通过这种被动摄食确保人和动物的肉体能够活存的基础上,“动物(层次的)大脑”仍然停留在相对固化的、基本的且关键的“行为世界”中,例如吃、喝、拉、撒、睡、交配和繁衍后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然而,只有“人类大脑(人脑) ”才能够通过主动学习、主动抽象、主动创造(符号逻辑),形成以语言文字等符号逻辑为载体和表征的人类文明历史。在此基础上,人类的摄食行为与繁衍后代等基本的生存活动只是人类(肉体)存在的基础和过程,却并非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后者则是人类不断地在自然界去发现、去创造新的知识和文明,从而形成了人类社会持续进步、源源不断的发展历程。
在这种面向“精神追求”谋求“主动进化”的“人脑(OS/3)”的驱动下,很显然人类后代将会比上一代发展得更好,这一点并不一定会表现在人类基因的层次上,这是因为OS/1是自然界经过数百万年时间的进化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遗传体系,而负责人类“摄食”记忆的OS/2则已经在地球上拥有长达36亿年的历史,更是非常稳定的遗传体系,因此人类的后代与上一代、甚至更早的时代相比,其进化应该说主要表现在“文化基因即OS/3”这样的层次。之所以把“文化基因”使用“人脑(OS/3)”来表征,这是因为前已述及,人脑记忆的对象以语言、文字、音像符号逻辑为主,通过这些符号的有序排列(类似于遗传物质DNA的有序排列)一样,代表了不同的含义,例如四书五经、《黄帝内经》、《物种起源》等,均可被认为是“文化基因”的表现形式与“遗传”方式。一本书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文化基因”,一段文字也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文化基因”片段。于是,古今中外,人类文明的历史不妨可被认为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丰富和充实着“OS/3”这个“文化基因”集合体。有价值的思想和知识体系,都会在以“OS/3”为代表的人类文明与文化的知识宝库中拥有一席之地,并作为后世传承文化和发展文明的基础。
据此,从“进化”角度反过来分析和判断“动机”的存在与发展特征,可认为分别包括“被动的物质需求”过程和“主动的精神追求”过程,前者在动物和人类均表现为由“菌脑”所驱动的饥饿与摄食等事关肉体存在的物质基础,该过程是由“菌脑”主动驱动、作为宿主的动物和人体被动应答而实现的,即在饥饿与摄食此类基本的、原始的物质需求方面,人和动物是被动(应答)的,而不是主动(追求)的。如果必须说摄食方面有“主动性”的话,那么其中的“主动性”则是源于“肠道菌群、菌脑、菌心”以生物化学反应方式在胃肠道中以破坏黏膜和分解肉体的方式向宿主传递饥饿感而驱动摄食的表现。此前由于未能发现和认识到这样的原理与过程,导致“菌脑”异常迫使人体过度摄食而导致肥胖并引发糖尿病、高血压等慢病,很可能是由于人们将“菌脑”对于以食物为代表的“物质需求”的“被动性”过程误认为“人脑”的“主动性”过程,从而过度“放纵”了“人脑”对于“菌脑”的合理约束和适当控制,从而表现为有一类人很容易被“菌脑”所主导的以食物为代表的“物质需求”所左右而表现为行为失控,例如贪吃甚至成瘾[18]。结合前述讨论,人类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就是人类能够通过“人脑”来实现对于“精神需求”的“主动追求”,那么通过使用正能量、真善美的“文化基因”来充实和丰富自己的头脑,并进而发展出新的人类精神文明,可以表现为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及社会科学的进步,尤其是哲学领域的认知升华。
由此可见,人们需要物质、需要食物,但是物质和食物并非是人类需求的全部,更重要的则在于内在的、内心深处的满足以及精神层面的追求、愉悦和幸福。在适当满足物质和食物需求的基础上,人类通过学习和思考,创造新的精神文明,表现为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美术与哲学等,是人类在满足物质需求之上更重要的事情。如果说自然界“创造”人类具有“私心”和“动机”的话,那么,不妨可以这样认为:自然界或许是在“善意地”期望人类通过自身的聪明才智和努力,让社会变得更健康、更美好、更幸福、更和平,而不是让人类陷入慢病的泥潭、战争的深渊和痛苦与灾难之中因“受罪”所引发严重的心理与精神问题。随着从“饥饿源于菌群”“(摄食)欲望源于菌群”到“慢病源于菌群”的认知发展与进步,通过改善“人菌关系”,确保“人菌言和”,人类与菌类和平共处,相信拥有智慧的人类摆脱慢病纠缠、进入身心健康的时代应该不会太遥远。惟其如此,才能够获得对于自然界进化出人类提供科学、合理的解释;否则,必将陷入到对于人类存在合理性的质疑与批判、乃至对于自然界本身存在合理性的质疑与批判的无休止争论之中,导致人们痛苦不已并难以自拔。
5 从达尔文进化论到菌心进化论再到动机进化论
自然界的发展过程符合“能量守恒,物质不灭”的客观逻辑。但地球围着太阳转、月球绕着地球转,这些貌似平淡无奇的重复过程,是否有意义呢?每当夜幕降临、人们仰望星空的时候,都会很容易在脑海中浮现出类似的问题和想法。且不说36亿年前的地球和现在的地球有什么区别,就以1万年之前的地球和今日的地球来看,斗转星移,日月乾坤,虽然地球上的生物换了一茬又一茬,人类也已经发展了若干代,从冷兵器时代、热兵器时代,经过核武器时代再到现在的信息化时代,也仍然符合“物质不灭”的逻辑。即便是今天和当下生活在地球上的70多亿人口,构成其身体的化学元素也还都只是地球上的那些化学元素而已,只不过在当下用于构成的人体元素,在1万年前可能是在土壤中、水里、动物身上或者细菌等微生物的元素而已,现如今只是在不同的肉体上以生物化学反应的方式进行循环往复,其中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在达尔文进化论中突出强调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谈的是生命领域的客观现象,因为事实上动物也只有通过“弱肉强食”这样的“丛林法则”,才能够生存下来,否则就会面临物种消亡的危险。然而,结合基于“饥饿源于菌群”的“菌心说”与“双脑论”(即“菌脑主吃、人脑主思”)来看,在达尔文进化论基础上提出“菌心进化论”[8],体现出“菌脑”通过向人和动物赋予“饥饿信号”而表现出对于与摄食行为的“绝对控制”,从而将以往深深地隐藏在达尔文进化论中关于动物对环境的被动适应以获得生存能力背后的“菌脑”控制因素即“万有菌力”揭示出来[30],而且其中充分体现了动物层次的“以食物为代表的物质需求进化源于肠道菌群繁殖后代的客观需求”,为人和动物以食物为代表的“物质需求”现象以及所表现出来的进化现象提供了科学合理的新解释。
“动机”与“意识”和“精神”密切相关,是动物和人类、尤其是人类所必须面对的问题。既然人类社会一直在发展,那么,人类的“动机”是否也在持续进化之中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即自然界虽然物质“不灭”,但是构成物质的化学元素却一直在通过生命体(微生物、藻类、植物、动物乃至人类)而反复循环。当进化到了人类、形成“人脑”之后,就能够表现出面向“精神追求”的“主动动机”。从基于人类大脑的“符号记忆体(OS/3)”的角度来看,就能够自然而然地通过人类的聪明才智而“加速进化”了,因为在当前的信息化、互联网、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人类科技高度发展的新时期,不再是以往的基于“物质不灭而生命循环”的慢速、低效循环模式,而是进入到借助于大数据、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时代的“符号逻辑”之“加速主动进化”模式了,其背后所隐藏的“动机”,当然应该是人们从内心深处和精神层面对于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与追求,这样就能够充分体现出从“物质进化”到“意识进化”乃至“精神进化”的自然逻辑,而且这样的“进化模式”充分体现了自然界利用物质体系(化学元素)、基于菌脑(OS/2)、通过宿主(人和动物的肉体即OS/1)、实现基于人脑(OS/3)经过意识向精神领域的新跃迁,从而总体上表现为人类从“物质文明”向“精神文明”的自然发展,代表了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必将迎来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大发展的美好时期。
6 动机进化论体现出自然界通过进化出人类实现对自然界自身的理解
如前所述,目前很难知道为什么地球上忽然有了生命并进化出人类,但是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两个需求,即肉体存在的物质需求与思想发展的精神追求,却贯穿了人类发展的全过程。以天灾人祸、慢病顽疾为例,此类事件使得人类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并不得不怀疑和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人类是因为痛苦而来?难道人类注定必将面临痛苦和灾难?人类究竟需要什么、需要到什么程度、为什么需要?人类应当怎样才能真正拥有健康、幸福、和平、美好的生活?结合近年来的系列来看,随着逐渐意识到“饥饿源于菌群”,即“菌脑”引导人们对于食物需求的“饥饿记忆”,而且可以通过靶向肠道菌群的柔性辟谷技术等进行合理控制,减少和消除源于异常“菌脑”的不良(客观)记忆,那么,人们在以食物为代表的物质需求方面的控制能力,显然可以通过现代生命科学技术的现实应用而得以科学、合理、安全、有效地控制,接下来应该就是“人脑”在“精神追求”方面重要性的体现了,具体包括文学、美术、舞蹈、表演等艺术以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方面。这些代表着人类文明历经数千年的发展与演化过程,实际上体现的是与人类物质文明并行的精神文明的大发展,只不过在“动机进化论”这一框架的理解下,变得更加重要和清晰起来。
由此可见,不妨可以这样认为,36亿年前地球上出现了微生物,随后进化发展出了植物、动物、人类,而后续出现和进化的生命体具有其自然而然的历史使命,尤其是号称“万物之灵”的人类,一方面兼备动物属性的生存需求,主要表现在“安身”方面。然而更重要的则是“立命”方面,即或许自然界进化出人类的“目的”和“动机”,是通过人类这样的高级智慧体,来理解自然界的发展过程和文明发展史,而这样的发展史,也只能由人类这样拥有高级智慧的生物来完成。通过音像和语言等符号逻辑的有序排列进行表征出来,并被人类所感知和理解,从而构成人类“精神世界”的集合体,其最终表现应该是艺术与科学、乃至于哲学体系。
因此,从无生命的物质到生命世界,再从无典型意识的微生物世界、植物世界到有意识然而表征能力有限的动物世界,乃至于进化到了具有充分意识与心理和精神表现能力的人类世界,从“达尔文进化论”到“菌心进化论”乃至“动机进化论”(或称意识进化论、精神进化论)。我们眼前的自然界就变得鲜活起来了,因为只有通过自然界创造出的人类,才能够实现其本身被人类所理解的自然界创造生命之美以及与之相伴的精神发展之美。惟其如此,作为不再仅仅只是停留在动物(属性)层面的人类,能够在满足基本生理需求的基础上,更加自由、自在、自然地追求精神之美,盛赞自然界(创造生命)之美。并且在赞美自然界的过程中,人类方能体验到前所未有的“获得感、幸福感、满足感、美好感”,其中体现了自然界的内在之美、尤其是只有通过人类,才能够体现到的创造之美、创新之美、自然之美与人性之美。至于与人体(和动物)共生的良好肠道菌群,当然也可以在不受人类发明、创造的抗生素的破坏,而是在人类对菌群的保护之下,能够“安居乐业”于人类胃肠道之中,伴随人类享受经口摄入的美食,供其自如地繁衍其后代,并一如既往、持之以恒、充满善意、并非敌意地向人体传递着摄食行为所必须的饥饿信号,从而构成了人体胃肠道之中的“肠道菌群的生命起源之美”。
7 结语
自然界的进化过程一直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发展,单纯的物质层次只是变化而不是进化,但是只有生命和意识以及精神层面的进化,才真正有意义和价值,尤其是就人类的进化而言,应该充分体现在精神层面进化的主动性、积极性、美好性等方面。当然,精神追求不能脱离物质需求,前者是主动的、主观的,后者则是客观的,同时后者还存在一定的主观性,然而本文讨论的重点则在于,在以食物代表的基本而又关键的物质需求方面,是“菌脑”而不是“人脑”在引导着人类的摄食需求即饥饿感产生的过程,而且已具备通过靶向肠道菌群消除人体饥饿感的生物技术,让人体能够优先使用库存糖原和库存脂肪提供能量,可协助人体暂时“放下”食物需求的纠结与困惑,避免人体成为食物的奴隶而导致意识失常和精神失控,从而让人体在身心健康两方面均获益。对于该事关人类生存、发展与健康重大问题的正确研判与解读,从“人菌共生、合作共赢”的“天人合一、和合思想”角度形成对于人体结构与功能的新认识,我们既能够“客观地”认识到人类肉体存在的“菌脑”与“菌心”对人体主动引导、人体被动应答框架下的食物等“物质需求”之源,同时又能够“客观地”认识到“人脑”所主动引导和追求的“精神之美”,有可能充分体现了自然界通过几十亿年的努力所进行的“从物质到意识、从思想到精神”的“动机”驱动下的持续进化过程。
所以,不妨可以这样说,从物质到生命,从低级到高级,从植物到动物,从动物到人类,自然界有可能是在最初貌似随机进化论(达尔文进化论)的过程中,在生命进化领域“万有菌力”和“菌心进化论”路径的约束下,最终发展出了人类这样的灵长类“高级动物”。一方面仍然通过继承动物之“菌脑”和“菌心”来记忆和约束人类摄食的物质需求之基本动机;另一方面则是能够让我们理解并且能够科学合理控制“菌脑”和“菌心”的基础上,彰显出人类对于“精神追求”这样的高级活动之“进化需求”,从而能够宏观地从生命起源与发展、乃至到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过程中,通过人类智慧与科技发展而推动知识进步,以语言音像等符号逻辑为载体和表现,体现出“动机进化论”这样的新逻辑,用来刻画、构建、理解和赞美我们人类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界,并形成下一步向着更加广袤的空间发展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新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