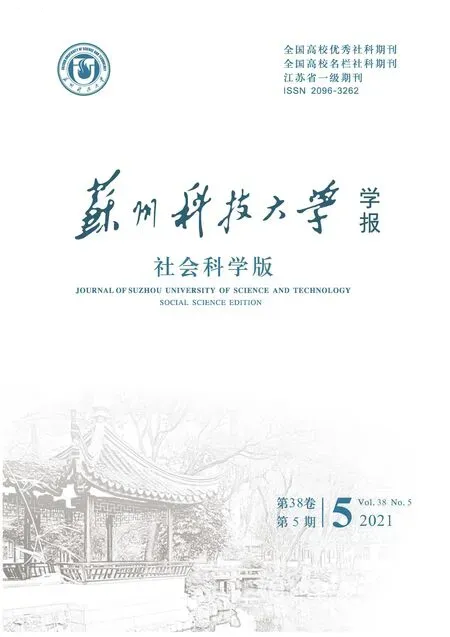况钟形象的历史变迁 *
周扬波,黄 越
(苏州科技大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明代官员况钟(1383—1443),江西靖安(今江西省靖安县)人,任苏州知府长达十三载,在任上减官租、理军籍、废杂税、捕兵痞、设济农仓等,以政声卓然垂名后世,至有“青天”之誉,与包拯、海瑞齐名。和后两者一样,一方面况钟得到的关注不可谓不多,另一方面其形象又颇为类型化。总体来说,依据当下的研究成果,况钟呈现出来的是一位清正、清明、清廉、清敏的典型清官形象。(1)目前关于况钟的学术论著主要有蒋星煜《况钟》,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廖志豪《况钟与周忱》,中华书局1982年版;王仲《况钟》,古吴轩出版社2003年版等。相关论文主要有:吴晗《况钟和周忱》,《人民文学》1960年第9期第76~81页;黄长椿《论清官况钟》,《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4期第70~75页;倪正太《明初的吏制改革和况钟的官声政绩》,《江西社会科学》1984年第6期第72~76页;谢天佑《况钟整顿苏州的官粮和吏治》,《江汉论坛》1988年第3期第47~52页;竺培升、吴建华《略论况钟的“兴利除弊”》,《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第61~74页;金军宽、王卫平《况钟治苏述论》,《史林》1989年第3期第20~23页;等等。诸论著对况钟政绩考订各有贡献,其中唯见蒋星煜《况钟》能注意对况钟史实和形象区别对待,但也未对其形象演变作历时性梳理。笔者基本认同已有研究成果对于况钟政绩的肯定,同时认为类型化形象不利于我们认知历史人物的丰富性,故通过梳理况钟形象的历史变迁,分明前期、明中后期、清代以后三个阶段进行考察,不虚美,不神化,力图深入历史情境观察历史人物。
一、明前期
况钟历仕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终于正统前期。本阶段重点考察况钟生前在士民心中的形象,兼及其卒后官方和民间的定论。
现存最早关于况钟的传记,是苏州乡宦张洪(1362—1445)作于宣德九年(1434)的《张太史赠太守况公前传》(以下简称《前传》),收录于况钟文集《况太守集》。《前传》作于况钟苏州知府任上第五年,由于并非盖棺定论而是为生人立传,故曰“前传”。《前传》使我们得以一窥苏州士绅对于时任太守的风评。篇首将况钟比为正史郡守立传之始的西汉循吏汲黯,“论事切直,不为软媚语”,“综理周密而不烦,行之甚易而不疏,可为为政之楷范”[1]55,勾勒出一位清正、清敏的清官形象。但前者的刚正之气,主要体现在况钟奏疏论事的言语,而非一般所谓的正邪之争。全文绝大多数篇幅落笔在况钟作为太守的善政,并描述了两次群鹤盘旋府治之异象,“观者以为和气所感”。文末则云“公为郡守而功绩章章如是,他日佐圣天子,为太平宰辅,事业广大”[1]55-59,期望况钟能够出守入相,体现了况钟最终连任苏州知府13年,未必全是因为当地士绅挽留,恐怕还有朝廷用人政策的通盘考虑。总体来说,《前传》呈现出来的况钟是一位清敏练达而兼具清正刚强之气的能吏形象。
况钟生前在民间即有“青天”之誉。正统四年(1439),况钟在夺情起复后再任苏州知府又满9年,将赴京调升他职,且继任人选业已确定,苏州士民饯别队伍长达百里,恳请况钟留下肖像以作纪念。况钟“不忍却其情”,留像并答诗一首,中有“敢劳父老,称曰青天”句。[1]164根据《前传》以及其他现存关于况钟生平的原始史料记载,况钟每次任满均有苏州士民长队惜别和盛情挽留,均出于对况钟惠民政绩的衷心爱戴。《前传》记载,宣德六年(1431)三月况钟因奔继母丧离任,苏州传唱一首民谣:“况太守,民父母,众怀思;因去后,愿复来,养田叟。”[1]57从“养田叟”之语看,百姓称誉仍着眼于况钟的抚郡吏干,而非一般“青天”意义上的清明和清廉。
《况太守集》收有杨士奇、杨溥、杨寿夫、周述、曾棨、周孟简、孙原贞7人为况钟所作像赞,主要呈现其清正一面,如杨士奇“刚正之气,卓特之才,其洁清之操一尘不染,其执守之固千夫莫回”[1]19、杨溥“刚毅之气,端肃之容”[1]19、周述“凛然廉厉之节,悠然清迥之思”[1]20、周孟简“既方其外,亦坦其中”[1]20、孙原贞“外方而直,内坦以夷”[1]21等语。这种不约而同的表述,一方面应有况钟事实上的清正之名为基础,另一方面显然还有像赞这一体裁既定的基调。每位作者均标明籍贯,7人除杨溥、杨寿夫外,其余均为江西人。明代是江西政治势力鼎盛期,而在“三杨”秉政的宣德、正统年间臻于极致,首辅杨士奇及永乐二年(1404)榜进士三鼎甲曾棨、周述、周孟简是该政治集团核心人物,而况钟及其上司江南巡抚周忱均属这一集团重要成员。[2]6-10关于像赞的写作时间,蒋星煜认为是正统七年(1442)为当年去世的况钟遗像而作,但从杨士奇“吴郡必古今而同心者与”[1]19、杨溥“宜乎晋阶增秩,而禄位功业之益隆也”[1]19、杨寿夫“巍乎庙堂之大器,自将入弼乎皇躬”[1]20、孙原贞“缙绅事业,遐寿为期”[1]21等语看,显然作于况钟生前。今苏州碑刻博物馆藏有《况钟像赞碑》,中镌况钟像,上刻杨士奇作像赞,下刻正统七年十月吴县儒学训导陈宾跋语:
东吴黎庶惧公之去,立石吴庠咏归亭,镌公之像,勒公之赞,以为邦人永久詹思,非谀也,宜也。然勒石一邑,而使四方之人徒闻公之名,而不得见公之像,孰若重刻广摹,传诸远迩,俾人人亲睹公之仪像,而为一代得人之贺,不其伟欤?[3]
像赞碑刻过两次,首次应是正统四年况钟离任留像之时,立石于吴县县学(蒋星煜误为“郡庠”(2)参见蒋星煜《况钟》,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2页。据《况太守集》道光二十八年(1848)胡容本跋(《况太守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7页),况钟像赞碑至清已移置府学况公祠内,碑左旧有庐陵杨少师赞,与今存杨士奇赞刻于碑上不同,且数处行文有异,应即正统四年初刻碑。且“碑阴有明正统元年七月十五日,耆民粮里秦孔彦等一万八百五十四人,为太守前传立石”,则立石先是为刻张洪《太守前传》,三年后复于另一面刻像赞碑,又三年后另立石重刻。),三年后陈宾作跋重刻并广摹拓本以期流传。况钟卒于是年十二月(见下引《明实录》),所以两次刻石均在况钟生前。杨士奇、杨溥等显宦作赞,应非苏州民众之力所能邀致,况钟本人参与其中亦有可能。像赞内容本多套话,此处则尚应考虑江西集团同声相应之造势因素。
民间认知的“青天”型官员,往往是决狱断刑明察秋毫的清明形象。况钟知苏州“到任九个月,问过轻重罪囚一千五百一十八名”[1]123,但今日所见《况太守集》并无一篇断案判词,不像海瑞《海忠介公文集》有多篇断案记录留存。所以,况钟在民间最为人熟知的断案如神之形象,反而最缺少史料支持。现存《况太守集》祖本,在况钟生前即由其次子况寰奉父命编定。[1]43可见,当时就未收录断案谳词,显然断案能力既非其本人也非时人关注焦点。至于清廉方面,况钟生前相关文献也鲜有涉及,仅有况钟本人在正统四年考满赴京作别耆民时口占诗句说:“清风两袖去朝天,不带江南一寸绵。”[1]163蒋星煜认为此语“从他自己的口中说出,显得完全以清官自居”,“并不是很妥当”[2]68。当然从另一个角度也不妨看作况钟对于自己廉洁操守的自信,但至少可以判定,况钟生前并不以清廉称著。
对况钟的盖棺定论,是礼部左侍郎王直(与况钟有“石交”之称的江西同乡)于正统八年(1443)为其所撰的墓志铭。墓志记载况钟的履历重点仍放在守苏十三载上,其云:
公慨然揽辔登车,勇于任事,纠官慝,惩吏(邪,纤弊必剔,积困必苏,前后为斯民请命,如减额除荒诸大政,抗疏至数十上,戆直无讳,而上)嘉纳之……(民)称之为青天、为父母。[4]
减削税粮是况钟苏州任上最为卓著的政绩,况钟的确为此屡上奏疏,积极为民请命。但蒋星煜辨析况钟抗疏对象主要是户部而非宣宗,其赴苏本身即带着宣宗“察其休戚,均其徭役”的敕书,具体执行也得到了宣宗全程支持。[2]25、34-39墓志“戆直无讳,而上嘉纳之”的用笔,则塑造了臣正君明的相得之状。墓志续称:
(公始受知于邑令俞益),早以孙伏伽、张元素期之。逮典郡政成,群以龚黄(颂之。晋秩而留任,杨相国致诗,则以赵清献、张益州方之。要皆为公实录,而非出于过誉)。[4]
况钟初被靖安县令俞益以同样吏员出身的唐代显宦孙伏伽、张玄素相期许,至苏州又被士民颂为堪比西汉循吏龚遂、黄霸,晋秩留任时杨士奇赠诗又以北宋出守入相的赵抃、张方平相拟。显然仕途前景是节节拔高,吏员出身已不重要,抚郡循吏也不足以比拟,贵至卿相才是未来可期。不过王直本人在况钟晋秩留任时也写了篇《送况太守序》,其中仅将况钟比拟为“汉世循吏于郡守最称”的黄霸。[5]所以,墓志的这种排比层次本身并没那么严谨。总体来说,墓志呈现的况钟是一名清正练达的循吏,君臣相得而具卿相之才,也是民众心目中的“青天”。
目前能看到对况钟最早的官方评价是《明实录》卷九九“英宗正统七年十二月”条,与上述评价既有契合之处,又有较大反差。该条在陈述况钟当月去世及其生平后评述:
钟有治剧才,故郡事虽殷,理之绰有余裕。惜其贪虐,犹有刀笔余习。一时与钟同奉玺书为郡者,若松江知府赵豫、常州知府莫愚、杭州知府马仪、吉安知府陈本深、西安知府罗以礼辈,往往能兴利除害,其得民心大率与钟伯仲间。豫尤和易近民,凡百词讼,属老人之公正者剖断,有忿争不已者,则己为之和解,故民以“老人”目之。当时论者以钟为能吏,豫为良吏云。[6]
“贪虐”之“贪”,应是指宣德七年(1432)江南巡抚成均诉况钟托同乡代购入官私盐船、买木料未付费若干事。蒋星煜已据况钟《遵旨辨明诬陷奏》辨明,除况钟买船一事不够检点外,其他皆属捏造,交讼另一方成均在《明实录》中的评价是“持身清谨,明于大体”,双方仅是工作矛盾,无关道德大节,宣宗也未对双方进行处分,二人继续共事多年而无新摩擦。[2]46-52至于“虐”,此处虽未明言,但后世有不同史源的史料多处言及,结合况钟的吏员出身,溯源于“刀笔余习”应可成立,具体置于下节再论。与况钟同批派到大郡任太守的赵豫、莫愚、马仪、陈本深、罗以礼,均因深得民心而反复延任,其中赵豫守松江、陈本深守吉安均达18年之久。可见,况钟守苏13年虽属难得,但非特例。《明实录》同批奉敕者“得民心大率与钟伯仲间”,应属公允。尤其在断案方面,松江知府赵豫更为和易亲民,故被誉为“良吏”,而况钟仅得“能吏”之名,这是官方文献对况钟最早的盖棺之论。
在明前期的文献中,况钟已有“青天”之誉,但主要是清敏干练的能吏形象。在像赞、墓志这样一贯正面的文体中,还比较强调清正,但清官常见的清廉、清明两项要素此时若有似无,且存在“贪虐”这样的负面评价,与后世“高大全”的形象存在较大距离。
二、明中后期
明中后期,况钟开始走进小说、笔记、方志、史籍等文献,多种记载之间还存在一些分歧,从而使得呈现出来的形象更为多元。
这一时期,况钟形象的最大发展是“况青天”形象诞生于坊间小说,可谓清代戏曲《十五贯》塑造的经典“青天”形象之雏形,极大地提高了况钟在民间的知名度。成书于天启四年(1624)的著名白话小说《警世通言》第三十五卷名为《况太守断死孩儿》,叙述夺情复任的苏州太守况钟在途经扬州仪真县时,审理一个市井无赖为谋财色致死二命案。[7]534-545小说称况钟吏员出身,由礼部尚书胡潆荐为苏州太守,在任官声以及夺情复任事均与史实相合。蒋星煜认为断案判词也与况钟传世文章有近似之处,推断小说可能有所依据,并指出清代苏州状元石韫玉说况钟“折狱明冤,惇史标其清节,稗官摭其轶闻”的“稗官”即指此篇,判断具备一定的合理性。[2]102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称况钟“在任一年,百姓呼为‘况青天’”[7]542,断案后“万民传颂,以为包龙图复出,不是过也”[7]545,首次确立了况钟在民间文艺作品中的“青天”形象。《警世通言》纂辑者冯梦龙(1574—1646)也是苏州人,其表述应有地域口碑作为渊源。不过,同由冯梦龙编纂的《醒世恒言》,依据宋元话本《错斩崔宁》编有一卷《十五贯戏言成巧祸》,虽是清代戏曲《十五贯》的前身,但故事设定在南宋临安,尚未与况钟发生联系。[8]
前述况钟自述被百姓称为“青天”,许是苏州名士都穆(1458—1525)《都公谭纂》所载民谣所称。该书称况钟去官之时苏州传唱二首民谣,一曰“况青天,朝命宣,宜早还”,一曰“况太守,民父母,愿复来,养田叟”。[9]后者与前述张洪《前传》略同而稍简,前者亦应有一定真实性。
况钟的清正形象在这一时期也有了较大发展。苏州人杨循吉(1456—1544)所作苏州掌故集《吴中故语》录有“况侯抑中官”条,专载况钟在苏打击宦官气焰之事:
时承平岁久,中使时出四方,络绎不绝,采宝干办之类,名色甚多。如苏州一处,恒有五六人居焉。曰来内官、罗太监尤久,或织造,或采促织,或买禽鸟花木,皆倚以剥,民祈求无艺。郡佐、县正少忤,则加捶挞,虽太守亦时诃责不贷也。其他经过内宦尤横,至缚同知卧于驿边水次,鞭笞他官,动至五六十,以为常矣。
会知府缺,杨文贞公以公荐,而知苏州有内官难治,乃请赐敕书以行。文贞难其事,不敢直言,乃以数毋字假之以柄。下车之日,首谒一势阉于驿,拜下不答,敛揖起云:“老太监固不喜拜,且长揖。”既乃就坐,与之抗论。毕出,麾僚属先上马入城,而已御轿押其后。由是,内官至苏皆不得挞郡县之吏矣。
来内官以事杖吴县主簿吴清。况闻之,径往,执其两手,怒数曰:“汝何得打吾主簿?县中不要办事,只干汝一头事乎?”来惧,谢为设食而止。于是终况公之时十余年间,未尝罹内官之患也。[10]
该书呈现的况钟是与为害地方的宦官势不两立的清正形象,应有一定的史实依据。但况钟是否与宦官势同水火,尚需全面考察。蒋星煜《况钟》一书辟专节考察了况钟与宦官的关系,推断况钟在礼部仪制司任内与宦官多有共事,结合况钟借坐来内官轿、科派属县款待过境钦差太监、采办促织以及其同乡上司江南巡抚周忱与宦官的友好关系,判断况钟与宦官之间不可能存在激烈斗争,宦官气焰的收敛更多是因为况钟的合作所致,很有见地。[2]84-86其中关于采办促织一事尚可补充,蒋星煜主要依据《况太守集》所载宣德九年(1434)《遵旨采解物件奏》,而此期沈德符(1578—1642)《万历野获编》尚有更为翔实的记载:
我朝宣宗最娴此戏,曾密诏苏州知府况钟进千个,一时语云:“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此语至今犹传。苏州卫中武弁闻尚有以捕蟋蟀比首虏功,得世职者。今宣窑蟋蟀盆甚珍重,其价不减宣和盆也。近日吴越浪子,有酷好此戏,每赌胜负,辄数百金,至有破家者,亦贾之流毒也。[11]524
《万历野获编》“堪称有明一朝百科大全,向为治史者所倚重”[11]1,记载可信度较高。今检况钟《况太守集》所载《遵旨采解物件奏》,说宣德九年七月十七日奉敕协同内官安儿、吉祥采办促织一千个,而上奏采办完备的落款是七月二十六日,九天内即采办毕千只蟋蟀,可见况钟态度之积极。[1]104两相印证,沈德符记载应可坐实。而促织采办流毒,其中只提到宣德年武将比功得官和万历年浪子赌博破家,这方面明末苏州人吕毖《明朝小史》可做补充:
帝(宣宗)酷好促织之戏,遣取之江南,其价腾贵至十数金。时枫桥一粮长,以郡督遣,觅得其最良者,用所乘骏马易之。妻妾以为骏马易虫,必异,窃视之,乃跃去。妻惧,自经死。夫归,伤其妻,且畏法,亦经焉。[12]
从这一粮长的家破人亡可见当时促织采办之峻急。另有清人曹寿铭称所见宣德八年(1433)八月初二敕云:“敕奉御刘安儿、知府莫愚、况钟等今年闰八月节候稍迟,尔等再取一千个两运送京。”[13]则宣德九年(1434)前况钟与同批奉敕能吏常州知府莫愚已反复贡送千只蟋蟀,恐怕当时地方官迎合采办是常态。当然,明代宦官为祸之烈主要在中后期,况钟生活时代尚处萌芽之期,宦官与地方矛盾尚未成为主要矛盾,通过合作缓和紧张关系不失为一项可行手段,但对于宦官采办之扰民,况钟依然需要担负一定责任。
《万历野获编》还对“今人传说”况钟奉敕便宜行事的“异典”作了辨析,认为“其说诚是”,但同时奉敕者有9人,其中温州知府何文渊之后还官至吏部尚书,且敕书授权也不像所传“凡其同僚皆得拿问”,只云“具实奏闻”和“提解来京”。该书记载,况钟因轻信“本府经历傅得”谤言,将吴县县丞赵浚“起送至京”,结果“其民千八百余人诉于巡抚侍郎成均周忱,言浚守法奉公、爱民集事俱善状”,经巡按核查,“果如民言,命浚复职,置得于法”。[11]481都察院请治钟妄奏之罪,宣宗仅对况钟“记其过”并“戒钟加慎”。沈德符最终评论说:“然则钟固一轻听躁动人也。吴人以其异途健吏,能抑豪强,一时誉之过情,流传至今不衰耳。”[11]482况钟苏州任上断案过千,仅因一件冤案即判断其“轻听躁动”,未免苛责。但沈德符所言况钟清名源于“异途健吏,能抑豪强”,有一定合理性。况钟在苏诸项政绩,固然是其过人吏干所致,但一方面他是带着敕书给予的特权和任务至苏,背后尚有首辅杨士奇、江南巡抚周忱等江西显宦大力支持;另一方面况钟主要致力于抑制地方势力和处理辖区问题,他与采办宦官、清军御史、监察御史等的斗争均应置于这个范围理解。除初期与江南巡抚成均因公务矛盾短暂交讼外,况钟对上并不存在也无必要有太强的斗争性。
关于况钟如何“抑豪强”,明中叶苏州人刘昌《悬笥琐探》载,况钟“至苏,廉察官吏,去太甚者四五人,严禁狡猾而惠爱穷弱,执势家侈恣不法者,立杖杀之。吏民大惊,奉令唯谨”[14]。而对于抑制其中的胥吏群体,陈建(1497—1567)《皇明通纪》有更翔实的记载:
钟初视事,为木讷。胥持文书上,不问当否,便判可,其弊蠹辄默识之。通判赵忱肆慢侮钟,亦唯唯不校。既期月,一旦,命左右具香烛案,并呼礼生至诸僚属以下亦集。钟言:“某有朝廷敕未尝宣,今日宣敕。”既宣,中有“僚属不法,径自拿问”之语,于是诸吏皆惊。礼毕,坐堂上,唤里老,言:“吾闻郡人多狡武,每轻诬善人。吾有彰瘅之术,然不能如阎罗老子,自为剖别。今以属等,速以善户恶户报来。善者吾优视之,甚则宾致乡饮;恶者吾且为百姓杀之。吾列善恶二簿,俟若曹矣。”又召府中胥悉前,大声言:“某日某事,你某作如此拟,应窃贿若干,然乎某日某如之。”群胥骇服,不敢辨。钟命引出,曰:“吾不能多耐烦。”命裸之,俾皂隶有膂力者四人舆一胥,掷空中扌颠死之。皂姑少投去,钟大怒曰:“吾为百姓杀贼,独鼠辈为吾树虐威耳?高投之,立死。不死,死若狗曹。”皂惧,如命,立毙六人。命屠人钩其发曳出,肆诸市。复黜属官贪暴者五人,慵懦者十余人。由是,吏民震栗革心,奉命惟谨,苏人称之曰“况青天”。[15]
核查《况太守集》所载赴任敕书,并无“僚属不法,径自拿问”之语,只云“凡公差官员人等,有违法害民者,即具实奏闻。所属官员人等,或作奸害民,尔即提下差人解京”[1]61。前述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亦对此专做分辨。所以,《皇明通纪》此条记载恐怕与史实有出入,但该书作为有明一代史学名著,取材谨慎而描述细致入微,其他史料相关记载亦无异词而仅详略有异,应有史实基础。知府并无专杀之权,况钟投死胥吏和杖杀势家显属逾权,此应即《明实录》“虐”字之评的根据,尤其将胥吏裸身投死和钩发示众之举实属暴行,“刀笔余习”之讥不虚。但与《明实录》“惜其贪虐”的批判态度相比,此期的《皇明通纪》和《悬笥琐探》在陈述况钟专杀时,均以正面首肯的态度刻画,呈现出况钟锄强扶弱的清正形象。
综上所述,明中后期一方面况钟正面形象更为放大,另一方面仍不时可见一些负面评价;但总体来说后一方面趋于淡化,代之而起的是况钟形象中清正、清明两个维度的增强。
三、清代以后
入清以后,况钟形象于前代基础之上,无论是在官方还是在民间,均又有显著提升,最终成为国史上著名的清官之一。
清代官修的《明史》,代表了官方对况钟的基本评价。《明史·况钟传》对况钟的结语是“钟刚正廉洁,孜孜爱民,前后守苏者莫能及”。开篇提到宣宗对于况钟等同批受敕9位人选的考虑时,表述是“命部院臣举其属之廉能者补之”。但全篇对况钟之廉实无只字涉及,主要篇幅在于通过陈述其政绩表彰其吏能,并在刚正这一维度较前代史料有所拔高。上任杀吏一事,删去血腥细节,仅简述为“立捶杀数人”。在况钟置善恶簿、通关勘合簿、纲运簿后,总结为“锄豪强,植良善,民奉之若神”。对宦官采办扰乱地方之事,则记述为“钟在,敛迹不敢肆”。而关于况钟的吏员出身,则言“钟虽起刀笔,然重学校,礼文儒”。[16]4381总体来说,《明史·况钟传》的况钟形象已较《明实录》有了全面提升,且相对于《皇明通纪》也因有所剪裁而淡化了“刀笔余习”的酷虐色彩,从而呈现出一位清敏、清正兼清廉的清官形象。不过,《明史》将况钟与同批奉敕者陈本深、罗以礼、莫愚,以及其他贤守如李昌祺、张昺等并列一卷,在卷末赞语云:“李昌祺、陈本深之属,静以爱民;况钟、张昺,能于其职。所谓承宣德化,为天子分忧者。”[16]4395
显然,况钟仍以吏能称著,与陈本深等“静以爱民”的治理风格有别。而且,同批奉敕9人仅赵豫一人入选《循吏传》,说明编撰《明史》的史臣仍未以“循吏”之格许况钟。入清以后,有关况钟的文献和遗迹得到全面整理和增修,其力度为前明所未有,背后推动的主力是苏州地方官员。
况钟一生所著奏疏、榜谕,在生前嘱其次子况寰汇辑成《忠贞录》八卷,由张洪题名;其手订谱帙及诗文,汇编为《文献集》;另有缙绅投赠诸作,汇编为《传芳集》。[1]43但这些文献的保存状况不佳,至清初多数已缺失。乾隆年间,况钟九世孙廷秀在三集残卷基础上,编撰列传冠于篇首。廷秀重外甥岳士景又访得苏州先儒编刻的况钟事迹汇编《膏雨集》及轶事若干,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在廷秀纂本基础上汇辑刊刻[1]2,即今存《况太守集》祖本。由于该书仅以家集的形式刊行而流传不广,清中叶官方力量的参与才使文集得以重刊传世。道光六年(1826),太仓州同陈鸿庆访况钟裔孙霞所藏家集刊本而未得,复于苏州士人董国琛处访得该刊本之抄本,在此基础上将《明史·况钟传》《辟疆馆记》《修祠碑记》及同人记载、题咏等另编一卷附后,刊刻以广流传。道光二十八年(1848),苏州府照磨胡容本在修葺况钟祠时得到该刊本,经校勘改订,增建附卷篇目后更名为《补遗》,再次刊行。这便是今日所见《况太守集》规模,其中况钟本人作品仅占不到半数,敕书、诰命、传记、年谱、同人题咏、轶事等占了更多篇幅。
和况钟文集一样,况钟祠的修建和增补主要也由清代地方官员推动。况钟祠的第一个修建高峰是明代,“七邑及市镇皆建祠”[1]12,但能确定官方所建的仅有附祀于郡学之祠。而且,况钟祠总体维护情况不佳,至清初均已圮毁,连郡学之祠亦“惟石刻遗像埋没于荆榛瓦砾间”。康熙四十八年(1709),江苏巡抚于准大修府学,具体负责的苏州知府陈鹏年顺势于故址重建况公祠。[1]178陈鹏年将偶然所得、传为三国东吴廉吏陆绩“廉石”移置况公祠,与郡学另一厢韦应物祠前“端石”相对,强化了况钟的廉吏形象。[1]180道光六年,经太仓州同陈鸿庆、江都知县陈文述兄弟首倡,包括苏州知府额腾伊、吴县知县万台等属县长官数度捐钱,在苏州西美巷落成况钟专祠,即今存况钟祠。该祠在府治东隅,明代为五显庙。况钟曾三祷五显王而旱潦皆应,故在正统三年(1438)请于朝而修葺旧庙。当年冬,况钟丁母忧而复夺情视事,即选择以庙南偏为居庐守丧,三年终制后,将此馆作为公余休憩之地,幕僚谭有章为题额曰“辟疆馆”。之所以取此馆名,是因为况钟修庙甃井时得断石有“辟疆东晋”四字。经其友蹇叔真考证,其地当为东晋名园顾氏辟疆园,唐代又为诗人顾况宅。[1]174不过到了康熙二十五年(1686),江苏巡抚汤斌禁毁淫祀,焚毁五通庙。道光六年(1826)陈氏兄弟倡议在此地建况钟专祠也遇到质疑,陈文述之子陈裴之说:“况公之兴祠也,为民迓福;汤公之废祠也,为民除患。救时之政,势若异趋;爱民之心,理无二致。”又说:“汤公既毁楞迦山之五通庙以祀关帝,复毁颜家场之五显庙以祀复圣。今以此祠专祀况公,此宋潘凯所谓崇正黜非,当亦汤公未竟之志欤?”[1]16由此,可谓非常巧妙地理顺了所有关系。而之前陈文述早已将友人王良士所藏况钟《辟疆馆记》碑石移入,该碑被苏州金石名家王芑孙辨为伪作,几乎被太守五泰所毁,被陈文述以“记石可伪,而庙碑、题梁不可伪”和“地以人重”之由保存下来。《辟疆馆记》主要体现的是况钟忠孝两全及公余清趣,有“爱此馆青葱蓊蔼,竹木明瑟,为簿书萧闲地。或宾客论政事,亦时为小诗”[1]174之语。况钟已然是一名典型的儒道互补之士大夫形象。
况钟形象在清代的更大提升是在民间。采办促织一事,是清初蒲松龄《聊斋志异》名篇《促织》的本事,但事件地点转换成陕西华阴,也未出现况钟。[17]而使得“况青天”形象家喻户晓的戏曲《十五贯》正是出现在此期。清初苏州派戏曲家朱素臣创作的这部名作亦名《双熊梦》,采用双线结构,写况钟在双熊衔鼠入梦的启示下,平反熊友兰与苏戍娟、熊友蕙与侯三姑两桩冤案的经过。[18]关于“十五贯”事件的真实性,论者多据《况太守集》“凡例”的“如熊友兰兄弟之事,非籍传奇曷由考见其大略哉”及《太守列传编年》“有熊友兰、熊友蕙兄弟冤狱,公为雪之,阖郡有包龙图之颂”二句,推断属实,但这两篇均为况钟九世孙廷秀编家集时所纂。蒋星煜已指出其作为晚出史料并未提供佐证。他还注意到,清代《拍案惊异》中《前明苏州案卷》及范烟桥《况公祠与“十五贯”档案》所载清末苏州有人以《十五贯》案卷牟利事,因此难以绝对排除况钟断“十五贯”案的可能性,转而又从剧中周忱形象、无锡与苏州关系及明代物价三方面质疑其真实性。其实从史源角度看,《拍案惊异》及《况公祠与“十五贯”档案》所提供的仍是隔代史料,而从宋元话本《错斩崔宁》、明末小说《醒世恒言》之《十五贯戏言成巧祸》、清初戏曲《十五贯》这一传承序列,明显可见将南宋崔宁故事嫁接到明代的痕迹,况钟断“十五贯”案的可能性可以排除。
1956年,根据朱素臣《双熊梦》改编的昆曲《十五贯》,将原双线结构改为更加简明的熊友兰、苏戍娟案单线形式,并突出了况钟重视调查以免冤杀的精神,这是“改编古典剧本中体现‘百花齐放’方针,在思想性与艺术性上获得卓越成功的典型”[19]。演出获得巨大成功,本已乏人问津的传统剧种昆曲也因此恢复活力,获得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被周恩来总理誉为“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20]。1960年9月,明史专家、时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吴晗发表《况钟和周忱》一文,继前一年《海瑞骂皇帝》《论海瑞》二文后进一步阐扬清官精神。该文从风头正劲的昆曲《十五贯》说起,也从史学专家角度指出《十五贯》故事其实和况钟并不相干。但正是因为况钟“一方面符合人民对于清官好官的迫切要求,一方面也反映了一定时期的历史情况”,《十五贯》与况钟的结合“是完全可以允许的艺术处理”。他指出,“宋朝的包拯,明朝的况钟和海瑞”是“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几个青天”,他们因为符合人民期待,所以成为“许多人民理想中的好事都被堆砌到他们身上”的“箭垛式的人物”[21]。这便是今日常见的况钟与包拯、海瑞并列“三大青天”之说的来源。吴晗作此文时逢“三年困难时期”,该文体现了吴晗寄托其中的政治理想——官吏清廉、政通人和。学者刘光永认为,身兼明史专家和政府高官的吴晗,对况钟、海瑞进行系列研究,是因为他具有浓郁的清官崇拜意识,将社会繁荣昌盛的希望寄托于清官这一传统社会特殊产物,最终导致一己人生悲喜剧,值得反复品咂。[22]
四、结 语
通过以上梳理可知,“青天况钟”是在历史上真实的况钟其人基础上,由历代大传统和小传统合力塑造而成的理想官员典范。这是一笔需要辩证对待的历史文化遗产,应拒绝抽离历史条件而无限拔高,理解况钟政声产生的环境氛围,为今天培育优质治理环境提供借鉴。况钟施展长才主要在明初宣德、正统年间,时值国势日上的明王朝开创期,尤其“仁宣之治”是明代较为难得的开明时期,注重整顿吏治舒缓民力。况钟带着宣宗指导性的敕书莅任苏州,着手整顿污吏、为民制产,并在宣宗皇帝、内阁首辅杨士奇、江南巡抚周忱、苏州僚属的合力支持下,勇于发现、面对和解决问题,和同批奉敕知府一道出色地完成了使命,方始成就“青天”之名。况钟生前以吏干称著,兼有清正之声,但亦有“刀笔余习”之讥评。明中叶之后,况钟形象的负面色彩日益淡化,在官方和民间,“况青天”形象均越来越高大,逐渐成为清正、清明、清廉、清敏四大要素兼备的清官典范,与包拯、海瑞并列古代“三大青天”。需要正视的是,中国古代对少数“青天”形成的清官崇拜,根源是民众在政治上力量微弱,并具有强化民众自卑自弱意识的作用。所以,王子今斥之为“清官迷信”,认为“所谓‘清官’在封建政体的浩荡浊流中绝对无力扭转专横腐恶的大趋势,……也绝不可能超越封建法统给予民众更多的政治权利。……许多事迹难免有虚美增饰的成分”,最终产生“对合理的政治权利的自我放弃”的“致幻作用”。[23]另外,民众通过为清官附增道德品质而导致的形象美化,还容易丧失对其实施公权力的监督和警惕。汉学家白鲁恂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最大的特色与核心是“道德权威”(Moral Force),道德是中国统治者的必备条件和统治能力的检验标准,伦理品质于是成为统治者的权威来源。[24]况钟形象在明清以来被历时性地附增许多美善的道德品质,正是这种政治文化的体现。但这种随着道德附加值提升的权威与权力存在滥施而免责的危险,正如法学研究者对包公故事研究所揭示的,清官往往施刑残酷,著名清官包拯和海瑞均可归入酷吏行列,而酷吏也多有清廉公正者,“清官与酷吏既不完全相同,也不绝然对立,而是一种交叉的关系;命名之差异,只是为了突出各自的特征而已”[25]417-418。原因在于,“民众赋予包公‘神性’的秉持,也是赋予包公‘永远正确’的超凡智力和能力;由此,独裁决罚也就理所当然”[25]389。况钟“刀笔习气”之酷虐在历史语境下的淡化,由此也可得到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