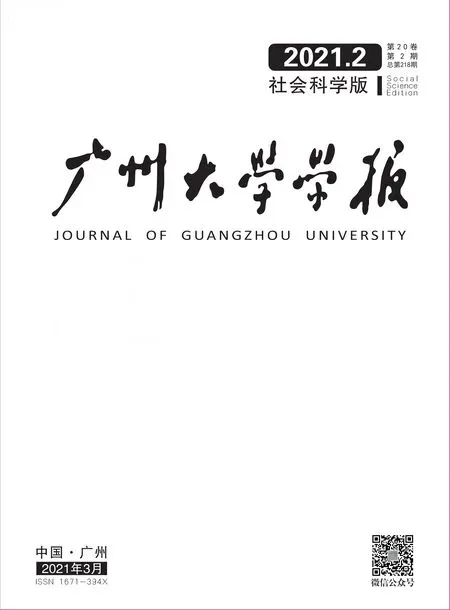为何说《伤逝》是哀悼兄弟恩情的小说
商昌宝
(天津 西青区学者公寓,天津 300384)
《伤逝》常常被阐释、被定性为鲁迅唯一的爱情小说,而且几乎已经作为学术共识和文学常识深入人心,但是这样的解读符合小说的主题或者说鲁迅创作的初衷吗?
一
《伤逝》被标签化为爱情小说,显然跟众多研究者和文学史教科书有关。比如在最新修订出版的、发行量已超过100万册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钱理群教授在其执笔的鲁迅专章中这样写道:“‘五四’时期勇敢地冲出旧家庭的青年男女,眼光局限于小家庭凝固的安宁与幸福,既无力抵御社会经济的压力,爱情也失去附丽,只能又回到旧家庭中。”[1]36
再来看发行量同样巨大的由朱栋霖教授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5—2016)》,执笔人朱晓进和汪卫东教授这样写道:“《伤逝》以‘涓生的手记’的形式,通过带有忏悔情调的独白,讲述涓生与子君的爱情悲剧。”[2]52在探讨小说的“恋爱悲剧成因”的主观原因时,两位教授接着写道:“这对五四时期勇敢地冲出旧家庭的青年男女,由于他们把争取恋爱自由看作人生奋斗的终极目标,眼光局限于小家庭凝固的安宁与幸福,缺乏高远的社会理想来支撑他们的新生活,所以他们既无力抵御社会经济的压力,爱情也失去附丽。”[2]52
不同的文学史教材、不同的文学研究者,不但对爱情主题的解读一致,而且在语言表达上都惊人地趋同和相似,相关研究的同质化和雷同化情形由此可见一斑。
作为早已经声名远扬的鲁迅研究专家,钱理群教授自然不会将目光仅仅停留在小说的表面,于是他又将解读空间拓展了一下:“小说的重心可能不在那失败了的爱情本身,而在于涓生明确意识到与子君之间只剩下无爱的婚姻‘以后’,他所面临的两难选择;‘不说’出爱情已不存在的真相,即是‘安于虚伪’;‘说’出,则意味着‘将真实的重担’卸给对方,而且难以逃脱犯罪感的两难,正是终身折磨着鲁迅的人生困境之一。”[1]41钱理群教授这样的解读,虽具有主题深化的意义,却使用了模糊的词汇“可能”,让人有些遗憾。更遗憾的是,他笔锋一转,来了一句“正是终身折磨着鲁迅的人生困境之一”,实在有些让人如坠雾里,或者说是牵强附会也不过分。
朱晓进、汪卫东两位教授大概也觉得单纯的爱情解读不足,于是接着说:“《伤逝》,似乎也是鲁迅在做出个人生活的重大抉择时,对未来结果的一种悲观预测,更是自我总结和自我清算。在做出最悲观的预测后,作者也开始与旧我告别。”[2]53这句看上去很高端的评论,不但使用了“似乎也是”这样的语句,而且不指明具体是什么“生活的重大抉择”,“悲观预测”又是指什么,大有一种不说还明白越说越糊涂的感觉。更为不解的是,文下的注释中有这样一句:“有学者提出,《伤逝》中,鲁迅借助复杂的‘隐含作者’,指向了一个极为隐深的自我反思层面。”[2]53这话到底在说什么呢?“极为隐深的自我反思层面”具体所指又是什么?
关于《伤逝》,作家莫言在跟孙郁教授对话时说:“……《伤逝》是关注自我的,是审视自己的内心的,有那么点拷问灵魂的意思了。这样的小说,太过沉痛,非有同样的大悲大痛,难以尽解。”[3]作为作家,莫言这样比较抽象的解读,在学理层面上很难再进行解释,因为其中的随意性和一家之言也只能说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正如同是作家的曹文轩教授在谈创作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既然无法去作清晰的解读,那么索性给出一个模糊,然后让读者在模糊中去体味。……模糊并不等于让你手足无措,一无所获。模糊的能耐恰恰在于给了你不能以数目来代表的不确切的但是却是丰富的感觉。正是因为模糊具有无边性,于是使你获得了感觉的无边性。”[4]但是教授、学者跟作家不同,作家可以抽象、模糊,而教授、学者进行学理阐释和论证才是其本职工作。
也不止是以上三位教授将《伤逝》看成爱情小说,《彷徨》小说集1926年出版时,当时的评论者李荐侬就在专论《读〈伤逝〉的共鸣》中写道:“纯洁的爱情每每就为了这‘面包问题’发生了变化,这是多么令人伤感而悲哀!”[5]文末他还写道:“他(指鲁迅——本文注)是不谈爱情了的先生,然而他看到人们走错了路,他又不得不略略一说。这就是《伤逝》。”[5]再翻翻当年期刊、杂志中登载的其他关于《伤逝》的评论文章,大体也离不开爱情论。[6]李长之甚至在《鲁迅批判》中称《伤逝》为“鲁迅最成功的一篇恋爱小说,其中对于女性最深切的了解,……可以代表鲁迅的一切抒情的制作”[7]。
二
《伤逝》被视为爱情小说由来已久。可是,为什么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先在1958年1月给曹聚仁的信中写道:“‘彷徨’中的‘弟兄’前面有一篇‘伤逝’,作意不易明了,说是借了失恋说人生固然也可以,我因了所说背景是公馆这一‘孤证’,猜想是在伤悼弟兄的伤失。这猜想基础不固,在‘小说里的人物’中未敢提出,但对先生私下不妨一说,不知尊见以为有一二分可取否?我的这些私见,藏着无用,虽然也无公表之意,故以奉阅。”[8]之后又在回忆录中十分有把握地写道:“《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这样说,或者世人都要以我为妄吧。但是我有我的感觉,深信这是不大会错的。因为我以不知为不知,声明自己不懂文学,不敢插嘴来批评,但对于鲁迅写作这些小说的动机,却是能够懂得。”[9]536
周作人将《伤逝》主题说成是“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给出的理由除此前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中谈及的“会馆”场景描写乃是鲁迅在北京住过绍兴会馆之“补树书屋”外,再有就是他说的“如果把这和《弟兄》合起来看时,后者有十分之九以上是‘真实’”[9]535,确实如他所说“基础不固”。众多研究者将关注点放在周作人在《京报副刊》发表诗歌译作《伤逝》,因为之后第九天,鲁迅创作完成了小说《伤逝》,再后11月3日写成《弟兄》,然后据此说这是对弟弟在译诗《伤逝》中写下的“我造了古旧的遗风,将这些悲哀的祭品,来陈列在你的墓上:兄弟你收了这些东西吧,都浸透了我的眼泪,从此永隔冥明,兄弟只嘱咐你一声‘珍重’”[10]等诗句的回应。这样的对接是否有道理,在没有足够证据前,是不能轻易得出结论的。
对于周作人的解读,相信写作过《周作人传》《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讲》《话说周氏兄弟》《周作人论》的钱理群教授,以及北大出身的朱晓进、汪卫东教授都不会陌生,当然还包括众多鲁迅研究的专家、教授们。但大家似乎都有一个共识,就是一边根据小说表面描写将其解读为爱情小说,于是如何维系爱情、关于说与不说、因爱情而忏悔等解读应运而生,还联想到《娜拉走后怎样》以说明经济问题在恋爱中很重要;一边捎带提及周作人的观点,并与周作人1925年发表译诗《伤逝》联系起来,却不深入进行研究和解读,也不给出具体论证,或者意图诠释文学上的永恒命题——“诗无达诂”,意即爱情小说和哀悼兄弟恩情断绝的解读都是可以而且能并列的。
评论家和研究者并非没有注意到周作人的观点,比如学者朱正在传记中写道:“普通读者阅读小说,重要的是看其中所写人物和情节,有兴趣去查考作者是因了怎样的情绪和影响才写这篇的人大约不会有很多。人们还是会把小说《伤逝》看作鲁迅写一个恋爱悲剧的名篇。”[11]朱正先生注重史料发掘和考证,在学术界是有口皆碑的,但在这里也仅仅是提出问题而没有解决问题,实在是有些遗憾。至于张洁宇教授通过推测鲁迅的散文诗《死后》与周作人的译诗《伤逝》的名称来源问题,承认“《伤逝》在爱情婚姻和女性解放的话题之外,的确存在一条与周作人有关的隐线”,但其为文“并不打算以考证和索隐的方式去解释这篇小说,更无意推翻或覆盖现有的合理阐释”,目的在于“通过《伤逝》中的兄弟隐喻讨论鲁迅与周作人在思想观念上的差异,并由此分析鲁迅在对这种差异的深刻反思中,如何突破了日常生活与私人关系的层面,抵达了对于大时代中知识分子前途与道路选择的思考”。他还进一步指出:“不得不说,周作人看到了《伤逝》中的兄弟隐喻,却错误理解了鲁迅的用意。鲁迅的‘痛惜’是对兄弟殊途的痛惜,也是对知识分子阵营走向分歧的痛惜,而绝非周作人所想象的那种私人语境中的感性表达。”[12]122应该说这个解读立论够高远深邃,或者说更接近鲁迅创作小说的本意也未尝可知,不过这一解读是建立在“兄弟隐喻”的前提和基础之上的,而他在行文中给出的考据却远远不够。也就是说,如果前提和基础不牢靠,多高远的解读都会显得虚悬甚至远离主题。
三
周作人关于小说《伤逝》主题的“感觉”和创作动机分析,究竟是否如他所说“不大会错”和“能够懂得”,以及《弟兄》“十分之九以上是真实”,有待细细考证。那么《伤逝》究竟有几分是真实的呢?不妨沿着周作人的思路去“考证和索引”一下:
子君不在我这破屋里时,我什么也看不见。在百无聊赖中,随手抓过一本书来,科学也好,文学也好,横竖什么都一样;看下去,看下去,忽而自己觉得,已经翻了十多页了,但是毫不记得书上所说的事。(1)引自《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以下出自本书内容的,均不再标注出处。
按照周作人的思路,这段文字如果隐去“子君”,是否就可以解读为鲁迅在兄弟失和后的一种真实状况?毕竟两人此前几十年兄弟怡怡,一起读书,一起翻译,一起创业,一起写呐喊文章,一起编杂志,买下八道湾也是为了兄弟会聚,忽然就这样东有启明西有长庚地不相往来,任何有感情的人都会表现出一定的不适应。那种无所适从的烦躁与失衡,其他人虽未曾亲历,但也完全可以想见得到。在这一点上来说,即使周作人发表诗歌译作《伤逝》属于无心,鲁迅紧接着写成小说《伤逝》和《弟兄》也假定并非如学者们认为的那样是一种明显的呼应,那么鲁迅在1928年9月2日的日记中所写也完全可以证明:“午后同三弟往北新书局,为广平补买《谈虎集》上一本,又《谈龙集》一本。”[13]94事实上,鲁迅购买、收藏周作人的书,远不止这两本。据学者倪墨炎考证,“周作人1923年7月至1936年9月,出版著作18种、译作11种,共29种,鲁迅藏有20种,占三分之二多,应该说重要的几种都收藏了”,“鲁迅购买周作人的著作赠人,还有数回。周作人翻译的短篇小说、散文、诗歌集《陀螺》于1925年9月出版,鲁迅即向北新书局购八本,分赠许寿裳、许钦文、韦素园、韦丛芜等人。周作人的第一本散文集《雨天的书》于1925年10月出版,鲁迅向北新书局购十本,分赠董秋芳等学生、朋友”。[14]
可见即使兄弟失和,鲁迅也依然关心、关注着弟弟。从《知堂回忆录》中,也可以感觉到周作人因为兄弟失和而备受伤害,他甚至到晚年也难以释怀,但同时又念念不忘昔日兄弟旧情。
再来看一段涓生的回忆:
破屋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语声,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
同样,这段文字如果隐去“她”,或者将“她”替换为“他”,是否就可以解读为鲁迅和周作人留学东京和汇聚北京时的生活、学习和讨论的场景呢?毕竟鲁迅长周作人4岁,又先到江南水师学堂和日本留学,包括后来到北京,无论学识、思想还是生活阅历,在各方面都可以说是周作人的领路人、指导者、推荐人。翻查两人从日本到北京时期的日记和发表的文章,可知二人经常一起讨论问题、写作文章,甚至还经常出现兄弟二人署名混杂的情况,最典型的莫过于鲁迅杂文集《热风》中的《随感录》三十七、三十八、四十二和四十三,确属周作人的文笔。
至于那间“破屋”,既可以解读成为他们共同在东京租住的房子,也可以看成是他们在北京时居住的所谓绍兴会馆。这一点周作人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中针对《伤逝》中“会馆里的被遗忘在偏僻里的破屋是这样地寂静和空虚”,以及“窗外的半枯的槐树的新叶,这样的败壁,这样的靠壁的板床”等描写阐释道:“我们知道这是南半截胡同的绍兴县馆,著者在民国初年曾经住过一时的,最初在北头的藤花馆,后来移在南偏的独院补树书屋,这里所写的槐树与藤花,虽然在北京这两样东西很是普通,却显然是在那会馆的旧居,但看上文‘偏僻里’云云,又可知特别是说那补树书屋了。”[15]241-242
如果说这样的分析还有一点道理,那小说接下来写涓生回顾子君的一段:
她却是什么都记得:我的言辞,竟至于读熟了的一般,能够滔滔背诵;我的举动,就如有一张我所看不见的影片挂在眼下,叙述得如生,很细微,自然连那使我不愿再想的浅薄的电影的一闪。夜阑人静,是相对温习的时候了,我常是被质问,被考验,并且被命复述当时的言语,然而常须由她补足,由她纠正,像一个丁等的学生。
这段近似粉丝见偶像般的描写,如果放到鲁迅和周作人在北京任职、任教和通过创作崭露头角后去看去年而稍显夸张的话,那么置于鲁迅第一次从日本回国与弟兄两个热聊的情境中,是不会有什么不适感的。对此,鲁迅的三弟周建人就在《鲁迅故家的败落》中曾描述说:鲁迅那次从日本回来、周作人从南京回来后,“我们三兄弟的话是说不完的,从楼上说到楼下,从楼下说到廊夏,从廊夏说到明堂”。[16]241-254这样的场景,一方面显示出三兄弟的亲密无间,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作为大哥的鲁迅如何被两个弟弟崇敬。而且,可以想见的场景中,一定是两个弟弟围着哥哥问这问那,作为哥哥的鲁迅则热情地为他们讲述在日本的所见所感。作为另外的证据,周作人在《知堂回忆录》中提及自己的笔名时说:“那时鲁迅因为小名曰‘张’,所以别号‘弧孟’,我就照他的样子自号曰‘启孟’。”[17]181在日本留学时的“最初几年差不多对外交涉都由鲁迅替我代办的,所以更是平稳无事”[17]241。这等弟弟喜欢并效仿哥哥说过的话、做过的事的行为举止,其实在非独生子女家庭中是很普遍、很常见的。
再举小说中的两处例子:
我们先是默默地相视,逐渐商量起来,终于决定将现有的钱竭力节省,一面登“小广告”去寻求钞写和教读,一面写信给《自由之友》的总编辑,说明我目下的遭遇,请他收用我的译本,给我帮一点艰辛时候的忙。
小广告是一时自然不会发生效力的;但译书也不是容易事,先前看过,以为已经懂得的,一动手,却疑难百出了,进行得很慢。然而我决计努力地做,一本半新的字典,不到半月,边上便有了一大片乌黑的指痕,这就证明着我的工作的切实。《自由之友》的总编辑曾经说过,他的刊物是决不会埋没好稿子的。
如果稍微熟悉一点鲁迅和周作人在东京时的生活,就知道二人曾不停地写稿、投稿(例如二人共同给《河南》杂志投稿)、翻译,尤其是兄弟二人合力翻译《域外小说集》。之后他们筹措资金,寻找出版商,终于在一年后出版了《域外小说集》。他们在《神州日报》《时报》做售书“小广告”,其中《时报》上不乏这样的广告词:“是集所录,率皆近世名家短篇。结构缜密,情思幽眇,各国竞先选译,裴然为文学之新宗,我国独阙如焉……至若装订新异,纸张精致,亦近日小说中所未睍也。”[18]这个经历,周作人后来也很认真地写在《知堂回忆录》里。[17]289-297至于《自由之友》总编辑说的话,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兄弟二人在日本时写稿、投稿以及与杂志主编联系那些事宜,包括两人翻译《炭画》投到《小说月报》被拒绝。周作人在《知堂回忆录》中对于翻译《炭画》的事这样写道:“可是译本的运气很坏,归国以后,于民国二年寄给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社,被退了回来,回信里说:‘虽未见原本,以意度之,确系对译能不失真相,因西人面目俱在也,行文生涩,读之如对古书,颇不通俗,殊为憾事。’……后来又寄给中华书局去看,则不赞一词的被退回了。”[17]304-305涉及翻译《黄蔷薇》时,周作人写道:“此书体式取法于牧歌,描写乡村生活,自然取景,虽运用理想,而不离现实,实为近世乡土文学之杰作。周君译以简练忠实之文言,所译牧歌尤臻胜境。”[17]305-306对于翻译事,周作人在《知堂回忆录》里有大量篇幅和笔墨,包括第一部译稿卖了稿费两百元,第二部译稿被退回,二人在翻译过程中的种种遭遇,等等,其中提及兄弟俩经常变换着口译、转述、笔述,有时候周作人“专管翻译起草,鲁迅修改誊正”。[17]268-271
限于篇幅,更多的小说文本和实际生活对照,这里不能一一列出和解读,只能简单示例如下。
小说中写涓生和子君“最多的是寻住所”,不免让人联想起鲁迅和周作人在东京时搬出伏见馆后先后入住东竹町、中越馆、西片町等多处住所;涓生做校对的事,周作人在《知堂回忆录》里提及许寿裳“给鲁迅找到校对的事务,稍微得到一点报酬”[17]291;小说中提及子君说“我们干新的”“来开一条新的路”,会让人联想起兄弟二人在东京准备要办的杂志《新生》,杂志未办成后二人开始合作翻译小说《域外小说集》;小说中的“屋子里总是散乱着碗碟,弥漫着煤烟”,与周作人笔下伏见馆中的一些不愉快的情形[17]259-261有些相像;小说中子君养的油鸡以及与女房东闹意见,与八道湾时盲诗人爱罗先科弄回小鸭子惹出用价钱昂贵的泥鳅喂养的是非[19]67异曲同工;子君的净身出户与鲁迅搬离八道湾的情形似乎有得一比;子君被家里人接走后病死,大概是鲁迅要告诉周作人,自己因为兄弟失和而大病了一场(鲁迅1923年11月8日的日记载:“夜饮汾酒,始废粥进饭,距始病时三十九日矣”[13]487);涓生操心家里的经济收入,而子君向来不大在意,与现实生活中鲁迅操心八道湾一大家族人的收支而“周作人时常在孩子大哭于旁而能安然看书”[19]63几乎如出一辙;涓生讨厌子君在他写作时喊他吃饭,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里写到“鲁迅在创作时,不愿意有人打扰他。若在创作时叫他吃饭等就不高兴”[19]212这一习惯,想来周作人也是知道的。
以上小说中的种种,以及周氏兄弟的情谊和生活经历,旁观的读者对此都有如此之多的联想和实证,何况作为当事人的周作人,他对那些点点滴滴应该历历在目,那些心照不宣之处,更应该心领神会。
如果上述小说中的诸多描写与兄弟二人的真实生活场景遥相呼应的话,那么小说中还有一些稍微隐晦的话,就可以有针对性地解读了。比如小说中说的“人们真是可笑的动物,一点极微末的小事情,便会受着很深的影响”。这话的意思是鲁迅在嘲讽原本兄弟之间那么深的感情,结果因为“一点极微末的小事情”闹得不欢而散,甚至有1924年6月11日的日记中记录的“詈骂殴打”[13]516,通常说的兄弟如手足的亲情竟然如此脆弱不堪。
再如,小说中有“其实,我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虽然因为骄傲,向来不与世交来往,迁居以后,也疏远了所有旧识的人,然而只要能远走高飞,生路还宽广得很”。这话的意思应该是鲁迅想说,原本自己一个人生活时,简单而且低消费,还能经常与朋友喝酒应酬,不时地去书店买书——这些鲁迅日记都可以证明。他后来买下八道湾,将一大家子人聚集到一起后,却因为支出经常大于收入,所以常常导致入不敷出,向朋友借贷。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中转述鲁迅的话:“自己负担轻,他们需用,就交给他们用好了”,“我总以为人不要钱总该可以家庭和睦了罢,在八道湾住的时候,我的工资收入,全行交给二太太,连周作人的,不下六百元,而每月还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借到手连忙回家。又看到汽车从家里开出,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呢?”“她们一有钱又往日本商店去买东西了,不管是否急需,都买它一大批,食的、用的、玩的,从腌萝卜到玩具,所以很快就花光了。又诉说没有钱用了,又得借债度日。”[19]61-64上述言论不仅仅是鲁迅和许广平的一面之词,鲁老太太、周建人、俞芳、许寿裳等都有文章为证。鲁迅对管家的周作人太太羽太信子颇有意见,小说中的“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苦痛,大半倒是为她”,其批判指向就很明显了。
随之,小说中的“子君的识见却似乎只是浅薄起来,竟至于连这一点也想不到”,以及“我拣了一次机会,将这些道理暗示她;她领会似的点头。然而看她后来的情形,她是没有懂,或者是并不相信的”,等等,意思也就都清晰起来。那就是鲁迅通过小说再次向周作人点明也是抱怨,自己曾经找过几个机会,委婉地提醒弟媳信子掌家大手大脚、阔绰过度的问题,可是周作人对于家庭生活的“识见”实在是麻木到“浅薄”,根本意识不到鲁迅所指出的那些问题的严重性。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里就说:鲁迅指出管家徐坤揩油、小孩子玩火等,“周作人视而不见,惟整日捧着书本,其他一切都可列入浪费精力和时间之类的处理生活方法”[19]63,“鲁迅有时还为周作人原谅:说他‘太木’(绍兴语),不知不觉的意思”[19]67。
最后来看小说的末尾处:“我仍然只有唱歌一般的哭声,给子君送葬,葬在遗忘中。我要遗忘;我为自己,并且要不再想到这用了遗忘给子君送葬。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这样一种阴冷、绝情又夹杂着坚忍、向上的抒情,是鲁迅要向弟弟表示,自己在努力忘却那段悲伤和痛楚,虽然感到艰难,但也要努力说服自己争取开始新的生活。到这里,再来回看周作人在《知堂回忆录》里所说的:“《伤逝》这篇小说很是难懂,……乃是全个是‘诗’,诗的成分是空灵的,鲁迅照例喜欢用《离骚》的手法来作诗,这里又用的不是温李的辞藻,而是安特来耶夫一派的句子,所以结果更似乎很是晦涩了。”[9]535-536的确,鲁迅是用安特莱耶夫式的“离骚”抒情手法,来晦涩表达他人生中堪称最痛楚的一段手足情绝。
关于小说《伤逝》,笔者做以上这种肢解性、纪实性、实证性的解读,实在是出于不得已,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最笨、最不具备文学赏析性的文学评论,不但不讨彩,还难免会出现一厢情愿的想当然和自以为是,甚至有些地方会犯张冠李戴式的错误。但有一点应该得到承认,这是对周作人的观点进行的一次证据充足的切实回应和补充。如果这样说还能有几分事实基础和内在逻辑的话,那么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对《伤逝》表面的爱情主题进行的一次修正。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伤逝》作为一部小说,有多种解读的可能和空间,或者说文本分析本身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研究者们也尽可以发挥才能和想象,但是无论如何解读,首先不能单纯地把它看作是爱情小说,而且更要重视昔日与鲁迅接触最多、对鲁迅最为了解的周作人的意见,否则不但解读和研究太表面化、不得要领,甚至是望文生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