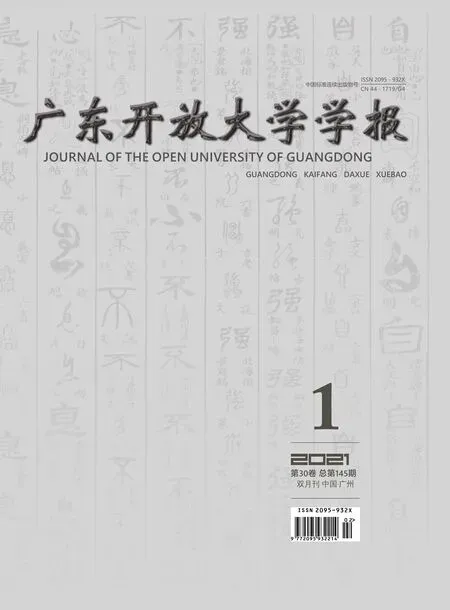民国时期岭南华侨的家国情怀
——基于对抗战前后伍氏家族侨批的解读
(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广州,510631)
侨批,又称“番批”,“批”是潮汕和闽南方言中对“信”的一种称呼。海外华人通过一些私人渠道或后来的侨批局等往故乡寄回信件、钱款及各种物品,被称为“侨批”,侨批是近代以来中国侨胞社会往来传递的重要民间文件。
侨批具有“银信合体”的显著特色,承担着缓解国内亲人家庭经济困难、供养父母妻儿的社会经济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国内家庭乃至家族的经济支柱。同时,侨批信件字里行间中既有对家人见字如面的问候,也包含了旅居国的时局变化、近期家人活动事宜等诸多信息。海外华侨通过侨批与在国内的亲人交流,了解国内政治局势等情况,侨批成为中外文化碰撞、交融的桥梁。此外,华侨有可能根据当时的国内局势做出自己的行动,对迁出地社会甚至国家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透过对侨批的研究可发现并解读华侨对“家”、对“国”的深厚情怀。
机缘巧合,笔者在广东省档案馆实习的过程中收集和整理了部分未公开的侨批档案,伍氏家族的一组侨批便是其中之一。伍氏家族侨批内容完整,字迹相对清晰。笔者不揣浅陋,在征得档案馆同意之后对其进行粗浅的解读与探析,其中,引用侨批内容中句读为笔者所加,如遇无法辨识字迹则用“囗”代替。
一、关于侨批的研究综述
近年来,海外华侨的相关历史文献逐渐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一些民间收藏家甚至特地前往华侨亲属家中收集侨信。这些侨信经由相关出版社、档案馆等组织收购、整理或出版,为学者们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华侨和侨批研究已有一定的学术成果,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侨信进行了梳理和研究:有的研究海外华人在外国的联合或同盟;有的从跨国主义和移民关系网的角度进行研究;有的关注侨信对海外华人及其家乡社会的影响。每一封侨批都有一个特定的历史情境,讲述小人物在大时代背景下的故事。因此,无论是对人的研究还是对家乡社会的研究,不仅要加强对抽象的、大写化的“人”的研究,还应加强对具体的、个体的“人”的研究。只有这样,对华人华侨和华侨社会的研究才能进一步深入。在丰富的案例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系统论述与理论建构才具有可能性。
侨批研究大约于20世纪初开始起步。1914年由台湾银行进行了名为《侨汇流通之研究》的调查;1929年,杨起鹏撰写了《汕头银业史略及其组织》一文;但在新中国成立后,侨批的研究陷入停滞[1]。改革开放后,对侨批的研究再度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特别是在“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成功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后,侨批研究成为相关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而作为侨乡的闽粤两省亦成为侨批研究的前沿地带,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
目前的侨批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类是从文献学、档案学的角度出发,研究侨批类型和内容要素的整理,探讨侨批材料特定的经济文化意义和历史研究价值,特别是地方社会史研究的价值[2],侨批材料的文物价值和文化传承功能亦被肯定。并在此基础上,为侨批的利用与开发建言献策[3]。
第二类是从历史学的角度出发,通过侨批,肯定华侨对家乡建设的贡献,认为其对工业、房地产业、交通业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并解读近代的移民网络和华侨社会,关注华侨与祖籍地的互动。不同侨乡的侨批材料往往能反映某一时间、某一地区华侨的心理状态和思想感情。在侨批中,我们能解读出当时华侨对自己的国家、故乡和亲人的情感态度,以及其自身在旅居地所处的生活状态[4][5]。
第三类则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着眼于侨批中的侨汇,把研究目光放在了侨批业上。侨汇在近代中国经济史上有着重要地位,有学者指出,中国支付入超的最重要货币来源是海外华侨的汇款[6]。这一方面的研究除了阐述侨汇的产生及其投递特点、生存业态、经营方略、投递的保障措施、信用问题外,亦有研究将侨批业置于宏观的经济体系中,探讨侨批业和银行业、邮政业之间的相互关联,探讨侨批和中国乃至亚洲金融体系的互动关系。
目前广东省的侨批研究对象主要在潮汕、梅州和五邑。相对于潮汕与梅州,五邑侨批研究的起步较晚,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还有待提高。且随着新的侨批材料的不断发掘,研究工作的推进也势在必行。
关于五邑地区华侨资料,广东省档案馆出版了《近代广东侨汇研究》等资料集,还收藏了宝贵的相关档案资料,如侨批业的口述、影像集和回忆材料等。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以伍氏家族寄归侨信解读为中心,探讨普通海外华侨在二战前后社会重建时期特殊的经历和心路历程。海外华人在某些历史格局中的个人经历和思想情感都具有深刻的时代烙印。解读这组侨批不仅有助于认识特定历史时期普通海外华人的个人生存状况和战后海外华人故乡和华人旅居地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而且有助于理解和分析海外华人华侨独有的家国情怀与文化认同。
二、旅居海外的伍氏子弟之简况
五邑地区的华侨与大部分旅居海外的游子一样,总是心系家乡,热心于在文化教育等领域通过捐赠开展慈善公益事业。同时在国内的实业投资上也常常可见他们的身影。民国初年至抗日战争时期,五邑、广州、潮汕等地的华侨均在家乡掀起投资兴办实业的热潮,涉及工业、交通、商业、服务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等领域。伍氏家族华侨亦是如此。
根据侨批所透露的信息和查阅相关文献进行简要推断,伍氏家族的侨批收件人多是伍勋宝。伍勋宝是台山全属民办公路股东主席团成员之一,曾与人合伙经营过一家轮船公司,家境还算不错,后因经营不善而破产,家道逐渐衰落。于是其三个儿子(伍耀初、伍耀贤、伍耀韶)与弟侄伍耀邦、伍耀璋等男丁先后前往美国纽约、旧金山等地谋生,年迈的父母与妻儿等侨眷则留在家乡。
伍氏子弟赴海外谋生的动力是改善家族乃至家乡的经济生活。根据侨批的相关内容可知,伍耀初、伍耀韶在美国经同乡引荐成为台山寗阳总会馆商董职员,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他们主要是通过这个会馆达成对侨乡的捐助。尤其是伍勋宝大儿子伍耀初,自从他在1921年离开家乡并寻求在美国谋生以来,已有十多年未回过家,与国内侨眷的联系与沟通只能依靠信件、物品、钱币等。伍耀初在写给父亲的信中称自己是“涉足海角天涯,只凭鱼雁几纸,慰儿异地远怀”,但“无奈时局与环境拘然,致疏修候”。由此可见,伍氏兄弟离开家乡的目的是为寻求更好的生活和家族的经济环境。
同时,旅居海外的五邑籍华人也逐步组成了一个同乡圈,旅外华侨可在其中互通信息和互相帮助。伍氏家族在美国的华人社区中有不少原籍同乡,在向国内亲属报平安时,他们经常会强调其与“惠贻合家人等平安康健”。伍耀贤在信中提到:“昨天抵美之华侨,我本乡有鼎光夫妇,及锡堂等,顺字告及。”这表明,在美国的华裔华人中基于亲缘、血缘乃至地缘间的图式关系,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交网络,可相互交流信息并团结互助。兄弟几人在美国勤勤恳恳,具有一定的事业基础,因而在抗战期间与战后初期,接济家乡父母妻儿的重担几乎全压在了他们身上。
三、伍氏子弟对“家族”的无比珍视
刚踏入异国土地时,这些来自于普通家庭的子弟往往举目无亲,甚至连自身温饱都成问题,但顾不上伤春悲秋,初抵异地的他们就迅速全力投入各种营生,赚取收入以养家糊口。美国在1882年通过了“排华法案”,并在其后通过了一系列的歧视性法律,如1884年的修正案、1888年的斯科特法案、1892年的基尔法案和1924年的移民法案。华人作为美国第一个被写入移民法的少数族裔,遭受了美国社会多方面的排挤与压迫,再加上物价的高涨,经济的恶化,使华侨的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但当他们手头略有盈余,总是要一点点攒起来,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把款物漂洋过海送到祖国的亲人手中,以尽赡养长辈妻儿的义务。从伍氏家族侨批档案中可以看出伍氏子弟对“家族”的无比珍视。
其一,伍氏家族侨批的内容显著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家庭关系的重视。海外华侨把省吃俭用积攒的钱寄回家,为的是让老家的亲人过上体面些的生活。因此家乡的人们都猜测这些海外华侨发了大财,在外国过着奢华的生活,殊不知大多数普通华人在国外只能干些底层的脏活累活,生活的窘迫与艰辛难以想象。1929年的中秋节,伍耀初在给父亲的信中谈到对此的深切体会:“……工程方面,基本停顿;物质方面,一日三变;商业方面,大底打击。我等实在水深火热之中,儿在外幸赖祖安,附银钱二十,祈安。”由此可见,一封小小的侨批,几句叮咛与嘱咐,夹带辛苦钱几许,万里迢迢,漂洋过海,几经辗转才能寄到侨属亲人手中,为家乡亲人送上异国游子的深深思念和拳拳关爱。
其二,侨批的内容还反映了伍氏家族对子女教育的重视。尽管伍氏子弟常年旅居国外,但他们很重视子女的教育和成长,勉励孩子遵循家中长辈的教导,体现了旅居海外的伍氏族人对子女教育和成长的重视。1933年间,伍耀贤多次写信让父亲“无论如何艰苦也要让吾儿求学”,并在信中反复告诫儿子:“汝在家须听从汝母亲教训,切勿自作自为。凡事行进,务祈磋商。”在得知自己继母添新丁后,伍耀贤在信中写道:“闻继母添新丁,即我得多一个细佬将来助力……望继母留心,用精神养育,根基(疑是新丁名字)长大,将来栽培,为家争荣,为国谋荣。”1936年,当从亲友口中得知儿子异常顽皮及不听祖父与母亲教诲的消息后,耀贤在信中严辞切责,劝勉告诫,强烈表达自己的不满与失望:“今日抵美之亲朋戚友谈及我儿,均言汝在家真是顽皮,不听汝母亲教道,汝日后若想在社会立足,务克勤克俭,痛改汝顽皮气性。”另一方面,耀贤又于信中叮嘱妻子:“小子顽皮,汝严令教训,切勿放松。”
其三,侨批所夹带的汇款除了用于赡养家中亲属外,常常还用于资助侨乡建祠堂、建校舍、修公路、修筑防御工事等,体现了以伍氏家族为代表的海外华侨深厚的乡土情谊。如1930年,伍耀初和伍耀璋就曾参与投标政府余地作为修建祠堂的备用地①据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近代华侨报刊大系》(第1辑·第21 册),广东经济出版社,2015 年,第452 页,其中有“第三十九号,由伍耀初投得,每井五百二十六元;第四十号,由伍耀璋投得,每井五百二十六元”等说明。;同样是1930年,旅美台侨筹建台山中学高中校舍募捐总所中也有伍氏华侨伍耀初、伍耀韶的身影,他们两兄弟作为台山寗阳总会馆商董职员之二,为筹建校舍出资出力[7]。
较为显著的例子则是由海外华侨出资建造的碉楼遗址。民国时期,台山、开平等地军阀混战,土匪猖獗,该地区治安令当地人倍感焦虑。以开平为例,仅1912~1940年间,就发生大型匪劫事件约71宗,掳去耕牛210多头,杀人百余,金银首饰无数,县城3次被攻陷,县长朱建章也被掳去[8]。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村民们考虑修筑防御工事并召集团练(地方民兵)武装力量以抵御土匪侵扰。不得不说,这种操作还是有一定效果的。例如1922年12月某日,土匪劫掠开平中学时,就被鹰村防御工事之一的碉楼的探照灯发现。当是时,四乡团练及时截击,救回了校长及学生17人[9]。此事轰动海内外,华侨纷纷倡议建碉楼和成立民团,武装保卫村民。在侨胞的大力支持下,开平掀起了兴建洋式碉楼的热潮。伍氏家族的华侨对此非常支持,多次汇专款回国,并通过侨信密切关注建造进程。碉楼的兴建起初是为了避洪涝。开平地势低洼,每遇暴雨,必生洪涝。开平人民于清初便开始建造碉楼,每当洪水袭来,村人登楼便可全部得救。开平共建碉楼3000多座(现存1833座)[10]。如今,这些洋式碉楼大多空置了,那些豪宅上半身是“西装”,折射着捐资华侨所在国家的洋派身影,下半身则是“盔甲”,本身碉堡的防御功能倾诉着所在地区内在的焦虑。
总的来说,大部分侨批都可见伍氏家族华侨对亲人的思念之情、对长辈的孝敬之情、对子女的舐犊之情和对故土的眷恋之情。但这种文化认同更多基于地方宗族血缘之上,对整个国家的关注往往只有寥寥数语,但这种国家文化认同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展助推到一个高潮。
四、伍氏子弟对“救国”的无私奉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侨批寄回国内变得更加困难,但客观条件所导致的侨汇迟滞不通仍然令华侨和侨眷无奈:“昨方接家中函,内情均悉矣,家中困难知悉……皆因中日战务阻滞,原拟八月寄送,九月初旬到港;方合有时消息不佳,有时船只不便……欲急不能,但寄留人境,又何可言哉!”在抗战期间,以伍氏家族为代表的海外华侨不仅一如既往地关切家乡亲人,更重要的是增强了家国之情,他们为处于战争状态的祖国捐献了大批物资。
美洲华侨组织成立了救国联合会、为捐救国会等救国组织,在美国的伍氏族人大多都参加了救国联合会。1943年初伍耀初在侨批中提及:“我今兄弟几人皆入救国会,为中日战争出资助力,听闻美已与日宣战,我国民族将更增坚囗”。伍氏家族此阶段的侨批内容多次涉及海外华侨在美鼎力捐助的救国活动,包括购买救国公劵、寄送医疗物资、购置军火武器等,强调了“保乡土、卫国家”,字里行间都体现了守望相助的殷殷爱国之心。在救亡图存的危急关头,中国人民总是能拧成一股绳,展现出同仇敌忾的民族情怀,体现了空前的民族团结。侨胞虽身处海外,但对祖国遭难及同胞受辱感同身受,时刻关注国家安危,并慷慨解囊。
抗战胜利后,中华大地亟待重建,但随之而来的就是侨乡严重的通货膨胀,加上当地官僚资本的压榨,国内普通民众的生活日渐困窘,而依赖海外侨汇接济的侨眷们对华侨的汇款更加急需。伍氏子弟对此深有体会,因而在1945年底写给父亲的信中称:“家中困难,儿等了然于心,兼之寒冬已至,正是饥寒交迫之际。吾亦明了。奈因谋事失慎,一时囗囗乏人之故耳。一候时机一就,定付多些回家,以济燃眉。”同时对于国内物资物价等情况也极为关注:“时下各种物价如何?米每担若干元?美元换国币若干?……可并禀知”。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国家和亲人的拳拳关爱,这无疑反映了此时的海外华侨已经具有高度的家国情怀与民族认同感。
刘博智在他的《再梦金山》一书开篇谈到他采访华侨出洋的原因时,第一句话是:“飘零去,莫问前因”[11],那是海外华侨心绪万千时的一句无可奈何之语。侨批就是旅居海外的中国侨民与其国内亲属互动的历史见证。一封封侨批就像一个个海外赤子的内心独白:从对家中亲人的关切思念,再到对国家和民族的强烈文化认同和爱国情怀。伍氏家族的这组侨批向我们展示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普通华侨的爱家爱乡之情和深厚的家国情怀。普通“小人物”的个人命运和生活经历不仅勾勒出了普通华侨在战争中对“家”和“国”的理解,同时也为研究中国侨民社会提供了独特的微观视角。
(本文部分资料来源于广东省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