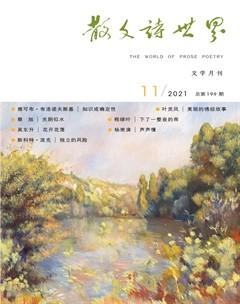神俗共鸣的小人间
李彬
人生黄昏之际,汪曾祺先生笔下的芦苇丛间,水声与诗意悠扬,驶出了一篇《受戒》。如果说《朝花夕拾》是鲁迅先生“从回忆中抄出来”的散文,那《受戒》好像也就成了汪曾祺先生“从回忆中抄出来”的小说。从记忆中沉淀辗转而来,不免带了点“复古”的味道,这或许便是《受戒》在80年代让众多阅者流连忘返的神秘之处。
为什么说“复古”呢?一来《受戒》出世的年代,文化与审美尚处于相对贫乏的状态,作品本身回避了热火朝天的现实旋律,也有意绕开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滚滚浪潮,选择将文学的笔触伸向人性的真、善、美,过滤掉外界的喧嚣尘埃,照见了和谐、朴实、健康的生命与爱。而由此呈现出的文学理想,恰恰延续并保留了被遗忘的抒情小说风格以及文人骨骼里携带的文化品格,颇有些京派文学的余韵,同时沾染了魏晋之世的隐逸气息。二来汪曾祺先生自己说过,《受戒》取自43年前的一个梦,时空距离的拉开,旧日生活的浮现,也使得这部作品蕴含了古香古色的滋味。
不过这可不是故意“做旧”,要知道,汪曾祺先生喜欢作画——原汁原味的水墨画,没有丝毫做作雕凿的工笔,全然讲究一个水到渠成。这份作画的好习惯带进了文学创作,却也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为什么那些老故事、老题材经过汪曾祺先生笔墨的浸润,一经靠近便露出“清水出芙蓉”的天成朴质之感。
《受戒》就是一个从纷繁的往事印痕中所剥落出的唯美、清澈的文学世界,翻开它的一页,微波红尘,情窦初开,那段晶莹剔透的初恋故事缓缓飘出:芦花摇曳的小天地里,寺庙里的小和尚明海遇见了水乡里长大的农家女儿小英子,他们在神俗相融、万物和谐的人间自然而然地相爱了。
一、“庙宇之高”:荸荠庵的俗
故事的开头,“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一开篇的叙事节奏被放置在一种从过去朝现在流动的时域里,仿佛蒙上了一层时光的雾气,不由引得阅读的脚步慢下来。循着明海出家的线索,一个颠覆传统佛门之地印象的庙宇将抖擞一身烟火,脱去庄重、神圣的宗教外衣,以世俗的,甚至是反叛的面目呈现在我们眼前。
书中写道,“大者为庙,小者为庵”,明海所在的寺庙正是位于赵庄的荸荠庵。这个设定很有意思,“小者为庵”,所以叫荸荠庵,而不叫荸荠庙,从一开始就先干净利落地划定了一个小型的地理空间,这个空間中上演的人事纷扰,也自然变得小了,变得纯粹了。因为宏大容易显得繁乱,小处反而容易简单透明。我们好似也就能理解为什么明海是小和尚,为什么得写明海的初恋——为了“小”。主人公须是一个年龄上的懵懂青年,在他身上萦绕的情事也须是小小的情事。所以小小的荸荠庵最先出现在读者的视野,用“小”牢牢把所有人目光锁定,奠定了整篇作品轻盈简明的基调。
对于荸荠庵,汪曾祺先生没有一来就描写里面住着的人、发生的事。他首先着墨的是荸荠庵周边的环境地势,这一点与其老师沈从文先生在《边城》的开头颇有些异曲同工之妙,得把人事存在发生的自然环境先交代清楚,人物命运才能自然地行进。
“荸荠庵地势很高,门前一条河,门外一片打谷地,三面环抱高大的柳树。”短短几句,荸荠庵作为佛门之地的神秘高远,已然削减了大半。试想一下,在传统文化里,我们一提到寺庙僧侣,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曲径通幽、密林古刹。可荸荠庵不同,它门前就匍匐着河水,河水不比溪水,不具有涓涓细流的叮咚婉转,少了静谧;靠近打谷地,打谷的丰收与劳作,是烟火聚集的气象,少了清远;再看三面的柳树,这里尤其值得留神,为何不栽种静穆挺拔的松柏,而选择窈窕招展的柳枝,平白折损庙宇的庄严之感?这正是汪曾祺先生的高明所在,所有看似简单的一笔带过,都有其深意。河流奔涌,自有一番生机活力;打谷场每逢收获之际的忙碌身影,增添几份热闹;柳树随时乘风摇曳,那份特有的舒放与细软,让人感到放松与闲适。如果你仔细推敲品味,便能从中发现一些隐晦的铺垫,一个庙宇从外部环境就已被消解了大半的神圣、庄重、肃穆,那在里面生活着的人,还会是我们预期里僧袍加身、不惹尘埃的神职人员吗?
小小的荸荠庵住了六个人。一是明海,日子过得很清闲。扫地、烧香、敲钟、挑水、喂猪、念经,大概是庵里最像和尚的人。二是仁山,明海的舅舅,庵里的方丈。是他把明海引上了出家的道路,整日教诲明海要做一个好和尚。大家管他叫“当家”的,桌子上放的是账簿与算盘。柴米油盐、租佃收账等鸡毛蒜皮之事,也都经他的手,确实是更像当家的营生,不见一丝“方丈”的影子。三是老和尚普照,一个很枯寂的人。成天关在“一花一世界”里,平日里吃斋,过年时除外。这个“除外”,是汪曾祺先生特有的幽默,和尚竟然可以在过年时不吃斋?也就只有荸荠庵里的和尚了。四是仁海,他有老婆。此话一出,仿佛平地一声惊雷响,一个和尚有老婆,多么惊世骇俗。五是仁海的老婆,每年夏秋来庵里纳凉,白日闷在屋里不出来。一个妻子的细心与善良透过一个“闷”字跃然纸上。六是仁渡,聪明年轻,打牌算账,放“花焰口”。“因此快乐起来的女人”,总是围在仁渡身边。
人们常说“偷得浮生半日闲”,而荸荠庵里的人则是偷了一生。这就是荸荠庵,从境到人,俱与平日里该有的佛门相去甚远,褪去面纱后显露的是一副尘世该有的俗气与自在,刚好对应了文中那句“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有人提起”。他们无所顾忌地活着,吃喝嫖赌均沾;他们无所顾忌地爱着,放肆地挣脱规矩束缚,遵循生命的原始欲望。人与宗教的隔膜在这方寸之地无声无息地自我消融,达到一种理性与情感的动态平衡。比起“正经”的神职人员来说,他们变得更加地“人化”,更加地鲜活,有自己的贪痴喜怒、酒色放纵,而非无欲无求、不食烟火。人性也由此得到了最为自然地舒展,从而闪耀出健康、和谐的光辉。
荸荠庵的俗,是将释的高远往下扯,归还以亘古传承的健康、自然的人性美。这种俗气不是肮脏下流,相反是一种轻盈的俗气,让生命在嘈杂的人世越过沉重,得以喘息。
二、“桃源之远”:世俗生活的仙
借着一只“铜蜻蜓”,明海跳出了荸荠庵,与小英子有了“亲密”的接触,开启了丰富饱满的世俗生活。不要小看了这个定情的物件,没有它,明海与小英子之间的懵懂初恋,还真就少了几分“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的青涩味道。这个用来偷鸡的工具,悄然间勾连起两个孩童的玩心,拉近了彼此的心灵距离,也为“明子老往小英子家里跑”埋下了伏笔。
沿着“小英子家”这个方向,一副悠然闲适的乡村风俗画卷徐徐展开。书中描写到:“小英子家像一个小岛,三面都是河,西面有一条小路通到荸荠庵。独门独户,岛上只有这一家。”一家四口人全生息于这个小岛上:门外,是结白或结紫的六棵桑葚、种满瓜豆蔬菜的菜园子;门里,是牛棚、猪圈、鸡窠、石磨、堂屋与住房;房檐下,一边石榴树,一边栀子花,夏日之时开了花,一红一白交相辉映,香气四溢,连荸荠庵都能闻见。至于一家四口,一个赵大伯,能干的“全把式”,和气结实,像株榆树;一个赵大娘,精神清亮,身上衣服格挣挣的,如同聚宝盆;一个大英子话少文静,一个小英子喜鹊似的呱呱不停,却都承袭了母亲的样子,眼珠黑白分明,如清水,如星星,一頭乌发发根通红。
此时仔细品读便会察觉,字里行间为我们勾勒的是一片“净土”,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存在,无论是在此地绵延的人还是周遭的山水,均透露出对于“小国寡民”的向往,隐约有老庄的影子伫立。只见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日光清幽,安定富足。想来只有这样的世俗,才可安放一段水晶般的初恋,明海与小英子也只能在这里的日日光景中,浇灌出爱的花朵。
明海出庙,是需要由头的,将他“牵入”世俗的由头便是大英子的出嫁。出嫁准备的挑花绣花,得仿照活花活草,小英子立马就想到了会画的明海。在他的画笔下,一朵朵石榴花、栀子花、石竹子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和着小英子做的鸡蛋芋头,可爱灿然。
画着画着,明海就变成了小英子家里的第五个人,往后的劳作时节,每每给小英子做帮手。他们在浓绿的秧田里薅草,小英子放出脆亮的嗓子;他们在傍晚牵牛“打汪”,瞧水牛打滚扑腾,浑身沾满泥点;夜晚并肩坐在石磙子上,听青蛙打鼓,听寒蛇唱歌……
情愫发酵滋长的过程,往往在等待一个点明的契机,而汪曾祺先生的方法不失为最委婉最纯洁的一种,他通过什么点破这段情事?一串美丽的脚印。小英子总爱“歪”荸荠,赤了脚踩进滑溜的泥里,在柔软的田埂上留下一串脚印,“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明海看傻了,心里痒痒的乱掉了,那双晃荡的脚丫分明踩进了他的心里,搅动了一池春水。脚印此刻作为一种隐喻,象征着欲望——情欲的若隐若现,再配合动词“痒”和“乱”,十分精准巧妙地把明海的内心悸动投射到明面,美好朦胧的爱意也就此萌生。
总得来说,聚焦于庙宇时,汪曾祺先生把它往下扯着,赋予其俗气,通过“俗”来展现人性不受束缚与阻碍的一种原生的状态;当场景转换到世俗,它本该是接地气的,汪曾祺先生偏偏又将其朝上提,处处弥漫诗意与仙气,云雾缭绕中创造出一个现世的桃源,通过“仙”来呈现人性中纯净无暇的一面。
三、一片芦花荡:破戒的诗意
作品结尾,明海受戒了,小英子划船来迎他。这时我们可以回溯到开头,明海从离家到荸荠庵,他和小英子第一次相见是在船上。等调转到结尾,明海和小英子依然是在船上,结构上首尾呼应,无形中成为一个闭环。
而船作为一个媒介,在两人的命运波澜中架起了一座桥,把两个本来没有交集的灵魂运载于宽阔的水面,串连一段因缘际会。正是在这片波光颤动的水面上,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划着桨穿过一片芦苇荡,两人心里那份不明所以的情意,便也随着波浪和芦苇一点一点的晃动摇摆、缠绕生长。
细密的芦花成为了见证明海与小英子爱情的信物,也预示着明海的破戒。在飞舞的紫灰色新穗中,明海突破了受戒施于他的种种羁绊,对小英子大声地说出了“要——!”伴随着青桩的飞远,一个神俗共鸣的小人间也远去,落下诗意的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