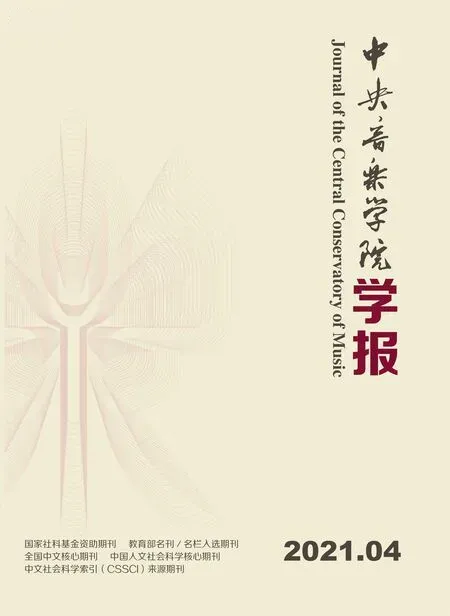清代音乐在朝鲜的传播及其影响
——以朝鲜使臣《燕行录》的分析为中心
崔玉花 罗 旋
引 言
《燕行录》是朝鲜李氏王朝时期(1392—1910)赴清使节的中国游记,主要记录了从朝鲜到燕京旅途中的所见所闻。在清朝250年间朝鲜使清共700多次,累计30多万人次,留下了对清代经济、政治、文学、建筑、伦理、道德、民族关系的真实观察、体验,同时也包括文化艺术发展在内的真实记录,其著录形式有且不限于日记形式的散文、笔谈、诗歌酬唱和小说。通过《燕行录》的研究可以更为清晰地探知清代中朝关系,还原历史真实,也可窥见域外文人(他者)眼中的中国形象。在《燕行录》研究方面,国内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其中文学、历史领域的研究成果甚丰,相比之下,在音乐领域的研究成果还不多。从笔者所掌握的《燕行录》资料来看,在音乐交流方面的内容比较丰富,包含了清代宫廷音乐、民间音乐、音乐思想、乐谱以及乐器形制和演奏等方面的音乐文化内容。通过这些内容不难发现清代中朝音乐交流的发展规律和特征,尤其是清代音乐对朝鲜半岛的音乐发展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本文拟从文艺传播学和接受美学的视角,以使清文人洪大容的《燕记》和朴趾源的《热河日记》等有关文献为依据,考察清代音乐思想、乐器和戏剧音乐在朝鲜的传播与影响,探讨中朝音乐交流的规律和特征。
一、音乐思想的交流及影响
清代音乐思想经由多种渠道传播到朝鲜,既有笔谈交流,又有通信形式,还有在燕京滞留期间耳闻目睹的亲身体验记录。其中,笔谈是清代音乐传播的主要载体和途径,即以汉字记录,通过一问一答形式进行交流。由于是面对面的交流对话,且在书坊、个人寓所、书楼、太学馆等非公共场所,所以交流内容比较真实、自由和丰富。中朝文人的汉文笔谈文本,已经成为在东亚汉文化圈内文化交流史研究的珍贵文献。
纵观整个《燕行录》中的音乐笔谈记录,朝鲜使臣朴趾源(1)〔朝〕朴趾源(1737—1805),字仲美,一字美斋,号燕岩,朝鲜李朝末期学者、诗人、小说家,实学派代表人物。的记录最为详尽,朴趾源1780年以使节团的成员身份来到中国,其回国后发表长篇纪行《热河日记》,在这鸿篇巨著中不难发现作者对清代社会的经济发展以及文学艺术发展的极大关注。其中,朴趾源与清代文人围绕音乐问题进行多方面的交流与对话,这些或以笔谈记录,或以观看体验记录收录在《热河日记》的相关部分中。朴趾源在《忘羊录》中以专题的形式记载了与王鹄汀、尹嘉铨进行探讨的情况。他们主要针对的问题有:何为五音,何为六律;不同时期的音乐风格为何会如此迥异,音乐随着时间、地点的改变会不会有所改变;中国雅乐的产生与发展以及在朝鲜半岛的接受与传承;中朝两国演奏乐器的传承与创新等。在这一系列文化的交流与传播过程中,朝鲜使臣的音乐思想得到了凝练与升华。
首先从审美主体的角度提出了“更张出新”的主张。朴趾源在《忘羊录》中问道:“古乐终不可复欤?”王鹄汀以音乐和美味为例子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夏之尚忠(推崇忠诚、朴实),殷之尚质(推崇质朴),周之尚文(推崇人文精神),嬴氏之罢封建、坏井田,为千古罪案,然其实,时运之所不得不然。刍豢,人之所同嗜也,至于久病之人,虽全鼎大美,闻臭虚呕;虽草根木实,欣然接味。虽有善唱,一曲恒歌则座者皆起。法久弊生,不知更张者谓之胶柱鼓瑟,此乃人情之所同然。故治非尧舜,则虽有《韶》舞,向背之间,神人难和。此圣人无奈乎世运之循环也。以上论运,且夫文字之生久矣,夫子之删述,即天地时运之一大变,固夫子不得已之事也。”(2)〔韩〕林基中:《燕行录全集》卷56,首尔:东国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66页。
这为朴趾源“反复古,求发展”的音乐观奠定了基础。他认为,夏之尚忠(推崇忠诚、朴实)、殷之尚质(推崇质朴)、周之尚文(推崇人文精神),都顺应了时代的潮流,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的审美需求和欣赏能力也在变化,孔子也无可奈何。所以必须不断创造出能够反映时代需求的音乐作品,满足人们不断升华的审美需求,这样音乐才有持久的生命力和永不磨灭的艺术魅力。“法久弊生,更张出新”的主张,为当时的文艺创新提供了理论基础。
其次,朴趾源提出音乐风格随时代发展而变化,指出了音乐风格既具有多样性,又具有地域的相对稳定性:“至于风,四方各异,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者是也。故刑政之所不及、口语之所难喻,惟乐能宣。几之神而用之妙,风动而光被之,鼓舞于不知不觉之中,其功化之速。至如两阶舞羽,七旬格苗,虽谓之移风易俗,一变至道可也。然其变南方之柔、北方之强,不可易也;郑声之淫、秦声之夏,不可变也。是乃土之声而气之禀,则圣人亦无奈乎风之所异,故曰放郑声而已矣。以上论风。”(3)同注②,第265页。他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百世不败,那么音乐自然也会经久不衰,各个朝代的音乐各不相同,各地方的音乐相差甚远。例如南方音乐的柔和,北方音乐的强劲,郑声的淫乱,秦声的正统,都很难轻易改变,圣人对此也无可奈何。朴趾源还把乐器比作山中的幽谷,声音比作谷里的风。山谷没有改变,但山谷里的风却有厉风、和风、飙风、冷风等多种。
再次,提出了“北学中国”的思想。《热河日记》是朴趾源北学思想的宣言,他通过与王鹄汀、尹嘉铨的对话,深入研究和探索,对于中国的音乐发展进行了积极的思考。朴趾源在追求音乐不断发展的同时强调“反复古”,倡导实用精神,主张实学,这一精神是“北学中国”的核心。其中《忘羊录》里朴趾源的“北学思想”体现在朝鲜雅乐对中国雅乐的推崇。朴趾源在《忘羊录》中记载:“史传箕子避地朝鲜,携《诗》《书》《礼》乐,医巫、卜筮、工伎之流五千人从之,与俱东出,故谓六艺全部独漏秦焰而流传敝邦也。”(4)〔韩〕林基中:《燕行录全集》卷56,首尔:东国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67—268页。他后来还用《牡丹亭》和《西厢记》的对比来说明民俗趣味是随着时代的改变而变化的。人们厌倦了《西厢记》,当《牡丹亭》上演时会感觉到欣喜。而士大夫想要恢复古乐,却不知道改腔换调,一味地寻求乐器上的改变来寻找古代的音乐是不对的。朴趾源透彻地分析和批判了当时士大夫恢复古乐的错误做法。在此基础上,还提出了解放思想、摒弃雅俗的对立,最终实现雅俗共赏的主张。从《忘羊录》内容的分析看,不仅可以看出朴趾源对中国音乐文化的热切向往与崇拜,还能窥视两国学者的学术交流动态,挖掘朝鲜音乐对清代音乐接受与融合的内在特征。
总之,朝鲜使臣们的音乐思想对朝鲜半岛音乐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忘羊录》中的“反复古,求发展”“乐由心生”“雅俗共赏”“北学中国”的音乐观为清代乐器及演奏法的传播、传习开辟了道路,与此同时,也对中国音乐思想的传播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为中朝两国音乐文化的交流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清代乐器及演奏法的传播和传习
中国的音乐和乐器在朝鲜的传播具有悠久的历史,比如在宋朝宋徽宗时期,曾向高句丽赠送了大量的乐器、乐谱、乐工及舞姬,并进行音乐传授,高句丽接受后,通过充分吸收,将此作为雅乐运用在朝鲜宫廷仪礼中。但到了李朝,由于经过多次战乱,朝鲜宫廷音乐遭受重创,乐器大量损毁,曲谱丢失严重,乐工流失殆尽,只能将庙社、文庙、山川祭祀等仪式音乐搁置一旁。直到清顺治登基,朝鲜又开始慢慢恢复宫中雅乐。据《仁祖实录》载:礼曹启曰:“乱后物力荡竭,人民离散,乐工、乐生被虏被杀者甚多,庙社、文庙、山川之祭,不能用乐。以待事定后复设,而至今十年,国家多事,不能复设。庙乐未复,则于他事不可用乐,故昨日莫大之庆,陈而不作,明日百官之贺,亦将难学,此诚欠事。今年饥馑之灾,近古所无,此时虽不得复设,而乐舞不可终废。事定无时可期,将来用乐当否,请令庙堂商议,或限以年数,或待岁稍丰,而宜预令乐工、乐生等肄习。”(5)选自《李朝实录》又称《朝鲜王朝实录》,为朝鲜历代王朝汉文编年体史书。本文参考的是1959年中国科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科学院、朝鲜科学院合编的版本。该书依据朝鲜金柜秘藏本,分10册,46卷影印出版。
在清朝初期朝鲜一度对清政府抱有敌视态度,随着康熙政权对朝鲜“怀柔政策”的深入实施,中朝两国政治关系出现缓和,透过燕行使臣的记录可以发现,此时朝鲜开始重新认识清朝政治、经济和文化,对清朝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朝鲜英祖时期开始重视乐器的修复工作,频繁派遣乐工跟随使团来中国购买和学习乐器,其中对唐琴(中国古琴发展的鼎盛)和笙簧(相当于现代的笙)的关注最多。英祖(1724—1776)继位初期,皇家的祭坛并没有雅乐器,朝鲜皇室在祭祀时大多用的是祭祀山川的俗乐器。此时,英祖只好命掌管朝鲜宫廷音乐的逵泰、李延德等人重新校正笙簧的音律,以保证到皇家祭祀用乐的规格和范式。次年,英祖又派遣朝鲜乐工黄世大前往燕京学习笙簧,命李延德再次前往燕京去学习雅乐。据《英祖实录》载:上问延德曰:“曾闻管声甚微,今则能得合笙之妙。 而顷者使臣所得来合笙之石,可用之否乎?”延德曰:“今者管声稍胜于前,而音律犹不合矣。”上命典乐,吹笙簧,曰:“予闻彼国笙簧,声甚訇亮,而此笙之声,极低微,可更厘正乎?”逵泰对以不能。延德曰:“笙声甚微,律亦参差,不可仍置。”上问典乐曰:“李延德慨然有厘正之意,汝其与延德校正其音律差误者。”(6)《英祖实录》(54),英祖17年9月6日戊辰年,清朝乾隆6年,1741年。出自中国科学院、朝鲜科学院合编:《李朝实录》,北京:中国科学出版社,1959年。
但是,英祖对唐琴和笙簧的音律并不满意,声称“以我国唐琴笙簧不成声,命乐工随燕行者,学其音以来。”(7)《英祖实录》(106),英祖41年11月2日癸酉年,清朝乾隆30年,1765年。出自同注⑥。1765年,英祖命乐工随燕行使臣洪大容(8)洪大容(1731—1783)字德保,号湛轩,作品《湛轩燕纪》,1765年随叔父洪檍访华。等到中国学习这些乐器的制作及演奏方法,并购买乐器。这便是洪大容在燕行时,格外重视笙簧、唐琴这两种乐器,并对其进行细致的观察和记录的缘由。洪大容在《乐器》中全面介绍了宴乐用到的六种乐器——笙簧、琵琶、壶琴、洋琴、玄子、竹笛,特别是对笙簧的音色、形制和演奏方法进行了解析:“笙簧乐之首出,而运意最精密,竹音之上品,邃古混沌,已有巧思如此,不可晓也。其管或用十四,或用十七。其长参差,而其律有清浊,簧叶轻薄如蝉翼。其室古用匏,今用木而漆之,或用白铜者尤佳,旁有穴,聚唇而吹之。簧激而出声,故呼吸俱用也。两手拱抱,而诸指分按管穴,随按而声出,不按者,簧虽激,而声不出,气有所泄而不能上出也,或别为曲嘴长尺馀,正坐而含吹之,甚便也。”(9)〔韩〕林基中:《燕行录全集》卷42,首尔:东国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74—475页。他不仅从乐器学上对笙簧的音色进行了深入的描述,而且从演奏角度提出了最佳演奏方案,这对于笙簧乐器的传播和学习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琴铺刘生》中洪大容不仅记录了唐琴的形制和音色,还记录了乐师在刘生的琴铺中购琴、学琴的经过,说明互市贸易是朝鲜使臣了解清代乐器的主要途径之一。洪大容谨记此次来京的重要任务,因此刚到京城便急迫想找到会演奏唐琴和笙簧的人弹奏一曲。正巧上通事使臣李瀷花一百五十两买了唐琴和笙簧。洪大容便将唐琴的形制和音色详细地记录了下来:“琴为蕉叶古制,水晶鹰足,青玉之轸,紫金为徽,拂之声韵清高。问其价,为一百五十两云......刘生运指轻快,音格虽近繁促,具高雅终非玄琴之比......习之十余日,粗得平沙落雁七八段而已。”(10)同注⑨,第89—92页。洪大容及跟随燕行的乐官终不辱使命,成功地学得笙簧和唐琴两种技艺,回国后英祖当即下旨,要求乐师将笙簧和唐琴的演奏方法教给朝鲜的乐工,并要求在教授的时候音律不要繁促,以便学习。见《英祖实录》:“命谢恩正使顺义君、烜、副使金善行同入,上曰:‘一行皆无事往还耶?’善行对曰:‘王灵所暨,皆无事往还矣。’上曰:‘乐师学乐而来乎?’善行曰:‘学之以来矣。’命乐师张天柱,持乐器入吹笙弹琴,各一曲。仍命善教乐工,而声音戒勿烦促。”(11)《英祖实录》(107),英祖42年4月20日己未年,清朝乾隆31年,1766年。出自中国科学院、朝鲜科学院合编:《李朝实录》,北京:中国科学出版社,1959年。毫无疑问,英祖派洪大容及乐官往来于中国和朝鲜之间,这对于丰富朝鲜的乐器种类,完善甚至创新朝鲜乐器的演奏技艺功不可没。同时,通过燕行,还涌现出一批积极学习清朝乐器的音乐爱好者,极大地满足了朝鲜对音乐人才的需求。
唐琴在洪大容的《琴铺刘生》一文中也有详细记载。由于雅乐只有祭祀时才演奏,而一般人又无法进入乐府,故洪大容求助于随行的两位清代官人,询问士人中是否有演奏唐琴者,这才找到了曾是清代乐官的刘氏进行演奏,以此观摩,并与朝鲜朝玄琴进行了比较,肯定了唐琴演奏在技与艺方面的造诣:“李瀷与乐师往访。乐师归言刘生运指快,音格虽近繁促,其高雅终非玄琴之比。”(12)〔韩〕林基中:《燕行录全集》卷49,首尔:东国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9页。洪大容回到朝鲜之后,不仅将所学的唐琴技法传授给了朝鲜琴人们,同时也在朝鲜朝掀起了一场中朝乐器合奏的变革,洪大容还在清代学习了有关于铜弦琴的调制方法,将唐琴与朝鲜乐器伽倻琴进行合奏,发现二者琴韵相合,音色优美,受到了朝鲜人们的喜爱,不仅如此,朝鲜的琴人们也纷纷效仿洪大容将唐琴与朝鲜本土的丝竹类的乐器进行合奏,取得了很好效果。这种将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的乐器合奏的做法在当时可以说是非常大胆和前卫的,开辟了朝鲜音乐创新发展的道路。
此外,朝鲜使臣在燕京滞留期间还大量学习了西方乐器。西方的管风琴对使臣们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他们对管风琴的发声原理、形制、声音记载得较为详细,指出管风琴有数百根音管和琴弦,外表华丽,该乐器是运用鼓风装置来发声的,演奏时需要一人按键一人鼓风来发声,管风琴的音色独特富有变化,音量磅礴大气。在《老稼斋燕行日记》中,朝鲜使臣金昌业(13)金昌业(1658—1721)字大有,号稼斋。作品《老稼斋集》《老稼斋燕行日记》,1712年以子弟军官的身份随长兄金昌集访华。在参观天主堂时,对管风琴声音进行了描述,他将管风琴的声音比喻成风声,如笙簧丝竹之声,所发出的乐声有曲调很动听。由此可见,朝鲜使臣更多地从声音及乐器形制对管风琴进行描述,因其体积比较庞大,使臣们只在南堂内见到此乐器。从记载中可知,南堂毁于乾隆时期,朴趾源来到北京的时候,未能亲眼见到堂内的管风琴,只能凭借金昌业、洪大容对管风琴的回忆来想象管风琴。洪大容在《吴彭问答》中,还有这样的记载:当洪大容得知吴永感为太常寺少卿时,立刻提出希望能听他演奏一曲雅乐,但是彭具庆却替吴永感说那是乐官的事,况且雅乐是祭祀的时候演奏的,平时不演奏;洪大容继续问到有没有练习的地方,想要去看看,彭具庆解答说乐官们在内务府的乐府练习演奏,那里是不能进的。洪大容的一系列询问不仅说明他对中国音乐的好奇与热爱,更能反映当时朝鲜朝音乐与清代音乐的差距。洪大容根据燕京体验发表了《燕记》,他在《刘鲍问答》一文中,对管风琴的制作及发声原理进行了解析,并且用弹奏玄琴的方法试着弹奏了一曲:“余请一听其曲,刘言解曲者方病不可致,略以指按橛而发声,以示其法,余仍就而按之,察其声与玄琴棵律略相合,始知玄琴设棵,虽为东方陋制,其盈缩分律,亦有所本也,乃依玄琴腔曲,逐橛按之,略成一章,笑谓刘曰,此东方之乐也,刘亦笑而称善,余仍说其引风发声之机以质之。”(14)同注释,第35—36页。
总之,朝鲜使臣详细记录有关乐器的信息并与中国文人的交谈记录,以及沿途所记的清代宫廷音乐和西方东传的西洋乐器,其影响是相当深远的,这直接促进了朝鲜后期音乐的改良与发展。同时,清代的乐器传入朝鲜后,与朝鲜王朝本土的乐器进行搭配合奏,为中朝两国乐器的合作提供了机会,清代宫廷乐器作为清代中朝文化交流的纽带,推动和影响了朝鲜音乐的发展。
三、清代戏曲音乐的体验与传播
《燕行录》中记载的宫廷音乐主要包括祭祀乐、朝会乐、宴飨乐和卤簿乐,而戏曲音乐则多属于清代宫廷与民间共同流行的艺术形式。文献中对于清代戏曲音乐及乐器的记录颇丰,无论是燕行使臣沿途的观摩还是进宫参加朝贡都看到戏台的存在,这足以证明当时戏曲在宫廷与民间都占据重要的位置。朴趾源在《戏本名目记》中详细地描述了乾隆朝万寿节时,在热河行宫隆重举办的戏曲表演。据记载,为乾隆祝寿修建的戏台结构精巧细致、豪华壮丽、可容纳千人:“八月十三曰乃皇帝万寿节,前三曰后三曰皆设戏。千官五更赴阙候驾,卯正入班听戏……另立戏台于行宫东,楼阁皆重檐,高可建五丈旗,广可容数万人。设撤之际,不相罥碍。台左右木假山,高与阁齐,而琼树瑶林蒙络其上,剪彩为花,缀珠为果。”(15)〔韩〕林基中:《燕行录全集》卷56,首尔:东国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60页。
《戏本名目记》记录了庆贺乾隆七十岁诞辰时上演的八十部戏本名目,并指出,这些戏都是用羽调倍清演唱,伴奏乐器为笙箫箎笛钟磬琴瑟八种乐器,乐律高亢如出天上,没有鼓,但是偶尔有叠钲。这与朴思浩在《万佛楼记》中记录的伴奏乐器一致。朴趾源记录的戏曲内容和戏本名都为研究清朝宫廷戏曲艺术提供了宝贵的史料。除了皇宫进行戏曲演出以外,朴趾源还描述了当时民间戏台的形状和规模,并且还特意强调了前来观戏的人很多,无论老少,凡是女子都盛装出席,说明当时戏曲艺术在民间音乐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如“寺观及庙堂对门必有一座戏台,皆架七梁,或架九梁,高深雄杰,非店舍所比。不若是深广,难容万众。凳卓椅兀,凡系坐具动以千计,丹腹精侈……尝于古家铺道中,车乘连络不绝,女子共载,一车不下七八,皆凝妆盛饰。阅数百车,皆村妇之观小黑山场戏,日暮罢归者。”(16)同注释,第67页。
金景善(17)金景善(1788—1853)字汝行,号汝文。作品《燕轩值指》,1832年作为书状官出使中国。在《场戏记》中不仅介绍了戏台的布置、戏班的组成以及表演的场景等,还详细地描述了清代戏曲表演者的形象、剧情以及演奏人员的编排等。金景善用“乐律高孤亢极,上下不交,歌声太清而激,下无所隐”来形容清戏曲伴奏的音乐,这与朴趾源描述的音乐完全一样。金景善通过观察发现,在中国所看到的戏曲最初为民间艺术形式,明末时期最为兴盛,随着时间推移,逐渐传入宫廷。金景善据此将中国的戏曲模式比作朝鲜朝的山棚戏,认为无论中国还是朝鲜朝,宫廷音乐都存在融合民间音乐的过程。
四、清代音乐的传播对朝鲜的影响
朝鲜使臣在记录所见所闻的过程中深受中国音乐思想的影响,以洪大容、朴趾源为首的北学派主张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在以人为本、实用主义的北学思想的影响下,朝鲜朝音乐加速发展。
首先,清代音乐对朝鲜朝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朝鲜朝乐器的完善方面。根据《王朝实录》记载,肃宗(1674—1720)时世子受朝时演奏的曲目都是由中国传入朝鲜的唐乐,运用的乐器还不是很齐备,演奏的曲目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前此朝参鼓吹乐,升座时,奏唐乐《圣寿无疆》,群臣拜时,奏唐乐《太平年》,还宫时,奏唐乐《步虚子》。今世子受朝参鼓吹,量减以定,出宫时,用唐乐《五云开瑞朝》,用尾后,群臣拜时,奏唐乐《水龙吟》,入宫时,奏唐乐《洛阳春》。其乐器、工人之数,方响本二仍旧,唐琵琶本六减二,洞箫、牙筝、大筝各二仍旧,觱篥六减二,唐笛四减二,大笒四减二,杖鼓八减四,鼓一仍旧,工人从乐器数用二十五人,服色亦仍旧。”(18)《肃宗实录》(60),肃宗43年7月28日庚辰年,清朝康熙56年,1717年。出自中国科学院、朝鲜科学院合编:《李朝实录》,北京:中国科学出版社,1959年。
到了清乾隆43年,正祖召见掌乐提调李重祜、金用谦、判中枢徐命膺商议乐器、乐曲、演奏等乐制,此时朝鲜的音乐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
第一,朝鲜现有乐器得到了整理,并按照雅乐与俗乐的形式将乐器严格划分为:黄钟磬(相当于编钟)、灵鼓、路鼗、笙、箫、埙、篪、籥、篴、柷、敔、缶、节鼓、钟、磬、玄琴(根据唐琴改良而制)、伽倻琴、琵琶、牙筝、奚琴、大笒、觱篥、唐篴、洞箫、太平箫、杖鼓、方响、小金、大金、建鼓、朔鼓、雷鼓。虽然暂时还没有特钟、特磬、宙鼓和路鼓,但是用黄钟磬和路鼗等其他乐器可以代替之。
第二,对乐工的管理进一步规范,乐工和乐生的人数有了很大的增长,演奏俗乐的乐工一百六十八人,演奏雅乐的乐生九十名。可见此时宫廷音乐的演奏者人数已经远远超过肃宗时期。对典乐、乐师、乐工、乐生的任用制定了一套严格的规定,如典乐由本专业中最优秀的人担任,乐师由曾经的乐工担任,乐工由官奴担任,乐生由旧乐工的儿子担任,选任制度已经相当完善。
第三,对雅乐与俗乐的演奏场合及乐制有了严格的规定。确定宗庙用俗乐,社坛、南坛、大报坛、先农、先蚕、文庙用雅乐。雅俗乐舞虽然大体相同,但是节奏完全不同,佾舞也有所不同。可以看出此时乐器的种类以及乐工、乐生的人数已经基本达到宫廷音乐的要求,雅乐与俗乐也已经被明确划分,说明通过燕行使臣的不断努力,朝鲜宫廷音乐已经有了质的飞跃。
其次,清代音乐对朝鲜朝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对其乐器的完善,更多的是对朝鲜朝音乐思想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当时儒家思想被朝鲜统治阶级敬仰和推崇,在他们看来,宫廷雅乐有利于捍卫传统的朱子理学,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对维护皇权至上的政治制度以及尊卑有序的等级制度也有重要作用,因此朝鲜过去一直保持着雅乐为中心的音乐思想。直到“北学派”的产生,彻底打破了朝鲜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观念,大众音乐逐渐参与其中,开始探索雅俗音乐融合之路。
洪大容和朴趾源可谓是朝鲜音乐“雅俗共赏”的倡导者,但两人的出发点并不相同。朴趾源是从宏观的角度提倡雅乐和俗乐能够共同发展,洪大容则是从实用微观的角度将雅乐器和俗乐器合理地编配到一起,但是不管从哪个角度出发,二人都是打破传统音乐思想的先驱。
朝鲜后期宫廷音乐和大众音乐在共同发展过程中,也在不断相互融合,其中雅乐逐渐融入了乡乐,而清代宫廷乐器也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从曾经的宫廷音乐走入朝鲜民间音乐。雅俗乐器能够融合发展要归功于洪大容,他主张音乐的实用性,提倡宫廷音乐与民间音乐共同发展、相互交融。因此,他勇于创新、大胆尝试,把在清朝学习的铜弦琴、唐琴与朝鲜的丝竹、伽倻琴等乐器一起合奏,呈现出另一番和谐的音响。与洪大容不同,朴趾源刚到沈阳时就看到有人用雅乐器笙簧演奏民间曲调,认为清代笙簧已经完全融入民间音乐当中,这一经历为朴趾源的音乐思想提供了现实依据。他强调解放思想,希望音乐不只是被统治阶级所使用,打破“程朱理学”思想对音乐的禁锢。更加注重雅俗之间的转化与沟通,摒弃雅俗的对立,渐渐模糊雅俗之间的界限,扭转复古、摹古的恶劣风气,实现雅俗共赏的音乐局面。
随着“雅俗共赏”观点被朝鲜后期文人普遍认可与践行,燕行使臣带回的清朝乐器、乐谱、音乐理论越来越丰富,朝鲜的音乐机制也在不断地完善。随着西洋音乐的流入和朝鲜自我意识的觉醒,使臣们开始认识到中国和朝鲜的地理风俗迥异,音乐领域的学者开始逐渐关注乐器、音乐理论和乐谱方面的独立价值,并在肯定中国音乐的基础上也进行批评,仔细推敲和品评其科学性与实用性,认为不能盲目照搬中国的音乐器物、音乐图谱和理论,开始提出自己的音乐见解。洪大容否定清代传入的“审声法”(19)审声法:根据阴阳五行说而来,通过人声定12声律。“候气法”(20)候气法:汉朝的易学者以及音律学者利用一年12节气定的音律理论。“累黍法”(21)累黍法:用竹子做的律管里装进黄米来定律的方法,在海州生产的黄米粒的长度设为1分,10粒为1寸,做出的黄钟律管是长度为9寸的黄钟管。就是一例。清代有关黄钟管的算法主要有审声法、候气法和累黍法。但洪大容从客观科学的数理角度准确揭示了律管的长度,对这三种算法都进行了否定:第一,人声发音部位不同,例如喉音和唇音是不一样的,古今的审声标准也就不同;第二,候气之法中的气是不稳定的,是根据自然环境而变化的;第三,黍的排列方法各不相同,有横、竖、斜三种方法,况且黍的大小也是因地理原因而有异同。据此他否定了清代的黄钟管律算法,提出用科学的方法来进行测量,用长度为九寸,空围面积为九分的管,以三分损益之法得出准确黄钟管律。之后洪大容还结合自己所学,写下了为音乐乐器、乐律正名的《律管解》《羽调界面调之异》《变律》《黄钟古今异同之疑》等文章,为朝鲜音乐理论增添了光辉的一笔。朝鲜后期实学家丁若镛的音乐观点深受洪大容的影响,他致力于如何克服以中国为中心的音乐论,尤其是音律方面。但是他具有非常理智的判断能力,对洪大容肯定的“三分损益法”和“隔八相生法”展开了大量的论证,还对中国音乐著述进行了客观的剖析。
结 论
《燕行录》作为研究中朝交流的重要文本,引起了“域外汉籍”文献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们的关注。专家学者们开始注意国家民族意识、区域文化认同、东亚文明对话、想象与历史记忆、文化往来影响等新问题。而《燕行录》恰为这些新的历史观念和观察视角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燕行录》不仅记录了清代康熙朝前后东亚音乐的多样化发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中国与朝鲜半岛的音乐文化交流的历史面貌,为中国学界进一步研究清代音乐提供了新材料。清代《燕行录》中大量记载中国乐器、西洋乐器、中国戏曲及音乐理论等内容的重要文献,成为恢复和完善朝鲜宫廷雅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朝鲜朝对清代音乐的学习经历了不断吸纳、融合、批判、创新的过程,以洪大容、朴趾源为首的“北学派”文人,在燕行的过程中,通过学习和创新,建构了一套具有“北学实用”特质的音乐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后期燕行使臣们的音乐认知。北学派提倡学习中国以及西方先进文化知识的理念,推动了朝鲜音乐的改革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