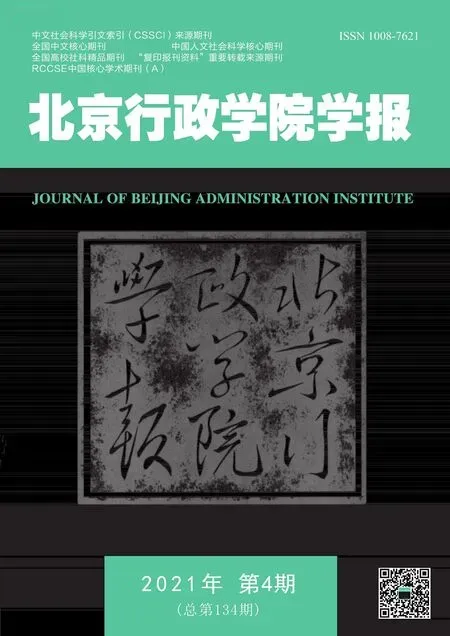珍视马克思作为思想家的视野、原则和品格
——以马克思对俾斯麦“功业”的评价及两人的“交往”为例
□聂锦芳
(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100872)
客观而全面地了解、把握马克思的生平及其思想是讨论马克思主义当代性的前提。遗憾的是,长期以来马克思的形象在某些论者的心目和言说中却是模糊、混乱乃至错位的。诸如,撇开他对资本时代的总体性把握、对历史发展的系统思考和人的解放与未来命运的深入探究,而仅仅将其学说归结为单纯的政治理论,或者鉴于马克思是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大部分纲领的起草者、持续关注世界工人运动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而将他界定为一位“政治领袖”。这些做法和意图姑且可以理解,但实际是不到位和偏离意旨的。在生活中,马克思本人不仅无意进入“政治家”的行列,而且对这一阶层是有自己独特看法的。就其一生的职业和身份来说,马克思始终是一个学者、思想家和理论家,他有基于这种职业和身份所具有的视角、思路、逻辑和志趣。笔者认为,明确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在本文中,笔者拟根据文献材料简单地对比马克思与俾斯麦关于德国发展思路的差异、马克思对俾斯麦与众不同的评价,以及他们之间有限的“交往”情况,以期从中辨明马克思作为学者、思想家所具有的视野、原则和品格。
一、关于德国统一和发展的两种不同思路
众所周知,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是普鲁士的政治强人。在关于德国发展的问题上,他坚持认为,“德意志的未来不在于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而在于强权”[1]1,并且“只有通过铁和血才能达到目的”[1]1。正是基于此,他被赋予“铁血宰相”(Eiserner Kanzler)的称谓,其中“铁”指武器,“血”为战争。他以超强方式和灵活手段,主导了德国的统一和统一后的初步布局,其间一系列大胆策略和举措的出台,犹如布下让人“猜不透的迷魂阵”,常常出敌不意,却屡屡奏效。特别是在国家统一过程中,俾斯麦精心策划和发动的普丹、普奥和普法三场战争,被认为是最显示其“政治智慧”的“杰作”。
俾斯麦从战略上考量,影响德国统一的首要因素并不在于德意志民族内部各个邦国有无意愿,而在于周围各个国家是否允许。于是,他上位后即着手清理这些阻障。首先,俾斯麦把目标对准位于普鲁士北部、力量较弱的丹麦,但当时仅靠普鲁士自身的力量还是不够的,于是他联合奥地利向丹麦开战,最终迫使丹麦求和。事成之后,他又立即出人意料地着手孤立奥地利。因为他意识到,虽然奥地利也属于德语区,但在统一进程和统一后的德国版图中不能有其一席之地,否则普鲁士一家独大、掌控整个局势的地位就会受到威胁。于是俾斯麦通过与俄、法、英秘密协商,出让微小利益,以确保这些国家一旦普奥战争爆发他们能够保持中立。但是即便如此,要战胜奥地利也是不容易的,于是他又与意大利结盟,确保普鲁士向奥地利宣战三个月后意军能直接参战。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再次让人们跌破眼镜。奥军败北之后,俾斯麦却没有乘胜追击,奥地利的执政者还没有缓过神来,他立即主动与其讲和,并且给予奥地利极为宽容的条件,从而迅速修复了两国关系。这之后,他又把矛头瞄准了对南德意志几个邦国颇有影响的法国。法国是欧洲大国,当时普鲁士根本不具备与其开战的能力,如果与其开战,除了能唤醒德意志民族各邦国之间的高度团结、一致对外,想要抑制法国的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俾斯麦操控普鲁士皇帝威廉一世从柏林远赴巴黎郊外凡尔赛宫,与法国皇帝路易·波拿巴三世会谈,并让其将会谈内容通过电报传回国内。接着,他篡改会谈内容并迅速在报刊上发表,以侮辱性的口吻刺激法国,力图“对‘高卢牛’起到一块红布的效果”[1]108。法国最终中计,仓促决定入侵德国。借此机会,普鲁士团结德意志诸邦,不仅击退了法军,更发起反攻,进入法国境内。至此,德国统一之路上的所有障碍被彻底清除。欲壑难填,一旦措施奏效,俾斯麦是不会停步的。这之后,他继续拉拢英、俄、奥诸国,排挤和限制法国,通过鼓励其把主要精力放在海外殖民扩张,削弱了法国在欧洲大陆的影响,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护了统一后德国的利益。
国家统一后,俾斯麦分出一部分精力处理国内事务。作为统治者,他感到当时国家稳定最棘手的难题和最大的威胁是工人运动。于是俾斯麦一方面通过颁布《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严厉镇压各地的秘密结社、大规模集会等活动;另一方面又督促国会立法,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工人养老金、健康医疗和社会保险制度,奠定和规划了后来被称为“福利国家”的基础和雏形。
这样,俾斯麦通过以上方式而建立的两项伟业彪炳于德国史册。很多人把德国的统一和发展归功于他,甚至连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和理论家、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弗兰茨·梅林(Franz Mehring,1846—1919)也颂扬他是“伟大年代的英雄”“百年一遇的伟人”[2]。而列宁的评论更为我们所熟知,他认为“俾斯麦依照自己的方式,依照容克的方式完成了历史上进步的事业……通过把分散的、受其他民族压迫的德意志人联合在一起,促进了经济的发展”①当然,列宁也指出,俄罗斯与德国存在着“差别”,因此并不需要走“俾斯麦的路”,“大俄罗斯的经济繁荣和迅速发展,却要求在我们国内消除大俄罗斯人对其他民族的压迫——这个差别往往被我们那些崇拜真正俄国的准俾斯麦的人所忘怀”。参见列宁:《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载《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52页。。
但是,必须注意到,以上这些有关俾斯麦的事迹和判断只是站在单一的国家立场和政治角度所做出的梳理和评价。如果转换一下思路和视角,会不会有另外的结论呢?
虽然随着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结束封建城邦割据、实现国家统一成为德国当时的首要任务,但是,以什么样的方式统一是可以有不同方向的考量和多种策略的。俾斯麦选择的是自上而下,借助王朝战争建立统一君主国家的方案。除此以外,至少还可以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先推翻各邦王朝,再建立统一的共和国。现在看来,俾斯麦的方案和举措确实迅速地促成了国家的统一,然而也并不是没有争议的,甚至毋宁说,这遗留下了诸多不良后果乃至严重的“后遗症”。他的政治生涯善始而未能善终,“功勋”卓著的他晚年竟产生了兔死狗烹、心灰意冷之感,于是不得已提出辞呈,提前下野。及至后来,他所奉行的“铁血政策”也变为“专制和战争”的代名词。两次世界大战均由德国发动,并给世界特别是德国自身造成了极为深重的灾难和难以挽回的后果。凡此种种,都或多或少与俾斯麦所确立的德国振兴和发展思路有关,甚至可以看作是他那“巨大的”政治影响的后续效应。
假如将俾斯麦所建立的“功业”置于资本时代世界发展和社会历史变迁的总体视野和格局之中,从人类文明的进程来看,就会得出与以上判断相异的观点。作为政治家的俾斯麦善于把错综复杂的局面简约化,用利益交换拉拢多数以孤立敌人,每次只设定与其实力匹配的有限目标,一击而中,见好就收。特别是他精心策划所布下的让人“猜不透的迷魂阵”等等,常为人们所津津乐道。而从相反的角度看,这些做法其实并不复杂和深奥,不过是功利主导下“不按常规常理出牌”的设计,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变化,是政客们常用的投机伎俩,既是“智慧”,更是狡黠,而在道德、逻辑层面上,更是不值得称道的。在俾斯麦所坚持的国家利益至上的信念背后,隐藏的不过是其最大限度地追逐个人荣耀和权势的自私考量。
马克思正是基于以上视角和立场来评判俾斯麦的。在对德国统一具有关键意义的普法战争结束后,他尖锐地指出:“普鲁士在胜利之后,难道曾有过片刻想要以一个自由的德国去和一个被奴役的法国相对抗吗?恰恰相反。普鲁士细心保存了自己旧制度固有的一切妙处,另外又采纳了第二帝国的一切狡猾伎俩:它的真专制与假民主,它的政治面目与财政骗局,它的漂亮言辞与龌龊手腕。”[3]而恩格斯则更是将俾斯麦的“思维方式和眼界”与资本时代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和看待,他认为,“俾斯麦借以获得成就的一切品质都是商人的品质:用耐心等待和实验的办法去追求既定目标,直到有利时机的到来,为了利益,经常进行后门外交,讨价还价,忍受屈辱,也就是说:‘我们不想当盗贼’,总之,到处都是商人的气质”,“如果注意一下这些大人物的手腕,往往会觉得自己好像是走进了曼彻斯特的交易所”[4]250-251。恩格斯晚年在回顾剖析统一后的德国状况时,再度指出,俾斯麦是“一个头脑十分实际和狡猾的人”[5]486。
显然,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所秉承的信念、价值、道德和逻辑与俾斯麦是完全不能融通的。
二、为什么“俾斯麦会来敲你的门”
至此,我们可以简单梳理一下马克思与普鲁士官方打交道的历程。最激烈的要数1842年至1843年“《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因抨击普鲁士专制主义制度、捍卫作为“具有最高的神性”的自由而遭到驱逐。当然,那时俾斯麦在政治上还未出道,此事与他个人无关。之后,为恢复国籍事宜,马克思先后被迫于1845年10月、1848年4月和1861年3月三次致函普鲁士内务部,但均遭驳回。俾斯麦是1862年9月才出任普鲁士首相的,所以这些情况也与他没有直接关系。此后,马克思长年客居伦敦,虽然也会对德国国内状况包括政局发表看法,但没有再与政府打过交道。在其经济极为拮据的时候,尽管燕妮的哥哥斐迪南·冯·威斯特华伦一度担任普鲁士内务大臣,但他们甘守贫穷或者宁愿另觅他途,也从未向其请求过任何资助。因为马克思认为,道不同不相为谋,也就不需要与官场有什么来往了。
在作为学者、思想家的马克思认为不能融通的东西、不需要往来的关系,在俾斯麦这样的政客看来却是另外一回事,认为一切都是可以的,也必须改变的。诚如聪明的恩格斯所预料到的,“俾斯麦会来敲你的门”[4]250。
根据笔者所掌握的文献,可以梳理一下此事的大致原委。贵为德意志帝国的宰相,俾斯麦不可能与作为流亡者的马克思公开而直接地进行交往,所以他是通过中间人来沟通的。
第一次交往发生在1865年10月。有一位名叫阿道夫·洛塔尔·布赫尔(Adolph Lothar Bucher,1817―1892)的人,早年曾担任过普鲁士制宪议会议员,因持左翼立场,1848年革命后被迫流亡伦敦,担任在柏林出版的《国民报》驻英通讯员。1860年,在马克思回击波拿巴主义的代理人卡尔·福格特(Karl Vogt,1817—1895)对其的诽谤时,布赫尔曾支持马克思。后来普鲁士对政治流亡者实行大赦(马克思被排除在外),布赫尔返回国内,进入外交部工作。他苦心经营各种关系,得到俾斯麦的器重,曾为俾斯麦与德国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创立者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1825—1864)之间的秘密会见牵线搭桥,还曾受命出使马德里。由于与俾斯麦、拉萨尔过从甚密,在拉萨尔死后布赫尔继承了其全部遗稿,并作为其遗嘱的主要执行人出版了拉萨尔的著作集。俾斯麦下野后,布赫尔也跟随其到乡下庄园,协助俾斯麦撰写了著名的三卷本回忆录《思考与回忆》。
对于俾斯麦这样的政客、拉萨尔这样的“机会主义者”与布赫尔的关系,马克思早就有清醒的认识。1851年8月31日在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说:“他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们投入了那些可尊敬的‘国家要人’的怀抱。”[6]甚至燕妮·马克思在1865年3月30日给恩格斯的信中,也这样说:“拉萨尔已经完全走上了一条歪道,这条歪道把他象他的朋友布赫尔一样引到俾斯麦阵营,引入内阁。”[7]很显然,作为“俾斯麦的心腹侍从”,又与马克思在伦敦有过交流,布赫尔一定也会做点事情的。
德国统一后经济处于起步阶段,俾斯麦政府对现代世界经济状况及其未来趋势毫无了解和把握,作为官方报纸的《普鲁士国家通报》“每月需要一篇关于金融市场(不言而喻,也有商品市场,只要两者无法分开)动态的报道”,那么,谁最熟悉世界经济发展并能胜任撰写这种报道的职责呢?俾斯麦和报纸主办者向布赫尔打听,看他“能否推荐一个人”,布赫尔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没有人比马克思“更适合做这件事了”[8]187-188。于是,1865年10月8日,布赫尔“征得他主子的同意”给马克思写信,邀请其“担任《普鲁士国家通报》的金融问题的伦敦通讯员”[9]491,为报纸撰写文章,“至于内容,不言而喻,您只管依照您的学术信念行事”[8]187,而稿酬条件则由马克思自己决定。马克思在11月21日致威廉·李卜克内西的信中谈及此事,明确地揭露了布赫尔此信的意图,不过是“向我示意,凡是一生中还想对德国有影响的人,就应当‘投靠政府’”[9]491。马克思把布赫尔的做法视为“天真”,尽管当时他的物质生活状况相当恶劣,这个送上门来的好处有助于使马克思的生活马上得以改观,但他压根没有产生这方面的念头,回写了几行文字就坚决拒绝了。
第二次发生在1867年4月。当月10日,马克思为《资本论》第一卷的校对和印刷事宜返回德国,在汉堡及其附近停留,因为事情有所拖延,他这次待了一个多月。其间到了汉诺威,在朋友路·库格曼(Ludwig Kugelman,1828—1902)医生家里做客。俾斯麦不知以什么方式知道了马克思的行程,23日派了一个叫瓦尔内博耳德的律师到马克思住地,转达了他的问候,希望“利用”马克思的名声和“大才为德国人民谋福利”。这只是一种“礼貌性”的拜访,当然不会有什么具体要求和允诺。马克思翌日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了这一情况,指出作为学者的他们与官员在认知和评价上的差异:“我们两个人在德国,尤其是在‘有教养的’官场中的地位,跟我们所想象的完全不同。例如,本市统计局局长梅尔克耳访问我,说他研究货币流通问题多年,但徒劳无功,而我却一下子就把问题彻底搞清楚了。他对我说:‘不久以前,我在柏林的同事恩格尔当着王室的面对你的德奥古利——恩格斯——作了应有的赞扬。’……本地铁路管理局局长也邀请我到他家作客。我去了,他有甘醇的葡萄酒和‘热忱的夫人’,在离开的时候,他感谢我给予他的‘无上的光荣’。”[10]294马克思还说,“这些都是琐事,但是对于我们却是重要的。我们对于这些官员的影响比对庸人的影响要大些”[10]294。
恩格斯收到马克思的信后,于4月27日回复了一封长信。谈及上述情况时,他说:“俾斯麦会来敲你的门,我是料到的,虽然没有想到这样快。这很能说明这个家伙的思维方式和眼界,他总是以己度人。……俾斯麦想:只要继续去敲马克思的门,终究会交上一次好运的,那时我们就共同来做一桩好买卖。这真是道道地地的哥特弗里德·欧门①哥特弗里德·欧门(Gottfried Ermen,1812—1899),与恩格斯父亲在曼彻斯特创办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合伙人。。”[4]250-251
如果说,这两次马克思都是处于“被动”状态,那么,第三次的“交往”算是他“主动”出击了.此事发生在1878年6月。纵横捭阖的俾斯麦称雄乃至主宰世界的野心愈益显露。为了平衡英、俄与奥匈帝国的利益并重建巴尔干半岛秩序,当月俾斯麦邀请欧洲列强与奥斯曼帝国在柏林开会。这就是在欧洲外交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柏林会议(Ber⁃liner Kongress),作为外交参事的布赫尔“被任命为会议的秘书兼档案官”。在伦敦,马克思、恩格斯看到路透社关于此事的电讯报道,愤慨于自己的祖国“到处进行的引起人心惶惶的搜捕和报界爬虫的喧嚣扬尘,都是为了制造舆论”,他们看出“俾斯麦公爵长期以来精心谋划的方案……既要使德国政府享有一个现代国家的全部财源,同时又要重新迫使德国人民接受被1848年风暴摧毁了的古老政治制度”[11],于是在12日联名给《每日新闻》编辑写信,揭露了布赫尔当年联系他的勾当。此信很快便被刊发出来。
布赫尔立即做出回应,于21日在《北德总汇报》上发表了一项《声明》,抱怨德国民族自由党和进步党的报纸转载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是“一个令人不愉快的情况”,同时声称那封信有“一大堆歪曲”需要“纠正”,“必须写3000行文字”。马克思自然不甘示弱,于27日写下《答布赫尔的<声明>》,公布了布赫尔原信的几段原文,称用“30行文字就绰绰有余”,可以“一劳永逸地确定布赫尔所做的‘更正’和‘补充’有几分真实性”[12]。为了写作上述答词,马克思还于25日写信给英国《自由新闻》主编与发行人科勒特·多布森·科勒特(Collet Dobson Collet,1812—1898),索要和复核资料,以便揭露布赫尔“用无耻的谎言为自己辩解”[13]的企图。这封信的原件现为我国中央编译局独家收藏。
三、马克思的善良和温情
不仅如此,马克思与俾斯麦之间通过中间人沟通但实际上没有产生任何“效果”的所谓的“交往”还有后续“花絮”。如果说,以上所述两人之间在德国统一与发展思路上的差异、马克思对他们邀请“合作”“衷心问候”的拒绝和冷淡,充分展示了马克思所具有的世界视野、独立思考和坚定原则,那么,以下所述事情的处理方式又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学者、思想家在品德上的善良、温情和高洁。
前文提过,布赫尔于1865年10月8日写信给马克思,邀请其为《普鲁士国家通报》撰稿,遭马克思拒绝后,马克思在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作为同道向其披露了此事,但同时特别叮嘱说:“不必在报纸上公布这件事,但是你可以私下告诉你的朋友们。”[9]4911867年4月23日,俾斯麦派瓦尔内博耳德到马克思住地转达问候,马克思在第二天写给恩格斯的信中做了通报,但同样嘱咐恩格斯说:“不要告诉别人”,还特别写了斜体字以示强调[10]294。5月7日在给恩格斯的信中,他再次告诫说:“关于俾斯麦那件事你千万要完全保密。”[14]那么,马克思为什么要反复这样做呢?可能的解释是,他考虑到,虽然坚决地回绝了与俾斯麦的合作和来往,但顾及是其主动“示好”以及两位中间人的“辛劳”,所以不必要把这种“驳面子”的事到处传扬。如果不是后来俾斯麦和布赫尔在“柏林会议”上表现得不可一世,他是不会主动重翻旧账的。那样的话,他们之间的这两段“交往”是会作为“隐私”被尘封起来的。这是马克思为人的厚道、心善之处。
更能说明问题的还有一则轶事,发生于1867年5月。在完成《资本论》第一卷的校对并督促付梓后,马克思从汉堡坐轮船回伦敦。在船上,一位带有“军人风度”的德国小姐引起了他的注意。在快到伦敦渡口时,马克思到船舱上透气,看到她已经提前把一大堆行李搬到甲板上。她告诉马克思说,当晚要从伦敦到维斯顿-修珀-梅里去,因带的东西很多,并且对伦敦又不熟悉,而情况更为糟糕的是,在英国星期六很难找到搬运工人,所以她不知该怎么办才好。马克思问她到伦敦后要去的火车站,她把一张由朋友在上面写着车站名称的名片递给马克思,是伦敦的西北火车站。马克思正好也要经过那里,于是,他“像一个真正的骑士那样”提出由他送这位女士到约定的地点去,她接受了马克思的建议。随后,返回船舱的马克思仔细一想,印象中维斯顿-修珀-梅里是在伦敦西南,而他要经过的这位小姐名片上写的车站却在西北。把握不准,马克思便去请教船长,结果弄清楚了,她该去的那个地方确实不是马克思要经过的地方,而是恰好完全相反。不过,马克思想,既然已经提出愿意效劳,当然只能勉为其难,先把小姐送到西南车站,他再折返一段路回家。下午二时,在渡口下船。马克思直接携带行李,伴送这位小姐到她要去的车站。到达之后才知道,火车要到晚上八点才开。这位小姐在伦敦举目无亲,形单影只,显得有点可怜,这样,马克思又不得不和她一起消磨掉剩下等待的时间。他们在存了行李之后,先在海德公园游逛了一番,又去吃了冰激凌等。在闲聊中,她告诉马克思她叫伊丽莎白·冯·普特卡默,是位高权重的德国宰相俾斯麦的外甥女,且刚刚在柏林其官邸住了几个星期。她给马克思留下的印象是,她是“一个愉快和有教养的女孩子,但是连鼻子尖上都带有贵族气味和黑白色彩”①黑和白是普鲁士国旗的颜色。。当然,她也询问了马克思的名字,当她知道与其在一起、陪伴她的是谁的时候,她感到“不胜惊讶”,因为她一方面知道舅舅非常看重马克思,另一方面又了解马克思是因言论激进而被驱逐出国的,而现在她竟然与他一起待了大半天。马克思和蔼地安慰她说,“我们的会见不会发生‘流血事件’”,最终平安无事地送她上了车。事后,马克思把这件事情详细地告诉了自己在德国国内的朋友,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有一部分人是马克思的反对者,于是马克思在叙述完事情经过之后幽默地说:“你想想看,这该会给布林德和其他庸俗社会民主党人一个多么好的把柄:我同俾斯麦有秘密勾结!”[15]
诚如恩格斯所言,作为一个在思维方式、价值追求和理论体系方面具有革命性变革的“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16]。
结语
以上事实不见诸德国官方档案、正史稗官以及俾斯麦的传记,而是记录在马克思与他人的通信之中。最近,笔者在系统地梳理1867年至1883年间马克思的理论创作和实践活动,当翻阅到这些分散的文献材料,进而追踪、连缀而成线索,并勾勒出相对完整的事件时,愈加钦佩马克思的思想和为人,感到自己对马克思的理解也更为具体和深入了一些。用心体会马克思当年的思考和选择,会很自然地与当代人的作为和见解做对比,于是就生发出这样的感慨:我们号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与马克思的境界和水准相比,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笔者认为,这与人们不认真学习经典原著和丧失独立思考能力有关。
由此也愈加显现出马克思的视野、原则和品格。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当今时代值得学者们倍加珍视和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