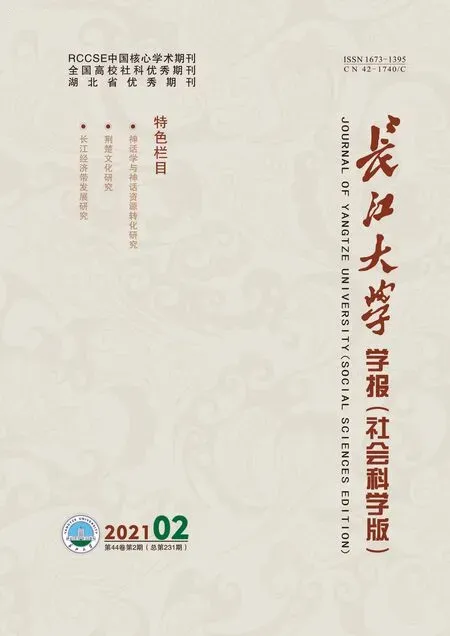清代女性诗人对《红楼梦》“昭君诗”的接受
杨勇
(三峡大学 期刊社,湖北 宜昌 443002)
《红楼梦》打破了传统的思想和写法,自问世以来,一直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所谓“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红楼梦》的传播和流行,对后世小说和诗词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红学家关注《红楼梦》对女性文学创作的影响,大多是在题红诗、咏红诗上,如周汝昌《买椟还珠可胜慨——女诗人的题红诗》[1](P993),傅天《咏红诗略谈(下)》[2],王力坚《清代才媛红楼题咏的型态分类及其文化意涵》[3]。近年来,有研究者注意到了《红楼梦》在女性诗人实际创作中的接受情况,如胡健将清代女性的咏菊诗纳入《红楼梦》文化研究的视野,探讨了乾嘉以来的闺秀诗人对《红楼梦》咏菊诗的模仿和超越[4]。其实,不只是咏物诗,《红楼梦》中的咏史诗,比如咏昭君诗对清代女性诗人的影响也值得关注。
《红楼梦》中的咏昭君诗共有两首,一是薛宝琴新编怀古诗之七《青冢怀古》:“黑水茫茫咽不流,冰弦拨尽曲中愁。汉家制度诚堪叹,樗栎应惭万古羞。”一是林黛玉所作《五美吟》之三《明妃》:“绝艳惊人出汉宫,红颜命薄古今同。君王纵使轻颜色,予夺权何畀画工。”《红楼梦》旨在“使闺阁昭传”,字里行间充溢着对女性的理解、同情和悲悯之情,引起了当时女性读者的强烈共鸣,她们读红楼、评红楼,甚至续红楼,形成了独特的闺阁红楼文化。清代女性诗人对《红楼梦》咏昭君诗的接受,不只是对其诗句的简单模仿和艺术形式的借鉴,还表现在对其批判精神的继承,更重要的是,她们对《红楼梦》咏昭君诗的超越和创新。
一
“昭君出塞”是一个重要的文学母题,历代文人墨客歌咏昭君的诗篇不绝如缕,可咏雪、戴其芳等人所编《历代吟咏昭君诗词曲》(全辑·评注)收录1333首(1)可咏雪、戴其芳等《历代吟咏昭君诗词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本文所引昭君诗原文,除特别注明以外,均出自此书。。
在数以千计的以昭君出塞为题材的诗词中,男性诗人占了绝大多数。他们大多以代言体形式,以昭君自拟,抒发了出塞之苦、远嫁之悲、乡国之思或明珠暗投之怨等。今见历代吟咏昭君诗词中,女性诗人的诗作并不多,尤其是清代以前更是屈指可数,比较重要的有:南朝梁·刘绘女的《昭君怨》、梁·沈满愿的二首《昭君叹》、隋·侯夫人的《遣意》、唐·梁琼的《昭君怨》、明·沈天孙的《明妃》等等。这种情况,到了清代有了很大改观。笔者据《历代吟咏昭君诗词曲》一书统计,清代女性诗人黄幼藻、徐德音、陈葆贞、蔡泽苕、万梦丹、张英、方婉仪、李含章、葛秀英、周秀眉、金颖第、郭漱玉、郭润玉、郭秉慧、王端淑、秋瑾等,共创作了21首咏昭君诗。
清代闺阁文学兴盛,很多闺阁诗集中的咏昭君诗尚未收入此书,比如:杨琼华《绿窗吟草》中的《题明妃出塞图》、谢香塘《红馀诗词稿》中的《明妃》、闵肃英《瑶草轩诗钞》中的《昭君曲》、李纕蘅《梦余吟草》中的《昭君》、杨惺惺《吟香摘蠹集》中的《明妃》,等等,不一而足。有清一代咏史诗中的“昭君热”,不仅体现在清代咏昭君诗的创作总量激增,亦表征为清代女性诗人对昭君命运的关注、同情、体认以及咏昭君诗的创作热情。与男性诗人的代言体不同,她们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展示其才智、诗情和史识,其咏昭君诗近年来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2)如张海燕、赵望秦《清代女性作家咏昭君诗探析》,《古典文学知识》2013年第1期;王颖《浅析清代女性诗人笔下的王昭君形象》,《社科纵横》2019年第9期。南昌大学王丹丽硕士论文《清代女性咏史诗研究》辟有专节介绍清代女性作家的咏昭君诗。
由于“三从四德”的道德约束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桎梏,封建社会才女们大多湮没不彰。清代闺阁诗人有些生平无考,生卒年不详,但根据志书记载、诗集提供的诗人交游信息和有关研究成果可以推断,上述所列吟咏昭君的女性诗人大多生活在乾嘉以后。
这与《红楼梦》的风靡一时不只是巧合。沈善宝(1808—1862)在为《红楼梦影》作序中提及:“《红楼梦》一书,本名《石头记》……此极奇幻之事,而至理深情,独有千古。……几至家弦户诵,雅俗共赏。”[5]可见当时《红楼梦》所受欢迎的程度。而《红楼梦》甫一问世,即引起了女性诗人的关注和评论。如乾隆朝宋鸣琼的《题红楼梦》四首[6](P427),被学界公认为最早的咏红诗。诗人们有的还通过诗歌唱和来交流读红感受。张问端之女丁采芝作诗《夏夜阅红楼梦偶作》:“焚香开卷月波流,替尔酸心不自由。魂到难消空洒泪,情原无种却生愁。潇湘馆阁悲妃子,金玉因缘误石头。自古繁华皆是梦,何须惆怅说红楼。”女儿陷溺于红楼的状况引起了她的担忧,张问端于是作了一首和诗:“奇才有意惜风流,真假分明笔自由。色界原空终有尽,情魔不著本无愁。良缘仍恨钗分股,妙谛应教石点头。梦短梦长浑是梦,几人如此读红楼?”(3)见《清代闺秀集丛刊》第24册第3种丁采芝《芝润山房诗词草》,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影印本,第460页。张问端和诗见《国朝闺秀正始续集》卷六,第260页。和诗和原诗是红学研究的重要资料,得以保存,实乃幸事。
《红楼梦》第64回作者借薛宝钗之口道:“做诗不论何题,只要善翻古人之意。若要随人脚踪走去,纵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义,究竟算不得好诗。即如前人所咏昭君之诗甚多,有悲挽昭君的,有怨恨延寿的,又有讥汉帝不能使画工图貌贤臣而画美人的,纷纷不一。后来王荆公复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永叔有‘耳目所见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二诗俱能各出己见,不与人同”。《红楼梦》共有5处涉及昭君,小说人物创作了两首咏昭君诗,作者通过人物之口对历代昭君诗进行总结和点评,并以昭君诗为例阐述诗贵创新的诗学主张,凡此种种,足见作者对昭君故事和昭君诗的偏爱。在阅读《红楼梦》文本的过程中,女性诗人以其敏感而细腻的心理捕捉到这一现象,引起对《红楼梦》咏昭君诗的重视,并在诗歌创作中对其特有的女性视角和悲怨主题予以接受,实在是情理之中的事。
清代女性诗人对《红楼梦》咏昭君诗的接受,一个明显的证据是诗句的化用。且对比下面两首昭君诗:
绝艳惊人出汉宫,红颜命薄古今同。进退权偏付画工,红妆千古怨秋风。(曹雪芹《明妃》)
君王纵使轻颜色,予夺权何畀画工。君王事事能亲理,那见琵琶出汉宫。(蔡泽苕《昭君》)
两首诗用韵相同,无论是遣词,还是立意,都可以看出后者对前者模仿的明显痕迹,特别是“进退权偏付画工”简直是“予夺权何畀画工”一句的翻版。当然,两首诗的侧重点还是有所不同:《明妃》由昭君悲剧的普遍性出发,揭示女性婚姻悲剧的根源在于没有自择婚姻的权利[7],而《昭君》则由对昭君悲剧的同情,归结到对元帝按图召幸的批评。两相对比,境界之高下立判。
二
在诗歌内容方面,清代女性诗人首先承袭了《红楼梦》咏昭君诗的悲怨主题。现存最早的昭君诗是《怨旷思惟歌》(托名为王昭君所作),该诗描写了昭君的出身、入宫、怨旷、出塞、思乡等多方面内容,奠定了昭君诗歌的悲怨主题。东晋石崇《王明君辞并序》是第一首文人昭君诗,亦以昭君“哀怨”为主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昭君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红楼梦》中的两首咏昭君诗虽然是对历代昭君诗悲怨主题的沿袭,但出之以女性作者的特殊视角,反映了女性的自我审视;更重要的是,第一次把昭君悲剧放在“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宏大历史背景下进行观照,分别从人和制度的层面进行了社会的反思和历史的追问,具有更加深广的意义。随着《红楼梦》的广泛流布,清代女性诗人在对小说文本的接受过程中,这种女性意识和批判精神无疑会影响到其昭君诗的创作实践。
李纕蘅的《昭君》诗云:“琵琶声冷漠云横,太息红颜作远征。一向玉门关外去,可怜不复问归程。”[8]继承了历代昭君诗“怜其远嫁”的传统主题,表达了对昭君远嫁大漠的同情,这或许与诗人远嫁异乡的经历不无关系,怜昭君亦是自怜也。
闵肃英的《昭君曲》:“玉颜已逐尘沙老,青冢千年怨春草。当时不自买丹青,死后何缘惜枯槁。琵琶调好无睽隔,汉使犹传出塞拍。长门湿尽阿娇衣,秋雁一声天地白。深闺十五盈盈女,不识黄云在何许。谱得清声欲断肠,日高无人作新语。岂知凄凉未忍说,青冢黄昏照明月。”(4)见蔡殿齐编《国朝闺阁诗钞》第六册卷一。诗人通过“琵琶”“长门”“秋雁”“明月”等意象的营造和“怨”“惜”“断肠”“凄凉”等词汇的运用,表达了对昭君悲苦命运的深切同情。
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成立,并于9月正式开学。闻一多被聘为该校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臧克家正是在此受业于闻一多。在青岛大学,闻一多发表了专攻中国文学的第一篇考证论文,并制订了长远的唐诗研究计划。其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从上述所举诗作来看,在表现昭君悲怨时,女性诗人们并没有简单地模拟前人,而是融入了自己的思考,有着切身的感受和真挚的情感,其批判意识则与《红楼梦》咏昭君诗一脉相承。
明人李东阳曰:“如《明妃怨》谓古人已说尽,更出新意。予岂敢与古人角哉?但欲求其新者,见意义之无穷耳。”[9]以《明妃怨》为例,主张诗歌的创作要有新意。历代吟咏昭君诗词的悲怨主题已被“古人说尽”,况且有《红楼梦》这座难以逾越的巅峰在前,清代女性诗人的咏昭君诗要想突出重围,必须开拓新的主题。
李含章的长诗《明妃出塞图》描写了多方面的内容:塞外恶劣的环境、和亲政策的由来、昭君见识超凡及其精神不灭。诗人采用“自请和亲”说,对昭君超出常人的见识、勇气和功绩表达了无限崇拜之情。诗歌的开头似乎定下了凄苦感伤的基调,与其它咏昭君诗略无二致,其实是为了反衬出昭君的伟大。结尾写昭君墓前草色青青,故乡香溪碧水红花,以优美的景色象征昭君精神的不可磨灭,一扫历代文人那种凄凉哀婉的悲苦情调。
周秀眉的《昭君》是一首昭君的颂歌。传统观念认为,和亲息戈止兵,带来了汉家边境安宁,而女诗人却着眼于和亲带来的匈奴社会繁荣,可谓独具只眼。琵琶反弹,认为昭君出塞不是悲苦的事情,而是建立了不世之功勋,这在清代女性诗人中并非个例,它如郭润玉的《明妃》、张英的《昭君二首》之二等。
清代女性诗人屡屡写道:“千载壮君名”“论到边功是美人”“应让娥眉第一功”“赢得千秋不朽名”“要令青史夸名姝”等等,对昭君和亲的历史功绩不吝赞美之词,这是对历代昭君诗悲怨主题的反拨,是昭君诗歌史上少见的现象。千百年来男性诗人以代言体的诗歌不断书写昭君的悲怨,实则以昭君故事为载体,抒发其怀才不遇的情绪而已;而正视和亲史实,对昭君出塞予以正确评价的任务最终由女性诗人来完成,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诗人笔下流露出强烈的功名意识,反映此时女性的自主意识已开始萌发,她们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将女性的意义提升到与男性相同的地位。李含章诗中议论道:“大抵美女如杰士,见识迥与常人殊。”折射出女性的觉醒和自我认同。早在晚明,思想家李贽就曾大胆提出男女平等的观点,其《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云:“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10](P59)女性的觉醒更重要的是受到清代妇女解放思潮的影响。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指出:“清代学术之盛,为前此所未有,妇女也得沾余泽,文学之盛,为前此所未有。”[11](P257-258)女性作家不仅数量激增,远超前代,而且她们往往跳出吟风弄月、春思秋怨的局限。譬如写“大抵美女如杰士,见识迥与常人殊”的李含章长于写咏史诗,抒发所感,爱憎分明,毫无脂粉气,被袁枚誉为“一代闺秀之冠”,认为其诗“见解高超,可与三百篇并矣”。
三
在诗歌的呈现形式方面,清代女性诗人对《红楼梦》咏昭君诗亦有所借鉴。
1.组诗的形式,增强了情感冲击力
《红楼梦》中的咏昭君诗《明妃》是《五美吟》组诗之一,组诗从历史的向度对封建时代女性的婚姻悲剧进行了审美观照,对女性的自我觉醒进程进行了如实书写。[7]这一组诗对读者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冲击力和震撼力,具有单首诗歌所不具有的集束效应。《红楼梦》之前虽然已经出现了一些吟咏历代美人的组诗,如明·张元凯的《四美人咏》、清·鲍皋的《十美诗》等等,但与《红楼梦》相比,无论是艺术成就,还是对后世的影响,它们都难以望其项背。清代一些女性诗人借鉴了《红楼梦》这种组诗的呈现形式。
万梦丹的咏史诗很大部分是吟咏历史上的著名女性,《豫章闺秀诗钞》选其七,即西施、昭君、文君、文姬、孙夫人、梁绿珠、潘贵妃等,都是悲剧性人物。其中《昭君》:“按图索去太相轻,岂有芳姿绘得成!枉向宫门诛画史,琵琶出塞已无声。”《文姬》:“父倾权相女蒙尘,乱世才人易失身。可惜胡笳传内地,凄凉不似故悼春。”《孙夫人》:“蜀山西望竟难归,婚媾兴戎计更非。一死报君遗恨在,芳邻可许觅湘妃。”《梁绿珠》:“兵端偏起妇人身,金谷园中草不春。一斛明珠楼下碎,芳魂千古化香尘。”[12](P304—312)诗人认为,昭君出塞是元帝按图召幸的轻率做法所致,蔡文姬的颠沛流离是因为生逢乱世,孙夫人之死是政治联姻的牺牲品,绿珠的悲剧是由于石崇斗富引来杀身之祸。姑且不论其观点正确与否,但我们看到诗人对封建时代女性的悲剧命运充满了同情,并努力探寻着女性悲剧的具体成因。把握《昭君》与另外几首咏美人诗的感情联系,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昭君的悲剧其实与画师无关,以及这种悲剧的不可避免性。
2.与其它艺术的结合,增强了诗歌的可接受性
《红楼梦》中另一首咏昭君诗《青冢怀古》乃灯谜诗,怀古之情出之以灯谜,饶有意趣。诗歌和其它艺术形式的结合,令人耳目一新。清代女性诗人的咏昭君诗对此亦有借鉴,只不过是采用了另一种形式——题画诗。
比如葛秀英、杨琼华的《题明妃出塞图》,这两首诗画面感极强,诗画互补,使意境更加深远。方婉仪的《次韵题明妃图》对昭君和亲的“幸”与“不幸”,有着诗人自己的思考。诗题曰“次韵”,说明另有人作明妃题画诗在先。
据《清代闺阁诗人征略》记载,清代女诗人工诗善画可谓“常态”。良好的绘画素养体现在咏史诗中就是对画面传神的表现,尤其体现在对于专属闺阁诗人的美人图题咏上。作为咏史诗的一部分,这种题画诗使得历史人物和历史现场如在目前,提高了诗歌的生动性,读者更易于接受。
应该指出的是,这种题画诗固然受到了《红楼梦》灯谜诗的影响,却也是渊源有自。清人胡凤丹所编《青冢志》卷十为“昭君图画”,即题画诗。笔者据此统计,历代以这种形式歌咏昭君的诗人有:宋5人,元15人,明18人,清39人。“昭君出塞图”是清代女性咏史诗中被吟咏得最多的图画。
不仅是题画诗、灯谜诗,清代诗人还为风筝作过诗,如袁枚《和金沛恩咏昭君纸鸢》:“玉门春老恨难忘,犹逐东风谒汉王。环佩影沉天漠北,琵琶声在白云乡。素丝解作留仙带,细雨弹成坠马妆。莫怪洛城多纸贵,画图终日对斜阳。”诗题中的“昭君纸鸢”,即是以王昭君为名的一种美人风筝。另外,蒋春喜《明妃纸鸢》曰:“飘零莫恨毛延寿,汉帝曾无一线情。”可见当时昭君故事已经以各种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进入人们的视野,题画诗的出现不是偶然的。
结语
《红楼梦》中有大量的诗词,随着小说的传播和流行而经典化,成为清代女性诗人创作的典范。纵观古代女性诗人的咏昭君诗,只有到了清代中期以后才出现规模性现象。这和清代女性文学的兴盛有密切关系,亦暗合于《红楼梦》的出现和传播。
在诗歌的表现内容方面,乾嘉以后女性诗人继承了《红楼梦》咏昭君诗的悲怨主题和批判精神,也创作了不少歌颂昭君和亲之功的诗歌,这是对《红楼梦》昭君诗悲怨主题的反拨,二者并不矛盾,反映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和自我肯定。这也是对小说中因昭君诗而引发诗贵创新的议论的一种积极回应。
在诗歌的呈现形式方面,女性诗人对《红楼梦》亦有借鉴。她们创作的系列咏史诗如《红楼梦》组诗一样,对读者的情感冲击力明显增强,应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察;而诗歌与其它艺术形式如图画的结合,提高了诗歌的生动性和可接受性。
《红楼梦》对女性才情和成就的肯定,极易引起女性诗人的共鸣。她们的咏昭君诗是清代闺阁文学活动场景和文化生态的侧面展示,是曹雪芹赋予小说的诗性情怀在现实中的反映和延伸,是对红楼文化的丰富。在《红楼梦》传播和接受中,清代女性诗人对《红楼梦》诗词的接受史,亦应成为红楼文化研究的重要谱系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