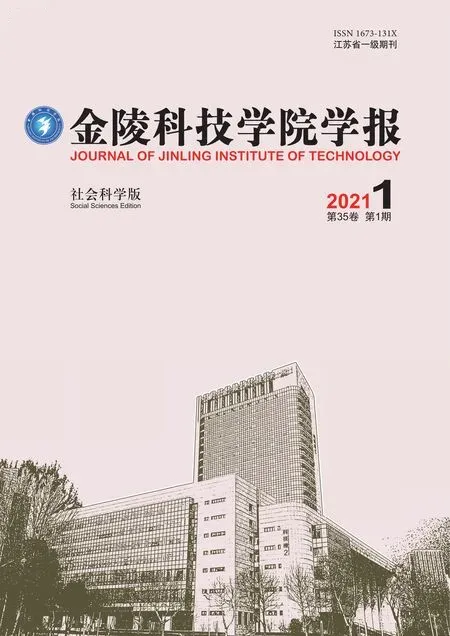《镜花缘》艺术思维的“别解”旨趣
乔孝冬
(金陵科技学院人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38)
“别解”,顾名思义就是回避词句原来的本义,用别的意义进行解释。《辞源》认为“别解”是一种发散性和求异性思维方式,并将其定义为“异于寻常的见解”。从思维方式上看,“别解”常常给人一种“存乎情理之中,出乎意料之外”的感觉。《汉语修辞美学》从辞格角度对“别解”进行了定义:“运用词汇、语法或修辞等手段,临时赋予一个词语以原来不曾有的新义,这种修辞手法叫‘别解’。这里所说的词汇手段,是指字(词)的多义;语法手段,是指改变词性或结构层次;修辞手段,包括比喻、谐音等等。”[1]“别解”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或修辞手法,也是谜语、笑话、歇后语等造谐的重要手段,由于其对词语本意的“正偏离”,因此往往能产生幽默、风趣的言语效果。
“以文为戏”“涉笔成趣”[2]717的创作心态,决定了《镜花缘》对谐趣的追求。李汝珍擅用“别解”造谐,风趣、冷嘲热讽的文笔成为《镜花缘》的一大特色。“别解”是《镜花缘》作者创造思维的解码,也是其显著的艺术特质。
一、翻新词语,其“别”在“戏”
在《镜花缘》中,唐敖、林之洋与多九公组成了海外三人行,陌生的海外世界通过唐敖的好奇之问与多九公“无一不知”的经验之答,被一一解说。为了让这个解说更加新奇、有趣,做海船生意的林之洋在旅行中充当了插科打诨者的角色。他在交谈中多用“别解”的思维方式,俚俗有趣,新鲜别致,有时自嘲,有时相互嘲谑。林之洋的“别解”让读者感受到幽默风趣的审美体验。
《镜花缘》前五十回描写的是唐敖、林之洋、多九公三人海外行游历的第一站——朱口山。三人边走边谈,就像是给海外风情镜头加上了解说词。他们沿途看到长在树上的穗长丈余的木禾,一粒稻米竟有三寸宽五寸长,这引起书生唐敖的探究:“此米若煮成饭,岂不有一尺长么?”多九公由此炫耀他曾见过的海外“清肠稻”:只要吃一粒大米,可以饱一年。林之洋对多九公倚老卖老、炫耀博识的话将信将疑,反驳道:“这等说,那米定有两丈长了。当日怎样煮他?这话俺不信。”然后林之洋借题发挥道:“怪不得今人射鹄,每每所发的箭离那鹄子还有一二尺远,他却大为可惜,只说‘差得一米’,俺听了著实疑惑,以为世上那有这样大米。今听九公这话,才知他说‘差得一米’,却是煮熟的清肠稻!”唐敖笑道:“‘煮熟’二字,未免过刻。舅兄此话被好射歪箭的听见,只怕把嘴还要打歪哩!”[2]49林之洋将“差得一米”别解为“差得一粒大米”之长,这种违反逻辑与常识、对海外游历所见奇物“清肠稻”之长的夸张描写,因符合当时的语境,让人不禁哑然失笑。谈话者突破固定思维模式而宕开常理,常常能创造出别开生面的新趣味。
随后,唐敖等人来到“白民国”。由于见到“诗书满架,笔墨如林”,唐敖连声说自己只是个晚生,后看到塾师无学,居然能将“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念成“切吾切,以反人之切”,“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念成“羊者,良也;交者,孝也;予者,身也”,这才明白“白民国”人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唐敖气得满面通红,后悔道:“但此等不通之人,我在他眼前卑躬侍立,口口声声自称‘晚生’,岂不愧死!”林之洋道:“‘晚生’二字,也无甚么卑微。若他是早晨生的,你是晚上生的,或他先生几年,你后生几年,都可算得晚生,这怕甚么!……如今平安回来,就是好的,管他甚么‘早生、晚生’!”[2]151林之洋将“晚生”别解为“晚上生的或后生的”,对“晚生”常规语义规约进行了出人意表的突破,原具有谦称语义的“晚生”与表示时间名词“晚上生的”的新语义构成反差,也造成了接受者心理的落差,注意力为之骤然集中,细思之,又使人不禁哑然失笑,体现了林之洋维护唐敖和多九公面子、化解委屈与尴尬的匠心。
林之洋作为海外贸易商人,思维敏捷,谈话也体现出“在商言商”的特色,有时故意把一个看似平常的词汇别解成另一种奇妙歪理,从商人视角讽刺社会现实,如第二十七回《观奇形路过翼民郡,谈异相道经豕喙乡》写三人来到“翼民国”,“翼民国”人头长,有翼能飞不能远,并非胎生,乃是卵生。林之洋道:“若是卵生,这些女人自然都会生蛋了。俺们为甚不买些人蛋?日后到了家乡,卖与戏班,岂不发财么?”多九公道:“班中要他何用?”林之洋道:“俺看这些女人,也有年纪老的,也有年纪小的。若会生蛋,那年纪老的,生的自然是老蛋;年纪小的,生的自然是小蛋。俺们有了老蛋、小蛋,到了家乡,那些戏班为甚不要?只怕小蛋还更值钱哩!”多九公道:“林兄把‘旦’字认作白字了。他们小旦并非鸡蛋之‘蛋’,你如不信,把他肚腹剖开,里面并无蛋黄,只有一肚曲子。还有拿的好身段,推的好衫子,并且还有绝妙的小嫩嗓子。”林之洋道:“九公说他并无蛋黄,据俺看来,只怕还有元丝课哩。再要搜寻,大约金镯子也是有的。就是那扛旗儿二等小旦,万不济,也有几块洋钱,也有一个包金镯子。就只令俺不懂的,刚才说的明明是个‘旦’字,为甚是‘白’字?若是‘白’字,下面多了一横,上面少了一撇,这是怎讲?”[2]182林之洋故意将戏曲行当中的“旦”别解为“蛋”,巧用谐音来制造双关的效果,引出多九公“肚里面并无蛋黄,只有一肚曲子”的争辩。林之洋则巧辩为肚里面有金镯子、洋钱。林之洋拿戏班的老旦、小旦寻开心,意在讽刺艺人得利之多。他又讲歪理,别解“旦”字不是“白”字,“下面多了一横,上面少了一撇”。多九公念白字的原意是念错字,林之洋故意偷换概念,歪曲多九公的原意为“白”这个字。《笑林广记》有则“日饼”的笑话:中秋出卖月饼,招牌上错写“日饼”。一人指曰:“月字写成白字了。”其人曰:“我倒信你骗,白字还有一撇哩!”这种用变异来造奇的思维方法,因背离了习惯思维的轨道,使整个谈话过程妙趣横生,从而产生幽默的效果。
《镜花缘》人物对话深得“别解”精粹,常常将普通词汇别解为特殊新奇的解释,如巧妙地使用了“酸”字“既可指口味酸也可指文人的文酸气”的双重语义。唐敖一行在“淑士国”酒馆里遇见的一个酒保,他也戴着眼镜,假充斯文,满口“之乎者也”;还遇到一个老者,他一连用了五十多个带“之”的句子“掉书袋”。而“淑士国”偏偏又以醋作酒,举国上下一片酸气。林之洋对假作“圣贤大儒”的老者道:“你这几个‘之’字,尽是一派酸文,句句犯俺名字,把俺名字也弄酸了。随你讲去,俺也不懂。但俺口中这股酸气,如何是好?”又道:“怪不得有人评论酒味,都说酸为上,苦次之。原来这话出在淑士国的。”[2]160将“淑士国的酒味”写成以“酸为上”,喝酸酒以致“口中这股酸气”,情节寓意双关,新鲜有趣。又如第七十二回《古桐台五美抚瑶琴,白亭八女写春扇》中对“香臭”的别解:“原来四位姐姐却在这里下棋!今日这琴棋书画倒也全了。就只紫琼、紫菱二位姐姐特把芷馨、香云两个姐姐拉来观阵,未免取巧。”紫琼一面下棋,一面问道:“为何取巧?”紫芝道:“芷馨姐姐是‘馨’,香云姐姐是‘香’,既有馨香在跟前,就如点了安息香一般,即或下个臭著儿,也就不致熏人。若不如此,此地还坐得住么?”易紫菱听了,不觉好笑[2]501。人名的“馨”“香”与棋的“臭”本来都无关味觉,但经过笑靥花孟紫芝这一番别出心裁的歪理解释,让人就不禁觉得好笑了。
作为线头人物,勾连百花游戏的孟紫芝与林之洋一样,对社会生活、人际关系的脉络异常敏锐,能在一瞬间以最出人意料的方式爆出惊人之语,是具有幽默诙谐性格特征的喜剧天才。李汝珍安排他们用“别解”的方法打趣调侃,勾连人物,串通上下情节,制造出别开生面的新意境,展示出“以文为戏”的巧妙匠心,而人物自身与小说情节因而也有了诙谐幽默的艺术效果。
二、制谜猜谜,其“别”在“奇”
“别解”是猜灯谜的基本法则之一,谜面与谜底之间的扣合关系是建立在“别解”之上的联想和解说,谜坛有“别解方成谜”的说法。清代许多灯谜被写入长篇白话小说中。钱南扬《谜史》云:“嘉道以降,新声竞唱,而古谜遂衰。同光之际,京师出灯极盛,当时所谓十五谜家者,名须海内,其《同岑》一集,猜谜者奉为圭臬也。清代小说,以谜语点妆事实者,莫先于《红楼梦》,莫多于《镜花缘》,莫精于《品花宝鉴》。”[3]《镜花缘》是收灯谜最多的小说。鲁迅先生对《镜花缘》罗列灯谜等游戏之盛评称:“盖以为学术之汇流,文艺之列肆,然亦与《万宝全书》为邻比矣。”[4]该书共六个章回有灯谜和谜事的描述,涉及的灯谜多达六十八条。《镜花缘》灯谜“别解”主要有语义别解、顿读别解、字形别解、语音别解等手法。
(一)语义别解法
《镜花缘》谜语范围很广泛,有地名、人名、花名、鸟名、药名、物名、曲牌名、书名等。第三十一回《谈字母妙语指迷团,看花灯戏言猜哑谜》有十三则谜语,这些谜语多采用语义别解法中的正面会意法,比较容易猜。例如:以“千金之子”打“女儿国”,以“螃蟹”打“无肠国”,以“腿儿相压”打“交胫国”,以“分明眼底千里” 打“深目国”,以“脸儿相偎”打“两面国”,以“永锡难老” 打“不死国”。 谜底所打国家既是对唐敖三人前边所历海外各国的总结,也是对下面将要游历国家的预叙。例如,以“万国咸宁”谜面暗示第三十九回《轩辕国诸王祝寿》海外异国大聚会情节的发展,构思独特别致。另以“游方僧”打《孟子》四字,林之洋猜为“到处化缘”,唐敖将其更正为“所过者化”;“守岁”打《孟子》一句,林之洋又猜为“要等新年”,多九公将其更正为“以待来年”。林之洋别解谜语的思维方式是对的,但林之洋读书不多,说不出“四书五经”的原文,但在饱读“四书五经”的读书人唐敖、多九公看来,就是当众出丑了。这场猜谜活动生动展示了三个人不同的身份、性格及学养。
猜谜的能力反映了一个人思维能力的强弱和天赋才华的高下。相对于“智佳国”猜谜,众才女在礼部尚书卞滨家制谜、猜谜活动则要复杂丰富得多。为了表现才女的博古通今和文心之巧,在第八十回和八十一回众才女酒筵上猜射的五十二则谜语中,“四书五经”谜高达二十六则。例如,“直把官场作戏场”打《论语》一句,谜底是“仕而优”。《镜花缘》评论“这题面又是儒雅风流的,不必谈,题里一定好的。” 谜底把“优”字别解作“优人”,也就是演员,以“官场”扣“仕”,以“戏场”扣“优”,谜面属于典雅一派,实得谜语“别解”的精粹。又如“国士无双”打《礼记》一句,谜底是“何谓信”。此处用典,“国士无双”是萧何对韩信的评价:“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国士无双”。谜底“何谓信”来自于《孟子·尽心下》中的“何谓信?”谜底是疑问的口气,即问别人“什么是儒家所说的‘信’”。作者借用别解,“何”指萧何,“信”指韩信,谜底精巧,与谜面丝丝入扣。清代费源《群珠集》成于乾隆年间,收谜二百零二条,其中也有一则同样的谜语,可见这则谜非作者自制。《镜花缘》又用“何谓信”作谜面,连引出一则文义谜:“何谓信?”打《论语》一句,谜底是“不失人亦不失言”,这也是用语义别解法揭出谜底。这些谜语都显示出清代文人很高的制谜水平。
《镜花缘》认为“凡谜当以借用为第一,正面次之”[2]555。这说的是语义别解中的侧面会意法。例如:易紫菱出的“四”字,打个药名,谜底是“三七”;柳瑞春出的“三”字,打《孟子》二句,谜底是“二之中、四之下也”。李汝珍借春辉之口评论侧面会意法是“此格在广陵十二格之外,却是独出心裁,日后姐姐会意过来,才知其妙哩”[2]557。第七十四回孟紫芝出的谜语是:“三九不是二十七,四八不是三十二,五七不是三十五,六六不是三十六。打一物。”掌红珠道:“我猜著了,可是‘十二’?”紫芝道:“‘三九’‘四八’‘五七’‘六六’,凑起来都是十二,姐姐猜的真好。但妹子刚才有言在先,打的是个物件,请姐姐把‘十二’取来看看,如果是个物件,就算姐姐猜著。”红珠不觉笑道:“呸!我只当是个数目哩。”邵红英道:“可是‘双陆’?”紫芝笑道:“这个猜的却好。”[2]513这则谜同样利用对多个并列关系因素的描述来归纳出其中某种共同的规律,从而进行谜面谜底的扣合,围绕谜底猜射,将孟紫芝活泼俏皮、喜欢打趣的性格生动地展现了出来。
清代谜语制作讲求“神品”“能品”“逸品”。例如,张文襄之“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射《易经》“中心疑者其辞枝”,传神阿堵,余味盎然,是为神品。叶奂彬吏部之“末座少年,异日必是有名卿相”,射《诗经》“绿衣黄裳”,文章天成,妙手偶得,是为能品。某君之“伯姬归于宋”(《春秋》),射唐诗“老大嫁作商人妇”,别开生面,妙造自然,是为逸品。《镜花缘》却认为制谜猜谜“不及会心格为最古”[2]557。会意法是一种最正宗、最普遍的制谜猜谜方法,因此《镜花缘》的制谜猜谜大部分采用语义别解的会意法,典雅传神,余味盎然,别开生面,妙造自然。
(二)顿读别解法
顿读别解法是《镜花缘》常用的猜谜方法。“无人不道看花回”打《论语》一句,谜底是“言游过矣”[2]540。“无人不道看花回”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玄都观桃花》诗中的句子。玄都观是唐代长安著名的道观,观中的桃花很有名。每年春暖花开,长安的官商士庶都要去那里赏花。“无人不道看花回”,“道”字是“谜”眼,“道”即“言”,看花回来即“游过了”。谜底“言游过矣”是《论语·子张》中的话,是孔子的学生子夏批评子游的,这里顿读作“言:‘游过矣(1)“游”,子游;“过”,过错。’”,指子游的话说错了。又采用谜底顿读别解法,以底扣面,“言游”别解为谈论郊游,“过”由错过别解为“过了”,以此恰到好处地笼括了诗句之意。一则谜作有无运用“别解”,其效果大不一样。以“言游过矣”为谜底, 别解谜面“无人不道看花回”, 凭空衍生出不同寻常的意蕴和风趣, 谜味十足,具有极其丰富的知识性和文学性,后亦被收入清代栖云野客《七嬉·冰天谜虎》等灯谜书中。
(三)字形别解法和语音别解法
字形别解法也是《镜花缘》常用的猜谜方法。例如,“昱”打《诗经》一句,谜底是“上下其音”[2]556。“上下其音”本是《诗经·邶风·燕燕》中的句子,此谜采用字形离合方式,将“昱”别解为把“音”字的上下调换位置,紧密扣合谜面“昱”字,构思非常巧妙。又如“”字,打《易经》两句,谜底是“离为火,为日”[2]555。谜底“离为火,为日”,取自《周易·说卦》,“离”是《周易》六十四卦之一,这里别解作“分开”, 卦辞“离”之意,此意实非“分开”之本义,风马牛不相及,充分运用了字形别解法。
除此之外,《镜花缘》还有语音别解。语音别解是利用汉字一字多音、一音多字、象声、拟声等特点制造歧义,由此产生异音异字的别解。如“重庆”,谜底是“父子有亲”[2]565。
徐珂《清稗类钞·谜有书家意江湖意之别》云:“光绪戊申,番禺沈太侔礼部宗畸在京师刊行《国学萃编》,其征谜语有云:‘书家意者方能照登,江湖意者恕不登录’。此语直得谜中三昧。谜之最忌者二:一曰俗,如乡人所猜之谜是也。一曰呆,如苏沪各地茶肆中丐者所书之谜是也。是皆太侔所谓江湖者是也。一染此习,便失文人身分,故谜虽属游戏,必非胸无点墨者所能从事。”[5]钱南扬认为《镜花缘》的谜语“皆今体,多平浅而鲜精警”[3]。因为李汝珍并不认为谜面通俗平浅的谜语就不如谜面典雅的好,“大凡做谜,自应贴切为主;因其贴切,所以易打”[2]557。只要谜底和谜面二者扣合紧密,在作者看来都具有巧思。“那难猜的,不是失之浮泛,就是过于晦暗。即如此刻有人脚指暗动,此惟自己明白,别人何得而知。所以灯谜不显豁、不贴切的,谓之‘脚指动’最妙。”[2]557-558近日还有一种数典的,终日拿著类书查出许多,谁知贴出面糊未干,早已风卷残云,顷刻罄净,这就是三等货了。”[2]555制谜是让人猜射的,如果制得太直露,失之浮泛,猜射者就会感到索然无味;反之,编制得太艰深,过于晦暗,也不是好谜。谜语制作要“显隐得兼”,谜语有味并不在于谜面的深浅,既体现智力水平又能愉悦身心的就是好谜。
《镜花缘》谜语的作用主要有四种。一是炫才,或征诸典借,或近取于诸身,如“对景挂画”的即景谜。有些是为了表现才女的风趣幽默和才思急智,比较平浅通俗。例如,褚月芳看到闵兰荪穿的背心,随口而出的“布帛长短同,衣前后,左右手,空空如也,打一物。”司徒妩儿道:“月芳姐姐所出之谜是‘对景挂画’;妹子也学一个:‘席地谈天’,打《孟子》一句。”芸芝道:“我倒来的凑巧,可是‘位卑而言高’?”妩儿道:“我这个也是面糊未干的。”谭蕙芳道:“你看兰荪姐姐刚才席地而坐,把鞋子都沾上灰尘,芸芝姐姐鞋子却是干净的;我也学个即景罢,就是‘步尘无迹’,打《孟子》一句。”吕瑞蓂道:“可是‘行之而不著焉’?”[2]557二是预叙情节发展且具有谜外之义的谜,其谜面和谜底都带有预言色彩。受明清时期“图谶”内化为一种美学思维或小说结构艺术的影响,《镜花缘》借用谜语预言红颜薄命。例如:钱玉英出“酒鬼”,打《孟子》一句,邵红英打“下饮黄泉”;谭蕙芳出“其涸也可立而待也”, 叶琼芳打药名“无根”;林书香出“辙环天下,卒老于行”,秀英打“尽其道而死者”[2]566。谜语以其谜外之义给读者一种暗示,以预示小说后边的情节并加以验证。这种以谜语为小说的情节建构服务的手法,丰富了古代小说的预叙手法。三是用谜语表现更为深刻复杂的文化内涵。这类谜语较为典雅深奥,往往猜射时较为困难。例如,六十四回玉芝出的“红旗报捷”,从“胜之”“战必胜矣”“克有罪”一直到宝云才打出谜底“克告于君”,既符合猜谜的过程,又暗含了“反周复唐”[2]442的道德使命,也预示了人物的身份与品性。又如唐闺臣出的“老莱子戏彩”,谜底是《舞霓裳》和《孝顺儿》[2]567两个曲牌名, 暗示唐闺臣的仙子身份和孝德。四是组织小说情节。例如:众才女相聚、游园、聚会到散场的过程,用“天下太平”打“普安”[2]554表示聚会活动的开始;用“鸣金”打《孟子》三字,谜底为“使毕战”,“高朋满座,胜友如云”打曲牌名,谜底为“集贤宾”[2]568,表示猜谜聚会的结束。整个时空的流动通过谜语形象地展示了出来。
三、解码《山海经》,其“别”在“新”
《镜花缘》前五十回海外游历的素材大部分出自《山海经》。《山海经》被胡应麟称为“古今语怪之祖”,清代纪昀编《四库全书》称其“侈谈神怪,百无一真”。《山海经》包罗万象,涉及面很广,其记载的海内外的名山大川和奇形怪状的动植物对《镜花缘》影响很大,如《镜花缘》提到的木禾、清肠稻、肉芝、刀味核、朱草、果然、不孝鸟等均出自《山海经》。鲁迅评赞《镜花缘》道:“惟经作者匠心,剪裁运用,故亦颇有虽为古典所拘,而尚能绰约有风致者。”[4]赵苕狂在《足本镜花缘·本书特点》中感叹:读了《镜花缘》,好似读了一部《山海经》。《镜花缘》第三十九回提到,“天朝有部书是夏朝人作的,晋朝人注的”[2]263,无疑是在抖落书中所写诸般异国原来大都出自《山海经》。李汝珍博识多通,“于学无所不窥”,对《山海经》更是烂熟于心,但他依傍《山海经》却不像其他地理博物体的志怪小说那样去仿照,为《山海经》所拘泥。李汝珍“花样全翻旧稗官”,他对原始材料大都进行了深度加工,对《山海经》海外诸国的名称设喻别解,既嘲讽现实,寄寓劝惩,又成为联结海外游历、推动情节发展的一种重要手段。
《镜花缘》前五十回以受人诬陷的落第才子唐敖心灰意冷出海访仙求道为主线,共写了君子、大人、劳民、无肠、犬封、鬼国、靖人、长人、两面、穿胸、结胸、长臂、翼民、豕喙、伯虑、轩辕等42个国家,这些国名多出于《山海经》。通过比对可以发现,《山海经》中对诸多国名只有形体外貌的描述,并无道德品行方面的记述,而李汝珍为了寄寓美好社会理想与对黑暗现实世界假、恶、丑的批判,凭借丰富的想象、幽默的笔调,通过对《山海经》的有意别解,运用谬推、错位、谐音、歇后、引典、夸张、比喻、双关等修辞手法对国名予以道德化解释,达到引人发笑的目的。
为了从道德品性上树立“君子”“大人”“轩辕”等国“礼乐之邦”的形象,李汝珍有意别解《山海经》。例如,《山海经》中“大人国”本义只是形体高大之人,并无道德上的语义。李汝珍虽说“其人较别处略长二三尺不等”,但从道德品性上别解“大人”之意,即“毫无小人习气”。作者通过多九公的辩说“大人”“长人”,给予“大人国”新的解释:“大人国”之得名是因为“毫无小人习气,因而邻邦都以大人国呼之”。这里的“大人”不是长得大之意,而且说“海外大人国身长数丈”也是讹传,身长数丈的是“长人国”。同样采用别解法,作者将《山海经》只是形体渺小的“小人国”别解为“诡诈异常”的小人,“两面国”别解为“两面三刀”,“犬封国”别解为“狗头狗脑”,“鬼国”别解为“鬼头鬼脑”,“毛民国”别解为“一毛不拔”,“长臂国”别解为“手伸得长”,“无肠国”别解为“悭吝心肠”,“穿胸国”别解为“心术不正”……通过对反面形象的别解和虚构,生动地将现实中的种种可笑与黑暗揭露了出来。
许乔林《镜花缘序》云:“是书……另具一副手眼,另出一种笔墨,为《虞初》九百中独开生面,雅俗共赏之作”;许祥龄《题词》云:“上超往古下超今,创格奇文意趣深”;陈瑜《题词》云:“花样新从笔底翻”;李汝珍亦自称其《镜花缘》“花样全翻旧稗官”[2]718。随着清朝科举制度的没落腐败、国外先进思想的渗入,知识分子开始“睁眼看世界”,“新”风直接冲击着中国的文坛,也给谜苑带来了新变。清代小说家、诗人、骈文家、评点家、考据家、学者名士等感到有才华又无处施展,于是纷纷把精力转化到灯谜这种“文字游戏”上来。《清嘉录》中顾震漪《打灯谜》诗曰:“一灯如豆挂门旁,草野能随艺苑忙。欲问还疑终缱绻,有何名利费思量?” 写出了当时人们热衷猜谜的现状。猜谜一方面是一种自娱和娱人的游戏活动,陶醉于游戏可以让人逃避现实,获得精神上的陶醉与满足;另一方面,又能炫才,可以展现读书人腹内珠玑以及“四书五经”“唐诗宋词”的学养,为展示他们的才情提供了绝好的表现机会。由是读书人纷纷投入制谜猜谜的游戏中。谜语大师李汝珍在小说创作中也充分展现了这种别解思维特质,运用灯谜出奇制胜预叙情节,暗示人物性格命运,又将自己的才学与传统制谜猜谜的技法相结合,将乾嘉学派经书、音韵、训诂等高深的学问通俗化、趣味化,打破人们头脑里固有的思维定式,独具只眼,另辟蹊径,使作品“存乎情理之中,出乎意料之外”。无论是站在创作者的角度,还是站在作品接受者的角度看,它的“求异”特性都是很突出的,其作用力之强劲、表现力之丰富,达到了“件件都可解得睡魔,也可令人喷饭”[2]158的游戏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