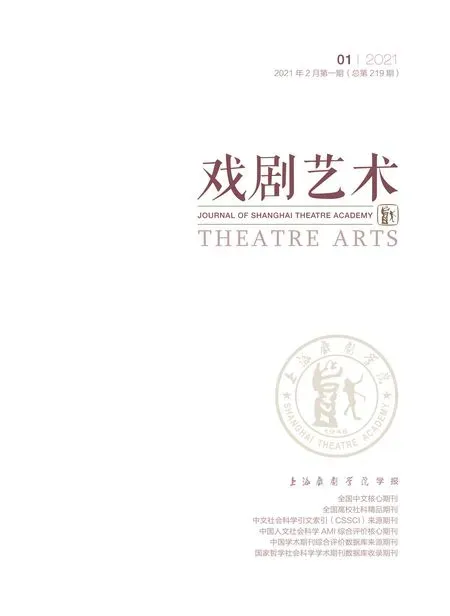色彩斑斓的服饰与稳定的剧场效应
——论曹禺戏剧服饰的色彩配置艺术
刘家思 刘 璨
戏剧服饰是戏剧艺术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戏剧服饰配色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服饰色彩融社会性与个体性于一体,既具有审美性又具有指事性,既具有再现性又具有表现性,以视觉冲击力对戏剧接受造成直接影响。戏剧人物的服饰色彩,可以表现人物的社会地位和精神性格,也与人物的生活状况与命运状态形成神秘的关联性;而在演出中,戏剧人物的服饰色彩作为一种运动着的色块,始终是观众视觉中的感知主体,能够通过内化,转换和形成一种审美能动作用。康定斯基认为:“在敏感的心灵那里,色彩能发挥出更深刻更动人的感染力。由此我们获得观看色彩的第二种体验,即色彩的心理效应。”(1)瓦西里·康定斯基:《论艺术中的精神》,余敏玲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0页。因此,中国传统戏曲的服饰配色富丽堂皇,给受众一种很强的视觉冲击。在话剧中,人物服饰色彩配置,虽然不要求像传统戏曲一样富丽堂皇,但也是非常重要的元素。这不仅是塑造人物的需要,还是思想表现的需要,更是满足审美接受中视觉观感的需要。曹禺十分重视戏剧人物服饰的色彩配置,总是恰当地运用各种色彩来象征、隐喻和提示人物的基本性格或命运趋向,从而刺激受众的审美心理,诱发其审美共鸣。可以说,曹禺对于戏剧人物服饰色彩的配置,成为了曹禺深化艺术表现、营造剧场性引力和稳定审美接受效应的一个基本手段。本文试图就这个问题进行一些探讨,以期抛砖引玉,并就教于大家。
一、冷色主导与暖色辅助:曹禺常用的服饰色彩
色彩是丰富的。但是,在戏剧舞台上不可能不加任何选择使用各种色彩。实际上,舞台上始终占据观众视觉中心的流动性色块——人物服饰色彩,都是剧作家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选择,其依据自然是表现的需要、审美的需要和接受的需要。黑格尔说:“颜色感应该是艺术家所特有的一种品质,是他们所特有的掌握色调和就色调构思的一种能力,所以是再现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一个基本因素。”(2)黑格尔:《美学》第3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81页。自然,在曹禺的戏剧中,人物服饰色彩也是曹禺做出的选择,实际上被赋予了特殊的艺术使命。总的看来,曹禺戏剧人物服饰的色彩配置,并不繁杂,更不纷乱,简约和素朴可以看作是曹禺戏剧人物服饰色彩配置的基本风格。他总是以冷色调为主,以暖色调为辅,基本上形成了“三色拼图”的审美效果。这与曹禺所表现的生活有关,也与曹禺戏剧表现的主题有关,还与他的审美追求有关。纵观曹禺戏剧,其服饰色彩的使用,通常有如下几种情况:
(一)古铜色是曹禺戏剧服饰常用的主导色调之一。古铜色凝重而沉滞,陈旧而腐朽。古铜色服饰穿在人身上,让人感到很压抑。在曹禺笔下,古铜色作为人物服饰色彩,出现的频率远远大于其他颜色,成为戏剧中的主色调。从《雷雨》《日出》《原野》到《蜕变》《北京人》《家》,古铜色总是备受“重用”,常常将它作为戏剧故事中权势人物的服饰色彩。如《北京人》中的曾家老太爷曾皓“穿一件古铜色的长袍,肥大宽适,外面套一件愫芳为他缝制的轻软的马褂——他是异常地怕冷的——都没有系领扣,下面穿着洋式翻绒鞋,灰缎带扎着腿”。《家》中的高老太爷在第一幕中“穿一件团花的丝绒马褂,罩在古铜色的缎袍上”,第三幕“穿着古铜色夹袍,外面套上丝绒黑马褂”;三老爷高克明在第一幕中也“故意穿了一件不十分新的古铜色缎袍”。《日出》中的潘月亭在第一幕中“穿一件古铜色的貉绒皮袍。上面套着是缎坎肩,上面挂着金表链和翠坠儿”。《原野》中的常五在第二幕中“穿一件古铜色的破旧的缎袍,套上个肥坎肩,披着一件黑衣服”。《蜕变》中的秦仲宣在第一幕中“着一身古铜色细花绸面的棉袍”。如此等等。可见,在曹禺戏剧中,凡是年龄较大的男性人物,其服饰色彩以古铜色为主。这不限于主要人物,也有次要人物。显然,古铜色是曹禺非常喜欢使用的一种颜色。古铜色是一种混合色,往往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纯色混合而成,而且对混合的纯色没有特定的偏向性,其色度既不是亮黄的明度,也不是铜黄的暗度,但它是两种黄色明度的混合体,这就使得色彩本身具有了多元性。曹禺让人物着这种色彩的服饰,预设着这些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既刻板守旧,又矜持霸道,也有内在的怯弱。高老太爷和曾皓,分别作为高公馆和曾公馆最高权力把持者,非常专制、古板,既腐朽又阴恶,都是年轻人悲剧的制造者,给人以厌恶感。秦仲宣、潘月亭和高克明,穿着古铜色服饰的同时,配着金色的表链或戒指,在视觉上就给人以狭隘、势利和腐朽之感。鲁贵与常五着古铜色的服饰则主要表现趋炎附势、欺弱怕强、腐朽而没有坚持的复杂性格。显然,古铜色用在人物服饰着色上,不仅显示了人物的个性特征,而且给作品确定了一个色彩基调。围绕这个基调,与其相近的色彩也被运用起来,如李石清“穿一件褪了色的碎花黄缎袍,外面套上一件崭新的黑缎子马甲”,也显示了李石清性格的复杂性。然而,从观众的审美感受而言,这些人物着这种色彩服饰,一出场就造成了阴冷、沉闷而压抑的气氛,冲击着受众的心理。
(二)黑蓝灰色是曹禺戏剧服饰用得最多的色调。黑蓝灰色,阴冷而不明朗,呈现出内在的晦涩与复杂。在曹禺笔下,《雷雨》《北京人》《日出》《原野》《家》中的一些主要人物,很多都着这一类颜色的服饰。不同明度的蓝色和黑灰色等系列的暗色调的应用,也显示了作者的主观取向。在这里,黑色有了丰富的象征意蕴。《雷雨》中的周蘩漪在第一幕中“通身穿黑色旗袍”。《家》中的觉慧第一幕出场“穿着短短的黑色学生服”;觉民在第二幕中“穿着黑制服由右面侧门进”;黑三“穿着黑衣服,戴着黑帽子”;焦母则“还穿着丈夫的孝,灰布褂,外面罩上一件黑坎肩,灰布裤,从头到尾非常整洁”等等。与黑色相协和的是藏青和灰色,经常被曹禺用于服饰着色。如《雷雨》中的周萍在第一幕中“穿一件藏青的绸袍,西服裤,漆皮鞋”。《北京人》中的曾文清则多着服色淡雅的宽袍,第三幕二景回家后则“换了一件深灰色杭绸旧棉袍”。《家》中的觉慧有时也“穿着藏青的旧制服”,而梅小姐则“穿一件银灰色的夹衫”。《日出》中的胡四在第三幕中“穿着皮大衣,琵琶襟紫呢坎肩高领碎花灰缎夹袍,花丝袜子,黑缎鞋”。蓝色也是一种冷色调,曹禺也经常使用。如《雷雨》中的鲁大海则“穿了一件工人蓝布褂子,油渍的草帽拿在手里,一双黑皮鞋”。《北京人》中的曾文彩在第一幕中则“穿一件半旧的蓝灰色羽纱旗袍,青缎鞋也有些破旧”,愫芳在第一幕却一身“深蓝色毛哗叽就旗袍”出场。《家》中的觉新在第一幕中不是“穿着品蓝缎袍,团花黑马褂”,就是“穿着品蓝缎袍子,青缎马褂”,甚至“还穿着那件深蓝洋皱的新袍子”,在第二幕中则“穿着半旧淡灰夹袍,黑皮鞋,拿着雨伞,面色憔悴”,第四幕仍然“穿一件灰布棉袍,白布鞋”;瑞珏在第一幕穿“一身天蓝色的软缎短袄和长裙”,第二幕第三景则“穿着一套淡蓝色隐约织了一点灰丝的羽纱衣裙”;钱太太在第二幕第三景中“穿着宝蓝绸上身,黑绸裙,除了额上多添几条皱纹外,旁处都不见老”。《日出》中的小东西一出场就是“穿一件满染油渍,肥大绝伦的蓝绸褂子,衣裾同袖管儿几乎拖曳地面”,到第三幕则“穿着蓝布夹上衫,黑裤子”。《原野》中的仇虎在序幕中“身上一件密结纽绊的蓝布褂,下面围着‘腰里硬’,一种既宽且大的黑皮带,前面有一块瓦大的铜带扣,贼亮贼亮的”。曹禺反复配置这些色彩的服饰,这是有其用意的。黑色是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社会心理蕴含的色彩。夏朝和秦朝崇尚黑色,公卿大夫的官服、礼服、祭服都是黑色,所以黑色在中国既象征尊贵、威严、肃穆,又具有坚毅、刚直、无私、严正的含义,代表着公正的力量。但是,黑色和夜色相似,又象征深沉、神秘、惊惧、压抑和极度紧张;黑色的暗度还和背后联系在一起,又包含邪恶、阴险、欺骗和恐怖的意蕴。青色是介于绿色和蓝色之间的颜色,是带绿的蓝色,藏青色是蓝与黑的过渡色,属于很深的蓝色,显得稳重而冷静;而铁青色为青黑色,隐喻矜持、恐惧、盛怒的意蕴。灰色是冷淡而退隐的颜色,给人以悲哀、愁怨、沉静、暴风雨、老年等感觉。蓝色也具有传统文化底蕴,又因明暗度不同而给人的主观感受不同。鲜明的蓝是天空的颜色,表现伟大、寂静、无争,象征稳固、庄严、悲哀、沉默、永久、神秘、沉静、清澈等,往往具有理智的特性;蓝又是冷色,又象征冷静、无同情心及寒冷,也容易使人感到陌生、空寂和孤独;混浊蓝容易引起暗淡、低沉、郁懑和神秘的感觉,暗度蓝便象征屈就、抑郁、谦蔼。在传统戏剧中,脸谱为蓝色的人,隐喻刚猛、骁勇、忠直、仗义,既表现其反抗精神又显示其智谋,有时也象征着恐怖、诡异。在曹禺笔下,不同人物着黑色服饰,其象征意蕴是不一样的。例如,蘩漪的黑色服饰就象征着尊贵、深沉、神秘、压抑、悲哀;黑三着黑色服饰,就象征着邪恶、阴险、欺骗和恐怖。蓝、黑颜色都容易使人产生恐怖、紧张、沉闷的心理。在曹禺的戏剧中,配置这些冷色调服饰者,都是直接影响剧情的人物,性格沉郁而复杂、痛苦而执著、愤懑而悲哀、忧郁而伤感,在剧场中形成了浓郁的情绪氛围。
(三)红、白色是有限运用的色调,相对前两类是比较少的。在曹禺的戏剧中,人物服饰色彩很少配置亮暖色的,形成了沉闷压抑的气氛。但是,他也有限地运用了红色等亮暖色调以及无色调的白色。《日出》中的翠喜“穿一件绛红色的棉袍,套上一件绒坎肩,棉鞋棉裤,黑缎带扎住腿”;而陈白露一出场就“穿着极薄的晚礼服,颜色鲜艳刺激”;顾八奶奶“穿一件花旗袍镶着灿烂的金边、颜色鲜艳夺目”,显然都不是白色就是红色,因为这两种色彩最鲜艳刺激。欧阳山尊导演的《日出》,陈白露第一幕身着极轻薄的红色晚礼服,就是对曹禺剧本准确的理解。《家》中的淑贞“穿着一套桃红小花的绸子袄裤。一双小小的天足穿着红挑花鞋,几乎可以撩乱人的眼,野兔似的在地上不停地跑动。手里拿着一袋红纸包好的喜果”。《原野》中的焦花氏在序幕中“穿着大红的裤袄”,第一幕“她穿一件红绸袄,黑缎裤,发髻扎着红丝线”,第二幕“穿一身血红色的紧身”,第三幕和仇虎逃入黑林子时“背着小白包袱”,“血红色衣褂紧贴在身上”。红色因为色彩鲜艳,能见度较高,是最引人注目的色彩,视觉刺激力很强。同时,红色的象征性意蕴非常丰富。由于红色是太阳、火一样的颜色,在中国通常具有温暖、热烈、吉兆、兴旺、活跃、顺利、吉祥、喜庆、忠诚和耿直等积极的象征意义,也象征热情、革命、进步、强烈的欲望和骚动不安的感觉;但红色的颜色又像鲜血一样,充满血腥气味,也使人感到恐怖、残酷。曹禺在戏剧中让人物穿上红色的服装,赋予的意蕴也是多方面的。《原野》中的焦花氏在戏剧中自始至终都穿着亮丽的红色服饰,在黑黝黝的原野中成为一团烈火,是整个剧作中一个热烈的人物形象。在这里,红色既表现热烈、活跃、顺利、忠诚、耿直、热情的内涵,也暗示着欲望和骚动、革命和复仇、恐怖与残忍的意蕴。这一团“火”在整个黑暗的剧情中一直充斥着受众的视线,也对剧情有预设作用:作为黑暗中的亮火必定要产生刺眼的火光。白色也是曹禺比较喜欢使用的。《雷雨》中的四凤第一幕“穿一件旧的白纺绸上衣”;周冲第一幕不是“穿着打球的白衣服”就是“穿一套白西服上身”。《北京人》中的陈奶妈“穿着一件月白色的上身”,曾霆“穿一身淡色的夹长衫,便鞋,漂白布单裤”。《家》中第二幕“觉慧穿淡灰色的学生制服裤,白衬衫,宽大舒适”;琴小姐不是“穿着月白闪光缎上身,浅蓝绸裤沿着花边,举止落落大方”,就是“穿一身女学生装,上身白洋布短衫”;梅小姐“穿一件银灰色的夹衫,镶着素白的滚边,一条较上身尤淡的灰白色薄薄的毛织品长裙,几乎拖在脚面”。如此等等。《淮南子·原道训》曰:“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3)刘安:《淮南子》,许慎注、陈广忠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8页。显然,白色是基准色,既表现纯洁、干净、青春与活力,也表现低贱、腐朽、衰败、哀伤、死亡,还隐喻愚昧、落后、愚蠢、寂寞、冷漠与歧视,且暗示凶残、恐怖、堕落和阴冷等等。这些意蕴显示出生命与灵魂的两极。曹禺给不同人物配置不同的白色服饰,显示了特定的意蕴。如四凤的白纺绸,周冲的白色球衣和白西服,都表现纯洁、干净、青春和活力;梅小姐着银灰色的夹衫,灰白裙,暗示其生命力不强以及衰败、哀伤的情感和即将死亡的命运。黄色也有很深的文化底蕴,既有尊贵和威严的一面,如纯黄一度是君主国王的服饰配色,也有枯萎、凋零的意思。曹禺在剧中也有使用,寄予着不同的意蕴。如黄省三着黄色服饰,就是喻指其生命萎缩、衰弱,没有活力。
应该说,曹禺戏剧服饰色彩的配置,既显示了很强的主观兴致,也显示了很强的审美追求。“冷主暖辅”色调的配置,形成一种有效的视觉刺激,又赋予了内在的意蕴,也形成了鲜明的特征。以冷色调为主色调,深沉而厚重;暖色调非常鲜明,但只是点缀,形成了“万绿丛中一点红”的审美效果。本来,以冷色调为主色调,与曹禺描写的题材和表现的主题是一致的、恰当的。但是,冷色调的视觉冲击力比较单向,容易造成沉闷的气氛,从而导致戏剧接受者的审美疲劳。因此,为了营造更加强烈的剧场性,曹禺通过人物服饰色彩的暖色调的配置来点染,增强了视觉的冲击力。
二、心理控制与视觉冲击:曹禺配置服饰色彩的原则
对于色彩的运用,中国早在远古时期就已经开始。如《礼记·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4)朱彬:《礼记训纂》(上),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83页。,就是突出的表现。后来不断完善,儒、道、释三家都形成了富于哲学意义的色彩观,对于色彩给人类直觉和心性上的影响,以及人类在色彩的认知和运用上的主观性和经验性,各自都有精彩的论述。当色彩进入人类审美的视域,不管是运用它,还是鉴赏它,又都有自己的讲究和偏好。这种主观性,自然是受主体审美追求主导的。在戏剧中,服饰色彩既是人物区别于他人的外在标志,这种外在的标志,是戏剧意蕴的重要载体,也能从视觉刺激转换成心理影响,深入刺激受众的审美欲望,强化剧场性。正是如此,曹禺戏剧对人物的服饰色彩的配置并不是随意的。纵观曹禺的戏剧,他把握了如下三个审美原则。
(一)以色彩心理学为原则。曹禺对戏剧人物服饰色彩的配置,总是以传统的色彩心理学为依据,让服饰承载着生命的隐喻意义和思想的象征意义。色彩心理学告诉我们,色彩对于人的生理与心理的影响是有其历史沉淀的基本指向的,但受民族、地域、国度和时代的影响,不同的民族、地域、国度和时代对色彩的取向不同,其象征指向也有差异。如历代《舆服志》都记载了历朝帝王服饰色彩的基本色调,除了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之外,秦恢复夏制尚黑,汉恢复周制尚赤,唐服则尚黄而旗帜尚赤,宋代则沿唐制,元制尚黄,明代改制而取法周、汉尚朱(赤),清代则又尚黄。同时,历代帝王的服饰色彩又以季节的变更而变化。《礼记·月令第六》载:孟春之月,天子“衣青衣,服仓玉”;孟夏之月,天子“衣朱衣”,季夏天子“衣黄衣,服黄玉”;孟秋之月,天子“衣白衣,服白玉”;孟冬之月,天子“衣黑衣,服玄玉”。(5)参见陈澔注:《礼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72页、182页、192页、202页。这都显示了不同的隐喻意义。曹禺配置人物服饰色彩首先考虑的就是这种传统心理。如古铜色服饰配在曾皓、高老太爷、潘月亭、秦仲宣、高克明、常五等人身上,自然与其创作的生活题材有关,也与曹禺表现的思想情感有关,是以传统色彩心理学为基础的。古铜是暗黄色的,明度比纯黄色低,有古朴之气,这种黄给人以厚沉、浑浊、不可穿透之感。这种服饰色彩与这些人物身份十分相配,给观众强烈的视觉刺激,形成心理上的压抑感。曾皓在曾公馆、高老太爷在高公馆、潘月亭在大丰银行、秦仲宣在战时医院,都是一手遮天的权力掌控者,是看不清楚的人物。而高克明则在高公馆代理家政,也是权力拥有者;常五则奉命侦察金子是否藏有野男人的事实,也掌握着危及金子命运的大权,都是让人难以琢磨的人物。这些人物穿着古铜色的服饰,是非常妥帖的,是色彩本体意义的灵活运用。对这些人物,受众在情感体验上并没有什么好感。再如红色,花金子始终着红色服饰,是整个戏剧中唯一的亮色配置,显然有曹禺的主观用意的。“红色的感性形式中积淀了社会内容,红色引起的感性愉快中积淀了人的想象和理解,或许原始人从红色想到了与他们生命攸关的火,或许想到了温暖的太阳,或许想到了生命之本的鲜血,反映出主体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6)彭吉象:《艺术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6页。正是这样,花金子着红色服饰,一方面显示了她强烈的主体欲望和生命追求,另一方面也像鲁迅在《女吊》中给女主人公配置红色服饰一样,赋予了相同的文化意蕴——一种强烈的反抗精神。显然,这就拥有了特别的心理主导力。可以说,曹禺在配置人物服饰色彩时的重要原则,就是要对接受者审美心理形成影响力。正是如此,这些人物的存在,增强了戏剧的气氛。
(二)以视觉美学为原则。视觉美学最重要最直接的原理,就是视觉冲击,是以色彩和构图为基础的。话剧作为一种视觉艺术,是依靠舞台色彩和构图形成艺术冲击力的。人物活动与交流场面的系列组接就构成了戏剧。戏剧场面如果是统一的单色调,就会缺乏活性,视觉审美刺激就会缺乏力度;如果色彩过于斑斓繁杂,视觉比较炫乱,会使人焦虑不安,也会影响审美接受效果。曹禺在创作中深谙舞台人物活动的整体画面对于受众的影响力,对于戏剧人物服饰色彩的配置始终遵循着“视觉冲击”的原则,像一个画家一样,十分重视调色和配色,创造色彩的对比度,使之主色明显而又有变化,常常在冷色调中加上暖色调,以人物之间服饰色彩的对比组合形成一幅幅运动的图画,从而优化视觉效果,形成视觉审美的冲击力。所以,曹禺创设出的戏剧场面如同美术画一般,色彩感很强。无论是《雷雨》中“喝药”的场面,还是《日出》中“救孤”的场面,或者是《北京人》中“议婚”的场面,以及《家》中“闹洞房”的场面等等,都是一幅幅美丽的图画,形成了很强的视觉冲击力。例如,《雷雨》第四幕的高潮一场,其色彩配置具有很强的视觉审美的冲击力。在这一场面中,周朴园着白纺绸衬衫外套一件团花的官纱大褂,蘩漪通身黑色旗袍,四凤、侍萍则为朴素暗淡布衣,周萍则是藏青色绸袍,周冲却着白装。尽管色彩从黑到白都有,同一场面呈现出多色调,但以黑白两色为主导,这不仅在视觉上形成了一种参差融合的图画,视觉效果突出,也暗示出黑白对立的冲突。这种色彩明暗对比,纷杂聚集,正暗示了剧情矛盾冲突的聚焦,是对整场悲剧大爆发的暗示。再比如《日出》第三幕,翠喜“穿一件绛红色的棉袍,套上一件绒坎肩,棉鞋棉裤,黑缎带扎住腿”;“小东西神气改了,她穿着蓝布夹上衫,黑裤子”;“胡四穿着皮大衣,琵琶襟紫呢坎肩高领碎花灰缎夹袍,花丝袜子,黑缎鞋,歪戴着西瓜帽,白衬衫袖子有寸来长甩在外边”;王福升“穿一件旧羊皮袍子,里面看得见他的号衣底襟”,小顺子自然是青色或灰色,黑三则是黑色皮袍。在这一幕中,整个戏剧场景本来就非常压抑沉闷,而人物服饰如果都是冷色调,那么就会给戏剧的审美接受带来消极性影响,造成视觉疲劳。所以,曹禺让翠喜穿上了绛红色的棉袍,让胡四穿上偏襟紫呢坎肩、白衬衫而且袖子在外边一寸来长,从而形成色彩的对比度,刺激受众,增强视觉审美效应。这样,作品的剧场性就增强了,能够主导受众的审美心理。
(三)以诗性感知为原则。戏剧人物出现在戏剧中实际上是一个诗性符号,演绎和传达出作者的思想。人物的服饰色彩,既可形成一种视觉冲击力,又可生发出许多联想,传递一些思想信息。因此,戏剧人物的服饰色彩,不是照搬生活,戏剧家应该赋予其诗性感知的符号化功能,这样才会显示更强的审美效果。正是这样,在中国传统戏曲中,人物一出场,受众通过其服饰色彩和脸谱色彩造型,就大致知道其中的能指与所指。曹禺从小接受中国古典戏剧的熏陶,对于戏剧人物服饰色彩在戏剧中的意义自然非常理解,因此在创作中对于戏剧人物服饰色彩的配置非常注意符号化的艺术处理。一方面,曹禺善于进行意象化处理。他总是赋予人物服饰较强的文化意蕴和社会心理印痕,使受众目其色,睹其形,便可发现其诗意。如周朴园的出场,“他穿的衣服,还是二十年前的新装,一件团花的官纱大褂,底下是白纺绸的衬衫”,“他的衣服很舒展地贴在身上,整洁,没有一丝尘垢。”官纱,是指浙江杭绍一带出产的丝织品,分别用生丝和熟丝做经纬线编织而成,既薄又轻,做夏衣凉爽可人,旧时多贡内廷。这是什么颜色呢?就是深紫色或古铜色,整体上很有质感,视觉效果好。因此,这种服饰色彩配置,让人能够从视觉效果入手,引起联想,理解其赋予的比较深厚的意蕴。这种意象化的色彩配置在曹禺戏剧中很普遍。如鲁侍萍的“头还包着一条白布手巾”,仇虎“密结纽绊的蓝布褂”,陈奶妈的“月白色的上身”,愫方的“深蓝毛哗叽织着淡灰斑点的旧旗袍”等等,都具有很强的诗意。另一方面,曹禺善于进行朦胧性提升。曹禺对于人物服饰的色彩,总是恰到好处地予以模糊化处理,形成一种可以理解和想象、富于诗性张力的色彩造型。如陈白露“穿着极薄的晚礼服,颜色鲜艳刺激,多褶的裙裾和上面两条粉飘带,拖在地面如一片云彩。她发际插一朵红花,乌黑的头发烫成小姑娘似的鬈髻,垂在耳际”。这种服饰色彩的配置,除了意象化的发际插的“红花”外,整体上是朦胧的,但又是可感的,在模糊中凸显一种诗性的感知特征,可以让排演者发挥自己的艺术想象,配置“颜色鲜艳刺激”的服饰,既给受众以视觉刺激,又寄予着深意。同时,曹禺还追求人物色彩配置整体性感知效果。诗歌的魅力常常在于诗人营造出了一种整体的审美意境。曹禺在人物色彩配置上也非常重视这种诗性效果。如鲁侍萍,“她的衣服朴素而有身份,旧蓝布裤褂,很洁净地穿在身上。远远地看着,依然像大家户里落魄的妇人。她的高贵的气质和她的丈夫的鄙俗,奸小,恰成一个强烈的对比。她的头还包着一条白布手巾,怕是坐火车围着避土的。”又如顾八奶奶,“穿一件花旗袍镶着灿烂的金边、颜色鲜艳夺目,紧紧地箍在她的身上。走起路来,小鲸鱼似地;肥硕的臀峰,一起一伏,惹得人眼花缭乱,叫人想起有(由)这一层衣服所包裹的除了肉和粗恶以外,不知还有些什么。”再如曾文清“穿着宽大的袍子,服色淡雅大方,举止谈话带着几分懒散模样。然而这是他的自然本色,一望而知淳厚,聪颖,眉宇间蕴藏着灵气”。显然,曹禺配置人物的服饰色彩,十分注重一种整体的视觉效应。这种整体视觉效应,显示的是如诗歌意境一样的美感,从视觉冲击进入一种心理撞击,从而形成一种审美意味,激活剧场的审美效应。
曹禺戏剧人物服饰色彩的配置,不仅将接受心理需求作为重要的依据,而且从强化视觉审美效应入手,同时又突出符号化的诗性张力,从而突出剧场性,强化剧场的审美活性,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在舞台剧中,人物在戏剧场面中是不断行动的,服饰色块自然也随之不断运动,从而形成了一个个流动变化的画面,刺激着受众的审美视觉,使之随着色块的移动而转换关注点。在这里,曹禺配置人物服饰色彩时坚持的三个原则,是紧贴戏剧演出的审美需求的,充分挖掘了服饰色彩视觉审美冲击的潜在可能性。
三、传递情节信息与展示性格命运:曹禺配置服饰色彩的基本功能
色彩在艺术审美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克劳德·莫奈说:“我日夜痴迷于色彩,色彩是我快乐的源泉,同时也是一种折磨。”(7)转引自戴维·霍尔农:《视觉艺术色彩——在艺术与设计中理解与运用色彩》,王雪婷译,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14年,第12页。因为色彩既是一种信息符号,也是一种信息载体,既具有明显的视觉感受特点,又具有潜沉的社会心理意识和文化语义。在文艺创作中,对于色彩的运用,艺术家都赋予了主观性极强的能指与所指,赋予了其传达信息与语义的重要功能,这除了以人类心理意识的共鸣性和相通性为依据之外,还有艺术家自己的主观取向。曹禺戏剧中对于服饰色彩的配置,就显示了这种审美追求。他总是根据人物的身份,紧紧围绕着人物性格和命运,围绕着情节推进,围绕着思想表达,围绕着剧场性营造的需要和戏剧审美的需要,精心配置人物服饰的色彩,强化其审美功能,显示了独到的艺术匠心。
(一)传递情节信息。在叙事艺术作品中,情节是作品的主干,必须首先考虑好如何讲述故事,推进情节。优秀的作家总是利用一切手段,充分发挥文学要素应有的功能,推动情节发展。鲁迅就是这方面的高手,邹七嫂一出现,就加速了阿Q悲剧命运的结束;赵七爷竹布长衫一穿,就预示着后面的情节如何发展。任何一个戏剧家在创作中都必须有“全局”观念,必须拨动各种戏剧要素,推动情节,进而塑造人物,表达思想,营造剧场性。曹禺的创作总是能够调动各种戏剧构件来为情节推进服务。其中,对于戏剧人物服饰色彩的配置,就赋予了这种重任。他总是以戏剧情节推进逻辑为依据,在人物的服饰色彩中传递出了戏剧情节发展的信息。
色彩具有很强的叙事功能,色彩的变化反映时间的更替和事物的发展。曹禺戏剧人物服饰色彩也是如此,总是与戏剧情节的推进联系在一起。在戏剧服饰色彩的配置中,他往往让主要人物的服饰色彩暗示出情节发展的信息。如《原野》中的焦花氏穿着红色服饰就显示了这一点。“红乃是象征热的颜色,富有刺激性的,许多心理上的描写,都用以象征流血与火。所以红象征流血、战争、悲剧、谋杀、危险、毁灭、残忍、犯罪、怨恨、火焰、炙热、勇敢、有力、强项、复仇、羞耻、怒恼、狂怒、热情、贪欲、大声、匆忙、紊乱、虔志、爱国、纯洁、创造力。”(8)《焦菊隐文集》第1卷,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年,第128页。显然,曹禺让她穿上红色服饰,实际上赋予她怨恨、勇敢、有力、复仇的个性精神,也暗示将会出现血腥的场景。但是,这种服饰色彩又经历了四次变化,也预示着戏剧情节的发展。序幕中穿着大红的裤袄和第一幕“穿一件红绸袄,黑缎裤,发髻扎着红丝线”,这是一个复仇者形象,预示着她要做反叛的事情。因此,仇虎一来,她便活起来了,离不开他了。第二幕“穿一身血红色的紧身”,血红象征流血和复仇,预示着与她有关,将出现杀戮。因此,仇虎杀死了焦大星,也让焦母杀死了小黑子。第三幕是背着小白包袱,“血红色衣褂紧贴在身上,右襟扣脱开”,象征匆忙、紊乱的状况出现,于是他们逃到黑林子里总是走不出去。显然,焦花氏的服饰色彩与整个戏剧情节融为一体了。《日出》中的陈白露第一幕“穿着极薄的晚礼服,颜色鲜艳刺激,多褶的裙裾和上面两条粉飘带,拖在地面如一片云彩”,显示了她的热情、勇敢、纯洁、美丽、健康以及渴望爱情,预示着将有浪漫的情节和勇敢、热情的行动出现。于是随即展开的是求婚与救孤的情节;到第四幕,她“穿着黑丝绒的旗袍,周围沿镶洒满小黑点的深黄花边,态度严肃,通身都是黑色”,预示着随着情节的发展,她的命运将发生突转。“黑色就是无光,所以代表夜间、黑暗、恼丧、诱惑、魔术、神秘、无限、睡眠、死亡、罪恶、失望、悲哀、恐怖、贱恶、魔鬼、寡妇、僧人、尼姑。”(9)《焦菊隐文集》第1卷,第130页。曹禺在让陈白露的服装颜色由光亮变为暗色,显然刺激了观众的审美视觉,实际上暗示了戏剧情节发展变化:社会的黑暗与罪恶使人们绝望,无法摆脱悲哀的命运,最终走向死亡。最后,不仅黄省三疯了,潘月亭自杀了,李石清儿子死了,而且陈白露心灵中的希望也从复苏走向了幻灭,最后她绝望地自杀了。于是,整个戏剧走向悲剧结局。《蜕变》中的丁大夫在第一幕中“穿一身深蓝色线条织入淡灰毛呢质地的旧旗袍,外面套一件宽敞的医生白布外衣”出场,到第三幕医院改组后,“她穿一件淡黄色细纹的旧旗袍,外面还是套着一件敞开的白试验衣。”这种从蓝白混合到黄白亮度的提升,暗示了医院环境的改变,预示着情节的发展,给人以暖意与希望,自然也是表现了在医院环境改变后的思想情绪。这种变化有正义战胜邪恶的象征意义。同样,《北京人》中的愫芳在第一幕中“穿一身深蓝色毛哗叽的旧旗袍,宽大适体”,到第三幕二景时“换了一件黑色的旗袍,衬着长长的黑发,苍白的面容,冷静的神色”。愫方在曾家忍气吞声,虽然忧郁,但心存希望。当曾文清出走后又回来了,使她原来寄托的希望全部磨灭,决定要离开曾家。她的这种服饰色彩的变化,显示了这种悲剧过程。
(二)展示人物的性格和命运。服饰作为人的重要外显特征,总是与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密切相关,虽然我们不能以貌取人,但认真去分析人物的衣着,总是能够发现其精神状态、性格特征和命运状态的一些信息。因为,“色彩具有极强的视觉张力与表现力,正因为它的这种多样性与复杂性,使得它在艺术表现形式上有着极为丰富的性格表现。”(10)张岩:《色彩艺术与构成》,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50页。就文学人物而言,其服饰色彩总是与其性格特征和命运状态密切相关。在小说人物服饰色彩的配置上,鲁迅就堪称圣手,从《祝福》中祥林嫂的服饰色彩到《女吊》中女主人公的服饰色彩,既显示了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又预示了故事情节的变化。在戏剧创作中,曹禺对于戏剧人物服饰色彩的配置,也是十分用心的。曹禺写戏总是写人,他为人物设置的服饰色彩,总是以人物描写为依据,进行主观性把握,彰显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命运起伏状态,让服饰色彩泄露出人物的个性特征与命运走向。这是一个鲜明的特点,也是曹禺戏剧人物服饰色彩的一个审美功能。
在戏剧中,人物是推动戏剧情节发展的主要原动力。(11)刘家思:《曹禺戏剧的剧场性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53页。这不仅是人物的性格与命运等内核主体在起作用,而且人物外在形态也起着作用。在戏剧演出中,人物的服饰色彩既是外在的视觉要素,也是人物描写的组成部分,是营造剧场性的重要构件。曹禺对于人物服饰色彩的配置,在人物描写上赋予了很强的艺术功能,不仅体现在彰显人物性格与精神的层面上,而且体现在对人物命运的暗示上,也表现在对故事情节的推进上。如《雷雨》中的周萍、《北京人》中的曾文清和《家》中的觉新,三人的服饰都是屈就、抑郁、悲哀的暗蓝色服饰,显然预设了他们软弱的性格。他们都是大家庭温室氛围中发酵的软骨儿,他们清楚自己处境,却懦弱地不愿做出丝毫的努力和抵抗,自然也预设了他们的悲剧命运。《家》中的瑞珏,除了第一幕第二景闹洞房时,“穿着粉红缎绣花服”和“红洋绉百褶裙子”之外,其他时候都比较素雅,但亮度不断变化。闹完洞房后,“瑞珏换了轻便的衣装:一身天蓝色的软缎短袄和长裙,裙子下沿绣着黑白两色的花朵,红缎鞋屏着金花。”到第二幕第一景,“穿着淡青洋纱上身和长裤,白鞋,发髻戴一朵白绒线花,一身素净,正为着公公戴孝”,第二景则“穿着一套淡蓝色隐约织了一点灰丝的羽纱衣裙,夹上身滚着灰边”。而到第三幕第二景,则“穿一件宽肥的深蓝色布袄”。“蓝是天空的颜色,表现伟大、寂静,无争的神气。世上恐怕再没有比天更神秘、沉默、舒展的了。所以蓝色象征稳固、肯定、真理、神圣、神秘、庄重、尊严、悲哀、希望、爱、忠心、大量、沉默、永久。”(12)《焦菊隐文集》第1卷,第130页。瑞珏新婚时的天蓝色是一种亮蓝色调,表现的是伟大、寂静、无争、神圣、庄重、尊严、希望、爱与忠心的意思,展现了纯净明亮的世界,而后来变成淡青、淡蓝灰色和深蓝色,暗示着人物从单纯天真到沉郁悲哀的生命轨迹,观众不仅可以感受到瑞珏在不同时期的性格和情感的变化,而且可以感受到她日益走向悲剧结局的不幸命运。这种蓝色明度的递进给观众以审美联想,其色调明度由浅入深的变化,暗示了剧情的发展。当然,在曹禺笔下,还有一些人物的服饰色彩只是显示人物命运的进程。《家》的婉儿在第一幕中,是在高家做自由的丫头,她“穿着白底子小蓝花裤,浅蓝夏布短褂,背后垂一条稍长的发辫”。但不幸被冯乐山收房后,压制和痛苦使原本如花般的生命枯萎焉息,所以在第三幕中,婉儿回到高公馆做客,这时“穿着藏青的衣裙,式样老旧,紧紧贴在身上像桎梏。头发梳成髻,扎着暗色的头绳”。婉儿的服饰由单纯鲜亮的色彩蓝白变为冷色调的暗色藏青,这种色彩变化暗示着人物命运的悲剧性变化。
(三)激发受众的审美感觉与接受欲望。色彩是影响世界观感的物态,具有强烈的心理感应作用。“当色彩现象对人的视神经产生刺激时,自然就会引起心理上的兴奋感,从而唤起感觉的经验。”(13)张康夫:《色彩文化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67页。话剧是以视觉接受为主体的舞台艺术,其中心是戏剧人物。这是刺激受众审美欲望的内在动力。作为戏剧大师,曹禺深知服饰色彩是戏剧人物凸显个性化和视觉化的重要元素,能够给受众以审美刺激,激发剧场感应力。因此,他在配置戏剧服饰色彩时,除了赋予其塑造人物性格、展示人物命运变化和暗示情节发展的重任之外,还充分考虑戏剧接受者的心理状态,服从剧场性的需要,让服饰色彩成为刺激受众审美感觉与接受欲望的重要手段,增强剧场性。他采取了突出主色,保持一定的参差和层次的策略,严格排除单色调,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首先,从整体上看,突出主色调,营造整体气氛。曹禺戏剧人物的服饰配色以冷色调为主。《雷雨》的服饰色彩以“古铜色”“黑色”“藏青”“蓝色”为主体;《原野》的服饰色彩以“黑色”“古铜”“藏青”“灰色”为主体;《家》的服饰色彩以“古铜色”“黑色”“藏青”“蓝色”为主体;《北京人》的服饰色彩以“黑色”“藏青”“灰色”为主体,如此等等,形成了整体上“沉闷”的气氛。这有利于塑造人物和表现主题。曹禺说:“宇宙正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14)曹禺:《雷雨·序》,《曹禺全集》第1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8页。这不仅是曹禺在《雷雨》中想要表现的哲学意蕴,也是他大多数戏剧作品的总体气氛。这种气氛集中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沉闷”。曹禺描写的是一个个“闷”死人的环境。因此,他“用一种悲悯的心情来写剧中人物的争执”,“诚恳地祈望着看戏的人们也以一种悲悯的眼来俯视这群地上的人们”。(15)曹禺:《雷雨·序》,《曹禺全集》第1卷,第8页。那么,如何使受众心生“悲悯”呢?曹禺说:“所以我最推崇我的观众,我视他们,如神仙,如佛,如先知,我献给他们以未来先知的神奇,我使他们征兆似地觉出来这酝酿中的阴霾,预知这样不会引出好结果。”(16)曹禺:《雷雨·序》,《曹禺全集》第1卷,第8页。曹禺是如何使受众“征兆似地觉出来这酝酿中的阴霾,预知这样不会引出好结果”的呢?人物的服饰色彩配置就是曹禺泄露“天机”的一个重要窗口。就整部戏剧的服饰色彩配置来看,以冷色调为主,就营造了戏剧气氛,而从个体服饰的色彩配置来看,不仅显示其个性特征,而且暗示出人物的命运走向。这样,受众容易产生一种“悲悯”的情怀,关注着人物命运的进程,于是作品主导着受众的审美心理。
其次,在人物个体的服饰配置上,突出参差性。一般来说,一个人物的服饰至少有主辅两种色调。例如,《雷雨》中蘩漪的服饰色彩除了“通身是黑色”之外,其“旗袍镶着灰银色的花边”。为什么还要镶着花边呢?实际上是从剧场接受中的视觉效果来考虑的,这样有变化,有调节,主次分明,看起来舒服一些;《日出》中的黄省三“只穿了一件鹅黄色旧棉袍,上面染满油污,底下只是一条黑夹裤”,这个无辜的受害者、边缘小人物的服饰主色调是“鹅黄色”旧棉袍,为什么要配上“黑夹裤”呢?自然不仅彰显其生命状态,而且包含着对于视觉效果的追求。为了追求人物服饰色彩配置的层次性,构成形式上的美感,形成一种视觉冲击,曹禺总是让男人套上马褂或者坎肩,以及其他饰物和佩戴。如《日出》中潘月亭的着装是古铜色貂绒皮袍,“上面套着是缎坎肩,上面挂着金表链和翠坠儿”,《家》中高克明的服饰是“一件不十分新的古铜色缎袍,外面罩着黑呢马褂,戴一副金边眼镜,瘦嶙嶙的指节上只有一只金戒指”。显然,就穿着打扮来说,曹禺笔下的人物都是主辅色融为一体,视觉效果非常好。有的人物,曹禺给他们加入黑色或白色,形成干净利落的配色,给观众一种色彩的醒目感。如《蜕变》中丁大夫第一幕出场,“穿一身深蓝色线条织入淡灰毛呢质地的旧旗袍,外面套一件宽敞的医生白布外衣。”《家》中的梅小姐“穿一件银灰色的夹衫,镶着素白的滚边,一条较上身尤淡的灰白色薄薄的毛织品长裙,几乎拖在脚面”。这种层次性和参差感产生的审美视觉效果,不是单一色调效果能够比拟的。这种视觉审美感受使观众能从视觉进入意觉再转换成审美注意力,从而在心理上倾注于对人物命运的关怀。这样,其独特的剧场性效应就产生了。
戏剧文学创作的终极目标是在剧场中成功演出,视觉刺激是审美接受活动中信息刺激与交流的主体形态,色彩本身固有的视觉效果在作品中就拥有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服饰既是一种文化元素,也是一种社会心理载体,还是一种视觉手段。“从本质上来讲,人类感知到的色彩仅仅是物体的显现,这与物体的实际色彩完全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人类只会感知到能够感知到的色彩,这种色彩感知仅仅存在于我们人类的大脑中。”(17)玛依耶芙娜:《色彩心理学》,闫泓多译,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15年,第6页。不同色彩沉淀着深厚的文化心理蕴含,显示出人类通行的精神取向与价值观念,这就使人面对色彩时心理上会受到影响。戏剧文学的创作必须考虑剧场中观看戏剧演出的受众需要,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艺术手段,运用各种可能的艺术因素,从视觉上冲击受众,从心理上控制受众,从文化上感染受众,从思想上影响受众。因此,人物服饰色彩的配置得当就十分重要。曹禺以冷色调为主、以暖色调为辅的服饰色彩配置,就是围绕营造剧场性的需要而创设的。在作品中,这些不同色彩的服饰,不仅因为颜色本身多层次性和多极化的隐喻指向,向我们传递了情节信息,暗示了人物的性格命运,又因为舞台上色彩的对比差异强化了视觉刺激,使不同的接受主体产生了不同的主体认知和自我阐释,可以满足更多的审美期待。于是,这种舞台上运动着的色块,在刺激和强化戏剧接受者的审美视觉的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主导着他们的审美兴趣,激活其审美情绪,影响其心理和情感,自然剧场性就增强了,审美接受效果也就优化了。因此,曹禺戏剧对于服饰色彩的巧妙运用,显示了他为发挥色彩艺术的审美功能而做出的努力,其戏剧的艺术张力也因此得到了增强。这是值得我们注意和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