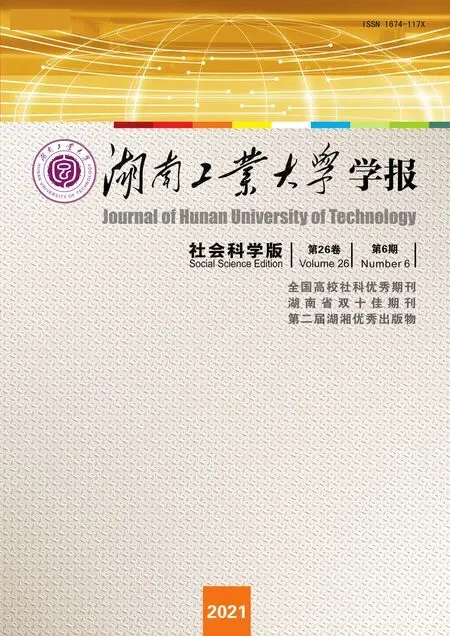《读史方舆纪要》大同地区路、堡记载辨误
张永江 ,彭佳成
(中国人民大学 清史研究所,北京 100872)
《读史方舆纪要》(以下简称《纪要》)成书于清康熙年间,是明末清初时人顾祖禹撰写的历史地理著作。该书虽以刻本形式辗转流传,但在作者生前并未定稿。近年来,贺次君、施和金等人对《纪要》进行了整理与校订,可以说,他们整理的2005 年中华书局版《纪要》是目前为止最为完整和通行的版本。不过,由于《纪要》篇幅宏大、流传曲折,整理本中仍存在错漏之处。《纪要》出版后,有不少学者曾对其中的问题进行辨析。笔者在阅读《纪要·山西六》时,也发现书中对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所辖堡的名称、数量记载自相矛盾。
其一,大同东路中,《纪要》记录迎恩、败胡、瓦窑口、永嘉等四堡,在总结处却言:“已上共七堡,与阳和、天成、高山、镇虏四卫俱属大同东路管辖。”[1]2026其二,大同中路中,《纪要》记录守口、靖虏、镇门、镇口、镇宁、云阳、牛心、红土、黄土等九堡,在总结处却言:“已上十一堡,与左、右、云、玉四卫俱属大同中路管辖云。”[1]2023-2024其三,大同西路中,《纪要》记录马营河、破胡、残胡、杀胡、马堡、铁山、三屯、阻胡等八堡,在总结处却言:“以上三堡,俱大同西路管辖。”[1]2027-2028
实际上,明末清初亦有另一部历史地理著作即顾炎武所著《天下郡国利病书》对明代大同地区形势、险要、卫所、城堡等进行了记录。《天下郡国利病书》成书于康熙初年,与《纪要》成书时间较近,书中对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所辖城堡的记载为:
东路参将驻天城城,所辖阳和、天城、靖虏、瓦窑、守口、永嘉、镇口、镇门、镇宁九城堡。
中路参将驻右卫城,所辖左卫、右卫、杀胡、破胡、铁山、牛心、残胡、马堡、云阳、红土、黄土、三屯、马营河一十三城堡。
西路参将驻平虏城,所辖平虏、迎恩、败胡、阻胡四城堡[2]1947。
其中,东路参将所辖阳和、天城,中路参将所辖左卫、右卫以及西路参将所辖平虏为城。若剔除城,可以发现《天下郡国利病书》总结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所辖堡的数目与《纪要》恰好相同,但两者对各路所辖堡名的记载相异。两部著作的作者都是饱学之士,著作性质也相近,那么,哪一家的记载更为准确呢?
对此,逻辑上不外乎两种可能:其一,顾炎武或顾祖禹对明代大同路、堡建置记载有误;其二,《纪要》成书于康熙年间,顾祖禹在撰写之时,或受到了清初大同路、堡地理方位及建置变化的影响。以下试比对资料,逐一检证。
一 明代史籍对大同东路、中路、西路所辖边堡之记载
由于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所辖各堡均为明朝设立,因此若要考察《纪要》《天下郡国利病书》的正误,需参阅明代记录。《三云筹俎考》《宣大山西三镇图说》作为明代方志,对大同地区的军事形势、建置沿革等方面有所论述,两书对大同各路所辖堡的记载大致相同。
大同东路:本路参将分属阳、高、天城、镇虏四卫及靖虏、守口、镇宁、镇口、镇门、瓦窑、永嘉等七堡,辖六守备、三操守。分边沿长九十六里四分,边墩一百七十八座,火路墩九十座[3]116,[4]334-336。
大同中路:本路参将原设左卫,嘉靖三十三年始移右卫驻扎……各城堡右卫马营河堡、破胡、马堡、残胡、杀胡堡、铁山堡俱极冲,左卫三屯堡、云阳堡、牛心堡、黄土堡、红土堡稍次之[3]132,[4]343-345。
大同西路:本路参将分辖平虏、败胡、迎恩、阻胡,凡四城堡,俱极冲之地。边墙东起灭胡堡界,西止南沙河,沿长四十七里六分有奇,边墩六十八座,火路墩四十八座,小市场一处。幅员非广,而以一参将、两守备、两操守当之,盖地冲故也[3]129,[4]347-348。
可见,《三云筹俎考》《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对边堡数目的记载,与《纪要》《天下郡国利病书》相同,均为大同东路辖七堡,大同中路辖十一堡,大同西路辖三堡,但对各路所辖堡名的记录不同。从成书时间来看,《宣大山西三镇图说》《三云筹俎考》均成书于万历年间。考虑到明末战争频发、军事设置变化较多的情况,若仅与《三云筹俎考》《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对比,恐难全面考察明代大同路、堡的建置沿革。据此,笔者参阅了年代较近的《(康熙)山西通志》。书中对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的记载为:
东路参将所管阳和、天城、靖鲁、瓦窑口、守口、永嘉、镇口、镇门、镇宁九城堡,援兵营、老家营并守城杂役,共五千四百七十二名。
中路参将所管左卫、右卫、杀虎、破虎、铁山、牛心、残虎、马堡、云阳、红土、黄土、三屯、马营河一十三城堡,援兵营、老家营并守城杂役,共九千九百二名。
西路参将所管平鲁、迎恩、败虎、阻虎四城堡,援兵营、老家营并守城杂役,共四千五百八名[5]329。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三云筹俎考》《宣大山西三镇图说》与《(康熙)山西通志》的记载相同。由此,可以推论明末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的建置未发生变化。
从时代背景看,大同镇属明九边之一。顾祖禹在《纪要》中亦强调了大同的战略地位:“女真之亡辽,蒙古之亡金,皆先下大同,燕京不能复固矣。故明都燕,以郡为肩背之地,镇守攸重。正统末恃以挫狡寇之锋,天顺石亨镇此,尝言:‘大同士马甲天下,若专制大同,北塞紫荆,东据临清,决高邮之堤以绝饷道,京师可不战而困。’盖府据天下之脊,自昔用武地也。”[1]1993可见,大同作为京师的屏障,在明代具有重要的军事功能。嘉靖、万历年间,明廷出于军事防御的需要,修筑了大同一带边堡。
万历末年,明廷虽仍面临着漠南蒙古的挑战,但此时蒙古处于分裂状态。林丹汗东迁,难以构成较大威胁。与之相应的,辽东地区满洲势力逐渐崛起。万历四十四年(1616 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建立“大金”,基本完成了女真部落的统一。2 年后,以“七大恨”作为伐明的檄文,向明军发动进攻。万历四十七年(1619 年),努尔哈赤在萨尔浒之战中大败明军,在辽东战场上占据了主导权。可以说,此时明朝军事防御的重点已转向辽东一线。
通过史籍比对与时代背景的考察,可以确定顾炎武所著《天下郡国利病书》对明代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记载无误,而《纪要》的相关记载存在问题,但这些讹误是如何形成的,仍需分析。
二 《读史方舆纪要》对大同东路、中路、西路所辖堡之记载
前文述及,在大同东路中,《纪要》与明代资料在迎恩堡、败胡堡的记载方面相异,迎恩堡、败胡堡在明代资料中属大同西路管辖,《纪要》对迎恩堡、败胡堡建置沿革、地理方位的记载如下文所示,其可与 大同守道分辖西路总图(图1)进行比对。

图1 大同守道分辖西路总图[3]420-421
迎恩堡:在平虏卫西北四十里。嘉靖二十三年筑,万历初增修,周一里有奇。分边十里零,内镇川墩最冲,老鹤嘴次之。嘉靖中石州之祸,此为难治。款塞后设小市场于此,亦防御要处。
败胡堡:在平虏卫北四十里。嘉靖二十三年筑,隆庆六年增修,周一里有奇。分边八里零,内镇川墩、泉儿沟最冲。嘉靖中寇由此入犯朔州一带,为冲险之地[1]2026。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纪要》所载边堡地理方位与 大同守道分辖西路总图所示大致相符,但距离里程、分边沿长的记载相异。《宣大山西三镇图说》记载:“迎恩堡东至平虏城三十里……分边沿长一十里五分。败胡堡东至平虏城三十里……分边沿长八里三分。”[3]423-424
大同中路中,《纪要》与明代资料在守口堡、靖虏堡、镇门堡、镇口堡、镇宁堡记载方面相异,守口堡等五堡在明代资料中属大同东路管辖。《纪要》对守口堡等五堡在建置沿革、地理方位方面的记载如下所示。
守口堡:在阳和卫西北十五里。嘉靖二十五年置,隆庆六年增修,周一里有奇。分边十二里零。堡为阳和之肩背,隆庆初寇从此入犯,全镇告急。后徙市于此,防御要地也。
靖虏堡:在守口西二十里。嘉靖二十五年置,隆庆六年增修,周二里有奇。分边十一里零,内碾儿沟、子濠沟诸处为最冲。堡一望平川,隆庆初由沙沟入犯,戒备不可不预也。
镇门堡:在守口东一十里。嘉靖二十六年筑,隆庆六年增修,周一里有奇。分边十三里零,内大、小鹁鸽峪极冲。
镇口堡:在阳和东北六十里。嘉靖二十五年筑,隆庆六年增修,周一里有奇。分边十三里零,内榆林、水磨等口极冲。嘉靖间寇尝由此入犯天成一带,备御尤切。
镇宁堡:在阳和东北八十里。嘉靖四十四年置,隆庆六年增筑,周一里有奇。分边十三里,内威狐口、白羊口极冲[1]2023。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纪要》所载各堡地理方位与 大同阳和道辖东路总图(图2)所示大致相符,但文字记载略有不同。一方面,《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在描述镇口堡、镇宁堡地理方位之时,与《纪要》选择的参照物不同:“镇口堡南至天城三十五里,西至镇门堡二十里,北至本堡边墙一里,东至镇宁堡一十八里。镇宁堡南至天城二十里,西至镇口堡十八里,北至本堡边墙一里,东至瓦窑口堡二十里。”[3]398-399另一方面,《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对镇门堡设置时间的记载为嘉靖二十五年[3]119,而《纪要》为嘉靖二十六年。

图2 大同阳和道辖东路总图[3]391-392
大同西路中,《纪要》与明代资料在马营河堡、破胡堡、残胡堡、杀胡堡、马堡、铁山堡、三屯堡的记载方面相异,马营河等七堡在明代资料中属大同中路管辖。《纪要》对马营河等七堡记载如下所示。
马营河堡:在右卫西北十余里。万历元年土筑,周不及一里。分边五里零,内十水口最冲。
破胡堡:在右卫东北三十里。嘉靖二十三年筑,万历二年增修,周二里有奇。分边四里零,内平梁、镇静二处极冲。
残胡堡:在右卫北三十里。嘉靖二十三年筑,隆庆六年增修,周一里有奇。分边十五里零,内东莺、北塔、首阳、林儿极冲,芹菜坡诸处次之。
杀胡堡:在右卫西北四十里。嘉靖二十三年置,万历三年增修,周二里。分边二十里零。
马堡:在残胡堡东。嘉靖二十五年设,万历初增修,周一里有奇。分边十里零,内山前沟、二道沟、虎头墩、驼山、双沟子最冲,而山前墩尤甚。
铁山堡:在左卫西七十里。嘉靖二十八年筑,万历二年增修,周一里有奇。分边十里零,内双墙墩极冲、孔家、半坡、莺黎稍次之。
三屯堡:在左卫北。隆庆三年土筑,万历二年增修,周不及一里。分边亦仅一里零……堡虽临边,而山险足恃,左卫之屏障也[1]2027-2028。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纪要》所载各堡方位与大同左卫道辖中路总图(图3)所示大致相符,但文字记载存在差异。差异因何而生?一方面,两者在论述破胡堡、残胡堡、铁山堡地理方位之时,选取的参照物不同。《宣大山西三镇图说》记载:“破胡堡南至牛心山堡三十里,西至马堡一十五里,北至边墙一里,东至宁虏堡三十里。残胡堡南至黄土堡六十里,西至杀胡堡三十里,北至边墙五里,东至破胡堡三十里。铁山堡南至云石堡二十里,西至边墙三十里,北至右卫城二十里,东至红土堡二十里。”[3]432,434,436另一方面,在《宣大山西三镇图说》中,铁山堡于嘉靖三十八年修筑[3]137,杀胡堡于万历二年增修[3]135,而《纪要》记载分别为嘉靖二十八年、万历三年,时间上与前者有差异。

图3 大同左卫道辖中路总图[3]427-428
综上所述,《纪要》所载各堡方位及建置沿革,与《宣大山西三镇图说》等明代著作大致相同,只是对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所辖堡名的记载不同。考虑到《纪要》成书于康熙年间的情况,顾祖禹对大同地区路、堡记载的错误,很有可能与清初大同地方建置的地理方位、军政建置变化有关。
三 清初史料对大同东路、中路、西路所辖堡之记载
2005 年中华书局版《纪要》点校说明记载:“顾祖禹最初撰写《读史方舆纪要》时,凡叙述明代事实,均用‘国初’、‘国朝’等字样,晚年修改书稿时,又改作‘明初’、‘明朝’。因为卷帙浩繁的缘故,圈改多有遗漏者……《读史方舆纪要》中还出现四处清初改置州县的文字记载。”[1]3可见,顾祖禹在撰写《纪要》时,受时局变动影响颇深。与此同时,彭士望所著《读史方舆纪要叙》记载:“祖禹之创是书也,年二十九……经二十年,始成是书,自为历代州域形势通论,至天文分野,共百三十卷,可六千页。”[1]3-4据此,可以确定《纪要》初稿于顾祖禹49 岁时完成,即在康熙十八年(1679年)完成。因此,若要对《纪要》记述内容进行考察,还需参阅清代史籍。
首先,就地理方位而言,清初《(康熙)山西通志》《(雍正)朔平府志》都兼述前明情况,其中附有边堡示意图,可对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所辖边堡的地理位置进行考察。顺治、康熙年间,大同府仍袭明制,并无大改动。雍正三年(1725 年),清廷发布谕令,设山西朔平、宁武二府。改右玉卫为右玉县,左云卫为左云县,平鲁卫为平鲁县,并割大同府属之朔州、马邑县,俱隶朔平府管辖。改宁武所为宁武县,神池堡为神池县,偏关所为偏关县,五寨堡为五寨县,俱隶宁武府管辖。改天镇卫为天镇县,阳高卫为阳高县,移原驻阳高通判驻府城,俱隶大同府管辖。改宁化所为巡检司,隶宁武县管辖[6]。受此影响,大同西路、大同中路所辖堡被划入朔平府,大同东路所辖堡被划入大同府。
就大同西路、大同中路而言,前文大同守道分辖西路总图与大同左卫道辖中路总图中,两路所辖堡由西至东的排列顺序如下所示。
大同西路:阻虎堡、迎恩堡、败虎堡。
大同中路:铁山堡、杀虎堡、马营河堡、红土堡、黄土堡、残虎堡、马堡、牛心堡、云阳堡、破虎堡、三屯堡。
《(雍正)朔平府志》所载右玉县疆域山川边关城堡图[7]144-145、左云县疆域山川边关城堡图[7]146-147、平鲁县疆域山川边关城堡图[7]148-149中,对各县所辖边关城堡方位亦有记录,各堡由西至东的排列顺序如下所示。
右玉县:云石堡、威平堡、归化城、铁山堡、威远城、杀虎、马营河堡、祁河堡、红土堡、黄土堡、残虎堡、牛心堡、马堡、云阳堡、破虎堡。
左云县:三屯堡、宁鲁堡、威鲁堡、灭鲁堡、云西堡、破鲁堡、助马堡、保安堡、高山城、拒门堡、云冈堡。
平鲁县:将军会堡、灭虎堡、阻虎堡、迎恩堡、败虎堡、乃河堡、大水堡、井坪城、威虎堡。
结合朔平府边关城堡总图[7]142-143的记录,上述三县由西至东依次排列顺序为:平鲁、右玉、左云。故而,若将《(雍正)朔平府志》的记载与明代资料对比,可以发现大同西路、大同中路所辖边堡的相对位置虽与《(雍正)朔平府志》所载略有差异,但未发生过大变化。
就大同东路而言,前文大同阳和道辖东路总图记载了大同东路所辖边堡位置,由西向东依次为:靖鲁、守口、镇门、镇口、镇宁、瓦窑口、永嘉。若将其与《(康熙)山西通志》所载山西边关图(图4)相比,可发现大同东路所辖各堡的相对位置未发生改变。与此同时,许鸿磐《方舆考证》中,对朔平府、大同府沿长城一线边堡情况亦有论述:

图4 山西边关图[5]76-77
朔平府长城……按自左云县拒门堡,接大同拒墙堡起,迤西曰助马堡,折而西南曰保安堡,再西曰威鲁堡,经左云北而西曰宁鲁堡,又西北为右玉县之破虎堡,再西北曰残虎堡,又西至府城北曰杀虎口,折而西南曰铁山堡,再西南曰云石堡,再西南为平鲁县之威虎堡,再西南曰大水口,再西南曰败虎堡,再西南曰阻虎堡,再西南曰灭虎堡,再西南曰将军会堡,再西南曰红门市口,西接偏关县之水边营。此朔平府沿边一带形势之大略也[8]。
大同府边墙即古长城也……其沿边一带,东起平远堡,接直隶宣化府怀安县界,迤西南曰新平堡,再西南曰瓦窑堡,历天镇县而西曰镇口堡,再西曰镇门堡,历阳和县而西曰守口堡,再西曰靖鲁堡,曰镇边堡,曰镇川堡,曰宏赐堡,至府北曰得胜堡,再西曰拒墙堡,接朔平府左云县拒门堡界,此沿边一带形势之大略也[9]。
较晚的资料也有参证价值。许鸿磐《方舆考证》成书于清道光年间。清前期,随着军事形势的变化,清廷曾对朔平、大同两府边堡进行过裁撤,故与图4 相比,《方舆考证》所载边堡数量较少,但从边堡的地理方位来看,两者大致相符。由此可以确定,在清前期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所辖边堡位置未发生过大变化。实际上,从边堡的性质来看,其多由黄土夯筑而成,难以移动。随着北部边疆形势的变化,这些边堡或增修或裁撤,又或逐渐演变为民堡、聚落。
其次,就建置沿革而言,笔者发现,顾祖禹没有直接记录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所辖边堡在清代的建置沿革情况。然而,在《(康熙)山西通志》《(雍正)朔平府志》中,对边堡的文字记载与《纪要》相比,已发生变化。
一方面,《(康熙)山西通志》中所载清代大同镇边堡数量与《纪要》相比有所减少,仅涉及瓦窑口、镇门等15 堡[5]339-341;另一方面,《(雍正)朔平府志》记载了大同西路、大同中路所辖堡的裁撤情况。大同中路所辖马营河堡、红土堡、黄土堡、残虎堡、马堡、牛心堡、云阳堡、三屯堡,在顺治年间已被裁撤。
右玉县境内马营河堡、残虎堡、马堡、红土堡、黄土堡、祁河堡、牛心堡、威平堡、云阳堡,以上九堡,建自明嘉靖、万历年间,俱设官兵。国朝顺治年间裁撤[7]164。
左云县境内云西堡、云冈堡、灭鲁堡、三屯堡,以上四堡,建自明嘉靖、隆庆、万历年间,俱设官兵。国朝顺治年间奉裁[7]166。
平鲁县境内灭虎堡,建自明嘉靖年间,内设官兵。国朝顺治年间奉裁[7]168。
就大同东路而言,《(雍正)山西通志》《(乾隆)天镇县志》记载了靖鲁堡、镇宁堡、镇口堡、永嘉堡的裁撤情况。
《(雍正)山西通志》:明制靖鲁堡,今隶守口堡汛[10]。
《(乾隆)天镇县志》:镇宁堡,明设操守一员,兵二百名,今裁并瓦窑口汛……镇口堡,明设操守一员,今裁归并瓦窑口汛……永嘉堡,设操守一员,兵五百名,今裁归并瓦窑口汛……瓦窑口堡,国朝顺治五年,复改操守,裁去坐堡。只存兵九十一名。康熙元年,改为把总。五十七年,改为千总,额设兵一百名[11]。
与此同时,《(康熙)山西通志》所载原明代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所辖边堡官兵数量,与明代相比已大幅减少。
《(康熙)山西通志》:瓦窑口堡设官兵83名;镇门堡92 名;守口堡87 名;杀虎堡182 名;败虎堡83 名;阻虎堡70 名;破虎堡70 名[5]340-341。
《宣大山西三镇图说》:明代大同东路所辖守口堡设官兵466 名;靖鲁堡461 名;镇门堡512 名;镇口堡311 名;镇宁堡302 名;瓦窑口堡468 名;永嘉堡298 名。大同西路所辖迎恩堡设官兵545 名;败虎堡434 名;阻虎堡373 名。大同中路所辖马营河堡设官兵200 名;破虎堡700 名;杀虎堡778名;残虎堡395 名;马堡364 名;铁山堡534 名;三屯堡292 名;云阳堡313 名;牛心堡434 名;红土堡275 名;黄土堡321 名[3]118-139。
结合时代背景来看,1635 年,随着漠南蒙古收归中央直接管辖,原明代九边地区的军事战略地位逐渐下降。顺治元年(1644 年),宣府巡抚李鉴上疏:“上谷一府,在明朝为边镇,在我朝为腹里。前经定制,兵多而员冗,今宜议裁汰。”[12]63宣、大两镇在地理位置上十分接近,故李鉴在此处对宣府军事形势的论述,一定程度上也涉及了大同地位的变化,即由“边地”变为“腹里”。顺治元年(1644 年)六月,大同总兵官姜瓖消灭大顺军后,向清廷投降[12]61。自此,大同等处收归中央直接管辖。顺治五年(1648 年),清军为应对漠北蒙古的动乱,派遣明英亲王阿济格领兵前往大同,引发了“姜瓖之乱”。同年十二月,“大同总兵官姜瓖闭门叛”[13]。顺治六年(1649 年)八月,杨振威与裴季中等人合谋,斩杀了姜瓖及其兄姜琳、弟有光,向清廷表示归顺[14]365,大同一带重新恢复了平静;但由于大同姜瓖与清军的激烈对峙,大同镇亦遭遇了浩劫。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 “姜瓖之乱”的爆发,促使清廷对大同驻军进行了调整。同年九月,清廷发布谕令:
丁丑。更定宣、大二镇官兵经制,宣、大总督标兵二千名,分二营……平鲁、井坪、天城、威远、得胜、助马、新平等路参将、中军守备各一员,兵各四百名。右卫、山阴、应州、马邑、高山、聚落、怀仁等城守备各一员,兵各二百名。宏赐、镇川、拒墙、镇边、破虎、灭虎、镇羌、将军会、杀虎、迎恩、破鲁、保安、拒门、威虎、镇门、镇宁、灭鲁、镇鲁、保平、守口、牛心、西安、乃河、云冈、镇口、败虎、阻虎、平远、威鲁、宁鲁、云石等堡,大水、瓦窑二口操守各一员,兵各一百名[14]368。
可见,在顺治初年,清廷已对大同路、堡建置进行调整,不再使用东中西三路总称,而是使用原来的城堡名称代替,转变为平鲁、井坪、天城、威远、得胜、助马、新平等说法。顺治九年(1652年)成书的《云中郡志》中亦记载:“得胜路官兵三百二员名……新平路官兵三百二员名……助马路官兵三百二员名……威远路官兵三百二员名……平鲁路官兵三百二员名……井坪路官兵三百二员名。”[15]但顾祖禹在《纪要》中,仍沿用大同东路、大同中路等说法,足见他并未受到清初史志记载的影响。
综上所述,山西大同作为明九边之一,在防御漠南蒙古之时,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1635年漠南蒙古收归中央管辖,原明九边地区的军事战略地位逐渐下降。虽然在清前期,面对青海、漠西蒙古等部的威胁,大同仍承担了一定的军事防御任务,但其功能已呈现出由军事向非军事功能的演变趋势,杀虎堡等边堡亦由明时的军事堡垒转变为集军事、交通、贸易等多重角色于一体的城镇。然而,若仔细阅读《纪要》,便会发现顾祖禹未对清初大同地区路、堡的新变化进行记载。据此可以确定,顾祖禹对大同路、堡名称及建置沿革的记录截止于明代。
关于《纪要·山西六》对大同路、堡记载的错漏,既然已经排除了客观因素,就应该从主观方面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或存在以下两种可能:其一是顾祖禹撰书过程中出现了错误。一方面,2005 年中华书局版《纪要·山西六》校勘记中记载:“附见山西行都司在大同府城内至以上四堡俱威远路管辖,此五千二百三十八字底本全脱,今据职本、敷本、邹本补。”[1]2054在2005 年中华书局版《纪要》整理过程中,其以北京图书馆特藏善本“商丘宋氏纬萧草堂本”为底本,顾祖禹原稿本、光绪二十五年新化三味书室邹代过校本、嘉庆十六年龙万育所刊敷文阁本为参校本[1]1。据此,笔者查阅了“商丘宋氏纬萧草堂本”与“顾祖禹原稿本”,发现商丘宋氏纬萧草堂本”对山西行都司至威远路部分的记录,的确存在缺载现象,然而,《读史方舆纪要稿本》对该处记载得十分详尽。虽然顾祖禹在记载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情况之时,为避免受文字狱影响,对部分堡名进行涂改,如将“靖虏堡”中的“虏”字涂改为“卤”,将“残胡堡”中的“胡”字涂改为“狐”等[16]。但总的来说,《读史方舆纪要稿本》的记载与2005 年中华书局版《纪要》基本相同,亦存在对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所辖堡名、数量前后矛盾的问题。另一方面,《纪要·总叙一》记载:“祖禹贫贱忧戚,杂乱其中,上之不能涉江逾河,登五岳,浮沅、湘,探禹穴,穷天下之形势;次之不能访求故老,参稽博识,因以尽知天下险易扼塞之处;下之不能备图志,列史乘,不出户而周知山川城郭里道之详。惟是守残抱缺,寤叹穷虑,吮笔含毫,消磨岁月,庶几无负先人提命之意,若以语于著作之林,余小子夫何敢。”[1]13此处虽有顾祖禹自谦的成分,但也从侧面反映了《纪要》中记载的许多地方其并未亲自考察,只是通过前人的记录编纂而成。因此,明清更迭的混乱局面,很有可能导致顾祖禹的认识产生偏差。
其二是后人整理过程中出现了疏漏。从《纪要》成书及流传过程不难发现,该书并无定本。一方面,顾祖禹去世后,因其子孙多贫困,无力刊刻,一时无新本问世,只有部分抄本流传。直至嘉庆十六年龙万育于成都刻印敷文阁本之后,《纪要》才逐渐盛行。顾祖禹稿本则直至民国时期由叶景葵先生购买、校阅,并经钱穆先生鉴定后,才逐渐为人们所重视[17]。另一方面,结合前文论述亦可发现,《纪要》对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所辖边堡,建置沿革、地理方位的记载与明代方志大致相符,只是对各路所辖堡名、数目记载存在前后矛盾。从顾祖禹对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记录的方式来看,其一般为先论述各堡地理方位、建置沿革,最后在末尾处总结各路所辖堡情况,但由于一路所辖堡数目过多,往往难以在一页中记载所有内容。故而,笔者认为《读史方舆纪要稿本》、敷文阁本等版本中,对大同路、堡记载的错漏,亦存在后人整理过程中错页、误植的可能。
总的来说,通过明、清方志及《读史方舆纪要稿本》的考察,可以发现,虽然顾祖禹在撰写《纪要》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受到明清易代的影响,但从《纪要》对清初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建置变化缺载的情况来看,顾祖禹对大同路、堡地理方位及建置沿革的记载,应只涉及明朝。结合《三云筹俎考》《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天下郡国利病书》《(康熙)山西通志》等书对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所辖堡数目与《纪要》记载一致的情况,《纪要》中的错漏,可通过上述史料补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