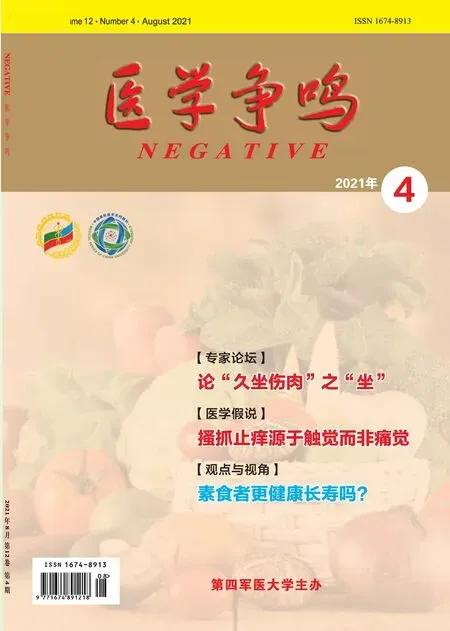由“COVID-19本该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却成了西方的滑铁卢”所引起的思考
罗超应,罗磐真,王孝武,王贵波(四川省羌山农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四川 绵阳 6000;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甘肃省中兽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甘肃 兰州 70050;西安市鄠邑区中医医院,陕西 西安 7000)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2020年10月14日刊文指出[1]:“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本该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却成了西方的滑铁卢。”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对新型冠状病毒(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SARS-CoV-2)的跟踪调查,美国每10万人中有65.74人死于SARS-CoV-2,总人数约为21.6万人;而中国每10万人中只有0.34人死于SARS-CoV-2,总人数约4 750人。这场目前已在中国得到控制的大流行,却仍在摧残美国的经济和国民——尽管这一切早在我们意料之中。“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是因为我们独特的个人主义文化、高度分散的地方-州-联邦分权系统、脆弱的公共卫生系统和分裂的政治体系,还有商业模式一直在削弱华盛顿的共和党,以及那么多从放大阴谋论并破坏真相及信任的社交网络中了解新闻的人[1]。”笔者以为,这看起来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但若没有学术界的简单化认识错觉,也许就不会有如此诧异的事件发生。故此不揣浅陋,对有关问题做一探讨,以抛砖引玉。
1 特朗普“独到解读”并非空穴来风
2020年10月6日,前一天刚出院返回白宫的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John Trump)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尽管有疫苗,每年仍有许多人死于流感,有时甚至超过10万人;但美国人不会因此封锁国家,而是学会与流感共存,就像现在学着去适应SARS-CoV-2一样。”他还表示,SARS-CoV-2在大多数群体中远没有流感那么致命。随后,推特对该文贴上了“误导”警告标签,脸书则撤下了相关言论[2]。当美国因COVID-19死亡人数达18万时,特朗普对外突然表示:其实美国只有数千人是死于SARS-CoV-2,而其他人都是死于心脏骤停或者是呼吸衰竭,完全不是因SARS-CoV-2死亡。这一说法遭到了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所长福奇博士(Dr Anthony S.Fauci)的反驳,他表示这些人都是因为COVID-19死亡,若不是COVID-19就不会有这么多人感染,也不会有这么多人死亡[3]。然而,从COVID-19的实际发生情况来看,特朗普的“独到解读”并非是空穴来风,福奇博士等的“正统”反驳也并非完全正确。
其一,即使有疫苗,美国每年仍有数万人死于流感,美国乃至全世界并没有封城,这是事实。如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估计,自2010年以来,流感每年造成900万~4 500万人染病,14万~81万人住院,1.2万~6.1万人罹难[4]。钟南山院士曾经指出:欧美一些国家“封城”措施不奏效,因为不是真正封城[5]。笔者以为,其原因除过欧美“个人主义民主文化”的因素外,与以往的封城经验及其在学术界的有关认识不无关系。如在中国2020年1月23日开始实施并不断完善武汉封城,以及在全国各地实施居家隔离等防控措施时,美国有专家在《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上发文却指出:中国规模巨大的跨湖北省防疫措施的有效性值得怀疑,因为封锁措施在此前的疫病暴发中未起作用,还因为与此前证明的公共卫生措施和国际卫生条例相悖而饱受诟病。如在1918—1919年流感大流行期间,美国卫生当局对主要城市进行了隔离,但对流感蔓延几乎没有持久的影响。2013—2016年西非埃博拉疫情刺激了检疫措施,利比里亚政府在蒙罗维亚西点对6万~12万人的警戒线不成功、饱受批评,导致暴力和公众不信任,有可能放大了埃博拉的蔓延[6-7]。2020年11月25日美国Science刊文指出:中国的疫苗努力被诅咒,因为其通过积极的公共卫生措施戏剧性地成功阻止与消灭了SARS-CoV-2的传播与流行,致使其失去了测试疫苗效力的机会[8]。在这样的学术思想影响下,加之美国的个人主义民主文化及其政治与经济学的需求,发生这样的事件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二,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截至2020年2月11日统计的44 672例确诊病例中,81%为轻症,14%为重症,5%为危重症;≥80岁占3%(1 408例),30~79岁占87%(38 680例),20~29岁占8%(3 619例),10~19岁占1%(549例),<10岁占1%(416例)。其中死亡1 023例,总病死率(case fatality rate,CFR)为2.3%,而≥80岁CFR为14.8%(208/1 408),70~79岁CFR为8.0%(312/3 918);危重病例CFR为49.0%(1 023/2 087);男性CFR为2.87%,女性CFR为1.7%;合并症患者CFR升高,其中合并心血管疾病患者CFR为10.5%,糖尿病患者CFR为7.3%,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患者CFR为6.3%,高血压患者CFR为6.0%,癌症患者CFR为5.6%[9-10]。意大利一份22 512例确诊病例资料显示,46.1%为轻症,24.9%为重症,5.0%为危重症,10.6%为无特征症状者,6.7%为少有症状者,6.7%为无症状者;≥70岁占37.6%,51~69岁占37.3%,19~50岁占24.0%,0~18岁占1.2%;男性占59.8%,女性占40.2%。其中死亡1 625例,总CFR为7.2%,≥90岁CFR为22.7%,80~89岁为19.7%,70~79岁为12.5%,60~69岁为3.5%,50~59岁为1.0%,40~49岁为0.4%,30~39岁为0.3%,0~29岁为0.0%[11]。在一组3 300例确诊患者中,1 998例至少有一种合并症,占60.5%(95%CI58.9%~62.2%)。在一组1 715例住院患者中,有915例死亡,CFR为53.4%。其死亡率相关独立危险因素分别为:老龄危害比(hazard ratio,HR)为1.75(95%CI1.60~1.92)、男性HR为1.57(95%CI1.31~1.88)、高吸氧量HR为1.14(95%CI1.10~1.19)、ICU入院呼气末高正压HR为1.04(95%CI1.01~1.06)或低动脉血氧分压与呼气末正压之比HR为0.80(95%CI0.74~0.87)、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史HR为1.68(95%CI1.28~2.19)、高胆固醇血症HR为1.25(95%CI1.02~1.52)和2型糖尿病HR为1.18(95%CI1.01~1.39)等等[12]。从以上统计结果来看,虽然都有SARS-CoV-2感染,但其成因显然不全是SARS-CoV-2感染所致,而是还有性别、年龄及合并症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传统的感染性疾病概念只强调SARS-CoV-2感染,而忽视其他因素的做法显然是有失准确的;而且随着慢性复杂性混合感染或合并症的日益多见,使感染性疾病防治所面临的挑战将日趋严峻。
2 宁可无药也反对用中医药
2020年3月2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湖北武汉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全国COVID-19确诊病例中有74 187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1.5%;其中湖北有61 449名患者使用了中医药,占90.6%。临床疗效观察显示,中医药总有效率达90%以上[13]。然而,尽管2020年2月7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向全国发出文件,就推荐使用中医药,而到2月12日湖北COVID-19患者中医药使用率只有30.2%,远低于全国87%的水平,不仅中医药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而且也影响了COVID-19救治效果[14]。某些科学家宁可无药也反对用中医药,是何逻辑[15]?无独有偶,美国《补充与替代医学杂志》(JACM)报告,针对COVID-19疫情,中国政府将中西医药迅速转变为“一体化”的方法,患者同时接受了中医药和生物医药。印度政府仅发布了一份备忘录,综合了印度阿尤什省的阿育吠陀、瑜伽、乌纳尼、西达、顺势疗法和自然疗法等,认为可能是有用的疗法。而相反,北美和欧洲政府通常对这些疗法除过警告可能的伤害和过度消费外,就是保持沉默;而对防疫的指导通常仅限于所谓的“健康等待”——社会距离、轻度锻炼、减少压力、禁止吸烟和限制饮酒等[16]。当初被媒体热捧为“人民希望”的瑞德西韦(remdesivir)[17]与氯喹(chloroquine)等抗病毒药,体外抗SARS-CoV-2效果都很不错,90%有效抑制病毒浓度(90% maximal effective concentration,EC90)分别为1.76 μmol/L与6.90 μmol/L,比中药连花清瘟效果要好很多。后者半数有效抑制浓度(50% inhibition concentration,IC50)为411.2 μg/mL。600 μg/mL连花清瘟处理细胞,可以见到SARS-CoV-2在感染细胞膜、细胞质和血浆囊泡表面的聚集减少[18-19]。而临床试验结果却证明,连花清瘟等中医药辨证施治对COVID-19的有效率达90%以上,瑞德西韦与氯喹等抗病毒药物的疗效却很小或根本没有[13,20]。5 000例严重或危及生命的COVID-19患者采用恢复期血浆(抗体)治疗,结果与严重感染的自然非治疗相一致;因为大多数早期感染患者都恢复了,要证明相对于安慰剂的益处不容易实现;而在重症患者中,炎症和凝血问题可能比病毒复制更重要[21]。即感染性疾病的临床疗效与治疗药物的抗病原体作用并不一致,其是由病原微生物感染所致的概念只是一个错觉而已。
这是因为,在以往的急性感染性疾病的认识与防治中,由于病原微生物的致病性都很强,只要对其进行准确认识、把握与处理,就可以解决其整个疾病的全部或大多数问题,而其他因素因为相对太弱,都可以忽略不计。而随着慢性复杂性感染性疾病的不断增多,尤其是混合感染或合并症疾病的日益普遍,使得传统的感染性疾病防治认识、把握与处理面临着愈来愈严峻的挑战。如SARS主要表现为重症,人们很容易发现其患者,且病毒传播高峰发生在疾病后期(约10天),而COVID-19危重患者虽然也表现为全身多器官损伤等多种临床表现,但其81%病例为轻症,表现为非肺炎或轻度肺炎,不易引起人们重视;尤其是其1%~6.7%的无症状感染者也可能成为传染源,就更大地增加了我们发现传染源的难度[9,22]。SARS-CoV-2核酸检测准确率不高,初期阳性率仅为30%~50%或76.4%[23-25],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在湖北省的病例诊断分类中不得不增加“临床诊断”,从而使湖北省2020年2月12日新增确诊病例一下子由前一日的1 683例激增到14 840例(含临床诊断病例13 332例)[26]。继加拿大多伦多、日本及国内多地康复病例核酸复检阳性[27-30],2020年3月4日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中,首次加入了抗体检测。而让人诧异的是,临床上发现有患者始终无法产生抗体,而导致多次“复阳”,并可能具有一定的传染性,从而使其不排除发展成慢性携带的可能[31]。
与此相应的还有SARS-CoV-2潜伏期的不确定性,也给其疫情的防控增加了难度与复杂性。如尽管SARS-CoV-2潜伏期多为14天,但甘肃一23岁男子从武汉回平凉19天后发病,超过14天医学观察期[32];河南长垣市出现连续17天无症状确诊患者[33];安阳医生报告观察一例32天无症状病例,第19天第二次核酸检测阳性,并接触传染了5名亲属患者,第36天与39天核酸检测阴性,解除观察[34];四川确诊20天无症状病例,同车从湖北返川4人全部确诊[35]。山西一65岁妇女2019年12月26日从武汉回到平遥后,身体健康一直处于良好状态,直到2020年2月1日出现咳嗽,2月3日出现发热,两天后确诊为SARS-CoV-2感染[36],其可能的潜伏期至少37天。广州市荔湾区一家6口2020年1月22日乘高铁由武汉到达广州,1月24日开始居家医学观察,至2月7日医学观察期满未出现异常,按规定解除医学观察,但2月20日、21日与22日,其中4人相继确诊为COVID-19,相关143人被隔离[37]。湖北恩施州确诊1例38天超长潜伏期无症状病例[38]。
3 尽管有疫苗美国每年仍有数万人死于流感
加州大学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 Engl J Med)发表一项有关抗体水平的小规模研究发现,COVID-19患者抗体水平在感染康复约2个半月后就近乎减半,这要比SARS丢失抗体速度快。香港大学研究团队2020年8月25日在《临床传染病》(Clin Infect Dis)发表报告,称全球首次发现一例COVID-19再感染病例后,美国、荷兰、比利时、阿根廷及巴西等地相继报告称发现康复者二次感染或疑似感染SARS-CoV-2病例[39-40]。俄罗斯亚历山大·切普尔诺夫(Alexander Chepurnov)博士,为了验证群体免疫的可能性,铤而走险地让自己第二次染上了SARS-CoV-2!在他首次感染后6个月,再次被确诊为阳性!这次感染来势汹汹,已经年近70岁的他直接病倒住院了。他感到嗓子痛,连续5天高烧39度以上,嗅觉和味觉也出现了问题,情况似乎越来越糟,好在最后康复了。据此他得出指望群体免疫来对抗SARS-CoV-2恐怕希望渺茫!疫苗虽然可以产生免疫力,但可能只是暂时的效果[41]。这一结论与香港大学论文的看法相似:①SARS-CoV-2可能会在自然或疫苗接种后获得的群体免疫下继续流行;② 疫苗可能无法提供终生免疫;③既往COVID-19患者也应考虑接种COVID-19疫苗,并继续在疫情期间佩戴口罩并保持社交距离[42]。美国哈佛大学一个研究团队认为[43]:“被我们寄予厚望的疫苗作用很可能会非常小!因为人类感染者产生的抗体有效期可能只有40周(<300天),比疫苗的研发周期都要短!如果疫苗不能起作用,那么COVID-19将会变成一个10~50倍致死率的流感,在全世界范围内反复暴发收割人头。”
其次,即使有疫苗也不能就万事大吉了,因为疫苗的效果是要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的。如据研究,9岁及以上年龄的美国人接种甲型流感H3N2和乙型流感疫苗后,免疫效果每个月下降约7%;甲型H1N1疫苗接种后每月下降6%~11%。流感检测阳性的可能性,在接种疫苗42~69天的人群中比在接种疫苗14~41天的人群中要高32%;接种疫苗后每增加28天就增加约16%,免疫154天后的人是接受免疫14~41天的人的两倍。流感疫苗效力下降在老年人中最强,他们比年轻、健康的成年人更容易出现并发症。而另一方面,在过去18年里,不包括2009—2010年的大流行季节,美国每年的流感季节通常是从12月或1月初开始,但其中3年却是从12月初开始的,再过3年又开始于1月的第三周或其以后;流感季节平均持续时间为13周,而有些可长达17周[44]。从而不仅给流感疫苗的应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也使美国即使有了疫苗,从2010—2019年每年仍有1.2万~6.1万人死于流感[4]。2021年2月25日,香港大学医学院陈志伟团队在Cell Host Microbe上发表研究成果表明,COVID-19疫苗接种可有效防止肺部感染,但不能防止鼻甲感染,很可能无法阻止SARS-CoV-2的扩散和感染。因而诚如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020年12月14日所建议人们的,即使已经接种了疫苗,也应继续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等[45-46]。而让我们在此深思的是,2003年的SARS及中国的COVID-19疫情,都是在没有疫苗与特效抗病原药物的情况下实现控制与消灭的;尤其是以往广泛开展的临床研究证实,中西医药学辨证与辨病相结合不仅可以提高与改善中西医药的临床疗效,而且还能完善现代医药学的临床认识方法,是现代感染性疾病防治不可或缺的重要整合因素与方法[47-48]。
4 转变科学观念,提高与完善感染性疾病认识与防治的准确性与有效性
4.1 转变科学观念,走出认识错觉的误区
中医药防治COVID-19,尽管其抗SARS-CoV-2的作用并不理想,但其不仅对重症辅助治疗也能力挽狂澜,恢复期促康复并减少后遗症,而且“承包方舱医院,中医成主力军”。隔离“四类人”,漫灌中药汤,练习太极八段锦等,增强患者信心与抗病能力,从而收到了90%的良好疗效[13,49]。糖皮质激素不仅没有抗SARS-CoV-2的作用,而且对机体的免疫功能还有抑制作用,但使用糖皮质激素治疗COVID-19重症患者,可降低20%的死亡风险。因此,世界卫生组织修改指南,建议使用糖皮质激素治疗COVID-19重症患者,不建议对非重症患者使用激素治疗[50]。而要正确认识与主动使用这些方法,就要转变科学观念,走出传统科学简单化地只关注疫苗与特效抗病原药的认识错觉误区,以使感染性疾病的防治更加科学合理与有效。
4.2 突破惯性思维的羁绊,正确认识与取舍疫苗等的防治效果与毒副反应
2019年美国等国家与地区发生了25年来最大规模的麻疹暴发。2019年8月之前的10个月里,美国30个州内总共有1 800人被感染,一种在世界范围内被消灭了多年的传染性疾病却正在卷土重来[51]。而据研究,麻疹暴发的根源就在于疫苗伤害及一些医生公开质疑疫苗安全性等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造成公众对接种疫苗的不信任,致使麻疹疫苗接种率低于“群体免疫”所需要的95%免疫覆盖率,全美国疫苗接种率仅为91%,而发生了麻疹暴发的华盛顿克拉克县只有78%的儿童接种了疫苗[52]。1998年8月,恒河猴-人轮状病毒重组四价疫苗(rhesus-human rotavirus reassortant-tetravalent vaccine,RRV-TV)在美国获得许可,但因1999年7月公布的15例免疫后肠套叠病例,该疫苗被停用并退出市场。在美国当时,每年轮状病毒性胃肠炎与5万多例患者住院有关,造成20~60名5岁以下儿童死亡;而RRV-TV可预防70%~100%的严重轮状病毒感染和48%~68%的轮状病毒性腹泻发作。在RRV-TV许可前试验中,10 054例接种疫苗组发生了5例肠套叠,4 633例未接种疫苗的对照组发生了1例肠套叠,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且大多数肠套叠病例可采用非手术治疗。因此,RRV-TV对减轻免疫疾病负担的总体效益超过了小风险,继续使用较停止使用更合适[53]。
而COVID-19疫苗的使用,也许正面临着同样的困惑。如Ipsos全球民意调查数据显示,目前有74%的人愿意接种COVID-19疫苗(如果可用)。其中,中国对疫苗接种的支持度最高,达到97%。27个国家中,俄罗斯人的接种意愿最低,只有54%。67%的美国人表示他们会接种疫苗,33%的人表示很少或不感兴趣。在那些表示拒绝的人中,有60%的人称副作用是最大的担忧,而37%的人认为疫苗无效。针对这项调查结果,世界经济论坛未来健康与医疗平台负责人Arnaud Bernaert分析表示:疫苗信心方面26%的缺口足以影响推出COVID-19疫苗的效果[54]。美国2020年12月15日开始了大范围辉瑞疫苗接种工作,阿拉斯加州接连发生两起医护人员接种疫苗后出现不良反应,美国大量医护人员对接种表现出了抵触情绪。一项调查显示,2/3医护人员希望推迟疫苗接种或不愿接种;超过半数则认为,联邦政府施压导致了疫苗研发过于仓促。专家认为,美国民众尤其是医护人员的接种意愿如此之低,将给接下来COVID-19疫情防控带来极大挑战[55]。因此,转变科学观念,突破惯性思维的羁绊,才能科学理性地认识与处理好此类问题。即以复杂性科学为指导,突破传统科学简单化惯性思维的羁绊,既不能幻想完全杜绝疫苗与药物的毒副反应发生,也不能一有问题就全盘否定,而是要理性分析,综合评判与精准处理。如一方面尽量认识与排除其不良反应发生的条件与因素,通过排除过敏性体质来减少过敏反应的发生等措施,尽量减少或杜绝不良反应的发生;另一方面,对已出现的问题是积极寻找解决办法,而不是因噎废食地简单不用。
4.3 重视辨证与辨病相结合,促进与完善感染性疾病的整合医药学认识与防治
中西医药学辨证与辨病相结合不仅是一种“多因素非线性分析与处理”的认识方法,而且还实现了复杂性科学所强调的“既要重视物质或因素本身的作用,也不能忽视物质或因素作用的初始条件”,完善了临床医药学的认识方法,促进与完善了整合医药学在感染性疾病认识与防治中的应用[48,56]。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它不仅可以在以往的中西医药学相结合能够弥补中医药学“有病无证可辨”与西医药学“有证无病可识”之不足,显著地提高中西医药的临床疗效,而且在这次COVID-19疫情防控中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使中国取得了全球最佳的疫情防控结果。
总之,其一,由于感染性疾病的新发与病原变异,无疫苗与无特效抗病原药物的防治也许将愈来愈多见。其二,由于感染性疾病的发生并非仅是由病原微生物感染所致,对其防治既要重视疫苗或特效抗病原药物的开发与应用,但也不能唯其是用或唯其是等而错失良机。其三,特朗普“独到解读”并非空穴来风;西方国家“滑铁卢”也并非仅仅全是由政治与社会方面的原因所致,还与学术界简单化的认识错觉与片面经验不无关系。其四,转变科学观念,以复杂性科学为指导,以辨证与辨病相结合为方法,来完善感染性疾病的临床认识与防治,也许才是应对愈来愈复杂的临床实际病情、提高与改善其防控效果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