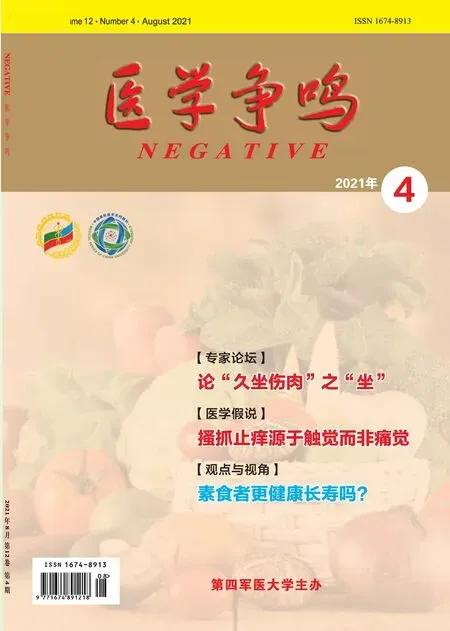基于中医药防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实践论中医思辨体系
鲁 海,胡赫其,胡佳慧,李香淑,康煜炜,刘小钰,高 璇,韩李莎,张春红(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天津 009;天津中医药大学,天津 067;浙江省人民医院,浙江 杭州 00;宝安纯中医治疗医院,广东 深圳 8000;国家中医针灸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天津 008)
2019年12月底于湖北武汉市突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在全国大范围内扩散,经祖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和积极防控,国内疫情已取得阶段性胜利,然而国外确诊病例数仍处于上升状态[1]。截至2020年8月末,全球确诊的COVID-19患者已达2 300万余人,死亡超80万人,疫情形势仍不容乐观。COVID-19来势汹汹,感染范围较广,传播速度较快,主要的临床表现为发热、干咳和乏力,部分患者伴有消化系统和神经系统的症状,严重者可发生急性呼吸综合征、肾衰竭,甚至死亡[2]。为快速有效地指导全国科学规范做好COVID-19的诊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于2020年1月起陆续发布更新了7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简称《诊疗方案》)。在第三版《诊疗方案》中提出对COVID-19的中医药诊疗策略,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相继制定了中医药防治方案,充分体现了中医因地制宜的整体观念[3]。第六版《诊疗方案》中参考西医的临床分型,将分期、分型相结合,提出了中医精细的辨证论治内容[4]。整体观和辨证论治是传统中医药理论体系中的支柱,中医思辨理论的主要内涵,即宏观思辨的认知观、诊疗观。张伯礼院士也明确指出,以整体观和辨证论治为特色的中医诊疗方案是病毒感染疾病治疗中的优势[5]。
1 五脏一体、正邪一统
整体是指人体的统一性和完整性。传统中医整体观主要包括三层含义: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天人合一),人体内部的和谐统一(五脏一体、形神合一)[6]。传统中医整体观着眼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对宏观诊疗形式发展的分析与研究。现代中医随着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逐渐形成与发展,使得整体观念不仅具有实践性、科学性,还具有现代化理论的思想内涵[7]。
在此次中医药防治COVID-19疫情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中医药的整体调控机制。虽然此次COVID-19病位在肺,传变极其迅速,可顺传脾胃,也可逆传心包,终而进入一个以“肺脏”为首、伴多脏器衰竭的状态,从而出现坏证或危重症[8]。但中医药作用亦重在保护肺、脾,且各有侧重,同时具有调节免疫、抑制病毒复制、消除炎症、改善机体代谢等多重功能。此外,初、中期侧重调节免疫、抑制炎症风暴;重症期增加细胞提供能量、保护心肌细胞的作用;恢复期则佐以神经保护与功能恢复的作用[9]。对于改善患者的肺损伤和多脏器功能障碍有潜在的疗效,能明显地改善发热、咳嗽、乏力、气短憋闷等症状,达到人体内部五脏六腑的和谐统一。再者,分析各省市制定的中医药防治方案,在围绕“疫气”这一核心病因的基础上,均根据各地气候及地势的不同进行辨证分型。在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防疫方案中发现,COVID-19的邪气成分特点主要包括毒、湿、热、虚、寒、瘀、燥、浊、风。“毒”即疫气,除“毒”邪致病外,“湿”邪在南北方、东西部亦均有分布;“热”邪主要见于南方;“虚”邪则主要在北方;“寒”邪见于南北方山区……而“风”邪主要见于四川省境内[10]。各地中医防疫治疫均做到了因地制宜[11],以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与通常中医药治病审证求因不同的是,此次致病因素是传染性与危害性极强的疫戾之气(病毒微生物),非风、非寒、非暑、非湿,故在治疗上注重“祛邪”和 “扶正”的整体调节,与现代医学提出的“抗病毒疗法”和“宿主导向疗法”存在较高的契合度,二者联合应用以达到病毒和宿主的和谐统一[12]。
2 群体辨证、微观辨证
辨证论治即通过四诊(望、闻、问、切)所收集的资料(症状和体征),综合分析、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以及邪正之间的关系,从而概括阶段性的病理变化,并确定相应的治则和治法的过程[13]。辨证是论治的前提与依据,论治则是治病的手段与方法。整体观下的辨证论治,实质上是中医学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过程。整体观指导辨证论治,辨证论治体现整体观,两者有局部与整体、内因和外因、原因和结果等方面的辨证关系。一言以蔽之,以“辨”应万变。本次中医药辨治COVID-19比较突出的特点在于群体辨证、微观辨证与组分中药配伍的运用。
本次COVID-19疫病的突然暴发,一时使很多医者束手无策,面对这个新的疾病,并无陈法可守。如何理清疫病辨治思路,国内临床专家尝试运用传统中医理论辨治COVID-19取得了良好的临床效果,例如“三系一体”辨治模式[14]、“五辨”辨治思维[15]、传统温病辨证[16]、《瘟疫论》“表里九传”辨证[17]、方证辨证[18]等。但在大规模传染病流行的时候,无法一一进行辨证论治,同时医生身着隔离服收集的四诊资料也是不准确的。然“疫邪”致病具有“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论大小,病状相似”的特点,故张伯礼院士将“中药漫灌”全面引入中医治疗,即在核心病因相同、症状类似的情况下进行群体辨证,采用通治方/标准方进行群体治疗,可在短时间内较好分离出非COVID-19患者、安抚病患心理、截断疫情蔓延。以清肺排毒汤、化湿败毒方、宣肺败毒方为代表的中药汤剂均在一定范围内普遍使用,实际效果良好。“中药漫灌”突破了传统中医辨证“一人一方”的论治局限。群体辨证下“中药漫灌”全覆盖的江夏方舱医院休舱时还达到“六个零”:零死亡、零转重、零复阳、零回头、零感染(包括医护、后勤安保人员)、零投诉,可谓是救人无数[19]。
整体观下的辨证论治多处于宏观层面的认识论,对于微观层面的证素资料往往涉及较少。在此次COVID-19疫情中,充分发挥现代医学的先进技术,微观地认识机体的结构、代谢和功能特点,扩大了四诊,尤其是望诊资料的范围。通过收集微观的影像、理化、病理等指标使得辨证论治更加精准,故微观辨证有一定的时代意义。对于COVID-19造成的一系列的病理变化,一线专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分析,有研究发现胸部CT的感染面积与病情呈正相关,早期呈现多发小斑片影及间质改变,以肺外带明显,进而发展为双肺多发磨玻璃影、浸润影,严重者可出现肺实变,胸腔积液少见[20];不同病程胸部CT变化与当日舌象特点的相关性,疾病初期、进展期、重症期、恢复期,舌质颜色从淡红—红—暗红(紫)—淡红,舌苔从薄—厚—薄,从白—黄(浊)—白,同时舌体胖瘦、齿痕程度均随疾病的变化而变化,反映着疾病的进程[21]。生化检查发现发病早期外周血淋巴细胞计数减少,多数患者C反应蛋白和血沉升高。严重者D-二聚体升高,外周血淋巴细胞进行性减少。重型、危重型患者常有炎性反应因子升高[21]。结合中医辨证,不同COVID-19中医证型的血沉和C反应蛋白均普遍升高,且淋巴细胞计数有一定的差异性,其中热毒壅肺证患者淋巴细胞计数低于寒湿束表、热郁津伤证(P<0.05);寒湿束表、热郁津伤证的总T淋巴细胞(CD3+)明显高于风寒袭表、气虚湿滞证及热毒壅肺证(P<0.05)[22]。此外,COVID-19死亡患者的病理解剖发现双侧弥漫性肺泡损伤伴细胞纤维黏液性渗出,肺内支气管腔内可见黏液及黏液栓形成,为湿邪辨证提供了很好的组织学依据[21,23]。结合CT影像、生化指标及组织病理形态等微观证素,使得中医辨“证”不断深入。在疫情大流行情况下,传统辨证条件不允许或无证可辨时,微观辨证可简便、及时、精准判断疾病进程、疗效及预后,对COVID-19的诊治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以清肺排毒汤、化湿败毒方、宣肺败毒方为代表的中药复方在防治COVID-19疫情时起到了“特效药”的作用。传统中药复方配伍,多根据中药材的性味归经选择合适的中药进行组方,单味中药即是方剂的最小元素。随着现代中药化学、中药药理学的发展,逐步分离出分子水平上的中药有效活性成分(单体)以及组分。在应用网络药理学、生物信息学以及数据挖掘等关联评价技术,预测作用机制,明确信号通路的基础上,可有效、快速地确认组分中药进行配伍组方,以形成新的复方有机整体[24]。此次用于COVID-19防治的中药方剂大多具有多种药理活性和广泛的药理作用谱,例如抗病毒、抗炎、免疫调节、保护靶器官、解热、化痰、镇痛、活血化瘀、抗氧化等[25]。以宣肺败毒汤治疗COVID-19为例,张伯礼院士利用天津中医药大学中药组分库筛选对新型冠状病毒有抑制作用的中药(例如虎杖)并组方配伍,后经网络药理学分析宣肺败毒汤的主要活性成分及其靶标,发现该方的重要靶标主要富集在病毒感染和肺部损伤相关的通路上,提示了宣肺败毒汤治疗COVID-19的潜在“特效”作用[26]。牛明等[27]针对新型冠状病毒侵染人体的S-蛋白与特异性受体ACE2蛋白,筛选出桑叶、苍术、浙贝母、生姜、金银花、连翘、草果等7味中药,均在抗新型冠状病毒中医组方“克冠1号”中配伍运用。基于有效活性组分的组分中药配伍,使得中药组方配伍更加精准化、客观化。
3 结语
新型冠状病毒来势汹汹,在国内外广泛传播,传播速度快、范围广,目前尚无特效治疗药物。中医药在防治过程中后来居上,经过临床的验证,各部门科学规范的指导,在全国得到普遍推广应用,并为世界范围内中医药防疫提供了良好的蓝本,实现科学精准施治,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治愈率,降低死亡率。
在防治COVID-19疫情期间,中医整体观与辨证论治贯穿始终。中医整体观与辨证论治历来被奉为中医思辨活动之圭臬。中药复方的多成分、多靶点、多途径的协同作用决定了它的整体调控机制[9],综合调节COVID-19对人体造成的多器官损害,恢复内稳态。COVID-19疫情全国大流行,但又依地区而不同,因地制宜的整体观使得各地区的中医药策略更具有针对性。“祛邪”和“扶正”一直是中医整体观念的重要体现,病毒与宿主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祛邪”和“扶正”的联合运用势必事半功倍,中医药通过清热解毒(抑制病毒)、扶正固本(增强免疫)、调节机体平衡(抑制炎症)、协调脏腑功能(整体调整机体功能)的组合治法取得了良好的临床疗效[12]。
整体观下的辨证论治在疫情大流行情况下有了新的体现,突破了“一人一汤药,一人一辨证”的个体化辨证,取而代之的是掌握核心病因病机的群体辨证。传统的辨证论治对于“证素”的提取多局限于症状与体征,宏观四诊合参模式下的辨证已然不能满足COVID-19的治疗。在现代医学诊查手段日益精准的今日,中医辨证论治也应该吸收CT、生化、病理等先进的技术和手段,延伸中医四诊的范围,使搜集病史资料客观化,以尽量减少因患者主观和环境对中医宏观病理反应和判断带来的意向性、随意性和不确定性[28]。微观辨证不仅体现证候的物质基础,还可协助判断病情严重程度及病势发展,体现中医的精准施治。在中医辨证组方原则前提下,选用现代药理研究证实对COVID-19有针对性治疗作用的药物,进一步提高临床疗效,故在COVID-19治疗中,亦可组分中药配伍遣方用药,不拘于经方、时方,不囿于某一流派。在面对人类共同疾病上,我们强调要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优势,敢于突破传统中医思辨体系的禁锢,宏观与微观、群体与个体、现象与病理融合辨证施治,必要时还要善于利用“组分制剂技术”创新方剂[24],体现新时代、新时期的中医思辨内涵,有助于完善和充实中医药学关于传染病的内容,具有一定的理论与临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