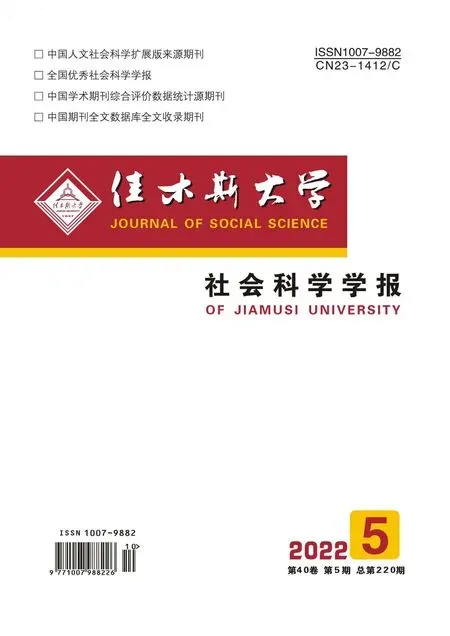菲茨杰拉德小说中感官与象征交织的叙述风格研究
吴 蓉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教育系,安徽 池州 247000)
印象主义对直观感觉的把握使其更切近事物本来的状貌,而其艺术追求向文学领域的延展则颠覆了传统叙事中偏重情节的传统,让直观的感觉体验成为文学叙事亟需把握的对象。声色光影的流动使文学具有了影像化的美感,倾注了作家主观情思的象征物折射着当时社会的时代症候,使菲茨杰拉德的小说获得了跨越时空的不朽魅力。
一、视听融汇的感官叙事
印象主义的风靡打破了文学与绘画之间艺术形式的间隔,对感官的直观体验的追求丰富了小说现代主义的技法,以感官叙事敏锐地捕捉创作主体的情思。于是视线所及的事物被纳入了小说的叙述,耳力所及的声音也成为文字所致力于捕捉的对象。菲茨杰拉德对感官叙事的应用赓续了济慈“以直觉与感官体验捕捉无尽的、处于动态之中的世间万物”的文学理念,将视觉画面与听觉体验大幅度地拥入小说的叙述中,以文学印象主义的技法建构了声光流溢的独特小说氛围。
印象派的画家擅长将瞬息万变的光线定格在画布之上,光线取代了绘画的对象成为艺术表现的主体,色彩的浓淡成为表现光线的重要技法。而文学印象主义则将光线转化为形塑人物、布置场景的重要手段,菲茨杰拉德的小说精准地运用了光线铺排。如《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盖茨比首次在小说中出场时,菲茨杰拉德极其吝啬于描摹他的真实形貌,我们只能藉由尼克的眼睛凝视着他:“倘若人的品格中带有一系列不断取得胜利的品质,那么他的身上就蒙着一层瑰丽的色彩,如同一台奇妙的、能够在万里之外记录地震的探测仪……”盖茨比就是这样一团“瑰丽的色彩”,不带任何细节地呈现在读者的脑海中[1]。这种“朦胧感”让读者将主人公盖茨比感知为一个创造力十足、带有成功气质的神秘“光团”,在对文字的阅读体验中产生视觉上的朦胧效果;《夜色温柔》则将“月光”作为创设故事氛围,推动情节发展的方式:“惨白的月光蹲伏在树枝上,洒下冰一样冷的辉光。屋子里的烛光暖极了,可是它驱不散这样的冰冷。一个醉酒的男人伏在门前的台阶上,雪白的前襟隐隐透出葡萄酒渍的湿红,月光犹如死亡的殓衣,静静地覆盖在他的身上。”[2]冰冷的月光带来了孤独的感官体验,人造光源“烛光”的温暖怡人与自然光“月光”的凄凉萧索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种感觉上的巨大的反差体验预示着狄克与尼克尔之间横亘的巨大阶级鸿沟,让读者不仅是在内容层面理解了两人爱情悲剧的成因,更在直观性的感觉体验层面觉察到了当时不同阶层之间的云泥之别;而《重访巴比伦》则更是化言语为“画笔”,以平铺直叙为读者呈现了文字形态的印象主义绘画:“窗外淅沥沥地下着小雨,雾蒙蒙的空气模糊了建筑们的轮廓。黄昏时节的街上行人神色匆匆,暗色的雨伞与雨披划过泥泞的大街,小小的橱窗里昏黄的灯光笼罩着精致的商品……广场上的雕塑笼罩在深绿色的光里,在车窗背后一闪而逝。”昏暗的天光与橱窗中的灯盏的光线带来压抑的心理体验,并无过多雕饰的词句犹如行走在画布上的利落线条,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社会的街边景致[3]。菲茨杰拉德不仅以光与色呈现了精妙的画面,更通过光的昏暗与色的压抑点明了当时的时代氛围。
而在印象主义流派的影响之外,菲茨杰拉德的感官叙事也显然受到了爵士乐兴盛的时代环境的滋养,听觉体验代入文字叙述使菲茨杰拉德的小说对感官的刺激更为丰富。如《一颗像里茨饭店那么大的钻石》中,声音便成为菲茨杰拉德环境描写中的主要质素,“一支像是泛着泡沫的短笛在伴奏着”,这虚幻的泡沫伴着轻柔的笛声吹进了读者的耳朵,使人联想起阿芙洛狄忒诞生时海洋涌起的珍珠似的泡沫,直观地激发了读者们对于“美”的直觉。而主人公约翰轻松愉快的心情也直接为读者所体验,具有了影像化叙事的效果;《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声音”更是成为形塑人物的重要方法,黛西的出场几乎每次都伴有音乐带来的听觉体验。她伴着“萨克斯管与小提琴演奏出的美妙旋律”在众人的拥簇中出场,瞬间抓住了盖茨比和读者们的心,“人们节节拔高的笑声汇聚成了欢乐的声浪”预示着黛西这个人物形象是“享乐”的象征。而盖茨比同贝克小姐友好的交谈时,黛西因为受到冷落而感到妒忌与忧伤,菲茨杰拉德巧妙地以低沉华尔兹舞曲《凌晨三点钟》作为该叙事场景的背景乐,低沉的乐章烘托了小说低沉忧郁的气氛,听觉体验丰富了读者的阅读审美感受,敞开了感官的“众妙之门”。
菲茨杰拉德的感官叙事藉由视觉与听觉形成的直观体验推动了情节发展,产生了“超文本”的叙述效果,让其文学写作成为读者可以沉浸式体验20年代美国社会的一面窗口。光与色的流溢使他的文学语言充满诗意的美感,视与听的融汇更使其小说具备了在当时具有超前性的影视化效果。感官叙事的灵动使菲茨杰拉德的写作可以被冠以文学印象主义的命名,以朦胧的语言美唤起读者审美的悦感。
二、层次丰厚的象征手法
菲茨杰拉德的小说经典性的建构不仅由于它艺术性地织构了一个纸醉金迷的上层社会、叙写了各种悲剧色彩浓厚的情爱故事,而是藉由理想主义者的悲剧影射了“美国梦”的倾颓与崩塌。不难发现,菲茨杰拉德的象征手法与印象主义画派的表现手法具有艺术上的共通性,他们都极其重视对接受者的感官的刺激。绘画的印象主义运用朦胧的线条与鲜明的色彩,诱发读者丰富的感性体验;而文学的印象主义则力图以文字的叙述,使读者产生强烈的直观感受,将丰富的意义凝练成具体的物象,并藉此跨越叙述的间接性,诱发读者直接性的联想与想象。菲茨杰拉德擅于抓住瞬间的感觉,并将其灌注到物质的外壳中,通过层次丰厚的象征手法诗意地使读者品察时代的氛围、历史的情态。
菲茨杰拉德乐于赋予颜色以象征化意义,通过色彩带给人的无意识感受增加小说的可感性,被赋予了相同色彩的不同物事可以被归置为同类象征物并加以读解,视觉化的感染力通过文字直抵读者内心的深处。如“红色”隐喻着欲望与暴力。《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上流社会的晚宴经常在汤姆与黛西夫妇的“红房子”中举行,衣香鬓影、华灯璀璨的舞会中布满了人们的尔虞我诈,充斥着源于欲望的重重交易;上流社会的富人们的花园中盛开着大丛的“血红的玫瑰”“如同火焰一般炽热,摄人的美丽不断地灼烧着他的视线”,艳丽的花朵暗示了他们不断膨胀的贪婪;而尼克从书商那里买到的有关股票投资的书籍是“红皮烫金”的,资本主义“烫金”的表皮下掩埋着工人苦苦求存的血泪史,残酷的工业伦理不断地汲取劳动力们的生命力作为自己的滋养。有些具有象征性的色彩的深层喻指甚至具有对立性,如“蓝色”的象征意义不断在“怜悯”“悲伤”与“梦幻”之间置换。这些象征意义的外延十分丰富,有时甚至相悖乃至产生对冲,无形中扩充了象征物的意义空间。它时而是《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埃克尔堡大夫在旁观“灰谷”中俗世男女的狂欢痛饮、寻欢作乐时忧郁的“蓝眼睛”,这双睿智的旁观之眼洞穿了他们物质上的丰足与精神上的空虚,既隐含道德层面的谴责,又带有上帝式的怜悯;时而是《夜色温柔》中与狄克偕行时尼克尔身着的“灰蓝色的礼服”,这件华贵的礼服不仅象征着二人之间巨大的身份鸿沟,也预示着二人之间爱情的悲剧结尾。随风飘动的纱裙“闪烁着亮蓝的色彩,灰色的底子沉沉地托着这抹跳脱的亮色”,尽管两人之间的爱情曾经甘甜若醴,但是却难以消解悲伤的底色;时而又是黛西头上的一根美轮美奂的羽毛,“一根蓝幽幽的羽毛落在她(黛西)金灿灿的头发上,带着毛茸茸的晕轮,像他航行时推动着小船的碧蓝波浪。”精心装扮后呈现的美貌令盖茨比深陷在梦幻之中,但梦幻的背后却是一片虚无,正如她纯真美丽的表象与空洞冷漠的内在。
凝集了菲茨杰拉德敏锐感触与艺术创造的象征物更是变成了具有时代意味的象征物,如象征着20年代声色喧嚣、物质丰足而传统道德体系却濒临塌陷的美国社会的“灰谷”。菲茨布拉德将艾略特的“荒原”意象进行了现代转化,“这里的灰烬聚沙成塔,无形的手不断地将其捏造,隐约间塑造成一个灰暗的人形,模糊地行走在时间,而且很快地消散在充斥灰尘的空气中了。”人民对“美国梦”的追逐逐渐变质,神性与信仰逐渐远离的时代正在蒙上功利主义的积灰,“灰谷”这一意象可以说是时代历史环境的一个精妙象征物[4]。而且,菲茨杰拉德的意象建构往往具有丰富的层次,他的象征物的意义边界是具有弹性的,可以从某种语境下从一种意义向另一种意义迁移。如与象征理想主义的时代业已倾颓的象征物“灰谷”相对的、代表着希望与梦想的“绿光”,这抹缥缈的理想之光是现代精神荒原上的一座“永无岛”。它既象征着盖茨比个人层面上对理想社会的坚实信仰,也象征着菲茨杰拉德向往的社会层面的“美国梦”。盖茨比透过朦胧得犹如轻纱一般的海雾第一次看见的“绿光”,绿色象征着内心的宁静与生命的活力,如同盖茨比一般是这纵情声色的社会中唯一保持着对理想的忠贞的“上帝之子”。最终这抹“绿光”在盖茨比弥留之际闪现并最终归于寂灭,不仅预示着理想主义者盖茨比寻梦之旅的终结,也象征着维多利亚时代的“骑士精神”在“爵士乐时代”的正式破灭。他们纵情视听的饕餮盛宴不仅是源于享受的需求,更归因于他们精神上的迷茫与痛楚,他们的时代症候表述了历史变动时期的躁动氛围。象征意义由个体层面过渡到社会层面,意义的符合构成了层次丰厚的审美体验。“绿光”的消失与“灰谷”的永存可以说是菲茨杰拉德为时代写下的预言诗,一座精神的荒原横亘在人文精神的废墟之上,揭示了道德理想的幻梦无法实现于资本主义社会复杂的阶级矛盾中。
以“骑士时代”对荣誉和个体奋斗的重视对抗“爵士乐时代”人们的精神空无和迷茫,盖茨比正是菲茨杰拉德理想社会的拟人化,他对儿时的情人充满忠贞、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取了庞大的财富并怀有着柔软的同情之心。尽管盖茨比的悲剧是工业文明时代人文精神陨落的必然结果,但是他所象征的菲茨杰拉德对理想主义的不弃坚守将个人的命运悲剧崇高化,让盖茨比成为文学史上一个理想主义的经典象征符号。
三、专注体验的叙事视角
叙事视角是织构、理解文学世界的必要通道,视角的变幻决定了读者怎样理解故事、理解什么样的故事以及代入了怎样的话语立场。而读解作家对于叙事视角的选择,无疑能够使我们觉察作家隐藏在叙事背后的深层动机。菲茨杰拉德小说运用的叙事视角是多元的,然而他们拥有的共同特征便是指向了对感觉体验的专注,视角选择的丰富使菲茨杰拉德的感官叙事带有鲜明的体验性,传递出了菲茨杰拉德独有的美学价值观。
叙事学家热奈特提出了“零视角”的概念,该叙事视角将隐含作者及其小说中的代言人置放在全知全能的观察位置,他们时而将故事的来龙去脉娓娓道来,时而冷静地旁观故事的发展,亦或者直接潜入人物的内心揭露其内心的隐秘。菲茨杰拉德在进行“零视角”叙事时既注重从细部把握外在的客观世界,也带领读者们深入人物的内心,体味他们五味杂陈的情感体验。如《伯尼斯剪发》中以全知视角进行叙述的叙述者旁观着年老者与年轻人的价值冲突。伯尼斯在剪去了美丽的长发后瞬间丧失了为年轻人青睐的时髦感,当她盯着其他女孩精心编起的长发时,她恍然间觉得“那两条长辫就像一双盘卷着的蛇”。“蛇”在西方的文化语境中具有“邪恶、妒忌”的含义,菲茨杰拉德以“零视角”向读者敞开了伯尼斯内心的隐秘,女性象徽的丧失带给她的受挫与失落也为读者感知,并由是引起深深的同情;而《了不起的盖茨比》中菲茨杰拉德则以“零视角”向读者描述了隐含作者尼克的内心世界——这种以“零视角”叙述隐含作者代言人的叙述行为显然带有着自白性。尼克在盖茨比的葬礼后直面盖茨比的冤屈难以洗刷,而真凶逍遥遁逃而去的场面时,他“感受到一种古老而未知的世界……无垠的混沌吞噬了他的梦想,夜色中无边的晦暗田野在天际延伸而去。”在“旁观者”尼克的眼中,印象主义的画面带来了超现实体验的感受,而这种抽象的、怪诞的、非线性的意义关系所呈现出的世界的本质却是那样叩击人心。随着理想主义者盖茨比的死去,“爵士时代”的梦幻色彩也褪下了诱惑的外衣。该时期的美国工业膨胀式地增长,工业机器的投入取消了人的劳动附加的价值属性,金钱不断冲决着大众的精神信仰之堤,濒临崩塌的价值体系与随之而来的人们道德感的丧失,随着理想主义者的陨落而了然于读者的心胸。
在“零叙事”之外,菲茨杰拉德更擅于使用“内视角”的叙述方式,使读者随着视角的转换感人物所感,直观地获得人物的切身体验。如《巴塞尔和克娄巴特拉》中菲茨杰拉德以“内视角”叙述主人公巴塞尔,此时正值青春的巴塞尔正在耶鲁大学研习,他对“成长”有着独特的理解与迫切的憧憬。菲茨杰拉德通过“内视角”为读者敞开了巴塞尔懵动着的内心世界:“在生活中,他热切地希望自己的感官能够更敏锐些,能够为每种弥漫在空气中的气味而激动。他想捕捉每一缕光线的变化,拥抱每一丝心灵的震颤……他极其热切地想要成熟起来,让稚嫩须臾间变得沉稳……”丰富的感官描写让读者深切地感受到了巴塞尔对于成熟的渴望[5]。菲茨杰拉德颠覆了既往传统叙事中以“外视角”的客观化叙述描写人物内心世界的方式,以“内视角”直接联通读者与巴塞尔的感官世界,使青年人对成熟的渴慕涌动在读者的血管与神经中。这种直观的感受被施加在读者的阅读体验中,引起他们在感官层面的惊奇,融解了读者对小说人物的陌生感,使作家能够满足不同类型的文学接受者对小说的阅读期待。同时,迥异的叙述视角虽在文本中各施其能,根据不同的情节需要带来多元化的叙述效果,但是其对于感觉体验的专注却使各种叙事视角的切换更加自如,使小说的叙述更加流畅。
四、结语
感官化的叙事与象征物的堆叠让菲茨杰拉德的情节织构充满了印象主义的风格,对社会吉光片羽式的观照与呈现让他的故事情节并非以明晰的逻辑进行串联,而是以拼贴的方式搭建起叙事的框架,让非线性、无必然逻辑性的情节牵引着读者的阅读感受。多元叙事视角的灵活运用全面地敞开了人物的感官,让读者的体验更加沉浸其中。菲茨杰拉德以文学印象主义织构了感官与象征交织的小说世界,将对理想主义的不弃言说隐藏在崇高的悲剧美感中,在世界文学经典的建构中留下了深刻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