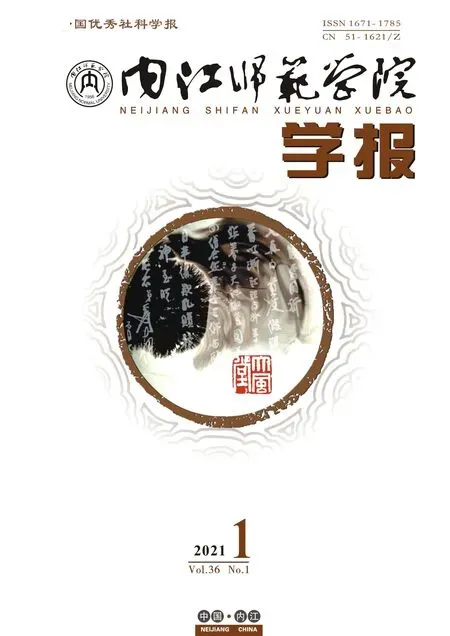魏裔介“清真”说探析
冯 浩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
魏裔介是清初的政治家、理学家和文学家。政事之余,不费吟诵,更在诗学观念上提倡“清真”。目前学界虽然对魏氏诗学已有关注,但是大都围绕其政治身份展开①。有清一代是各种文学集大成的时代,诗歌理论更是吸收了历代丰富的经验。从政教功用角度认识魏氏诗学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其审美方面的价值。另外,清初的庙堂诗人何以对“清”这一范畴格外重视?“清真”作为风格概念如何被建构为带有政教色彩的“清真雅正”?这些问题都需要回归当时的文化语境进行探究。魏裔介颇好持论,加上台阁重臣的身份,他对“清真”的阐说值得我们作为清初庙堂诗人个案进行研究。
一、右文政策下的燕台诗人身份和对诗教的申张
魏裔介(1616—1686),字石生,号贞庵,直隶柏乡人。顺治三年(1646)进士,历仕顺、康两朝,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可谓“居庙堂之高”。不仅著有《屿舫诗集》《兼济堂诗文集》等,还编选了《观始集》《唐诗清览集》《清诗溯洄集》,毕生致力于文学活动,是清初政治地位最高的文学家之一。
台阁诗人是清初诗坛的一个重要群体,马大勇将这一群体细分为“二臣诗群”和“入清第一代诗人群体”[1],按照这种划分,魏氏无疑当属后者。他未在前朝任职,出仕没有二臣的矛盾心理,加上深受顺治的器重,是当时肯定新朝并积极主动地参与建设的文臣,这种建设在文学上同样没有缺席。为了稳定天下、巩固政权,顺治实行右文政策,形成引人注目的燕台诗人群体。学界对于这一群体的认识多集中在“燕台七子”身上,魏裔介无疑在其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吴伟业在魏氏文集序言中称:“值世祖章皇帝兴治右文……一时文学侍从之臣,无不掞藻摛华,对扬休命,而公实岿然为冠首。”[2]1从吴氏的回忆来看,魏裔介不仅身在燕台诗人之列,其领袖地位更是得到公许。创作上润色鸿业之外,他还力图通过诗歌观念的厘正建立起合乎开国盛世的诗风。
魏裔介持有儒家复古思想,与吴伟业论诗曰:“子不见夫水乎?当其发源,涓涓细流,其清也可凿,其柔也可玩;继而潢污行潦,无不受也。”以河流喻诗史演变,虽源头清正,然而之后必受不正之风的影响,颓势难抑。魏氏继而感慨明末诗歌一如国力衰退到极点:“自兵兴以来,后生小儒穿凿附会,剽窃模拟,皆僴然有当世之心,甚且乱黑白而误观德,识者虽欲慨然厘正,未得其道也。”[3]魏氏不满明末诗坛充斥模拟流弊、不正之风,心怀厘正诗坛风气的志向。
魏裔介希冀通过编选诗集的方式来树立新的诗风标准,他意识到明末诗坛衰败的根本原因在于诗教传统的缺失:“后人于诗,以为酬应耳目快意適观之具,其所争者,在乎声调气格,六义之指,缺然不讲。”[2]102明七子的提出复古理论集中在形式格调,忽视对《诗经》教化本旨的讲求,魏氏深谙其弊,因此重申:“诗之为教,优柔敦厚,足以和人性情”,并且以身作则,主张“天子近臣不可以不亲风雅”[2]112,希望台阁近臣能够主动参与文学建设,在明季鼎革之后,使诗风协于《三百篇》之义,开“郁勃昌明之气”,实现“一时文治彬彬然润色鸿业,而百世之风气习尚因之以成”[2]6。这是魏氏怀抱的理想,也是他论诗的出发点。
魏裔介虽然重视诗歌的教化功用,力图恢复经学本旨,但并未忽视审美意义:“《传》曰:‘不有君子,其能国乎?’然则不有文章,川岳之气将黯淡无色也。”[2]104这里的文章当包括诗文在内的美文,他将文章比作“国之君子”,认为其审美的价值是不可或缺的。因此,魏氏积极地向台阁诗人以外的群体学习,其诗学思想也得以在清初的庙堂文人群体中独树一帜。
二、格调思想与推崇王、孟
魏裔介仕途平顺,活动范围相对有限,以京城和直隶为主,然而凭借显赫的地位,得以与当时的诗坛名家多有交往。
魏裔介入京伊始,当时京城诗坛上活跃的是以王铎、薛所蕴、刘正宗“京师三大家”为首的诗人群体。白一瑾指出,由于地缘因素,他们是明七子的正统继承者[4]。魏氏在与京城诗人群体的酬唱赠答中接受了他们的诗歌观念,肯定前后七子,主张宗法三唐,讲求体格声调,诗论带有鲜明的格调派思想。此外,魏裔介又与地方诗人交往不断,如中州的宋荦、许傅严,太仓的吴伟业、吴乔,闽中的严方贻、魏宪等。其中,对魏氏诗学影响最大的当属其故里的河朔诗派。
河朔诗派泛指以申涵光、殷岳和张盖“畿南三才子”为首,具有共同诗歌创作倾向的诗人群体。乡缘关系使得魏裔介与他们交往密切,并对其诗论多有借鉴,尤以“一仕一隐”的杨思圣和申涵光为代表。
杨思圣(1617-1661),字犹龙,直隶巨鹿人。与魏裔介为同科进士,交情莫逆,诗歌酬唱不断。杨思圣虽然仕宦在京,但是早年学诗风气影响下,诗歌面貌与河朔诗人相近,徐世昌称他“与永年申凫盟、鸡泽殷伯严同以诗鸣河朔间,人品高洁,虽历仕中外,无一日不思归隐”[5]。杨氏论诗推崇王维,间接影响到魏裔介的诗学取向。更重要的是,他还促成了魏裔介与申涵光的交往。
申涵光(1620-1677),字孚孟,号凫盟,直隶永年人。明亡后绝意仕取,累荐不就。魏裔介很早就在杨思圣处读到过其诗作,但遗憾未识其人。顺治九年(1652),申涵光为父事奔走京师,据魏氏称:“余之识凫盟实始此也,自是诗文相往来无虚日。”[6]298迨魏氏辞官归里后,二人的交往愈加密切。魏裔介晚年作感怀诗称:“犹龙与凫盟,我辈论诗早。王孟如复生,晨夕相倾倒。”[6]473将与杨思圣、申涵光之间的关系以王维、孟浩然作比。申涵光论诗以杜甫为宗,兼采王、孟之长。梁清标评价魏氏诗歌说:“石生诗温柔敦厚处似《三百篇》,潇洒处似陶、韦、王、孟。”[7]283在杨、申等河朔诗人的影响下,魏氏对陶、王、韦、柳一派诗风的偏好可见一斑。
魏裔介受到清初格调派观念的熏陶,同时向河朔诗派等群体取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诗学观念,来看其诗史观:
李唐复尚清真,自陈伯玉力挽颓趋,踵事增华,则有若杨、卢四杰,王、孟诸家。迨李、杜集成,光焰万丈,钱、刘嗣响,亦其征也。有明自伯温、季迪振徽于前,而袁、杨诸君和之。洎弘、正,则有李、何、边、徐数公;嘉、隆则有王、李、谢、吴诸子。一时才华飚起,若珪璋并陈,埙箎叶奏,猗欤休哉![2]110
不同于明末清初诗坛对明七子的一概否定,魏裔介论诗远宗三唐,近法明代,反而标榜前后七子,认为有明一代诗歌斐然,直可与经典化的唐诗齐观。同时,又不满明末以来的“绮靡淫佻之习”“激愤悠谬之词”[2]105,本着肃清诗坛风气的目的,魏氏论诗主张“清真”,《唐诗清览集序》云:
太白云:“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尚清真。”夫诗不清真,不足言志,不清则亦不真。“清览”名集,义取诸此。[2]102
“清真”一说,是魏裔介取法自李白而提出的,以之来命名自己的唐诗选集,可谓重视。前面的分析指出,魏氏论诗宗唐,他将有唐一代诗歌的特点归纳为清真,又称“唐代清真,文质并茂”[2]103,每每在序文中鼓吹,可见“清真”在魏裔介诗学观念中占据极高的地位。
三、“清真”说内涵
“清真”一词最早出现在《世说新语·赏誉》中,称赞阮咸为人不慕荣利。诗歌理论中的运用则始于李白《古风》一诗,李白提倡的“清真”当与六朝“绮丽”相对,即清新自然的涵义,为后人熟知。明代以来“清真”一词的使用更为频繁,如李沂曰:“学济南则鹜藻丽而害清真,学竟陵则蹈空虚而伤气格。”[8]陈子龙说:“文人墨客所为诗歌,非祖述《长庆》,以绳枢瓮牖之谈为清真,则学步《香奁》,以残膏剩粉为芳泽。”[9]对于“清真”取义也多指向与“藻丽”相对,又不同于俚率的内涵。综上来看,历代对于“清真”的涵义使用相对有限,主要包括:人格上的高节寡欲和语言风格上的清新,魏裔介“清真”一说在此基础又有新的发挥。
不同于过往将清真作为单义词使用,魏裔介划分为“清”“真”两个语素来看,“不清亦不真”,“清”是“真”的基础,“清”的目的在于实现“真”。
首先,魏氏讲求清真是提倡诗歌言情志,以区别于不讲性情的伪诗。明七子树立起宗法汉魏盛唐格调的复古理论,以格调优先,忽视性情,往往止于字句、音律层面模仿古人,饱受明末诗论家诟病。魏裔介不满时人重蹈七子之病:“夫今海内之为诗者,家握隋侯之珠,人擅昆山之璧,自以为摹拟汉魏,而步趋三唐矣,其果汉魏耶,三唐耶?即使其优孟衣冠似汉魏,似三唐,于己之性灵何与耶?”[2]126批评时人追随明七子,只知“取法乎上”,自以为模拟汉魏盛唐就能习得好诗,实则是优孟衣冠,自己的性灵也无处安放。值得注意的是,“性灵”一词在明末为公安派所倡,魏氏虽受到格调派的思想的影响,但是认同公安派对明七子诗歌缺乏性灵的批评,并未步趋明七子“格调为先”的策略:
诗以自道性情耳,若必悉心步趋仿佛,则生气索然,故历下之敲金戛玉,终不若公安之任真独往也。余昔年选诗兼尚体格而必以性情为本。[10]316
历下派即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相较其“句摹调仿”,魏裔介更加认可公安派 “任直独往”的面貌,因而对格调派进行改造,主张在性情为本的基础上讲求格调:“沉酣于汉、魏、三唐,能达己之情而不袭其句,为诗之善者也。”[2]117即是提倡诗歌学古的同时发抒自己的真性情,主张诗要“灵快”:
今之心犹古之心,何分于《三百篇》,何分于汉、魏、六朝,何分于唐、宋、元、明欤?夫今之人,标新领异,不受羁缚,灵快无前,自得其所为真诗者斯足矣。余尝见庸人为诗,甫出口,已觉酸馅,而大家著述,历千百年,如方启之华。此何故?灵快与不灵快之异也。[2]107
从性情角度论诗,魏氏反对以时代论优劣,这种见解在明代以来宗唐祧宋的背景下显得尤为超前。继而反对文学退化论:“唐与汉、魏,各有其时代人才,不必相同。若谓后人必屈于前人,则《赓歌》后无《三百》矣。唐不及汉、魏,亦气格声调之末论,而言志者所弗取也。”[2]102魏氏之所以有这样的识见,是因为他破除以气格声调论诗的流弊,从诗歌言情的角度来看待的。其所谓的“灵快”即是敢于抒发内心性情,可以万古长新的真诗。
其次,魏裔介评点时人诗作曰:“浅语自真”“诗简切,此诗真实。”[10]635出于“求真”的目的,他提倡“浅语”“简切”,又体现了“清真”另一个内涵:语言上的浅淡。历代台阁诗人由于长期处于宫廷,诗歌题材有限,因而多以富辞丽藻、堆砌典故为能事,魏裔介何以提出这样的迥异观念呢?除了总结前代诗歌经验外,还与河朔诗派的影响和自身持有的复古思想相关。
一方面,魏裔介与河朔派诗人素有交往。易代之后,这一派诗人多寻求归隐,远离世俗,诗歌以“孤云野鹤”为描写对象,趣味上喜好王、孟诗歌不喜雕饰,以白描为主,造语平淡的风格。魏裔介在交往中受到他们的影响,反复称赞他们如“芙蕖出水”的作品[2]142。另一方面,魏裔介持有复古思想,认为愈古朴愈近风雅,排斥六朝那种绮艳诗风:“夫靡丽之言易工,而深静之致难遇。……六朝绮缛,专事华彩,识者鄙为雕篆。唐代清真,文质兼茂。”[2]135对于宋初的西昆体,他同样认为“太雕琢矣”。他在这里提倡的“清真”,是与雕篆绮缛之风相对的,接近于李白以至明末以来使用的浅淡自然的涵义。清初诗坛同样存在着婉缛的风气,如虞山派“二冯”以温、李为宗,提倡六朝、晚唐诗风。吴伟业对此十分惋惜:“每恨江左诸子虽风流可观,不无靡靡之响。”[7]283魏裔介同样指出时人作诗“绮靡淫佻之习,流荡忘返。”[2]132提倡浅淡的诗风正是为了肃清诗坛雕砌绮靡的风气,刘淇瞻肯定魏氏的鼓吹之功:“惟朴故雅,惟淡故真,是以砥柱狂澜,竞妍斗巧,绮靡之习为之一变。”[7]283值得注意的是,魏裔介反对雕砌,追求的浅淡绝不是浅俗,而是通过反复锤炼,形成削尽铅华的自然风貌,称赞胥廷清的创作:
今观永公之诗,镵削铅华,独全真理,其命意造语,如“青山原有待,明月正相宜。”……此即求之长庆、开成以前,亦未可多得。苏子瞻曰:“渐老渐奇,乃归平淡,非平淡也,炫烂之极也。”[2]128
举证胥氏诗作镵削铅华,惟有真意,语言平淡质朴不可多得。继而引证苏轼观点,认为实现平淡的语言风貌绝非易事,实乃求老求奇的极致。
受到河朔诗人的影响,魏裔介不仅对“清真”在语言上质朴自然的本义有所发挥,而且提倡诗歌在风神意境上的澹远绝俗,下笔无尘。明清易代导致社会上出现了大量遗民,归隐山林成为了他们的主要选择。魏裔介虽然高居庙堂,但与畿南周围的许多隐士都有交往,如孙奇逢、申涵光等。试看魏裔介对于隐士的态度:“仕、隐不可以分也。古之君子,得时则驾,不得时则蓬累而行。”[2]145“嗟乎,世之艳心名利久矣。……虽樗木瓠落,未必有济于用,然朋志松石,忘机麋鹿,其澹泊无求,有足多者。”[2]147可见,魏裔介虽处庙堂,却十分敬佩隐士淡泊名利、举世高蹈的品格,并且由对人格的关注旁及诗风:
诗以道性情,而山林之性情与廊庙之性情,亦微有异。如孟浩然、孟冬野、林和靖、魏仲先、谢四溟、徐文长,此山林之性情也。而其诗高寄霞表,超然物外,无一点烟火气,不作富贵纷华态,亦其自处者然耳。[2]134
作为庙堂诗人,在廊庙性情之外,魏裔介特意拈出山林之性情,实际上是肯定后者存在的意义。他列举自唐讫明的山林诗人,称赞他们诗作高远绝俗,超然物外。
魏裔介推许河朔隐逸诗人赵秋水的诗歌“平旷高远”“萧然冲适”[2]134。评价陈子逊创作“高怀澄澈,一物不挂于胸中”“有韦苏州之澹远、皮从事之遐旷”[2]135。又肯定后学吴星若诗歌:“清真澹远,不事铅华,自然近于风雅。岂濯魄于冰壶而飘飘然遗世独立者耶!”[2]138将清真与“澹远”并举,可见,他推重的诗歌带有排斥尘俗,澹然物外,高情远致的风格特点,以韦应物、皮日休等为代表。出于这样的诗风偏好,魏氏指出明七子创作上的不足:
明之盛,前有何大复七子,后又有王凤洲七子,骎骎乎盛唐矣。至于高、岑、王、孟之清辉,韦苏州之澹远,则无之矣。[11]35
我们知道,明代格调派独尊盛唐的观念实际上是以李杜为法,且偏重于杜甫。但在魏氏看来,王、孟、韦、柳一派同样是盛唐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着意批评七子对王孟一派清辉、澹远的诗风的忽视。
受到河朔诗人的影响,魏裔介推崇王、孟、韦、柳一派诗风,偏好澹然物外的趣味、清幽绝俗的意境和高远的风神。诗歌面貌同样有所体现,兹举《园居即事》一诗:
为园依堞雉,苍郁亦群山。霞带秋光净,云收野鹤还。移花遮曲径,激水下松关。酒史茶经外,吾生聊复闲。
诗歌前三联铺写田园、短墙,群山、晚霞、白云、野鹤、花径、和流水,尾联聚焦于翻看酒史茶经的场景,以享受闲适作结。这些意象营造的清幽意境和表露出的闲适心态,让人很难联想到出自一位富贵显宦之手。吴淇评曰:“通首清逸,总从闲字领略出来。”宋国荣评:“读次联想见胸中空旷不染一尘,而通体秀浑。”②类似的评语多见于时人对魏氏诗作的评价,程康庄评其《送辩若弟进士归》:“高旷之极,即在陶诗中亦是最佳者,岂可多得”;陈玉琪评其《慧香廊》:“清绝,如独坐幽篁之作”;董以宁评其《迟友人不至》:“澹远”。以上评语虽碍于魏氏权位而有过誉之嫌,却得以窥见他在诗歌创作中对于闲澹高远风貌的追求。
魏裔介主张的“清真”内涵包括:重视诗歌抒发性情之真,追求浅淡自然的语言风格和澹然高远的风神。如此来看,“清真”似乎出自魏氏个人的审美偏好,迥别于以往台阁诗人群体歌功颂德的风气,更无关乎其建设开国盛世文风的理想。实则魏裔介作为清初右文政策的重要推动者,他对“清真”的建构,正是以“雅正”的原则为前提的。
四、另一个角度照下的“清真”:雅正
首先,来看魏裔介提倡的“真”。明末清初的诗坛上兴起了一股对于“真诗”的探讨,一方面,当然是对模拟风气的批判和诗道性情的强调;另一方面,真与伪相对,是作为绝对正价概念存在的,涵义远不止于真情的范围,背后隐含的是儒家诗教的复兴。“诗以道性情”,道出的是“性之情”,这种“情”是以“性”为规范的。魏裔介追求的真性情以合乎《诗经》为规范,以“正”为旨归:“夫诗以言志,发抒性情,故作者代兴,论述不一。要之协于《三百》之义,斯为正耳”[2]116,“诗言志”一说最早见于《尚书》,被汉儒阐释为以性节制情感的温柔敦厚之说,成为儒家诗学观念的共识。甲申之变后,大量遗民身经亡国之痛,悲愤难抑,纷纷改造传统性情之说。申涵光认为“愤而不失正,固无妨于温柔敦厚也。”[12]钱澄之在重性情之真的基础上提倡“悲”情[13]。实际上都在为怨愤之情摆脱“性”的约束寻找理论依据。魏裔介作为新朝诗风的建设者,反复强调抒情要合乎风雅之正,认为:“古之君子如贾太傅,刘随州,或作《鵩鸟》之赋,或披《荒草》之什,皆不免于幽愁抑郁之气,以言乎才则美矣,以言乎道,则未也。”[2]123贾、刘两部作品历来被视作名篇,然而在魏裔介眼中都成为了否定的对象,因为他们空有美感而不合诗道正统。这种批评正是针对当时诗坛而论:“今海内言诗者颇多,……而愤激悠谬之词,杂不出经,亦岂鸾鸣凤哕耶。”[2]105诗坛上的“愤激悠谬”,是背离经学正统的表现,因此,其讲求的“真”是包含着儒家经学讲求的雅正为规范的。
其次,语言上的浅淡追求的是合乎元音的质朴与雅洁之美。语言风格上的浓丽与浅淡本属于审美偏好问题,无关乎正变,但是在魏裔介看来,语言上的过度修饰会破坏诗歌元音,造成绮艳:“自古风变为近体,始绮丽不足珍。”[2]133此外,中唐以后,诗歌为追求新的出路,传统的古典美学分别从各个方面发生了新变,魏氏不满这种变化:“以枯寂为尚,僻艳为奇,中晚以后,波靡斯极矣。”[2]116他是以正变观念来看待这一问题的,枯寂和僻艳使得诗风有乖于元古之音,是传统文质观的破坏。魏氏对组织雕缋、绮靡卑弱的不正之风正是以浅淡雅洁革之,力图恢复诗歌本来的面貌,他标举好友沈荃之诗作:“本于性情之正,风调高洁,故不为婉缛之体,绮丽之音,而一复元古清真。”[2]111在魏氏看来,诗体规避婉缛,语言不落绮丽是“性情之正,风调高洁”的体现,即元古诗歌的本色。
最后,魏裔介对风神上澹然高远的提倡乃是基于对“文如其人”说法的表象认识,即道德层面的人品与文品的一致性。他曾言:“余尝谓欲求天下之士,必自观其言始。其人清者则多为澹泊之言,其人鄙者则多为龌龊之言。”[14]292求才先观其“言”,惟有人格清高才能出语澹泊高远。他在诗歌内容上多提倡与现实无关的自然风物,表达出对荣辱名利的超脱和悠然闲静的隐逸心态,实际上是对清和之风的崇尚:“周子之人,萧然澹远,其所处最为困约,而一觞一咏,陶陶兀兀,盖古之所谓达者欤?……寄余一帙,读之,温润清脱。”[2]146周氏的现实处境极为困约,但反映在诗作中却是“陶陶兀兀”“温润清脱”,对外界荣辱得失不失温和地宣泄与表达,这便是澹远的理想诗风。如此来看,“清真”实际上构成了对明末以来遗民的亡国悲愤之音的消解,魏氏为申涵光作传:“高风远韵,寄心霞末,虽近于孟襄阳、陆龟蒙诸人,假使据其蕴藉,以应朝庙燕享征伐礼乐之制,其矞黄麟炳,弸中彪外,使小儒惊怖又不知其当何如?”[2]116关于“蕴藉”的涵义,魏裔介自释为“清真和雅,得三百篇遗意。”[13]309申父战死于抗清,本人也拒不出仕,一再鼓吹诗歌要抒发悲愤。“高风远韵,寄心霞末”,展示给我们的是一个不计较,不激进,澹然于国仇家恨,心态闲适的隐者形象,甚至诗歌可以作为新朝的庙堂之音。魏裔介对于申涵光诗歌这种有选择的品评,近乎粉饰,实则是有意识地构建合乎新朝的雅正观念。
综上来看,魏氏“清真”的基本内涵都隐含了雅正的前提,无疑是一种有意识的建构。再举一个鲜明的例子,魏裔介十分推举“清”:
陶、谢、韦、柳为正风,何也?以其才清也。诗最可贵者清,然有格清,有调清,有思清,有才清。才清者,王孟储韦之类是也。若格不清则凡,调不清则冗,思不清则俗。[11]38
魏氏此处对“清”的论述,当出自胡应麟《诗薮》并有所改动③。对比二人论述,他们都主张诗歌要“才清”,魏氏却首先将陶、谢、韦、柳诗风定义为“正”,继而指出原因在于才清,这样一来,“清”被推举为诗歌最重要的范畴,同时被偷换为“正”风的前提。作为格调派诗论家,胡应麟对才清的标举更多的是基于诗史的认识,而魏裔介对清的推崇,在风格喜好之外,更着重于将“清”向雅正的一面引导。魏裔介排斥变风,对“元轻、白俗、郊寒、岛瘦”等风格都加以排斥[2]109, “清”正是合乎雅正的重要范畴。
总之,一方面,作为风雅爱好者的魏裔介积极与诗坛名流交往,借鉴他们的诗学观念;另一方面,庙堂身份又要求其诗学思想重视教化功用,以合乎雅正为前提。魏氏针对明末以来的诗坛弊病,以儒家诗教观念为本,吸收前代格调派和河朔诗派的诗美经验,形成了雅正的“清真”诗学主张。
五、结语
罗宗强评价台阁文学思想说:“纲常名教统一思想引导下的士人,文学独抒性灵、感悟人生、艺术追求的特质在他们的视野中,已退居于次要的地位;而它的辅助政教的功能则成为主要的目的。”[15]这个论断放在明代之前的台阁创作中十分恰当,但是在清代来看就显得不是那么准确。翻看魏裔介的诗集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大多数的诗歌为赠答之作,其次则是表现闲适、恬淡生活作品,很少见到以往台阁诗人歌颂名主、宫殿和江山的内容,甚至还有《哀流民》一类诗歌,效法杜甫反映民瘼。这种现象在清初绝非个例,马大勇《清初庙堂诗歌群体研究》中多有举例,他将原因归结为人性中“夜行人”的一面。从人性的复杂性的角度来理解这一现象固然可取,我们还应当看到,随着诗学理论的积累,不同诗人群体交流的频繁,庙堂诗人群体越发重视自我的诗人身份,对于过往诗歌沦为颂德和载道工具的情况,他们同样避之不及。面对诗歌政教和审美双重功能的对立,清初庙堂诗人的方式是调和,不偏废一方,这在魏裔介的“清真”思想中尤为明显。作为诗歌审美范畴的“清真”和“清”,经过魏裔介的建构就成为了合乎雅正而又兼具美感的诗学理想。这样一种建构思路同样出现在其他台阁诗人诗论之中,如施闫章对“清正”的崇尚。直到在王士禛这样的大家手中发扬光大,“神韵”成为契合康熙盛世的诗风。这种理念在影响后世诗歌观念的同时,也为后代文风建设提供了借鉴,从雍正提倡“雅正清真”到桐城派方苞提出“清真古雅”“雅洁”,将雅正与清浅之美结合不难在魏裔介“清真”诗论中找到渊源。从这个视角来看,“清真”之说可谓真正实现了润色鸿业,“百世之风气习尚因之以成”。
注释:
① 据笔者所见,目前讨论魏裔介诗学的研究主要有:邓晓东《顺治右文与燕台诗人群体的复古诗风》,《文学遗产》2017年第3期,第93—105页;白一瑾《清初庙堂文人诗学意识形态之建构——以施闫章、魏裔介、冯溥为中心》,《上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9期,第45—59页等集中于其诗教主张方面的探讨。王学强《魏裔介诗论述评》,《安康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第58—62页;张子宁《魏裔介诗歌研究》,西北师范大学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等对其诗歌观念有所涉及,但都未关注到他对“清真”观念的提倡。
② 魏裔介. 兼济堂诗选[M]// 中国古籍珍本丛刊·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卷:第51册.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321.本段评语皆出自此书,不复注。
③ 胡氏原文作:“诗最可贵者清,然有格清,有调清,有思清,有才清。才清者,王孟储韦之类是也。若格不清则凡,调不清则冗,思不清则俗。” 参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出版,胡应麟《诗薮》,第1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