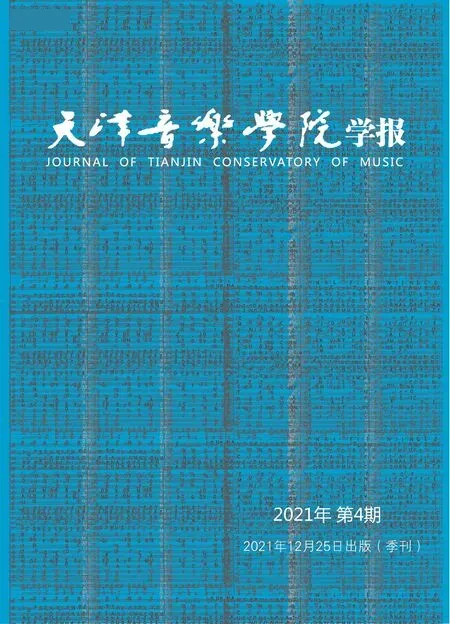天籁爽声 深邃恢弘
——刘德海琵琶音乐创作探析
傅利民
刘德海先生不仅是我国著名的琵琶演奏家、教育家,而且他在琵琶音乐创作中的美学理念、表现手段以及对琵琶音乐的继承与创新等方面,已然成为了当代琵琶音乐的典范。本文总结了刘德海先生琵琶作品中的技术价值和丰厚的文化底蕴,并对刘德海先生一生的求学问是、孜孜不倦、勤谨创作的精神进行阐释与分析,以期能客观深入地揭示先生在琵琶音乐创作中的核心思想与创作之心路历程。
一、作品的表达方式
古今中外的作曲家们在创作中特别重视演奏技术的拓展,身为演奏家的刘德海,在创作中更是把乐器技术的拓展放到了极为重要的位置加以观照。刘先生认为,作曲就是文化的思考,他的作品将琵琶音乐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就是刘先生在琵琶音乐创作中所展现的独到的“乐器语言”。与其说这是纯琵琶技术的表达,不如说这是作曲家在用琵琶来表达我们民族的语言、民族的情怀、民族的品格、民族的精神。从我国琵琶艺术的发展历史来看,大唐盛世时那开放豪气的天籁爽声,宋代那兼具宫廷雅致与民间乐坊情调为一身的勾栏瓦肆之乐,明清时那恢弘的武曲和细腻灵巧的文曲,无不体现着琵琶音乐的历史辉煌,而刘德海先生却一直在思索当代的琵琶音乐怎样才能表现当下人们的喜怒哀乐,这已成为了他一生的追求。
1.生活表达
刘德海先生在创作中追求本真,直抒胸臆,将自己的人文情怀融于其创作中。在艺术表现方面,无论是直观式的表达,还是内涵式的表达,都能在他丰富的琵琶音乐作品中找到音乐的自我,使人如痴如狂。他通过“秦俑”“天鹅”“春蚕”“晚霞”等大自然和历史的恩赐,创造出琵琶音乐中诸多的艺术精品,并将作曲家的人生感悟融于其中。例如在作品《秦俑》中,作曲家运用了高低两组绞弦演奏、包括人工泛音在内的多种泛音技术,这些技术的显现,足以体现中国古代战场那宏大的气势,正是这些独特的演奏技术呈现了一种不可多得的新音响,丰富了琵琶音乐的表现空间。
例1.《秦俑》

他的创作也有句逗清晰、比例均匀、张弛有致的唯美画卷。如在《晚霞情趣》中,那凝重而深刻的佛乐色彩中所透现出来的江南雨花季节中迷人的晚霞彩虹。
例2.《晚霞情趣》

对民俗、人文景观的塑造是刘先生创作的偏爱与追求,其作品《踏青》《磨坊》《纺车》《陀螺》《滚铁环》《杂耍人》《不倒翁》《木鸭》《风铃》等,不仅在旋法、结构的布局上独具匠心,而且在演奏技法上对右手食指、中指、无名指与大指反正弹的演奏之组合的使用等等,将其不同作品中的音乐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
保持一颗至真至美的童心、执着追求艺术理想形成了刘先生与其他作曲家琵琶音乐创作的主要区别,他的作品如《太阳公公晚安》《跳蚤迎亲》《快乐的夏令营》《小青虫化石的复活》《母驼喂奶》《螳螂姑娘的舞步》等,就是这一题材的典型代表,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而作为主题温柔亲切、质朴秀丽的《故乡行》《一根丝线牵过河》等作品又使我们感受着江南水乡那如诗如画的别样美感,让人流连忘返。
2.内心独白
在刘先生的作品中随处可感其 “起点”与“止点”的哲理性思维的内质,这点表明了刘德海的“希望”与“追求”是始终如一的,也是其独具特色器乐语言的一种表达方式,更是作曲家的心境独白。如果说刘先生早期作品是以明朗性格为基调而表现出的欢乐与幸福,那么在他中晚年时期作品中那凝练如髓、深蕴禅机的琵琶语言则给人们以宗教或哲理的深层领悟。如作品《滴水观音》《白马驮经》中的大指按主音、小指轻轻触弦的庙堂之神音,无一不是作曲家的神来之笔。《长生殿咏叹调》的主题是一个顺分节奏为主的舒展起伏的长旋律线条,曲首虔诚式的特征,恰似温柔的倾诉,这种纯粹的音乐语言风格和安详的音乐音响性格,似乎就是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内心情感的流露。作品《天池》中,我们不仅能见到以级进上行为特征、充满渴望和力量的主题,更能感受到“满天星斗”的多声织体,这都体现了他在音乐中的积极思考,苦苦求索,寻求希望的精神和意志。
二、富于个性的音乐美
富于个性的音乐美,这是笔者对刘先生作品的第一印象。刘先生创作的琵琶音乐中无论是抒情造型类的还是叙事言说类的,总是那样的深切动人。他的作品风格中既有刚强、高洁的高贵气质,又有活泼、轻快的生活气息。他几乎花了近40年的努力,先后完成了着意人生写照的“人生篇”,憧憬田园之美的“田园篇”,以宗教和历史故事为题材、体现中国式传统审美取向的“宗教篇”,表达寓情于景之创作手法的“乡土风情篇”,还有表现唐代历史题材的“怀古篇”等作品二十余首。刘先生非常重视对新音色的开发与利用,他特别注意到这个广阔的“音乐世界”,作品《一指禅》中,就是要求演奏者只用一只大拇指演奏,在极小的技术范围中去挖掘和开发大拇指的独特演奏技法,成功地展现了弹拨乐器的“点”状之美,赋予了作品那浓厚的“禅意”色彩。
例3.《一指禅》

刘先生在作品《滴水观音》中,其点与线对位上严密且富于情趣,在技法上所运用的挑外弦、轮里弦和模仿碰铃声的向上拨弦等,把滴水观音之意境刻画得淋漓尽致。
例4.《滴水观音》

在《喜庆罗汉》一曲中,刘先生以长时间的持续音、大量的模进音型和持续的高速律动行进的处理等,完成了音乐表达中的古老与现代、宗教与民俗、东方与西方、孩童与长者的身份互换,其音乐形象惟妙惟肖。
例5.《喜庆罗汉》

刘德海先生强调民间音乐内在的质朴美,认为在作曲技术理论的研究中,对乐种中所蕴含的乐器技术的探讨与研究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他对不同地域的民间乐种在文字、曲谱及音响等方面均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搜集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对各乐种的常用曲目、主奏乐器、旋律发展手法、宫调体系、曲式结构等方面都进行了研究与提炼。例如在其琵琶作品《柳青娘》中,所使用的潮州筝乐中重三六、轻三六、活五的技法等,深刻地揭示了我国传统弹拨器乐独具个性的旋律美。
他的音乐作品之美都在“情理”之中,每个音符都是那样充满激情,这是内心的体验,通过音乐旋律表达而成为情感的外观形式。先生在琵琶作品中,处处洋溢并渗透着童心之美,他以轻柔纤细、明净透亮的音色,表现着大自然的蜻蜓、小鱼、雏燕、蝴蝶和飞燕等,其作品中的简单而夸张之对比、自然流畅之律动,全面地体现了作者天真活泼、纯洁“稚拙”之童心。正如先生所说:“吾浸泡在大自然中,转化作日、月、星、空、山、草、木、花、鸟、鱼、虫……做它们忠实的‘代言人’。”(72)刘德海:《凿河篇》,《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9年第1期,第18页。先生在其音乐作品中,创造了高雅清新之意境,追求着自由美好的未来。他在作品中尤为重视“心”在音乐审美体验中的主导性。《凿河篇》中说到“世界之美,取之不竭,用之不尽。……心美则乐美;倾注着赤子之心之音乐,感人至深,魅力无穷”(73)同上。,其作品由内到外都深刻地体现着他那崇高的音乐审美之理想,也正是如此审美体验才使我们随处可感刘先生琵琶作品那富于特色的个性美。
三、创作理念与主张
刘德海先生强调音乐创作民族化的关键在神不在形,认为创新应以传统音乐文化为土壤,不断丰富音乐语言,对琵琶新技法的追求与传统不对立,因为只要表现的是民族的精神、气韵、风骨,不一定非用五声音阶,认为民族风格主要在神韵上,而不是外在的形式上。刘先生还强调个性并不意味着不顾民族性,强调民族性也不意味着抹杀个性,民族性寓于个性之中。正是基于上述理念,刘先生创作的作品主要有以下两种类型:一是从具体各民族乐种中移植和引用的,二是没有吸取具体的民族民间音乐而创作具有中国风格的琵琶作品,它们多采用五声性音乐语言,或用完全个性化的音乐语言表现当下个体的自我。
刘先生在其《凿河篇》中谈到“‘如歌’仍然是器乐所需求的永恒之美,因为它反映了现实最为普遍的审美要求。尤其生活在‘戏曲大国’的中国百姓,只有当他们在器乐曲中听到自己所熟悉的‘歌’时,才会引起对乐器的兴趣。”(74)刘德海:《凿河篇》,《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9年第1期,第21页。这就是作曲家坚守的创作理念之一。任何一种音乐行为和作品都有一定的观念在其中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也是在这种音乐观念意识中所形成的个性体验,在琵琶作品中总是“如歌”地表达内心与情感,无论是一个细小的动机,还是整体旋律之进行,其音乐始终扣人心弦,给人于“留连忘返”的审美体验。在这个“如歌”的器乐旋律中足于让你感受到“五彩缤纷”的世界和气骨不凡之品质。作曲家在《一字篇》中所论述的“技法易编,气氛好造,寻觅一条感人肺腑的旋律难上加难”(75)刘德海:《刘德海琵琶作品集》,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年版,第60页。即为刘德海先生琵琶音乐创作的最高准则与理念。
在对待中国音乐的创作与发展的问题上,刘德海先生既不妄自菲薄,走向“西化”,亦非妄自尊大,固守国粹心理,他主张我们应主动学习和吸取西方先进的创作经验,借鉴西方作曲技法,创作具有中国风格的音乐作品。上世纪70年代先生与作曲家吴祖强、王燕樵共同创作的琵琶协奏曲《草原英雄小姐妹》就是我国第一部琵琶与西洋管弦乐队协奏的恢弘之作,已然成为中西音乐合璧之典范。
21世纪初,刘德海先生就提出“民族器乐的希望在田野”的理念,在其《〈“1”行动计划〉备忘录》(76)刘德海:《〈“1”行动计划〉备忘录》,《中国音乐》2002年第2期,第18—19页。一文中比较充分地表达了生活是音乐创作源泉的主张。作曲家应该深入生活、体验生活,他所说的生活主要是指民间音乐生活,在这篇文章中详细地阐述了我们(作曲家、理论家、演奏家)如何向地方民间音乐学习的新视角、新思路、新观念、新行动。
他认为分析一个音乐作品的好坏应该基于大众的审美角度,音乐应该是平等的而不分国界的。刘德海先生在音乐创作中始终坚守中国传统音乐的思维,没有多年的理论探索与创作实践便难于形成精气神十足的琵琶音乐的“中国表达”。刘先生琵琶音乐的中国表达的核心就是承继和弘扬中国传统音乐的艺术精神。作为创作语汇,刘先生作品的简约、素净,渗透了中国传统美学的写意、神似的美学品格,其程式性、虚拟性、时空自由交错的琵琶音乐思维,散发着浓郁的传统音乐文化之芳香。
刘先生注重吸收前人琵琶创作的经验,推崇并重视历代琵琶音乐流派的观点与技法,但他在琵琶音乐的创作中更加注重对琵琶演奏技巧的大胆创新。“他的作品带有演奏家从事作品创作的那种特殊的‘即兴性’”(77)汪毓和:《刘德海琵琶音乐与中华文化——兼与梁茂春先生商榷》,《人民音乐》2005年第5期,第21页。,在以上举例的作品《秦俑》《一指禅》《滴水观音》《白马驮经》《一根丝线牵过河》等等就是此种类型的代表。
结 语
上文通过对刘德海先生的作品的表达方式、富于个性的音乐美、创作理念与主张等方面进行的分析与总结,使我们获得了许多新认识。“‘欢娱之词难好,愁苦之音易之’,琵琶尚缺少高层次的‘欢娱’之作;跳出琵琶传统大套,再寻求民间传统音乐作素材创作传统乐曲。”以及“须通过‘中国’,汲取‘世界’养料,塑造有民族特点的‘自我’。发挥‘自我’精神,才能创造出有血有肉的世界共性。”(78)刘德海:《刘德海琵琶作品集》,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年版,第61页。是刘先生重要的创作理念,也是他“金三角”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来自于他长期的音乐创作实践和理论,为我国当代民族器乐的创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只有深刻领悟刘德海先生音乐创作中的艺术主张、美学思想,才能全面准确地揭示其琵琶音乐作品的价值与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