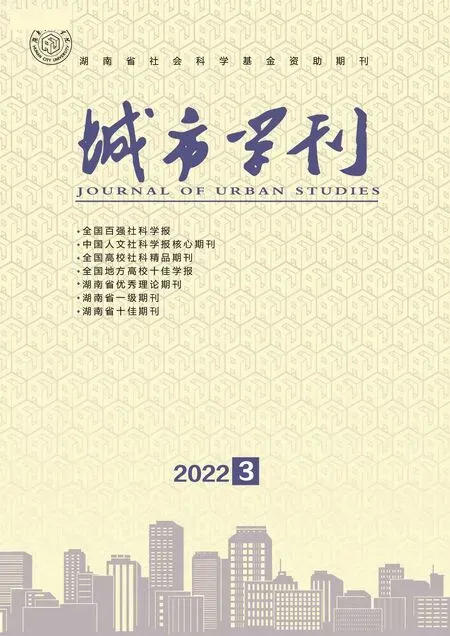陶渊明诗文的农耕意识与农耕之美
江建高
(湖南科技学院 文法学院,湖南 永州 425100)
一、陶渊明在出仕与归田之中纠结
(一)“弱冠逢世阻”“代耕本非望”
东晋末南朝(宋)初陶渊明(365—427年)的曾祖陶侃曾为晋大司马,封长沙县公,祖父陶茂与父亲陶逸也做过官,可惜陶渊明8岁时父亲即去世。陶家本非大族,至此家道中落。陶渊明29岁出为江州祭酒,旋自动去职。《饮酒》十九曰:“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1]晋安帝隆安二年(398),陶渊明出任荆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的幕僚,约两年后去职。元兴三年(404),刘裕起兵讨桓玄,出为刘裕手下的镇军参军,并作《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次年出为江州建威将军荆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义熙元年(405),41岁时任彭泽县令,80余天后即断然归田。
陶渊明初仕后,东晋王朝已百孔千疮,先是司马道子与王国宝专权,晋武帝被杀,新立的安帝是个傀儡,致东晋政权陷入悍将与大族的攻伐之中。之后孙恩造反、司马元显专权。元兴二年桓玄诛元显后篡位并将安帝迁到浔阳。次年刘裕据浔阳讨灭桓玄,兴复晋室。这一系列混战与变乱,多发生在陶的家乡,因之极大地冲击陶渊明早年“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的人生理想。诗人曾数次出仕又数次归隐,其诗说:“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饮酒》其十)
(二)仕与隐的二律背反
陶渊明自出仕到41岁辞彭泽令,一直在仕与隐、温饱与饥寒、“适俗韵”与“返自然”的二律背反中纠结。“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萧统《陶渊明传》)。[2]陶为生计而出仕,“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归去来兮辞并序》)。又由追求心性自由而归田,“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杂诗》其八);“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归田躬耕而艰难度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有会而作》);“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杂诗》其八);“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艰难度日而深知农耕为本,稼穑艰辛,“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移居》其二)。因此诗人竭力劝耕、勉农,“舜既躬耕,禹亦稼穑。远若周典,八政始食”(《劝农》其二),“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劝农》其五)。
陶渊明在仕与隐的二难选择中,决然归田,终老是间,长达20余年。穿衣吃饭是人的第一需要,陶渊明年轻时家里尚有田庄如上京里(柴桑某里名)、园田居(即古田舍,也叫南里)、南村(栗里)等。辞官归田后因火灾、旱灾、虫灾等原因,生计艰难,“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 (《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甚至沦落到乞讨的境地,“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乞食》)。陶家是八口人的大家庭,至隆安五年(401),上有老母,中有妻子,下有五男儿:俨、俟、雍、佚、佟(其《责子》曰“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陶渊明是一家之主,因为没有了“代耕”的俸禄,他只能躬耕自给,因此留下许多意蕴深远的农耕诗。这些诗或重农劝农意识鲜明,如“民生在勤”“八政始食”等;或写村景、乡情与心性,将农耕美化诗化。就以《乞食》而言,“叩门拙言辞”,村头乞讨,本十分尴尬,但一转笔就写到施惠者与行乞者即乡邻对诗人的理解、友好与慷慨,一下变得温馨与诗意:“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陶渊明不仅是躬耕垄亩的第一诗人,同时也是将农耕、村景与性情纯化美化的伟大诗人。[3]
陶渊明躬耕的作用十分有限,并未改变“箪瓢屡空”的生活状态。但身历之后,其诗体现的鲜明重农意识如“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民生在勤”“勤则不匮”等,至今仍然具有深刻意义。同时,他的诗文构建了充满诗意的自耕自食的理想社会形态:没有剥削、没有机巧、消靡王税、老幼有恃、男耕女织、安居乐业。从中体现出劳作生活中的诗意人生,诸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其一)等,所有这些都是前所未有、不能小觑的!
二、陶渊明的农耕意识与社会理想
(一)农耕意识
1.“八政始食”与“民生在勤”
陶渊明的120余首诗中,“涉农”诗就多达60余首。组诗6首《劝农》,每首四言八句。诗先追溯往古,“悠悠上古,厥初生民”的逍遥自在、自给自足的生活,在于远古哲人诸如后稷、舜帝、禹帝等的传技与倡导。后稷被尊称为农神,他曾教民稼穑。舜帝率先垂范,躬耕于历山。禹帝率众以疏通的方法治水,同样与稼穑相关。追述或描状先圣之后,诗人提出两个重要观点:其一,农耕乃是“八政始食”。“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尚书·周书·洪范》)周初八项政事,食列最先,意即穿衣吃饭乃第一大事。其二,“民生在勤”。诗人描绘了其所希冀的农耕面貌,“卉木繁荣,和风清穆。纷纷士女,趋时竞逐。桑妇宵兴,农夫野宿”,男耕女织,不误农时,庄稼繁茂,丰收在望。同时,“气节易过,和泽难久”,若误节令,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因此诗人提出不误农时,“民生在勤”,连冀缺、长沮、桀溺等贤达都结伴勤耕,普通人更应如此。第五首反问道:“宴安自逸,岁暮奚冀?担石不储,饥寒交至。”若贪图安逸,误了农时,则家无储粮,岁暮年关,将饥寒交迫。反之,“勤则不匮”,受用不尽。明人黄文焕《陶诗析义》称:“杜民智巧,惟在劝农,民农则必朴……举舜、禹、稷、周作榜样,以劝君相之重农;举冀缺、沮、溺作榜样,以劝仕隐之重农,竟无一人不在农中矣。”[4]
第六首中诗人责备孔子只沉溺于道德学问,当樊迟向他请教农技时,孔子责之曰:“小人哉,樊须也!”(《论语·子路》)他对董仲舒乐琴书而三载不践田园更是不满。被老丈称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孔子曾对其弟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 (《论语·卫灵公》)“学而优则仕”,孔子至整个儒家思想体系,都看轻农耕。颜之推《颜氏家训》言:“多见士大夫耻涉农务”。《南史·到溉传》载:到溉先祖曾担粪自给,被人骂为“尚有余臭”。东晋至南朝崇尚清谈,玄风盛行,更轻农耕。陶渊明不仅决然归田,而且特别表明躬耕的意义是“八政始食”“民生在勤”,可谓思深瞩远。
2.民以食为天,“衣食固其端”
《劝农》组诗从虞、夏、商、周等圣君到往古贤达,莫不重农,正劝反劝,其大旨在“播殖”“稼穑”“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则是从普遍的生存与生活着眼。开篇便突出衣食的重要性:“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端”者,首要、根本也。衣食是人类生存与发展最基本的条件。继而设问“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若不营农事,将无以自存。再写自己耕作之勤、之苦、之乐,并以古贤长沮、桀溺自勉,表达归田的决心,“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
陶诗中,与乡亲们话农事、勉农耕的诗意,所在多有:“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其二);“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移居》其二)。“但道桑麻长”“解颜劝农人”“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诗人重农,对乡亲们解颜相劝,语重心长。陶渊明归隐园田从心性畅、田园乐到悟出民生以力耕为先、以衣食为端,这是其躬耕垄亩而产生的远见卓识,是其农耕意识的突出体现。
(二)社会理想
黄土文明是以农耕文化为主要特征的。陶渊明归田躬耕,重农劝农,其社会理想主要体现在《桃花源记》与《桃花源诗》中。“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桃花源社会与世隔绝,没有剥削,男耕女织,安居乐业。与散文相映衬的《桃花源诗》:
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1]167
此中体现的社会理想更加具体:其一,人们争相事农,日入而息;其二,菽稷桑蚕,春种秋收;其三,消靡王税,摒弃机巧;其四,祭祀从古,民风淳朴;其五,童叟有恃,四时成岁。此乃带有小国寡民、弃圣弃智、顺心适性的老庄思想特征。陶渊明早年受儒家思想影响,经历世事后受老庄影响更深,据统计其诗文引用过老庄与列子的言论多达70余次。
三、陶渊明诗文的农耕之美
(一)戴月荷锄,春种秋收的耕作美
陶渊明躬耕自给,其农耕诗写归田后的所见、所闻、所感,特别着重写躬耕时的生活体验:农事、村景、乡情与心性之美。袁行霈说:“以自己的田园生活为内容,并真切地写出躬耕之苦,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人。”[5]
陶诗所写四时农事,写春种:“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所引第三四句特别写到春苗长势喜人,田地上庄稼一片葱绿,南风轻吹,如绿海泛波,生意盎然。再看《归园田居》其三,先写豆苗长势,“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作者一介书生,其农技怎比得上耕作能手?所以豆苗长得稀稀落落。再写早起晚归的辛勤,“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末了表达躬耕的决心:“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写秋收:《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从“开春理常业”始,继写劳作之艰辛,“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终于有了“岁功聊可观”“斗酒散襟颜”的丰收与喜悦。
春种秋收的喜悦中,又包含读书之乐的诗意人生:“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读山海经》其一)。“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和郭主簿》其一)。所引前一首诗写耕作之后,读我书、酌春酒、摘园蔬,而润物细雨,当春乃发生,农事中含诗情画意与耕读之乐。后一首诗农闲时游闲业、弄琴书、高粱美酒、自斟自酌,一派躬耕与琴书之乐。
(二)绿树婆娑,凯风因时的村景美
先看《归园田居》其一,陶家的庄舍园田居与周围村景之美:宅院占地空阔,“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绿树环绕,“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前屋后村,炊烟袅袅,鸡鸣犬吠之声,如闻熟悉的乡音,“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从庄院登堂入室,窗明几净,房间空敞,“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再如:“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和郭主簿》其一),诗状村舍盛夏之阴凉舒爽,“堂前林”“贮清阴”,南风时来,拂我衣襟,空闲时节,弄书抚琴,爽心惬意。村景之美更见于《归去来兮辞》:“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木欣欣以向荣,涓涓而始流。”
(三)邻曲时来,奇文共赏的乡情美
陶渊明农耕诗乡情淳厚。其归隐后先住园田居即南里,义熙四年(408)园田居失火后迁居南村即栗里(今江西九江城外),《移居》其一曰:
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1]56
诗人与南里乡亲过从甚密,交情很深。《移居》称这次搬家谋划已久,虽然新居南村不太宽敞,但因村民更加纯朴厚道,故特别乐意与之朝夕相处。怎么相处?邻曲时来,谈古道今,同赏奇文,共析疑义。浓浓乡情中,耕读之乐,自在其中。
“白日掩荆扉,对酒绝尘想。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田园居》其二);“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移居》其二);“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乞食》)。诗人和乡亲们交往密切,或“披草”相访“道桑麻”;或过路 “更相呼”“辄相思”“无厌时”。当诗人生活拮据临门乞讨时,乡亲们“解余意”,慷慨解囊,情如新知,千杯不醉。又如诗人所希冀的归田境界:“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归去来兮辞》)再看《饮酒》其九:
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与?田父有好怀。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繿缕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1]92
乡邻相访,诗人激动得倒裳相迎。来访乡亲还自携酒食,同情诗人褴褛茅檐的遭遇,说诗人与时俗乖离,劝其与世沉浮,以改变其生活境遇。虽然乡邻全是好心,但本性难移,诗人恳切而坚决地回答:“禀气寡所谐”“吾驾吾不回”!
(四)固穷守节,心远地偏的心性美
由于魏晋风流的高蹈凌空,晋宋易代的政治倾轧及诗人志趣的固穷守节、心远地偏,造就了陶渊明的诗意人生。其归耕诗把自己塑造成了真实亲和、有血有肉的“固穷之士”。[6]先看诗人37岁之作《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
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园林无世情……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1]75
陶渊明出仕或归耕的13年间,特别自41岁彭泽挂冠之后,始终没有忘怀“园林”“耦耕”“旧墟”“衡茅”,以“养真”“善自名”,保持自己“性本爱丘山”的真性情与固穷守节的善名声。“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敝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饮酒》十六);“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杂诗》其八);“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馀。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饮酒》其十);“九十行带索,饥寒况当年。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饮酒》其二);“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有会而作》); “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五柳先生传》)从这些诗文可见,陶渊明生活境况即使终老都“环堵萧然”“短褐穿结”“箪瓢屡空”,但都不改其固穷守节之志。
陶渊明不是神,不是圣人,因固穷守节而饥寒交迫,内心不是没有矛盾与纠结。“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屡空不获年,长饥至于老。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饮酒》十一)。先贤“一生亦枯槁”,实乃诗人的夫子自道。故杜甫说“陶潜避俗翁……颇亦恨枯槁”(《遣兴五首》)。诗人以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为两大精神支柱,前者以古贤为榜样,以求慰藉,“何以慰我怀?赖古多此贤”(《咏贫士》其二)。因之常以颜回、黔娄、袁安、荣启期等固穷之士自勉。《咏贫士》其三、四、五中曰:“荣叟老带索,欣然方弹琴……敝襟不掩肘,藜庶常泛斟”“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一旦寿命尽,敝服乃不周”“袁安困积雪,邈然不可干……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陶渊明尚自然,乐农耕,寄意于世外桃源,因之面对贫穷与枯槁,恬然自安,悠然自得。且看《饮酒》其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1]89
此诗作于41岁辞彭泽县令之后。虽结庐人境,因“不慕荣利”,便感受不到世间尘俗的喧嚣。东篱采菊,随意见山,无荣利萦怀,与智巧无关,因觉心静如水,景美如画。观南山景,傍晚最佳。看飞鸟还巢,外面世界纵然喧嚣,而我心归于宁静。“心远地自偏”,此庶几就是其诗意人生的“真意”,其微妙莫可言说。
即使陶渊明居官代耕,而乐山归耕之意,亦颇见于诗:“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代耕本非望,所业在桑田”(《杂诗》其八);“田园日梦想,安得久离析”(《乙已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日入相与归,壶浆劳新邻。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
钟嵘称陶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陶又常被称为“田园诗之祖”,唐人胡曾与宋人周紫芝诗曰:“英杰哪堪屈下僚,使栽门柳事萧条。凤凰不共鸡争食,莫怪先生懒折腰。”(《彭泽》)“千秋但有一渊明,肯脱青衫事耦耕。”(《杜鹃三首》)前者状其“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萧统《陶渊明集序》)的高洁心性;后者赞其脱衫躬耕的千古独有。然而陶渊明其人其诗,决非“隐士”与“田园诗”所能概括,因其“衣食固其端”“民生在勤”的重农劝农意识在焉,因其门前五柳、悠然南山的村景在焉,因其“复得返自然”的“真意”、真性情在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