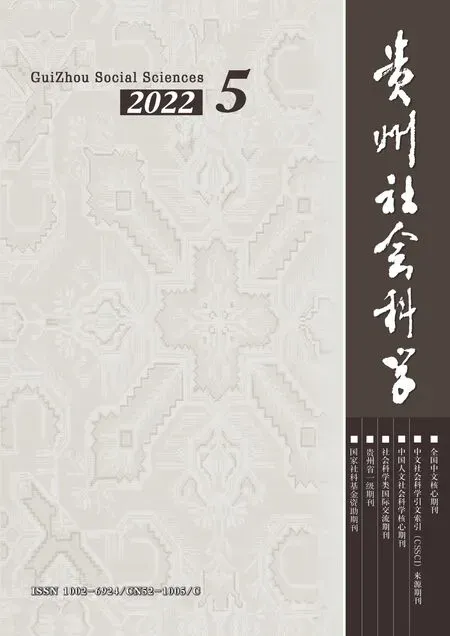《山海经》的史前文化信息
——以黄帝玄玉和熊穴神人为例①
叶舒宪
(1.上海交通大学,上海 200240;2.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732)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一主人公黄帝,在古文献中有“黄帝有熊”与“黄帝食玉种(玄)玉”两个重要的早期叙事。以之为切入点,结合当下文化创意产业的再创作与《山海经》热,我们提出三重追问:第一,中华文明发生的重要信息如何在断裂的神话叙事中被遗忘和失落;第二,如何探寻历史断层背后的真相,如何找回失落的文化信息,重建古老的文化记忆链条;第三,如何理解《山海经》叙事内容中深远的史前文化真相。
针对《山海经》内容古奥和难读难理解的情况,有必要先做出三点说明:其一,《山海经》透露出其他古籍中罕见的远古历史信息。这些非常古老的内容由于缺少其他文献的旁证和参照,显得孤立无援,难以索解。其二,理解《山海经》中真实信息的方式,是超越文字记录和书本知识局限,尝试到前文字时代的其他媒介中去寻找和验证。其三,找到前文字时代的其他符号载体有助于走出文字叙事小传统的限制,真正打开“物的叙事”的文化大传统之门(1)本文原为笔者2020年10月24日为浙江美术馆“山海新经——中华神话元典当代艺术展”所作演讲稿,观照到古代神话资源的文创转化方面。如今作为论文发表,未能补足大量相关文献。若深入探讨熊穴神人和黄帝有熊的关联,请参考萧兵著作《楚辞文化》和裘锡圭论文《“东皇太一”与“大熊伏羲”》等。②国内文学人类学派在2010年提出文化大传统理论,将甲骨文汉字出现之前的文化传统即史前文化,称为“文化大传统”。参见叶舒宪、柳倩月等编:《文化符号学——大小传统新视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2021年再度出版李继凯、叶舒宪主编的《文化文本》第一辑(商务印书馆),将大传统和小传统全部整合到“文化文本”概念之中。。而文化大传统的再发现和再认识,更足以彰显《山海经》内容的独特性和珍贵性。
以上对《山海经》三个层次的理论阐发表明,被视为华夏千古奇书的《山海经》所记载的内容绝非纯文学的虚构,而是保留着许多失落的文化大传统信息的“宝库”。从中华文明探源视角看,《山海经》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过去被认为是荒诞和无稽之谈的某些叙事,借助考古发现的遗址和文物新知识,会逐渐显露出某些历史真实性。因此,“与其说它记录着可以考实的地理知识,不如说反映的是作为权力的一种形式的知识生产模式。”[1]
一
研究中国上古文化问题,需要从中国本土话语出发。催生《山海经》叙事的先秦社会背景,属于十分典型的信仰支配下的社会。当时社会所传承的文化传统,可以作为生成演变中的文化文本来理解,其中必然蕴含着丰富的信仰话语体系和神话观念集群。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跨学科研究新流派——文学人类学,力图在传统的文字学、历史学等实证研究方式上,进一步打破学科界限,以实地考察的调研材料为基础,充分利用四重证据法的多学科知识求证优势,在文化大小传统之间寻找接榫的符号节点,尝试从多维度的文化阐释去回应上述三重问题,进而深入到《山海经》名物叙事的史前原型探索方面,找回具体的考古学文化语境,重新诠释“奇书”背后被文字遮蔽的权力话语体系和神圣资源的时空地理分布情况,揭示华夏文明发生期的原型编码情况及其神话观念动力。
首先以《西山经》所述黄帝吃白玉膏与播种玄玉[2]68-69事件为例。对于此事,古往今来几乎没有人将这样奇幻的叙事视为历史事实,为《山海经》做注疏的古代学者们亦语焉不详。博学者如文字学家加博物学家郭璞也不过写出一句话的注释:“言玉膏中又出黑玉也。”[3]68这是将玄玉解说为黑色玉石。清代学者郝懿行的《山海经笺疏》,面对此处所记载的“玄玉”名物,也只能援引《礼记·玉藻》和《淮南子》中的两个说法来加以旁证:“公候佩山玄玉”和“玄玉百工”[2]68。山玄玉,还是玄玉,这样的注释等于同义反复,问题并没有解决。
我国古玉收藏界一般对偏黑色的玉不叫玄玉或黑玉,而习惯称“墨玉”。既然《山海经》《礼记》《楚辞·招魂》等多个先秦文献都记载过“玄玉”的存在,那么当代学者考证所需要做的,是找出先秦和远古时期的偏黑色玉器实物,让古今语焉不详的对象有所参照和对证。因此,文学人类学的调研采样工作,通过以河南灵宝仰韶文化墓地出土的墨绿色玉钺实物为基准,在渭河沿线各个支流流域的几十个县级博物馆和文管所库房做地毯式搜索,共举出类似材质的史前玉礼器189件,年代大约从仰韶文化延续到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距今约5300年至4000年。2021年元月又在陕西咸阳博物院文物库房中辨识出属于仰韶文化的15件玄玉玉钺。这些工作不仅给古今无解的“玄玉”名物求证打开一道突破口,更有助于今人充分认识到中原文明发生期最初的玉器时代就是“玄玉时代”[3]58-66。从渭河上游向下游的蛇纹石玉料输送,开启历史上持续不断的西玉东输运动的先河,随后以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效应,将中原文明发现和采用西部玉石资源的位置一步一步向西移,经过洮河流域的马衔山、河西走廊南侧的祁连山、敦煌三危山(2)参见叶舒宪:《玉石之路踏查三续记》中《玉出三危——第十三次玉帛之路(敦煌道)考察报告》,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26—235页。、肃北马鬃山,最后抵达新疆的天山和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其间一系列新发现的古代玉矿资源储备情况,不仅弥补了历史文献记录的空缺,而且以扎扎实实的物证所组合成的证据链条,证明西玉东输路径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从而给丝路并非一条直线的单一路径认识,打开了广阔的再思考空间。这项对玄玉考证的研究成果,将丝绸之路中国段的起源史研究,从张骞通西域的两千多年前,拓展到距今五千年以上。
综观中国玉文化的发展史,在中原地区的用玉取材,确实存在过一个先玄玉后白玉的时代更替过程。换言之,目前经过考古发掘的中原史前文化,只是在距今5300年的河南灵宝西坡仰韶文化墓地首次批量发现墨绿色蛇纹石玉礼器的存在。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组织的玉帛之路考察活动已经完成对中原和西部地区的十四次考察和数据采样,追踪到中原地区史前用玉的西部来源情况,即沿黄河第一大支流渭河,从甘肃东部的武山县蛇纹石玉矿山,一直输送到关中和中原地区,并通过渭河的主要支流泾河和北洛河等,继续呈现多点开花的四散传播局面。此类实地调研和采样工作,不仅可以解开《山海经》所述黄帝时代的玄玉传播之谜,而且能够对《山海经》记录的140多处产玉之山多数在西部地区的事实,在我国西部版图上勾画出一个总面积达200万平方公里的西部玉矿资源区[4],由此进一步聚焦西部玉矿资源的散点分布与中原国家玉文化兴起的依赖关系,突出玉文化传统对华夏文明国家的重要性,同时彰显出《山海经》这一远古文本中所隐藏的玉石神话的深远信仰内涵。
其深远能够达到何种程度?至少有一些记载的内容属于史前文化期的信息范围。在2019年出版《玉石神话信仰与华夏精神》一书中,笔者已经用专章论述过以《山海经》为独家信息源的白玉崇拜在商周时期的起源情况,并将白玉崇拜理解为“玉石神话宗教史”上一次空前绝后的“新教革命”。正是由于商周时代以后,白玉崇拜取代以往所有颜色的玉石,定于一尊,而且至高无上,由此催生出《礼记》规定“天子佩白玉”的礼法信条。玄玉的信仰传统和原有的光辉也就随之一落千丈,并最终被后人彻底遗忘干净。《山海经》叙事中与黄帝相关的峚山玄玉,就这样成为死无对证的哑谜。如果将《山海经》叙事中“黄帝吃白玉膏”神话和《竹书纪年》所说西王母献白环神话,以及《礼记》天子佩白玉的规定,《史记》鸿门宴叙事中刘邦带给项羽的白璧为礼等等系列事件联系起来看,才能够看出中国式完美的理想——“白璧无瑕”——背后的神圣化物质的价值观真相。再去梳理10000年的玉石信仰神话向3000年的白玉崇拜的演变脉络,可以看出玉石神话信仰如何一步步驱动华夏国家的资源依赖,而文明国家核心价值的形成又是怎样伴随着神圣物质的颜色而变化的过程。
二
早在2004年出版的笔者与萧兵的合作著述《山海经的文化寻踪——“想象地理学”与东西文化碰触》中,曾表明对《山海经》性质的总体认识:这部书的构成,有着十分明确的政治动机。它的出现和上古文化走向大一统的政治权力集中需求相关。因此在当时将这部书界定为一部“神话政治地理书”,它以山川地理志的外观,表现现实与神话交织的叙述内容,其所构建的是一种虚实相参的空间图式,这种虚实相间、半真半幻的空间图式的实质,是服务于宗教政治的想象图景。就祭政合一的远古社会政治特色而言,《山海经》的巫书性质和功能就容易理解,那是为走向大一统的文化权力话语提供神权政治的空间证明,通过对各地山神祭祀权的认识和把握,达到对普天之下的远近山河实施法术性的全盘掌控。如今再度引入考古学和玉文化研究视角,我们已充分意识到《山海经》成书背后的国家意志和资源藏宝图性质正在得到进一步的显现。看似玄幻或虚构的叙事中,或许就潜藏着对古老名物的一些真实信息,包括甲骨文汉字产生之前的史前文化信息。像神人“珥蛇”的九处记录[5]、黄帝玄玉的一次记录,皆可以从史前玉文化的考古实物方面得以求证。其时,我们的方法论尚且停留在三重证据法所能达到的认知境界上。该书初版一年之后,笔者才正式提出四重证据的思路(3)关于四重证据法作为文学人类学新方法论及其应用情况,可参见《文学人类学教程》第九章、第十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杨骊等:《四重证据法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而日后的研究方向,也就日渐转向考古发现的第四重证据,尝试用出土的数千年以前的实物,再去求证《山海经》有关史前文化的独家记录的珍稀性。从《山海经》叙述的黄帝播种玄玉的神话情节中,既然已经可以找出玄玉作为黑色玉石的史前原型存在,便进一步以此为据,提出存在一个持续时间达一千多年的中原地区玉文化的发端期,采用《山海经》的“本土话语”,命名为“玄玉时代”。再进一步顺藤摸瓜地找出盛产玄玉资源的渭河上游地区的玉矿山,再根据调研的文物数据,描绘出玄玉礼器(玉钺)的时空分布图谱。
第二个案例还是和黄帝有关,即黄帝为“有熊氏”问题。司马迁写《史记·五帝本纪》时,根据《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记录黄帝为“有熊”,黄帝所建国家为“有熊国”:
“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6]45
即此,可以确定黄帝的国号和东亚大地上的陆地猛兽“熊”有关。除此之外,司马迁没有提供任何解释和相关信息。黄帝“有熊国”的得名也同样成为未解之谜。和前文运用四重证据法考证玄玉的案例一样,《山海经·中山经》的熊山熊穴神话叙事,提供的恰恰是司马迁的国家正史写作不敢采用的古老信仰材料:
“又东一百五十里,曰熊山。有穴焉,熊之穴,恒出神人。夏启而冬闭。是穴也,冬启乃必有兵。其上多白玉,其下多白金。”[2]259
这条记录材料对于求证黄帝“有熊”雅号的来源,无疑提供了神话信仰的真切说明。吾国先民们为什么崇拜神熊和天熊?《楚帛书》创世神话叙事为什么开篇说出“曰故天熊”四字,随后才是创世大神伏羲出场。《中山经》的叙事地点,明明说是熊山上的熊穴,为什么从熊穴中走出的主体,却不称之为熊,而要称之为“神人”呢?离开神话叙事背后的支配性信仰,问题是难以索解的。一旦恢复对原初神熊或天熊的信仰观念的理解,所有的疑问也会迎刃而解。好在《山海经》叙事不像司马迁叙事那样简略和粗线条,而是极为真切地保留下原初信仰的语境内容,这就是在《中山经》叙述的中次九经山脉的结语处,再度提示熊山的重要性原因:
“凡岷山之首,自女几山至于贾超之山,凡十六山,三千五百里。其神状皆马身而龙首。其祠:毛用一雄鸡瘗,糈用稌。文山、勾檷、风雨、騩之山,是皆冢也。其祠之,羞酒。少牢具,婴毛一吉玉。熊山,席(帝)也。其祠:羞酒,太牢具,婴毛一璧。干儛,用兵以禳,祈,璆冕舞。”[2]260
“禳”,指的是祭神消灾的禳解仪式活动;“祈”,则是祭神祝祷的仪式活动。前者用手执干戈者为舞蹈,后者则是用美玉装饰并头戴冠冕和身穿礼服者舞蹈。由此可观上古时期祭拜熊山圣地的仪礼盛况。
此处称“熊山”为“席”,对这个字,郭璞的意见是:“席者,神之所凭止也。”按照他的看法,熊山就是神山,也就是一个祭祀拜神的圣地。对郭璞如此的看法,郝懿行提出异议,他指出:“席当为帝,字形之讹也。上下经文并以帝冢为对,此讹作席,郭氏意为之说,盖失之。”[7]288如果采纳郝懿行的解释,熊山是帝所在之处,其神圣性的等级就更高出一层。清末著名学者俞樾《读山海经》也对此争议发表看法:“据下经堵山冢也、騩山帝也,疑此文席字,亦帝字之误。冢也神也,则冢尊于神;冢也帝也,则帝又尊于冢,盖冢不过君之通称,而帝则天帝也。”[7]288-289
郝懿行和俞樾,有着作为国学大家的慧眼和洞见,在此表现得十分清楚。读古书需要怎样细致入微的观察力,这对后人治学很有借鉴意义。既然《山海经》经文细致记录上古社会祭祀山神的仪式细节、用什么样的礼数和何种祭品都说明得清清楚楚,明眼人可以从这些非文学性的叙事中判断出多重的历史文化信息,尤其是玉资源和玉礼器对于上古信仰者和仪式主持者的重要意义。既然祭祀熊山时需要动用国家级祭祀礼仪的最高等级祭品——羞酒加太牢,再加玉璧,那么熊山熊穴所处神人的尊贵,也就恰好对应俞樾所说的天帝级别了。这不是给华夏共祖黄帝号有熊的哑谜,提供出信仰的“底牌”一般有力的情景化信息吗?
司马迁写到《史记·大宛列传》结尾处,提及他所见到的古书中有关河出昆仑的记载,他有如下的取舍判断:
“太史公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6]45
司马迁在此明确表示对传世古书的两种不同态度:对儒家经典《尚书》认为是可信的书;对《山海经》和《禹本纪》之类则认为是不可信的书,为他所不取。试想一下,如果西汉国家的史官自己都说“余不敢言”,那么后人谁还敢用正眼去看待《山海经》这样的“怪物”之书呢?《山海经》在汉代以后的历史上,再也没有得到史学家的青睐,只能给陶渊明、李白、曹雪芹们去参考和诱发更多奇特想象。《山海经》潜含的历史信息就此被尘封起来。
三
如今,根据考古学提供的第四重证据给出的史前文化信息,我们不得不说,在记录史前文化信息方面,《史记》的《五帝本纪》等篇章只有非常粗线条的帝王家谱,其真伪难以判断。倒是《山海经》提供了更多的具有真实性的相关信息。对于理解黄帝“有熊国”之谜,《山海经》熊山熊穴出神人叙事,发挥着重建失落的历史之重要作用。
1983年,考古工作者在辽宁省凌源县(现凌源市)和建平县交界处一座小山包上,发掘出距今五千年前的一座神庙。小山包名为牛河梁,于是该神庙被定名为“牛河梁女神庙”。这里出土了神熊偶像,号称“中华第一神庙”,同时也是迄今所知东亚最古老的神庙。时至今日,女神庙已经是名满天下,中国高铁还专门在这里设置了一个车站——牛河梁站!牛河梁女神庙中只发现了女神的塑像,还有熊和鹰的塑像,以及一只真熊的头骨的下半,却没有发现男神的塑像。汉代字典《尔雅》说熊是“蛰兽”,这两个字的解释,足以点明“熊”被史前先民奉为死而复生神物的关键联想,即熊的生活习性像昆虫那样冬眠夏出,这不正是《山海经》熊山熊穴“夏启而冬闭”特色叙事的真相所在吗?
在当代研究《山海经》的专家学者中,有人提出对熊山熊穴的具体地理位置加以考证落实,认为是在湖北的神农架地区。因为神农架地区常有关于野人出没的报告,所以就指认当代人所说的野人,即是《山海经》熊穴中出没的神人[8]。窃以为这样的看法,貌似可信,实际则出于现代人的误解。误解原因还是对《山海经》神话叙事的信仰底蕴关注不足。当今需要链接的新知识增长点,不在湖北神农架大山,而是在西辽河流域的小山包牛河梁,这里的距今五千年的神熊庙的基本结构是,让一个泥塑大熊的形象正面覆盖在庙宇建筑的顶上。此情此景,是当年的重要发掘者之一,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所长郭大顺先生在2019年8月辽宁省朝阳市举办的熊文化国际研讨会间所透露的。
2006年国家文物部门将黄帝有熊的故里,确认在河南省的新郑。新郑当地建起怀念五千年前华夏始祖黄帝的纪念性广场,广场中央是一件三足大铜鼎,其三足设计采用三只站立神熊的形象,希望前来祭拜的中华儿女们,多少能够想见人文共祖的熊图腾偶像。如今根据牛河梁女神庙建筑设计中的巨型天熊伏在屋顶的史前情境,或许可以重新创意设计出更符合史前形象的三熊足大鼎吧(不过从历史考证的意义看,若黄帝果真是五千年前的帝王,那时并不具备铸造大鼎的冶金技术条件)。
既然《山海经》叙述的熊山熊穴恒出神人,夏启而冬闭。我们当代艺术家和创意工作者们,是否可以尊重这个罕见的信仰和仪式的提示信息,构想出一些按季节交替而开关,围绕着神熊的冬眠夏出习性而表现的循环生命的神话景观呢?“冬闭”,是指熊入洞冬眠习惯;“夏启”,是从熊冬眠中醒来,自然要走出洞穴。“恒出神人”四个字,已经把熊崇拜的关键说明了:那就是拥有能够死而复生神圣能量者。熊的本字为“能”,不是恰好体现神熊崇拜和正能量信仰的内在关联吗?距今3700年的二里头遗址出土镶嵌绿松石熊形铜牌,可以从绿松石的天蓝色泽,联想到“天熊”形象的创意设计。还有距今5000年辽宁牛河梁出土的红山文化双熊首三孔玉器(现存辽宁省博物馆),这些具体鲜活的史前造型艺术案例,进一步昭示出被误读神熊图像的多样性,以及考古实物中所蕴含的丰富的信仰编码信息,同时也能够说明玉石神话信仰的文化“底牌”作用。这些都有助于阐释我们生活的文化小传统,是如何受到文化大传统及其信仰价值观念支配的。将单一的文献考证和语词训诂研究,转变为文化文本的系统重建和思想史溯源的研究,可以为华夏文明的源起找回其发生发展的连续性脉络,并重构某些早已失传的链条环节。
概言之,《山海经》是古代传世文献中保存史前文化信息最丰富的一部书,其中有不少早于甲骨文的神圣符号叙事,尤其是有关玉礼器方面和玉矿资源方面的叙事,能够体现先于青铜时代的玉器时代的意识形态与崇拜信仰情况,还有特殊的玉石神话观所支配下的礼仪活动情况。将《山海经》视为玉石神话信仰支配的国土资源圣典,其所记录天下400座山和140多处产玉之山,是当年的大数据形式呈现华夏王权“资源依赖”的圣书。同时,考古新发现的万年玉文化史传承不息的实况,将带来重新解读《山海经》的学术契机。
黄帝是否存在,目前的学术条件无法得到实证。与黄帝相关的物质文化母题“玄玉”和“有熊”,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五千年文化的深度求证。从考据学策略上看,从这种运用四重证据法的研究实践中,提炼出一个原则,即“物证优先”原则。这就是本文对《山海经》所包含的史前文化信息的尝试性解读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