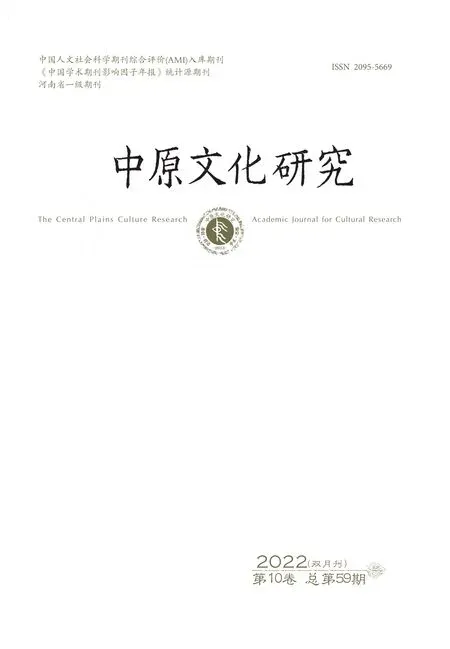“婚姻以时”:儒家婚礼诠释中的婚龄和婚期问题覆议*
王国雨
在儒家对婚礼的诠释中,一方面强调基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经由纳采至亲迎的“六礼”,从而彰显“成男女之别而立夫妇之义”[1]3648的人伦秩序意义;另一方面,基于对广义婚姻礼制和婚俗的关注,强调“男女以正,婚姻以时,国无鳏民”[2]45乃是理想社会治理蓝图的重要方面,如孟子将“内无怨女,外无旷夫”[3]视为先王施教化与行仁政的理想图景。在儒家礼学看来,婚礼之于婚姻家庭的成立和社会人伦秩序及时有序展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只有“婚姻以时”才能“男不旷,女不怨”[4]246。
儒家“婚姻以时”的观念,一方面体现在对初婚年龄的要求上,即认为男婚女嫁的年龄要合礼合宜;另一方面要求婚期合乎礼俗,具体包括婚礼亲迎的月份及良辰吉日的选定。然而,在儒家婚礼诠释史上,关于初婚年龄和嫁娶时月问题,聚讼不已,议论纷呈①,其中蕴含着战国秦汉以降儒者的婚姻伦理观和试图通过经学诠释规范现实婚姻伦理的努力。与之相关的,以对《周礼》婚制记述的讨论为中心,儒家还关注到对“旷男怨女”的婚配救济问题。本文试图在梳理和考证儒家婚礼的婚龄之时和婚期之时问题基础上,透视儒家婚姻伦理之意蕴和婚配救济之政的启示。
一、婚龄之时:“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说考辨
“婚姻以时”的观念,首先要求嫁娶“及时”,即初婚男女之年龄不能“逾时”,否则即为“失时”。在儒家《诗》学中,《毛诗序》便以此观念诠《诗》,如《周南·桃夭》被看作“男女以正,婚姻以时”的典范,《召南·摽有梅》被看作“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时”的展现,而《卫风·有狐》《郑风·野有蔓草》《唐风·绸缪》则被视为“男女失时”“昏姻不得其时”的先民歌唱。然而,礼学文献如《仪礼·士昏礼》中并无关于嫁娶年龄的礼仪规定,到底男娶女嫁在多大年龄进行是合礼合宜的,在后世引起了长期争议。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经典中所讨论的适婚年龄之应然,与历代行政诏令往往不一致,亦与事实上之嫁娶年龄时常扞格②。这里拟对先秦以降关于该问题的经学论争做一番彻底的检讨。
真正说来,初婚年龄问题,周代婚礼不载,早期儒家仅偶有论及,真正成为经学史话题实际上始于汉代。争议主要围绕是否“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这一论题展开。持肯定观点者认为,三十、二十为男娶女嫁之正年;持否定观点者认为,三十、二十为“期尽之法”,即为男娶女嫁之最高年龄限制;持中间态度者认为,大夫士以上,嫁娶不拘年龄,唯有庶民才“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持肯定观点者中,如班固《白虎通义·嫁娶篇》从生理依据、阴阳奇偶之数和大衍之数的角度加以论证:
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阳数奇,阴数偶。男长女幼者,阳舒阴促。男三十,筋骨坚强,任为人父;女二十,肌肤充盛,任为人母。合为五十,应大衍之数,生万物也。[5]231
《大戴礼记·本命》亦云:
中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合于五也,中节也。太古男五十而室,女三十而嫁。备于三五,合于八也。[6]
这也是依据阴阳奇偶之数,对理想中的“中古”和“太古”加以描述的溯古之论。《逸周书·武顺篇》同样从阳奇阴偶之数的角度说:“男生而成三,女生而成两,五以成室。”[7]西汉伏生《尚书大传》观点亦相同,并托言孔子认为:“女二十而嫁通乎织纴纺绩之事,黼黻文章之美,不如是,则上无以孝于舅姑,而下无以事夫养子。”[8]这是从三十、二十始具备承担婚姻伦理责任之能力的角度强调嫁娶之正年的。东汉郑玄注《周礼·地官》时认为,之所以“圣人为制其中,令民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乃是因为“过时则奔随,先时则血气未定”,因此三十、二十可“防其淫泆”[4]479,是恰到好处而最为合宜的初婚年龄。
上述汉儒的言之凿凿,其实是在战国以降儒家论说误读基础上的发挥与引申。被认为支持肯定说的文献材料,首先是《周礼》和《礼记》中的如下论说:
媒氏掌万民之判。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9](《周礼·地官·媒氏》)
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女)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1]3186(《礼记·内则》)
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壮,有室。[1]2676(《礼记·曲礼》)
从论说语境而言,上引材料其实均不能视为以三十、二十为嫁娶之正年的有力证据。首先看上引《周礼·地官·媒氏》这句话,郑玄注云:“二三者,天地相承覆之数也。《易》曰‘参天两地而奇数’焉。”[10]1034郑氏依然从汉代盛行的阴阳之数加以发挥,似乎以三十、二十为嫁娶正年。但王肃《圣证论》认为,这句话是:“谓男女之限,嫁娶不得过此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不待礼而行之,所奔者不禁,娶何三十之限?”[4]362联系《周礼·地官·媒氏》的文本脉络,下文有“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可见王肃“言其极法耳”的意见可从。正如孙诒让引俞正燮观点所指出的:“此令也,非礼也。礼不下庶人,令言其极不是过。”[10]1036媒氏作为负责掌管庶民得耦以成夫妇的职官,这里的政令是通过婚姻救济政策让尚未嫁娶的三十之男和二十之女杀礼以成婚配。可见,《周礼·地官·媒氏》之论恰恰表明三十、二十是嫁娶的最高年龄限度,超过便需要婚姻救济。同时需指出,《周礼》的媒氏乃“掌万民之判”者,是针对庶民婚配而非士以上的贵族阶层而言的职官。《礼记·内则》的“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中,郑玄注:“男事,受田给政役也。”[11]772从上下文看,这里的“三十而有室”是放在男子从幼年到“七十致事”的生命历程中定位的,其实是说贵族男子三十岁已经有了妻室,要受田给政役了,并非三十岁始得婚娶。下文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郑玄注:“谓应年许嫁者,女子许嫁,笄而字之。其未许嫁,二十则笄。”[11]773既然十五许嫁便“笄而字之”,未必要等到二十才嫁。“二十而嫁”是其大概,并非定礼,这从“有故,二十三而嫁”一句可明显看出。“有故”,王夫之注:“谓父母死及婿之父母死,辞昏而待其服除也。”[12]若因父母亡故而需要服丧,则最迟也要二十三岁而嫁。
关于《曲礼》的“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壮,有室”,郑玄注云:“人年二十,弱冠,成人,有为人父之端。”孙希旦也说:“愚谓二十而冠,三十有室,四十而仕,五十服官政,亦制为大限如此耳。……大夫士之冠昏未必皆至于二十三十。”[11]14既然二十已经成人,“有为人父之端”,自然便可婚娶。联系到早期儒家历史叙述中的舜因三十未娶而被称为鳏,可见,早期儒家并不认为娶嫁要晚至三十、二十。《礼记·冠义》说:“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孔疏云:“人二十有为父之道,不可复言其名,故冠而加字之。”[13]1616古礼中冠笄之礼之后即成人,成人即可嫁娶,应是基本认识。顺便要指出的是,从上引郑玄《礼记》注可以看出,郑氏并未认为不满三十、二十必不可以嫁娶。当然,不同贵族阶层所行冠礼年龄是不同的,二十而冠是士,若为诸侯,十二即可以加冠,如《左传·襄公九年》晋侯对季武子说:“国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礼也。”孔颖达正义曰:
案此传文,则诸侯十二加冠也。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则十二加冠,亲迎于渭,用天子礼。则天子十二冠也。《晋语》柯陵会,赵武冠见范文子,冠时年十六七,则大夫十六冠也。士庶则二十而冠,故《曲礼》云“二十曰弱冠”是也。[14]
可见春秋士以上的贵族男子行冠礼而婚娶时尚不及二十岁,对于范围更广的士阶层而言,男自二十至三十,女自十五至二十,进行嫁娶都可视为“婚姻以时”③。
对是否“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的问题,其实《孔子家语·本命解》中通过鲁哀公和孔子的问答,有过颇为自觉的讨论:
公曰:“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则可以生民矣。而礼,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有夫也,岂不晚哉?”孔子曰:“夫礼言其极,不是过也。男子二十而冠,有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许嫁,有适人之道。于此而往,则自婚矣。”[15]
《孔子家语》应源自战国儒家之论,并非王肃向壁虚造。“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从男女生理上具备“生民”可能性而言的,类似论说亦见于《大戴礼记·本命》《韩诗外传》和《黄帝内经·素问》等。从鲁哀公与孔子问答内容看,《本命解》篇写成时已有礼类文献强调“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但被质疑太晚,并借孔子语指出,男子二十、女子十五之后,便可“自婚”,即父母可适时自主决定嫁娶而成婚。这则材料显示,在战国秦汉间之儒家内部对“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有自觉反思和辩驳。
结合史实从更宏观的视野来看,无论是大夫士以上之贵族还是庶民阶层,并无“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之礼。关于民众的初婚年龄,统治者和民众本身均希望早婚,但实际上能否如愿,则可能更多地与家庭生计和财力有关。《墨子·节用上》在讨论如何实现人口倍增理想时,对“圣王之法”和现实情况作了比较:
昔者圣王为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处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圣王之法也。”圣王既没,于民次也。其欲蚤处家者,有所二十年处家;其欲晚处家者,有所四十年处家。以其蚤与其晚相践,后圣王之法十年。若纯三年而字,子生可以二三年矣。[16]159-160
这里的男二十而娶,女十五而嫁乃墨子心目中的往昔“圣王之法”,也应该是民间认可的嫁娶婚龄。这里的“次”,孙诒让注:“次读为恣,言恣民之所欲。”[16]160圣王既没之后,墨子时代民众肆意而为,早的有二十婚娶的,晚的有四十婚娶的,平均三十岁,晚“圣王之法十年”,假设三年生一子,十年可以生三个孩子了。墨子认为,婚娶的早晚关系到生育和代际更迭的速度。吕思勉先生《昏年考》认为:“蕃民,古人之所愿也。然精通而娶,始化而嫁,为古人财力所不逮,是以民间恒缓其年。”[17]《召南·摽有梅》毛传曰:“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礼未备,则不待礼会而行之者,所以蕃育民人也。”[2]93可见,为促使民众婚姻及时,甚至允许三十、二十的大龄男女不备聘礼而嫁娶。因此,《周礼·地官·媒氏》所谓“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确乎是促使民众早婚而不要超过的最大年龄,并非嫁娶之正年。而统治者从富国强兵的角度出发,考虑到民众初婚年龄常有拖延趋势,因而时常诏令民众早婚,如《国语·越语》中,越王勾践为了增加人口,曾颁布“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18]的诏令。
对汉代颇为流行的以“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为嫁娶之正年的观点,不仅汉代即有不同意见,如上述毛亨、王肃及其所注《孔子家语》之论,而且在后世有更精彩的辩驳。如晋代范宁注《春秋穀梁传》时引谯周之说:“凡人嫁娶,或以贤淑,或以方类,岂但年数而已。若必差十年乃为夫妇,是废贤淑方类,苟比年数而已,礼何为然哉!”[19]机械地以三十、二十为嫁娶之正年,明显不合情理。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摽有梅》疏曰:“诸经传所以皆云三十、二十,都不言正嫁娶之年,而皆为期尽也。”[2]92清代俞正燮也说:“士以上婚有礼,礼无嫁娶年者,国家各有事故、政役、丧纪,不可豫期也。”[10]1037同时,俞氏还对为何有“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之说的提出,给出了原因分析,他说:“令著三十二十者何也?女子精化早通,止于四十九,故以二十为极;男精化通迟,止于六十四,故以三十为极。”[10]1037这是从生理年龄和政策伦理的角度给出的合理解释。孙诒让《周礼正义》总结说:“通校群经,并无男未三十女未二十不可嫁娶及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同法之明文。”[10]1036戴震《诗摽有梅解》认为,诸经典中的“男十六而精通,女十四而化成”,是就生理基础“举其端言之”,墨子所谓“丈夫二十毋敢不处家,女子十五毋敢不事人”,是“举其中言之”,而《周礼》“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则是“举其终之大限言之也。不使民之后期,而听其先期,恐至于废伦也”,而且,“若民之先期,男十六而娶,女十四而嫁,亦不闻古人有禁也”[20]12-14。戴震之论,可谓通达。
综上所论可见,儒家“婚姻以时”的观念认为,婚姻的缔结,不能“过其盛壮之年”。故在初婚年龄方面,主要体现为期望嫁娶及时,从而“内无怨女,外无旷夫”。早期儒家所谓男“三十而有室”和“女二十而嫁”并非以三十、二十为男女娶嫁之正年,而是期望民众婚姻及时的“期尽之法”。汉代以阴阳奇偶之数和大衍之数对婚龄的诠解,是不符合早期儒家观念和社会各阶层嫁娶实际的附会与引申。汉儒之所以有如此论说,或出于对汉代早婚现象的一种强烈反动和批评,如陈顾远先生《中国婚姻史》认为是汉儒“托古以言晚婚之理想”的“设法”之论[21]97-98。总的来说,由于“嫁娶之故,情事万端,圣人不能预定,姑示以极至之期而已”[22]。因而婚礼文献无明确初婚年龄规定便容易理解。一般而言,贵族阶层嫁娶早于庶民阶层,十五至二十举行冠笄之礼后,即可嫁娶,且无过晚需要婚配救济之虞。而庶民阶层也可早婚,统治者基于富国强兵考虑也鼓励早婚以增加人口,但由于家庭财力所限,常有推迟嫁娶现象,甚至达到或超过三十、二十,因而需要统治者施行婚姻救济政策以促进之。
二、婚期之时:婚有定期还是通于四时
除初婚年龄问题外,儒家“婚姻以时”观念还体现在关于婚期之时的经学争论中,认为举行婚礼之亲迎仪程的具体月份、吉日和时辰均应合乎礼俗之要求。在诠解经典文本时,儒者往往根据其所理解的婚礼之正期,对嫁娶给出“及时”抑或“失时”的褒贬评价。
关于亲迎之良辰和吉日的选定,就上古时期而言,是没有争议的。先看时辰方面,新郎亲迎新妇必须于昏时进行,《仪礼·士昏礼》有夫家初昏陈馔,然后新郎“从车二乘,执烛前马”前往迎娶的记载,后世演绎为“洞房花烛夜”的文化意象。之所以昏时亲迎,有学者认为是古代掠夺婚的遗迹,而汉唐诸儒则从阴阳往来的角度加以诠释,如班固《白虎通义·嫁娶篇》云:“婚姻者,何谓也?昏时行礼,故谓之婚也。”“所以昏时行礼何?示阳下阴也,婚亦阴阳交时也。”[5]248-249许慎《说文解字·女字部》云:“礼,娶妇以昏时,妇人阴也,故曰昏。”[23]4孔颖达《礼记正义·昏义》疏:“娶妻之礼,以昏为期,因名焉。必以昏者,取其阴来阳往之义,日入后二刻半为昏”,“婿以昏时而来,妻则因之而去也。”[13]1617这些都是对为何亲迎之礼用昏时的义理诠释。接着是关于吉日的选定,“六礼”中谓之“请期”。《仪礼·士昏礼》云:“士昏礼,凡行事必用昏昕。”意为除亲迎于昏时举行外,“六礼”中包括“请期”在内的其他仪程均于黎明进行。所谓“请期”,就是夫家占卜得到吉日后,告诉女家之礼,所以请期即是告期。孔颖达《礼记·昏义》疏解释说:“请期者,谓男家使人请女家以昏时之期,由男家告于女家,何必请者,男家不敢自专,执谦敬之辞,故云请也。”[13]1619所以“请期”是男家之谦辞,迎娶的吉日以男家事先占卜的结果为准。《仪礼·士昏礼》记载,“请期”时男家使者说:“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请吉日。”就是说男方家三族康吉,可以行嘉礼,所以请求择定完婚的吉日。《礼记·曲礼》还有“日月以告君,齐戒以告鬼神”的记载,即将结婚日期告诉官方,并禀告庙中祖先之灵。总之,关于婚礼亲迎的时辰和吉日,是有程式化规定的,上古无异义。
然而,关于婚礼亲迎的季节和月份,则是经学史上纷争不已的一大问题,涉及毛传郑笺之争、郑玄王肃之辩等。梳理此问题的诠释史,相关观点概言之,就是婚礼有定期还是通于四时之争,其中又有诸多同中之异。与初婚年龄问题一样,《仪礼·士昏礼》等礼类文献无关于举行婚礼之时月的记载,亲迎时月成为争议话题也是从汉代开始的。最早提到婚期话题的是《荀子·大略》,其文云:“霜降逆女,冰泮杀止。”④《毛诗正义·东门之杨》孔颖达疏引荀子此言云:
霜降,九月也。冰泮,二月也。然则荀卿之意,自九月至于正月,于礼皆可为昏。荀在焚书之前,必当有所凭据。毛公亲事荀卿,故亦以为秋冬。《家语》云:“群生闭藏乎阴,而为化育之始。故圣人以合男女,穷天数也。霜降而妇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农业起,昏礼杀于此。”又云:“冬合男女,春颁爵位。”[2]447
根据孔颖达的解释,荀子认为嫁娶婚期在九月至正月之间的秋冬时期。同时孔颖达认为,《荀子》在秦火之前,可以凭信。这里提到的毛公即毛亨,其在《毛诗传》中贯彻了以秋冬为嫁娶之正期的观点。略举两例如下,如《邶风·匏有苦叶》的“士如归妻,迨冰未泮”,毛传曰:“迨,及;泮,散也。”[2]143显然毛公认为娶妻应在冰未散,即正月以前及时迎娶。又如《陈风·东门之杨》首章“东门之杨,其叶牂牂”,毛传直接判为“言男女失时,不逮秋冬”,以回应“刺时也。昏姻失时,男女多违”的《毛诗序》之意[2]446。《唐风·绸缪》孔疏云:“毛以为,婚之月自季秋尽于孟春,皆可以成婚。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乃得以仲春行嫁。自是以外,余月皆不得为婚也。”[2]388孔颖达认为,毛亨是受荀子影响而持此观点的。这里所引《家语》,出自《孔子家语·本命解》,观点完全与荀子相同,并从顺应阴阳化育和顺天时农事两个方面,指出以秋冬为嫁娶之正期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董仲舒《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也从阴阳往来之天道的角度肯定荀子的婚期说,其文云:“天之道向秋冬而阴来,向春夏而阴去,是故古之人霜降而迎女,冰泮而杀内,与阴俱近与阳俱远也。”[24]此外,被认为与董仲舒同属于齐学的西汉《焦氏易林》观点亦一致,如《易林·复之履》云:“十五许室,柔顺有德,霜降归嫁,夫以为合。”[25]而王肃《圣证论》驳郑玄时引《韩诗传》云:“古者霜降逆女,冰泮杀止,士如归妻,迨冰未泮。”[4]362可见,韩诗和毛诗、齐诗一样,都以秋冬为婚姻之正时。
不过,与上述秋冬说不同,以东汉的班固和郑玄为代表人物的另一观点认为,仲春为婚礼之正期,亦有很大的影响。班固《白虎通义·嫁娶篇》云:
嫁娶必以春者,春天地交通,万物始生,阴阳交接之时也。《诗》云:“士如归妻,迨冰未泮。”《周官》曰:“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令男三十娶,女二十嫁。”《夏小正》曰:“二月,冠子娶妇之时。”[5]236-237
《白虎通义》认为,之所以春季是嫁娶的正期,乃因春天是万物始生而阴阳交接之时,故此时男娶女嫁是顺应天时之正时。不过,这里所引《邶风·匏有苦叶》诗句,毛传和《孔子家语》恰认为是秋冬嫁娶之证。所引《大戴礼记·夏小正》语是“二月,绥多士女”的某氏传,此条材料和所引《周官》虽为主仲春说的主要依据,但实际上并不能支持其观点,后文详论。郑玄注“三礼”和笺《诗》也极力贯彻其仲春正期说。如注《周官》“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云:“中春,阴阳交,以成昏礼,顺天时也。”[10]1040仲春举行婚礼是顺阴阳相交之天时的。又如注《礼记·月令》“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云:“玄鸟,燕也。燕以施生时来,巢人堂宇而孚乳,嫁娶之象也。媒氏之官以为候。”[13]473而在笺《诗》时,郑玄更是不遗余力地强调仲春为正期,并以此为准解读诗篇中婚姻的“及时”或“失时”。如《周南·桃夭》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毛传云:“夭夭,其少壮也。灼灼,华之盛也。”毛公认为,《桃夭》反映的是花季年华出嫁,年龄及时合礼。而郑玄笺则云,“喻时妇人皆得以年盛时行也”,“宜者谓男女年时俱当”,认为嫁娶不仅是以“年盛时行”,而且“行嫁又得仲春之时”[2]46。与毛传相比,郑笺强调了仲春为婚礼正期。又如笺《召南·行露》“厌浥行露,岂不夙夜,畏行多露”云:“谓二月中,嫁娶时也。”[2]79笺《陈风·东门之杨》云:“失仲春之月。”笺《小雅·我行其野》“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尔居”云:“樗之蔽芾始生,谓仲春之时,嫁娶之月。”[2]678此外,《召南·摽有梅》《唐风·绸缪》郑笺,亦皆以仲春为婚姻之时,兹不赘述。
对于郑玄仲春说,王肃起而批驳,再申荀子、毛传和《孔子家语》的秋冬说。其《圣证论》曰:“吾幼为郑学之时,为谬言,寻其义,乃知古人皆以秋冬。自马氏以来,乃因《周官》而有二月”,“时尚暇务须合昏因,万物闭藏于冬,而用生育之时,娶妻入室,长养之母,亦不失也”[4]362。这里的“马氏”为马融,可见郑玄的仲春说,可能源自班固和马融。同时,上文已论及,王肃认为,《周礼·媒氏》的“仲春之月,令会男女”,联系下文“于是时也,奔者不禁”,乃是“昏姻之期尽于此月矣,故急期会也”之意。王肃的理解符合《周礼·地官·媒氏》之意。这里“奔者不禁”之“奔”,乃是“六礼不备谓之奔”,“此奔亦由媒氏,但礼不备耳”[10]1044。旨在权许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于婚期将近之时,杀礼以成婚。戴震曾申述曰:
《周礼》中春之令,专为不备六礼之民,纠察其杀礼之由。且三十之男、二十之女,至是尽许其杀礼婚嫁,过此岂有后期者哉?凡婚嫁备六礼者,常也,常则不限其时月;其杀礼不聘者,权也,权则限以时月。夫婚姻不使之六礼备,则礼教不行,夫妇之道阙,而淫僻之罪繁。不计少长以为之期,则过其盛壮之年,而失人伦之正。不许其杀礼,则所立之期不行,既杀礼而不限以时月,则男女之讼必生。[20]15
应该说《周礼·地官·媒氏》“仲春之月”这条材料的确不能支持仲春说。同时,《大戴礼记·夏小正》的“二月,绥多士女”与《周礼·地官·媒氏》的仲春会男女意思一致,都是因为“时已近夏,民间昏事渐杀,故令其及时成礼”[10]1044,乃是期尽之法。至于《夏小正》的某氏传所谓“冠子、取妇之时”,并不能解读为二月是冠礼和婚娶之正期,因为联系《士冠礼》的“屦,夏用葛”,“冬皮屦可也”[26]之文,显然冠礼不限常月,从而可知这里的“取妇之时”,不能理解为以二月为正期。针对王肃的驳难,郑玄后学马昭和晋代张融又起而为郑玄辩护,兹不赘述[27]1661。
针对上述涉及毛传郑笺之争和王肃郑玄之辩的秋冬说和仲春说,西晋束皙认为都不对,并在其《五经通论》中提出了调停之论,认为婚礼通于四时,“通年听婚,盖古之正礼”。其论据有以下几点:
春秋二百四十年,鲁女出嫁,夫人来归,大夫逆女,天王娶后,自正月至十二月,悉不以得时失时为褒贬,何限于仲春季秋以相非哉?
凡诗人之兴,取义繁广,或举譬类,或称所见,不必皆可以定时候也。又按《桃夭》篇叙美婚姻以时,盖谓盛壮之时,而非日月之时,故“灼灼其华”,喻以盛壮,非为嫁娶当用桃夭之月。其次章云“其叶蓁蓁”,“有其实,之子于归”,此岂在仲春之月乎?又《摽有梅》三章注曰“夏之向晚”“迨冰未泮”,正月以前。“草虫喓喓”,未秋之时。或言嫁娶,或美男女及时,然咏各异矣。
夫冠婚笄嫁,男女之节,冠以二十为限,而无春秋之期,笄以嫁而设,不以日月为断,何独嫁娶当系于时月乎?[27]1678-1679
束皙的理由是这样几点:第一,《春秋》对于毫末小事都有褒贬评价,婚姻是人伦之大者,若婚期限以秋冬或仲春,必然会有褒贬的春秋笔法。然而,自正月至十二月,《春秋》均有嫁娶事件记载,《春秋》三传却均不以得时、失时作褒贬评价。第二,《诗经》论及婚礼的诸多诗句,不足以作为判断婚期的凭据。因为“凡诗人之兴,取义繁广,或举譬连类,或称所见,不必皆可以定时候也”。第三,束氏也指出,《周礼·地官·媒氏》所谓仲春会男女,乃“非常人之节”。同时,冠笄之礼仅限以年龄,不限以月份,婚礼亦当如此。唐代杜佑在《通典》中认同束说,并补充和评价说:“婚姻之义,在于贤淑,四时通用,协于情礼,安可以秋冬之节,方为合好之期?先贤以时月为限,恐非至当,束氏之说,畅于礼矣。”[27]1679
束皙的通于四时之说,得到了清代学者孙诒让、戴震及现代学者黄焯的认可和回应,他们从社会阶层角度作进一步分析。如孙诒让认为,既然“《士昏礼》不著时月,则本无定时可知。荀卿所说始于季秋,杀于中春者,盖谓齐民之家,及时趋暇,大略如是,非必著为令也。”至于士以上的贵族阶层,则“无农事之限,则昏娶卜吉,通于四时,既非限于中春,亦不必在秋冬。”[10]1044戴震针对荀子“霜降逆女,冰泮杀止”的解释,与孙诒让相通。他说:“盖季秋之月,农事备收,婚嫁之礼渐举,至冰泮已盛行。仲春耕者少舍,犹得合男女之事,是时从容用礼者固多。”“自是而后,民急农事,婚嫁亦渐止矣。”[20]14-15孙诒让之论显得更为通达,使“通于四时”说与《春秋》三传不褒贬婚礼“得时”“失时”相协调,同时又可解释荀子、毛亨的秋冬古说。
然而,探究并没有止息,现代学者闻一多先生别出新解,提出了“古者本以春、秋为嫁娶之正时”的新论。他首先将“泮”训为“合”,将“迨冰未泮”解读为“归妻者宜及河冰未合以前”,乃是秋娶之证。同时,他考索《诗经》,认为婚期“春最多,秋次之,冬最少”。进而,闻一多先生作出了原因分析[28]:
初民根据其感应魔术原理,以为行夫妇之事,可以助五谷之蕃育,故嫁娶必于二月农事作始之时行之。郑注《周礼》所谓“顺天时”,《白虎通》所谓“天地交通,万物始生,阴阳交接之时”,皆其遗说也。次之,则初秋亦为一部分谷类下种之时,故嫁娶之事,亦或在秋日,然终不若春之盛。……迨夫民智渐开,始稍知适应实际需要移婚期以就秋后农隙之时。……降至战国末年,去古已远,观念大变,于是嫁娶正时,乃一反旧俗,而向之因农时以为正者,今则避农时之为正。
闻一多之说可谓发前人所未发,颇有见地。其关于初民巫术思维的论述,与乔治·弗雷泽的人类学名著《金枝》中所提到的案例相一致,乃是人类早期之关联式巫术思维的体现。从“有女怀春”等诗句审视《诗经》的文化意象,人类早期的男女结合应的确曾盛于春天。然而,这种文明早期初民的性的结合,是否可以看作体现为嫁娶的婚姻,应是存疑的。初民的“感应魔术原理”,至殷周以降作为礼俗的婚俗的形成,恐怕尚有很长的距离。不过,闻一多先生从民俗角度揭示出,男女结合或许经历过盛于春天的前礼仪时代,并遗存于《诗经》时代。
综上所论,“婚姻以时”的观念当然要落实到婚期亲迎时月上,但是,婚期更多的是基于习俗和礼俗,而非大传统礼制或诏令所规范的结果。这就与婚龄之时不同,由于初婚年龄事关人口生聚和蕃育,故政府多有诏令干涉,而婚期时月不影响生育,故不见诏令对婚期时月的规定和干预。总体来说,受居住环境和农事生产影响⑤,婚期在民间多是季秋至孟春,这应是荀子对周代民众嫁娶时月的实录,也在民间乡村社会沿袭至今。但不可僵化地理解婚礼之正期,不仅不排除有盛于春天的前礼仪时代,而且“冰泮杀止”是渐止之义,仲春是期尽之论,因此,至少春秋时代以降,春天也是可以嫁娶的。至于士以上的贵族,婚礼通于四时乃是常态,不涉及守礼还是违礼的问题。此外,需要指出,《春秋》所记婚姻事件,主要是士以上阶层,对于民间多行于秋冬,实则有所遮蔽,常被经学史学者所忽略。
三、婚姻失时与婚配救济
从上文关于婚龄之时和婚期之时的讨论中,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周秦以降,士以上的贵族阶层不存在婚姻“失时”和“逾时”的问题,不仅婚龄普遍早于庶民阶层,而且婚期也是通于四时,因而不存在婚配救济问题。所谓“旷男怨女”现象,乃是庶民阶层所特有的婚姻“失时”问题。正如陈顾远先生所指出的,由于庶民家庭财力问题或者遭遇灾乱等原因,“旷夫怨女现象之救济,又或礼之所穷,莫能为计”[21]15。也就是说,对于庶民阶层而言,婚姻“失时”现象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是婚姻常礼所难以规范的。因此,就需要因时制宜地制定“婚政”从而“辅礼并济其穷”。
旨在进行婚配救济的婚姻行政的设置,从《周礼》《管子》及后世行政诏令类文献中可见一斑⑥。如《周礼·地官》中的大司徒,负责“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在其所施行的“十二教”中,“三曰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郑玄注云:“阴礼谓男女之礼。昏姻以时则男不旷,女不怨。”[4]259也就是说,大司徒掌管男女婚姻之礼,旨在使民众乐于婚姻中之恩亲,从而使男女无失时之怨。大司徒所施教之理念中,首先强调婚姻救济和婚姻失时的预防,即要从婚姻伦理教育开始,从树立相“亲”开始,“不失时”何以可能?在于救济于未然之时。又如《周礼·地官》的“遂人”一职,其“治野”职责中有“以乐昏扰甿”一项。根据郑玄注,“乐”,劝也;“扰”,顺也;“甿”,民氓也;“乐昏”就是劝其婚姻。“遂人”注重劝成民氓之婚姻,以使之安居和顺。当然,前文已经提及,在《周礼》职官系统中,婚政的主管官司是“媒氏”。“媒氏,掌万民之判”,郑玄注:“判,半也。得耦为合,主合其半,成夫妇也。”[10]1033这里的“媒氏”不同于“谋合二姓”的民间媒妁,乃是负责年龄登记、结婚登记、婚姻管理和审判婚姻诉讼等“礼法政令”的。其重要职责之一便是婚配救济,所谓“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郑玄注:“司犹察也。无夫家,谓男女之鳏寡者。”[10]1046这里的“无夫家者”就是三十未娶、二十未嫁的大龄青年男女,“会之”就是“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之“会”,通过杀礼以促成其婚姻。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鳏寡”,和《王制》的“老而无妻者谓之矜,老而无夫者谓之寡”不同,古代将“凡男女过时未有室家及贫不能嫁娶者”[10]1046,亦称为鳏寡,如《尚书·尧典》的“有鳏在下,曰虞舜”,这里舜被称为“鳏”是因其“长而无妻”,而非“老而无妻”。此外,《管子·入国》中提到“凡国都皆有掌媒”,“掌媒”类似《周礼》的“媒氏”,其职责是通过“合独”促成鳏寡之婚姻结合。其文云:“丈夫无妻曰鳏,妇人无夫曰寡,取鳏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后事之,此之谓合独。”[29]这里的行政干涉意味更为强烈,要之,亦是一种婚配救济政策。
造成婚姻失时的原因有多种,但归根结底,往往表现在庶民财力不足上。无论是灾荒所致,还是其他原因,家境贫寒、生计维艰常常造成嫁娶拖延而“逾时”。因此,杀礼以促成婚配,是行政力量所努力的方向。所谓“仲春之月,令会男女”,就是让因财乏而“六礼”不备者,及时完婚;所谓“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就是一反“聘则为妻,奔则为妾”的常态要求,使“不备礼而嫁娶”者具有婚姻合法合礼性。在聘礼方面,《周礼·地官·媒氏》规定“凡嫁子娶妻,入币纯帛,无过五两”,这是旨在防止僭越奢侈的规定。后世如“汉代各帝屡次诏禁嫁娶之僭侈过制”[21]17。可以说是“媒氏”作为婚姻管理职官,在私媒之外,助力民间婚姻嫁娶。若遇灾荒,更以“多昏”的治理思维实施婚配救济。如《周礼·地官》的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其“十曰多昏”。郑玄注:“荒,凶年也。郑司农云:‘多昏,不备礼而娶,昏者多也。’”[4]259贾疏云:“昏礼有六,并有玄束帛。凶荒为昏,不可备行此礼,使有女之家得减口数,有男之家易得其妻,故娶昏者多也。”[4]260又如《卫风·有狐》毛诗序云:“古者国有凶荒,则减杀其礼,随时而多昏,会男女之无夫家者,使为夫妇,所以蕃育人民。”[2]245总之,灾荒乃非常之岁,民众更加困顿,此时杀礼即不拘常礼,更易于男婚女嫁,从而希望避免旷怨的发生。
作为儒家经典文本,《周礼·地官》中关于婚配救济的记述,不仅对《管子》,而且对历代行政诏令也产生了切实的影响。兹举一例,据《唐会要》卷八十三,唐贞观元年(627年),中央政府诏令地方州县官员负起婚配救济之责任。唐太宗诏令云:
宜令有司,所在劝勉,其庶人男女无室家者,并仰州县官人,以礼聘娶,皆任其同类相求,不得抑取。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妻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婚媾,令其好合。若贫窭之徒,将迎匮乏,仰于亲近乡里,富有之家,裒多益寡,使得资送。其鳏夫年六十,及寡妇年五十已上,及妇虽尚少,而有男女,及守志贞洁,并任其情,无劳抑以嫁娶。[30]
诏令首先强调“州县官人”要利用行政权力“申以婚媾”,推动“庶人”婚配。这里包括达到婚姻年龄者和丧偶但已经除丧者。如果因为贫困而“失时”,则号召亲戚邻里相互资助。但是,对于六十以上鳏夫和五十以上寡妇,及虽年尚少之妇而不愿再嫁者,则应“任其情”,尊重其意愿,不可强迫。这就和《管子》“合独”之强烈干涉性有所不同。此外,明代也屡次“诏以互助之法,使民嫁娶”[23]26。
综上所论可见,受婚姻之“六礼”仪程的约束和影响,以及民间财力之限制,往往造成庶民阶层不自然的婚姻“失时”。政府通过诏令对民间嫁娶加以规范、引导和帮助,有助于解决婚姻“逾时”问题。在今天人口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和日益城市化的现代社会中,如何创建更有效的适龄婚育政策,以使适龄青年得以及时婚配,政府需要思考并积极作为。儒家关于“婚姻以时”的婚姻伦理观念及历代关于婚配救济的理念与实践,对当下构建新型婚育文化和打造生育责任伦理共同体,有重要借鉴意义。
注释
①唐代杜佑《通典》卷五十九设“男女婚嫁年几议”和“嫁娶时月议”条,清代秦蕙田《五礼通考》卷一百五十一设“昏年”和“昏时”两条,对历代争议有梳理与分析。清代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二十六在对《周礼·地官·媒氏》疏解时,亦有详论。现代学者吕思勉先生撰《昏年考》亦有综论,参见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76-278 页。②陈鹏先生说:“适婚年龄,始载于经,继入于令”,“而历朝诏令,多等具文,民间习俗,各行所是,盖三者不相侔久矣。”参见陈鹏:《中国婚姻史稿》,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81页。③晋范宁注《春秋穀梁传》曰:“娶必先冠,以夫妇之道,王教之本,不可以童子之道治之。”对于国君而言,冠礼举行颇早,乃是考虑到“欲人君之早有继体”。④参见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480页。王引之认为,“杀止”今本作“杀内”,乃后人误改。⑤吕思勉认为:“古人冬则居邑,夏则居野,结婚的月份,实在是和其聚居的时期相应的。”参见吕思勉:《中国文化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19年版,第19 页。⑥关于婚姻行政的设置,笔者赞同陈顾远先生之见,即“《周礼》虽不必为周公佐周之设制,《管子》所述虽不必为管仲治齐之政策,而亦必谓战国或汉初之学者,认为社会有此需要,而应为之施设”。参见陈顾远:《中国婚姻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