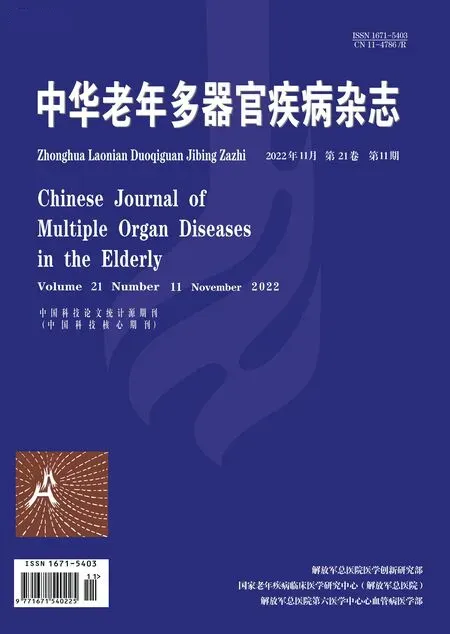晚期癌症患者痛苦体验:一项丧失与疏离死亡相关的质性研究
徐雯菁,许湘华,谌永毅,王英,卜晓繁,刘翔宇*
(1中南大学湘雅护理学院,长沙 410006;湖南省肿瘤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2健康服务中心,3护理部,4姑息疼痛病房,长沙 410031;5香港理工大学护理学院,香港 999077)
全球癌症死亡病例呈快速增长趋势,我国癌症死亡病例300.3万例,占全球癌症死亡30.2%[1],居全球首位,癌症已成为我国居民的首要死因[2]。晚期癌症患者是指无法根治且抗癌治疗不再获益,且处于多种不适症状并持续病情恶化中的恶性肿瘤患者[3]。因感知死亡威胁,不仅承受躯体上的折磨,加之经济负担重[4]以及各种未能满足的社会支持需求[5],更多的是无法摆脱焦虑、恐惧、无助、绝望等心理痛苦[6],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7],甚至出现加速死亡的意愿,增加自杀风险[8]。痛苦是晚期癌症患者最常见、且持续的生命体验[9],目前我国关于晚期癌症患者的痛苦研究主要从医护人员视角出发,使用相关量表进行结构化测评[10,11],无法从晚期癌症患者的角度发掘其对痛苦认知、情感及行为感知与体验。因此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中的描述性现象学的研究方法,对晚期癌症患者进行深度访谈,深入了解其痛苦的体验,旨在为制定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依据,现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2022年4月至6月湖南省某三级肿瘤专科医院安宁疗护病房的晚期癌症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肿瘤淋巴结转移分期(tumor node metastasis,TNM)分期为Ⅲ期或Ⅳ期;(2)年龄≥18岁;(3)患者知晓疾病诊断及病情状况;(4)具有正常沟通交流能力。排除标准:(1)存在心力衰竭、呼吸困难等情况无法耐受访谈;(2)伴有精神或认知障碍。采用最大差异抽样,选取人口学资料、疾病特征差异较大的患者纳入研究。样本量以资料分析不再出现新主题为样本量饱和[12]。
1.2 方法
1.2.1 确定访谈提纲 根据研究目的及文献回顾,通过专家小组讨论修改,对2例晚期癌症患者进行预访谈,根据预访谈结果进一步修订访谈提纲,形成访谈提纲终稿,具体内容如下:(1)您能谈谈您的患病经历和感受吗?(2)您在患病后有哪些困难和问题?(3)回顾整个患病和治疗过程,您认为疾病给您带来了哪些痛苦?(4)患病后您是如何看待自己的?(5)患病后您与周围人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6)您未来的计划有哪些变化?(7)患病后您是如何看待生命意义与死亡的?
1.2.2 资料收集 访谈过程中全程录音,观察受访者非语言行为,并做好备忘录。访谈全程按照访谈提纲为指导提问,全程无引导,鼓励访谈对象表达真实感受,每次访谈时间为32~60 min。每次访谈结束后24 h内将录音转录为文本,采用Colaizzi 7步资料分析法分析资料[13]:(1)反复阅读访谈资料;(2)提取与痛苦体验有意义的陈述;(3)对反复出现的陈述进行编码形成概念;(4)根据共同的概念,聚类形成不同的主题及主题群;(5)对主题进行详尽的叙述;(6)反复辨析类似的主题,陈述构成该现象的本质性结构;(7)将最终主题返还访谈对象求证。
1.2.3 质量控制 研究前,研究者将自己对晚期癌症患者痛苦的既有认知进行“悬置”,以尽量开放的状态收集资料,论文撰写严格遵循国际质性研究报告规范(standards for reporting qualitative research,SRQR)[14]。
1.2.4 伦理考虑 本研究已获得中南大学湘雅护理学院伦理审查委员会批准(编号:202211)。为保护受访者隐私,研究结果均采用匿名方式呈现。为最大程度维护受访者心理状态,对于痛苦感受较为强烈的患者,研究者将其转介至心理咨询师,接受免费心理辅导。
2 结 果
2.1 患者一般资料情况
最终纳入研究对象15例,编号为P1~P15,其中男性6例,女性9例;年龄32~70(50.60±13.04)岁;病程10~85个月,中位数18.00(14.00,50.00)个月。肿瘤类型:肺癌8例,乳腺癌2例,宫颈癌1例,胆管癌1例,肾恶性肿瘤1例,鼻咽癌1例,结肠癌1例。
2.2 丧失相关痛苦
2.2.1 自我完整性丧失 受访者因手术肿瘤切除导致身体部位的残缺,抗肿瘤治疗毒副作用导致躯体形象的改变、身体机能衰退影响其对自我形象的认知,无法接纳自身完整性的丧失。P4:“我这里切掉了(指着胸部),总觉得自己少了点啥,平常也不敢照镜子,自己都嫌弃自己的身体(停顿,低头看地面)。”
2.2.2 自我尊严感丧失 伴随着身体的持续性衰弱,受访者自我独立性、自我控制感、自主权与决策权逐渐丧失,甚至遭受他人的歧视及不公平对待,感到自卑和羞耻。P10:“我回村里,一出门,村里有些人像躲瘟神一样,好像害怕被我传染一样,那个时候其实我挺自卑的。”
2.2.3 自我价值感丧失 受访者因无法履行家庭、社会责任,价值感丧失,出现自我否定及自我贬低,感到消沉、懊恼、沮丧、挫败及悲伤。P13:“你就说得了这个病,谁还会找你去他那儿上班,不上班,我就一分钱没有,我还有什么用处,现在靠低保支持不住了。”
2.2.4 生命意义丧失 面对病痛的折磨和未来不确定性时,部分受访者表示,患病后生活缺乏目标,求生意志低,感知生命意义丧失,感到悲伤、绝望与无助。P5:“我不知道我生活下去的目标在哪里,得了这个病后我的生活被完全打乱了,我再也不用为以后打算了,我对生命不再渴望了,我随时都可以死,我现在活下去,都只是为了家属不那么难受(叹气)。”
2.3 疏离相关痛苦
2.3.1 社会关系疏远 一些受访者不断出现的症状与不适困扰、活动耐力持续下降,躯体功能受限,活动空间局限于医院和家庭,无法与外界沟通和联系,患者孤独感倍增。P10:“生病后也不愿意听朋友们提及癌症、化疗,或者询问我的病情,所以干脆就把自己关在家里,不出门了,白天一人在家就爱胡思乱想,越想越郁闷。”
2.3.2 情感联结疏离 公众认为癌症具有传染性,代表“死亡”,是不吉利的、晦气的,部分受访者表示感到亲友的回避与区别对待,无法获得情感支持,感到和周围人情感疏离。P9:“我生病以后再也没和我老公一张床睡过,也不能说嫌弃,只是我这个病(宫颈癌),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忌讳,久而久之我和他话也变少了。”
2.4 死亡相关痛苦
2.4.1 想到死亡充满恐惧 随着生理状态越来越逼近死亡,部分受访者表示自身存在感逐渐消失,随之对死亡威胁产生恐惧,主要表现为恐惧死期将至、畏惧濒死过程、惧怕死后之事。P4:“我有时候痛起来就会想,我死的时候会不会也这么痛苦啊(哽咽),我不希望我走的时候什么胃管、尿管全插在我身上,全身沾满屎尿,痛的死去活来的。”
2.4.2 面对死亡焦虑不安 随着疾病的持续进展,一些受访者对即将到来的死亡感到焦虑,对与亲人的分离感到忧虑,对与美好生活诀别感到不舍,对尚未完成的心愿感到遗憾。P4:“想着我要是走了,再也不能和我儿子、父母一起了,我儿子、父母以后谁来照顾,他们过的开不开心我也顾不上了(流眼泪)。”
2.4.3 期待死亡结束痛苦 受访者在癌症晚期多种痛苦症状和躯体不适的折磨下,生存意志日渐消磨,希望可以通过死亡从痛苦中得到解脱,出现“求死”的念头。P9:“我以前当兵的时候什么苦没吃过,但是现在把我弄得痛不欲生,生不如死,太难熬了,我恨不得能让他们(医师)给我一针就这么过去就好。”
3 讨 论
注重晚期癌症患者丧失相关痛苦,鼓励重拾尊严与生命意义。本研究中,晚期癌症患者因身体意象紊乱、自我独立性、自我控制感、自主权与决策逐渐以及角色功能的丧失,对其自我完整性、自我尊严感及自我价值感构成威胁,出现生命无意义感,与Ellis等[15]质性研究结果相似。自尊是人们对生命意义和自我价值感的体会,生命意义能显著影响自尊[16]。积极寻找生命意义,能使患者身心稳定平和,有尊严地面对死亡,达到善终[17]。因此,医务人员可采用生命回顾、尊严疗法、意义中心疗法、叙事疗法等心理干预方法[18],帮助患者构建和寻找人生意义,回忆过去成就与荣誉,鼓励其重拾尊严与生命价值。同时,协助患者制定预立医疗照护计划,让其在了解自己的病情和预后的基础上,主动选择生命终末期的治疗护理意愿,并且对自己临终阶段的事情做出安排,让患者有尊严的逝去。
关注晚期癌症患者疏远相关痛苦,增进关系圆融与情感联结。本研究结果中,晚期癌症患者由于遭受亲人、朋友的疏远与排斥,情感联结受到被动阻隔,或自身不愿与外界接触,主动封闭情感联结,感知到孤独无助,引发痛苦体验,与Best等[19]研究结果一致。因此,这提示医护人员可搭建丰富深刻的关系性联结以纾解患者痛苦体验,通过共情陪伴与耐心倾听[20],了解其内心感受与照护需求,与其共同直面痛苦和死亡。同时,医护人员应鼓励家属陪伴患者,协助其提供适当的照护,从而让患者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享受亲情的温暖。本研究访谈处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常态化管理期间,由于防控政策的实施,病房实施封闭式管理和严格限制的陪护制度[21],医院拒绝探视,导致患者与外界隔离,客观上造成社会关系的疏离,情感联结需求得不到满足[22]。为了弥补晚期癌症患者因活动空间隔离而缺失的情感慰藉,医务人员可借助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通过电话、视频以及虚拟现实技术提供沉浸式体验,从而突破时间和地域的限制,帮助患者达成心愿,与家属及朋友道歉、道谢、道爱、道别,以实现关系圆融与情感的联结,使患者与家属生死两相安。
正视晚期癌症患者死亡相关痛苦,引导坦然面对与接纳死亡。本研究结果显示,大部分晚期癌症患者都经历了因恐惧死亡而产生焦虑与痛苦的体验,主要表现:恐惧死期将至、畏惧濒死过程、惧怕死后之事,焦虑死亡的不确定性、与亲人的分离、与美好生活诀别以及尚未完成的心愿等方面,影响患者的身心状态和抗癌信心,总体生活质量下降,与Vehling等[23]的研究结果相似。主要原因如下:一方面晚期癌症患者经历综合抗癌治疗后效果不佳,同时长时间饱受多种痛苦症状和躯体不适的折磨,感知到死亡的必然性与不确定性[24];而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中的“好生恶死”的观念,对死亡采取消极、逃避的态度,使患者与家属、医务人员之间针对临终治疗与死亡无法进行有效沟通,从而进一步加剧患者死亡相关痛苦,这与杨丽华等[25]的研究结果相似。由此可见,医护人员应最大可能地控制患者的痛苦症状,帮助其疏导负性情绪,给予精神和心理支持。另外,应鼓励患者充分表达对于死亡的担忧与顾虑,探寻死亡相关痛苦的根源,根据评估有针对性的开展适用于患者的个性化死亡教育方式,引导其坦然面对与接纳死亡,缓解其死亡焦虑和恐惧,走好人生最后的一段旅程[26]。
综上,本研究采用描述性现象学研究方法,对15例晚期癌症患者痛苦体验进行分析,归纳出丧失相关痛苦、疏远相关痛苦及死亡相关痛苦3个主题。医务人员应基于其痛苦体验的特点,以及其背后所蕴含的照护需求,尊重生命规律、遵循生命意愿、维护生命尊严、提高生命质量,让晚期癌症患者得到有温暖、有关爱、无痛苦、无遗憾支持性照护。然而,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仅在湖南省一家肿瘤专科医院收集访谈资料,有可能降低研究样本的代表性和研究结果的可推广性,未来可以扩大样本选择的范围,对社区医院、医养结合机构以及居家的晚期癌症患者进行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