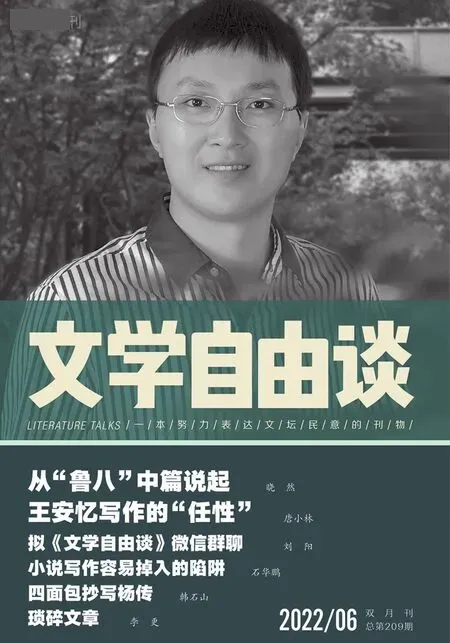钱谷融先生仙逝五周年祭
□钱 虹
今年9月28日,是著名文艺理论家钱谷融先生(1919-2017)逝世五周年的日子。凑巧的是,这一天也是他的生日,并且,万世师表孔老夫子的诞辰,也是这一天。
五年前的这一天,正如钱先生的公子钱震来在悼辞中所说,“很多领导、他的弟子和朋友都陆续来了(医院——笔者注),在大家的祝福中,他很开心地和大家一起切蛋糕,幸福之情溢于言表,尽管他话不多,但他总是以笑容向每个来看望他的人示意,表示感谢。傍晚时分,父亲示意我们拉上窗帘,需要小憩一会儿,然后便沉沉睡去。也许父亲是真的累了,这一觉睡得显然是长了点,但他睡得很安稳,我们都不忍再去打扰他。”在开心地度过了他的九十九岁寿辰后,钱先生在睡梦中驾鹤西行,安详地离开了这个让他欢喜让他忧愁的世界。
噩耗传来,几乎无法置信。就在不到半年前的清明节,应浙江省临安市人民政协邀请,我陪同钱先生去拜谒位于临安的钱王陵。他净手上香,三叩九拜,行了钱氏后裔的祭祖大礼。事后年近百岁的钱先生十分高兴,对我说:“你陪我到临安祭祖,终于完成了我给祖宗磕头跪拜的一桩夙愿。”同年6月,在中央电视台《朗读者》节目里见到他,老人家正抑扬顿挫地朗读着鲁迅先生的《生命的路》:“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自然赋予人们的不调和还很多,人们自己萎缩堕落的也还很多,然而生命决不因此回头……”朗读时,钱先生精神饱满,情感洋溢,完全看不出他已年近百岁。那一集《朗读者》的主题词是:“青春”。8月6日,我奉艺术家钱大统先生之命,将他专门从景德镇为钱先生烧制的大幅先生头像瓷版画送至钱老府上,他高兴地开怀大笑。我受上海钱镠文化研究会钱成锡会长之托,请他老人家为温州钱氏祠堂题写匾额。我展开曹友泉宣纸,为钱先生研墨,他提笔饱蘸浓墨,挥毫写下“钱氏宗祠”几个苍劲有力的大字,一口气写了三幅,一边照例摇头说:“我的字不上台面的,你们挑一下,看哪张可派用场。”音容笑貌,宛在眼前。谁知仅一个多月后,他竟在其生辰日这天乘鹤西去,每念及此,怎不让人潸然泪下?
“文学是人学”
钱谷融先生是我的研究生导师。我原是“高考”恢复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首届本科生。当年,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有好几位“国宝级”大师:施蛰存、许杰、徐中玉、钱谷融、徐震锷等。在中文系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对老一辈教授都敬称“先生”,如施先生、许先生、徐先生、钱先生等等,而年轻一些的都称某某老师。读本科期间,我曾聆听过钱先生关于《雷雨》中的人物分析以及文学之魅力的精彩讲座,大二时还曾选修过他和徐中玉教授合开的“文艺学专题”选修课。1979年我第一篇发表在《上海文学》名为《对小说〈阴影〉的一点意见》的评论,也是为交这门课的期中作业而写,受到徐中玉先生的鼓励后大胆投稿得以发表的。但当时并不太了解钱先生的性格和学问。
本科毕业留校之后,我之所以考入这位“文论泰斗”门下,完全是一个偶然的机遇,至今我都深感幸运。那时他已年过花甲,但精神矍铄。1983级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钱先生只招了我一个。先生给我上的第一堂课是:“文学是人学”。他说,文学是人写的,文学也是写人的,文学又是写给人看的,因此,研究文学必须首先学做人,做一个文品高尚、人品磊落的人,这是人的立身之本。先生严肃地指出,他喜欢踏踏实实做学问的老实人,讨厌东钻西营搞关系的投机家,对自己的学生更是如此要求。他语重心长地说,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要把主要的精力最大限度地放在做学问上,而不要放在人际关系的斡旋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品比文品更要紧,人格比才学更宝贵。他的话给我这个无意中撞入钱先生门下、懵里懵懂的学生以很大的心灵震动。
在跟着先生学做人的同时,也跟着先生学做学问。先生不光考察研究生慧眼独具,如考试科目中必考“作文”一科且由他亲自批阅外,他指导研究生的方法也很特别。他并不像如今一些导师给研究生上课也如本科生一样从头至尾地满堂灌,也并不指定我们非得啃许多佶屈聱牙、深奥难懂的理论书籍,他只是反复强调两条治学经验:一是尽量多读、精读古今中外第一流的文学名著,只有多读好作品,才能真正懂得什么是文学,“读书,一定要读好书。”二是要多写、多做读书札记,不必宏篇大论,但必须确是自己的心得和体会,不要重复别人的话,“写文章,一定要有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他尤其反感有的研究生论文写得像“新名词爆炸”、让人不知其所云如坠云里雾里的“天书”,他说:文学论文本身要具有可读性,堆砌一个个自己都没搞明白的“理论术语”,让人看都看不下去,这种文章离文学本身的特性就很遥远。至于研究生具体读哪几本书,写什么内容的文章,用怎样的方法表述,那完全由自己决定,钱先生从不强求学生按照他的思维方式做学问。他鼓励我们尽量开拓视野,广泛涉猎中外文学名著。他说,你没读过托尔斯泰、曹雪芹等一流作家的作品,你就不会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文学。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相通的,是可以超越国界的。所以,我那时就选修了王智量老师开设的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研究”和倪蕊琴老师开设的“托尔斯泰研究”,这两门课的作业后来都作为论文发表了,尤其是写托尔斯泰“心灵辩证法”的那篇文章还受到先生的赞许和推荐,使我至今铭记在心。
“我相信我的观点没有错”
说起“文论泰斗”,不能不提到钱先生那篇著名论文《论“文学是人学”》。这篇后来被誉为“具有学术界公认的创新性、又能产生重大社会影响和在理论上取得重大突破的理论成果”的文章写于1957年。起先,论文的题目叫做《文学是人学》,是当时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的许杰教授让他加上一个“论”字,说这样有个挡箭牌。5月,《论“文学是人学”》在《文艺月报》(《上海文学》的前身)上发表。可是没过多久,他就受到了全国范围内口诛笔伐的批判。他说,自己是从季莫费耶夫的《文学原理》上得知著名作家高尔基有把文学当做“人学”的意思,觉得讲得很对,所以写了这篇论文。
钱先生的意思在论文一开始就交代得很清楚:“高尔基曾经做过这样的建议:把文学叫做‘人学’。我们在说明文学必须以人为描写的中心,必须创造出生动的典型形象时,也常常引用高尔基的这一意见。但我们的理解也就到此为止,——只知道逗留在强调写人的重要一点上,再也不能向前多走一步。其实,这句话的含义是极为深广的。我们简直可以把它当做理解一切文学问题的总钥匙,谁要想深入文学的堂奥,不管他是创作家也好,理论家也好,就非得掌握这把钥匙不可。”在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界,钱先生是掌握并且从来也没放开这把“理解一切文学问题的总钥匙”的第一人。论文发表时钱先生年届三十九岁。对于当时劈头盖脸的粗暴批判,甚至已有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针对《论“文学是人学”》的批判集,还标明是“第一辑”,意思是还有后续。钱先生后来说自己“木知木觉”:“我已经被学校内定为右派,不过真的感谢当时文化部的一位领导,他说‘这可以作为学术问题讨论’,因此,我还不算右派。”
多年挨批判、归入“另册”的人生代价当然是沉痛的,甚至有过“撕肝裂肺的痛苦”:做了三十八年讲师,期间四次十二指肠溃疡和胃大出血,很长时间不能写作、发表文章,甚至一度还被剥夺了上讲台的资格和权利,在那个荒诞的十年岁月中更是受到肉体和精神的迫害。可是钱先生对我说,他至今从来没后悔过。他说:“因为我相信我的观点没有错”,“到现在我还认为,(我的)每篇文章都没有错,我没有说过后悔的话。”半个世纪之后,九十一岁高龄的钱先生因这篇论文荣获华东师范大学唯一一篇论文原创奖。之所以在众多评选论文中脱颖而出,评委之一的葛剑雄教授的话说得很在理:“钱谷融先生提出‘文学是人学’的观点,到现在已经有半个世纪了。半个世纪的考验,充分证明了他提出的理论具有正确性和预见性。这是经过实践和历史考验的一项具有原创意义的成果。”据云南学者马旷源先生考证,高尔基并没有明确说过“文学是人学”,这句话的发明权其实是钱先生的。用钱先生当年在《论“文学是人学”》中的原话说,“这句话也不是高尔基一个人的新发明,过去许许多多的哲人,许许多多的文学大师都曾表示过类似的意见。而过去所有杰出的文学作品,也都充分证明着这一意见的正确。”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发展,尤其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数十年的各种实践和成绩,充分论证了钱谷融先生提出《论“文学是人学”》的理论的正确性和前瞻性。
记得有一次曾跟钱先生谈起一个人如何不改初心、坚持自我的问题。他说到了自己,“我想我这辈子很多时间是与时代潮流擦肩而过的,不是说我有什么先见之明,而是很长时间我被打入另册,做了三十八年讲师,环境逼迫着我接受这样的生活状态。最初遭排斥,错过了宝贵的机会,会有一点懊恼,甚至内心痛苦。但每次都错过,就像赶车一样,你知道反正赶不上,那就不赶了,慢慢走,慢慢看,看多了,自己也会有一点人生感悟,尤其是与周围那些永远唱高调的人物论调相对照,我慢慢明白了一点道理。世界很大,只要自己用心去做一件事,没有做不成的。很多人生的道理,都是慢慢体会出来的,积少成多,时间久了,会有一个质的变化。”
2014年12月,九十六岁高龄的钱谷融先生荣获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
文学如人,有品第之分
我考上钱先生的研究生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很少听到他提起《论“文学是人学”》的理论。但他的这一理论却潜移默化地贯穿在他的言行举止和教学实践中。在攻读硕士学位的三年中,每两周去他家上一次专业课,聆听导师的教诲。渐渐地,我不再拘谨。师生二人,就像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样,相向而坐,畅所欲言,谈文论艺。这样自然轻松而又充实愉悦的授课方式,我在许多年后回想起来,都是十分珍贵的求学记忆和终身受益的精神财富。他强调说,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学问应当渊博,眼界需要宽广,研究现代文学的,也要懂文艺理论、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古今中外的优秀作品都应该有所涉猎,千万不要自我封闭,只关注某一学科的狭窄空间。钱先生非常重视一个人的学(学问)、才(才气)、识(识见)。他说,最不容易的是识见,它既是一种眼光,更是一种胆识。
我至今都无法忘怀的是,有一次课间,先生问我近来读了哪些作品,于是我提到了小说《烟壶》,说它很吸引人,言辞中大加赞赏。当时他没看过这篇作品,事后特地找来看了,并约我去他家,坦率地跟我交换了自己的意见。他说,《烟壶》确是一篇非常出色的京味小说,犹如一幅满清末年的京华风俗画,应该列入能够流传下去的作品之一。但是,如果按照古人钟嵘把诗歌分成上、中、下三个品第的话,那么,像《烟壶》这样的作品还够不上文学中的上品。接着他举了另一篇小说《驼峰上的爱》加以比较。他说,论作者的艺术功力,前者在后者之上;论作品的情节、结构、文字,《驼峰上的爱》比之《烟壶》也稍逊一筹,然而读《烟壶》时并没有触动我的心灵;而《驼峰上的爱》所描写的母骆驮阿赛与小女孩塔娜之间那纯朴而真挚的超乎物种之间的爱,却让人深深地动情。真正优秀的好作品,首先应该具有动人心弦的艺术力量。他说,“外国作家中我偏爱简·奥斯汀和托尔斯泰。”他认为,比起十八、十九世纪甚至是中国古代的文学经典作品来,二十世纪以后的现当代小说“多了理性”而“少了情致”。文学本身主要是通过移情、审美来感染人,教化人的,如果不能使人感动,让人动情,文学的技巧、叙事的手法再高明再完美,也算不上是一流的佳作。
这一文艺观点,钱先生坚持了一生,他认为一个真正的作家,思想的力量与感情的力量应该融为一体。他去世之前,针对当时一些文艺作品“技巧高明却少有情致”的情形,他说,“我觉得文学作品应该富有情致和诗意,使人感到美,能够激起人们的某种憧憬和向往。使我遗憾的是,最近一百年来,……作家们的思想和技巧虽然日新月异,时显奇彩,可是在他们的作品中却少有丰厚的情致和浓郁的诗意。那令人憧憬、惹人向往,永远使人类灵魂无限渴望的美,则更是日见其杳如了。”“今天的有些作家似乎理智远胜于感情,好像更多的是在用头脑而不是用整个心灵写作,思想力量大于感情力量。而后者恰恰是我以为文学所迷人的地方。”
魏晋风骨,散淡人生
钱谷融先生一生酷爱读书。他去世前一年的11月2日,我去先生家拜访。走到他住的那间卧室兼会客室门口,令我不无讶异的是,年近百岁的钱先生戴着老花镜,端坐在一张靠背椅上,手上拿着一本淡紫色封面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正在阅读。先生一生所涉猎的书很广泛,文学类的书,除了他喜爱的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英文原版一直保留外,钱先生最喜欢读的书要数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这本书的各种笺注本钱先生都有,但他认为余嘉锡的版本最好。《世说新语》又名《世语》,主要记录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言清谈,是一部记录魏晋风流人物的故事集,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笔记小说”的代表作。钱先生曾充满诗意地这样评论它:“《世说新语》里所记载的谈吐,那种清亮英发之音,那种抑扬顿挫之致,再加之以手里麈拂的挥飞,简直如同欣赏一出美妙的诗剧,怎不给人以飘逸之感,怎不令人悠然神往呢?”
钱先生一生崇尚魏晋风骨,一向不事权贵,淡泊名利。许多人都把他为人处事的态度说是“散淡”,钱先生也不否认,还把自己的第一本散文集取名为《散淡人生》。他曾在《〈艺术·真诚·人〉后记》中坦言:“在现实生活里,我最不喜欢的是拘束,最厌恶的是虚伪。我爱好自由,崇尚坦率,最向往于古代高人逸士那种风光霁月、独往独来的胸襟与气度。名、利我并不是不要,但如果它拘束了我的自由,要我隐藏了一部分真性情,要我花很大的气力才能获得,那我就宁可不要。我决不愿斤斤于烦琐委屑的小事,我的情趣常逗留在一些美妙的形相上。”钱先生就是这样坦坦荡荡、虚怀若谷地生活了一辈子,这是常人难以做到和企及的。
他生前每出新著,总会认真地题了字赠我一本,如《文学的魅力》《艺术·真诚·人》《中国当代大学者对话录·钱谷融卷》《散淡人生》等等。其中他最珍爱的,正是这本散文集《散淡人生》,它向读者展示了先生在学术著述之外的另一种真性情,另一面“自我”的真实画像。钱先生在这本书的《序》中对此书的出版表示了格外的欣喜,他说:“我感到莫大的欢喜。这样的欢喜,是过去从未有过的。即使是第一次看到自己写的东西所感到的那种欢喜,也不能与此相比。其原因主要就是因为这里面真切地记录了我早年的心路历程。”该书首次收入了先生当年在重庆中央大学求学时的一些少作。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曾亲眼见过这些因年代久远而泛黄变脆的少作底稿上,有的还清晰地留存着钱先生的恩师伍叔傥先生当年的亲笔遗墨,所以弥足珍贵,先生也格外珍视。
这本散文结集最大的艺术特点,我以为也正是体现了先生不论做人还是为文都一贯主张的“真切”二字:抒真情,说真话,道真理,求真趣。无论是少作中的抒情摹景、谈文论艺,还是近作中的怀人忆旧、作序言志,皆贯穿着始终如一对“真善美”的事物的崇尚与追求。所以,要了解钱谷融先生的世界观、人生观、文艺观以及处世哲学的话,最好还是读读他的《散淡人生》,它将先生参悟“宁静以致远,淡泊以明志”的人生真谛,表达得再清楚不过了。而要了解先生是怎样睿智达观地知人论世、待人接物的,那就更应该读读这本书中的《我的老师伍叔傥先生》《哭王瑶先生》《悼唐弢先生》《曹禺先生追思》《关于戴厚英》《谈王元化》等篇,这些散文并非只是简单地记叙先生与他们的交往,而是写出了先生对这些故人至交的真情实感,既有相知相惜的深厚情谊,又有君子之交的善解人意,读来真是感人至深。
《散淡人生》,其实是真诚坦然地充实人生,宽厚温良地善待人生,从容舒缓地面对人生,宁静恬淡地回味人生。而人生的滋味,尽在其中的“散淡”二字上。我以为这正是钱谷融先生近百年来生命与生活的真实写照,正如钱震来先生谈到自己与父亲的根本区别在于:“鲁迅曾这样评价俄罗斯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氏对人的灵魂的剖析是如此深刻,他不但要从善的表象中拷问出人性之恶来,他还要再从这恶的背后拷问出善来。我想我只是自鸣得意地看到了笑脸后面的人性之恶,而我父亲则再进一步在恶后面看到了善。所以他活得比我平静,洒脱,快乐。他虽然对别人的欺骗,出卖,恶意,心知肚明,但他能理解,宽容,不求全责备,不斤斤计较。他深知人性之脆弱与无常,包括自己在内谁都不是圣人。”
以此,为恩师钱谷融先生仙逝五周年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