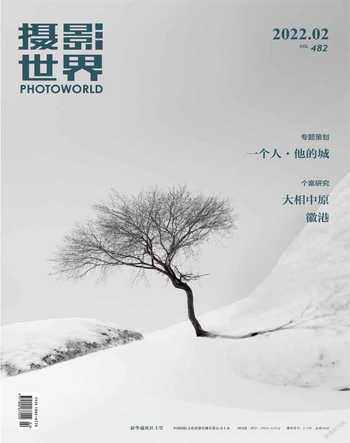藏在时间里的人
曾泽鲲

1990年,第一海水浴场。吴正中 摄
吴正中现在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每天拎着相机走街串巷,就像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刚拿起相机一样。有些东西变了,有些东西未曾改变。他将自己的生活过得尽量单纯,正如他这个人一样。他仿佛使出全身力气堵住与世界交流的通道,只留下摄影。他追求纯粹的专注,专注影像的每一个细节。
对吴正中来说,摄影是“无碍”的。他从不把自己固定在某个影像风格,也从不刻意地去改变什么,一切都仿佛是自然形成。从最早获奖的沙龙风格的作品《工地序曲》到长期实践的纪实类影像《小本买卖》《波螺油子路》《崂山大院》《老青岛》,再到肖像类作品《面具》,相机背后的吴正中,用摄影家袁东平的话说“如入无人之境”。他在南方创作的影像专题作品《候鸟》和《大沥人家》足以证明,在他眼里已经没有地域差别,真佛只说家常话。直至六十七岁完成的专题作品《老屋余温》,吴正中的影像从“三十而立”,走到了“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常言“摄影是时间的艺术”,拿起相机的吴正中便藏在了时间里,他毫不关心自己的照片是否有价值,他把一切交给时间,笃定时间会成就这些照片。他需要的是回到内心,将自己对现实生活的态度和个人立场尽情表达于其中,构建一个影像的桃花源,企图把我们这些凡夫俗子都装进去。那里面没有冷漠,没有愤怒,只有市井平民世俗生活的煙火气,生机勃勃。
1981年,27岁的吴正中从部队复员,回到青岛第九橡胶厂(双星集团),在工会宣传处工作。机缘巧合,他拿起了相机。除了满足单位宣传类工作需要之外,他更愿意将镜头对准胶鞋流水线最艰苦的“炭黑工”,拍摄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故事。这一时期的摄影师吴正中在影像控制方面已经显现出了高超的天赋,特别是营造事物在画面当中的瞬间关系方面,吴正中深受布列松有关符号构成关系理论的影响,并在他自己的持续实践过程中,逐渐成为一种对摄影语言的认知和自觉。
1985年-1988年,吴正中的摄影作品接连获奖。《工地序曲》获山东化工行业职工摄影比赛一等奖;《母女情》获中国日本联合举办《劳动与生活》摄影展金奖;《龙的传人》获得华东六省市摄影比赛一等奖。彼时的国人享受着改革开放的初期红利,渐有丰富多样的精神追求。不少人摆弄起了相机,摄影行业也出现了大量以沙龙美学为标准的比赛。对于从小画画,早年在部队参加过美展,并在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浙江美术学院进修学习过的吴正中来说,不论是用集锦摄影方法制作版画效果,还是在海滩上捕捉温情浪漫的画面,参与这样的摄影赛事并获得各种奖项,吴正中已经可以驾轻就熟,俨然成为个中高手。
正当我们以为吴正中会继续在沙龙比赛中披荆斩棘屡获殊荣时,他却停止了对沙龙美学趣味的追求,开始转向了纪实摄影的实践。
《海滩情》是吴正中从沙龙摄影向纪实摄影的过渡之作。他完成了两个转变:第一,在拍摄青岛东部海域石老人海滩的日出数月后,吴正中放弃了单一审美向度的风光摄影,重新把镜头对准了人。第二,不再刻意营造温情的画面。在他看来,影像的唯美、温情是他人给出的某种趣味和标准,他需要找到自己的判断标准与出发点。他敏锐地感受到时代的快速变化,将镜头对准城市年轻人的种种时髦行为,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融入现实观察与影像采集的过程当中,不断制造着那些充满了冲突、滑稽、幽默意味的照片。那个躲在相机背后善意调侃的摄影家吴正中逐渐清晰起来。
1992年,吴正中离开了橡胶厂,开始了他作为自由摄影师的纪实摄影实践。他沿着“海滩情”留下的反思和经验,开始系统拍摄和他同样白手起家的小本买卖人。在他看来,工厂里的“炭黑工”和青岛街头的小本买卖人才是真正的精神贵族。他们处境艰难却不言放弃,磨难历尽仍然自得其乐。他毫不掩饰对他们的敬意与尊重,但他不是在单纯地拍摄那些小本买卖人的状态性肖像(比如桑德那样)而是努力显现出那些小人物的行为信息:他们从事的营生,他们与周边环境的关系。通过强调影像的这种叙事性,营造出一种氛围感与空间气息,从而赋予他的照片一种超越视觉感官的能力。让我们除了看到胶州路与观象二路交叉口卖红薯的姐妹、安徽路上推着馄饨车的父亲与孩子、福建路上做棉被的夫妻,还能感受到青岛冬天的湿冷以及夏天聒噪的蝉鸣。
1996年,吴正中与孙京涛在《大众日报》联名发表了一组图片故事《盲人按摩师》。此时,国内各种纸媒开始尝试转型。人们不再满足于文字阅读,印刷技术的变化与提升,让不少报纸开设了大篇幅的图片版,图像的视觉信息传播开始受到重视。此时的吴正中成为了《半岛都市报》摄影记者。他不断地修正和突破自己的视觉语言,拓展对影像的理解,开始尝试各种开放式的画面构成,注重照片的视觉强度,强化照片与照片之间多重信息的互补关系,以丰富照片的叙事性。亦是机缘巧合,他遇到了时任《大众日报》图片总监的孙京涛。在孙京涛的热情指导与倾力支持下,吴正中拍摄了《郭素爱》《滑板小子》《母爱托起的美丽》《青岛地图》《老院落新房客》《中国式婚纱照》等大量精彩优质的图片故事,并得以在媒体上陆续发表。多年以后,孙京涛在文章中描述了当时吴正中的状态:“老吴每天白天出去拍照,晚上便在屋子里冲洗胶卷、放大照片。冲洗出来的底片像海带一样挂在横贯屋子的一根铁丝上,照片就摊在床上、地上,到处都是”。
吴正中是一个不容易满足的人,正如他当初不满足于只拍厂里的宣传照一样。他很快意识到,图片故事这种体式本身较为集中的话题性,以及较为单一的叙事逻辑,决定了它不可能形成一个更为丰富复杂的视觉结构,很难满足他通过摄影来对青岛老城区进行整体描述的企图。他开始在一个更大的格局和结构意识当中来观看整个青岛老城区,大量地拍摄这一区域内相关的建筑、街道院落以及在这一区域讨生活的平头百姓。
1996年-2002年,吴正中完成了两个重要的影像专题作品《波螺油子路》和《崂山大院》。“波螺油子路”是极具青岛特色的街道,顺山而建,上下起伏,十处转弯,路面用小青石块铺就,周围坐落着中西结合式两层小楼,西北段毗邻农贸市场,市井气颇浓。在吴正中眼里,这条路不仅是一条城区街道,也是他儿时滚铁环、打纸牌、打木头、跳房、抗拐的游戏场所。而“崂山大院”作为青岛市历史上最有名的棚户区之一,虽有“崂山”之名,却无崂山之美。大院用石块、土坯搭起的房子低矮拥挤,人均居住面积不足4平方米,三百多户人家一千多居民共用一个水龙头,一个厕所。当他得知横贯青岛东西的快速路建设将要拆毁“波螺油子”这条独具青岛特色的街道时,作为一个摄影师,他已经清晰地意识到,大规模的现代化城市改造进程,正在抹掉与他生命过程相关的那些痕迹。他能做到的,只有通过自己的影像记录和描述,为自己留下一份未来可以观看的少年记忆。
2000年,摄影评论家刘树勇在《中国摄影》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图像的社会学功能—从吴正中的老青岛说起》,对吴正中有关青岛老城区的影像记录予以梳理分析,并从社会学有关社区研究方法论的角度,对摄影师如何通过照片来进行空间性描述予以详细的阐释。吴正中开始将“波螺油子路”和“崂山大院”的个案经验延展到有关整个青岛老城区的影像描述当中。他清晰有序的一条街道一条街道地拍:吴淞路、上海路、夏津路、武城路、陵县路……一个院落一个院落地拍:广兴里、积厚里、永泰里、平康五里……继而登堂入室,深入居民家庭,寻找和捕捉那些百姓日常生活的绵密细节。
2010年,吴正中的《青岛变迁》获“徐肖冰杯”关注现实典藏作品奖,并被徐肖冰、侯波纪念馆永久收藏。他在不同时间站在相同地理位置,用相同的视角拍摄的有关老青岛城区的影像并置在一起时,时间的力量开始显现出来。大规模的城市现代化进程,视觉景观梦幻般的变迁,以及一个时代的急速推进,都一一凝结在这些朴素而坚实的照片当中,成为未来无法抹去的历史痕迹和城市记忆。
至此,从“小本买卖人”到“老青岛”,再到“青岛变迁”,吴正中用纪实摄影的语言完成了他对青岛老城区的人物描述、空间描述和时间描述,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富有内在逻辑结构的关于这座城市的影像群。正如孙京涛所说:“经过七八年的努力,老吴也完全可以像阿杰宣布‘拥有了整个巴黎’一样,说自己拥有了整个老青岛—他记录了一个城市最有魅力的部分,记录了一个城市生命中最华丽的乐章。”
2014年,年满六十的吴正中从报社退休,但他一如既往地对周遭世界和事物保持着好奇。评论家刘树勇曾感叹,“以老吴这样的年纪,竟然还有这种犹如童年的惊讶与好奇,哪怕是一砖一树,他都好奇。这好奇意味着一个人与这个世界有一种特别的关联,有一种观看的冲动与敏感。”
凭借这份冲动与敏感,吴正中开启了他新的语言探索之路。2014年,吴正中拍摄的系列作品《面具》亮相平遥摄影展。身着泳衣带着“脸基尼”的中年女性肖像,单纯而诡异,具有一种超现实的荒诞感。吴正中抛弃了他所擅长的影像叙事,将细节的组合转为细节的放大。被放大的女性状态赋予这些影像某种奇特的矛盾感:身份与身体的遮挡与暴露,男性与女性的自然本能与自我认同,现实世界当中存在的某种不真实的人物形态。吴正中用他过去鲜有使用的方画幅,冷静地展示着这些普通人生命活动的痕迹。这像是对他原有影像风格的反叛,又像是对城市空间描述方法的一种转换,也可能是两者的叠加。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吴正中撕下了贴在他身上的作为一个纪实摄影家的标签。《面具》的策展人、《南方周末》的图片总监李楠说,“真正的摄影家,是没有标签的,或者说,他总是要尽力地去标签化,而不是将标签作为自己的护身符和价码牌。我非常高兴这个观点,在吴正中身上得到了充分印证。”
《混搭之城》在吴正中过去的影像叙事中是无迹可寻的:一把破旧的镜子和拿着镜子的手反复出现在影像的前景,镜子中反射的场景与镜头前的场景,企图构成某种微妙关系,毫无美感甚至让观看者产生不悦。这是吴正中的照片吗?他为什么这么拍?直到我回到青岛与他共同进入拍摄场景时,我知道这组照片是吴正中自拍摄“波螺油子路”以来压抑多年的一次情感释放。持续不断的城市改造让他记忆中的“老青岛”无处寻觅。这种现实和过去的巨大落差,让他不再躲在相机背后,而是将各种视觉符号和自己的身体嵌入到城市之中,用更为直接的画面表达对现实的观点。这种介入性的直观表达和具有隐喻性的道具使用,让我们看到了他希望找到更多的观看视角与影像表达可能性的企图。
2021年,吴正中完成了他最新的一个专题《老屋余温》。他将镜头对准了城市的内部空间—搬迁之后废弃一时的老屋。那些生命曾经存在的痕迹—老式家具、席梦思床垫、沙发、残破的木质地板、陈旧的挂历图片,等等,如强大磁场般吸引着他。这些老屋曾经的主人是他的同学、亲人、同事。吴正中走进这些老屋,宛如走进一个个人生剧场,目睹和倾听着在这里发生过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吴正中用细腻沉稳的影像语言,赋予了这些即将拆除改造的破败不堪的老屋以人世的温情。他放弃了此前擅长的略具嘲讽调侃的观看姿态,重回一种质朴平素的视觉表达,只有一个目的,让影像充满昨日的温暖记忆,就像居住此处的人们永远不会散去那样。
回顾吴正中的摄影生涯,从题材内容和语言表达两个层面,交织发生着不同程度的转变。他在不同时期,调整着自己与现实、与摄影的关系。特别是2014年以后,依赖于长久以来形成的笃定信念和坚持,不断为自己的摄影表现找到新的灵感与活力。尽管他一再表示自己并不在乎什么新旧之类的说辞。他只是将摄影当做他的“出气筒”。他对摄影的态度与法国摄影家安德烈·柯特兹高度吻合“相机是我的工具,经由它,我给予我周遭所有事物一个理由”。
检视他的整个摄影生涯,吴正中已经活成了他想活成的样子,择一事,终一生。在漫长的人生历程当中,纷纷扰扰、举棋不定、踌躇不前总是人之常态,吴正中则向我们展示了人生的另外一种可能。他不是榜样,也不是标本,他的个案只是可以告诉我们,人,原来可以这样的活着。他像一生都在调整画圣维克多山角度的塞尚一样,你分不清楚他们这么做是为了艺术还是为了活着本身。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一个人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就足够了。我只想做好自己的记录,其他都不管了,我也管不着。我是一个旁观者,又是其中的生活者,通过摄影记录人生的軌迹,我觉得这样挺好。别的职业都无法像摄影这样给我这么大的乐趣。”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此“水源”乃时间之意,此山或名为“青岛”。吴正中站在山前举起自己的相机,那一刻他看到了光。沿着这束光的指引,他心无旁骛地走了进去,换来了他心中的桃花源。
我想,吴正中的照片们是幸运的,他们被吴正中制造出来,又见证着吴正中慢慢老去。他们既是时间的切片,又被时间拉长。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将延续着吴正中的生命,出现在未来的时间和空间里,被我们不断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