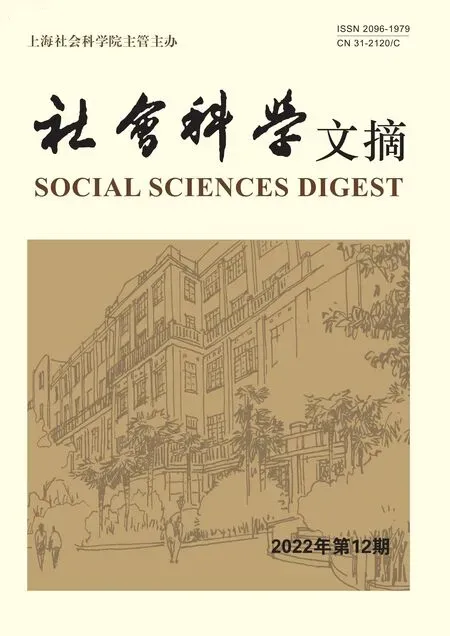中国戏曲文学阐释视角论略
文/李昌集
中国戏剧演艺的特质与戏曲文学阐释的思路和视角
中国戏曲文学阐释,首先面临的问题是:由于现代全球通行的戏剧样式是话剧,系统的戏剧理论是西方话剧理论,但戏曲和话剧的表演形态、剧本文体有所不同,所以要明确中国戏曲文学表达方式的自身特质,以建构中国戏曲的阐释理论。
戏曲不同于话剧对生活真实的模仿,表演形式是取样现实生活而修饰之的“写意”——非生活常态的曲唱、修饰性“戏腔”念白、程式化肢体动作、格式化脚色行当、象征性脸谱及服装道具和舞台布景——从表演到场景,皆非现实情景的仿真再现,而是对现实存在的某种虚拟性意象化表现,戏曲剧本与戏曲表演相表里,故戏曲文学同样是“写意”。
从艺术学角度说,写意本是中国一切艺术的古老传统,中国古代没有如同西方严格而精致的写实艺术。中国人所云艺术的“写真”,不在外部形态,而在神态之真、情意之真,戏曲亦不例外;从文化生态学角度言,戏曲扮演有头有尾的故事,最初是市井民间娱乐活动中的创造。娱乐本是人的一种天生习性,娱于意,乐于情,动于心,故“写意”是娱乐文化的戏曲与生俱来的文化本性,在历代雅俗群体的共同娱乐中凝聚为中国特质的“戏曲传统”。
戏曲文学,广言之为“故事文学”。中国古代故事文学包括史传、小说(及讲唱)、长篇叙事诗、戏曲剧本四大类。史传作为正统文学,“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第一规则是记述真实的故事,根本宗旨是对“故事”的理性评判。娱乐文化的戏曲也是“古装戏”,但戏曲文学的“写意”是对生活的情感理解和评判,本质上与理性反思的历史书写完全不同。戏曲文学表现的是情感的人,历史文学书写的是理智的人,二者合之乃是完整的“人”——中国人。
上述戏曲文学的写意性、情感性,是戏曲文学阐释的基本思路和各种阐释视角的聚焦点。戏曲文学阐释视角从微观到宏观,涉及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艺术学、美学、文学史等若干学科,本文基于文学的本体研究选择三个视角,讨论戏剧文学阐释的几个方面。
传奇与诗性思维的互洽:中国戏剧文学的叙述构架
戏曲文学的载体是人物传奇故事,所以戏曲写作和观赏的思维活动首先是“传奇思维”;戏曲最出彩的是曲唱,“曲”为广义的诗歌,诗歌重情感抒发,故曲辞写作势必带入情感性的“诗性思维”。“传奇”和“诗性”双重运思的磨合和互洽,成为戏曲体建构和历史演变围绕的中心,概言之约有三个历史节点:宋元南戏、元代杂剧、明清传奇。
(一)宋元南戏:汲取“话文”的戏曲体传奇
今存最早剧本宋代南戏《张协状元》,有着浓厚的讲唱小说色彩,“唱”和“说”的叙述功能尚无明显区分,都是故事性“行为叙事”。今存第一部文人写作的南戏剧本《琵琶记》,叙述构架与民间南戏大体一致,但故事结构的松散之弊大为改观,“传奇”与“诗性”的交构、角色语体的区分,对明清传奇戏曲体的建构具有重要影响。
(二)元杂剧:“诗性”与“传奇”交融的样板
元杂剧是古代文人戏曲体建构的第一个里程碑,情节结构较南戏简明紧凑,曲唱抒情大为扩展,说白则专主叙事。早期典型关汉卿杂剧以“传奇”为主导,但“诗性”较宋南戏明显增强,提升了“传奇”的意蕴;此后马致远杂剧,将“诗性思维”扩展到整部戏剧,以故事情节生发和推动情感,以情感作为全剧的重点与终结,是元杂剧最具特色的叙述构架。
(三)明清传奇:“传奇思维”的提升与“诗性思维”的交织
明代文人传奇的构架主要是对元文人南戏的继承,同时汲取了元杂剧的“诗性”构思。晚明清初,剧坛对故事结构尤为重视,王骥德《曲律》提出戏曲写作的“大头脑”“贵剪裁”“贵锻炼”“审轻重”,吕天成《曲品》提出“局段严谨”,李渔《闲情偶寄》提出“结构第一”。诸家戏曲结构论,反映了晚明清初文人的戏剧观和写作意识向“传奇思维”的回归。以“传奇”为本而与“诗性”互洽,成为明清“戏曲体”演变的主导趋势:科白的“行为叙事”与曲唱的“情感叙述”交叉行进,故事触发情感,情感催动故事,从而赋予“传奇”以诗性意味,“情感行为”成为故事展开的内在动力,情感世界成为戏剧表现的内在主体。
“传奇”与“诗性”交织的二重叙述结构,是中国戏曲文学别致的艺术方式。“传奇思维”植根于民间大众“听故事”的朴素喜好,“诗性思维”的主导是文人文化的传统情怀雅致,文学的写意则将“传奇”与“诗性”相洽为一种意象。中国戏曲的作者和观众都明白:舞台上和剧本中的传奇故事都是“戏”而不是现实,唯其如此,此“戏”才不单是“这一个”传奇,而是诉说着、寄托着雅俗大众广泛的诗性情感思绪——这就是中国戏曲。
中国戏剧故事:生活逻辑与情感愿望的冲突与聚合
美国学者布罗凯特在《世界戏剧艺术欣赏》中说:“西方的观众有时不易了解中国剧,因为它每每集中于高潮,而把故事的发展委之说白。因此之故,兴趣的焦点是高潮的片刻,而不在全部故事的戏剧化。”这隐含着中国戏曲“戏剧结构”不够完整的意思。确实,以西方观众熟悉的西方戏剧衡量,中国戏曲的虚拟性和意象性写意与西方戏剧要求故事的真实性和逻辑的合理性,看上去常常背离,这是中国戏曲文学阐释无以忽略回避的问题。学贯中西的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对元杂剧既有“中国最自然之文学”的极高评价,也有三点批评:“关目之拙劣,所不问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讳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顾也。”这一对元杂剧的正、反两方面评价,关系到中国戏曲文学阐释的全盘布局,遗憾的是王国维亦未展开,只以“固不待言”一句带过。
应当承认,“关目拙劣,人物矛盾”在宋元戏曲中均有程度不同的存在,今天也似乎找不到可以回护反驳的理由。因此,根本问题在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矛盾,如此“戏剧”的意义和“戏剧效应”是什么?答曰:因为中国戏曲是写意而不是写实。宋元戏曲是雅俗文化交融的产物,文人戏曲创作的“写意”,乃将自己的“意”与民间大众所期待、所能理解的“意”融合在一起,以“民间想象”的故事逻辑构成戏剧“关目”,剧中的具体故事是特定的,“故事类型”则是民间大众熟悉的;故事中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具体身份和行为动作不同,而故事发生发展的基本因果关系则大同小异,其“因果”不是理性思考,而是民间的直观抽象经验和情感愿望。于是,各种陌生角色的故事,便以世俗化的情节构成一种大众“熟悉”的故事。但是,当现代文人以其熟知的历史知识和对社会现实的思考,理性审视戏剧中“民间想象”的情节结构,便不免觉得“拙劣”“卑陋”“矛盾”了。
但是,此乃现代文人的眼光,古代大众和文人却不这么看。在大众眼中,一个戏剧故事并不就是“这一个”,而是超越这个故事的所有类似故事,激起的是民间大众对“这类故事”的普遍情感反应。所以王国维推许为“最自然之文学”,因为民间大众对这些“拙劣”“卑陋”“矛盾”,“自然而然”认为就应该这样。若《张协状元》的“痴心女子负心汉”和“磨难妻子得团圆”,负心汉是民间的共同憎恶,团圆是大众的集体愿望,故事前后连接的“关目”和“人物”是否合理,民间大众“所不问也”;《汉宫秋》表现的被迫失去所爱的痛苦,是千百年来雅俗文学延绵不断的共同主题,一个皇帝可能这样多情吗?汉元帝真情而懦弱的君王与平民形象的叠合,王昭君烈女与志士的双重形象。“人物矛盾”乎,作者和大众“所不顾也”,其人其事已不单是一个帝王和妃子的个人之情,更是普遍的人类爱情的意象。当这种超越个体的爱情故事获得古往今来接受者的共鸣,一切“关目之拙劣,思想之卑陋,人物之矛盾”皆被淹没,戏剧故事表层结构上的矛盾,恰聚合为超越个体、超越阶层、超越时空的集体心灵,其深层底蕴乃是中华民族普遍的人文观念。而这,乃是中国戏曲文学“写意”的精粹和特质。
中国戏曲文学的人学主题
戏曲文学的“人学主题”,指其表现的人生、人性、人道主题及蕴涵的人文观念。古代戏曲故事的最大一宗是爱情婚姻,可谓古代文类中最突出的专类“爱情文学”。兹以爱情剧为例,从戏剧故事和人物形象两个视角,讨论古代戏曲的人学意涵。
(一)爱情故事的人学意涵
中国古代爱情喜剧的主干构架大相一致:相爱结合—被迫分离—姻缘美成。这一构架本身即是现实中自由爱情艰难处境的反映。“美成”只是一种愿望,若状元及第和各种“巧合”的团圆,虚拟“喜剧”的实质恰是现实悲剧的倒影。
没有喜剧的“美成”而终结于毁灭,即是爱情悲剧。悲剧,较喜剧更深刻。《汉宫秋》的人学主题是:现实的爱情可以毁灭,精神的爱情永恒不灭。同样是帝王家爱情《梧桐雨》的悲剧主题是:人,既是个体的,又是社会的,爱情并不是自身的独立存在,爱情行为如果脱离了正确的轨道,便会因爱情自身而毁灭。平民的爱情悲剧更有普遍意义,《娇红记》的人学主题是:情,是人的生命本体,是人之为“人”的第一标识。这一人学主题,是晚明新人文思潮“情本论”在戏曲领域的时代回响。明·张琦《衡曲麈谭》:“人,情种也;人而无情,不至于人矣,曷望其至人乎?”《红楼梦》对“情种”有这样的解释:“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娇红记》双双殉情的悲剧,正是“情种”被“无情”现实扼杀的悲剧。
中国古代爱情悲喜剧,“悲”“喜”内在同质,彼此互文,这与西方悲喜剧颇有差异。严格说来,中国戏曲没有如同西方定义的悲剧和喜剧,悲剧的“喜剧”结尾,既违反故事逻辑,现实中也不可能发生。古代不少戏曲剧本的写意主题与作品折射的现实并不统一,所谓“关目之拙劣”“人物之矛盾”,实质性要害即在此,是戏曲文学阐释中一个复杂而难以把握的问题,也是需要深入研究的深刻课题。
(二)戏曲人物形象的人学意涵
戏剧形象的人学意涵,是戏剧故事的人学主题更具体的展开,每部剧本人物形象的具体分析都有若干话题,这里仅从古代两性文化的视角提出一点概略思考。
1.爱情婚姻戏剧中的女性形象。中国古代正统观念的女性形象,是汉代确立的。中国古代第一部专论“女德”的经典是东汉班昭的《女诫》,该书讲述闺秀到妻子应当具备的各种道德品行,是对官方确认的儒学经典《诗经》“二南”之“后妃之德”和“夫人之德”的展开和发挥,所标举的女性形象,概括之:勤劳俭朴,恭敬孝顺,婚姻以时,男女以正,无嫉妒之心,辅佐丈夫成功。以此标准看戏曲故事中的妻子,都是合乎正统“女德”的形象,温柔顺从,一心一意“辅佐君子”,体现了古代女性的集体意识。但戏曲中追求爱情的女子,则是“逆反”形象。宋代官方将“存天理灭人欲”确立为集体伦理观念,爱情作为“人欲”遭到绝对禁锢,“贞洁”成为女性形象的第一标准。但中国古代两性文化中仍有一脉不断的自由爱情,虽然从来都是非主流,却是中华自由爱情精神顽强不息的反映。戏曲文学中自由爱情女性形象的深层意味,是中华女性虽然微弱但从未消失的追求实现自由之我的人学命题。
2.戏曲爱情故事中的男性形象。戏曲爱情故事的男性主角,除了个别帝王几乎都是书生,一类是男权主义的“负心汉”;一类是与女性平等的“专情男”。负心汉是被谴责唾弃的对象,最突出的是“戏文之首”《赵贞女》中的负心汉蔡二郎被雷劈死;明清以来,妇孺皆知的负心汉陈世美被包龙图铡了脑袋。这是民间大众打破男尊女卑的正义显现和肯定爱情的一种方式。
戏曲文学对自由平等爱情更富有意义的肯定,体现在爱情戏剧中的书生“专情男”形象上。中国有知识崇拜的悠久传统,知识人是大众集体意识中的优秀者,爱情戏剧的男主角之所以大多是书生,有文人剧作家的自我体验和心理折射,深层意味则在以大众心目中书生的文化人身份将平等爱情赋以“文化”的意义。
3.古代戏曲人物的“复合型”形象:中国特色的戏曲文学形象“这一个”。中国戏曲将不同社会身份的形象复合为“这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戏剧“真实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但如果以中国的“写意思维”解读戏曲故事的环境和人物,则不妨理解为中国式意象化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例如,富贵人家的后花园,即是剧中大家闺秀的一种典型环境,但此“花园”不仅是人物行动的“环境”,深层意味是那个时代的女性被禁锢的意象,是被“女德”和“礼义”封闭的孤独心境的象征,同时也是年轻女性跨出闺房走进“自然”的心灵向往。走出“花园”的闺秀,乃是突破现实世界禁锢的自由之人的意象。这种诗性写意的多重意味,是中国特色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其意义不在西方理论话语中的“现实主义”,而是中国人文语境的情感意象。
因此,中国戏剧人物形象的深层意味,在于故事中的“这一个”既是自我,同时也是他者,使“这一个”成为各种身份形象元素的复合,成为具有某种“集体意味”的形象,让观戏的雅俗众人都能找到某种自己的影子,找到自己的生命体验,找到自己的忧伤,找到自己的快乐。男女老少在对现实的感叹、愤懑和情感愿望满足的平衡中获得心灵的快乐。一场场戏曲演出、一本本戏曲故事,汇聚成雅俗共赏的“大众共和曲”,将一个个“复合型”人物形象,凝聚为中国戏曲和全球各种戏剧共同的人学追问:人,应当怎样活着,应当做一个怎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