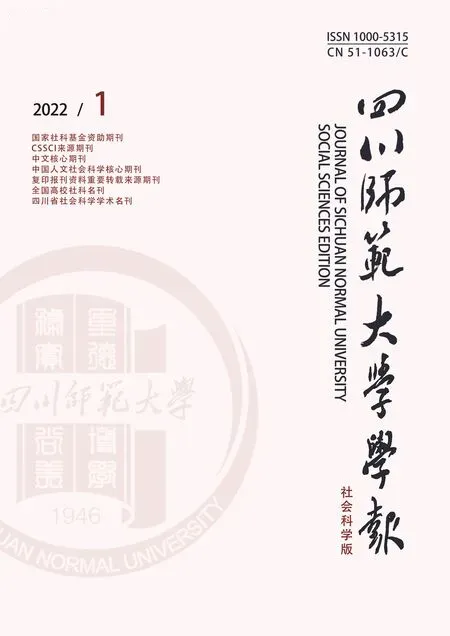多元主体视角下生态补偿减贫路径比较与行动方案选择
宋碧青 龙开胜
生态补偿的本质是寻找生态系统服务生产、消费和价值实现过程中相关方利益不均衡、交易成本过高的领域,通过制度安排使受益方付费、受损方得到补偿,并激励(或避免)相关方实施有(不)利于全局、整体和长期利益的行为(1)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编著《生态补偿的国际比较:模式与机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生态补偿政策多与特定的土地利用服务有关,其实施区域多为生态脆弱区且多与贫困地区在地理上有着高度的重叠性(2)吴乐、朱凯宁、靳乐山等《环境服务付费减贫的国际经验及借鉴》,《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9年第11期,第34-41页。。脆弱的生态环境会加剧地区贫困,农户贫困又会增加对自然资源的攫取,加速脆弱的生态环境恶化,容易陷入恶性循环(3)Shixiong Cao et al., “Win-win Path for Ecological Restoration,” Land Degradation & Development32, no.1 (August 2020): 430-438.。生态补偿政策的设计初衷是为保护生态环境,近年来逐渐成为应用于减贫的政策工具,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环境治理问题往往与贫困问题交织,越来越多的研究聚焦于生态补偿对缓解农户贫困的作用机制及影响效应。
已有研究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生态补偿对农户减贫的影响,如不同的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减贫的效果(4)李军龙等《激励相容理论视角下生态公益林补偿对农户的增收效应——以福建三明为例》,《自然资源学报》2020年第12期,第2942-2955页;吴乐、靳乐山《贫困地区不同方式生态补偿减贫效果研究——以云南省两贫困县为例》,《农村经济》2019年第10期,第70-77页。,生态补偿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影响(5)朱烈夫等《生态补偿有利于精准扶贫吗?——以三峡生态屏障建设区为例》,《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42-48页;马橙、高建中《森林生态补偿、收入影响与政策满意度——基于陕西省公益林区农户调查数据》,《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0年第11期,第58-64页。,以及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辨析生态补偿对农户可持续生计的作用(6)赵雪雁等《生态补偿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地理研究》2013年第3期,第531-542页;袁梁等《生态补偿、生计资本对居民可持续生计影响研究——以陕西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为例》,《经济地理》2017年第10期,第188-196页;Genowefa Blundo-Canto et al., “The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Livelihood Impacts of 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PES) Schemes: A Systematic Review,” Ecological Economics149, (March 2018): 160-183.。制度环境是构建生态补偿机制的先决性条件(7)曾庆敏、陈利根、龙开胜《我国耕地生态补偿实施的制度环境评价》,《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第114页。,项目的补偿对象一般为土地承包者,这意味着土地所有权制度和分配形式对于项目的扶贫效果而言十分重要,以致于同一块土地的不同权利主体(比如土地承包者和土地经营者)在参与生态补偿时也存在利益冲突(8)Stefano Pagiola, Guidelines for “Pro-poor” 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Washington: World Bank, 2007).。生态补偿政策对依赖土地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不同类型农户收入均有影响,包括土地承包者、土地经营者以及农业雇工。多元主体生计水平的提升是项目效果持久性的有效保障,但以往研究通常只关注生态补偿的参与农户即土地承包者,少有研究考虑其他土地权利主体,论述生态补偿对不同类型农户减贫的作用路径。
生态补偿作为中央扶贫工作有力的政策工具,为脱贫攻坚目标的实现贡献了重要力量。本文从多元主体视角出发,首先系统回顾国内外生态补偿政策减贫的实践经验,阐明生态补偿对不同类型农户减贫的一般作用路径及其差异,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不同主体特征的生态补偿行动方案,以期优化生态补偿政策设计机制,从而为我国后脱贫攻坚时代生态补偿减贫战略的推进提供相关对策建议。
一 多元主体视角下生态补偿的减贫路径:基于文献成果的归纳
生态补偿多与特定的土地利用服务有关。由于补偿项目的实施使依赖土地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相关主体生计受到影响,可能会进一步引发农户生计水平下降、收入差距扩大等其他社会问题。本文围绕参与生态补偿的土地承包者以及生计受影响的未参与项目贫困农户(包括土地经营者和农业雇工),总结生态补偿对不同主体收入的一般影响路径。
(一)土地承包者与生态补偿减贫
一般而言,生态补偿的作用对象是土地承包者。对于可自愿参与的项目,土地承包者能否顺利参与,首先取决于地块位置是否位于项目划定区域,其次是农户是否有意愿和参与的能力(9)Stefano Pagiola, Agustin Arcenas, Gunars Platais, “Can 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Help Reduce Poverty? An Exploration of the Issues and the Evidence to Date from Latin America,” World development33, no.2 (February 2005): 237-253; 王立安等《西部生态补偿与缓解贫困关系的研究框架》,《经济地理》2009年第9期,第1552-1557页。;而对于强制实施的项目,只要土地承包者的地块范围符合要求则必须参与。生态补偿通过多种补偿方式弥补土地承包者损失,具体包括现金、实物、岗位、技术和教育等。
生态补偿对土地承包者给予的现金或实物补偿将直接影响其净收益水平,当获得的补偿金额大于农户参与项目的机会成本即净收益为正时,无论农户参与项目时是否自愿,生态补偿都能提高其收入水平。但当项目的补偿金额设置不合理时,农户将面临较高的机会成本,这会导致农户的收入水平降低(10)李国平、石涵予《退耕还林生态补偿标准、农户行为选择及损益》,《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年第5期,第152-161页;Sven Wunder, “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and the Poor: Concepts and Preliminary Evidence,”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13, no.3 (June 2008): 279-297.。现金或实物补偿往往期限较短,对农户只存在短期的作用效果,为保证项目效果持久性,需要提升农户发展的内生动力,达致减贫增收的长效机制。生态补偿对土地承包者收入的间接影响则表现为通过岗位、技术、教育等补偿方式使农户的生计资本得到积累,进而转化为农户的生计能力,最终助力农户增收。
农户的生计能力包括农户的市场参与度和抗逆力。首先是农户的市场参与度。生态补偿中的教育、培训计划能够提高农户的技能水平和就业竞争力。岗位补偿为贫困农户提供就业机会,并对生态管护人员进行专业技术培训和指导。如青海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中为农牧民设置生态管护公益岗位(11)赵翔等《社区为主体的保护:对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公益岗位的思考》,《生物多样性》2018年第2期,第210-216页。,四川省实施的诺华川西南林业碳汇项目对林农进行苗木繁育、补植、管护等方面技术培训(12)张译、杨帆、曾维忠《网络治理视域下森林碳汇扶贫模式创新——以“诺华川西南林业碳汇、社区和生物多样性项目”为例》,《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2019年第12期,第148-154页。,洞庭湖区湿地生态补偿为农户提供环保、生产管理方面的技能培训(13)杨新荣《湿地生态补偿及其运行机制研究——以洞庭湖区为例》,《农业技术经济》2014年第2期,第103-113页。。其次是农户的抗逆力。抗逆力是指农户应用自身资本去抵御风险冲击的能力。贫困地区生态环境脆弱以及农户抵御风险能力不足使得农户呈现出脆弱性特征(14)杨龙、汪三贵《贫困地区农户脆弱性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年第10期,第150-156页。,而生态补偿提升了农户的社会资本,增强村民间的合作和社会联系(15)Rina Maria P. Rosales, Developing Pro-poor Marke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in the Philippines (Lond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2003), 58-59.,有助于集体行动的达成(16)Lindsey Roland Nieratka, David Barton Bray, Pallab Mozumder,“Can 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Strengthen Social Capital, Encourage Distributional Equity, and Reduce Poverty?” Conservation and Society13, no.4 (January 2016): 345-355.,从而分散农户个体面临的风险冲击,增强了农户的抗逆力,缓解农户脆弱性。此外,相较于农业收入而言,生态补偿款收入是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能够对抗农户因自然灾害、价格波动而造成的农业收入损失。
(二)土地经营者与生态补偿减贫
不同的生态补偿项目对土地利用安排存在差异,如耕地保护生态补偿允许农户继续耕种土地,而退耕还林、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等则限制对土地的使用。土地利用安排的差异将影响土地经营者租赁农地的能力,即改变其与土地承包者间的租赁关系。如果生态补偿的实施区域已有土地租赁合同安排,那么生态补偿介入可能会影响这种安排(17)Stefano Pagiola, Guidelines for “Pro-poor” 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Washington: World Bank, 2007).。在限制土地使用的项目实施前,土地经营者能够从土地承包者租入农地并按合同约定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但项目实施后要求停止耕种则土地承包者将会终止租赁合同,土地经营者无法继续租入土地,失去一部分农业收入来源致使其生计水平受损。
在部分允许继续利用土地从事农业生产的项目中,土地经营者能够继续向土地承包者租入土地,土地承包者在获得生态补偿收益的同时获取租金收入。由于实际耕作者是环境服务的直接提供者,对于提供了优质环境服务的土地经营者,理应得到相应补偿,以激励其持续采用生态友好的土地经营方式,但在现实中这部分农户的权益往往被忽视。以我国耕地保护生态补偿为例,政策实践中涉及土地所有者、土地承包者和土地经营者三类土地权利主体,而实际的受偿权利人为土地所有者与土地承包者(18)赵亚莉、龙开胜《农地“三权”分置下耕地生态补偿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第119-127页。,对于采用环境友好型耕作方式的土地经营者未给予合理补偿,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耕地使用过程中粗放利用、质量退化问题频发。虽然近年实施的部分耕地保护生态补偿在补偿款分配中考虑到不同土地权利主体的利益,如苏州市休耕补贴补偿对象为土地经营者,南京市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分配给土地承包者和土地经营者,但大部分补偿项目仍未考虑到多元主体间的利益格局。此外,对于采用环境友好型生产方式的土地经营者,其生产出的农产品蕴含更多的生态价值,在市场交易过程中能获得较一般农产品更高的价格,这一溢价也是作为对其采用生态经营方式的激励补偿。但在市场交易中,采用环境友好型生产方式的土地经营者是否获得合理报酬具有不确定性。
(三)农业雇工与生态补偿减贫
生态补偿对区域劳动力的需求程度产生影响,表现为影响农业雇工的就业岗位安排。部分生态补偿项目对劳动力需求降低,减少了项目实施区域为农业雇工提供的就业岗位。如森林生态补偿要求农户停止耕作,通过造林恢复生态环境,而同样面积的林地所需劳动力投入远低于耕地所需劳动投入(19)胡霞《退耕还林还草政策实施后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对宁夏南部山区的实证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05年第5期,第63-70页。,劳动力农业供给时间缩短,原先被雇佣的农业劳动力变为闲置劳动力。而贫困地区农户往往缺少其他正规部门的就业机会,多依赖于农业收入,因此导致农户收入水平降低。如我国退耕还林工程要求停止在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的土地耕种,广西珠江流域森林碳汇项目为避免碳泄露,限制项目实施地及周边区域农户的林下种植、林下放牧、采伐薪柴等活动(20)陈冲影《森林碳汇与农户生计——以全球第一个森林碳汇项目为例》,《世界林业研究》2010第5期,第15-19页。。这些生产限制性措施会导致原先存在农业雇佣关系的农户失去部分收入来源。部分生态补偿项目对劳动力需求增加,为农业劳动力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增加了农户的经营性收入。如山东省云蒙湖水源地生态补偿在保护区设置了生态保洁和垃圾运输岗位,带动当地群众就业(21)耿翔燕、葛颜祥、王爱敏《水源地生态补偿综合效益评价研究——以山东省云蒙湖为例》,《农业经济问题》2017年第4期,第93-101页。。一项针对中国大熊猫自然保护区的研究表明,在保护区内开展生态旅游为农户提供了部分就业岗位,帮助农户获得了更多收益(22)Yi Li, Peichen Gong, Jiesheng K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Forest Use Transition, and Farmers’ Income Differentiation: The Impacts of Giant Panda Reserves in China,”Ecological Economics180, (February 2021): 6-11.。
由此可见,当补偿项目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时,农业雇工的工资性收入增加,生计水平提升,有助于缓解其贫困;而当补偿项目支持对象为非劳动密集型的土地利用实践时,其提供的就业岗位数量减少,原先的农业雇工失去了部分收入来源,面临生计转型的局面。但由于技能水平不佳、受教育程度低等因素,农业雇工较难在非农部门找到长期、正规的岗位,因而生态补偿导致这部分农户生计水平下降。
二 生态补偿减贫路径比较:不同主体路径的差异
生态补偿对环境服务的出售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收入产生影响,由于各主体在环境服务中扮演的角色各异,其减贫路径存在异质性。本文围绕生态补偿项目地块上不同类型农户的权利及义务特征、补偿形式及影响机制,总结生态补偿对不同主体减贫路径的差异,结果见表1。

表1 生态补偿减贫路径比较
(一)各主体享有的权利及承担的义务存在差异
拥有土地产权是参与生态补偿的前提条件,也是生态补偿款项分配的基本依据。生态补偿实施的项目地块上不同主体享有不同的土地权利,其所需履行的义务也不相同。对于土地承包者而言,作为生态补偿的参与者,拥有项目地块的土地承包权,承担项目合同规定的环境服务义务,是生态补偿的受偿对象。如我国实施的退耕还林以及耕地保护生态补偿,地方政府在政策实践中一般将生态补偿款项支付给土地承包者,并要求其提供合同中规定的环境服务。土地经营者拥有项目地块的土地经营权,其向土地承包者租入土地从事农业生产,不存在法理意义上的环境保护责任。但对于提供了优质环境服务的土地经营者,符合生态补偿的运作规则,应当对其进行补偿。农业雇工不享有项目地块的土地权利,也无需承担提供环境服务义务,不纳入生态补偿款项的支付对象,其仅通过出售劳动力换取工资报酬。
(二)生态补偿对各主体的补偿形式存在差异
针对不同主体提供的环境服务特点,设定差异化的生态补偿形式。一般而言,要求土地承包者提供的环境服务公共性较强,多需借助政府转移支付对其进行补偿。政府转移支付的具体形式包括纵向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以及横向的地方政府间转移支付,实践方式包括发放现金、给予实物、设置岗位、技术培训和教育投入等。土地经营者通过采用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一方面能够生产出生态农产品,另一方面,由于生态价值外溢产生的环境外部效应,因而对土地经营者的补偿,可通过政府转移支付方式或借助市场交易机制实现。已有地方政府在耕地保护补偿资金中设置一定的比例额度对土地经营者进行转移支付,或通过市场交易使土地经营者生产出的生态农产品获得生态溢价而获得补偿。农业雇工则是基于市场定价对其劳动投入支付相应报酬,如通过开展生态旅游为农业雇工提供服务业岗位并支付工资报酬。
(三)生态补偿对各主体减贫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
生态补偿对不同主体的减贫路径存在异质性。具体而言,土地承包者是生态补偿各类补偿措施的直接作用对象,补偿项目通过给予现金或实物补偿直接影响土地承包者的净收益水平,若参与项目后净收益为正值,则有助于土地承包者增收减贫。此外,借助一系列配套的补偿方式,包括岗位、技术、教育等提高农户增收的生计能力,间接助力其减贫。生态补偿对土地利用安排的差异影响土地经营者租赁农地能力,而土地租赁合同的维系或终止决定其农业收入水平。对提供了优质环境服务的土地经营者的补偿能激励其持续采纳生态友好的土地经营方式,同时也可增加其收益。生态补偿具体的运作安排影响项目实施区域为农业雇工提供的就业岗位安排,进而作用于其收入水平。当补偿项目支持对象为劳动密集型的土地利用实践时,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增加农业雇工收入。部分项目为农业雇工提供技能培训,增强其胜任岗位能力,有助于其获得更稳定的工资报酬。
三 后脱贫时代不同主体生态补偿的可选择行动方案
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解决,后脱贫攻坚时代的主要任务是巩固拓展扶贫成果以及治理相对贫困(23)曾福生《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构建》,《求索》2021年第1期,第116-121页。。生态补偿也需契合现实情势,向构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长效机制转变。基于前文的实践经验分析,在今后的生态补偿政策制定中,不仅要关注项目参与者的福利水平变化,也要兼顾相关利益主体的生计水平,确保农户协同发展,最大程度取得项目的生态、社会及经济效益。为此,本文以提升土地承包者收入水平,维护土地经营者权益以及保障农业雇工福利水平为具体目标,提出契合不同主体特征的生态补偿行动方案。
(一)土地承包者增收行动方案
由生态补偿对土地承包者减贫的影响路径可知,部分项目使参与者的净收益水平降低,产生负面效果,为此通过优化实施策略使项目参与者实现利益最大化。
其一,增强生态补偿项目瞄准性。有研究指出,部分补偿项目的益贫性不显著,较富裕农户反而获得了更多的项目福利(24)Nitta Atomu et al., “Direct Payments to Japanese Farmers: Do they Reduce Rice Income Inequality? Lessons for Other Asian Countries,”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42, no.5 (September-October 2020): 968-981;吴乐、孔德帅、靳乐山等《生态补偿对不同收入农户扶贫效果研究》,《农业技术经济》2018年第5期,第134-144页。。在后脱贫时代,生态补偿应与精准扶贫工作相结合,重点瞄准相对贫困人群,优先向易返贫群体倾斜。为此,需调整农户的参与门槛,放宽对农户土地面积、资金投入、技术能力的限制并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使政策起到较好的帮扶效果,但参与项目的农户必须具备能够提供所要求的环境服务的能力。
其二,优化补偿标准制定规则。科学合理的补偿标准是弥补农户机会成本、调动农户参与积极性的前置条件,在补偿标准制定中需充分尊重农户意愿。不同区域的自然资源禀赋、社会经济条件存在差异,参与农户的机会成本、家庭状况也各不相同,要对不同地域、不同收入层次的农户制定差异化补偿方案,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动态调整补偿标准。
其三,开展多样化补偿形式。拓展当前政府主导的财政资金转移支付的单一形式,如为有劳动能力的相对贫困农户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加强教育、技术培训等扶智措施,如农机服务推广、专业技能培训等;不断引入市场机制,立足当地自然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农业产业。通过多种措施构建农户生计能力培育和发展的有利环境,增强其生存韧性,实现生态补偿巩固脱贫成果的长效机制。
(二)土地经营者权益维护行动方案
生态补偿通过影响土地经营者租赁农地能力及土地经营方式进而作用于其收入水平,本文为维护土地经营者权益,提出以下改进策略。
对于土地经营者可继续租赁农地从事农业生产的情形,考虑对提供了优质环境服务的土地经营者给予一定补偿。如政府可以在补偿方案中设定土地承包者和土地经营者间补偿款分配的比例,以环境服务供给质量作为定价依据,构建环境服务质量评价体系,依据不同环境服务质量等级设定对土地经营者的补偿数额,以此提高土地经营者的收入水平并增强其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此外,也有学者提出土地经营者由于不承担法定的生态保护责任,不宜参与生态补偿资金分配,土地经营权人直接生产农产品,通过产品价格获得补偿是优先方式(25)赵亚莉、龙开胜《农地“三权”分置下耕地生态补偿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第119-127页。。由此,为激励土地经营者提供更优的环境服务,需建立物质化生态产品质量认证制度,体现优质生态农产品与普通农产品的价值差异,帮助土地经营者获得更高收益。
针对土地租赁合同终止的情形,土地经营者可耕种的土地面积减少,减少了其农业生产活动,部分农户变为闲置劳动力,这部分劳动力面临生计转型的局面。为此,生态补偿应扩大技术培训、产业扶持的覆盖面,将因项目实施而生计受损的这部分农户纳入政策范围,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优化农户劳动力配置以获得更多收入。
(三)农业雇工福利保障行动方案
农业雇工仅按照雇佣合同约定提供体力劳动,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环境服务提供者,不属于生态补偿资金的分配对象。生态补偿影响农业雇工的就业安排,对于补偿项目支持对象为非劳动密集型的土地利用实践,项目实施后产生闲置劳动力,部分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到二三产业,但多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收入低且不稳定(26)缪丽娟、何斌、崔雪锋等《中国退耕还林工程是否有助于劳动力结构调整》,《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年第3期,第426-430页。。针对这部分农户,生态补偿在设计时要考虑实施区域的劳动力就业结构调整问题,使这部分因项目实施而产生的闲置劳动力得到有效配置。
具体而言,一是促进闲置劳动力“离土”即本地非农就业。以政府为主导,积极吸纳引进社会资本,依托生态保护建设项目,落地生态产业发展,如生态旅游、生态农业等,为闲置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二是促进闲置劳动力“离乡”。对于自身素质较优的闲置劳动力,政府需发挥中介桥梁作用,与劳动力需求度较高地区建立合作关系,积极引导闲置劳动力流向经济发达地区收益更高的非农产业。
对于补偿项目为劳动密集型的土地利用实践,已有研究指出当前岗位类生态补偿提供的就业岗位质量不高,且减弱了参与者拓宽就业渠道的主动性(27)杜洪燕、武晋《生态补偿项目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影响——基于农村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视角》,《人口与经济》2017年第6期,第116-124页。。为此,政府可联合高校或科研单位,下沉基层为农业雇工提供农业技能培训,一方面有效提升农户的技能水平,另一方面也促使其提供更优质的环境服务。
(四)保障措施
生态补偿项目的平稳、有效运行离不开相关保障措施发挥的辅助性作用,主要应围绕完善生态补偿监测机制、建立退出机制以及完善补偿立法展开。
第一,完善监测机制。需定期监测评估农户收入情况和环境服务提供水平。当前需重点关注易返贫人群,包括不稳定的脱贫人口以及边缘易致贫人口,将上述群体纳入监测范围,通过建立易返贫人口数据平台,定期走访摸排,及时了解农户动态并施以帮扶措施。对农户提供的环境服务质量的监测则可通过在村庄设置管护人员岗位,定期对森林保护、土地耕作等环节进行监管。
第二,构建退出机制。依托监测平台获得的信息,动态调整项目参与者,使有限的补偿资金达到最优配置。具体而言,若农户有效提供了环境服务并已脱贫,则将其退出;若农户提供了环境服务但属于易返贫人群,则考虑转变补偿方式、优化帮扶形式;若农户未按规定提供环境服务但属于易返贫人群,则加强对其环境服务质量的监督;若农户未有效提供环境服务但已脱贫,则主动终止项目合同。
第三,完善生态补偿立法。生态补偿为我国的减贫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后脱贫攻坚时代仍将继续发挥价值,为此,需健全生态补偿立法体系,有效补足当前生态补偿立法零散、标准各异、监管不严等短板,形成一套规范的法理约束。一是出台正式的生态补偿政策,明确各类生态补偿的补偿标准、范围、程序等内容,界定各利益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将各类生态补偿制度纳入统一、完整的制度运行框架中;二是制定生态补偿市场化运作规则,包括市场化准入、具体流程、收益分配等细则,确保生态补偿市场化机制的规范运行。
四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多元主体视角,在系统梳理国内外生态补偿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探讨了生态补偿对土地承包者、土地经营者以及农业雇工减贫的影响路径及其差异,并针对不同农户特征提出后脱贫时代生态补偿行动方案。结果表明,不同类型农户的土地权利及义务特征、适用的补偿形式以及减贫作用机制存在差异。土地承包者拥有项目地块的土地承包权,需承担提供环境服务义务,其减贫机制在于生态补偿影响土地承包者的净收益水平与生计能力;土地经营者拥有项目地块的土地经营权,不承担提供环境服务义务,其减贫机制在于生态补偿影响土地经营者租赁农地能力和干预其土地经营方式;农业雇工无参与项目地块的土地权利,不承担提供环境服务义务,其减贫机制在于生态补偿影响农业雇工的就业岗位安排以及通过提供技能培训提高其胜任岗位能力。
本文依据路径分析提出针对不同主体的生态补偿行动方案:为促进土地承包者增收要增强项目瞄准性、优化补偿标准制定规则以及开展多样化补偿形式;为维护土地经营者权益,可在补偿方案中设定土地承包者和土地经营者间补偿款的分配比例或构建生态农产品市场化机制,并对土地经营者提供技术培训、产业扶持;为保障农业雇工福利水平,可依托生态保护建设项目,落地生态产业,通过政府引导其非农转移就业,为农业雇工提供农业技能培训。此外,还需完善生态补偿监测、退出机制,推动生态补偿立法以保障项目有效运行。
诚然,不同的生态补偿项目在设计机制、实施方式上存在差异,这表明对项目的减贫效果和实施策略还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今后的生态补偿机制设计中,应当重视所有的权益主体而非单一利益主体,既要考虑提供环境服务的直接权利主体,也要兼顾因项目实施而受影响的相关主体,充分考虑多主体的利益格局变化,增强政策扶贫效力。
-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其它文章
-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研究
——概念界定及一个重要的规模差异成因 - “比象”探源
- 汉语二语学习者学术汉语写作能力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