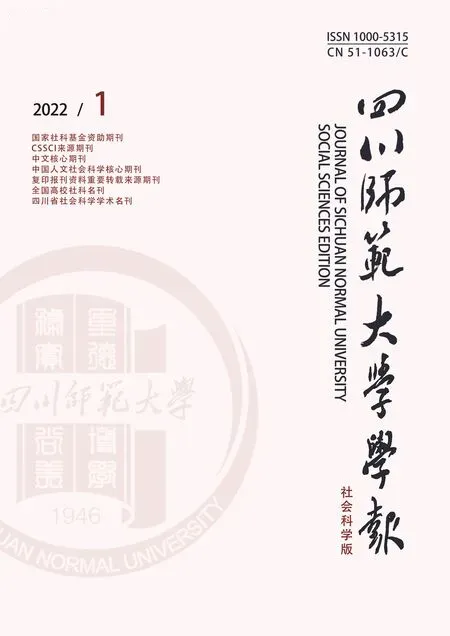“比象”探源
王海龙
“比象”是中国独特的传统思维方式,对中国哲学、美学、部门艺术等文化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比象”思维在当代只是在中医药领域较受关注,哲学、美学界却鲜有人论及,更遑论对该概念的专题探讨了。当代中国的一些美学辞典和范畴史教材等,也均没有收入“比象”一词(1)相关辞典虽然收入了关于“象”、“赋”、“比”、“兴”等条目,但看不到“比象”这一条目。。从中国历史上看,“比象”一词最初见于《左传·桓公二年》:“五色比象,昭其物也。”杜预注:“车服器械之有五色,皆以比象天地四方,以示器物不虚设。”(2)左丘明传、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42页。这是源于古人用青、白、赤、墨、黄“五色”表示东、西、南、北、中不同的空间、方位,又以“天玄地黄”指称天地,由此说明人所使用的一切“器物”都不是“虚设”的,而是人“比象”天地万物创造出来的。这是中国美学所说的“比象”的一大优点。它充分肯定了“比象”既是人的创造性活动,但又是以天地万物为依据的,并具有与“五色”相关的美。但为什么古人要将天地、五色等与“比象”关联起来呢?这就涉及到比象思维的源起问题了。
一 “以天统人”:“比象”思维的原初形态
中华民族主要发源于黄河流域,活动于沿河而成的平原地带,并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农耕文明模式。由于农业的发展非常依赖天时,风调雨顺的情况下农业生产才可以丰收,而旱涝等自然灾害则会导致农业歉收甚至绝收,所以要想获得稳定的收成,就必须顺应好的天时,规避坏的天时。因此,中国古代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天文、历法、数学等领域就获得了较早的发展。但由于理性思维能力不够发达,远古先民只能通过效法、模仿天地自然的运行状态和规律来指导农业生产。由此,对天象的观测,从而效法、模仿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而“比象”思维正是在这个文化背景下产生的。
(一)“比象”与四方四时
由于四方和四时是时空结构的最基本要素,时间和空间又标示着宇宙间的基本秩序;同时又由于古代中国主要是农耕的生产模式,农业的发展有赖于天时和历法,因此,面对外在世界的变化莫测,古人在感到惊惧、恐慌和疑惑的同时,为了生存和发展,就力图想从混沌的外部世界中寻找和掌握各种可以理解的秩序和规律,首当其冲的就是四方四时的观念。也就是说,对于秩序的需求是原初先民思维方式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动力。列维-斯特劳斯就指出:“我们称作原始的那种思维,就是以这种对于秩序的要求为基础的,不过,这种对于秩序的要求也是一切思维活动的基础,因为正是通过一切思维活动所共同具有的那些性质,我们才能更容易地理解那类我们觉得十分奇怪的思维形式。”(3)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4页。这话是有道理的,指出了原初先民的思维方式的原动力及其典型特质。因此,这种建立在农业生产需求基础上的天象观测,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而关于中国古代四方四时的观念,《尚书·尧典》中有非常明确集中的论述: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鹬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4)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19-120页。
通过上面这段话我们可以知道,尧命令羲和根据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律,制定历法并传授给民众有关天时节令的知识,并分别命令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别往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去辨别测定太阳的运行情况,从而确定四季时令的变化和年月日的周期长短,最终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叶舒宪将其概括为中国神话宇宙观的原型模式的时空坐标:
1.东方模式:日出处,春,青色,晨,旸(汤)谷。
2.南方模式:日中处,夏,朱色,午,昆吾。
3.西方模式:日落处,秋,白色,昏,昧谷。
4.北方模式:日隐处,冬,黑色,夜,幽都。(5)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页。
从其归纳的四方模式中,我们可以看到代表东西南北的四种颜色,恰恰跟我们开篇所说的五色比象里的四种颜色相吻合,而且其对应关系是非常固定的,这显然不是一个巧合,而是说明将颜色与方位相对应,早在尧舜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关于这一点,丁山已有过系统论证(6)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在此不再赘述。
在这个四方模式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天地四方不只用颜色来指称,还与春夏秋冬和晨午昏夜相对应,可以说是一个多元的对应关系,没有将时间和空间完全区别开来,而是以空间的变化来说明时间。这就说明尧帝时代所处的阶段正是费尔巴哈所说的原初先民混沌不分的思维阶段,即时空浑融一体观的阶段。这种对应其实就体现了原始思维的典型特质,即通过联想进行类比,每个方位和颜色也都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这应该是象征的最初源头。

当然,这里的比象还不是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推理演绎,而是一种关联和类推,即将日月星辰等天象的运行变化与时间和空间等予以关联,并以此类推,从而将天地万物都关联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一点类似于列维·布留尔所讲的原始思维的“互渗律”的特征。这就可以看出原初先民的思维方式具有非常明显的直观性、实用性和神秘性的特点。因此《周易·系辞上》云:“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8)王弼注、孔颖达正义《周易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82页。天象的变化可能会预示着人事的变化,掌握了这种变化就可以指导人事活动,趋利避害。这就突出了天的地位,以及天人的某种一致性。因此,中国人会特别重视比天,以至于发展出一种对天的崇拜。
而最初的天确实是作为一种至上神而被崇拜的。丁山先生认为,“石器时代人都认识天为万物之原,天就是宇宙间的至高无上的大神。”这是很有见地的,同时他还举前面所说的《周易》中所讲的八卦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他认为,“‘八卦’正是中国初民所崇拜的比较原始的宗教,这个宗教,不见金属,最可反映出来石器时代的文化。”(9)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第179页。在当时的阶段,天、地、雷、风、水、火、土、泽被原初先民认为是宇宙间的八种基本元素,而其中,天又是最本源的元素。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天的至高地位,有赖于对天的认识,才能指导现实的人事活动。这是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的。在原始思维的阶段,先民们还没有独立的自我意识,物我不分,多是采取直感的方式进行认知。这时候的天仍然具有较强烈的人格化的色彩,是最高的主宰,具有让人敬畏依从的权威。
(二)“比象”与原始巫术
天的崇高重要除了体现在指导农业生产外,还在于其具有赋予人间君王以统治的合法性的功能。“绝地天通”的神话故事很能说明这一点。这一神话最早见于《尚书·吕刑》:“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10)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48页。颛顼命重黎分管通神和人事,以便重建一种秩序,即天地相分,人神不扰。
余英时先生认为,“这个神话的历史意义主要不在对萨满文化盛行古代中国的描绘,而在于对萨满文化的政治操纵”(11)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68页。。这是很有见地的。为了解决社会中民神杂糅带来的各种乱象,颛顼主导了绝地天通的巫教改革,禁止民与神直接交流,从而垄断了与天、地交通的渠道,而独享与神交流的特权。这就为其获命于天的统治合法性带来了便利和可能,余英时将其看作是稍后所谓“天命”观念之滥觞(12)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第70页。,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而“绝地天通”的改革虽然使颛顼垄断了与天地交通的特权,但一个人无法应对庞杂的巫教事宜,因此,他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来帮他打理与天交通的相关事宜,并由此衍生出来居于高位的巫觋的群体。而这些群体都是“民之精爽不携贰者”(13)徐元诰《国语解集》,王树民、沈长云点校,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12页。,即非常聪慧的人群,大概是因为与天沟通需要高超的手段,而只有聪慧的人才能掌握并有效运用,从而可以使“明神降之”,即神灵降附在巫觋的身上。由此,巫觋阶层成了与天交通的中介,从而获得了较高的地位。
然而古时候巫觋阶层不但事鬼神,还从事祈福等事宜,因此,余英时认为“‘巫’不仅具有独特的‘事鬼神’的法力,而且同时也是祭祀之礼的设计者和执行者”(14)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第27页。,并由此推论出“礼乐源于祭祀,而祭祀则从巫的宗教信仰中发展出来”(15)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第26页。。礼,《说文解字》释曰:“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16)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7页。而“豊”,《说文解字》释曰:“豊,行礼之器也。从豆,象形。”(17)许慎《说文解字》,第102页。也就是说,礼本意指的就是事神致福的行为,而这种行为其实就是一种宗教行为,也即巫术。也就是说,礼的产生最早是一种宗教行为,而巫恰好是专门从事这种行为的人群,因此,巫成为事神致福系统的设计者和执行者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一点从礼器的形象中可见一斑。《周礼·大宗伯》中云:“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郑玄注曰:“礼神者必象其类:璧圆,象天;琮八方,象地。”(18)郑玄注、贾公颜疏《周礼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762页。这里的苍璧和黄琮就是作为礼天地的礼器而使用的,而其形象,“璧圆象天,琮八方象地”,不正是古人比象天地而创制出来的吗?天圆地方是古人的传统观念,因此,将苍璧和黄琮制成圆形和方形,正是以此象征天地,从而实现沟通天人、事神致福的目的。

这时候对天的崇拜,主要是在宗教-政治领域。由于理性思维能力的不够发达,这时候的天还是高高在上的,人只有屈服的份,而没有太多的自主性。因此,“比象”的思维方式仍处于神性的笼罩之中,尚未取得自己的独立地位,更多地是以一种神秘的比附的形式,通过巫术和祭祀等宗教活动来“比象”天地,表达对天命的敬畏,以及对天命所归之人的绝对服从。这时候的巫术和祭祀主要是模仿至上神的语言、动作,最早的形态以舞蹈和唱和为主要形式,这都是一种简单的模仿。也就是说,这时候的“比象”,主要是比神,或者说是比天的神性。

而这种亲密的样子,刘怀荣通过考证指出,“‘比’字本是原始舞蹈中携手并肩的集体舞和男女双人舞的象形”(26)刘怀荣《赋比兴与中国诗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8、69、73、76页。。而这种原始的男女双人舞是“原始人生殖巫术的表现形式之一”,“明确以男女亲密和人自身的繁衍为目的”;主要出现在氏族内盛典和氏族间的会盟这两种情况中。也就是说,“比”的产生源于原始的舞蹈和巫术,主要指舞蹈的样态和功能,即用富有亲密性和整体性的舞蹈形象以促进生殖、团结氏族成员。而舞蹈的这种样态和功能,明显表现了原初先民思维的直接性和富有情感性。诚如格罗塞所说:“狩猎民族的舞蹈一律是群众的舞蹈。通常是本部落的男子,也有许多次是几个部落的人民联合演习,全集团于是按照一样的法则和一样的拍子动作。凡记述舞蹈的人们都再三指陈这种‘令人惊叹的’动作的整齐一致。在跳舞的白热中,许多参与者都混合而成一个,好象是被一种感情所激动而动作的单一体。”(27)格罗塞《艺术的起源》,蔡慕晖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版,第170页。这里对原始舞蹈的整一的秩序和跳舞的热力的描绘,凸显了原始舞蹈的典型特质,即情感真挚、强烈,表现方式直接、大胆。《吕氏春秋·古乐篇》中又云:“昔陶唐氏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阏而滞著,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28)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梁运华整理,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00页。这里指出了中国原始舞蹈还有强身健体、宣泄情感的作用。而这种舞蹈,“无疑是具有巫术意义的”(29)刘怀荣《赋比兴与中国诗学研究》,第74页。。
因此,“比”的原始语义一开始就带有原始巫术思维的印迹。而这种巫术思维经过人的自我意识的不断觉醒而不断祛魅化,逐渐理性化。从“比”的原始语义可以看出它与“密”的亲缘关系。故段玉裁注曰:“要密义足以括之。其本义谓相亲密也。余义辅也、及也、次也、校也、例也、类也、频也、择善而从之也、阿党也,皆其所引伸。”(30)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386页。用山的“密”来解释人的“比”,把自然界事物的性质、特征援引到人身上,通过一种相似性将二者关联起来,这本身就是一种附会,是一种典型的比附、类比的思维方式。由此可以看出,从“比”的产生伊始,就包含着先民对世界认知及进行文艺创造的独特思维方式。而且从原始舞蹈的形象特征来看,“比”字的创制本身也是对现实的人事活动样态的一种比拟。因此,无论是山的“密”还是原始舞蹈的亲密性和密集性特征,无一例外都凸显了“比”字的形象化比拟的典型特征,同时还指出了文艺创造所具有的社会功能。
二 “以人合天”:“比象”思维的人文转向
然而到了殷商末期开始,这种绝对的天命思想就有了松动。王国维明确提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31)《王国维手定观堂集林》,黄爱梅点校,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247页。王国维这句话是很有见地的,非常准确地揭示了殷周之际的社会大变动所带来的文化大变革这一史实。而这一变革时期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天的祛魅与人的觉醒,而在这一此消彼长的过程中,“比象”思维的内涵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一)比象与礼
据现有史料,在殷商时期尚没有“天”这一字眼,但关于“天”的思想却已经比较成熟了,集中地体现于殷商的至上神——“帝”的相关论述之中。关于“帝”的思想的演变,丁山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论述:
在殷商时代,帝不仅为天神的专名,凡山、川、风、云一切自然界的大神,都可以冠以帝号,凡巫、娄、梦、卜一切宗教教主的先祖,也可附以帝名。到了晚期,王死之后,子孙也配于皇天而追尊为帝了。帝几乎成为天界、空界、地界以至人鬼一切比较尊重的神祇之共名。周因于殷礼,将“上帝”特尊为“皇天上帝”,将“帝五臣”也尊为“五帝”;所以周礼春官大宗伯之职,“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小宗伯之职又说“兆五帝于四郊”,分皇天与五帝为两界。周人尊祖配天,先王之名,未有冠以帝号者;而“皇祖”、“帝考”,在在证明先王措庙立主可以称帝,即公卿大夫的先祖,也未尝不可冠以帝皇之辞。再以金文作器之人拜受王赐,辄尊时王为皇君、皇王、皇天子视之,不但先王配天,即生王也比隆上帝了。(32)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第207页。
这段话对帝的概念演变进行了梳理,指出了周人对天的崇拜源于殷商对“帝”的推崇,但进行了改造,帝由独尊而逐渐被天所取代成为最高的至上神,并且对“帝”的泛化使用,使其原始神秘的宗教意涵得到了淡化,从而开始突出了人的地位。
这种人性的觉醒,从龟卜到筮占的演变就可见一斑。《左传·僖公十五年》载:“龟,象也;筮,数也。”(33)左丘明传、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807页。也就是说,龟卜主要是依据龟骨经过火烤后出现的裂纹的形象来进行的活动,而筮占则是依据蓍草的数目来进行占卜的。朱伯崑指出,二者有两点不同:“其一,钻龟取象,其裂痕是自然成文,而卦象是手数蓍草之数,按规定的变易法则推衍而成。前者出于自然,后者靠人为的推算。其二,龟象形成后,便不可改易,卜者观其纹,便可断其吉凶。但卦象形成后,要经过对卦象的种种分析,甚至逻辑上的推衍,方能引出吉凶的判断,同观察龟兆相比,又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更多的思想性。这两点都表明,占筮这一形式的形成和发展意味着人们的抽象思维能力提高了,卜问吉凶的人为的因素增加了。就这一点说,从殷人的龟卜到周人的占筮是一个进步。”也就是从这两点不同出发,朱伯崑认为,“由于《周易》筮法,重视数的推算和对卦象的分析,总之,重视人的思维能力,所以后来从《周易》中,终于导出哲学体系,而龟卜始终停留在迷信的阶段,逐渐被人们所抛弃”(34)朱伯崑《易学哲学史》,昆仑出版社2009年版,第8-9、9页。。也就是说,虽然周人还非常崇尚仍然具有迷信色彩的卜占行为,但已经大大增强了人的能动性。也正是在这种不断的推衍阐发中,人的主体意识不断凸显。随着理性思维能力的提高,这种占筮活动开始进入到了对于天地的外形和内在结构、性质、功能、意义的模拟,八卦的比象即是如此,如天尊地卑、乾父坤母等。《周易·贲卦·彖辞》有言:“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35)王弼注、孔颖达正义《周易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7页。圣人通过观察天象和人事活动的诸种现象,就可以了解时令的变化、人性的特点,从而因人施教,达到教化民众、安定社会的目的。这时候的“比象”思维,就被赋予了政治伦理层面的内涵。
陈来指出:“周人的理解中,‘天’与‘天命’已经有了确定的道德内涵,这种道德内涵是以‘敬德’和‘保民’为主要特征的。天的神性的渐趋淡化和‘人’与‘民’相对于‘神’的地位的上升,是周代思想发展的方向。”(36)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94-195页。这一点在占筮中也有非常明显的反映。陈来在对春秋占筮案例进行分析后指出:“春秋中期以前的卜筮文化和筮问活动,都没有对于德行的要求。而现在,筮问者本身的德行和筮问者将要从事的行为的性质,都成为筮问是否正确预知未来的前提条件。筮占的正确性,要求筮问者具备基本的德性,要求所问之事必须合乎常情常理。如果这些条件不能满足,无论筮占的结果如何,事实的发展和结果必败不吉。这样一来,‘德’的因素成为卜筮活动自身所要求的一个重要原则。这是以前所没有过的。”(37)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6页。也就是说,在春秋时期,“德”已经日益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因子。
其中,从铸鼎象物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窥见“比象”思维的伦理学转向的一点征兆。《左传·宣公三年》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主要记载的是禹收九州之金铸九鼎而象百物的故事,后世多用此来称颂君王的功德。杜预注曰:“象所图物,著之于鼎。”(38)左丘明传、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868页。这里象物的象其实就是前面讲的描绘、象征的意思,象物也就是依据远方民众所图之物铸在鼎上,用我们今人的话来讲,就是比葫芦画瓢,将物象铸刻于鼎上,这是其第一层含义。这就与比的意思有了一致之处。因为比就是取两个事物的相似点或者共同属性并使之发生关联。因此,这里的象物也可以理解为比物,也即比物之象。但是,“‘象物’者,并非简单地模拟客观自然存在之物……而是包含着超现实物质存在的幻想之物在内的,例如上帝、鬼、神,以至夔龙、饕餮等等”(39)敏泽主编《中国美学思想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页。。这就说明,远方图物的图物,不单指将具体的事物描绘出来,而且还包括想象之物的表现,但是想象之物又不是凭空杜撰,而是仍然以先民的生活环境为基础,因此,这种图物的活动就不是一种简单的模仿,而是经由意识的主动创造。而这种主动创造本身就是“比象”思维的典型体现,而这种描绘物象的图和鼎上的图案纹理都是“比象”思维的结果。因此,“铸鼎象物”,其首要目的就是象物,即首先是一种描绘、模仿和象征的活动。而“铸鼎象物”的第一层意思则在于“使民知神奸”,即分辨晓魑、魅、魍、魉等川泽山林中害人的精怪,这本身其实是一种宗教活动。而其最后的落脚点又在“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杜预注曰:“民无灾害,则上下和而受天佑。”(40)左丘明传、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868页。也就是说“铸鼎象物”的最终目的仍是“以承天休”,即接受上天赐予的福祉,这仍可以视作是一种对天的崇拜,这时候的天仍然带有一种神性色彩。因此,这时候的“比象”还带有某些神秘性和宗教性。但是对上下和的重视,则体现了对于等级和秩序的追求,符合农耕文明的生产要求。
但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开头说昔夏之方有德,因此远方部族才纷纷归附,将四方物种全部用图画出来送呈君王察鉴,并且上贡黄金,终促成君王铸鼎象物,既为“使民知神奸”,又是为了彰显功德。结合上下文语境,我们知道这是王孙满回答楚庄王问鼎之大小轻重时说的话。这时候的楚庄王觊觎周天子的地位,而王孙满作为使者,为维护周定王的权威,而以铸鼎象物的典故来说明君王执政在德不在鼎,已经给予这个古老的故事以新的阐释,凸显了君王德的重要性。这已经有了天人合德的思想在内了。但他最后又回到天命的立场上,指出:“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41)左丘明传、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868页。也就是说,虽然对德性有了创造性的生发阐释,但受限于所处时代,王孙满只能继续回归到天命那里去寻找根据,最后仍然还是以天命为最终依据和旨归。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比象思维的内涵虽然增加了道德伦理的维度,但仍然与原始的天命观兀自纠缠。
(二)“比象”与道
前面我们指出,在《尚书》一书中,“天”或“上帝”已不是人所不能认识的东西,反而是人能认识它,并在行动中达到自己的目的。尽管这里所说的“天”、“上帝”还是有意欲的存在,但又不能由此推论出它们就是西方基督教所说的人格神。到了与《尚书》不同的《周易》及先秦诸子出现后,开始产生了一个划时代的变化。这时候的天人观的内涵才实现了人文理性的转向。这其中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是先秦时期的主要流派,基本上奠定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基本结构和主要内涵。孔子的“吾道一以贯之”,老子的“道法自然”,庄子的“道数将为天下裂”,三人都在言说“道”,可见那时“道”已经成为当时思想的主题。而关于“道”,最具代表性的当推老子。
《老子》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里的道,老子认为是不可以命名的,也即无法用概念来加以界定的,一旦给它强行取了名字,那就不是“道”了。也就是说,“道”是不可以用概念来确切把握的。因此,这种道“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湛,楼宇烈校释为“深暗不可见之貌”。也就是说,道是深暗不可见的,连天地都不能及,以至于天帝都在其后而生。由此,道就取代了“帝”,而成为了最高的本源性的存在了。《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42)以上见: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12、14、66页。因此,天不再是最高的存在,而是要师法道,即“天法道”。由此,天也被祛除了神秘的宗教因素,成为从属于道的范畴,从而获得了形而上的哲学意义。
可以说先秦诸子思想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本面貌。余英时援引雅斯贝斯的理论,将这一时期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思想大解放浪潮称为中国的“轴心突破”。他指出:“先秦各家都是靠自己思维之力而贯通‘天’‘人’,巫的中介功能在这一全新的思想世界中完全没有存在的空间。诸子的系统性思维取代了巫的地位,成为精神领域中的主流,这是中国轴心突破的一个最显著的特色。”(43)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第41-42页。这一时期,先秦诸子纷纷提出的自己的“道”,用以沟通天人,摆脱原始巫术和传统天命观的束缚,促进了人性的觉醒。而由此形成的“天人”关系被视作一种新的“天人合一”,以与旧的“天人合一”相区分。余英时认为这种新的天人合一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道”与“心”的合一,从而实现了内向超越(44)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第56页。。也就是说先秦诸子所提出的“道”和“心”的范畴取代了旧有的天人观,而发展为以“心”比象“道”的新型天人观。道成为最高的概念范畴。无怪乎金岳霖讲道:“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似乎是道。所谓行道、修道、得道,都是以道为最终的目标。思想与情感两方面的最基本的原动力似乎也是道。”(45)金岳霖《论道》,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6页。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道”成为了中华文化传统的思想主题和核心范畴,一切都要以“道”为本源依据和最终旨归。而由于这种“道”是祛魅后的形而上的范畴,使得中国传统的天人关系实现了人文的转向,而且心成了沟通天人、物我的媒介。张岱年指出:“心为能知能觉者,人为天地间物类中之有知有觉者,故可谓天地之心。”(46)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69页。因此,心即只有人才能具有的充分自觉的自我意识,这也是人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本质所在。正因为有了心才使人成为最高贵的物种,而“心是能知能思之官,知觉是心之特殊功能,心实即认识作用,这是中国哲学家所大体一致承认的”(47)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第249页。。钱穆也指出:“全部中国史实,亦可称为一部心史。舍却此心,又何以成史?”(48)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73页。这明显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因为它忽视了决定人之心产生,并使人不同于动物的根本基础,是马克思指出的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但在肯定历史的发展不能离开心的作用这一点上,仍有其合理之处。由于人是思维的主体,思维又不能脱离心的作用,现在加上了心的条目,心、性就进入了比象思维的视域。既作为思维主体的心又作为思维对象而存在,从而呈现出中国文化中独特的思维向度,以心比象道。其实这也是人与天地自然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无论是天地自然之道,还是人伦理性之道,都是在天人之间展开的。
无论是哪一种思想,天人关系一直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问题,其发展确实是经过原始宗教的信仰阶段而逐步发展到形而上的理性层面。经过先秦诸子的改造,天基本上脱去了其神秘外衣,呈现出更多人文理性的色彩。
如《周易·系辞》所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49)王弼注、孔颖达正义《周易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76页。这时候的天,就是一种自然意义上的天,即指人头顶上的物质的天,当然也包含天象运行的规律、法则和天数的意思在内。也即是说,通过对天象、地形的观测,我们就能了解天地万物的变化,从而指导人事活动。如《汉书·艺文志》中所云:“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50)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65页。也就是说,天象的运行是有规律的,也是有一定的秩序的,人类通过观测和领会把它应用到人事活动中,就可以分辨吉凶,从而使政通人和。
但不论是具有神秘意义的天,还是自然意义上的天,都是人类赖以生存并指导人事活动的依据,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明吉凶顺人事。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比象”思维,就被赋予了更多政治伦理层面的内涵。因此,虽然“比象”思维的对象还是天地,但经过先秦诸子的创造性阐释,这时所“比象”的天地的内涵、意义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转化为哲学上具有本体意义的天。
当然,经过改造,天的内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具有了强烈的人文理性的色彩,但依然没有完全摆脱主宰之天的影子。如汉代董仲舒就仍然认为天是一切的最高主宰。尽管如此,他也否定不了《周易》所建立的,能通向人事的自然之天的思想。所以董仲舒也讲“天人相通”、“人副天数”。冯天瑜曾指出:“中国人跨入文明门槛,因未与氏族制决裂,也就没有同原始思维彻底分离,抽象思维未能从原始表象思维中剥离出来,而将初民的‘观物取象’朝精深微妙发展,形成一种特有的‘直观抽象’,在表象思维的基础上,以八卦衍化方式完成中国式的分类、归纳、概括、综合、抽象等高级思维,运用‘直观抽象’顿悟因果关系。”(51)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4页。也就是说,中国“比象”思维的形成,是在原始思维基础上的更高层面的发展。中国原始巫术在神秘形态下固有的直观性,使“比象”思维保留了巫术的形象性、想象性等特征。但又因为原始巫术可以沟通天人,具有神圣的宗教向度,以及卦象和爻象的文化符号性质,使“象”具有了超越的形上意义,使得象在后来可以与“道”、“德”、“心”等联系起来,逐渐祛除了神秘色彩,获得了形而上的理性内涵。于是,在先秦轴心突破时期,“比象”已经脱离巫术而日趋理性。
统而观之,“比象”思维强调直感,依赖于事物的具体形象,注重想象作用的发挥,同时又不脱离理性思维。此外,随着先秦诸子百家提出“德”、“道”、“心”等概念范畴,对早先的天命观予以了创造性阐发,使得天由具有情欲意志的天逐渐演变为一种道德之天和自然之天,逐渐褪去至上神层面的神秘色彩而具有了形而上层面的意义。由此出发,“比象”天地逐渐实现了人文理性的转向,从而获得了哲学、政治、伦理等层面更广泛的意涵。这种转变深刻地影响到了“比象”思维的内在结构,使“比象”思维呈现出中华文明思维方式的典型特征——“比道”。
三 “比象”的审美介入
受到哲学思想的影响,艺术很注重对道的“比象”。作为最具中国特色的艺术之一的中国书法,从诞生之初就与“比象”思维密切相关。因为中国书法的基础——汉字,就是远古先人“比象”天地万物所创制出来的。《说文解字·叙》中云:“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这段关于仓颉造字过程的描述,正体现出中国文字与“比象”的密切关联:文字的产生是先民观察鸟兽蹄迒之迹相别异而创造出来的。也就是说,从鸟兽的蹄迹我们能知道走过的是什么鸟兽,通过文字的创造我们也可以来指称我们所要认知的事物。因此,许慎讲:“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52)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754页。最初的文是依类象形的结果,而字则是形声相益的结合。这种象和形其实就类似于前面所说的鸟兽蹄迒之迹,可以由之指称人们所要表达的某种意义。“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53)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754页。。
文字的发明经历了一个由简单的物象出发,经由想象力的发挥,造出更多合体的形声字、会意字等的过程。这种文字创造的过程有点类似于黑格尔所说的人的意识的认识过程:“按照时间的次序,人的意识,对于对象总是先形成表象,后才形成概念,而且唯有通过表象,依靠表象,人的能思的心灵才进而达到对于事物的思维地认识和把握。”(54)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版,第37页。也就是说,有物象之本的文,再到形声相益的字,其实遵循的也正是由具象到抽象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有赖于理性思维能力的作用,当然更离不开想象力的发挥,因为它的发明建基于依类象形,非常注重文字的形象性。近人经常用形象性思维来指称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是有一定道理的,中国文字从而具有一种形象性的特征也就自然而然、不足为奇了。
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中讲道:
庖牺氏发于荥、河中,典籍图画萌矣;轩辕氏得于温、洛中,史皇、苍颉状焉。奎有芒角,下主辞章;颉有四目,仰观垂象。因俪鸟龟之迹,遂定书字之形。
……是时也,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创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颜光禄云:“图载之意有三:一曰‘图理’,卦像是也;二曰‘图识’,字学是也;三曰‘图形’,绘画是也。”又,周官教国子以六书,其三曰象形,则画之意也。是故知书画异名而同体也。《周礼》保章氏掌六书:指事,谐声,象形,会意,转注,假借,皆苍颉之遗法也。洎乎有虞作绘,绘画明焉。既就彰施,仍深比象。于是礼乐大阐,教化繇兴,故能揖让而天下治,焕乎而词章备焉。
《广雅》云:“画,类也。”《尔雅》云:“画,形也。”《说文》云:“画,畛也。象田畛畔所以画也。”《释名》云:“画,挂也。以彩色挂物象也。”(55)张彦远撰、承载译注《历代名画记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页。
张彦远认为,文字不是史皇、苍颉凭空的创造,而是根据河图洛书这种天之“垂象”,以及参照鸟龟之迹等“比象”的产物。汉字构造法则“指事、谐声、象形、会意、转注、假借”中的“象形”就是直接的比象产物。而绘画,在张彦远看来,与文字是同体同源的。比如《周官》教国子以六书,其三曰“象形”,就是绘画之意。原始艺术中,可以印证张彦远解释画之源流时所说的“比象”、象形,直观地认识到先民的“比象”思维。
在半坡、仰韶、马家窑等原始文化丰富的彩陶遗存上,描绘着先民生活中常见的各种动物、植物、人物的形象,很好地抓住了各种形象的特征,生动而活泼,使用的却是简略的线描和平涂技法,这一阶段的原始艺术,如张彦远所说,“象制肇创而犹略”。在其后的发展中,原始艺术进一步地精细化,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原始艺术的形象越来越具体。如中国远古的岩画,其兼具绘画与雕刻的双重特点,受限于工具、环境等,大多采取典型化的处理手法,只刻画出物象的基本形态,简洁、粗犷、明快,让人一见便知所画为何物;另一方面,原始艺术的形象越来越抽象。如龙山文化的鬶,造型像鸟,却又不是完全具象层面的鸟,而是古代以鸟为图腾的少昊和太昊部落的文化表征。因此,“比象”是一种象征性的比拟,中国文人画创作讲“意足不求颜色似”,也是由此而来的。
由于“比象”这一概念与艺术的相通性,在西晋陆机那里,“比象”这一语词就被他直接应用到诗赋创作领域里了。他在《瓜赋》中云:“五色比象,殊形异端。或济貌以表内,或惠心而丑颜,或摅文而抱绿,或披素而怀丹。”刘运好注曰:“五色比象,意谓瓜具五色,比象万物。”“殊形异端,意谓形状不同,种类有别。”(56)陆机著、刘运好校注整理《陆士衡文集校注》卷一,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110、112、113页。刘运好的注释直接援引杜预的注释,以五色比象天地万物,正是比象思想一脉相承的最好注脚。而刘运好的题解既回答了此赋的写作缘由,更是对“比象”思维的很好说明。他在题解中说:“此为状物小赋。主要写瓜德之美,生长之美,果实之丰,品种之多,形状之异,色彩之鲜,味道之醇。然此赋特别点明瓜蔓赴于广武侯之宇,其意当别有寄托。张华因力主灭吴之功而封广武侯,陆机兄弟入洛受张华之器重,而声誉鹊起,故赋之‘嘉时’、‘惠霑’、‘朗日’、‘惠风’云云,实托物以喻张华之恩惠,且亦以瓜德自况也。”(57)陆机著、刘运好校注整理《陆士衡文集校注》卷一,第103-104页。这里,瓜具五色,比象万物,既有对瓜的生动描述,更有借喻自比,显示自己的德行。这样,“比象”思维就成为了一种艺术修辞手法,既指瓜的形象,又以人的境况类比,托物言志,从而使得“比象”作为一个固定语汇进入到艺术创作领域,以至于后来者更是不断将其运用于文艺创作领域。
张衡《西京赋》云“思比象于紫微,恨阿房之不可庐”(58)萧统编《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0页。,唐吕温在《吕衡州文集》卷三《联句诗序》中云“研情比象,造境皆会”(59)吕温《吕衡州文集》,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31页。,唐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序中云“既就彰施,仍深比象。于是礼乐大阐,教化由兴,故能揖让而天下治”(60)张彦远撰、承载译注《历代名画记全译》,第4页。。唐颜师古在注释东汉班固的《汉书》时又直接援引“比象”来解释文学创作。《汉书·扬雄传》云:“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颜师古注曰:“拟谓比象也。”(61)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15页。这是班固在为扬雄作传的时候论及的,大意是说扬雄非常钦佩司马相如作赋的才华,每次作赋都把他作为榜样来效仿。拟,也就是效仿的意思。但是颜师古却将其释为“比象”,意谓比拟司马相如所作赋的诸多形象,同时也暗含有象征的意思。这正抓住了文艺创作的规律,即以比拟、象征等手法进行创作。因此,“比象”成为一个美学范畴,实在是情理之中,是思维发展的必然。至于后来人,诸如白居易、欧阳修等人对“比象”语词的使用则更为普遍,“比象”的意义也更为宽泛,逐渐成为文艺创作领域的惯常用语。
四 结论
综上,对“比象”思维的探源大概可以得出下述几点相互联系的观点。
第一,“比象”思维古已有之,而且是原初先民认识世界的重要思维方式,其产生与原始的占卜活动密切相关。
第二,“比象”思维是以天地和人类社会为首要对象和本源根据的。这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观念密切相关。
第三,“比象”作为固定语汇最早的出现与五色、五章相关。而五章、五色又体现于车服器械之中,即“车服器械”的制作具有“五色”、“五章”之美,因此能成为人的欣赏对象。同时,“车服器械”的产生存在是由“天”决定的,并非人的“虚设”。因此,车服器械的创制和欣赏就与美和艺术密切相关,并且这种美与艺术是与人生活于其中的天地不可分的。
第四,“比象”活动主要体现为比拟、效仿、象征、想象等方式,而这些方式又是艺术创作领域的重要手法,可见“比象”思维在产生伊始就充满了美的意味。同时,“比象”又有赖于现实中具有感性形象的各种对象的存在,这又使得“比象”具有形象化的特点,即不脱离形象去应用比拟和象征等手法,并使对象的美生动地呈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