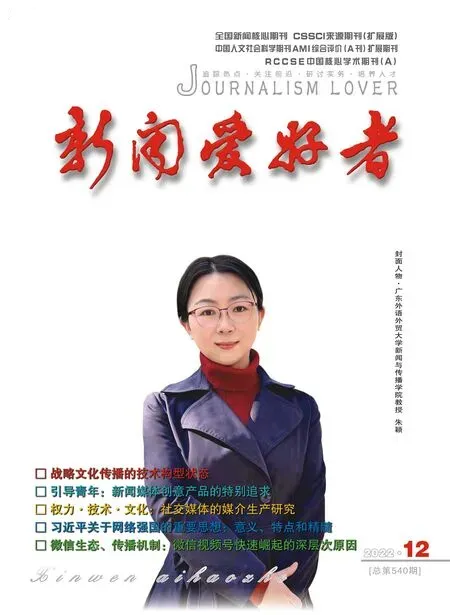用户思维下传统文化“迎合式”出圈的路径与困境
——以文化节目《舞千年》为例
□程 羽 刘 静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实力的增强, 引发了对软实力的强烈呼唤。 国家对讲好中国故事的强烈需求也引发了学界对传统文化传播的研究热潮。 为满足这一呼唤, 文化传播者开始寻找一种符合当代审美的表达方式, 借助现代话语体系对传统文化文本进行再包装, 吸引普罗大众尤其是Z 世代青年群体的广泛关注和认同。 媒体领域内,以李子柒为代表的短视频节目、 以河南卫视和中央电视台为代表创作的各类文化节目等都完成了较为成功的传统文化传播实践。 本文以文化节目《舞千年》为例,通过分析传统文化“迎合式”出圈现象及其路径与困境,试图揭示目前在“用户思维”引领下传统文化传播实践所取得的成果与不足,以促进传统文化传播实践的进一步发展。
一、出圈路径:“迎合式”出圈背后的用户逻辑
现阶段, 传统文化传播的底层逻辑大多从用户出发,无论是技术的引入还是平台的合作、流行文化的融入还是表达方式的创新, 都是基于迎合用户的某一特定心理需求而作出的传播实践, 通过对用户需求的迎合达到传统文化破壁出圈的目的。 显然,在新媒体时代,“迎合式” 出圈已成为当下传统文化传播的主要策略。 以《舞千年》为代表的一系列文化节目基于传统文化以及数字媒体自身的特点, 主要从认知满足、 审美满足和参与满足三个方面满足用户需求,从而达到文化出圈的目的。
(一)认知满足
传播层面,《舞千年》 最大的突破之处在于地方主流媒体平台与以青年亚文化为特色的短视频平台之间的“跨界合作”。 通过跨平台的方式,将传统文化引入到青年用户群体之中, 突破了青年用户与固有用户、网络用户与电视用户之间的传播壁垒,满足了用户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需要;认知层面,节目用影视展示古典舞, 并借用特效、VR 等数字技术展现舞蹈背后的文化内涵, 实现了从舞台到荧幕的媒介转变,既弥补了舞台表演在传播力上的劣势,又利用影视媒介的自身优势对古典舞表演进行再加工, 为观众理解古典舞提供可能。 两方加持使得《舞千年》有效突破了古典舞传播中的传播和认知壁垒。 同样,《典籍里的中国》等文艺节目也借用了“戏剧+典故”等思路,通过跨媒介的方式,利用不同媒介各自的特质,取长补短,实现“1+1>2”的传播效果。
通过对媒介融合的有效利用, 使得不同圈层用户之间的矛盾得以调节, 从而满足用户对于传统文化认知的共同需要, 这对于其他优秀传统文化打破圈层壁垒、实现大众性传播提供了有效路径。
(二)审美满足
传统文化与大众用户尤其是青年用户之间的“审美代沟”引发了用户对于传统文化审美需求的呼唤。 传统文化常被视为“阳春白雪”,是属于少数人的“高雅文化”。 这种刻板印象上的距离感促使用户面对传统文化会产生一种天然的“文化自卑”,并将传统文化划归精英文化的范畴。 这与新媒体时代用户与媒体之间的平等关系, 以及用户对于话语权的呼唤产生落差。 落差的产生促使传统文化进一步流失并被束之高阁,使得传统文化被符号化、扁平化,在未被用户深入了解之前就先冠上了 “老古董” 的名号。 审美上的代沟阻碍了用户欣赏传统文化的需求。传统文化要想出圈,传播者必然积极转变叙事方法,打破传统文化与大众用户尤其是青年用户之间的“审美壁垒”,从而实现用户对审美需求的呼唤。
《舞千年》通过分析现代用户的审美方式,赋予古典舞以当代性的表达。 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叙述形式的创新。 古典舞作为一种抒情性的艺术形式,要求观众有较高的情感敏感度和艺术欣赏水平。 为了降低审美门槛,节目导演通过转变叙事模式,将舞蹈中的抽象情感具象化为身份特点鲜明的人物故事,并运用影像语言帮助大众捕捉 “应当注意的部分”,使用户能够更加轻易地接受并欣赏舞蹈背后所蕴含的古典美与情感美; 共情化也是传统文化现代性叙事的主要手段之一。 以《赵氏孤儿》一舞为例,主人公悲惨经历的展现, 引发观众对历史记忆的追溯与情感记忆的共鸣。 通过挖掘传统文化背后共通的文化符号和情感符号,为观众创造一个共同意义空间,帮助观众理解其背后的文化内涵。
(三)参与满足
用户需要推动媒体身份转变。 与传统工业时代的受众不同,互联网时代的用户更加主动。 他们不再满足于一味地被动接受,而是渴望亲自“下场”参与其中,近距离地与创作者进行交流和共享。 这意味着传统文化传播不仅要注重创作的单向传播, 更要关注用户的参与暨实践, 推动用户与传播者之间的双向互动,从而拓展传统文化的传播空间。
《舞千年》将“十二风舞志”12 支舞蹈的最终决定权交给观众,并在播出时加入弹幕、评论等互动形式,使得观众能够实时发表自己的感受、与节目制作和参与者直接进行线上互动。 这种实时互动、间接参与的传播理念, 打破了以往传统文化传播的单向规则,将接受者摆在了与传播者几乎平等的位置,最大限度地保证了观众的体验感,做到了使“‘体验’取代文本的‘阅读’‘观看’”[1],满足了用户对“身体在场”的需求。
当然,仅仅是传播过程中的双向互动,还不足以达到现代用户对于参与的强烈需求。美国学者亨利·詹金斯提出了“参与式文化”这一概念。 他将粉丝视作积极挪用文本,并以不同目的重读文本的读者,把观看电视的经历转化为一种丰富复杂的参与式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的观众。[2]也就是说,在数字化时代,用户“不再仅仅是流行文本的观众,而是参与建构并流传文本意义的积极参与者”。[3]用户不仅渴望拥有实时反馈、互动的权力,还进一步呼唤个体对于文本的选择性理解与再创。 《舞千年》播出后,节目制作方立即在微博上发起了# 你心中的舞千年#话题活动,鼓励观众对节目内容进行二次创作,大大激发了用户的创造力, 满足了用户对于主动性参与的需要。 用户通过自主选择、自主加工的方式对节目文本进行再创造、再传播,提取出传播内容中为自己所爱的文本材料,通过剪辑、漫画、表情包等实践,给传统文化套上其所在圈层习以为常的外衣, 吸引圈层关注助力文化传播的同时,也在“文本盗猎”的过程中为自己收获了更多的流量和创作素材。
二、出圈困境:“迎合式”出圈的现实困境
一系列传统文化传播的“迎合式”创新实践在用户层面激起了较大的水花, 受到广大群众的普遍好评,值得我们欣喜和赞扬,但其创新实践背后所隐含的一系列风险和问题也不容忽视。 显性层面,众多文化“迎合式”传播实践的成功范例背后出现了一批将传统文化视作迎合用户的流量密码的传播乱象。众多文艺作品将传统文化作为收视率的“敲门砖”,不顾及传统文化本身所具有的深厚内涵,囫囵吞枣式进行借用和加工,制作出一批打着宣扬传统文化旗帜的低俗作品。此类错误范例的出现为众多侥幸者提供了可乘之机,致使传统文化传播的粗制滥造之风露头。
但就社会影响力而言, 显性层面的风险具有易识别、易整改的特质,其危害力和影响力远小于传统文化传播中的种种隐性危机。 就传统文化“迎合式”传播而言,隐性危机的形成超越了人为层面的因素,往往缘起于传统文化自身的特性与当代话语体系之间的矛盾,常于潜移默化之中对观众造成较大影响。这两种风险造就了“迎合式”出圈的现实困境。综合考量两种风险,“用户思维”造就的“迎合式”传播策略在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媒介个性的消解
全媒体时代,各种媒介形态的融合趋势,促使传播内容在多种传播媒介之间不断流转,其流转次数之频繁、流转方式之便捷使得人们忽视了媒介本身所带来的独特“讯息”,造成信息在传播过程中的流失。
以《舞千年》为例,作为传统文化的古典舞有着自己的独特媒介——舞者的身体。 身体媒介的特殊性决定了其特殊的传播效果, 即观者身体在场所获得的某种“通感性”体验。这种特殊体验本身就构成了古典舞文化内涵的一部分。而数字技术对古典舞的呈现则无法保留现实在场带给用户的独特感受,从而消解了这种独特的体验。 除此之外,影视语言本身也部分消解了古典舞想要传递的美学意义。 如特写、中景等运镜手段的使用使得观众只能通过机器代替人眼进行观看,使得影视媒介无可避免地对古典舞进行二次塑造, 这种二次塑造必然会带来古典舞内涵的消解。 不仅是《舞千年》,包括优酷推出的《中国潮音》中传统乐器与特效舞台的结合,以及《青春守艺人》中杂技、 京韵大鼓与影视舞台的结合中都能够看到这一问题。 不同媒介的融合如果不能够保有原本的媒介特质,往往会造成喧宾夺主,甚至“1+1<1”的结果。
(二)多义性的消解
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决定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文化符号具有无可比拟的多义性。 但现阶段,由于传统文化的传播受制于媒介特性以及传播目的,传播主体往往仅侧重于对传统文化某一侧面进行解读,或通过转变其文化意义的方式进行现代化包装。在满足现代用户审美的基础上忽视了传统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多义性和独特性特质。这种扁平化的传播倾向,易使观众形成对于传统文化的片面性理解, 从而造成传统文化多重内涵在用户解码层面的消解和扭曲。
《舞千年》中对于传统文化现代性表达的背后就存在着对于古典舞丰富内涵的消解和扭曲。 《踏歌》作为汉代流传至今的传统舞蹈之一,敛肩、含颏、掩臂、摆背、松膝、拧腰、倾胯是它所要求的基本体态,舞者在身体各个部位的流动之中完成对舞蹈动作的诠释, 这种动作的集合性和整体性要求观众从整体上去欣赏舞蹈的呈现, 但影视创作为了避免画面效果的单一化给观众带来视觉疲劳,频频变换镜头,频繁的运镜切碎了《踏歌》呈现的整体性表达,使得舞蹈的内蕴被大大消解。 除此之外,节目将影视文学与舞蹈艺术融合来寻找为现代大众所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 这种叙述方式创新的背后隐含着两种艺术形式创作原则和基本理念的背离与矛盾。 以《踏歌》为例:《踏歌》本来是汉代人民为了表达一种“达欢”的精神母体所创造的一种身体语言,在《舞千年》中却被简单地局限在了少女及笄之日的种种少女思绪之中。 在《唐宫夜宴》、中国节日系列节目以及一些早期的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节目实践中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即只强调了“形似”,而忽视了传统文化内在精神内涵的“神似”。 形式与内容上的本末倒置,使得用户只能接收到片面的、符号化的内容。
(三)严肃性的消解
当下,泛娱乐化大行其道,传统文化的传播往往陷于消费主义的泥潭,丧失了基本的价值坚守,使中华文明赖以生存的根脉遭到消解和扭曲, 大大消解了传统文化应有的严肃性。
这种严肃性的消解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来源于传播方。 传播者为了吸引用户眼球、 营造节目“爆点”,对传统文化进行曲解和恶搞。 如《欢乐喜剧人》恶搞花木兰、周立波丑化汉服等事件都反映了部分节目为了迎合市场、“博用户一笑” 而刻意抹黑传统文化的恶劣倾向。二是来自于用户方。传播者为了吸引、迎合用户,刻意降低用户的再创作门槛,放任用户对节目内容本身进行恶搞, 致使传统文化在再传播的过程中被不断叠加抹黑, 造成其在某一圈层内的“丑化”出圈。 以参与式文化实践为例,用户对传统文化的二次创作中,常常将青年亚文化和网络流行文化融入传统文化的再传播之中,在扩大其传播力的同时,也消解了其本身所具有的严肃性。当然,我们不否认文化融合式创作中存在对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的成分,但在更广阔的社会语境之下,传统文化严肃性的丧失,使得这种创新性发展得不偿失。
追本溯源, 这两种消解方式的背后是传统文化传播者对自身定位的模糊。 新媒体时代,媒体与用户之间是相互平等与相互监督的关系, 而非迎合与被迎合、讨好与被讨好的关系。 消费至上的观点在大众传播中不能完全适用。 一旦滥用消费主义观念,“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 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 传统文化成为“娱乐的附庸”,“最终我们变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4]要想避免“娱乐至死”时代的到来,传统文化的传播必须冲破片面的“迎合式”传播思路,打破泛娱乐化思想的壁垒,以一种平等的姿态面对观众,保持自身基本的价值准则。
三、结语
现代性语境下,“迎合式” 出圈从用户的视角出发,通过“分析—满足”用户需要,积极拥抱新的话语体系、迎合当代用户、占据传播市场,从而走上符合时代语境的实践道路,并取得了不小的实践成果。 这一实践尝试为传统文化出圈提供了有益且有效的思路。 但我们也必须意识到,现阶段传统文化“迎合式”传播实践并不成熟,“误入歧途”的现象仍时有发生。因而, 通过追本溯源的方式寻找突破困境的有效手段, 从而实现自身的进一步发展是非常必要且急迫的。 当然, 想要真正实现传统文化在各个层面的出圈,真正推动传统文化重展光芒、走上正路。 无论是传播者还是用户都应该积极参与到传统文化传播中来,不断突破传播实践中所隐含的一系列困境,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和手段、发挥各界智慧,将传统文化传播引向更宽、更远的道路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