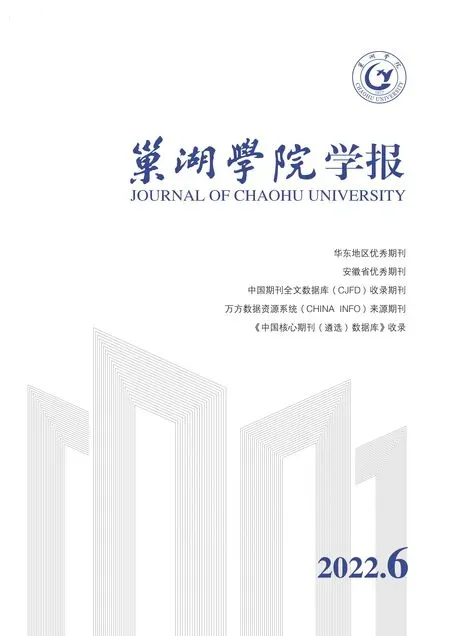译者角色化与林译“讹”的再研究
——以《冰雪因缘》为例
汪 琳 余荣琦
(巢湖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巢湖 238024)
引言
林纾在二十余载的翻译生涯中,译介了近二百部、涉及十余个国家、百余位作家的作品,涵盖军事、言情、政治、侦探等多种类型,成为我国近代译介西洋小说第一人。林译小说风靡一时,成为晚清国人开眼看世界的重要窗口,对中国翻译史、文学史和文化史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然而林译的“讹错”不断,又受到诸多学者的指摘和诟病。刘半农就曾公开痛斥林译文的谬误,郑振铎也直言林译小说有自行增删的坏毛病。直到钱锺书指出“这部分的‘讹’起了一些抗腐作用,林译多少因此而免于全部被淘汰”[1],后世学者才开始重新审视林译之“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更是为重新评价林纾及其翻译之“讹”提供了开阔的视野。尚文鹏、刘洪涛和吴小琴等多位学者[2-4]从社会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等不同角度阐释林译“讹”的合理性和创造性,为其正名。无论是语言层面对林译“讹”的片面判断,还是文化层面强调话语、文化等外在因素对林译“讹”的操控,这些研究往往忽略了译者自身的个人经历、文化身份等因素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性。
随着翻译研究的“译者转向”,译者从幕后走向台前,学界也更关注对“译者身份”“译者角色”“译者惯习”“译者伦理”等的研究。只有让译者在译作生成过程中“现身”,才有助于看清译者在翻译活动的“中心”地位,也才有可能避免对译者翻译活动复杂性的视而不见。鉴于此,文章从译者角色化出发,以林译《冰雪因缘》为例,探究林纾译者角色化过程中各种“讹”的表现形式和生成机理,认为林纾为实现务实性社会目标而不断迎合社会、调整和改变自己的社会人角色,其各种角色相互交织,互为补充,形成了林译的“讹错”景观。译者角色化研究顺应了翻译研究的“译者转向”范式,有助于进一步理解译与非译的关系,是进行翻译批评的一个有效途径。
一、译者行为批评与译者角色化
译者行为批评是我国学者周领顺经过十年的学术积累和沉淀,逐步发展和完善的以译者和译者行为为切入口来认识翻译的本土化理论。该理论一经提出,就引起了翻译学界的广泛关注,更是受到了许钧、刘云虹、王克非等译界知名学者的高度评价,认为其为“翻译研究开展的有效性提供了可资深化的主题”[5],极大地丰富了国内本土的翻译批评研究。
译者行为批评注重“以人为本”,兼顾了翻译内与翻译外、译者的语言性和社会性、翻译和非译等文本视域的研究,有助于对译者行为和译文质量作出更为合理、全面的评价。“角色化”是该理论的一个重要批评术语和核心概念。所谓译者“角色化”,是“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借翻译实现务实性社会目标而进行的不断迎合社会、调整和改变自己社会人角色的过程”[6]。周领顺指出译者兼具语言性与社会性的双重属性,决定了译者“语言人”和“社会人”的双重角色。这与谭载喜对译者主次身份的划分殊途同归,都强调译者并非扮演单一角色,用一种声音讲话。与之相反,译者会把抽象的、静态的译者角色融入到动态的、与不同社会因素和环境密切互动的社会人角色之中。具体到“怎么译”上,译者通常会采取严复所谓的非正法(偏法、变法、变译)翻译方法;具体到译文上,译文往往会呈现出语言性翻译成色的减少和社会性选择性翻译成分的增多,即译文总会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也会违背或不太贴近原文。从译者角色化来看,这些失真和走样往往是译者采取的一种积极的翻译策略,体现了他们在翻译活动中的社会人属性以及翻译的社会化过程。承认译者角色化,有利于看清译者在复杂的翻译活动中所真正体现出的权利和义务,也有助于理解译文中会有“译”和“非译”的成分[7]。换言之,对译者角色化的研究,有助于认清译者超越传统语言对等意义上的非译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译者多元角色和译文多样性。
二、林纾的多元角色与《冰雪因缘》之“讹”
林纾个人丰富的生活经历、教育背景使其能文、能诗、能画,共同构建出林纾的多元身份,如古文家、文学家、画家等。这些多元身份融入到林纾的翻译活动中,使其呈现出多元角色特征,扮演着操控者、协调者、创作者等各种临时可变的非译者角色。这些角色虽然使林纾游刃于原文和译文之间,但也易使其摆脱原文的桎梏,造成译文与原文语言、内容、形式或主题的不对等,形成各种“讹错”景观。下面将从文学叙事、伦理道德和视觉审美三个方面来探究林纾译者角色化过程以及其对译文“讹”的合力作用,从而客观地理解和评价其译者行为和翻译效果。
(一)林纾的古文家角色与叙事之“讹”
林纾一生学习、研究、讲授和捍卫古文,对史传等经典文学更是熟记于心,运用自如,称得上是一位古文家。凭借其深厚的古文造诣和超强的文学感悟力,他常以读史传方法理解和欣赏原文的谋篇布局,认为外国小说“往往于伏线、接务、变调、过脉处,以为大类吾古文家言”[8],并叹曰“西人文体,何乃甚类我史迁也”[8]。可见,林纾不是以单一的、静态的译者角色走进另一个文本,而是在文本解读中融入了古文家角色,从而对原文部分叙事进行古文化的调整和改造,以照顾士大夫阶层和晚清知识分子的阅读口味。
第一,增加文内标注。身为古文家,林纾常用古文中“伏脉”观念去理解狄氏小说中的隐性预叙。所谓隐性预叙,即读者需要读到下文时才能发觉前文是在预先透露后来的情节。他指出狄氏之文“伏脉至细,一语必寓微旨,一事必种远因”[8],又认为其文“盖于未胚胎之前已伏线矣”,“往往潜用抽换埋伏之笔而人不觉”[8]。这里所谓的“伏脉/伏线”“埋伏之笔”,都指向狄更斯的隐性预叙与古文的“伏脉”有相通之处,具有“猝观之实不见有形迹”[9]的叙事效果。因此,林纾会在译文内以加注“伏线”的方式来提醒读者关注后文中人物、事件的发展。纵观全文,他在《冰雪因缘》的多个章节(第 4、5、18、19、30 章)都做了这样的标注。以第30章为例,林纾在“爱迭司,汝能于此时死者,正为其时。盖眼前尚有一人足施其爱,若求以天年终者,则前路均严冰矣”[10]一句后增加了“伏线”的标注,为后文情节埋下伏笔——爱迭司最终与情人私奔,身败名裂,孤独终老。虽然文内标注改变了原文的悬念设计,但有助于减少读者的阅读障碍,增加读者对原文情节的理解和期待。
第二,增加史家的叙事口吻。“外史氏曰”是外史或野史作者在写作中采用的一种称谓,同《史记》中的“太史公曰”和《左传》中的“君子曰”一样,用于发表议论、表明写作宗旨,抒发对故事中人物、事件的情感倾向以及揭示对人生、社会的感悟等。受史传传统的影响,林纾会在译文中嵌入史家的干预叙事口吻,以“外史氏曰”的方式与读者交流读书心得。以第39章麦克斯廷厄太太好不容易找到卡特尔船长,破门而入的情景为例。原文写道:
How the captain,even in the satisfaction of admitting such a guest,could have only shut the door and not locked it,of which negligence he was undoubtedly guilty,is one of those questions that must for ever remain mere points of speculation,or vague charges against destiny.[11]
流露出叙述者对船长即将遭受麦克斯廷厄太太的指责和辱骂的同情。而林纾译为“外史氏曰,吾乃不审船主如此精审之人,胡以今日迎迓其良友,乃忘拴其门,得此巨祸,良天意也。”[12]“外史氏曰”的增译淡化了原文叙述者说故事时的情感流露,增添了译文的史传色彩。叙事者仿佛变成故事外冷静的叙事观察者,口吻更加含蓄隐晦。
第三,删减大量描写,重塑古文简练之风。狄更斯的小说中不乏场景描写,也不乏对小说中荒诞人物的外貌描写及心理描写等。身为古文家,林纾深谙“喋言成絮,弊在不知举其简要”,便“弃其骈枝耳”[9],有选择地删去大量细节描写,最大限度地实现古文的雅洁和精练之风。在第1章,原文花了大量笔墨描述讨克司小姐的容貌、神情、服饰、动作等,而林纾在整体上把握了讨克司小姐出场时滑稽、荒诞的形象之后,就粗其人文大略,摘其精要述之:“讨克司长瘦人也,衣服半旧,貌至足恭。平日好闻耳语,故倾其首,因而永永其首皆微偏”和“其鼻本如悬胆,所恨半道复突一峰,遂将峰内钩,成为鹰啄之状”[13],译文不及原文的三分之一。在第48章,林纾又简化了佛罗伦司离家出走时沿途的街头场景,转以三两闲笔“次日乃大出,人声亦大喧”,使“孝女遂直前行”和“孝女左右初无所见,遥遥已见木偶人矣”[14]这两组情节相扣起来。改造后的译文句式短小精悍,读来颇有古文风韵。美国汉学家韦利就十分赞赏林纾的大量删减,认为“原著中所有过多的细节描述、夸大的叙述和喋喋不休的饶舌都消失了”[15]。
综上观之,无论是对原文叙事结构的补充说明,还是对原文叙事口吻的改述,又或是对原文叙事描写的大量删减,严格意义上来说都是一种“讹”,是林纾对原文叙事的各种“不忠实”。这与其说是林纾以译者角色直接处置文本,不如说是其译者身份下古文家角色对小说文本的介入,是“译者很大程度上以非译者的角色或者超越翻译的角色而有条件地对‘原文’的再分配,是对译文的处置(不完全是翻译)”[6]。据统计,晚清小说的读者大都“出于旧学界而输入新学说者”[16]。这些旧式文人多浸润于传统文学中,林纾古文化的叙事风格符合传统文学规范,更容易赢得他们的青睐。换言之,林纾对原文的改造是为迎合读者阅读习惯和审美需要而采取的一种积极的翻译策略,凸显了其社会人本质。从翻译效果上看,其用中国传统文学形式包装西方文学的手段,给晚清读者似曾相识之感,有利于域外文学在目的语社会的接纳和吸收[17]。
(二)林纾的儒生角色与伦理阐释之“讹”
林纾深受正统儒家思想的影响,注重宣扬传统道德,捍卫儒家正统。至老年,他仍就儒学的存废问题与新文化文人展开笔伐。他一生虽未入仕途,但“以其大半生非科举应试,即传道授业的身份来说,判其为‘业儒’也并不为过”[18]。林纾儒生角色融入翻译活动中,促使其用中国的伦理道德标准去阐释或改造西方观念,捍卫儒家传统伦理。
第一,用“孝”置换基督教观念。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狄更斯作品中的重要元素。其中,对狄更斯影响最大的就是基督教博爱精神。他的每一部长篇小说都宣扬“爱”,也塑造了不少天使般的形象。在《冰雪因缘》中,佛罗伦司就是“爱”的天使,有着未受玷污的纯洁心灵。她就像一盏明灯,用爱给予弟弟保罗光明和温暖,用爱唤回冷漠自私的父亲,令他回归到家庭生活中。而在林译文中,这种世间血浓于水的手足之情、父慈子爱被升华到“孝”的伦理高度,佛罗伦司的“天使”形象变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女形象。在第48章和第49章中,林纾不仅频频直呼佛罗伦司为“孝女”(多达二十余次),映射佛罗伦司之所为均“为孝感所逼”[14],更借他人之口来赞叹其“孝”,称“佛罗伦司之心,万年不变,孝行令人生感”,“非但女也,且贤女而孝女”[14]。如此一来,原文内嵌的宗教博爱精神被置换成以“孝”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伦理,实现了对佛罗伦司“天使”形象的“孝女”改造。这样的改造有利于认识到“西人不尽不孝矣,西学可以学矣”[8],从而让晚清读者顺利接受西学。
第二,以“礼”和“义”阐释人物言行。林纾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礼”和“义”的道德伦理观深深烙印在其思想中,在林译小说中出现频率极高,几乎每部小说中都可见。一方面,他会用极具儒家色彩的“礼”来阐释长辈与晚辈之间、夫妻之间、朋友之间的各种行为规范,“执手为礼”“接手为礼”“引手为礼”等与“礼”相关的表达频频出现在译文中。另一方面,他会赋予小说人物“义”的价值取向,在他们身上构建儒家精神的理想人格。倭而忒远赴印度时对船长说:“I don't mean to say that I deserve to be the pride and delight of his life—you believe me,I know,but I am.”[11]原文表达的是倭而忒担心自己走后,伯伯会因失去他而大受打击;林纾却将之译为“吾未有图报之期,而伯伯乃施其奇爱”[19]。佛罗伦司的“God bless you,dear,kind friend!”[11]也被译为“佛罗伦司报之以礼,呼之为恩人”[14]。可见,林译中的“图报之期”和“恩人”均为原文所无,是林纾将“知恩图报”的中国传统美德注入人物的言行之中。他认为伯伯对倭而忒有养育之恩,卡特尔对佛罗伦司有救命之恩,理应回报。这反映了林纾将“义”作为判断是非善恶的价值规范、人们立身处世的根本和有节操之人应坚守的“道义”。
林纾用自己熟悉的儒家伦理改写原文的基督教思想和内容,可以看作其儒生角色融入到翻译活动中,与社会因素和文化环境进行互动的结果,凸显的是其社会人角色。为求译文之用,林纾常会“稍为渲染,求合于中国之可行者”[8]。具体到译文的伦理价值观上,表现为其改造或者调整原文部分思想或内容,使之符合中国文化的价值规范。为此,他有意淡化原文的基督教观念,而强化中国传统伦理的“孝”“义”“礼”,以迎合中国的传统道德和个人伦理需要。历史证明,这种为外国观念套上中国伦理外衣的做法,既有助于目的语地的中国读者接受西洋小说,也避免了译作有悖道德准则、违反礼防而受到社会的谴责。
(三)林纾画家角色与符际翻译之“讹”
狄更斯的小说都配有插图,每幅插图都突出了小说中的重要场景、人物及故事情节,成为其小说的精彩组成部分。这些插图不仅成为当时目不识丁的下层英国人民领略原文大意的重要手段,也成为不识“蟹行文字”的林纾捕捉原文风格、人物风貌的重要途径。林纾曾因看到《拿破仑传》中气势恢宏的数幅图画而欲译之,他会特别留意狄更斯小说中的插画就不足为奇了。插画成为连接林纾的画家角色和译者角色的一个重要符际通道,也为其因符际翻译(非语言符号转化为语言符号)而产生的“讹”提供了重要线索。
第一,增添小说人物的外貌特征。狄氏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丰富,且特色鲜明。虽然狄更斯对人物动作、衣饰等做了描写,但具体到插画上,插画师仍需在人物外貌的具体细节上下功夫,以使人物更加立体饱满,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船长卡特尔就是其中之一,他为人热情,言行滑稽可笑。请看图1:

图1
At these words Captain Cuttle,as by an involuntary gesture,clapped his hand to his head,on which the hard glazed hat was not,and looked discomfited……
……Again the Captain clapped his hand to his head,on which the hard glazed hat was not,and looked discomfited.[11]
语至此,船主以手自摩其顶,顶毛已秃,然惶恐之状已露。……船主又摩其秃顶,状至惭悚。[10]
通过对比原文和译文,可以看出林纾将原文中“on which the hard glazed hat was not”略去不译,在译文中增添了“顶毛已秃”“摩其秃顶”的外貌细节描写。乍一看,原文与译文出入颇大,但结合原文插画,就能明白林纾的良苦用心。画中船长正用左手铁钩挠头,几根稀疏的头发散落于船长头上,显得十分滑稽可笑。林纾丰富的作画作文的经验使其深谙绘画当同“欧公之文学昌黎……善于传摹移写”的道理,也赞同“顾长康颊上三毫,其妙理为人叙述不出者,此则专在神会矣”[9]的做法。于是,为了突出船长的滑稽之态,林纾添枝加叶,强调船长的秃顶,既让读者加深了对这个人物的印象记忆,也为译文增添了幽默风趣,达到了其所谓“移貌而取神”[9]的目的。
第二,夸大或增添小说人物的动作。林纾在阅读古文和史传时喜欢留意原作中不经意流露出的风趣,指出“风趣者,见文字之天真;于及庄重之中,有时风趣间出”[9]。连写古文也要追求风趣的林纾,翻译时看到原文的滑稽插画,难免手痒心动,为作者代劳,以增加小说的幽默感和戏剧化。再以上文提及的麦克斯廷厄太太带着她的孩子们找到船长的情景为例。找到船长后,她大吼大叫,孩子们又哭又闹,船长欲避而远之。这一场面夸张得像在上演一场闹剧,诙谐感十足。插画师将这一闹剧在插画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活灵活现。请看图2:
But,the moment Captain Cuttle understood the full extent of his misfortune,self-preservation dictated an attempt at flight.Darting at the little door which opened from the parlour on the steep little range of cellar steps,the captain made a rush,head foremost,at the latter,like a man indifferent to bruises and contusions,who only sought to hide himself in the boss of the earth.In this gallant effort he would probably have succeeded,but for the affectionate dispositions of Juliana and Chowley,who,pining him by the leg—one of those dear children holding on to each—claimed him as their friends,with lamentable cries.[11]
其始但震恐,后乃自顾性命,遂夺门而逃。复室中有小门,通地窖。船主启之,且下,然后襟及股咸为周利亚及却而司所执。[12]
林纾虽然没有逐字逐句将原文译出,如省略了修辞语句“like a man indifferent to bruises and contusions,who only sought to hide himself in the boss of the earth”,但原文的戏剧性却不减分毫。“self-preservation”被译为“自顾性命”,给人一种船长正处于性命攸关之际的感觉,而“夺门而逃”的“夺”字更是突出十万火急,渲染出事情的严重性。在林纾的经营下,船主“启之”和“且下”这一连串的动作让读者身历其境,烘托出船长在开门逃走的那一刻被两个孩子抱住,动弹不得的滑稽场景。这样的改造使一个惊慌失措、急于奔命的人物形象呼之欲出,有利于让读者透过译文,领略原文“虽可哕可鄙之事,一运以佳妙之笔,皆足供人喷饭”[8]之妙。
林纾多年的绘画经验和画家眼光赋予其敏锐的艺术鉴赏力,也弥补了其不通西文的劣势,使之能够透过狄氏小说中的插画捕捉到原文的幽默风趣。他充分发挥画家角色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将原文插画中蕴含的意义以语言形式表达出来,造成了种种偏离原文语言,却与原文插画细节相吻合的“讹错”现象。正如林元彪所言,林纾把插图的视觉效果直接写进译文,才导致译文与原文不合[20]。从译者角色化来看,林译的这些“讹错”正是其画家角色融入翻译活动时留下的意志体译者的行为痕迹,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其多方面的才能。总之,林纾的看图翻译与原文插画有异曲同工之妙,令人物形象更加生动,增添了译文的幽默风格,亦有助于读者透过文字领略原文的人物风貌和诙谐的文风。
三、结语
林纾虽然以译介西洋小说闻名于世,但其古文家、儒生和画家等多重身份角色在其翻译活动中的作用不容小觑。这些角色相互交织,互为补充,在译文中留下各种行为痕迹,对林译的“讹”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古文家角色促使其对原作叙事进行古文化的叙事改造,儒生角色推动其对西方观念进行传统伦理的改造,画家角色又助其看图改写,再现原文风格。林纾的多元角色,使他不囿于原文的束缚,巧妙通过各种增删改的策略化解翻译中因语言不通、文化不同而造成的各种冲突,如文化缺省、艺术审美、意识形态等,从而顺利地将译本融入到晚清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达到传播西学、维护传统的翻译效果。文学翻译绝非简单的字面对等,而是原语和译语两个文化系统之间的碰撞和协调[21]。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大背景下,一个理性的译者应该在文化碰撞和协调中做一个能够诠释不同角色的“千面人”,而不是一个只关注语码转换的“工具人”。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对外传播,译者应具备多元的教育和文化背景、化解中西方语言文化差异造成冲突的能力。
—— 百年林译小说研究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