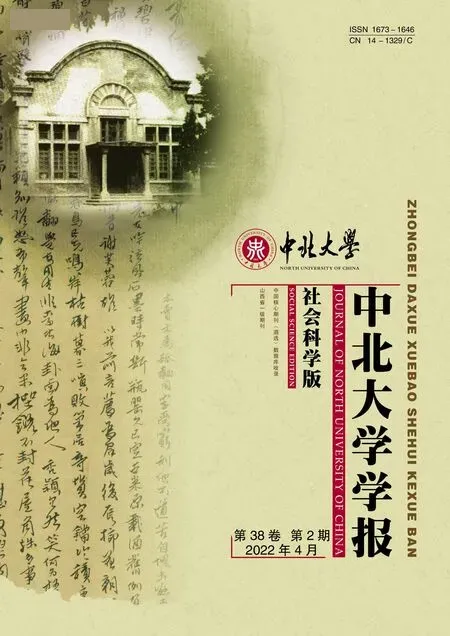“赏”的意蕴转向与六朝文风新变
——兼谈刘勰“正奇”文学观
隋雪纯
(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 北京 100871)
“赏”内涵的变动与转换, 与古代文学创作和文论的自觉与发展有着重要关联。 诞生于文运转关之中的六朝, 刘勰《文心雕龙》在条理文章思致、 抉摘品式利病的同时, 也对“赏”的意义之变有着洞见与发现。 从“赏”的意蕴转向中, 可以窥见六朝文学创作、 观念的承变特点。 本文拟从《指瑕》篇的论述切入, 在考索字句、 诠解篇意的基础上, 以“赏”字的意蕴转向为线索, 考察文学创作及观念的流变, 并在文学时风与《文心雕龙》的冲突中, 对刘勰思想特点作进一步的考察, 以及处于转型期的六朝文学理论与创作之间的互动。
1 “赏际奇至”之“赏”考辨
《文心雕龙·指瑕》篇, 旨在论“虑动难圆, 鲜无瑕病”。 其中有语段谓:
若夫立文之道, 惟字与义。 字以训正, 义以理宣。 而晋末篇章, 依希其旨, 始有赏际奇至之言, 终无抚叩酬即之语, 每单举一字, 指以为情。 夫赏训锡赉, 岂关心解; 抚训执握, 何预情理。 《雅》《颂》未闻, 汉魏莫用, 悬领似如可辩, 课文了不成义, 斯实情讹之所变, 文浇之致弊。 而宋来才英, 未之或改, 旧染成俗, 非一朝也。[1]496
其中, 关于“赏”及“赏际奇至”一句, 《指瑕》所论未详, 注本亦多从简, 如范文澜《校注》云:“此节所论, 未得确解”[2]642, 黄侃《札记》云:“‘赏际奇至’ ‘抚叩酬即’二语, 今不知所出”, 王运熙、 周锋《译注》释为“无考, 其意不详”等。 有所诠解者, 亦论说纷纭, 总而视之, 可归纳为两种观点:
第一种, 将“赏际奇至”列为四个字。 向长清《浅释》云:“开始有‘赏’‘际’‘奇’‘至’这样的字眼, 后来又有‘抚’‘叩’‘酬’‘即’这样的语言。” 祖保泉《解说》认为“始有赏际奇至之言, 终无抚叩酬即之语”是从“八个单词”的角度来阐述问题, 并逐一考求本义和晋宋以来使用失范的用例, 指出:“在晋宋人的诗文中, 赏、 际、 奇、 至、 抚、 酬、 即八个字……有超越常规的用法”, 刘勰认为晋宋文士对此八字使用不当, “导致文章含义不明”[3]782。
第二种, 将“赏际奇至”视作整体呈现意义的语段, 意义约指赏评文章之时, 内心产生惊奇之感。 如张立斋《注订》云:“此言文成当赏鉴之际, 而有惊奇高至之感, 至犹致也。” 李曰刚《斟诠》亦称:“赏际奇至, 犹言‘赏会奇致’, 亦即‘欣赏领会奇异情致’之意也。” 范文澜同持此论, 并认为刘勰此论与举一字以“赏”的风气在六朝的兴盛有关, 王运熙、 周锋《文心雕龙译注》论“赏际奇至之言”谓:“从下文‘赏训锡赉, 岂关心解’之语推测, 大约是指‘赏’用作爱赏之类的意思而违反了赏赐的本义。”[4]408
笔者以为, 以上两种观点皆各有依凭, 也有其逻辑未自恰处。 第一种观点最大的问题在于擅自改字。 此说解释成立的逻辑前提, 乃在于将与“有赏际奇至之言”属并列结构的“无抚叩酬即之语”[1]501之“无”改作“有”。 改字的做法最早由黄侃《札记》提出, 铃木虎雄亦谓“无”作“有”义长, 王利器《校证》、 王运熙《译注》、 祖保泉《解说》皆据改。 笔者认为不当改作“有”, 首先, 从《文心雕龙》的骈体行文方式来看, 并列结构句式相仿如《养气》“若夫器分有限, 智用无涯”、 《宗术》“虽前驱有功, 而后援难继”、 《物色》“然物有恒姿, 而思无定检”等, 均以“有”“无”相对; 更重要的是, 此种改字并无版本依据。 合以上两点来看, 第一种解释的合理性有待商榷。 第二种诠释将“赏际奇至”作为缩略句, 意义不够晓畅完足, 且与后文对“赏”“抚”的单字训义的强调难以合契。 故亦存在一定问题。
依笔者拙见, 通过与后文“每单举一字, 指以为情。 夫赏训锡赉, 岂关心解; 抚训执握, 何预情理”合而观之, 此处应当着意于强调“赏”和“抚”的字训, “际奇至”和“叩酬即”为刘勰给出的语义场, 意在助益理解“赏”和“抚”的具体意义。 从“始有赏际奇至之言”与《指瑕》篇前后文意的关联考察, “终无抚叩酬即之语”与之属同一语义层, 就疏通句意而言, 笔者以为当从“抚”本训考释入手。 “抚”, 《说文》:“抚, 安也。 一曰揗也。 又: 揗, 摩也。”[5]315《诗经·蓼莪》有“抚我畜我”[6]987, 先秦文献中多用“抚”于涉及家国军政的篇章之中, 如《改葬共世子诵》“镇抚国家”[7]179、 鲁僖公《祷请山川辞》“愿抚万民”[7]48等。 而最早呈现出将“抚”与情感、 意识有关联倾向的是宋玉《神女赋》“怅然失志, 于是抚心定气, 复见所梦”[7]147, 然其基本指向仍是“心”“气”相关的人体实存, 还未直接与情感有涉; 而汉代用“抚”的基本面, 仍为尤指军事社稷的“安抚”之义。 至晋, 潘岳《阳城刘氏每哀辞》有“抚膺恨毒”[7]3993、 《哀永逝文》“咸惊号兮抚膺”[7]3995、 陆机《感时赋》有“抚伤怀以呜咽”[7]4016; 更重要的是, 晋代文章中, “抚”的对象呈丰富和扩大的趋向, 除了抚“臆”“心”“怀”“膺”外, 还可以“抚卷”“抚琴”“抚孤松”等, 通过“抚”景以寄情。 “抚叩酬即”之“抚”应指符合原训之义的“抚”, 刘勰认为“抚叩酬即”为晋末以降文章所“无”, 实说明符合“抚”原初意义使用方式的衰减。
由此来看, 《指瑕》中“赏”和“抚”的字义应从两字分别与“际奇至”和“叩酬即”形成的语义序列中理解; “始有赏际奇至之言”与“终无抚叩酬即之语”分别对应承接上文所涉及的“字以训正”与“义以理宣”。 前句意在晋末篇章中取“赏”等词汇之新义, 导致与字训相偏; 后一句“终无抚叩酬即之语”, 盖指晋末部分文章创作将“抚”等原训舍弃不用, 与汉魏文章有别, 违背了“义以理宣”的“立文之道”。 “赏”和“抚”的“有”和“无”, 这在刘勰的观照中, 这本质上都属于“每举一字, 指以为情”的表现, 实属文之“瑕”。
《指瑕》篇中指出了“赏”字自本训至晋宋以降的变化, 刘勰虽则从批驳的角度言“赏”字, 但实则显示出“赏”与“奇”等语义趋近关联的意义发展趋向, 六朝文学创作和审美观念的转型, 亦由此昭彰。
2 “赏”的意蕴转向与六朝文学“情讹、 文浇”之变
刘勰所云“始有赏际奇至之言”, 揭示出“赏”语汇在晋末以降的发展衍变。 从“赏”意蕴及其施动对象的转变, 实则蕴含了文学书写行为的自觉和审美物象的扩容, 并进一步与六朝文风产生关联与双向影响。
关于“赏”的原初内涵, 《说文解字》谓:“赐有功也”[5]159, 即《指瑕》篇所言“赏训锡赉”即谓“锡赉”为“赏”的训义。 为考察“赏”字在文学作品中的具体内涵及承变沿革, 笔者以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所收诗文为基础, 对先秦至晋代文章中“赏”字的使用及内涵进行了梳理分析, 如表1 所示。

表1 先秦—刘宋诗文使用“赏”数量及涵义统计
汉代及其以前的诗、 文中所用“赏”字均表示“罚”相对的概念; 至三国, 嵇康《四言诗》“钟期不存, 我志谁赏”[8]484、 曹植《求自试表》“或有赏音而识道也”[7]2271分别为诗、 文中最早用“赏”表示“欣赏”的用例, 其余仍全部为“锡赉”之义。
诗、 文两种体裁中“赏”意为“欣赏”的明显增多均出现在晋代。 如王羲之《杂帖》言其所植二十余枝花“颇有可观。 恨不与长者同赏”[7]3216等, “赏”不再持“锡赉”之义, 而是与“欣赏”音乐、 景致等活动相关。 刘勰所言“晋末篇章……始有赏际奇至之言”盖意指于此。 “赏”在先秦至六朝的内涵更迭, 在深层上关涉不同文学体裁在内容、 结构方式和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变迁, 下面分而论之。
2.1 在文章方面, “赏”的意蕴转向与篇章注重个人经验和情感体验的发展趋向密切相关
“赏”训“锡赉”, 用在军政颁赏, 故与诏令文书等实用文体密切相关, 晋明帝《存轻典诏》云:“王者所用, 唯在赏罚”[7]3024, 书写者的个人意志被遮蔽在明确的政治意旨之下; 而“赏”表“欣赏”用义在晋代以降的增多反映出的是实用类文体中个人经验和情感体验因素的增强。 考察魏晋六朝诸作, “赏”作“欣赏”之义多用于诔、 赞、 表、 序、 书、 论等, 而刘勰论上述文体, 亦对其中的情感内质或发展趋向有所注意。
第一,“表”。 曹植《求自试表》“赏音而识道”[7]2271启“赏”为“欣赏”义之先; 而刘勰《文心雕龙·章表》“表”类恰恰独拔曹植, 认为其能一改魏初之表“指事造实”、 未足靡丽的特点, 以“应物制巧”、 能彰显其志为特征。 又谓“表”乃“标”也, 用以陈请, “敷奏以言” “昭明心曲”, 然刘勰又指出表文发展过程中存在“情伪屡迁”之弊。 后有姚嵩《上述佛义表》论佛理“赏味增深”[7]4690; 虞龢《上明帝论书表》有“陛下爰凝睿思, 淹留草法, 拟效渐妍, 赏析弥妙” “诏臣……料简二王书, 评其品题, 除猥录美, 供御赏玩” “人之看书……赏悦留连”[7]5461, 以“赏析”“赏玩”“赏悦”等论品书法之心境。
第二, “书”。 范晔《狱中以诸甥侄书以自序》言:“多不能赏” “应有赏音者”[7]5037, 王微《以书吿弟僧谦灵》有“无不研赏”[7]5076; 《文心雕龙·书记》则谓书之文体“本在尽言”, 故能“散郁陶, 托风采, 故宜条畅以任气, 优柔以怿怀。 文明从容, 亦心声之献酬也”“述理于心, 著言于翰”。
第三, “诔”。 《文心雕龙·诔碑》篇耙梳诔文流变, 认为“诔”即“累者, 累其德行, 旌其不朽”, 指出这一文体源于周代, 至鲁庄公始用于士人, 东汉傅毅以后, 多序“致感”, 重在工丽; “道其哀也, 凄焉如可伤”是为其旨。 从具体的文学创作来看, 西晋潘岳《夏侯常侍诔》“虽实唱高, 犹赏尔音”[7]3990, 东晋谢万《七贤嵇中散赞》“钟期不存, 奇音谁赏”[7]3876等, 以知己“赏”音寄告哀思, 的确呈现出主笔者感怀趋于深切的发展指向。
第四, 其余用“赏”者, 以更清晰明确地呈现心亦及所思所感为倾向, 书写者主体更为突出和明确, 实用文体的辞藻更丰赡, 文学性增强, 如朱昭之《与顾欢书难夷夏论》“赏深悟远”[7]5485、 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天下良辰美景, 赏心乐事, 四者难并”[7]5232等, 谢氏还首将“欣赏”引入赋类文体, 《山居赋》“托之有赏”“研书赏理”“在兹城而谐赏”[7]5215。 此外, 六朝佛学对会心体悟、 静照忘求的强调, 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重视审美观感的“赏”的自我发现并促进了文学表达。 如姚嵩《上述佛义表》“欣悟之至, 益令赏味增深”[7]4690、 释慧远《万佛影铭》“津悟冥赏”[7]4805、 释僧恒《释駮论》“妙赏”[7]4813、 释僧卫《十住经合注序》“存闻赏事”[7]4851等, 顿悟道生、 研求佛理的诉求也进一步推动了“赏”向观物心态和审美直觉的转化。
2.2 在诗歌方面, “赏”的用义变化, 可见出五言诗即景灵思、 观物兴感的发展趋向
诗歌中用“赏”表欣赏之义亦起于三国时期, 嵇康四言诗“钟期不存, 我志谁赏”为现存最早的用例。 整体来看, “赏”表“欣赏”之义多用于五言诗, 五言诗相对于四言诗而言, 不仅是句式的拉长、 物象和情感的扩容, 更是诗歌结构方式的变化。
首先, “赏”促进了写物主题诗歌的心象化。 从诗歌逻辑结构来看, “赏”作为观照外物的起点, 同时也是对物象之发现后之结果; 在联结物象与情感过程中具有重要的逻辑结构功能。 晋傅玄《歌》“曲池何澹澹, 芙蓉敞清源。 荣华盛壮时, 见者谁不赏叹”[8]568从纷葩芙蕖联想至人生盛年, 继而有年华飞驰、 君恩流水之感; “赏”起笔于摹物, 最终落实于“心”解和情感思想的抒发。 鲍照还将“赏”系于闺怨题材, 以对物类的观赏比类无人赏识的坎壈命运, 如《代白头吟》“心赏犹难恃, 貌恭岂易凭”[8]1261、 《秋夕诗》“临宵嗟独对, 抚赏怨情违”[8]1307等。 此种由外物激发的思绪的模式与《诗经》“兴”的笔法有近似的从“物”到“情”的书写顺序, 但其深层情理结构实则本质有别。 《诗经》之“兴”法乃“托物”, 物象为烘托渲染之用, 与情感实为两截; 然对于上述所举诗歌而言, 景物经由“赏”的审美行为使诗人产生兴发感动, 景致与情思紧密关联, 是内心对外物真正审美意义上的观照与发现。
其次, “赏”促进了山水田园诗歌的结构层次生成。 谢灵运是使用“赏”最多的文人, 其将“赏”引入山水纪游题材, 并成为“赏”作为联结景情关系、 推进情感展开的重要枢纽。 如其《登江中孤屿》诗, 首两联“江南倦历览, 江北旷周旋。 怀新道转迥, 寻异景不延”先陈述游览缘由; 三四联“乱流趋正绝, 孤屿媚中川。 云日相辉映, 空水共澄鲜”写川流、 孤屿、 云日、 空水等景象; 第五联“表灵物莫赏, 蕴真谁为传”用“赏”将“物”与后文“想象昆山姿, 缅邈区中缘”[8]1162等展现的“缅邈”之“想象”缀合, 成为从眼前之景走向内心情思的枢纽; 体现出谢灵运五言诗在过程和情景关系的处理方面的结构创新。[9]另如《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 开篇即以“朝旦发阳崖, 景落憩阴峰”交代游历山水, 更进一步以“舍舟眺迥渚, 停策倚茂松”表现着意于景致的流连; 第三至八联从川壑林溪写至篁蒲鸥禽; 第九联“览物眷弥重”道出对心系外物的情怀; 最终以“赏废理谁通”[8]1172作结, 表现“孤游”于此, 无人达眷赏之妙的哀婉之叹。 至若其他谢诗如《游南亭》“赏心唯良知”[8]1162、 《石门岩上宿诗》“妙物莫为赏”[8]1167、 《田南树园激流植楥诗》“赏心不可忘”[8]1172、 《入东道路诗》“心赏贵所高”[8]1175等, 均使用“赏”景及心的展现方式。 鲍照诗亦承此种“景—赏—情理”结构, 如《望水诗》以“刷鬓垂秋日, 登高观水长”起首陈述“望水”的起因; 以下三联“千涧无别源, 万壑共一广。 流驶巨石转, 湍回急沫上。 苕苕岭岸高, 照照寒洲爽”在行驶过程之中途径千涧万壑, 观察岭岸寒洲荡人心魄的景色; 第五联由景物转向内在感发, 道“东归难忖恻, 日逝谁与赏”的感慨, 遂转入“临川忆古事, 目孱千载想。 河伯自矜大, 海若沉渺莽”[8]1310的联想和思索。
山水纪游类作品发展至齐梁时期, 以“赏”联结景与情的书写方式更为稳定, 并对“赏”的审美活动有更加充分的认识, 如谢朓《游山诗》言己“经目惜所遇, 前路欣方践”品味山水的观赏活动, 在“寻谿”“傍眺”等行游山水过程中, 通过徜徉“坚崿既崚嶒。 回流复宛澶。 杳杳云窦深, 渊渊石溜浅”的景致, 终得“即趣咸已展”之自适, 并通过诗歌开端“乘闲遂疲蹇”与诗末“得性良为善”的顿悟之对比, 表现主体在“触赏聊自观”[8]1424过程中出入物我的融通。 另外, 如其《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桥》“赏心于此遇”[8]1429, 以及沈约《游钟山诗应西阳王教》“赏逐四时移”[8]1632、 何逊《慈姥几诗》“一同心赏夕”[8]1704等, 皆表现出日渐成熟稳定的写作方式。 “赏”在大小谢等六朝诗人笔下的使用, 可见“赏”的建构参与山水诗的发展, 有着由物入心、 勾连景情的结构意义。
2.3 “赏”的意蕴之变及与之关涉的体裁、 内容的变化, 在根本上反映的是六朝观物撰文“情”化与审美自觉
刘勰《指瑕》论“赏”固然是对晋宋以降篇章的批评, 但从中可以见出晋末兴起、 南朝相承的文学新变; 而刘勰对“赏”的意蕴转向这一现象加以关注, 说明其在彼时文学创作中已经较为普遍。 与刘勰基本处于同时期的钟嵘《诗品序》亦言:“方今皇帝, 资生知之上才, 体沉郁之幽思, 文丽日月, 学究天人。 昔在贵游, 已为称首。”[10]15同样说明晋宋时期“赏”得到认知理会与引用发生了变化, 以及作为美学范畴的确立[11]。 “赏”的意蕴之变具体包括两种内涵, 细而考辨, 可见其中的文学观念衍变。
2.3.1 词义更迭, 即从“锡赉”变为“欣赏”之义
进一步考察之, “赏”为“欣赏”之义诸诗也经历了对象物由人之才志到景物的变迁。 三国至晋诗中虽已出现表“欣赏”的用义, 但被“欣赏”之对象本质为作者本人, 从嵇康“钟期不存, 我志谁赏”的感喟发端, 后有刘琨、 孙绰、 谢安、 陶渊明等承之, 有《答卢谌诗》“音以赏奏”[8]852、 《答许询诗》“赏音者谁”[8]900、 《与王胡之诗》“在我赏音”[8]906、 《答庞参军诗》“有客赏我趣”[8]977等, 在寄赠诗中表志趣相知、 良朋相契之意, 表达对同声相应、 同气相求的知音之渴求, 抒发孤独心志。 《世说新语》设“赏誉”篇, 记丞相对王蓝田“甚相叹赏”、 桓温“叙古今成败由人, 存亡系才。 其状磊落, 一坐叹赏”[12]251等, 用“赏”以表钦慕赞赏之意, 被“赏”的对象为风流名士, 与彼时流行的人物品评风尚有关。
涉及物象者, 虽谓“赏”观景物, 实则用以自喻。 如范泰《鸾鸟诗序》以禽鸟喻人, 言“兹禽何情之深”; “赏”荷诗自西晋傅玄“曲池何澹澹, 芙蓉敞清源。 荣华盛壮时, 见者谁不赏叹。 一朝光采落, 故人不回延”发端, 通过荷由盛及衰的过程中, 观者“赏叹”到“不回延”的变化, 将“荣华盛壮”到“光采落”的荷花类比人生青春暮年的变迁。 这种以物色类比人之才志、 以观赏比附人之得遇的书写方式成为一种书写传统, 张华《荷诗》“荷生绿泉中。 碧叶齐如规。 回风荡流雾, 珠水逐条垂。 照灼此金塘, 藻曜君玉池。 不愁世赏绝, 但畏盛明移”[8]622、 鲍照《学刘公干体诗其五》“荷生渌泉中, 碧叶齐如规。 回风荡流雾, 珠水逐条垂。 彪炳此金塘, 藻耀君王池。 不愁世赏绝, 但畏盛明移”[8]1299等皆先绘物色, 继而以荷之美质与“世赏”难久留对比, 重在强调个体的才情与衷情需要外铄的“欣赏”与契合, 纾解心怀、 以期用世。 然此虽关注到“赏”之行为和对象, 在本质上实属于比兴之法, 托外物以寄情言志超于对物色的鉴赏, 对景物本身样貌的关注和审美掩抑于主体思想情感和灌注和附加之下。
谢灵运在推动“赏”之转向山水物色审美方面, 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方面, 谢诗对既有书写传统有所承续, 希冀得知音“赏”遇。 如《相逢行》言“赏契少能谐”又谓“情苦忧来早”, 表现对于“邂逅赏心人”[8]1149的渴求; 《游南亭诗》“我志谁与亮, 赏心惟良知”[8]1162、 《酬从弟惠连诗》“永绝赏心望, 长怀莫与同”[8]1175等诗作中, 无俦同赏的孤独情感也不断复现。 与此同时, 谢灵运的独特贡献在于, 其于山水纪游书写过程中, 通过景象摹画, 逐步实现对物色之美的真正体察与发现。 如《晚出西射堂》诗, 以行游的推进方式叙“步出西城门, 遥望城西岑。 连鄣叠巘崿, 青翠杳深沉。 晓霜枫叶丹, 夕曛岚气阴”, 慨叹“节往戚不浅, 感来念已深”。 诗中用大量篇幅叙景, 并以“羁雌恋旧侣, 迷鸟怀故林”作比, 表现“含情尚劳爱, 如何离赏心”[8]1161的寄托。 虽然此处“赏”仍然指自身与知音相赏, 但从“人之相赏”扩展至“人之赏物”, 与景象建立起更加紧密的情感关联。 而至其《登江中孤屿》《从斤竹涧越岭溪行诗》等作品, 则真正将“赏”主体移至自身, 将审美活动建立在对景物细腻体察的基础之上。 《登江中孤屿诗》已点明其游览山水是出于自觉的“怀新” “寻异”之举; 《从斤竹涧越岭溪行诗》前半篇纪游写景, 开篇即写“猿鸣诚知曙, 谷幽光未显。 岩下云方合, 花上露犹泫”的秀野山色, 进而移步换景, 叙己“傍隈隩”“陟陉岘”“过涧” “登栈” “乘流”的游览经历; 并细腻捕捉“苹萍泛沉深, 菰蒲冒清浅”的细节与“企石挹飞泉, 攀林摘叶卷”的赏玩活动, 相比静止的观览在深入景物与互动方面推进一层。 第十联用“情用赏为美”总揽景致, “赏”心与“情”合, 进而“观此遗物虑, 一悟得所遣”[8]1167, 在赏奇观物中默识悟道。 此种审美心态, 不仅成为山水诗的兴发机制, 更使“赏”成为文学书写的内蕴思想肌理, 故至宋代《类篇》, 释“赏”在引《说文》的同时又补曰“一曰玩也”[13], 显示出“赏”之内涵进一步向审美方向转换与深化。
2.3.2 “赏”意义边界泛化与扩容, 从字字落实到注重整体意境的意蕴
“赏”由于与感觉经验相结合, 在物我融会之际, 注重兴发感动。
依刘勰《指瑕》篇, 其反对“赏”的同时, 进一步指出与之相关的文学“情讹”现象。 认为“赏”字不“预情理”, 批评其晋末以来文章“每单举一字, 指以为情”。 “何预情理”, 《斟诠》谓“情趣理会”, “情趣”为名词, “理会”为动词, 和“心解”一词相对; 以锡赉作心解之意, 用执握指情理为言, 是文家引申本义的撰文方法。 如《校释》所言:“盖一字初本一义, 及文家转相引申, 而后数义一字。” “每单举一字, 指以为情”一句, 郭晋稀《文心雕龙注译》认为“指以为情”即“用一字表达二字之义”; 《斟诠》直解为“主客问对之时, 往往但对片言单字, 指事类情, 以相嘲谑”; 骆鸿凯《文选学》论《指瑕》云“赏”“抚”“即”等字的新义, “上非故训, 下异方言, 后人沿习, 不以为异。 而当时骤读, 破费摸索, 谓之‘情讹’ ‘文浇’, 非过语也”。
观晋宋诗文, 由于“赏”与好尚、 兴味等抽象精神旨趣相关, 加之文人寓托心迹往往寄意深曲, 故文句铺展而意义弥漫。 如陶渊明《答庞参军诗》首有“有客赏我趣, 每每顾林园”, 末云“物新人惟旧, 弱毫多所宣。 情通万里外, 形迹滞江山”[8]977, 全篇叙与庞氏“相知”的深厚交谊与闲饮欢谈, 叙事纪实简略而以情结体。 然其所“赏”之意趣的具体内涵, 则并未昭彰。 另外, 如鲍照《答客诗》自云“幽居属有念, 含意未连词”并创设情境, 以“会客从外来, 问君何所思。 澄神自惆怅, 嘿虑久回疑”主客问答的方式叙情志, 言“爱赏好徧越, 放纵少矜持”, 以陈“专求遂性乐, 不计缉名期”之“深忧寡情谬”[8]1286的心绪, 陈情言理占主体部分, 同样可见浓郁的主体情感充溢和灌注。
情感的蔓延和词汇的灵活运用相对应的是修辞技巧的多样化与叙景篇幅的增加。 如谢灵运《入东道路诗》记其“整驾辞金门, 命旅惟诘朝”的行游经历, 用“行路既经见, 愿言寄吟谣”的方式述“满目皆古事, 心赏贵所高”的怊怅之情。 其中, 以八句的篇幅叙清明时节的物象“陵隰繁绿杞, 墟囿粲红桃。 鷕鷕翚方雊, 纤纤麦垂苗”, 从麦苗纤纤, 翚鸟嘤鸣、 绿杞红桃的细致观察, 体察“荣华感和韶”的节候变化; 并从眼前“隐轸邑里密”遥想“缅邈江海辽”[8]1175, 虚实动静、 宏宇微观皆囊括之。 又如王筠《望夕霁诗》摹景, 其用“连”“长”“密”“遥”等修饰词汇, 并参以“乱云”“众籁”“绿滋”“翠霭”等物色状山林树峰之貌; 水文景象则不仅有“石溜”“山泉”等类别之分, 更有“潨潺”“澄汰”更为细腻复杂的语汇, 在“望夕霁”的整体观照下, 聚合更为丰富纷繁的景致物象。
需要指出的是, 刘勰虽然反对“赏”字义之变, 但对审美与欣赏活动本身有所体察, 如其《物色》“物色相昭, 人谁获安” “物色之动, 心亦摇焉” “情以物迁, 辞以情发”、 《诠赋》“情以物兴” “物以情观”、 《神思》“物以貌求, 心以理应”等, 充分重视物象与人心之间的感发交映机制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 实际上, 《指瑕》批驳“赏”字义更为深层的原因, 即在于这种“每举一字, 指以为情”的创作现象, 会导致“悬领似如可辩, 课文了不成义”。 因此, 被刘勰称为“实情讹之所变, 文浇之致弊”。 “悬领”, 郭注“犹言凭空领会”。 “课文”, 郭注云:“课, 责也, 引申有推求之义。 课文, 推敲文字”; “浇”, 《校注》谓“犹言文薄”, 如李康《运命论》:“文薄之弊, 渐于灵景。” 《文选》翰注:“文德之浇薄。” 表示“欣赏”尤其是品赏景物之义的“赏”相较“赏赐”、 与“罚”相对的“赏”之原初意义而言, 与审美体验和作者内心的情感产生了渐趋密切的关联; 而词汇意蕴的丰富在本质上乃是“情”张扬的表现, 是“心”与外物的融会。 刘勰“‘赏’训锡赉, 岂关心解”的论点亦当由此生发。
3 执正驭奇: 从与时风之冲突重审刘勰的文学观
刘勰在《指瑕》篇中批驳“赏”等字义变化, 反对“每举一字, 指以为情”创作趋势, 范文澜注本指出:“六朝人好言赏, 然如上例, 似不应致讥”[2]142; 观六朝文风, 恰以《明诗》所谓“情必极貌以写物, 辞必穷力而追新”、 繁钦《与魏文帝笺》“哀感顽艳”、 陆机《文赋》“缘情而绮靡”的张扬为特征。 笔者认为此种现象恰体现出刘勰所持理论与六朝创作时风的裂隙, 从根本上反映了刘勰“正奇”观及“执正驭奇”的文学标准。 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3.1 对“赏”字的苛究, 根植于刘勰摈“奇”崇“正”的理论根柢
《指瑕》从“立文之道, 惟字与义, 字以训正, 义以理宣”的角度, “‘赏’际奇至”为创作的偏谬, 由此导致晋末篇章“依希其旨”的倾向。 “正奇”观念为《文心雕龙》中的重要范畴, 在刘勰的理论体系中, 为文“正”道乃“师圣” “宗经”, 为建言修辞之“本”; “奇”则与正道、 典雅相对, “新奇者, 摈古竞今, 危侧趣诡者也”, 以重视辞藻、 驰才骋情、 取新求异为特点; 一方面, “奇”能够赋予文章以变化和新意; 另一方面, 刻意寻“奇”的追求往往会使文失于雅咏温恭的“正”途, 刘勰论“奇”往往是就此方面而论, “赏”用字偏离古制即不遵训义, 是在文辞方面用字之“奇”的重要表现; 除此之外, 《练字》篇同样强调缀字属篇“依义弃奇” “避诡异”的“正文字”之要求。
“奇”作为一种具体的文章结撰技巧, 除了字训之义, 还包括文法层面。 《定势》篇中指出“奇”为一种“自近代辞人”以来的颠倒文句、 率意求新的句法, “文反正为乏, 辞反正为奇。 效奇之法, 必颠倒文句, 上字而抑下, 中辞而出外, 回互不常, 则新色耳”。 其出于“新学之锐”文人“率好诡巧, 原其为体, 讹势所变, 厌黩旧式”的“讹意”, 在本质上“似难而实无他术”, 属于“穿凿取新”的表现, 会导致“文体遂弊”的误区。
刘勰将“正奇”对举, 将单纯求“奇”的方向作为文学发展的谬误, 如《知音》“爱奇者闻诡而惊听”, 《史传》“若任情失正”, 则文其殆哉”。 同时, 《乐府》指出“奇辞切至”为“诗声俱郑”的表征。 《知音》以观“奇正”为观文章优劣之方法, 他对“莩甲新意, 雕画奇辞”的肯定, 是以“熔铸经典之范, 翔集子史之术”为基本前提的。 《情采》称:“理正而后攡藻, 使文不灭质, 博不溺心”, 最终归结为反对“逐奇而失正”, 主张应“执正以驭奇”的文学创作规式。
3.2 《指瑕》言“赏”, 体现出刘勰以《雅》《颂》和汉魏文章等“前秀”为范本, 并对竞丽时风有限度认同
刘勰反对“赏际奇至之言”的原因, 在于会导致“每举一字, 指以为情”的弊病, 并认为其作为“《雅》《颂》未闻, 汉魏莫用”的文学发展趋势之表征。 由此可见, 其文学观念尚立于晋代以上的文学传统之中, “希风于前秀”的基本取向。 近世文章则颇有微词。 就具体体裁而言, 刘勰同样体现出贵古贱今的倾向。 如《明诗》以四言诗为“正体”; 五言则为“流调”; 《章句》篇再次褒美“四字密而不促” “诗颂大体, 以四言为正”, 而“变之以三五”仅为“应机之权节也”; 然自永嘉以降, “体密而近缛, 言丽而斗新, 藻绘沸腾”的五言诗恰是文学发展之新向。 梁萧绎《金楼子·立言》将“文”的特点概括为“吟咏风谣, 流连哀思”, 钟嵘《诗品》评“上品”之曹植云“骨气奇高, 辞采华茂”, 刘桢“仗气爱奇”, 将“奇”作为对作家的赞辞; 刘勰论“奇”实则表明其亦已对于性灵摇荡、 文辞绮靡、 篇幅铺展等文学新变有所注意, 但对此肯定极其有限, 《乐府》篇以为晋末以下文章为“情讹”“文浇”, “宋发夸谈, 实始淫丽”; 指出“艳歌婉娈, 怨诗诀绝, 淫辞在曲”, 则“正响”不生。 从《文心雕龙》中以《时序》为代表的文学史之发展论述中, 同样可看出刘勰对时风的有意识疏离。 《时序》篇论晋世“不文”, 但又论:“茂先摇笔而散珠, 太冲动墨而横锦, 岳湛曜联璧之华, 机云标二俊之采。 应傅三张之徒, 孙挚成公之属, 并结藻清英, 流韵绮靡”, 可见, 晋世文学发展尚兴盛, “不文”者, 该由其不及刘勰之标准。 其解谓“运涉季世, 人未尽才, 诚哉斯谈, 可为叹息”, 从中可以亦可窥见其文学观念和好尚。 其论宋齐, 《通变》称“宋初讹而新”, 《定势》称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厌黩旧式, 穿凿取新”。 然《诗品》引其从祖、 齐正员郎钟宪所言:“大明、 泰始中, 鲍、 休美文, 殊已动俗。”[10]192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认为宫体诗于晋宋之间“后有鲍照, 前有惠休”, 鲍照兼学旧曲新声, 擅于乐府之体, 有“发唱惊挺, 操调险急。 雕藻淫艳, 倾炫心魂”[14]908的特色; 沈约实则沿着侧艳之词一路发展, 而《诗品》所称鲍照“不避危仄”[10]127实则与刘勰《体性篇》中“危侧趣诡”相通[15]411, 后者即“新奇”之义, 同样可见刘勰对“奇诡”文风的摈弃。
3.3 《指瑕》所反映的“执正驭奇”观念体现出刘勰“折中”的理论特点与调和“辞”与“理”的尝试与“衔华佩实”的文学理想
刘勰在《序志》篇谓己“擘肌分理, 唯务折衷”, 《章句》篇亦强调以“折之中和”为作文法, 而“奇正”正是其执中允和的重要表现。 《定势》指出:“奇正虽反, 必兼解以俱通”, 刘勰一方面保留对“奇”之辞采的追求, 《丽辞》认为:“若气无奇类, 文乏异采, 碌碌丽辞, 则昏睡耳目”, 更认为应当“矫讹翻浅, 还宗经诰”, 沿着“五经”等圣人之文的雅正路径发展, 主张情理调和, 即《征圣》所谓“理融情畅”, 要求“衔华而佩实”, 《附会》云:“以情志为神明, 事义为骨髓, 辞采为肌肤, 宫商为声气”, 实现《章表》所说“繁约得正, 华实相胜”之臻境。 通过“凭轼以倚《雅》、 《颂》, 悬辔以驭楚篇, 酌奇而不失其贞, 玩华而不坠其实”成“按辔文雅之场, 环络藻绘之府”的统一, 实现“驱辞力”和“穷文致”之目的。
统合“致义”与“会文”实乃理想之境界, 固然偏倚无失, 然以“执正驭奇”的理念观照文学, 在处理“承”与“变”关系方面不仅会呈现论述互相抵牾、 导致部分忽视文学发展新向, 且就其体系内部而言, 也难以完全调和。 就“赏”字之义来说, 刘勰务求用字准确遵循本训, 以“字不妄”而实现“句之清英”的用心, 固然有回转腴辞繁句带来的“为文造情”弊病之功, 然而其反对字义的发展、 变化和引申, 不仅是一种泥古的表现, 且与其“通变”的主张相冲突。 即一方面主张“文辞气力, 通变则久” “趋时必果, 乘机无怯” “情者, 文之经” “情以物迁, 辞以情发”, 倡导“望今制奇, 参古定法”; 另一方面, 正如祖保泉所指出的, 刘勰却“逼着作家只能在古籍中寻找词汇来表达自己的感情”, “‘宗经’的思想烙印却深深地烙在他的创作论中, 甚至成了他的理论的伤痕”[3]789-790。 刘勰《序志》指出文章皆“经典之枝条”, 推重奏疏对策“纬军国”之用, 强调还宗经诰、 师范汉篇, 将文学的顺美匡恶、 贵风轨而益劝戒之作用推置首位, 规制抒情叙志于儒家风教的阈限内, 从而六朝发轫的山水诗题材不乏“俪采百字之偶, 争价一句之奇” “图状山川, 影写云物”等贬抑评价, 更对六朝小说的兴起有所忽视。
笔者认为, 《文心雕龙》一定程度上疏于自恰之特点, 与刘勰所浸润的六朝文化风尚和家世背景影响下推重典训之志的作用有关。 一方面, 其身处齐梁“精神色泽, 溢自气表”之趣尚浸染, 审美态度受到文学“声色大开”[16]1407时代审美理想的影响; 另一方面, 按本传, 刘勰祖父“灵真, 宋司空秀之弟”, 父亲“尚, 越骑校尉”, 然至刘勰, “早孤” “家贫”[17]710, 整体上属于没落士族, 坚守“穷则独善以垂文, 达则奉时以骋绩”的儒家信条, 加之南齐高帝、 武帝以来儒学复兴的趋势更为昌炽, 故在“树德建言” “名愈金石之坚”理想导引下, 《文心雕龙》试图建立“体大精深”、 以“原道”“征圣”“宗经”为依据的文学批评系统, 从而使这一理论体系先天具有“将文学自觉纳入政治教化, 违背了文学发展规律”[18]219的局限, 而史载刘勰“自重其文, 欲取定于沈约”并负书干于沈之车前, 此种以期用世的著书行为本身即是其儒士人格的直接说明。 然而这种于心有寄的文学书写诉求和以政治价值掣肘诗文的观点, 本身又与六朝文学的文体自觉及审美和情感深化等新变相悖, 一定程度上也为《文心雕龙》书成而“未被时流所称”提供了解释。 因此, 其一方面“详其本源, 莫非经典”规制文章典范, 另一方面, 又出入于锤句析字、 和音谐韵等表现修辞学的探讨, 并对凝思畅意、 感物赏心等主体情志的表达有所彰显。 虽有未得圆融之处, 但能见出刘勰欲取守承与从新、 附物切情与时务政理之中和的理想与追求。
4 结 语
综上所述, 本文试从考辨《文心雕龙·指瑕》所论“始有赏际奇至之言”之“赏”切入, 并通过《指瑕》所论“赏”字偏离“锡赉”本训的现象, 结合对晋宋及以前“赏”字在诗文中的内涵变化梳理, 研究“赏”在六朝的意义转型及其所反映出的晋宋之际诗文体裁、 内容衍变, 在本质上体现出魏晋以降诗文创作中个体“情”的彰显和即景体物观念的深化。 而《指瑕》对南朝“赏”“情”流衍的批驳, 实则为刘勰“执正驭奇”的思想的展现, 体现出其思想趋时与守道相合、 力图牵挽“文”“质”的努力, 在根本上反映出刘勰由其家世和时代双重影响下带来的理论体系内蕴之矛盾, 而这一现象本身也是六朝文风发生转向的重要表现, 展示出文学创作与流变中辞情义理、 承古启新的互动与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