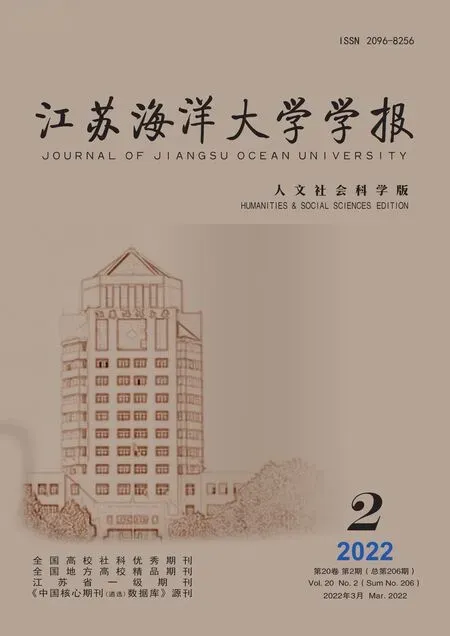《野草》“双声语对话体”的诗性探微与溯源*
张景兰,尤一涵
(江苏海洋大学 文法学院,江苏 连云港 222005)
鲁迅在1935年写给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信中说,自己“是散文式的人,任何中国诗人的诗,都不喜欢。只是年轻时较爱读唐朝李贺的诗,他的诗晦涩难懂,正因为难懂,才钦佩的。现在连对这位李君也不钦佩了”[1]337-338。然而,就是这个自认为“散文式的人”的鲁迅,凭借着一部“散文式的诗”——《野草》,使中国的新诗有了现代性意义上的全新开拓。诗人张枣认为,鲁迅是“我们新诗的第一个伟大诗人,我们诗歌现代性的源头的奠基人”,而他“奠基了现代汉语诗的开始”的伟大作品,就是“无与伦比的极具象征主义的小册子《野草》”[2]146。而且,《野草》的语言恰恰符合鲁迅年轻时钦佩过的那位“诗鬼”李贺作品的风格——晦涩难懂。《野草》自然不是有着谨严或不谨严格律的分行文字,所以它是“散文式的”,但《野草》的语言又显然和这位自称“散文式的人”的作者此前和此后所有的小说、散文、杂文作品都有着十分显著的不同。这晦涩、幽微、瑰丽而又富于音乐性的语言,这语言中折射出的尖锐矛盾特性和复杂的对话关系,以及这矛盾和对话里折射出的强烈的情感性和深刻的思想性,显然能够说明这不分行的文字拥有“诗性”,也能说明这不分行文字的作者拥有“诗人性”。
一、以对峙和争辩为特征的“双声语对话体”
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中这样阐释“微型对话”的概念:“所有词语都是双声的,每句话里都有两个声音在争辩。”[3]118可以说,这种相互争辩的“双声语”在鲁迅的作品中是普遍存在的。他的小说,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其现代性的特质恰恰也表现在对“情节”这一传统小说要素较低的依赖性。巴赫金提到传统的“独白型”小说时说:“对话间的一切对立关系,都在剧情的发展中得到消除,而剧情体现出的主题思想,则纯属独白型的思想。”[3]44换言之,在所谓传统的“独白型”小说中,人物间的对话是为了推动剧情的发展并最终达到某个特定的“主题思想”而服务的,但鲁迅在小说创作中显然摒弃了这种以推动情节来获得结论的方式,而是在不断的怀疑、否定和追问中提出新的问题,并且这问题往往指向一个无从获得答案的僵局。比如《狂人日记》里,狂人就是在“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的精神驱动下和“从来如此,便对么?”的反问中,由“他们吃人”“大哥吃人”“母亲吃人”一步步推导出“我也吃了人”的;推导出了“我也吃了人”的狂人,发现这局面的无解,他所发出的“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的追问和“救救孩子……”的呼喊也显得语气微弱了不少。《祝福》中的“我”被祥林嫂问倒后,自嘲“‘说不清’是一句极有用的话”和得知祥林嫂死讯后“为人为己也都还不错”的自我开解,《伤逝》里涓生对于是否该将真实说于子君、“我没有负着虚伪的重担的勇气,却将真实的重担卸给她了”的反思也是一律。最典型的自然是《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两篇,它们被视作最具有“复调性”特质的小说,最主要的论据是“我”与吕纬甫、“我”与魏连殳这两组对话关系的存在,但事实上这两个叙事者和两个主人公各自使用的都是这种“有两个声音在争辩”的“双声语”,叙事者与主人公对话时,其实有四个声音存在于场域之中,吕纬甫“我现在什么也不知道,连明天怎样也不知道”的自白,和结尾时“我”所叙“见天色已是黄昏,屋宇和街道都织在密雪的纯白而不定的罗网里”的景色显然是暗合的,魏连殳信里“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的奇怪宣言和申飞描写魏连殳尸体口角间的笑是在“冷笑这可笑的死尸”,都是语义在矛盾关系中的回环生长。而这些故事的叙述者作为生者的结局有着惊人的相似:在别人的故事获得了名为“死亡”的收束后,生命尚未终结的他们不得不继续“走”,至于“走”向哪里,却是无从知晓,也无法交代了。由此可见,鲁迅的小说创作不依赖情节的跌宕,而依赖思想在“对话”中获得的动能,他的小说并不是一个故事发生、发展到结局的过程,而是思想不断自我问询、自我辩难从而不断自我生长的过程,但这个留给思想的场域是开放的,鲁迅并不希求这个问询、辩难、生长的过程能指向一个确定的结果,这恰恰符合了巴赫金复调理论的“开放性”特征,“每本小说里写的都是众多意识的对峙,而对峙又没有通过辩证的发展得到消除,这些意识并不融合为某种正在形成的统一精神”[3]56。
这种以争辩和对峙为特征的“双声语”,显然在《野草》这部诗性作品中获得了更加具有象征性的新形态,甚至可以说,《野草》的语言几乎完全是由一种形式上整饬而内容上对应的“双声语”构成的。这首先表现为由语义相互对立的语词构成的矛盾关系。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在《野草》中发现若干基础的短语构筑模式:“明与暗”“生与死”“也不拥抱也不杀戮”“既不安乐也不灭亡”……连接词的两端显然是截然对立的两极,这种鲜明的对照关系,使得语言的张力凝固于语言所描绘的时间点,并获得极大的增益效果。《影的告别》中“影”处在“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的状态下,仿佛后顾有猛虎,而前面是悬崖。《复仇》的主体就是“又不拥抱也不杀戮”的两个人,这持刀对立的两个人本应处于一种尖锐而紧张的矛盾关系之中,作者在引入这组矛盾关系之前,是这样描绘不到半分厚度的皮肤后生命本身的动能的:“于是各以这温热互相蛊惑,煽动,牵引,拼命地希求偎依,接吻,拥抱”,这时候又写“用一柄尖锐利刃,只一击,穿透这桃红色的、菲薄的皮肤”,尖刀靠近人体薄而绷紧的皮肤,鲜血的喷薄似乎只在瞬间,凸显爱与恨、生与死的极端对立。《希望》里用“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这所谓“血腥的歌声”变作的空虚的暗夜与“希望的盾”抗争,似乎这盾薄得像一层纸,即将被空虚的洪流冲破。“死火”本身即作为无可保存的矛盾体出现,一被唤醒就立刻面临“或冻灭或烧完”的二难抉择。《墓碣文》中墓碣正面“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希望中得救”的文字,每一组都是由相互对立的两个语词揉成的一个综合矛盾体,而墓碣给“我”留下的“答我。否则,离开!”的这两个选项又将墓碣与“我”置于了直接对立的矛盾关系中。可以看出,这些语义相反的词句构成的矛盾关系,不仅使语言本身获得了更多所谓“陌生化”的张力,更使矛盾本身在瞬态上获得了大的动能,处于一种亟待解决的紧张状态中。那么,这矛盾获得解决了吗?
这些看似亟待解决的矛盾,不仅没有在其被作为语词凝固下的瞬间获得解决,反而在一组又一组语词的对立中,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由一个又一个瞬态的“矛盾点”织成了一张错综复杂的“矛盾网”。“影”的矛盾由三个世界里存在它“所不乐意的”因而“不愿去”始,推出这不乐意的对象——主体“你”,作出“我不想跟随你了”的结论后,立刻面临新的矛盾:或被黑暗吞并,或因光明消失。“影”因为“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而作出“不如在黑暗里沉没”的决定,可因为自身为黑暗与虚空的综合体,又陷入了“我愿只是黑暗”和“我愿只是虚空”的彷徨,“影”看似自己作出了选择,但从它“独自远行”的结局就可看出,它的矛盾并没能得到解决。《复仇》中本来应该直接对立的两个持刀而立的人,却保持着这个“将要复仇”的状态,而“将要拥抱,将要杀戮”却始终是“也不拥抱,也不杀戮”,复仇的对象转为了观看他们复仇的看客,直至复仇者与被复仇者都老死并干枯,沉默对峙的局面也没发生改变。正如汪卫东所说:“虽然‘复仇’终获成功,但实际上是一场无奈的胜利,因为复仇的对象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敌人,而是自己曾经试图竭力救助的民众。”[4]53复仇虽完成,复仇者的矛盾却显然没能得到解决。《希望》中的“我”眼见着身内身外的青春都逝去,从以希望之盾抗拒空虚的暗夜,到决心自己肉薄空虚的暗夜,但终于发现“而我的面前又竟至于并且没有真的暗夜”,最终得出“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结论,显然又一次把矛盾推向无解的死局。“死火”在和“我”的对话中达成了结盟的关系,自己在冻灭和烧完的二难抉择中选择了“烧完”的结局,并且真的自己“烧完”,且“并我都出冰谷口外”,但这个“我”却突然被“大石车”“碾死在车轮底下”,死前对于不知对象的“你们”“再也遇不着死火”的“得意”,也并不能算作“死火”这一矛盾的解决。《墓碣文》中的墓碣在呈现多组由反义语词揉成的矛盾体之后,进一步向“我”提出了“本味何能知”和“本味又何由知”这一组无解的问题,“我”显然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所以只好在“答我”和“离开”中选择“离开”,但“我”固然离开了,这个无解的矛盾问题却始终存在于墓碣之上,并且永远等不到能化解它的人。因此,汪卫东指出:“《野草》成了矛盾的漩涡。几乎每一篇都由矛盾构成,形成一个个的漩涡,整个《野草》也以矛盾的相互展开、碰撞、纠缠、合并、分裂、再生、抵消……为动力,一个个漩涡汇成一个大的漩涡,让人应接不暇、艰于呼吸。”[4]139不难看出,提出这一系列矛盾的作者,虽然看似将这些矛盾置于亟待解决的尖锐而紧张的对立状态之下,却丝毫没有希求、并且似乎也并不认为这些矛盾可以得到解决,这些矛盾对立的紧张状态和由此产生的语言张力,似是他一种美学上的追求,在若干组鲜明对立的矛盾下展开的《野草》,呈现出的整体的艺术效果,就像汪曾祺评价李贺的诗“是画在黑底子上的画,故颜色特别浓烈”[5]270一样,但倘若这位李君在这浓黑的底色上作画用的是蘸满金色颜料的软笔,鲁迅拿来作画的工具就是硬而锋利的刻刀,他呈现出的黑白分明的图景是《野草》最鲜明的艺术特征。但他这把刻刀却不仅用于雕刻这幅艺术的画作,还要用于解剖自己的灵魂。如果说这些双声语“微型对话”的形式表达构成张力、亟待解决的矛盾是鲁迅美学上的自觉追求,这些矛盾相互碰撞和生长的过程,比起矛盾能够获得解决的结果,更像是他精神上的主要需求。在矛盾不断生长发展又无从解决中不得不继续踏上路途的“影”和那些“我”,获得的不能算作结局的结局,正和他小说中的涓生和申飞们一样,是朝着未知继续地“走”。“走”这个动作本身的意义显然大过了未知的“目的地”,而“走”的过程显然拉伸了这些矛盾所存在的点时间,将其延长为线性时间,即这一不可调和的“二元对立”出现了“中间地带”。
二、二难困境与二元对立的“中间地带”
鲁迅在《写在〈坟〉的后面》一文里这样写道:“以为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6]301-302《野草》中的许多矛盾,看似是不可调和的二难困境、二元对立的两极,但这点与点之间却又往往存在着一个奇特的“中间地带”。如果没有这个“中间地带”的存在,矛盾就好像原子弹一样即刻要爆发,可在爆发前的一瞬间,矛盾的制造者却好像突然按下了“暂停键”,躲进了一个只有自己能动弹、能思考的“个人时间”。这个“中间地带”的构造显然也是矛盾悖论式的。
《影的告别》一开篇,“影”还未使主体失声之前有一句提示语“人睡到不知道时候的时候”,这个“不知道时候的时候”显然就是一个典型的“悖论体”,作者通过将现实时间转化为心理时间,为自己和“影”在人类无法违抗的连续不断的时间河流里争取到了额外的时间,“影”和主体的对话关系就是在这个“额外时间”里开展的。“影”在主体暂时失声的这个时间场内发表了一通“我不愿去”的讲话,因为在预设的目标空间里有它“所不乐意的”对象存在,否定了“天堂”“地狱”“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这些去处之后,“影”做出了本篇除了否定语外的第一个主动选择“我不如彷徨于无地”,这个“无地”显然也和“不知道时候的时候”一样,是一个悖论式的生造的概念。对“影”来说,“天堂”与“地狱”的“中间地带”,显然并非“人间”,因为在“影”说出“我不愿去”的时候,它已经在挑选目的地,即它已经决定要辞别主体离开,所以,“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人间,我不愿住”。这是被“影”省略了的、它的说话的大前提,在这个大前提下,“影”为自己挑选目的地,挑来挑去都“不愿意”,最终只能以“无地”这个悖论式的新造概念代替原有的“人间”成为“天堂”和“地狱”的“中间地带”。在“时间”这一概念上也是同理,“影”在决定离去之后,又陷入“黑暗与光明”的二难抉择中,属于“黑暗”的时间是“黑夜”,属于“光明”的时间是“白天”,而日夜交替的时间,从自然界的逻辑上讲,是“黄昏与黎明”。但“影”却又因为“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再一次主动放弃了“黄昏与黎明”这两个属于自然逻辑的天然的“中间地带”,而将自己“独自远行”的时间再一次定为这个悖论式的生造概念“不知道时候的时候”。所以,当“影”终于宣布“我愿意这样”时,它看似遵从了自己开始的“不如在黑暗里沉没”的选择,但其实留给它“独自”远行的那个既没有主体也没有其他“影”的“全属于我自己”的“黑暗”的场域,已经违背了原本属于“黑暗”这个词的现实逻辑,不是它先前选择的那个“黑暗”,而是悖论式的“无地”的代名词了。
《这样的战士》中,举着投枪的战士一直被视作是鲁迅本人的一幅精神自画像,战士走进的“无物之阵”和“无地”是一样的悖论式的矛盾构词。战士走进“无物之阵”,面对着“杀人不见血的武器”,面对一系列的“好名称”“好花样”,举起投枪,并且“正中了他们的心窝”,可在这之后却发现“无物之物”已经从外套中脱走,“得了胜利”,自己也成了“罪人”,在敌人胜局已定的情况下,战士一直在这个属于敌人的“无物之阵”的场域中战斗、衰老、寿终。这个发现“敌人”实为“无物”的矛盾推演逻辑在《野草》中不是第一次出现,就像《复仇》中的两个人,复仇的对象由原本意义上的“敌人”变为自己曾经试图挽救的民众,因而复仇的成功是无可奈何的成功一样。这里的“成功”和“失败”已经由两个相对的概念变为一个统一的概念,就像魏连殳所说:“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希望》里,主体从用希望的盾“抗拒空虚中暗夜的袭来”,到决心自己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再到发觉“又竟至于并没有真的暗夜”——对手根本不存在,又有什么成功或失败可言呢?就像《风筝》中的主体所感慨的:“全然忘却,毫无怨恨,又有什么宽恕之可言呢?无怨的恕,说谎罢了。”《希望》里的主体最终得出“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结论,和“影”的“我不愿去”一样,有个被叙事者视作理所当然不必说明而省略的大前提,即“希望是虚妄”的。一开始便发觉人间不值得停留,一开始便认为希望是空虚,可见《野草》的起点就是矛盾。旧的矛盾未曾解决,新的矛盾又已产生,直至最后发现连抗争的对象都是不存在的,事情本该以无解的僵局静止了。但发觉此局无解的人却仍然希求“于无所希望中得救”,提出“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7]477。要保留此反抗的姿态,便要把“成功——失败”“希望——绝望”之类的矛盾都暂且放下,“在最终定型的这句话中,既没有站在‘绝望’一边,也没有站到‘希望’一边,而是站到了‘虚妄’之上”。在这一番矛盾的进化和推演中,显然有新的逻辑生成了,在此新造的逻辑场域之中,原本被置于两极的“希望和绝望”不能通过肯定一极而达到否定另一极,因此“它不再是‘不明不暗’的固有状态,而是否定了所有前提和目的后的虚待之‘无’,是一次自我的‘清场’和‘重新洗牌’”[4]31。“虚妄”经由鲁迅再定义之后成为“希望与绝望”这一组矛盾的“中间地带”,其含义显然已经超越了其自身。就像“影”最终沉没的“黑暗”已经不是它一开始选择的“黑暗”,而是新的概念“无地”的代名词一样,“虚妄”也获得了语义上的新生长,成为了“无物之物”的代名词。
不难发现,为尖锐对立的矛盾两极寻找“中间地带”的过程,其实是诗人鲁迅寻找“新的语言”的过程。鲁迅在《题辞》的开篇就说:“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诗人张枣认为,这预示着这一时期的鲁迅正在面临严重的“语言危机”,而在这危机下诞生的《野草》对这场危机最终的克服意义重大,“在语言困境与克服困境的强大意志之间产生了一种独特的互动关系,正是这种互动连同其他因素一起,造就了鲁迅的伟大以及其文学的现代性”[8]40。鲁迅在尖锐的矛盾对立中寻找“中间地带”,与其说这个过程是“寻找”,不如说这个过程是“创造”。《颓败线的颤动》中被子女驱赶的老妓女,站在荒野的中央,过往的一切并合为“眷念与决绝,爱抚与复仇,养育与歼除,祝福与咒诅……”这些对立的二元矛盾,她于是“举两手尽量向天,口唇中漏出人与兽的,非人间所有,所以无词的言语”,“无词的言语”和“无地”“无物之物”一样是悖论式的矛盾构词法,这“无词的言语”就是诗人鲁迅为自己“沉默和开口”这一组尖锐矛盾创造出的“中间地带”。然而,雕塑式的老妓女可以使用“无词的言语”以自我表达,身为诗人的鲁迅却还要继续寻找语言以作为思维的承载物。这个“寻找”的过程显然又变为“创造”了,这创造显然不仅是对他自己语言危机的疗救,也是对中国新诗的一次伟大贡献。中国的旧诗人往往不只是“诗人”,中国的旧诗也因为其特殊的社会功能不只是诗,在“诗言志”的要求下,旧的中国诗和作为纯语言艺术的诗似乎天然有了距离。张枣因此说:“中国的古典诗歌没有寻找、追问现实,也没有奔赴暗喻的超度。我们的母语是失去了暗喻的母语,我们的民族是没有暗喻的民族。没有暗喻就不可能有真的纯文学。”[2]49鲁迅寻找的“沉默与开口”的“中间地带”,希望借由“无词的言语”寻找到思维与语言间隙之间的“言不尽意”,这个过程既是身为诗人的鲁迅自己寻找语言的过程,也是中国的新诗寻找新的栖息地的过程,这个过程恰是所谓的“现代性”萌芽和生长的过程。
但《野草》对尖锐矛盾的“中间地带”的找寻和创造,似乎还没有止步于此。假如“沉默与开口”的中间地带是指向暗喻的“无词的言语”,“希望与绝望”的中间地带是立于虚妄之上的“无物之物”,“明与暗”和“生与死”的中间地带是代替“人间”的“无地”,“过去与未来”的中间地带是代替“现在”的“不知道时候的时候”,我们还要继续追问,鲁迅要将这“一丛野草”献于的“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的中间地带又是什么呢?答案呼之欲出,是“我”。在寻找“归处”而不得、创造了“不知道时候的时候”和“无地”以彷徨,寻找“敌人”而不得、创造了“无物之阵”中的“无物之物”以对抗,寻找“语言”而不得、创造了“无词的言语”以表达之后,这位伟大的诗人还有一个任务,即需要寻找“自我”。而这个“自我”,显然和他的“归处”、他的“敌人”、他的“语言”一样,被置于重重矛盾因果纠缠的网中,是一个复杂的“悖论体”,这个“寻找自我”的过程,也必定如寻找“归处”“敌人”“语言”的过程一样,是一个需要诗人“创造”的过程。可以说,这个存在于鲁迅“自我”之上的重重矛盾才是《野草》最核心的矛盾。如果《野草》作者的灵魂不是这样一个复杂的矛盾体,语言的女神就不会让他成为这有诗性的“双声语对话体”的使用者,他也无从创作出《野草》这样伟大的作品。这个寻找和创造自我的过程,显然也和他在矛盾和悖论中产生新矛盾和新思想的过程一样,是一段在开放的场域中的没有终点的旅程。
三、从自我审问的主体到语言创造的主体
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中引用过卢那察尔斯基形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作为一个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自己算不上一个主人。他的个性的解体,他的个性的分裂,他想相信的东西却不能给他真正的信仰,他想否定的东西却经常使他狐疑不决——这一切使得他主观上适宜于做一个充满痛苦而又不可缺少的喉舌,来表达自己时代的不安。”[3]69这段话用以描绘创作《野草》时期的鲁迅的精神世界,居然也合适得惊人。鲁迅自己在《〈穷人〉小引》里这样写道:“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9]106可以说,在鲁迅的写作中,他自己一直既扮演着“审问者”,又扮演着“犯人”的角色。这首先和他对一切所抱有的“从来如此,便对么?”的怀疑态度和“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的探索精神密不可分。狂人一番研究之后,得出自己是吃过人的罪人的结论。《祝福》中的“我”被祥林嫂问倒后,得出自己“也还是完全一个愚人”的结论。魏连殳在“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之后问申飞:“你将以我为什么东西呢?”答案是自我放弃式的“你自己定就是,我都可以的”。不难看出,这个从自我怀疑到自我解剖再到自我厌弃的过程,在鲁迅的创作中是个常见的结构。他的在中国作家中难能可贵的“罪感”意识,显然与他天生多疑的个性和不肯自我放过的态度密不可分。就像钱理群先生所说:“他也绝不因为这种质疑而趋向另一端的绝对肯定,他总是同时观照、构想两个(或更多)不同方向的观念、命题或形象,不断进行质疑、诘难,在肯定与否定之间不断往复,在旋进中将思考引向深入与复杂化。”[10]75而这个自我怀疑、自我审问的过程,显然是鲁迅在《野草》中寻找和创造自我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过程。
《求乞者》中的主体“我”原本是被求乞者,以“居于布施者之上”的态度,给予求乞者“烦腻,疑心,憎恶”,但即刻,这个高高在上的“被求乞者”就开始自问“我将用什么方法求乞:发声,用怎样声调?装哑,用怎样手势?……”并且自答“我将得到居于布施者之上的烦腻,疑心,憎恶”。这个由布施者向求乞者身份的转换,其实就是“审问者与犯人”的身份一体性的一个有着高度象征性的版本。“我”说出“我至少将得到虚无”的声音,其实是一次对自我的宣判。《野草》中许多主体都获得了这个实际是来自作者自我的宣判。《风筝》中的“我”说“然而我的惩罚终于轮到了”,获得了兄弟说谎式的“无怨的恕”,无法再希求什么,心“只得沉重着”。《复仇》中两人的“也不拥抱,也不杀戮”,只是一种无奈的“复仇”:令看客无戏可看。《这样的战士》中战士对着敌人举起投枪直至生命消逝,而敌人“无物之物”却是胜者。《狗的驳诘》中,主体“我”被“狗”一通追问,由傲慢而偃旗息鼓,最终只好逃走。《墓碣文》中,“我”解不开墓碣上无解的问题,只好在墓碣的命令下“离开”,并且甚至“不敢反顾”。可以说,这个主体不仅被自我流放,并且身后始终有祥林嫂“灵魂有无”式的无解的问题一刻不停地追踪着他,咬啮着他的灵魂,无怪乎化为游魂的长蛇“不以啮人,自啮其身”了。
我们不禁要发问,鲁迅一直解剖、审判、拷问这个“自我”,是因为他对这个“自我”完全厌弃了吗?答案好像并不尽然。鲁迅在1924年写给李秉中的信中说:“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我虽然竭力遮蔽着,总还恐怕传染给别人,我之所以对于和我往来较多的人有时不免觉到悲哀者以此。”这段话被人引用得颇多,然而在下一段里,鲁迅接着说:“然而这些话并非要拒绝你来访问我,不过忽然想到这里,写到这里,随便说说而已。你如果觉得并不如此,或者虽如此而甘心传染,或不怕传染,或自信不至于被传染,那可以只管来,而且敲门也不必如此小心。”[11]452甚至在四天后,鲁迅又回一信道:“看了我的信而一夜不睡,即是又中我之毒,谓不被传染者,强辩而已。我下午五点半以后总在家,随时可来,即未回,可略候。”[11]453-454这口气诙谐又俏皮,相信这灵魂的主人恐怕也很难对它只有憎恶和厌弃。“影”固然对主体说“而你,就是我所不乐意的”,可临行前却还要“姑且举灰黑的手装作喝干一杯酒”来同他辞行,并且歉疚于没有什么可以赠予他。这份特有的温存,在底色如此冷暗的《野草》里是并不少见的,如“我”在梦中看到“美丽、幽雅、有趣”的“好的故事”,想要在碎影中把它留下,目光灼灼的一片“病叶”被“我”小心翼翼夹在《雁门集》里,“我”在冰谷里遇到“死火”,和它成为盟友,要带它出冰谷,最终被它的燃尽带出了冰谷。外壳冷硬内里滚烫的“死火”多么像这位诗人的一幅灵魂的画像,诗人在梦的最后安排它得偿所愿,终于“燃尽”,并且在自己的死亡到来后还要为了别人再也遇不到“死火”而“得意”,显然他也珍惜这不管有意无意成为他灵魂画像的死火。《腊叶》固然是“为爱我者的想要保存我而作的”[12]356,这口气看似漫不经心,但诗人安排主体“我”将病叶保存于《雁门集》中,本来就是对这“爱”的回应。
一个对“自我”全然死心的人是不会有那么多“我不愿意”的,不思考的灵魂固然没有思考所带来的痛苦,可会思考的灵魂难道会愿意为了避免这痛苦主动放弃思考的能力,甘于庸碌吗?恐怕至少鲁迅的灵魂是不会这样自我放弃的,否则他写不出《野草》。就是因为没有自我放弃,鲁迅才会对自己有这么多不满意。应该说,他最大的矛盾,其实是“我不愿意”和“我还想生活,在这社会里”[6]300之间的矛盾。否则他即使面临着语言的危机,也大可以先把真话痛痛快快说尽,不必有那么多说与不说、说真实还是说谎的顾虑。这层矛盾被他明明白白地写在《立论》里了。《立论》以往一般被视作社会批评,其实这个梦里的小学生和先生都是他“自我”的分裂,他不想“谎人”(因为“我不愿意”),也不想“遭打”(因为要在这社会上生活),先生只好建议他“阿唷!哈哈!Hehe!He,hehehehe!”这似是他的一场无奈的、自嘲的自述,即他所说的这些看似已经冷到极致的话,其实都是经过了很多妥协之后的敷衍。这时候再回过头去看《影的告别》,就能看出这个接连说出若干个“我不愿意”的“影”,当然不只是什么“鬼气和毒气”的象征,这“我不愿意”的酣畅淋漓的表达,才是那个看似被迫失声的主体一直以来期盼的表达,毕竟“我还想生活,在这社会里”的困难,几乎人人有之;可“我不愿意”的矛盾,对于在“想做奴隶而不得”和“坐稳了奴隶”的生命线上苦苦挣扎的国人来说,却显得太奢侈了一些。就像由于生理的构造,人的耳朵只能接收二十到两万赫兹的声波,在这个频率范畴之外的声音对人来说就只能等同于一片静谧,“我不愿意”这力量宏大的次声波、这属于伟大灵魂的“奢侈”烦恼,注定是难于被理解的。倘若不理解他的只有那些被他唾弃和憎恶的敌人,这对他当然没什么所谓,但可惜的是,他的“不愿意”对那些爱他的和他爱的人来说,恐怕也不在容易接收到的频率上。然而,他想要“在这社会上生活”,很大程度上也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们。想做奴隶的人们和能让人“坐稳奴隶”的时代、不选择真相的庸众和不允许真相的时代,他们彼此间相合,正负极的力量对撞,即归于虚无,得到属于彼此的大和谐,世间唯余不愿做奴隶者、不放弃真相者自身的矛盾和痛苦。就像傻子替奴才砸那泥墙开一扇窗,奴才立刻哭嚷撒泼起来,赶走了傻子又顺势向主人邀功。鲁迅的“开口”与“沉默”之间的矛盾不仅是个体的语言危机,他既不愿意说些“阿唷!哈哈!”式的废话,又不愿他的真实伤害到做着好梦的人们,“沉默”和“开口”的悲哀已经是妥协过的结果,对内心深处总是“不愿意”、也不想给自己留余地的鲁迅来说,这组矛盾几乎等同于真实和说谎之间的矛盾,无论是说谎还是沉默都让他痛苦,可是习惯了“瞒和骗”带来的虚假的舒服的人和时代却又拒绝他的真实。这就意味着,他必须自己带着这个无解的矛盾走下去。
鲁迅的精神气质,除了怀疑、探究、自虐之外,当然还有反叛。不论是对他的时代、对他的民族还是对他自己来说,他都是一个伟大的叛逆者。这种怀疑、探究、自虐并且反叛的精神气质,就是他可以自如地使用这晦涩、复杂、深刻而又美丽的“对话体双声语”的精神源泉。他用这特殊的诗学语言创造出的这片由他自命名为“无地”的场域,就是西西弗斯推石头的那座山,而他反叛的方式,就是“走”。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却也像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但我也并未遇到全是荆棘毫无可走的地方过,不知道是否世上本无所谓穷途,还是我幸而没有遇着。”[13]461-462
四、结语
《野草》是由一个又一个尖锐的二元对立矛盾组成的一个巨大的矛盾旋涡,身为诗人的鲁迅使用特殊的、富有诗性的“双声语对话体”,在这个复杂的矛盾旋涡里寻找并创造了名为“归处”“敌人”“语言”和“自我”的“中间地带”,在这个过程里诞生的新的语言,使中国的诗歌由暗喻缺失的古典范式中脱出,踏上寻找其自身“现代性”出路的旅途,迈出了极有象征性的里程碑式的一步。这个伟大的诗人,因其怀疑、探究、自虐且反叛的矛盾性的精神特质,被语言的女神选中,成为这晦涩、复杂、深刻而又美丽的“对话体双声语”的使用者,他也用这语言创作出了这部伟大的《野草》。他爱他的野草,并且不愿以这野草为地面的装饰;他在这个自己创造的纠结了无数矛盾且永不闭合的开放场域里,一直以“走”的姿态作绝望的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