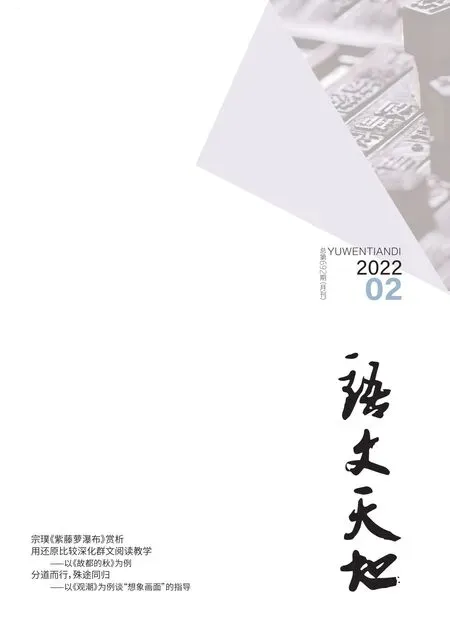察觉并理解“时间分岔”的奥义
——读博尔赫斯《交叉小径的花园》
杨 扬
高二选修教材《短篇小说选读》中第五个专题叫“小说怎样说”,编者力图在短小文章中呈现出别样的文本编排方式。小说不再仅用人物、环境和情节浇筑内容,作者博尔赫斯更是敷演出自己的文本“迷宫”来构建内容,并虚构自我宇宙的“时间观”。
一、阿根廷文豪
博尔赫斯是阿根廷诗人、小说家、评论家、翻译家,西班牙语的文学大师,在国立图书馆工作,一辈子徜徉书海。后来即便失明,依然通过口述继续创作小说和诗歌。博尔赫斯本人喜欢东方文化的神秘,他在该篇小说里也用“符号”“文化”“哲学”来表达自己心中的迷宫“哲思”。博尔赫斯拥有考究样式的写作手法,他将自己丰沛的知识运用在小说的开头,如引用《某某百科》《某某史册》的某某段落,用一段材料或者背景来辅佐自己的小说,这让他的文本看起来更像逻辑谨严的考究论文,《交叉小径的花园》第一段“欧洲史”正是体现了这样的艺术样式。
二、侦探小说的觉察
翻译家王永年先生在短篇小说集《小径分岔的花园》序言的开头写道:“第七篇《小径分岔的花园》是侦探小说,读者看到一桩罪行的实施过程和全部准备工作,在最后一段之前,对作案目的也许有所觉察,但不一定理解。”
于是,小说第一段就这样从真实的历史进入,《欧战史》的段落拿出来了。13团英军队(1400大炮)于1916年进攻,因大雨停止,这是一战的事实。小说虚构了人物俞琛,青岛市英语教员,有一份“怀疑的口述”,指出停战的原因是其他。博尔赫斯最喜欢的手法,把子虚乌有的情节糅入文献材料中,第一段似乎就要让读者真伪难解,陷入迷宫般的阅读效果。
小说就这样用第一人称叙事,通过文本的第2、3、4、38段落构造了侦探故事的大体概貌。俞琛,英语教员,中国人,间谍,受雇于德国,祖先叫崔朋。“我”的同伴是维克多·鲁纳贝格,他此刻被理查·马登上尉追杀。他要传递的消息是:英国人要炸德军,“我们”作为德军间谍,已经确切知道英国大炮的位置,就是第一段《欧战史》中1400英军大炮驻扎的地址。理查·马登上尉,冷酷无情的人,爱尔兰人,却服务于英国。他打死了鲁纳贝格,接着有一个小时追捕“我”俞琛。维克多·鲁纳贝格和“我”俞琛一样,也是德国间谍,但是被马登上尉杀了。还有一个人物阿尔贝,中国通,汉学家,在天津当过传教士,研究过“我”祖先“崔朋”留下来的书。课文中第2节中透露“我在电话簿上查到那个惟一能帮助我传递情报的人的名字”,还有37段,“我”实施“我”的计划,“我仔细开了枪”,阿尔贝立刻倒了下来。38段继续提到“那个城市的名称就叫阿尔贝,只好杀掉一个叫阿尔贝的人”。
此刻不难总结侦探故事的真貌:一战中,英国人要炸德军,而“我”俞琛作为德国间谍,正好知道英军执行者的具体位置,我利用城市与人“同名”的效果,杀死阿尔贝来传递情报。
三、理解“迷宫”与时间
整个侦探故事从第5到37段就是在讲述俞琛实施自己杀人念头的过程,过程中他与汉学家阿尔贝交谈,聊起曾祖崔朋,在崔朋身上绕不开的话题是手稿《交叉小径的花园》。 首先在第5段博尔赫斯透露自己是一位真正的个人主义者,他觉得自己无法成为任何人的仇敌,俞琛的心理活动也折射作者秉持的想法:“我想,一个人可能成为别人的敌人,但到了另一个时候,又成为另一些人的敌人。”小说里俞琛决意杀阿尔贝,并非因为阿尔贝是他的仇敌,而马登杀俞琛,也并非因为两人之间的直接仇恨。
接着在第21段,崔朋的迷宫,并非实体,文本中强调是“一座象征的迷宫”。“造一个迷宫”和“写一本小说”在这里是“一回事”。崔朋留下的小说复杂混乱,正是“迷宫”特点。曾祖小说的名字叫《交叉小径的花园》,花园就是“迷宫”。22段进一步写下了“小说”(迷宫)的特点:“我将我的交叉小径的花园,遗给各种不同的(并非全部的)未来。”迷宫象征小说,交叉的小路象征时间的分岔,不同的时间线,于是小说拥有“不同的时间线,也就拥有了不同的可能性和不同的结局”。
博尔赫斯不要读者误会他的小说里的“时间观”,它不是因为循环而无限,而是因为不同的时间线而拥有不同的故事结局。第24段,强调“这是时间上,而不是空间形象上交叉的形象”,交叉的小路在此刻有了隐喻的对象“不同的时间线”,因而“人选择一种”时间线,或者说故事的结局,就“排除其他”时间线,或者说排除了其他的故事发展的安排。于是曾祖崔朋“创造各种的未来,它们各自分开,又互相交叉”,他选择了各种可能性,也就是不同的时间线,衍生不已,枝叶纷繁,各种发展和结局都拥有了。
那么,时间是否有交集点,博尔赫斯又通过史诗作品的两种写法来表明“时间理论”的自洽和严密。一种写法是军队觉得“生命毫无意义”,于是绝望地取得胜利;另一种写法是军队经过“宴会”的鼓舞,于是充满希望地去取得胜利。虽然是军队选择不同的情绪,不同的战斗过程,但都指向一个结局——胜利,这是一个交集点。“我”俞琛也逐渐在阿尔贝教授的话语中,内心焕然而醒目的念头在慢慢清晰。第32段揭露了谜底,正是“时间”!它不是“绝对、一致”,它是“网线”,或者“交叉”,或者“隔断”,或者“接近”,或者“各不相干”,不同的形体,组合成“一切的可能性”。时间从常规的概念从起点顺时流淌到以后,到将来,到终点,从古而今的这种概念就此打破。博尔赫斯此刻赋予“时间”新的形态:不是绝对,而充满可能性;无数的可能性,就有无数的分岔,无数的生命发展和结局。
四、人世间的悲哀
即便如博尔赫斯那样赋于“时间”新的定义,我们在文本“追杀”的结局里依然没有看到人可以摆脱“命运的嘲讽和安排”。 汉学家阿尔贝早已参透曾祖崔朋小说,等待着“我”俞琛的到来,对“我”说出“某一个交叉点里,我是您的敌人”。而俞琛此刻作为一个德国间谍,也毫无犹豫“十分仔细开了枪”。马登上尉也在一小时后赶到,逮捕“我”,最终将“我”暗杀阿尔贝教授的消息登报,让一战中的德国识破。再次回应第一段中英军被迫推迟进攻的另外一个原因。 小说结尾中“我”俞琛陷入“无穷的悔恨和厌烦”,对应曾祖崔朋的“花园”理论,他已经杀了无穷次的阿尔贝。因为经过无穷的时间线,才会在文本的第3段里发生那么多巧合:选择“坐一辆街车”,我“买了张阿希格罗夫再远一站”的车票,“只有几分钟”我赶上了车,月台的孩子又恰好给我指路,阿尔贝的家虽然很远,但“每次只要左拐就能找到”。这些巧遇,正是俞琛透过“时间的花园”,在无数时间线中经历过了,而自己最终选择了最符合最准确的方式来完成一次杀害。
博尔赫斯似乎创造了新的“时间”:花园是喻体,时间就是本体。分叉的路是喻体,本体是分岔的时间线,不同的生活结局。这赋予人看待生活的新视角——“上帝视角”,俯瞰生活,跳出具体的某一次选择,某一次时间线,给予人类精神上片刻的自由和放松,也寄托人类要窥知自身命运的渴求。然而现实最好的例子就是,你一旦选择某一条时间线,你就排除了其他,有且只能经历一条发展结局的过程,人类终究还是对命运无从探知,无助而懊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