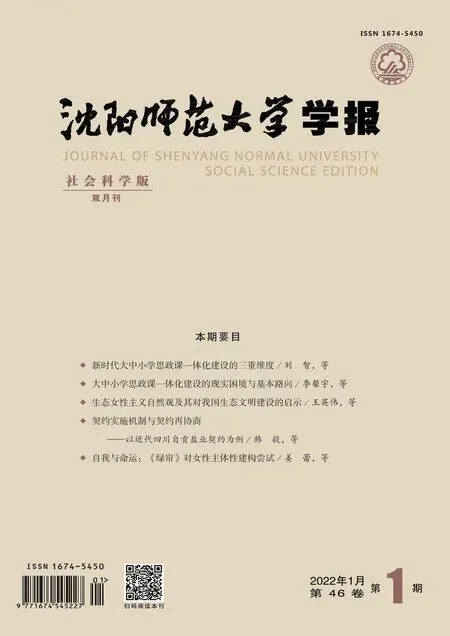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哲学基础
韩东旭,王国坛
(辽宁大学 哲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6)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1]50。应该说,生态文明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它不仅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还是一种“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2]394。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发展需要完成由外延发展向内涵建设的转型。同时,随着后疫情时代的来临,人们也在反思和质疑西方文明形态存在的危机及诟病。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便蕴含着人类未来新文明形态的“中国方案”。生命共同体思想既包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来社会发展的“中国模式”,同时也为世界提供了一种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形态。因此,从学理上揭示生命共同体思想内涵,特别是挖掘和确立其内在的哲学基础和根据是十分必要而迫切的。
一、中国传统道家哲学中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思想
中国道家哲学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开始思考人与自然统一问题。老子的《道德经》一开始就总论包括人和自然界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普遍规律。他认为,世间万物皆有名,而名都是来自无名。所以,整个世界都在有名与无名之间运作发展,具体表现为美丑、善恶、有无、难易、长短、高下等对立双方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关系。之后,他在《道德经》第25章又阐述了天地人各要素共属一体的根据:“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3]57老子一方面告诉人们,道是一种整体规律,整体中的各个要素是通过层层效法关系而隶属于整体的道;另一方面,他又告诉人们,虽然道乃无限广大,但道并非不可知,道就存在于我们身边的具体事物的变化发展之中,所以道不远人,人可以见近知远,见小知大。之所以远近一致,大小一体,是因为这些东西都有着共同的本原。《道德经》第42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3]92这里,除了说万物皆有共同本原外,还讲述了万物皆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这就是说,不仅人有生命,而且自然界也有生命。因此,人与自然才可能形成一个生命共同体。
中国传统道家哲学总结这些普遍规律主要目的是给人提供价值参照,也就是为人的执政方式和生活方式提供根据。刘笑敢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老子之自然表达的是对人类群体内外生存状态的理想和追求,是对自然的和谐、自然的秩序的向往。这种价值取向在人类文明的各种价值体系中是相当独特的。”[4]361可见,道家哲学的主要目的是给人们的生活实践提供理想目标。同时,也是对做人和生活方式提出的要求。
二、西方近代德国古典哲学为生命共同体思想提供了辩证统一的哲学观
西方近代历史主要有两大任务:一是实现上帝人本化以突出人在世界的中心地位;二是通过认识论的探索以实现认识世界的任务。资本主义是这两大任务的成果,这里暂且不谈。这两大历史任务实际上是自相矛盾的,主要反映在康德哲学中。这个矛盾就是:如果人要成为世界的中心,则人就必须摆脱宗教和自然界的束缚而达到自由。但人如果达到了这样的自由,就将在认识上存在不可知问题。要解决这个矛盾——既使人达到自由,又使人全面认识自然界——就必须在人与自然界之间寻找统一性。第一个尝试解决这个矛盾的人是德国哲学家谢林。根据黑格尔的看法,谢林在近代成了自然哲学的创始人。因为“谢林的功绩并不在于他用思想去把握自然,而在于他改变了关于自然的思维范畴,他利用概念、理性的形式来说明自然,他不仅揭示出这些形式,而且还企图构造自然、根据原则来发挥自然”[5]384。谢林认为,自然界是有理性的,但这种理性与人的理性是有区别的。他称自然为“死气沉沉的”“僵化了的”“顽冥不灵”[5]283的理智,它只是潜在的理智,还没有达到自我意识,这就是自然的理性与人的理性的差别。但是,在谢林这里,自然已经闪烁着理性的光芒了。那么,自然是如何来达到它自身的最高目的呢?是通过人,也就是通过人的理性。人的理性具有自我意识,通过人的理性活动,自然才能充分地发展到它的最高目的,于是谢林通过自然哲学的探索,使自然富有理性的内容和倾向。也就是说,宇宙本身是一个以自我为根据的有机体系统,宇宙中一切必须从一个最高的根据出发,也必须要服从一个统一的原理。如此,无论是自然万物,还是人类的理性认识都不过是最高“绝对”的不同样态的呈现。从这个意义看,自然是“绝对”的物质化样态,而人的理性则是“绝对”的精神化样态,二者同一于“绝对”本身。这便为我们提供了“万物归一”的、有机整体的世界观。
谢林之后,黑格尔有了更为深入的考察,他认为,“自然哲学是概念的考察,所以它就以同一普遍性的东西为对象,但它是自为地这样做的,并依照概念的自我规定性,在普遍的东西固有的内在必然性中来考察这种东西。”[5]394可以看出,关于自然界的考察,黑格尔强调的不是从外在于自然界的规定性出发,而是把自然界自身作为一个整体,从其自身的内在规定性出发来考察自然,自然的各个阶段“是在内在的、构成自然根据的理念里产生出来的”[5]397。这种构成自然根据的理念就是自然的理性。与谢林不同,黑格尔把自然理解为理性外化为现实的过程,黑格尔理解的自然具有历史性。也可以说,自然的本质就是理性,自然的最高本质是理性思维。而思维是精神的最高层次,可以统摄其他方面,包括意志、情感、想象、欲望等。精神是生命的本质,那么,自然不仅仅是外在于人的思维的有机体,它还是一个具有精神本质的生命体。具体来说,自然是一个生命体,具有内在的本质规定性,而这种本质规定性的表达只能是通过人的理性思维,通过抽象的精神劳动,只有人的理性思维才能抓住自然的本质规定,进而将其表达出来,成为现实。黑格尔充分发挥了精神劳动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却忽视了被动的方面。正因为如此,自我意识才能永不停息地外化与扬弃,在不断否定自身中实现发展。这就体现了精神劳动的创造力和推动力,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所以,马克思评价说:“黑格尔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把人的自我产生看做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做非对象化,看做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6]101可以看出,黑格尔实现了自己哲学的任务,即人(普遍理性)与自然(现实理性)在抽象的精神劳动中达到了和解。
从谢林到黑格尔,自然具有了精神的表达,这在西方近代具有非凡的意义。在人与自然界有了理性或精神的统一性前提下,一方面,人通过自我意识的统摄作用而有可能获得自由;另一方面,人也有可能全面地认识世界。但是,由于唯心主义抽象性的局限性,这既导致对人的理解的抽象性(人=自我意识),又导致认识上的局限性,即自我意识仅仅封闭在意识内在性圆圈中而不能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系。所以,费尔巴哈以感性代替了黑格尔绝对理性,实现了向与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的转变。但由于费尔巴哈不懂得黑格尔的辩证法,不懂得把感性当作感性活动去理解,因而他仅仅以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人和自然界。这样一来,他不仅只是达到了市民社会单个人的直观,而且在社会历史领域,他又必然导向唯心主义。这些问题的总根源,在于他的感性直观无法达到人和自然界的本质认识。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生命共同体提供了实践统一的哲学观
马克思在理解人与自然关系时,既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又吸收了费尔巴哈感性思想的唯物主义基本内核,并同时克服了二者的局限性。马克思运用了对象性的方法,把感性当成对象性的感性活动去理解,从而在对象性的感性活动基础上才真正达到了人和自然界的本质认识。
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只有通过感性活动即实践才能把握人与自然界本质及其对象性关系。实践在黑格尔那里被理解为抽象的精神劳动,是自我意识外化实现自身的抽象的历史过程。在费尔巴哈那里却被理解成了“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7]133。显然,对于以上两位哲学家的观点,马克思都不赞同。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是人自身本质力量的实现方式,是人的生命力的本质表现。又是互为对象性的人与自然界联系的中介,也是自然界本质规定性的表达方式。马克思所理解的实践,既不同于黑格尔抽象的精神劳动,也不同于费尔巴哈被动的感性直观。关于自然界,也是如此。马克思既反对唯心主义把自然当成绝对精神外化的现实部分,也反对旧唯物主义把自然当成被动的、客体的感性直观。他指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6]56马克思重点强调“物”的问题,当人的感觉和特性都得到彻底解放的时候,在实践中的感觉直接成了“理论家”,自然界纯粹的“有用性”才会失去。这样的自然界才是人的自然界,人化的自然界才能真正产生。
我们认为,自然界自身进化不是盲目的,而是有方向、有目的的,这种进化在自然界的本质规定性的指引下进行。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人也是自然界自身进化的结果。人出现之前的自然界,自然的生命本质处于潜在状态。只有自然界进化到人这里,这种潜在的生命本质才能达到现实。因为人具有自我二重化的特殊本质机能,这种特殊技能使得人不仅能够意识到自身,也能够意识到对象世界——自然界。人的活动的全面性在于人可以运用自己的尺度与自然界的尺度保持全面的统一,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人身上具有类本质,这种类本质是一种具有普遍理性的生命本质。那么,人的这种普遍的理性或是生命本质如何表达出来呢?也就是说,我们怎样才能把握和确证这种类本质呢?我们要从人的对象世界中把握,那就是自然界。进一步说,只有自然界具有普遍理性的生命本质即类本质,人才可能是类存在物,人与自然之间才能建立起普遍的、一般的联系。因此,人和自然之间是具有先验的统一性的。马克思也证明了这样的观点: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做自己的对象[6]56。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另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和工具。”[6]56这里面的深层含义,其实也表现出了马克思的生态哲学思想。自然界成为人的无机身体,变成人身体的一个部分,这进一步证明了自然界具有生命本质。那么,我们会进一步追问,自然界的生命本质是怎样实现出来呢?这要到自然界发展的最高阶段才能找到答案。在自然界进化的高级阶段里,“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6]105。人的身上具有自然本质,这种自然本质变现为视觉、听觉、触觉、语言、意识等先天机能,在此基础上可以满足人的吃、喝、穿、住等。人的这些自然本质是直接受到自然界规定的。虽然人的这种自然本质同自然界中其他生物(尤指动物)的纯粹自然本质是有区别的,但仅靠这一点,还不能完全体现出人的生命本质。因为人的生命本质的实现是一个人自身的发展过程、社会化的过程,马克思强调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135。也就是说,人只有在现实的社会化的过程中,自身全部本质的可能性才能完全实现,才能实现解放,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在这一点,马克思指出了唯心主义的错误,片面追求精神的自由来实现人的解放和追求人的自由是虚假的解放和虚假的自由,人必须在现实的生活中获得解放,才能实现全面的自由发展。这样,人的生命本质才能够全部实现出来。人的解放就是自然的解放,因为人是自然界本质力量的主体性的体现。马克思认为,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椭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设定的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它所以只创造或设定对象,因为它是被对象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6]105马克思这些话强有力地告诉我们,人不是脱离自然界独立存在的主体,而是在人与自然统一中形成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作为对象性存在物的人与自然界,通过对象性的活动,达到了本质力量的相互确证。只有对象性的存在物才能进行对象性活动,因为它们的本质规定中包含了各自本质力量的主体性。这也进一步证明,人与自然之间是具有先验统一性的,人实现解放的过程就是自然实现解放的过程。从历史观的角度看,人类历史既是实现人自身生命本质的过程,又是实现自然界生命本质的过程,完成了的人类史就是自然史。同样道理,完成了的自然史也是人类史。人在创造和设定自然的同时,也就是在创造和设定人自身,因为人本来就是自然界。
马克思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把握,并不是付诸感性直观,也不是通过抽象的自我意识,而是把自然当成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来理解,在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中确证二者的本质。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人自身本质实现的一个阶段,所有的可能性都蕴含在这个阶段里面,这些可能性的展开和实现一定是要到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寻找与确证。可以看出,马克思是通过阐述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自然与历史、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多重关系来说明自然界的生命本质的。人类史是自然史的高级阶段。在高级阶段里,自然界的生命本质可以完全得到确证和表达,人的生命本质同样如此,自然史的完成就是人类史的完成。这样,当我们考察整个自然史的时候,无人的自然界应该就是自然史的潜在部分或是低级阶段,自然史的发展同样经历了潜在、展开、发展和完成的各个阶段。人作为一种特殊的存在物在自然界出现之后,自然史进入了发展的高级阶段。在高级阶段里,自然界的生命本质通过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显现出来。自然史在高级阶段可以达到发展的完成,也就是人类史发展的完成。人属于自然界,人类史属于自然史。人类史是自然史的一个阶段,但绝不是简单的一个阶段,而是具有本质表达的高级阶段。在高级阶段里,自然的本质可以得到全部的表达,人类史可以看做是自然史的代言人。因此,马克思指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6]83所以,“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现实部分”[6]90。
四、寻求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哲学基础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既具有中国传统哲学的和谐智慧,又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内涵,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为解决中国当下生态问题,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指导,同时,也为解决全球性生态难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方案”。
生命共同体理念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新指南。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与自然原始的和谐被打破,资本中介物导致的必然是一种资本逻辑和货币原则,自然界变成了价值化的客体。人单纯地从有用性和利己主义的角度对待自然,必然会导致自然生态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自然问题,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的总体战略布局。自然生态是关系我们党的宗旨和使命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中国人民福祉的重大民生问题,又是关系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生产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和进步,但却伴随着自然环境污染、生态系统破坏等大量问题的出现。例如:大气污染、水污染、垃圾处理、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破坏等,其中一部分破坏甚至是不可逆的。这些自然生态问题的出现导致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需要无法得到全面的、充分的满足。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处于压力重重、负重前行的状态。因此,习近平提出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他强调的是两个方面的辩证统一。一方面,是“生命”的概念,按照前文的表述,不但人具有“生命”的意义,自然同样具有“生命”的意义,把自然简单理解为客观有机体是远远不够的。只有自然具有同人相统一的“生命”本质,人才能够在实践中同自然界建立普遍的联系,全面地把握自然界的“生命本质”。另一方面,是“共同体”的本质,这体现出人与自然是共存、共生、共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关系。若是片面强调其中之一,必然会造成片面的、孤立的、直观的、分裂的后果。当下经济发展中由于片面地强调了人的能动性,强调了人的“生命”本质,忽视了自然的“生命”本质,必然会导致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出现大量的自然生态问题。关于生态问题的治理与生态文明的建设,习近平持续关注并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指导性思想,他在2021年“领导人气候峰会”上发表了以《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主题的重要讲话,讲话中提出的“六个坚持”原则,既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创新发展,又为中国乃至全球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
生命共同体理念是走出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新路标。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是对象性关系。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人不是独立于自然界之外去认识和创造世界,而是作为自然界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在起作用。人的本质力量不是先天具有的,而是在对象性的活动中通过外化和扬弃的机能把自然界本质力量吸收到自身的结果。人与自然界之间本质力量的交换是不能通过直观来把握的,只能在实践中证明。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从根本上表明了二者是生命共同体的本质,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不仅关系着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而且还进一步关乎着全球的生态安全。因此,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建设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实基础。同时,“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8]171。绿色的发展方式,重点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调整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科技创新水平,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由粗放增长模式向集约增长模式转变;绿色的生活方式,要在社会中全面树立生态文明自信,增强全民的环保意识、节约意识、生态道德意识、行为准则意识,以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促进生产方式的绿色改革。这种生态文明自信的建立要体现出人的需要方式的改变:一方面,人不能一味地向大自然进行索取,要懂得回报自然;另一方面,人更应该注重自身需要的改变,不要一味注重自己索取多少,最重要的是得到社会的认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应该是这样一种状态:人既为自己存在,也为他人存在,而且只有为他人存在,才能真正地为自己存在。这时,人才能以审美的、诗意的生活方式为主[9]。由此可见,绿色的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内在的统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