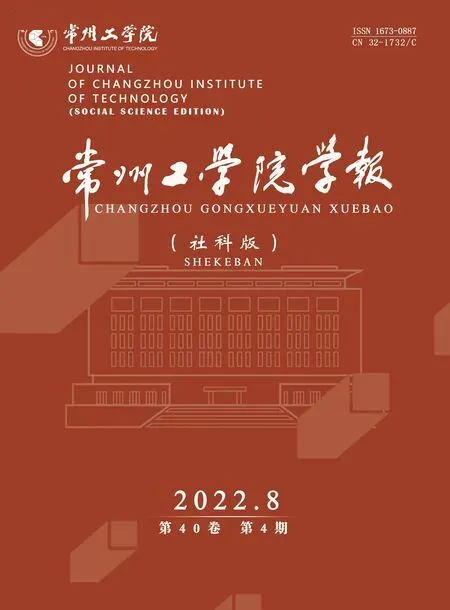《无声告白》中的家庭伦理叙事探析
王文哲
(河南警察学院外语教学部,河南 郑州 450046)
在《批评的伦理》中,希伯斯说:“伦理的核心就是对群体生活的渴望。”[1]家庭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组成单位,承载着最稳定、最核心、最典型的伦理关系。美国华裔女作家伍绮诗的处女作《无声告白》就是一部关乎家庭伦理的文学作品,小说以二女儿莉迪亚的突然自杀为开篇,讲述了一个中美混血家庭因为爱而失去爱的故事,华裔父亲詹姆斯是大学教授,母亲玛丽琳是一位追求独立的白人女性,3个孩子品学兼优,乖巧懂事,一切看似完美,却又危机四伏。
以往学者们对小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种族歧视[2]和创伤理论[3]方面,着重分析了华裔族群作为夹缝中的“他者”,在混杂空间里所遭遇的歧视和困境。也有人结合小说中不同女性的生活方式,展现了她们所遭遇的压力和苦闷。有学者从边缘人角度[4],分析了小说中两性角色的身份认同危机和身份建构焦虑[5]。还有一些评论分析了作品中家庭教育[6]等方面的失误,探讨了白人至上语境下跨族裔家庭教育的复杂性与艰巨性。总的来说,《无声告白》对传统华裔小说既有传承也有超越,它继承了华裔小说常见的叙事主题,也大胆跳出了纯粹华裔家庭的局限,小说人物进而从传统的华裔转向白人和混血儿,各色人群的故事与华裔的故事并存。在笔者看来,伍绮诗描述的这个中美组合家庭是受美国主流社会排斥的,其成员自然而然也都是边缘人。由于在价值观、生活习惯和种族方面与美国主流社会相异,他们长期处于伦理困境的两难之中,并一次次做出看似有违主流常规的选择,究其本质,他们都是在以各自的方式逃离令人憋闷的社会现实,追寻精神上的自由。然而迄今为止,还少有研究者从家庭伦理叙事的角度剖析该文本,因此,本文将对此作一分析。
一、夫妻伦理关系——误解与权力
詹姆斯和玛丽琳的跨种族婚姻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对彼此的错误认知基础之上的。詹姆斯认为玛丽琳是一个普通的白人女孩,普通到在第一节课上,他根本没有注意到她。而玛丽琳则被詹姆斯的独特东方面孔吸引。事实恰恰相反,玛丽琳最渴望能够与众不同,詹姆斯则希望能够隐没在人群中。带着对彼此的误解,二人即将结为夫妇,这桩婚姻却没有得到玛丽琳的母亲的祝福,她一遍遍地重复着“这样不对”,所说的“这样”指的就是跨种族的通婚。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就通过了反族际混血法,即使到了小说背景中的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对异族通婚依然并不友好,在弗吉尼亚的一些乡村地区,跨种族的婚姻是违反法律的,被认为丧失种族的自尊,混血儿处处受到歧视,他们的身份很难得到周围人的认可。因此,玛丽琳和詹姆斯的结合毫无疑问是有违当时的传统的。所谓“门当户对”并非专属于东方,而是人类共同家庭伦理观演化历史的浓缩,指的是男女在婚姻缔结的过程中,倾向于选择与自己在教育、种族、宗教、社会阶层以及价值观等方面情况相似的异性为配偶,因为相同的文化背景、教育水平、生活方式是稳固婚姻的纽带和黏合剂。根据美国社会学家巴纳德提出的婚姻梯度理论,在大多数社会的婚姻关系中,男性和女性在人格特征等方面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别,这种差别一般表现为“男高女低”,即:年龄上男大女小;学历上男高女低;职业上、经济条件上男优于女;等等。詹姆斯除了在学历上是哈佛博士,有一份教职以外,并无十分突出的地方。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对夫妇的婚姻都算不上良配。然而玛丽琳还是注意到了詹姆斯,他有着棕色的眼睛,像游泳运动员一样宽阔的肩膀和茶色的皮肤,那是被太阳炙烤过的秋叶的色泽,总之,“她从来没有见过像他一样的人”[7]36。而那些约她看电影、看橄榄球赛的男生,“外表似乎都差不多”,“这样的男生比比皆是”[7]38。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作为少数族裔的詹姆斯反而能迅速吸引玛丽琳,可以说,与詹姆斯的婚姻最大程度地实现了玛丽琳想要与众不同的愿望。
生活的平淡虽然会冲散浓烈的激情,但始终无法磨灭玛丽琳对个人理想的渴望。马斯洛曾指出,自我实现需求是“人对于自我发挥和自我完成的欲望,也就是一种使人的潜力得以实现的倾向”[8]。玛丽琳便是这样一个有着强烈自我实现需求的人。她从来都不甘心像母亲一样,一辈子只是家庭主妇,小小世界里只有丈夫、孩子和家务琐事,这样的人生是渺小、孤独、可悲的。这充分说明作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玛丽琳的伦理意识已经觉醒。但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即使第二次女权运动发展得如火如荼,给女性的思想和家庭伦理观念带来极大冲击,但女性被赋予的伦理身份依然是做一个贤妻良母,人生的重点在于相夫教子和操持家务。小说中的一个场景可以诠释这一矛盾:在大儿子内斯上一年级、二女儿莉迪亚刚上幼儿园之际,玛丽琳曾长篇大论地向化学系教授汤姆·劳森解释自己曾经就读化学专业,希望能成为他的研究助理,获得同意后,玛丽琳满怀希望憧憬着重回校园。然而詹姆斯对她的这一想法并不支持,他担心别人议论他挣得不够多,才导致妻子不得不出去找工作。为了丈夫的“颜面”与“自尊”,玛丽琳再一次放弃了成为职业女性的机会。此时的玛丽琳心如死灰,伍绮诗这样描述厨房窗外的环境:“外面已经没有了春天的感觉,风又干又硬,日渐升高的气温让院子里的水仙花低下了头,茎杆残破,无精打采地趴伏着,黄色的花瓣已然凋谢。”[7]91-92正所谓,景者情之景,情者景之情。我们不难体会玛丽琳在维持家庭伦理身份与追求社会伦理身份之间的摇摆不定与痛苦挣扎,一方面,她深爱丈夫和孩子,另一方面,她又难以割舍对个人梦想的憧憬,这种夹缝中的困境让玛丽琳不堪重负。
玛丽琳的母亲去世,它如导火索一般点燃激化了丈夫与妻子、家庭与梦想之间的矛盾。像当年异族通婚一样,玛丽琳决定再次挑战世俗,她“抛夫弃子”,离家出走以求能完成学业。这一冲突实质上是一种伦理冲突,涉及性别身份和社会价值。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就提到,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话语中已经意识到了社会性别不是由生理性别决定的,而是由社会建构的,强调了社会、文化在社会性别形成和分工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康奈尔在《男性气质》一书中指出,在性别秩序中权力关系的核心就是总体上维持女性的从属地位和男性的统治地位。“即使有中产阶级背景甚至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也很难避免这样的命运。”[9]作为妇女,就必须在各方面低于男人。因此,许多美国女性被迫安于一种单调且乏味的日子,困囿于烦琐的家务劳动中,看不到人生的前途,生活毫无意义。在中国,“三纲五常”中的“以君为纲,以父为纲,以夫为纲”同样体现了儒家提倡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要求女性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因此,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天性软弱、理应对男性顺从是社会对女性一贯的印象和要求。社会伦理环境要求女性处于从属地位,这是特定社会文化构建的结果,也是一种权力关系的体现,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并非一朝一夕能够转变。詹姆斯从小看到母亲操劳,而父亲深感愧疚却无能为力,这一幕深深地影响了他对夫妻关系的理解,他认为丈夫对妻子最高的爱就是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但这并不是玛丽琳想要的。结婚8年时间里,她学会了鸡蛋的6种基本烹饪方式,单面煎的给詹姆斯,煮熟的给内斯,炒鸡蛋给莉迪亚[7]84,这一切毫无快乐可言,她为鸡蛋难过,为一切难过。玛丽琳内心的痛苦不言而喻,一走了之是她又一次尝试挣脱这种令人窒息的夫妻伦理冲突的选择。
种族、家庭环境、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塑造了个体不同的价值观。詹姆斯和玛丽琳的对立还表现在语言上。两人在结婚时便达成了一条约定:让过去的事情过去,停止问问题,向前看,决不向后看。玛丽琳是被她不熟悉的异族文化吸引,进而拉进婚姻的,她从未向丈夫畅谈过自己的梦想。由于自幼饱受种族歧视的痛苦,詹姆斯也从未向妻子袒露过自己是“契纸儿子”后代的事实。这对夫妻之间从未就彼此心底的秘密进行过交流,这无疑预示了这个家庭必将产生某种危机。在调查莉迪亚死亡原因的过程中,玛丽琳对警察的调查进展和结果颇为不满,而詹姆斯始终以理性克制的态度配合警方询问。丧女之痛的绝望和愤怒使玛丽琳失去理智,她口不择言地说出,“不像某些人,我不会对着警察叩头”[7]113。很显然,作为白人的玛丽琳对这些话的杀伤力一无所知,这不亚于用锋利的刀子刺进詹姆斯的胸膛。他仿佛看到一群头戴尖顶帽、留着大辫子的苦力趴在地上,他始终怀疑在别人眼中,自己看起来唯唯诺诺,奴性十足,这是他最厌恶的样子。言语对立与精神隔阂就像越缠越紧的藤蔓,让这对夫妻“像两头并不匹配的牲口”[7]153,被强行套在一起却又无法挣脱。伍绮诗对詹姆斯夫妇形象与性格的刻画和其自身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作为第二代华裔移民,伍绮诗的价值观具有明显的杂糅特质:既受到了西方价值观的熏陶,也体现了东方价值观的影响。作者笔下的玛丽琳勇于打破性别限制,敢于向社会规范和家庭规则抗争,这符合西方价值观中的公平、自由和追求个性。而詹姆斯和他中国父母的勤劳、隐忍则体现出作者对中国传统优秀品质的认可。在伍绮诗看来,正是种族歧视、文化冲突以及以男性为中心的二元社会伦理体系为两性预设的性别角色,才最终造成了这对跨族裔夫妻的诸多问题。
二、父母与子女伦理关系——以爱之名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家庭生活方式是人们在特定的社会条件和价值观念的指导下所形成的满足自身生活需要的活动形式与行为特征。莉迪亚的突然死亡是小说的核心事件,作为父母的掌上明珠,夫妻二人很难接受这一结果,在他们查找事情真相的过程中,也看清了自己与3个子女的关系。詹姆斯和玛丽琳共育有3个孩子,分别是大儿子内斯,二女儿莉迪亚,小女儿汉娜,这3个子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得到的父母关爱却是天差地别。内斯和汉娜遗传了父亲的亚裔特征: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而莉迪亚却公然违抗遗传定律——有着和妈妈一样的蓝色眼睛。莉迪亚生理上的天然优势给了父母无限的希望,他们把各自未竟的梦想全部投射到她身上。詹姆斯虽然出生在美国,但是“契纸儿子”的后代是他深埋心底的秘密,东方面孔以及与中国有关的一切带给他的只有不安和自卑。他竭尽全力想要融入这片土地,却始终没有朋友和社交圈,游离于社会的边缘。被孤立、被排斥的痛苦他自己一个人承受就够了,作为父亲,詹姆斯无论如何不愿意看到自己的悲剧在下一代身上重演。这样令人难以启齿的经历导致他只关心莉迪亚有没有交到朋友,看到女儿和朋友们打电话,詹姆斯终于露出心满意足的微笑。可内斯和汉娜却知道莉迪亚其实一个朋友也没有。父亲甚至将人际交往变成了一项任务,送给莉迪亚的生日礼物也是《如何赢得朋友和影响他人》,希望她能尽快融入白人朋友圈,显得更像“自己人”。
如果说当年的意外怀孕中断了玛丽琳的大学学业,那么离家出走时的第三次怀孕则彻底终结了她的人生理想,她的宏伟复学计划只持续了9周,命运的轮盘再一次将她拉回到“舒适温暖,却压抑憋闷”的旧生活中。家庭是她的牢笼,也是她的软肋,更是迫使她放弃梦想的最后一根稻草。出走归来的玛丽琳转而将全部精力都投入二女儿莉迪亚身上,她倾尽全力想指引女儿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小到加减乘除的算法练习,大到提前学习高二物理甚至是大学化学课程,她都全程陪同亲自辅导,只希望女儿的成就能弥补自己心中永远的遗憾。母亲制订的学习计划迫使莉迪亚取消了所有的社交活动,而父亲又殷切地希望女儿能呼朋引伴,两者的愿望本身就南辕北辙。
面对父母如此炽热的爱,莉迪亚只能努力让他们开心满意。这一切都源于母亲曾经的离家出走,被抛弃的恐惧给莉迪亚幼小的心灵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拉卡普罗认为,“不能改变或治愈的创伤通常来自缺失”[10]。因父母抛弃而给子女带来的家庭创伤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年玛丽琳的不辞而别打破了家庭结构的平衡,莉迪亚认为是自己和哥哥没能满足母亲的期待。于是她暗自发誓,如果母亲能回家,她会实现母亲的每一个要求。自母亲归来后,每天放学,莉迪亚都会急于赶回家,确认母亲没有再次离去。她期待着从母亲口中说出“明天”的约定,因为这意味着母亲还会陪在她身边。母亲吩咐的每一件事,她只会答应“是的,是的,是的”,而她的真实想法却从不敢告诉父母:她不喜欢数学,大学物理太难了,她没有朋友,等等。恐惧与焦虑成了莉迪亚挥之不去的梦魇,作为宇宙的中心,莉迪亚被迫承担着家庭团结的重大责任,整个家庭都是因她而链接在一起,她被父母寄予厚望却几近窒息。重压之下的莉迪亚逐渐明白,“我们终此一生,就是要摆脱他人的期待,找到真正的自己”。于是,她深夜悄悄离家来到湖边,乘着小船飘到湖心,夜空下她决定改变这一切,将游回码头视为新生活的开始,却不幸沉入湖底。
作为莉迪亚之外唯一了解父母的人,内斯对她的痛苦感同身受。曾经,他也是父亲极力培养社交能力的对象。游泳池里,面对一群陌生的孩子,内斯被父亲催促着找大家玩,即使内斯只认识新搬来的杰克。詹姆斯没有耐心去理解小孩子之间的气氛,只觉得儿子的羞怯和迟疑像极了曾经的他,当年被戏弄的屈辱、对合群的执念使他不顾儿子的紧张不安,逼着他去学学怎么交朋友。在种族问题仍未破冰的年代,这样一厢情愿的结果可想而知,只是这一次被奚落的对象换成了内斯。目睹这一场景,詹姆斯很想把儿子揽进怀里,告诉他,自己明白他的感受。转眼间,他又想摇晃儿子,扇他一巴掌,把他逼成一个自信、受欢迎、合群的人。然而,詹姆斯最终什么也没有跟儿子说。曾经,选择逃避和遗忘是詹姆斯的处理方式,现如今,相似的经历在儿子身上重演,他再次选择沉默,他觉得这些痛苦终究需要内斯自己消化。这是内斯第一次失望,也是詹姆斯的合群之梦遭受的第一次和最痛苦的一次打击。之后,内斯又“因为‘太瘦’不能参加橄榄球队,‘太矮’不能打篮球,‘太笨’不能打棒球,只能靠读书、研究地图、玩望远镜来交朋友”[7]90。他早已习惯了父亲眼中的失望,母亲的视而不见。对内斯来说,世界是不公平的,10年来,他不仅要独自排解父母的忽视带给他的痛苦,还要一直支撑着莉迪亚,承担着她的重量,不让她一路下沉,直到他自己也不堪重负,录取通知书就是他获得自由的承诺。作为莉迪亚最大的精神支柱,内斯的同情和理解是她苦苦坚持的力量来源,内斯的即将离开无疑加速了莉迪亚的精神崩溃,她无法想象内斯离开之后的情景,她将一个人在家里赢得朋友、影响他人和成为科学先驱,没有人再会倾听她的心声,这也是为什么莉迪亚死后,内斯深感愧疚的原因。
如果说莉迪亚是整个家庭的焦点,内斯是聚光灯之外的暗淡背景,那么汉娜则是彻底的透明人。自婴孩时期,汉娜便住在阁楼上的卧室,那里堆放着没人想要的东西。即使长大一点后,家人们也时常忘记她的存在。小说中描写了这样一幕:“玛丽琳在餐桌上摆放了四只盘子,直到汉娜来到桌边,她才意识到少拿了一个。”[7]157每一次当她小心翼翼靠近家庭中的任何一名成员时,他们都会迅速把她从身上抖下来,或者把她哄走。在缺少关爱的家庭中,汉娜逐渐成长为善于察言观色的小孩:“她喜欢躲在角落和柜子里,还有沙发后面、桌布底下,退出家人的视野和脑海。”[7]157也正是因为近乎透明的存在感,使汉娜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个家庭成员压抑的内心世界:妈妈的疯狂施压,爸爸的沉默逃避,哥哥内斯的苦苦坚持,姐姐莉迪亚的不堪重负,这个危险又脆弱的家庭摇摇欲坠,最终失去平衡支离破碎。目睹这一切的汉娜决定不再做透明人,她要修复家人心中的裂痕。当玛丽琳孤独无助时,汉娜和母亲一起在莉迪亚的床头抱头痛哭;当詹姆斯回归家庭时,汉娜主动拽着他的胳膊,大着胆子依偎着父亲,和父亲重温姐姐莉迪亚小时候玩过的游戏;当内斯想要和杰克谈谈莉迪亚的事情时,因为担心打架,汉娜以惊人的力气拉住哥哥,她的出人意料表明她已经做好了靠近倾听的准备。自莉迪亚死后,汉娜逐渐勇敢地承担起自己在凝聚家庭中扮演的角色,坚定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通过证明自己的存在来疗愈家人心中的创伤,同家人们一起走出困惑与悲伤的泥淖。不难看出,家庭和谐的基础在于家庭成员之间能够互相关爱,而爱就是伦理性的统一。
三、结语
作为社会镜像的文学作品是“特定历史阶段伦理观念和道德生活的独特表达形式,文学在本质上是伦理的艺术”[11]。《无声告白》正是通过对家庭伦理的叙述,讲述了一个因为爱而失去爱的故事,从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角度细致入微地展现了跨种族家庭面临的伦理困境和情感冲突,通过倒叙、插叙、闪回等方式,曲折地反映了家庭成员之间的伦理关系,揭示了作家在小说中寄托的伦理立场和人性关怀。伍绮诗曾表示,这是她身边的人物和故事,也是读者自己的故事,从某种程度上讲,小说中詹姆斯一家被排挤、不被理解的恐惧感也是作家的心路历程的再现。正如伍绮诗在扉页上所写的“献给我的家人”,她以这部作品阐释了自己对婚姻、家庭、教育和责任的理解——家庭是支撑社会的脊梁,移除家庭,人们将失去赖以依附的支柱,四处游荡。
——《园丁》阅读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