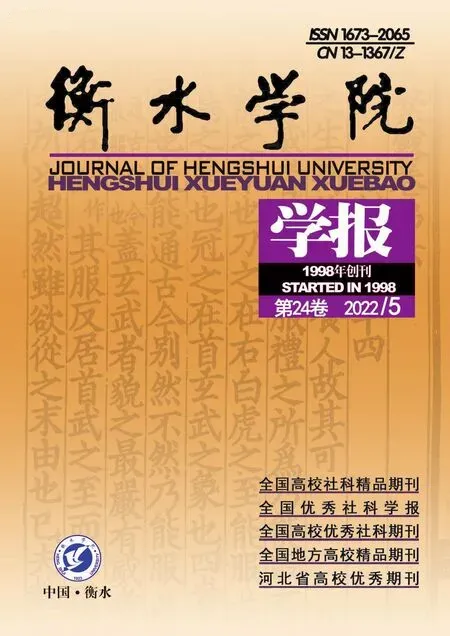《董仲舒与儒学研究》专栏特约主持人按语
作为中国哲学界的一位非常值得敬重的资深专家,向世陵教授长期研究宋明理学,对儒家仁爱思想颇有精当不刊之论述。他把董仲舒理解为“儒学史上天人合一论的重要代表”,董仲舒“是首先将本源性的天与儒家仁学直接关联并为之进行系统论证的哲学家”,给予了董仲舒非常准确的思想定位。董仲舒之前,儒家的天仁关系,偏向于“间接性的思考”,作为情感、德性或境界的仁,主要还在“人”的视域下被理解和运用,董仲舒释“仁”则基于天之仁,而创设出一套天道逻辑,“人之仁”是天之仁赠予的结果。天爱民,也爱君王。天现灾异,既在维护天的权威,也是珍爱君王不得已的手段。“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以仁厚远”是董仲舒推崇圣人之善的真实目的,以源于《孝经》的普遍之爱而“最充分地展现仁的情感和境界”。这些见解非常独到、有力,富有启迪价值,能够彰显出董学的博爱光辉。
天命转移是早期儒家的一大重要思想。著名海外董学专家邓红教授指出,董仲舒对“天命论”的贡献在于他没有停留在“一般性的故事传递和内容诠释”,而是独创了“天人合一”论,对“天命论”进行了“发展性改造”,并通过贤良对策而直接提供给作为“大一统”帝国秩序奠基人的武帝。其天命论是“天人合一”的“天命论”。司马迁以“天命”承传作为“大一统”历史观的核心,其整个叙事有神话也有历史,有理论也有情节,因而实现“天人相通”,通过“究天人之际”而达成“通古今之变”。作为深受董仲舒公羊学影响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按照汉帝国的天下观和历史逻辑撰写出一部“通古今之变”的历史。其中的“白鱼赤乌”则是殷商“天命”将要转移到周王朝的一个象征符号,不过是用于“究天人之际”的一个具象故事(story),是描绘“大一统”蓝图中的一个环节。《史记》所谓“究天人之际”其实就以儒家一脉相承的“天命论”为基调,再按汉帝国政治逻辑而编撰历史的一个“理论大纲”。诠释有新意,的确能够发人深省。
汉宋学术关系一向复杂、纠结,朱熹对董仲舒的评价虽说:“汉儒惟董仲舒纯粹,其学甚正,非诸人比。”“汉儒最纯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纯者莫如《三策》。”肯定其有传播周礼之功,但又并不满意,而以为春秋学、史学背景下的汉儒们多有牵强与自创。陈永宝副研究员认真梳理了朱熹涉及董仲舒的各种论述,具有重要的学术史价值。朱熹把董仲舒看作汉代为数不多的继承孔、孟遗训的儒者,是孟子与二程之间的重要过渡,而这种继承与朱子本人意图建构的心性之学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朱熹充分肯定董仲舒的传续之功,但对其人性论思想的“不纯粹性”却颇有微词。朱子始终把性理学视为儒学正宗,而非春秋学。朱熹遍注群经,唯独不注《春秋》,也可能是因为春秋学背景下的儒学思想并不是他所追寻的理想儒学模式。至于说“汉初诸儒专治训诂”,则显然是误解,公羊家、董仲舒皆以经义诠释见长;“今之做春秋义,都是一般巧说,专是计较利害,将圣人之经做一个权谋机变之书”,则又是没读《春秋》的先入之见。
近代中国,康有为发挥公羊大义,汲汲于维新之用,故其经学诠释总惹来饱学诸儒的不满,苏舆便是其一。刘芝庆副教授指出,康有为以今文经为主,苏舆则今古文并取;苏舆并非反对改革,只是批评康梁式作法,但并不认可革命。苏舆主张,《春秋》是立义之书,不是改制之书,忍受不了康有为的篡意。康有为的史学论证,总披着考据的外衣,“自己的话多,古人的话少”;苏舆的资料排比、训声考字,看似较为稳妥,其实也不是要呈现历史真相,而是要钩沉微言大义,发挥《春秋》“立义之书”的功能。康、苏之同则在于都坚持“义是第一序,事是第二序”。苏舆对“三代改制”的质疑,与其说是对口说系统的不满,对康有为的不认同,还不如说是对史实的追求。这些比较都切中了康、苏异同之核心精要,总结精当,概括准确,值得肯定。文末呼吁“回到《春秋繁露》本身”,其实更应该回到《春秋公羊注疏》本身,方能获得《春秋》要义。一味迷走或沉醉于康、苏解读之学术“八卦”,则如同吞下别人咀嚼过的饭菜。主标题著以“史实”,即已去公羊意旨甚远。
董子发挥《春秋》“五石六鹢之辞”,形成其独特的“名物”观,有别于“多识草木鸟兽之名”的名物训诂。张靖杰博士后指出,董仲舒继先秦名学思想之余绪,并将其组织进其宇宙论、本体论的论域之中。“物”的不同面向之间环环相扣,共成一体。这便突破和超越了历来研究者或将之归于“天人感应”框架内,把“物”当作天人关系中的参与者,将之归于认识的或语言或曰“名”的把握对象。由名物、真物、别物三个角度分析董仲舒的“物”哲学,发现了董子“名物”与孔子《诗》教之“名物”的不同,更侧重于“名伦等物”的含义,既包含了草木鸟兽之名,也包含人伦与政治制度,并且以后者为重。这些都是助推董学、富有启发的探讨,值得关注。
“汤武革命”是儒家内部一直有争议的问题。钮则圳副教授耙梳孟荀、西汉儒生的争论,联系汉初政权合法性与历史背景予以阐发。他指出,董仲舒强调“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设置了“天-君-民价值序列”,君王依附于天,百姓服从于君王,但天意又表现为民意。当统治者失德时,民意可以影响君位稳固。在“天人感应”思维模式下,上天也会对君王降下祥瑞或灾异以警醒,要求统治者讲求道德修养,避免“被革命”。于是天、君、民并不是单线条的依附关系,而是多元互动的关系。董仲舒由此而证明君王权力正当性,并巧妙地实现了对汉帝国政治的监督与批评。这些都是很有创意的诠释,具有很好的学术价值。
冯友兰是中国哲学史大家,他在不同时代所撰写的《哲学史》三书对董仲舒有着不同的论述和不同的评价。柴文华、张收指出,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对董仲舒哲学的系统梳理是“在西方哲学的框架下”进行的,“较为理想地”完成了董仲舒思想材料“由传统学术到现代哲学意义上的转化”,可视为中国哲学史“以西释中”的“典范”。但却看不到其给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带来的负面影响和宰制性伤害。至于“任何个人的思想也都一定会打上时代的印记,我们不能完全以跨时代的眼光去苛求前人”“作为哲学史家和哲学家的冯友兰,其本身对哲学史认识的不断深化和时代的发展共同造就了其对董仲舒哲学研究的动态变化”,则流于俗解,时代原因绝不能成为哲学史家丧失独立人格和独立思考的理由。
董仲舒养生观近来已成为一个学术热点,本栏目相继发表过唐艳、白立强的精彩专论。常会营副研究员紧扣《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文本,从“循天之道,以养其身”“民皆知爱其衣食,而不爱其天气”“人其天之继欤”三方面阐发董仲舒的养生哲学思想。人因循上天之道,以便存养其身体。董仲舒根据公孙之养气之说“君子怒则反中而自说以和;喜则反中而收之以正,忧则反中而舒之以意,惧则反中而实之以精”,君子无论喜怒忧惧,都必须返回到中,从而达到和、正、意、精的良好养生效果,所论平实、中肯。而援引世界卫生组织(WHO) 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道德健康的健康定义,也有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