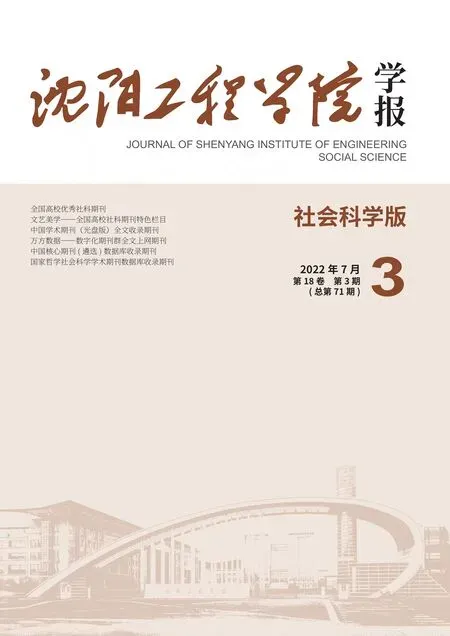亚裔美国小说中流散者伦理观与叙事美学研究
郑光锐
(中国医科大学 外语教研部,辽宁 沈阳 110122)
20 世纪90 年代伊始,全世界兴起移民热潮,同时,也引发流散研究的新热点。此后,“流散”演绎为诸多概念,即越界、家国(园)思乡、移位的创伤、文化身份、混杂性与多元文化等。可见,流散之内涵宽泛并具有深刻意蕴。近年来,亚裔美国文学创作方兴未艾,涌现出一批凸显流散主题或涉猎诸多层面的作品,“如对‘家’的寻求,对美国当今社会问题的探讨,对美国霸权历史书写的颠覆以及对世界主义主题的关注”[1]。亚裔美国作家洞悉所在国社会现状,深切体悟亚裔族群疾苦,汲取民族文化营养与创伤经验,发掘其伟大的民族精神。同时,他们赞颂流散者四海为家,重构其新的伦理身份与多元文化伦理观,弘扬其创建新世界之开拓精神。
此外,亚裔美国作家不仅注重主题创新,而且,其写作手法也有新突破。他们结合流散主题,采用诸多叙述策略:如非线性叙述、多重叙述、时空叙述与意识流等技巧,使小说主题书写与美学技巧相融合,构建出一种“混杂、错置、含混、属下的‘离散美学’”[2]144。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与叙事美学策略,发掘文本的多元意蕴。“该批评已经从单一的是非评价方法发展成读者、作者以及文学形式包括的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体系,实现从规定性向描述性的转变,从单一向多元化的转变,即布思所谓的‘批评的多元主义’”[3]52-53。故此,研究者不仅探究文本的流散主题,而且拓展文本之外的文化语境与审美意蕴。正如伊赛尔在接受美学理论中阐明“文本是一个充满各种潜在因素因而有待读者在阅读活动中加以具体化的结构”[4]582。
鉴于此,本文以文学伦理学批评与叙事美学理论,深刻探究《不适之地》《美国在心中》《同情者》等亚裔美国经典小说中流散者移居海外的伦理困境、心灵创伤与蜕变轨迹,发掘其多元文化观与文本的叙事美学特征,赞颂海外移民践行各族民众和谐互爱的至高伦理观。
一、亚裔移民伦理困境与非线性叙述之审美观
我国著名作家刘小枫指出,“伦理学是关于生命感觉的知识,考察各种生命感觉的真实意义”[5]。换言之,文学伦理学批评应探寻各种人物的人生意义,以及人物或事物之间关系演变过程与因果联系。同时,注重发掘文本的形式美,即“海因兹首次提到了文学形式的因素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意义,实现了该理论发展中的一个突破”[3]51。当今,学界研究亚裔移民流散中体现的思想美德与文本中叙事美学意蕴仍存在一定发掘空间,亟需学者深入探究。
1.追忆流散者乡愁所彰显的家国情怀
亚裔流散者身居异国他乡,常常把对故国与家乡的思念转移至海外同胞之情上,他们经常聚会、品尝家乡美食、共忆家园美景与难忘往事。他们的乡愁增进了彼此友情,凸显了人文关怀与人的精神追求。小说中的“人文关怀则是作家观照人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欲望,探寻人类生存的本质与价值、精神追求与道德思想的使命要求”[6]。诸如,印裔美国作家裘帕•拉希莉在《不适之地》“一生一次”短篇中,开篇讲述了少年主人公海玛参加父母为好友一家回归故国而举办践行派对的温馨场景:“家具擦得亮晶晶,桌上摆好纸盘和餐巾纸,家里充满羊肉咖喱、炖饭和比翼双飞淡香水的香味,妈妈在特别场合才用这种香水……”[7]显然,作者不仅描写同胞情谊,也通过他们品味家乡的美食,将流散者浓浓乡愁转换为对家乡美好的向往。接着,小说作者笔锋一转,采用非线性叙事技巧,以第二人称“你”回忆了主人公母亲讲述她过去与卡西克及家人的相识与友谊情景:海玛未出生前,其母与卡西克母亲在剑桥市小公园萍水相逢。此时,两位孟加拉族少妇相聊甚欢,彼此畅谈在加尔各答居住的美宅,眼前时常浮现美宅周边盛开的艳丽芙蓉与芬芳玫瑰花;她们还谈起婚前那段温馨的家庭生活。二人一同上街买菜、烧菜与织毛衣,彼此亲如姐妹。其间,两家还与家乡好友频繁举办家庭派对活动。可见,亚裔民众相互交往与友谊缓解了他们思乡愁绪,传承了民族文化,也保持他们的民族文化身份。同时,“离散者之间相互的信息交流又为他们在新环境中的生活提供了更多的机遇与方便”[2]108。拉希莉描写海外移民乡愁,这是人类存在的普遍性生存问题与情感寄托,凸显作者家国情怀。同时,作者赞颂亚洲移民勇于摆脱伦理困境,在创建新家园、融入新环境中展示的新风貌。
2.交错展现移民身份危机及其多元文化观重构
荣获普利策小说奖的越南裔美国作家阮清越在《同情者》中阐述了流散者异域思乡之情,褒扬流散者艰辛、睿智与奋进精神以及伦理身份重构之旅。小说以第一人称“我”叙述主人公漂泊海外的生活窘境:他与别人共居底楼的一居室内,阴暗潮湿中散发着臭味。主人公受聘美国西方学院东方学系秘书助理,每日从事琐碎的工作,拿着最低薪酬。令其纠结的是,该系女秘书莫莉对其的冷淡态度,常以俯视目光与他谈话。同样,系主任对东方知之甚少,却对他说:“在西方,许多东方特质被看成是负面的东西。”[8]74显而易见,亚裔移民处境艰难,也导致主人公伦理身份的缺失。
此外,该小说多处以非线性叙述与线性叙述交错展现,叙事错落有致,营造历时与共时交织叙说、回忆与遐想交融叙述的奇幻美感。诸如,主人公回忆在家乡时所喜爱的鱼露。他目睹鱼露制作工序复杂与精细,用它烹制的菜肴味美极致,回味无穷。此后,小说叙述又拉回现在,描写主人公写信告诉姑妈:“啊,鱼露!我们多想吃到鱼露啊,亲爱的姑妈,菜肴不加鱼露,味道有多么不正;我们多想再看看富国岛上规模庞大的酿造园,多想看看一排排盛满上等鳀鱼鱼露的大桶!”[8]82阮清越在小说中从饮食入手,以小见大,抒发他的家国情怀,表达了亚裔民众民族文化自豪感。接着,他又将笔触移至主人公在美国大学就职情景,描述他广受学生赞誉,也博得同事好评。主人公还详实论证东方人优秀特质而深得上司赏识,也改变系主任对东方人的偏见,并称赞主人公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继而,小说在追溯主人公功成名就之动力时,再次以非线性叙事技巧,回忆主人公在故国时,母亲坚定地对他说,“记住,你不比任何人弱一半,你比谁都强一倍”[8]165。主人公在母亲鼓励下,从不畏缩,砥砺前行,终成强者。小说作者将人物过去与现实交融展现,刻画主人公多元文化观与至美心灵。同时,作者展示亚裔移民家国情怀与践行各族友好的伦理观相得益彰,令读者感同身受,受益匪浅。
三、流散者伦理观蜕变与多维时空叙事美学
亚裔美国小说书写了亚裔流散者失落感、移位感与对精神家园的渴望。美国著名菲裔作家卡洛斯•布洛桑的《美国在心中》以第一人称,叙述其移居异国后的生存窘境、乡愁与艰难奋斗之旅。最终在布洛桑带领下,同胞们维护了自身权益,他也赢得众人的尊重。
1.菲裔移民伦理观重构与梦幻空间叙事美学
该小说叙述布洛桑在异国颠沛流离、生活拮据的历程。特别是,当他目睹两个哥哥摒弃使用本族语言时,其倍感民族文化身份面临危机。于是,布洛桑出版了多部弘扬本民族传统文化书籍,颇受人们赞许。
毋庸置疑,亚裔移民在多维空间中漂泊,这为小说作者拓展空间叙事视野,更利于追寻流散者身份重构之旅。“空间不是叙事的外部,而是一种内在力量,它从内部决定叙事的发展”[9]。布洛桑将梦境描写与叙事空间技巧巧妙融合,引导读者寻觅亚裔流散者伦理身份转换之艰难历程。同时,印证了“文本空间架构具有美学意义,并传达了独特的情感体验和叙事伦理。”[10]不言而喻,该作品创设空间架构,巧妙展现流散者漂泊异质空间的边缘美学,给读者以审美愉悦感。例如,小说中主人公穿梭于过去、现在与未来时空:他踏上美国西雅图,又被贩卖到冰魂雪魄的阿拉斯加等地务工。其间,布洛桑在领导工人运动时,被警察追捕,逃至洛杉矶市,幸运地被陌生人相救。他在住院时,受到好心人悉心照料,还赠送他文学经典著作,引导他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并成为著名作家。而后,小说运用时空转换手法,描写主人公梦境:他梦到自己回归故国家中,父亲说道,“你不要再逃走了,卡洛斯。我们有足够的食物了,儿子。”[11]继而,作者笔触又转回现实,叙述主人公获取新的文化身份,走上事业成功之旅。作者通过变换叙事时空,表达了亚裔民众渴望幸福生活与各国民众和谐共融的美好愿望。
2.印裔女子跨国婚姻危机与时空叙述交融之审美观
拉希莉在《不适之地》中叙述了印裔妇女露玛身处两种文化观困惑,倍感孤独与婚姻危机。她婚后为照顾幼子,辞去律师工作成为家庭主妇。该作运用空间叙事手法,描述她随丈夫辗转宾夕法尼亚、纽约市布鲁克林、西雅图。文本中空间屡次变换,预示主人公命运的逆转。先是与几位好友失去联系,不久又辞去工作;她身处陌生环境中,犹如笼中鸟。加之,丈夫常年公出,她独守空房,徒增彼此疏离感。此时,露玛将思绪转向多年前在布鲁克林时的美好时光:她参加妈咪互助会,多位好友陪伴在她的产房,她们经常去公园遛弯。小说打破时空顺序,将多处空间交错的情景呈现在露玛脑海中,暗示她内心错置与焦虑,以及对现状不满与无奈。
而后,小说作者的笔触又延伸至露玛丈夫转换的工作空间。其夫亚当就职美国多家公司,经常往返国内外各地出差。露玛不仅感到夫妻心理距离渐远,更意识到婚姻面临危机。此时,令主人公慰藉的是,她时刻思念已故母亲对她的挚爱,其音容笑貌浮现在她眼前,缓解了其孤独感。小说结尾处,主人公又将思绪转移到父亲身上,露玛喜欢父亲曾在她的花园里种植母亲喜爱的绣球花,并忆起父亲鼓励她尽快适应新生活的话语。从此,露玛踏上了新的人生之旅。可见,亚裔移民定居美国后,仍然保持与同胞联系及对家乡的眷恋。同时,他们也认识到只有开拓新空间、广交新朋友、践行多元文化观,才能开创美好未来。
四、亚裔移民伦理观重构与文本中多重叙事结构之审美情趣
亚裔美国作家追溯流散者海外漂泊轨迹,发掘他们文化身份困境与创伤渊源。同时,阐明他们多元文化身份特征。正如骆里山所言,“亚裔美国身份和离散文学具有异质性、混杂性和多元性的特点”[12]。
1.不同人物的多元文化观与套盒式叙述相融合之审美观
亚裔作家采用多元叙述结构,展示亚洲民众至美品格,追寻各国民众友好相处之场景。进而,赞美流散者“奋进”“开拓”“友爱”的高尚情操。诸如,拉希莉在《解说疾病的人》中将多重叙述技巧发挥得淋漓尽致,凸显文本多重审美观。作者在小说表层结构中以主人公赴异国求学就职的曲折经历为主线。同时,其在深层构设套盒式叙述结构,分别讲述了与主人公相关的三个女性感人故事:其母含辛茹苦地抚养两个儿子,她因丈夫病逝而患癔病,主人公陪伴其身边至辞世;其妻贤惠,精于素描与诗句,主人公婚后几日就赴美就职,妻子只身留在故国;房东与主人公和谐相处的情谊。这令主人公记忆犹新,也使读者感动万分。显然,该小说叙述了流散者伦理身份困境,赞颂他们家国情怀与多元文化融合的至高伦理观。可见,这种套盒式叙述手法,深化文本中不同人物的多重品格,为读者带来审美体验。恰如学者李靓评价该作,“小说有着丰富的内涵,在简单的表层文本之下有着含义深远的潜文本,看似简单的情节后面是对移民心理的多层次呈现”[13]。
2.不同民族文化差异与多线索并行叙述之美学特征
华裔美国小说《少女小渔》描写异国移民的流散生涯与其秉持的多元文化观,赞颂他们践行各族民众和谐共融的思想美德。作者严歌苓以少女小渔在异域中开创新家园为叙述主线,构成纵向结构,即在故事表层中,阐述小渔无私奉献与质朴的人格魅力。同时,还在故事中并行创设多重叙述副线,形成一种横向结构,阐明诸多人物迥异伦理观与矛盾冲突。例如,小渔男友江伟为获取澳洲绿卡,策划小渔与意大利老翁假结婚。然而,当小渔与老翁登记结婚后,江伟却郁郁寡欢;在小渔照顾中风老翁时,江伟冷嘲热讽,对小渔敬而远之。再如,意大利老翁固执、邋遢与龌龊:他整日饮酒浇愁,仅靠女友瑞塔做工维生,有时还盘剥小渔的钱物。还如,瑞塔懒散、刻薄:她不愿打扫房间,更为小渔来访而妒嫉,最终她抛弃老翁。小说以多重叙事结构,勾画了不同人物性格特征,也展现流散者坎坷人生,凸显了人类社会普遍性生存问题。
显而易见,该小说中纵横交错叙述与多线索并行叙事,建构了文本中的混杂美学。这为读者创造了众多缺乏话语权的“属下”阶层生存之审美体验。从而,增强主人公形象的立体感,深化文本多元意蕴。进而,彰显了亚裔族群崇尚和谐互爱的高尚情操。
五、结语
本文追溯亚裔美国小说中流散者异域漂泊之悲情与乡愁,发掘亚裔移民伦理身份缺失之渊源。继而,讴歌亚裔先驱们传承民族优秀文化、崇尚各族友好的高尚情操;展示亚裔后代开拓奋进、创建新家园的人格魅力;赞美他们践行多元文化观与为促进人类文明做出的贡献。同时,研究者探究亚裔美国小说多元叙事策略,以及所构成的“含混”美学特征。进而,丰富了读者审美体验,也彰显亚裔移民的至高伦理观,这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契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