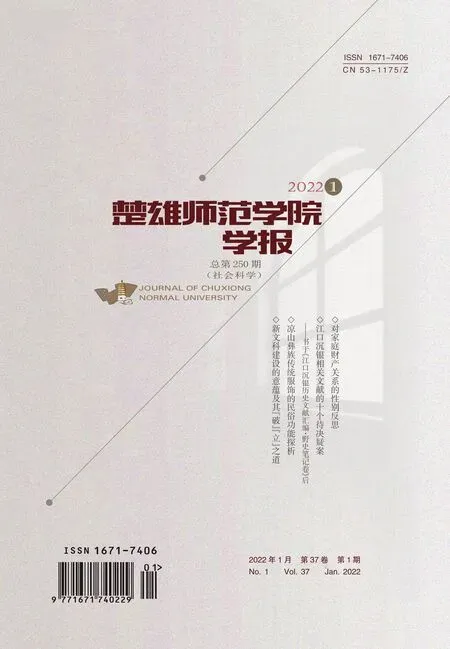社会圈层与社会话语的双重构建
——论第十二届骏马奖中短篇小说
张译匀
(中央民族大学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北京 100081)
各社会等级间存在着一个隐形的“圈层制”,不同圈层间有着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不能与其他圈层进行共融。权力是“圈层制”形成的至关重要的一环,米歇尔·福柯称:“权力并非是某种获取、夺取或分享的东西,人们不能把它抓住不放或让它溜走。权力的行使来自无数方面,在各种不平等与运动着的关系相互影响中进行。”①米歇尔·福柯:《性史》,姬旭升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1页。权力实际是一种关系,不计其数的权力构成了无所不在的权力关系网,也称之为“社会圈层”或社会“圈层制”。权力之所以战无不胜、无懈可击,其根源是权力来自任何地方,它在权力关系网中的任何一个节点都能生根发芽。譬如官场社会里的上级领导与下级领导;儒家文化里的长辈与晚辈;法制社会里的正义与邪恶;两性社会里的男性与女性等都是权力的生产地。
权力角色的确立,势必带动话语体系的建立。权力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主体,那么,话语实际上就是权力主体孕育的言说实践,称之为“主体性话语”。福柯“一切话语都是权力的话语,而一切权力都是话语的权力”②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23—27页。这一命题在无形中将权力和话语捆绑在了一起。在2020年评选出的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中短篇小说集,海勒根那的《骑马周游世界》、拉先加的《睡觉的水》(藏文)③拉先加:男,藏族,1977年出生。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短篇小说集《睡觉的水》荣获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因作品用民族文字(藏文)书写,故不在此次讨论范围之内。、李约热的《人间消息》、吕翼的《马嘶》、苏兰朵的《白熊》五部作品,就印证了权力与话语之间的隐形矛盾与关联。
一、冲突与妥协:坚守与逃避
权力的本质是关系,而权力本身就是二元论的,它既是权力的主体又是权力的受体,彼此之间存在一种“主体间性”,即互为主体。“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反抗”,一方面人们以主体身份对强势权力进行反抗,最终可反抗成功或是失败;另一方面主体在反抗的同时,又以受体的身份出现,常常伴随着反抗失败而告终,表现出认同或屈从的立场。
(一)权力冲突中的坚守
俗话说“一个人能力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即是说在赋予个人指挥权力的同时,个人也担当了对应的责任,若权力与责任不匹配时,就会直接导致“官僚主义”“贪官”的出现;一旦坚守权力与责任,造就的就是“廉政清官”。李约热的《人间消息》中,小说《村庄、绍永和我》通过驻村干部“我”的视角,将当下扶贫攻坚的艰辛和困苦悉纳笔底。我初次以驻村干部身份访问村民时,就遭受到了一次权力与责任之间的考量。在村主任的安排之下,我驻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劝说曾经身陷传销迷局的年轻人挣钱养家,替父分忧。突如其来的任务让“我”无法适从,作为一个在单位懒得和人说话、懒得和人分享的人来说,我是无法完成任务的。但因头顶驻村干部的名号,让我重新思考名号赋予的权力,而权力的施展与否则更多与自身责任心相关。不善言辞的我最终选择坚守手中权力,顺利完成了第一个驻村任务。海勒根那的《骑马周游世界》中,《最后的嘎拉》揭秘了锡林郭勒草原上一种古老的职业,“嘎拉”意为运盐的人。小说通过倒叙的方式讲述阿爸在运送盐的过程中,碰到了作为老一辈嘎拉的姥爷和我的母亲,阿爸对母亲一见钟情,却因嘎拉的身份以及手握更多人食盐的权力,在姥爷的催促之下与母亲别离,暂时搁下儿女之情,肩负起运盐人的使命。阿爸不仅坚守着权力的威严,更是坚守着自身的本心,从他身上我们得以窥探一个时代浮躁面影下的人性未受污染的坚守初心。
儒家文化影响了中国文化上千年,譬如“三纲五常”“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等男性权力的彰显及女性权力的弱化,乃至演变至今的“朋友妻不可欺”的男性权力道德规范,无不显示出男性权力的转化。吕翼的《马嘶》中,小说《逃跑的貔貅》里,舍且依靠卖石为生,有着自己的感情生活,但遇到发小马宽身边的女人英姿时,就暴露出男性占有的欲望,以及不顾当下“一夫一妻”的道德规范,想行使男性“一夫多妻”的权力——“他忍不住了,就会想英姿,英姿给过他亲近,给过他暗示……一方面觉得马宽太过分了,不仅拥有金钱,而且占有那么好的女人;另一个方面是朋友妻不可欺,他让舍且活着,重要的是要有一种品质。”①吕翼:《马嘶》,北京:作家出版社,2019年,第99页。在内心欲望和情感的纠葛下,舍且最后坚守了内心的道德品质,摒弃了由男性权力带来快感之后的愉悦。
“家和万事兴”的家庭权力推崇往往成为中国社会解决家庭矛盾的首选。苏兰朵的《白熊》中,小说《白马银枪》里,吕彤一次无意识浏览拍卖会网页的行为引发出一段家庭的爱恨纠葛。得知真相的吕彤在面对自以为是亲生父亲的男人突然转换成养父角色,另一个从未出现在自己生活中的男人却是亲生父亲时,“他感到从未有过的疲惫,心里空落落的……那种温暖太虚假”。②苏兰朵:《白熊》,北京:现代出版社,2017年,第109页。在面对是否承认生父时,吕彤的权力选择至关重要。在这里没有过多的权力争夺和权力冲突,更多的则是内心的纠葛,但吕彤秉持着“家和万事兴”的道德观念,坚守了道德本心,选择了就故事而言是正确的权力,显露出对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依恋。
权力的冲突在当今是常见的。譬如金钱和权力的冲突、价值和权力的冲突以及性别和权力的冲突等。在众多的权力冲突之下,人们最难做的就是坚持权力的本心和坚守权力的责任。而坚持权力的本心和坚守权力的责任也成为四部小说集里想要表达的一个重要主题。一方面个体选择权力时,需要我们坚守本心、坚守责任,选择正确的权力;另一方面权力选择个体时,在强调向心力和共同体意识的当下,很多时候社会环境会代替个人做出选择。例如前述中的道德观念和家庭观念的权力选择,或许是主人公的本意选择,又或许是主人公不想被社会诟病而做出的选择,无论出于何意,权力最终是朝向社会普遍认同的正能量。
(二)权力妥协中的逃避
权力之所以妥协是由于欲望的存在。因为在欲望之下,当人们内心信念不足以支撑时,便只好做出妥协来逃避权力的正义一面。站在卡伦·霍尔奈的“真实的自我”(即人所拥有的实现自身价值的生命潜能)①卡伦·霍尔奈:《神经症与人的成长》,张承谟、贾海虹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198页。来看,这种逃避应该被视为人物谋求逃避内心深处“真实自我”的外在表现。官场文学是本次获奖的中短篇小说里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官场文学常常与“反腐败小说”一词联系在一起,当今“以反腐倡廉现象为审美对象的小说,即‘反腐倡廉小说’(有的又叫官场小说或新官场小说)在文坛逐渐风行起来”,②顾凤威:《反腐倡廉小说的社会学、文化学透视兼论“依法治国、以德治国”方略》,《桂海论丛》2001年第5期。该类型不仅着眼于反腐败,更多的是反思权力体制和关注社会现实。
吕翼的《马嘶》中,小说《命定的石头》里,觉布是一位乡村壮年,以贩卖石头为生。因石头的造型独特,一时受到官场及生意场人的追捧,有身份地位的人纷纷购买石头或送石头来祈求平安、财富与仕途等,助长石头贩卖成了产业链。麻主任因受贿被双规,觉布为救麻主任出狱,无意识地充当了行贿者的角色。从讲述他人受贿到自己行贿的角色转变,透露出在面对金钱诱惑与他人崇拜中,权力坚守防线崩溃,权力坚守的初心被遗忘,人们在一次次的诱惑中不断妥协。而他们的妥协并不是逃避现实社会,是逃避内心深处真正的自我。如麻主任的虚荣心理,觉布自以为“知恩图报”的心理,都是其内心深处无法触碰的痛点,而这些在潜意识里也为他们的逃避和妥协找到了绝佳的借口。
二、话语与想象:不屈与寻找
话语秩序中,创作主体的内心深处往往隐藏着或隐或现的人格心理焦虑。面对权力的压抑,不同权力主体在同一情境下会作出不同的应对,甚至同一权力主体在不同的情境下也会选择不同的策略,这种心理防御策略的选择实际上体现了权力主体的基本话语立场。美国社会文化派精神分析学家卡伦·霍尔奈根据动物面临危险时的表现,提出三种人际关系防御理论:屈从、反抗和疏离找寻。③卡伦·霍尔奈:《我们的内心冲突》,王轶梅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7-18页。一般而言,屈从、反抗和疏离找寻这三种话语立场会在同一权力主体中共存,不过,客观来说,在某一个特定的空间中必定会有一个话语立场占主导地位,而另外两种话语立场则处于边缘位置。
(一)权力话语中的不屈
吕翼的《马嘶》中的《冤家的鞋子》,是乌铁、开杏和胡笙三人感情纠葛和命运转折的书写。在土匪横行、族群界限分明的乌蒙山,身为汉人的开杏和胡笙情投意合,却被金沙江对岸的彝人乌铁打乱了平静的生活,乌铁见色起意抢走了开杏。面对突如其来的灾祸,作为权力主体的人,开杏在被凌辱之前“猛甩头、猛动手、猛蹬脚,努力用嘴去撕咬……你做梦吧!你这个强盗!你这个野蛮子!开杏举起鞋子朝他头上砸去”④吕翼:《马嘶》,北京:作家出版社,2019年,第8-9页。通过肢体语言进行了反抗,直白的身体宣泄和明确的语言传达激发了她潜在的抵抗心理防御策略自然启动,开启了对自身及其话语权力的某种隐形自卫。但直接的反抗并没有阻止住乌铁的侵害,随后,开杏被乌铁捆绑回家。开杏作为权力主体又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抗,第一阶段开杏采取绝食,以死抗议,计划失败;第二阶段开杏痛恨自己的双手,她认为正因为自己在河边做鞋才被乌铁抢来,便用力将手指掰得变形,并试图用嘴咬断手指,也以失败告终;第三阶段开杏每天晚上都用热水和皂角清洗身体的各个部位,一遍又一遍,内心的抗拒似乎在该阶段成功了,但乌铁却不认为这是开杏在反抗,而只是单纯地以为开杏爱干净。
开杏从开始的以死相逼到摧残身体,都是她试图挣脱枷锁最直观的、也是最低级的自卫手段,可没有一次得到解脱。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成为乌铁女人的几年之后,开杏仍没有放弃作为权力话语主体的自卫行为。她不断用热水和皂角清洗身体的自卫,表面上看是让开杏找到了心灵救赎的方式,但实际上却是她内心深处对自我的否定与抵触:“我是一个脏女人,我是一个臭女人,这些日子以来,我天天洗,从未间断,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洗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洗干净”①吕翼:《马嘶》,北京:作家出版社,2019年,第31页。开杏依旧在现实和权力话语主体矛盾中斗争着。
权力主体的第二类是物。作为权力话语中的精神抵触者,物往往表现为一种在文化困境中或权力对立中自我抗争的精神人格,传达出人潜藏在内心的某种坚守和不屈。吕翼的小说《冤家的鞋子》中的“鞋子”便是这样的物品。居住在乌蒙一带的彝族群众有着赠送定情信物以表达爱意的风俗,其信物可是手帕、腰带、鞋子等,各地习俗不一,所赠送之物也各有特色。在小说中开杏对乌铁说:“你!你做梦吧!你要我的什么都可以给你……你怎么对我都可以,我都给你。但你要那只鞋,呸!下一世吧!”②吕翼:《马嘶》,北京:作家出版社,2019年,第21-22页。的一方面鞋子是开杏和胡笙爱情的见证,代表着他们对美好爱情的追求和向往;另一方面鞋子是乌铁最想要的信物,因为他觉得虽占有了开杏的身体,却无法得到开杏的心。鞋子既是自我抗争的物化表现,又象征着真实自我外化的“他者”的心理防御,这一点在《马嘶》中也得到了印证。在海勒根那的《骑马周游世界》中,小说《我的叔叔以勒》里的“鸽子”,象征着叔叔以勒想找寻的自由。反观叔叔的一生,他曾到铁路上装卸火车货物却折断两根肋骨,再到南方打工却误入传销组织。一件又一件的经历摧残着叔叔的肉体和心灵,但叔叔仍和命运抵抗,毫不屈从。某次鸽子的偶然出现,却和叔叔内心莫名地达成了“灵魂上的契合”,最后叔叔以勒便跟随鸽子飞走了,去找寻自由、传递幸福,这是他在精神上与生活进行“韧战”的艺术写照。
(二)话语想象中的寻找
审美性的自然或风俗话语的营造,使作家在各自的小说文本中建构了别样的话语想象空间。对于话语权力的压迫,这些如诗歌一样优美的话语如同某种“清洗剂”或“软化剂”,为主人公寻找自我提供了一个赏心悦目的精神家园。海勒根那的《骑马周游世界》中,小说《寻找巴根那》里,因被父亲一顿训骂的哥哥巴根那,一夜之间与羊群消失了。人们“用羊嘎拉哈为哥哥占卜,把七个羊骨头抛撒七次,这是一盘迷卦,嘎拉哈最终指向没有去向,相互抵消”③海勒根那:《骑马周游世界》,北京:作家出版社,2019年,第77-78页。风俗话语预示着哥哥巴根那已经无法找寻。而“我惊呆了,因为那眼神是我再熟悉不过的,它是属于乞彦姓氏的我的家族……那只头羊与我深情了片刻,跛着一条腿踉跄而去……”④海勒根那:《骑马周游世界》,北京:作家出版社,2019年,第85-86页。最终寻找到的哥哥巴根那,却化身成羊群中的领头羊。回顾哥哥的一生,其一,养殖兔子失败;其二,因家境差又跛脚,没有女孩做巴根那的妻子;其三,到城里做盖楼小工,工头卷款而逃。三件事情积压着哥哥巴根那,一直以来哥哥都处于“压迫——反抗——再压迫”的过程中,在抗争中他彻底迷失了自我,而家中的羊群就是哥哥巴根那找到真正自我的重要因素。“那莽莽苍苍的草原浑然横亘在黛色的天空之下,九曲蜿蜒的藏蓝色大河正在它辽阔的怀抱中缓缓奔流……一群群牛羊、一簇簇骏马……”⑤海勒根那:《骑马周游世界》,北京:作家出版社,2019年,第84页。小说对草原的审美性描绘,引申出了哥哥内心如草原一般辽阔、干净、无忧虑的真实自我。风俗话语的勾勒和自然美景的描写,净化了巴根那一生中的不幸与挫折,他最后找寻到了合适自我生存的方式即化身为领头羊。
在海勒根那的《骑马周游世界》中,《羊圈里的弟弟》里主人公弟弟三四岁时喝了羊奶,自此就不会说话,只会“咩”的发声,甚至最终与羊群同吃同住,或出于“奶水之恩”,又或者是“母亲之恩”,这一切都是弟弟在找寻自我的过程。其实生活在人类世界的弟弟并不开心:“弟弟是沉默不语的,和家人不说一句话……默默发呆”①海勒根那:《骑马周游世界》,北京:作家出版社,2019年,第102页。弟弟用沉默的方式拒绝着人类生活,而此时的弟弟仍旧是迷茫的,丢失自我的。直到占卜结果出来之后,“他正蹲在羊群的中央,歪着脑袋眨眼巴着一双黑眼睛,神态和羊简直没有两样”②海勒根那:《骑马周游世界》,北京:作家出版社,2019年,第105页。后续他是无意识地朝着结果发展,“与小羊们站在一起,他会欢叫连天,好像有唠不完的嗑”。③海勒根那:《骑马周游世界》,北京:作家出版社,2019年,第106页。风俗占卜成为弟弟的转折点,此后,弟弟不再无声抵抗,反而是光明正大地与羊群相处。而风俗话语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成了帮助弟弟找寻真正自我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诚然,上述的不屈话语与自我找寻都是作家让读者体验“他者”的一种投射。即通过人们潜在的心理同情,有意无意地发现并坚守了潜在的自我。譬如《羊圈里的弟弟》《我的叔叔以勒》《寻找巴根那》《冤家的鞋子》等,表面上是写主体异己的人物形象,其深层次则是人格心理结构中被压抑的真实自我的凸显。
三、文化与文本:批评话语的构建
西方在话语批评建立之初,笛卡尔、康德、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阿多诺和福柯等一批学者,就为话语批评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西方话语主体性的演变过程中,又经历了多次话语对象的转移,甚至趋向于“主体的隐退”。批评话语理论传入中国之后,其主体性话语就是用人道话语解构政治权力话语;用欲望话语解构公共人文话语,并迅速被“中国化”和“本土化”。例如:“天人合一”“和而不同”“文以载道”“身体欲望”等经过装扮,成为民间主体诗意的人生、民俗、文化的原始形象,纵观本次获奖的四部中短篇小说集无不彰显着“本土化”的话语权力。
(一)古歌、民间民俗文化与文本
所谓“日常生活诗歌”或“身体写作诗歌”,都来自对“象征”的解构而又无法重建象征体系。正因这种“象征”的缺失,诗歌话语犹如一种个人共鸣的语言孕育而生,“在共同体的象征秩序成为一种‘强置仪式’或‘象征的暴力’时,个人的内在性话语是对这种秩序的一种批判与解构,但这种象征秩序从共同体视阈中消失时……诗歌话语力图再次成为它的显现,哪怕仍然是碎片化的显现。”④耿占春:《失去象征的世界——诗歌、经验与修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9页。简明来说,诗歌话语是运用心理独白与自我的心灵对话,一方面传达出人们对自由和辽阔的呼唤;另一方面是对个体生命体验的审美表达,其真正表明的仍是对真实自我的寻找和回归。
“本土化”话语权力的彰显途径之一是引入民间歌谣的文学形式,并将歌谣置于主角的位置,贯穿全文。如海勒根那《骑马周游世界》中的“小黄马”就是以古歌的名字命名的,在这首古歌的背后隐藏着一个被救与救赎的故事。“小黄马的颠簸呀,使我的心没法安稳;美丽的姑娘哟,你是我的太阳,你的温柔和善良,永远留在我的心房。”⑤海勒根那:《骑马周游世界》,北京:作家出版社,2019年,第131页。古歌的歌词具有诗歌话语般的魔力,实现了小说人物与心灵的对话。古歌在文中一共唱响了两次,其一是弟弟扎勒嘎和母亲被土匪绑架时,弟弟给土匪唱了“小黄马”后,弟弟和母亲得救。小说写道“古歌接近尾声时,背着身的土匪肩膀微微抽搐了几下……乌铜的脸颊比平时湿润了一些,胡子上好像粘了几星晶亮的唾沫”⑥海勒根那:《骑马周游世界》,北京:作家出版社,2019年,第137页。很明显,土匪头人被这首古歌所感动,与诗歌话语般的“小黄马”产生了共鸣。其二是土匪头人被红军所擒,刑场上在土匪头人的要求之下,弟弟又再一次唱响了这首古歌:“小黄马若是有来世,我会修行做菩萨”①海勒根那:《骑马周游世界》,北京:作家出版社,2019年,第140页。在生命的尽头,诗歌话语再次显现,土匪头人似乎感悟到了心灵深处的自我救赎,与自我产生了对话,忏悔一生的恶劣行迹,建造情感寄托的“精神的庙宇”,让灵魂以此获得栖身之所。
“本土化”话语权力的彰显途径之二是引入民间习俗等仪式形态,通过习俗仪式的象征表现唤醒缺失的生活意义。李约热《人间消息》中的《南山寺香客》,因信佛结缘的李大为、寺庙主持李师和一对夫妻,几人出于不同的目的于佛教结缘,最终成为虔诚的佛教门徒,净化了内心的污秽,消解了行为的过错。在小说里“你不信就算了,但是你不能笑话佛”②李约热:《人间消息》,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43页。一句话表明了信佛人的心态,即佛祖的神圣性是不可侵犯的也是不容置疑的。作者将民间信仰文化渗透进民众日常生活中,对地方、宗教等因素进行强化,民俗文化话语在彰显人物情感时,亦是话语“本土化”不可或缺的部分。
(二)欲望主体与文本
欲望是由人的本性产生的想达到某种目的的要求,欲望并无善恶之分。从人的角度讲,它是从心理到身体的一种渴望和满足,人的消费行为和身体行为则是在欲望的渴求之下所产生。
欲望与身体。身体性话语是文学在“身体叙事”之内观照世界的一种价值选择。简单来说,身体在话语权中就等于欲望。而欲望往往涉及“女性身体”“性欲望”等敏感词汇,即在“被看”和“看”的权力关系中,暴露出男性价值观与“男权”。苏兰朵小说《白熊》中,“白熊”陈木身患抑郁,只有性爱可以让他感受到快乐。在和仿真女性玩偶凯伦的相处过程中,陈木将人生的不幸“释放”到凯伦身上,看到玩偶被蹂躏之后的残缺,陈木内心无疑是快乐的,只因为他一直是在与女性角色相处中寻求优越感。但最可笑的一点莫过于凯伦不是真人而是仿真女性玩偶,因凯伦的特性决定了她在“被看”和“性欲压迫”下没有反抗性,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这时,陈木霸露的“男权”就显得有些可笑和滑稽。吕翼《马嘶》中的小说《来自安第斯山脉的欲望》里,格布的爱慕之情得不到真人的回应,捡到的女性仿真玩偶就自然成了格布对女性恨意“发泄”的出口。
仿真女性玩偶在面对“女性身体”被男性“看”和“释放欲望”的过程中没有反抗性,这隐喻着女性在面对男性的身体欲望时,是麻木接受、无力还击的群体。男主人公选择仿真女性玩偶作为发泄对象,更多影射出“男权”对女性的绝对掌控只是男性的一种幻想。作品从外视角观照身体内视角,由内视角转到身体意义,进而将欲望、身体和时代思想相联系。
欲望与消费。消费是欲望的物质体现,欲望催生出消费。消费主义不仅影响商品的性质与商家政策,同时也影响到个人、集体和性别在消费方面的身份认同。例如,在身份认同或社会圈层认同的背景条件下,人们产生出金钱欲望、名利欲望和奢侈欲望等,进而带动了商场的奢侈品消费、餐桌的排场消费等。苏兰朵的《白熊》里,《歌唱家》中的王春生以模仿歌唱家浩良来维持日常生活,在得到浩良儿子杨十月的肯定之下,开始了利益追求与名誉追求。杨十月之所以同意这场欺骗行为,甚至成为该欺骗行为的策划执行者,一切都源于家庭经济压力以及自身好赌的特性。欺骗不仅给杨十月带来了歌唱家儿子的“荣誉称号”,也带来不曾想过的金钱财富,他自此追求与身份相匹配的奢侈消费。“看上了一条爱马仕丝巾,三千多块,决定买下来”。③苏兰朵:《白熊》,北京:现代出版社,2017年,第20页。作为欺骗行为的发起者王春生,起初也是为了满足基本生存的欲望,与杨十月展开“合作”之后,王春生从最初穿旧衣和发黑的白运动鞋,散发出羞涩和胆怯的气质,到成名后的名牌西服和发亮皮鞋傍身,倨傲的自信由内发散而出,这种改变可谓欲望的作用是功不可没的。王春生与杨十月相同的一点是在有了名誉和金钱的积累之后,就开始追求所谓匹配身份的高消费:“王春生整个人放松下来,从兜里掏出手机摆弄了两下,是一款崭新的iPhone6Plus。”①苏兰朵:《白熊》,北京:现代出版社,2017年,第41页。吕翼《马嘶》中的《命定的石头》里描写:“神佛谁不尊敬啊……佛石真起作用,把它当真佛供奉在堂屋里,祈求神佛保佑……本来感觉风声很紧了,感觉迟早要出事了……可供上石佛之后,居然一点事也没有。有事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②吕翼:《马嘶》,北京:作家出版社,2019年,第192页。只因石头上有形似神佛的图案,由此便打开了佛石的消费市场,佛石的价格也在不停地高涨。于是,觉布由此看到了隐藏在佛石消费后的“侥幸心理”“攀比欲望”,借机做上了石佛的买卖。
综上所述,海勒根那的《骑马周游世界》、李约热的《人间消息》、吕翼的《马嘶》和苏兰朵的《白熊》这四部获奖中短篇小说集,在现实主义和虚幻主义的交织下,在自然草原、乡镇小城和大都市的时空背景转换中,均凸显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权力观念与现代民众的博弈;官场文学中权力与信念的纠葛;权力话语中人和物的双重反抗。在当下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的语境浪潮中,文学与风俗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结合,是一种有根本价值意义的抽象,并且构成了众多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让人们由此窥见文学中影射的文化现象和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