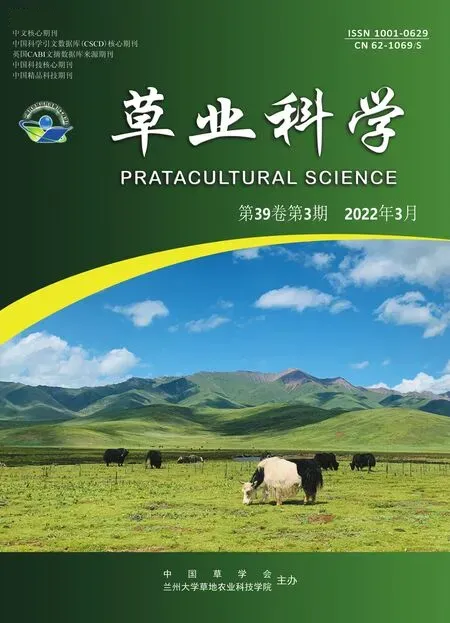种植密度对东方旱麦草生长与品质的影响
王玲秀,娄亚桦,邵 帅,2,3
(1.新疆农业大学草业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52;2.西部干旱荒漠区草地资源与生态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52;3.新疆草地资源与生态重点实验室,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52)
我国天然草地幅员辽阔,但过度放牧、粗放管理和自然因素导致草地退化严重,生态与生产功能低下。因此,建植优质高产的栽培草地是实现草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1]。草种选择、种植模式与田间管理决定栽培草地生产效能。在草地生产过程中,种植密度是制衡牧草产量与品质的关键。种植密度过高,种群内个体间竞争加剧,不利于生长,造成品质降低;种植密度过低,基础群体小,生长前中期叶面积生长慢,导致光能利用率低,生长速率小,难以获得高产[2-3]。在一定的施肥条件下,播种量 为450 kg·hm-2或 种 植 密 度 为400 万 株·hm-2时,燕麦(Avena sativa)的草产量与品质最优[4-5]。在中等种植密度375 万株·hm-2时,青贮大麦(Hordeum vulgare)具有较高的产量和营养品质[6]。王晓娟等[7]研究发现,在河西走廊中段,随种植密度增加,不同品种青贮玉米(Zey mays)的生物产量增加,收获天数延长,茎粗减小,持绿性降低,品质下降。低密度种植条件下,‘草原3 号’苜蓿(Medicago sativa)茎叶比较大,产量显著降低[8]。不同种植密度下,‘冀草1 号’、 ‘ 冀 草2 号’高 丹 草(Sorghum bicolor×S.sudanen)的株高、茎叶比及总产草量无显著差异[9]。因此,选择合适的种植密度是建植和管理栽培草地的首要条件。
在新疆北部地区,天然草地资源季节分配不平衡,特别是春草资源严重不足,家畜容易出现冬瘦春死的现象。在春季牧草短缺之际,短命植物适时萌发,成为家畜的主要采食对象,对恢复家畜体膘和提高幼畜的成活率具有重要意义[10-11]。利用短命植物生长特性,进行天然草地补播或建植专用于春季补饲的栽培草地,或可成为解决春季牧草短缺的可行方案。东方旱麦草(Eremopyrum orientale)是禾本科小麦族旱麦草属一年生短命植物,在新疆北部荒漠和荒漠草原地带较为常见,其质地柔软、分蘖旺盛、营养价值较高、适口性较好,是一种可以在春季利用的优良牧草[12-14]。关于东方旱麦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杂种保存技术[15-16]、基因克隆与表达[17]、种子萌发及抗旱性[18-19]、生殖生态学等方面[20],在牧草资源利用方面还未见研究报道。因此,本研究探讨不同种植密度对东方旱麦草生长与品质特性的影响,为建植适用于春季补饲的栽培草地与合理开发利用春季牧草资源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与设计
2019 年,东方旱麦草种子采收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清除杂质,室温保存。采用盆栽法,完全随机试验设计,设置3 个密度处理,即3、6、10 株·盆-1,约为100、200、335 株·m-2,分别用D1、D2、D3表示,每个处理重复6 次。2021 年4 月初播种,花盆(直径19.5 cm,高度14.0 cm)中盛装等重的取自原生境沙土,挑选籽粒饱满的种子每盆撒播30 粒,覆土深度为1~2 cm,每个花盆即为1 个重复,待出苗10 d 后,选择长势相同的植株,按照3、6、10 株·盆-1进行定苗,施尿素60 kg·hm-2和过磷酸钙60 kg·hm-2。生长期内人工去除杂草,每周一次。待出苗后45 d 进行相关生长指标的测定,并采集样品进行品质分析。
1.2 测定指标与方法
1.2.1 生长指标测定
在收苗时,每盆随机选取长势基本一致的5 株植株(D1处理选取3 株),采用直尺测量其基部到顶端之间的绝对高度,统计分蘖数,并使用游标卡尺测定茎粗、叶长与叶宽;将每盆植株的地上、地下部分分开称量鲜重,然后置于105 ℃烘箱内杀青30 min,65 ℃烘干至恒重,称干重。根冠比为地下干重与地上干重的比值。总生物量为地上鲜重与地下鲜重之和,单株生物量为总生物量除以对应的植株数。
1.2.2 牧草品质的测定
采用凯氏定氮法测定粗蛋白含量(crude protein,CP)[21];中性洗涤纤维(neutral detergent fiber, NDF)和酸性洗涤纤维(acid detergent fiber, ADF)采用Van Soest 法测定[22-23]。
1.3 统计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Excel 2010 整理统计,并采用SPSS 17.0 软件进行方差分析,用Origin 2018 软件作图。
2 结果
2.1 不同种植密度对东方旱麦草生长性状的影响
不同种植密度对东方旱麦草生长性状的影响不同(表1)。随着种植密度的增加,东方旱麦草的株高、叶长和叶宽均呈上升趋势,在D3处理下达到最大值,株高、叶长和叶宽分别为12.08 cm、48.80 mm和2.98 mm,D3处理下株高较D1和D2分别提高了49%和31%,叶长较D1和D2分别提高了39%和19%,且D3与D1或D2处理间差异显著(P< 0.05),D1与D2处理间差异不显著(P> 0.05);D3处理下叶宽较D1和D2分别提高了27%和16%,D3与D1处理间差异显著,D3与D2、D2与D1处理间无显著差异。随着种植密度的增加,东方旱麦草的分蘖数与茎粗没有显著变化,各处理下每株分蘖数为4~5个,D1处理下茎粗最大,为1.55 mm,D2、D3处理下茎粗大致相同,为1.33 和1.34 mm。

表 1 不同种植密度对东方旱麦草生长性状的影响Table 1 Effects of different planting densities on the growth traits of Eremopyrum orientale
2.2 不同种植密度对东方旱麦草生物量的影响
东方旱麦草的总生物量和总地上生物量随种植密度的增加呈增加趋势,在D3处理下达到最大值,分别为148.79、105.59 和43.21 g·m-2;且D3处理下总生物量和地上生物量与D1处理间差异显著(P<0.05),D1与D2、D2与D3处理间无显著差异(P >0.05);地下生物量在各处理间无显著差异。在不同种植密度下,东方旱麦草的单株生物量与总生物量变化不完全一致,单株地上和地下生物量均无显著差异。根冠比之间亦无显著差异(表2)。

表2 不同种植密度对东方旱麦草生物量的影响Table 2 Effects of different planting densities on the biomass of Eremopyrum orientale
2.3 不同种植密度对东方旱麦草品质的影响
东方旱麦草的CP、ADF、NDF 含量均随密度增加呈增加趋势,各处理间差异显著(P< 0.05) (图1)。在D3处理下,东方旱麦草的CP、ADF、NDF 含量最高,分别为26.07%、30.81%和40.92%;D2处理次之,D1处理下含量最少;D3处理下CP 含量较D1和D2分别提高了10%和6%,ADF含量较D1和D2分别提高了33%和19%,NDF 含量较D1和D2分别提高了21%和7%。

图1 不同种植密度对东方旱麦草品质的影响Figure 1 Effects of different planting densities on the quality of Eremopyrum orientale
3 讨论与结论
3.1 不同种植密度对东方旱麦草生长性状的影响
种植密度是影响植物性状的重要因素之一。种植密度在合理的范围内,植物间会产生正相互作用,植物性状表现良好[24-25]。在黑龙江地区进行施肥和种植密度对5 个燕麦品种产量和品质的研究表明,随种植密度的增加,燕麦的株高显著提高[4]。在青海海北州地区研究不同播种密度对23 种多年生牧草生产性状的影响发现,不同的播种密度对牧草的草层高度有一定影响,密植时牧草的草丛高度普遍较大[26]。对高羊茅(Festuca elata)与黑麦草(Lolium perenne)混播对密度效应的响应研究[27]表明,在生长前期 (移栽后60 d),混播条件下的高羊茅叶长与叶宽伴随种植密度增加而升高,表现出正相互作用;单播条件下的高羊茅与黑麦草叶片宽度随种植密度增加而下降,表现出种植密度的制约效应。本研究中,335 株·m-2处理下东方旱麦草的株高、叶长与叶宽均较100 和200 株·m-2处理好,说明高密度的种植能够促进株高、叶长与叶宽的生长,高密度种植对东方旱麦草的株高、叶长、叶宽产生了正相互作用。此外,不同处理下的茎粗虽无显著差异,但100 株·m-2处理下的茎粗较200 与335 株·m-2处理的略大,这与罗金等[28]研究结果一致。这可能是因为种植密度可通过影响植物生理状况和冠层结构来调控植株的生长发育[29],随着种植密度的增大,相邻植株冠层遮蔽,引起植物的避荫反应,使其将更多的同化物从储存器官分配到营养器官,引发茎秆快速纵向伸长,导致壁厚变薄、节间直径下降[30]。王岩等[31]研究结果亦表明,随着种植密度的增加,辣椒(Capsicum annuum)植株的株高呈增加趋势,茎粗呈下降趋势,其原因是密植压缩植株横向生长空间,进而促进了植株纵向生长。
种植密度对牧草甘蔗(Saccharum officinarum)‘闽牧42’影响的研究表明,种植密度可非常显著地影响种植当年的牧草分蘖数,且随种植密度的递增牧草的分蘖数相应降低[32]。不同播种密度对饲用燕麦‘太阳神’生产性状影响的研究表明,随播量的增加,单株分蘖数逐渐减少,低密度下植物的分蘖数极显著高于其他高密度处理[25]。本研究表明,随着种植密度的增加,东方旱麦草的分蘖数无显著变化,这与前人研究结果不一致,可能是因为在此密度下东方旱麦草的分蘖数不受影响;同时,植物自身的品种差异、地域之间气候因子均会影响植物对密度的响应[33-34]。胡宏伟等[25]研究亦表明,播量不同,植株生产性状有差异,播量较小的小区,单个植株生长所需的营养充足,分蘖表现较好。反之,播量较大的小区,单个植株生长所需的营养不充足,分蘖表现较差,这可能与植株所占有的营养主要供主茎生长有关,因此,本研究设置的3 个种植密度下东方旱麦草单株生长的营养充足,所以在促进主茎生长的同时其分蘖表现一致。
3.2 不同种植密度对东方旱麦草生物量的影响
低密度下单个植株的生长空间较大,资源充足,但群体产量受到个体数量限制。相反,密度增加提高群体产量的同时也会导致群落内资源竞争增加[35],影响单个植株的生长发育和干物质积累[36]。种植密度对达乌里胡枝子(Lespedeza davurica)生物量的提高主要是通过群体产量实现的,但对单个植株而言密度的影响为负效应,主要是因为种内竞争加剧所致[37]。随着种植密度的增加,玉米单株的饲用物质产量显著降低,但群体鲜物质和干物质产量显著增加[38]。本研究表明,不同种植密度下,东方旱麦草单株生物量无显著差异,但群体生物量显著提高,由此可见,种植密度对东方旱麦草生物量的提高主要是通过群体产量实现的。这可能是因为种植密度的增加显著增加了植株数量,提升了收获产量[39],也有可能是在此种植密度和营养供给条件下,东方旱麦草种内存在的正相互作用与负相互作用相当,使得在促进群体生物量的同时单株生物量没有随密度的增加而降低。此外,不同植物种群密度存在差异,荒漠植物种群在不同环境与气候条件下波动极大,猪毛菜属(Salsola)植物种群密度在10~2 000株·m-2[40];有研究发现,沙地一年生草本植物狗尾草(Setaria viridis)和虫实(Corispermum macrocarpum)最高种群密度分别为267 和846 株·m-2[41]。种群密度增大会抑制猪毛菜(Salsola collina)个体生长,进而导致生物量分配发生显著变化[42]。在本研究中,可能由于密度梯度设置较少,最高种植密度约为335 株·m-2,并不能完全反映种植密度对东方旱麦草个体生长的影响。
3.3 不同种植密度对东方旱麦草品质的影响
粗蛋白、中性洗涤纤维和酸性洗涤纤维是衡量牧草品质优劣的重要参数[43]。合理的种植密度不仅能够提升土地资源利用率,更能对牧草品质产生显著的调控效应。随着种植密度增加,青贮玉米[44-45]、燕麦[4]粗蛋白含量降低,同时酸性洗涤纤维与中性洗涤纤维含量升高。种植于沿海盐碱地的饲用高粱(Sorghum bicolor)粗蛋白含量随种植密度增加呈先升后降的趋势[46]。在苜蓿中也有类似的发现[47]。本研究结果显示,东方旱麦草的粗蛋白、中性洗涤纤维、酸性洗涤纤维随密度的增加而增加,与前人研究结果略有差异;随密度增加,粗蛋白增加的原因可能是东方旱麦草的粗蛋白主要集中于叶片中,茎秆中蛋白含量较低,而随着密度的增加其叶片的长度和宽度增加,因此粗蛋白含量也呈现相同的趋势。酸性洗涤纤维、中性洗涤纤维含量与牲畜采食率和适口性呈负相关关系,纤维素含量越高动物消化率越低,饲用品质越差[48]。随着密度增加,东方旱麦草的株高增加,茎秆变长,造成植株的中性洗涤纤维和酸性洗涤纤维增加,饲用品质降低。
根据牧草特性建立物种与品种多样化的栽培草地能够避免发生爆发性灾害的风险,提高牧草生产力和生态系统稳定性,真正实现生产和生态功能的双赢。短命植物以其独特的生存策略有可能在栽培草地建植上发挥其特殊作用。本研究结果表明,高密度种植对东方旱麦草大部分生长指标的促进作用最大,并且能够显著增加群体产量和粗蛋白含量。因此,在10 株·盆-1(约335 株·m-2)种植密度下东方旱麦草能够在春季补饲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另外,为了明确种植密度对东方旱麦草群体和个体生长的影响,仍需要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