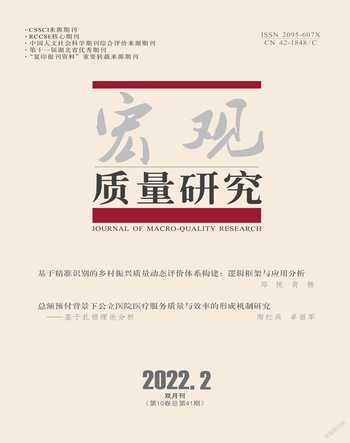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民主观生活质量变化及影响因素研究
周长城 王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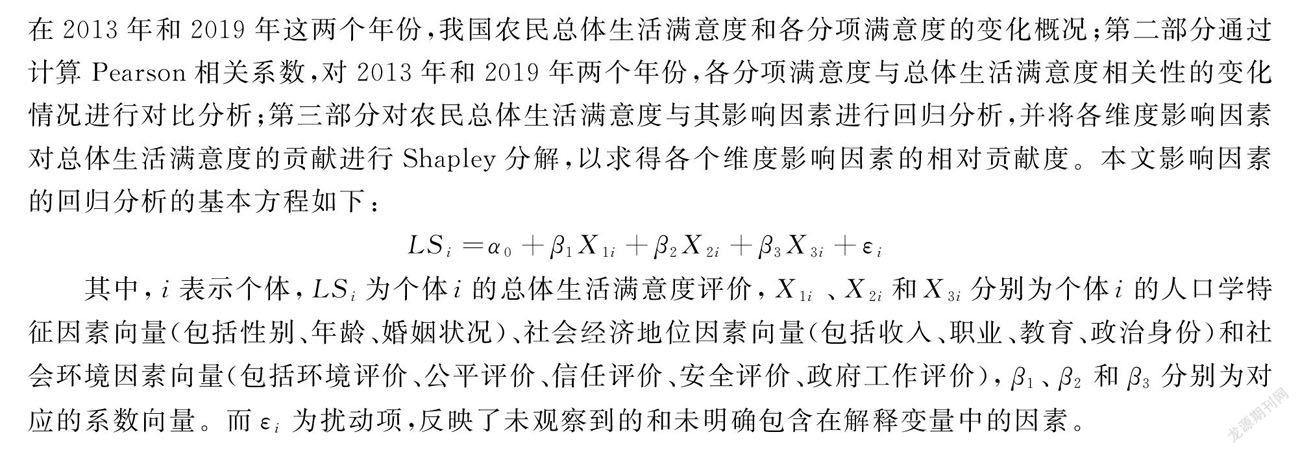


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在农村地区全面开展脱贫攻坚及乡村振兴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CSS)的研究发现,与2013年相比,我国农民的总体生活满意度以及在家庭经济状况、家庭关系、养老保障等分领域的满意度在2019年显著上升,而在休闲娱乐、社交生活、医疗保障这三个领域的满意度有所下降。通过对农民总体生活满意度与其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发现,无论在2013年还是2019年,农民对社会公平、社会信任、生态环境、政府工作的感知和评价对其主观生活质量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影响效应远远超过收入、职业、教育等个体社会经济因素和性别、年龄、婚姻等人口学特征因素。因此未来应重点改善包括社会公平和社会信任在内的宏观社会环境,以进一步提高农民的主观生活质量,并将主观生活质量纳入到脱贫质量和乡村振兴质量的指标体系中。
关键词:主观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精准扶贫;乡村振兴
一、引言
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十八大”)召开,选举产生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次年1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精准扶贫战略思想,把脱贫攻坚摆到了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吹响了全面脱贫攻坚的嘹亮号角。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从2013年到2020年,精准扶贫政策让我国832个贫困县、12.8万个贫困村、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成功实现了脱贫,提前10年实现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的减贫目标。2020年,我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3年的6079元提高到12588元,达到了全国农村平均水平的73.5%,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的差距进一步缩小,大大加速了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这八年时间也是中国在扶贫开发道路上成就最辉煌的时刻。与此同时,自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国家从产业、生态、乡风、治理等方面,不断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了重大成效。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扶贫政策和乡村振兴政策的实施对我国农村地区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其在改善我国农民客观生活质量方面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客观生活条件的改善有没有使我国农民整体的生活满意度(主观生活质量)得到提高?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民的主观生活质量呈现出怎样的变化趋势?哪些因素会影响我国农民的主观生活质量以及影响我国农民主观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在这期间是否发生变化?这是本文将要研究和回答的问题。本文的研究意义及主要贡献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揭示了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民主观生活质量的变化情况。已有研究通常是对特定时间时点、特定区域、特定人群的生活质量的研究,没有对重要历史节点,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民生活质量的变化情况进行研究,缺乏从主观生活质量角度对十八大以来农村工作和农村政策效应的评估。本文基于2013年和2019年两期数据做了历时比较研究,通过比较两个年度农民生活满意度的变化情况,可以得知农民主观生活质量在这七年间的变化趋势。通过比较同一变量在两个年度的不同影响效应,可以得知影响农民主观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在两年期间有何变化。因此,本文的研究可以为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村政策和农村工作的成效评估提供一个量化的观察窗口。
第二,本文将人口学特征变量、社会经济特征变量、社会环境因素变量这三个维度的因素放在一起与总体生活满意度进行回归分析,并基于回归分析结果,对各维度影响因素的相对贡献度做了夏普里(shapley)分解,如此便可得知三个维度的因素分别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农民的主观生活質量,有助于加深对主观生活质量影响因素的理解和认识,丰富和拓展关于主观生活质量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第三,目前关于脱贫质量的指标体系和乡村振兴的指标体系的研究,通常是从客观生活质量和客观维度来构建的,然而,人的感受是主观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等农村工作和农村政策的最根本目的是提高农民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因此对十八大以来的农村工作和农村政策(特别是扶贫和乡村振兴)的效果评估,亟待将主观生活质量纳入考评体系,将主观生活质量作为评估脱贫质量等农村政策效果的重要指标。本文对十八大以来农民主观生活质量的变化情况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有助于从主观生活质量这一角度思考和构建有关脱贫质量和乡村振兴的指标体系,从而更全面、更准确地评估扶贫脱贫和乡村振兴等政策效果。
二、文献综述
(一)主观生活质量的概念界定
易松国和风笑天(1997)通过对国内外生活质量研究文献的梳理和总结认为,国内外学者关于生活质量的研究主要存在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从影响人们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客观条件方面来理解生活质量 ,认为生活质量是生活条件的综合反映,生活条件的改善就意味着生活质量的提高。第二种模式是从人们的主观感受方面来理解生活质量,Bukenya(2001)通过对美国西弗吉尼亚州乡村地区的研究发现,客观生活质量只能解释居民生活质量的15%,而主观指标如健康评价、人际关系评价和总体生活满意度能解释70%~80%,所以,目前,国外关于生活质量的研究主要采用的是这种模式。第三种则是将主、客观方面结合起来进行理解 ,认为生活质量是在一定的客观物质条件基础上,社会个体对自身及其社会环境的认同感。本文所要研究的生活质量属于第二种模式,主要关注的是人们对生活总体的满意程度及对生活各个方面的主观感受,即主观生活质量。
主观生活质量, 也称之为可感生活质量, 即为人们所感觉到生活质量,它的基本假设是生活质量可以根据人们对快乐感和满意度的认识来决定(周长城和蔡静诚,2004)。在研究人们的主观生活质量时,有的学者将主观生活质量等同于“主观幸福感”(邢占军,2006),有的学者将主观生活质量等同于“生活满意度”(林南,1987),究竟应该采用“生活满意度”还是采用“幸福感”作为测量主观生活质量的指标,目前,学界并没有统一的定论。林南和卢汉龙(1989)认为,“幸福感”代表的是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它与生活压力和社会支持有关,而“生活满意度”是通过与他人比较,而做出的对自己客观生活状况的评价。国外学者坎贝尔(1981)认为,“幸福感” 所表达的是一种短暂或瞬间的情感体验,这种感觉是会经常变化的,然而“满意度”却代表着一种较稳定的和长久的态度意愿,所以建议用“生活满意度”来作为测量主观生活质量的指标。Schuessler(1985)等指出,用对生活的满意程度来测量主观生活质量是被大多数(国外)学者认为更为合适的方法。结合以上学者的理论分析和本文的研究需要,本文将“生活满意度”作为测量主观生活质量的指标。gzslib202204012037(二)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
国外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开始研究哪些因素会影响人们的主观生活质量,Easterlin(1974)通过对幸福感的跨国比较研究发现:对所有国家来说,个人范围内,越多的钱意味着更多的幸福。然而,所有成员的收入增加并不会增加所有成员的幸福,长期来看,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呈“ U ”形变化趋势,这个研究结论后来被学者们称为“伊斯特林幸福悖论”。Day(1987)认为家庭关系、健康状况、娱乐休闲、精神状态、自我评价、社会生活、与工作有关的生活、经济状况、政府的政策措施等对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均存在一定影响。
在国内学界,关于主观生活质量的研究文献里面,对主观生活质量影响因素的探讨和研究是占比最多的,说明这是一个被学者们广泛关注的问题。总体来看,目前学者们对我国居民主观生活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人口学特征变量(包括年龄、婚姻、性别、户籍、地区)、个体社会经济变量(包括教育、收入、职业、健康、社会交往)、社会环境变量(包括生态环境、公共政策、公共服务、政府质量、社会公平、收入差距、社会信任)这三大因素上。
唐倩(2020)、叶闽慎(2017)、李越和崔红志(2013)、白描和吴宝国(2017)等学者从人口学特征方面研究了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等因素对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发现:就性别而言,女性的主观生活质量要普遍高于男性;就年龄而言,与年纪较轻者相比,年龄较大的农民生活满意度更高;就婚姻状况而言,与已婚或离异者相比,未婚农民的生活满意度更高。
关于个体社会经济特征与主观生活质量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多,就经济特征而言,胡荣华和陈琰(2012)研究发现,居民家庭年收入对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邢占军(2011)通过对山东省城市居民连续7 年的调查发现,高收入群体幸福感得分高于低收入群体,富裕程度较低地区居民个人收入与总体幸福感之间的相关性要强于富裕程度较高地区。苏钟萍和张应良(2021)研究认为,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正向影响,农村居民绝对收入影响幸福感的“倒U”形拐点没有出现。廖永松(2014)调查发现,农民具有“小富即安”的生活观念,农民幸福感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生活水平的绝对提高以及与同村居民的横向比较。就社会特征而言,苑鹏和白描(2013)研究发现,社会联系是影响农民个人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农民社会联系资源的广度越大,其个人幸福感越强。约翰·奈特等(2014)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那些对生活的满意感更多来自人际关系而非物质产品和服务的农村居民要更幸福。
目前,关于社会环境特征与主观生活质量关系的研究也有很多,但大多是以城市居民为研究对象。曹大宇(2011)从自然环境层面研究了空气质量对城市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发现我国城市居民生活满意度与空气环境质量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空气污染显著降低了居民幸福感。在社会环境层面,关于经济增长与主观生活质量相关性的研究最多,刘军强等(2012)通过对2003-2010年我国国民幸福感变化趋势的分析,认为经济增长可能是幸福感提升的动力。吴晓刚和李骏(2013)研究发现,地方经济增长速度对居民生活满意度有正向影响。李路路(2017)研究认为,从长期来看,由于“财富适应”效应和相对剥夺效应的存在,经济增长并不一定会使人们的幸福感得到同步提高。另有一些学者研究了收入差距、政府质量、财政政策、公共服务、社会公平、社会信任等因素对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王鹏(2011)研究发现,收入差距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呈“倒U”形,临界点为0.4,当基尼系数小于0.4 时,居民的幸福感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而增强,但超过0.4 时,扩大的收入差距将导致居民幸福感下降。陈刚和李树(2012)研究发现,政府质量(包括政府效率、公共物品供给和财产权利保护等)会显著影响居民幸福感,且其对居民幸福感的促增效应远远高于经济增长。谢舜等(2012)研究发现,宏观税负和地方政府基建投资对于城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负效应,政府用于科教文卫和社会保障的支出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效应。周绍杰等(2015)研究发现,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提升可以显著增强个体的生活满意度,且比收入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程度更大。谭旭运等(2020)研究认为,当人们的社会信任水平越高,能感受到生活环境各个方面都比较公平时,民众的生活满意度就会越高。
从上述关于主观生活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来看,已有的文献至少存在以下两方面的不足。
第一,已有文献虽然关注了人口学特征变量、社会经济特征变量、社会环境因素变量对人们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但没有明确指出这三个维度的因素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主观生活质量,也没有将这三个维度的变量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和讨论。
第二,关于主观生活质量的已有研究大多是基于某一时点和某一地域的静态研究,只能反映特定调查时点和调查区域内人们的生活状况,缺乏历时性的和全国性的比较研究。我们认为,生活质量,特别是主观生活質量是处于一个变化的状态,某一时点、某个影响因素的变化可能就会导致人们主观感受的变化,而对这种变化方向和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可以有助于我们制定更切合实际、更有效的政策,或者对现有的政策作出更科学的评估,所以对主观生活质量的历时性比较研究也是极具现实意义的。以上两方面的不足,为本研究提供了可能的创新空间。
基于对已有研究文献的梳理,我们提出了本文的研究问题:一是十八大以来,农民的总体生活满意度和各个领域的生活满意度呈现怎样的变化趋势?二是个体的人口学特征因素、社会经济特征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这三个维度的变量对农民总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作用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三、数据、变量与实证模型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是由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3与CSS2019(目前最新数据)两期截面数据组成。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组织的两年一次的纵贯调查,调查区域覆盖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包括了151个区市县,604个村/居委会。2013年的数据反映的是我国脱贫攻坚工作刚刚开始之前的情况,2019年的数据反映的是脱贫攻坚工作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前一年的情况。CSS2013共有城乡样本10206个,CSS2019共有城乡样本10283个。2013年问卷与2019年问卷在大部分题项设置上是一致的,这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两期对比数据。gzslib202204012037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户籍为“农业户口”的所有农民。根据这一标准进行筛选并剔除存在缺失值的样本后,共获得有效样本数为:2013年农民样本有2401个,2019年农民样本有3374个。
(二)变量选取
1.总体生活满意度
“总体生活满意度”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在问卷中,通过询问受访者“总体来说,您对生活的满意度”来测量其总体生活满意度,回答从“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共10个等级,分别赋值1~10,得分越高代表越满意。
2.分项生活满意度
分项生活满意度包括家庭经济状况满意度、家庭关系满意度、休闲娱乐活动满意度、社交生活满意度、教育程度满意度、医疗保障满意度、养老保障满意度,题项和赋值同“总体生活满意度”一样,也是分为10个等级,赋值1~10。
3.总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影响因素变量分为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人口学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 第二个维度是个体社会经济特征变量,包括:家庭人均年收入(取对数)、个人年收入(取对数)、职业、教育程度和政治身份(是否是党员),之所以将政治身份作为个体社会经济特征变量,而不是作为人口学特征变量,是因为考虑到我们的样本和研究对象都是农民群体,对他们而言,党员这个身份并不是能够轻而易举就获得的,党员身份对他们来讲,更多的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而不仅仅是一个人口学特征。以上这些变量在2013年和2019年的问卷中都有直接相关题项,且题项设置是一致的。第三个维度是社会环境因素变量。由于CSS数据中没有关于社会环境的客观测量指标,参考其他学者的做法,本文将用被访者对社会环境的评价作为社会环境指标的替代变量,具体包括:居住地环境状况评价、社会公平状况评价、社会信任状况评价、社会安全状况评价(主要测量的是个人信息和隐私安全)、地方政府工作评价。
(三)实证分析模型
本文的實证分析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2013年和2019年两期均值数据的对比分析,描绘出在2013年和2019年这两个年份,我国农民总体生活满意度和各分项满意度的变化概况;第二部分通过计算Pearson相关系数,对2013年和2019年两个年份,各分项满意度与总体生活满意度相关性的变化情况进行对比分析;第三部分对农民总体生活满意度与其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并将各维度影响因素对总体生活满意度的贡献进行Shapley分解,以求得各个维度影响因素的相对贡献度。本文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的基本方程如下:
LSi=α0+β1X1i+β2X2i+β3X3i+εi
其中,i表示个体,LSi为个体i的总体生活满意度评价,X1i、X2i和X3i分别为个体i的人口学特征因素向量(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社会经济地位因素向量(包括收入、职业、教育、政治身份)和社会环境因素向量(包括环境评价、公平评价、信任评价、安全评价、政府工作评价),β1、β2和β3分别为对应的系数向量。而εi为扰动项,反映了未观察到的和未明确包含在解释变量中的因素。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农民主观生活质量变化概况
1.农民总体生活满意度和分项生活满意度变化情况
参考李路路和王鹏(2018)关于转型中国社会态度变迁的分析方法,表1和表2从“总体生活满意度”、“家庭经济状况满意度”、“家庭关系满意度”、“休闲娱乐活动满意度”、“社交生活满意度”、“教育程度满意度”、“医疗保障满意度”、“养老保障满意度”八个方面对我国农民群体的主观生活质量在2013~2019年这七年间的变化情况作了整体描述和分析。
从表1和表2的统计分析结果我们可以发现:就总体生活满意度而言,与2013年相比,在2019年,我国农民的主观生活质量总体上是呈现上升状态,而且在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职业、不同婚姻状态、不同教育程度、不同政治身份的农民群体身上都表现出了一致的变化趋势。
从表2的统计分析结果我们还可以看出两个年份分项满意度的变化情况。首先,总体来看,在2019年,我国农民在家庭经济状况、家庭关系、养老保障三个方面的满意度都比2013年有显著提升,其中,家庭关系满意度提升幅度最大(均值差为0.610)。其次,与2013年相比,2019年,我国农民在休闲娱乐、社交生活、医疗保障三个方面的满意度有所下降。其中,休闲娱乐、社交生活领域的满意度下降可能与近年来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有关,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民来说,以前他们是生活在农村“熟人社会”中,有着充足的休闲娱乐和社交生活体验,但是他们进城务工以后,既没有时间进行休闲娱乐,也没有亲戚朋友可以开展社交活动,所以休闲娱乐和社交生活的满意度就会急剧下降。就医疗保障领域满意度而言,本文发现医疗保障领域满意度有所下降,这个研究结论与已有相关研究结论一致,比如王雅婷等(2018)通过对1994-2017年以来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发展状况的横断历史研究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对农村合作医疗各项服务的满意度水平并未逐年提高,反而对报销流程、医疗机构服务态度与技术水平的满意度均呈下降趋势。另外,霍灵光和陈媛媛(2017)通过对多期数据的对比分析也发现,总体上,新农合对改善农民幸福感的作用并不显著。参考其他学者的研究,我们认为导致农民医疗保障领域满意度有所下降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通过异质性分析我们发现,年龄较大、学历较低的农民对医疗保障领域的满意度评价是下降的,原因可能在于,目前我国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报销制度对部分农民来说可能存在一定障碍,比如报销中的不规范性或者违规操作、报销手续和流程过于繁琐等,对于年龄较大而文化程度又较低的农民来说,报销流程的繁琐和不方便,会给他们带来大量的时间成本,而就医过程的体验对参合农民满意度的影响又是最显著的(何文盛等,2019),所以报销过程会影响部分农民对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满意度。第二,很多关于农村医疗保险满意度的调查都发现,农村合作医疗存在定点医疗机构服务水平参差不齐、管理机构的行政效率较低等问题,这些短板的存在与农民对农村合作医疗的较高期望出现了矛盾,使得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就医体验没有让农民完全满意。当然,本文研究结论只能表明,相比2013年,农民对2019年医疗保障满意度这一综合主观评价有所下降,并不能完全反映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和农村医疗保障本身的客观情况。gzslib202204012037进一步地,从表2可知,不同农民群体在分项满意度评价上的变化存在异质性。与总体满意度的变化趋势一样,2019年,家庭经济状况、家庭关系和养老保障三个领域的满意度在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职业、不同婚姻状态、不同教育程度、不同政治身份的农民群体身上都表现出了一致的上升趋势。异质性主要体现在休闲娱乐活动满意度、社交生活满意度和医疗保障满意度上。
其中,休闲娱乐活动满意度变化的异质性主要体现在职业和婚姻状况两个方面,具体来讲,只有职业为“只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民和“非在婚”的农民的满意度是上升的,其他职业的农民和婚姻状况为“在婚”的农民的满意度都是下降的,其原因可能在于“只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民和“非在婚”的农民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和条件进行休闲娱乐活动。
社交生活满意度变化的异质性主要体现在年龄上,具体来讲,只有年龄在60岁以上的老年农民群体的满意度是上升的,可能的原因是中青年农民因為忙于生计和工作,社交时间被压缩,而农村老年群体大多在家务农或赋闲,有更多的社交时间,社交生活的满意度相对更高。
医疗保障满意度变化的异质性在职业、年龄、婚姻状况、政治身份、教育程度方面都有体现,具体来讲,职业为“只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民、年龄在“18~38”岁的农民、婚姻状况为“非在婚”的农民、是“党员”的农民和“大专以上教育程度”的农民的满意度是上升的,职业为“半工半农”或“全职务农”的农民、年龄较大的、学历较低的农民对医疗保障领域的满意度评价是下降的。
2.分项满意度与总体满意度的相关性变化情况
我们通过分别计算2013年和2019年各分项生活满意度与总体生活满意度的Pearson相关系数,进而发现在两个不同年份,分项生活满意度与总体生活满意度之间关系强度的变化。Pearson相关系数是用两个变量的协方差除以两个变量的标准差得到,其值介于-1和1之间。当两个变量的线性关系增强时,Pearson相关系数趋于1或-1:当一个变量增大,另一个变量也增大时,表明它们之间是正相关的,相关系数大于0;如果一个变量增大,另一个变量却减小,表明它们之间是负相关的,相关系数小于0;如果相关系数等于0,表明它们之间不存在线性相关关系。因此,Pearson相关系数能够反映农民总体生活满意度与分项生活满意度之间的线性相关程度。从表3的统计结果来看,在2013年,与农民总体生活满意度关联最强的三个领域是家庭经济状况满意度、休闲娱乐活动满意度、社交生活满意度,其Pearson相关系数分别是0.628、0.599、0.459,其次为家庭关系满意度(0.438)、教育程度满意度(0.403)、养老保障满意度(0.300)、医疗保障满意度(0.266)。而在2019年,与农民总体生活满意度关联最强的三个领域是家庭经济状况满意度(0.523)、社交生活满意度(0.462)、休闲娱乐活动满意度(0.442),其次为教育程度满意度(0.368)、家庭关系满意度(0.350)、医疗保障满意度(0.302)、养老保障满意度(0.296)。
对比2013年和2019年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第一,无论在2013年还是2019年,农民对自身家庭经济状况的评价与其对总体生活满意度评价的相关性都是最高的。不同的是,在2013年,与总体生活满意度第二相关的因素是休闲娱乐活动满意度,而在2019年,社交生活满意度成为与总体生活满意度第二相关的因素,这说明,农民生活方式和主观生活感受在发生变化,在2019年更加重视社交生活方面的体验。第二,相比2013年,在2019年,家庭经济状况满意度、家庭关系满意度、休闲娱乐活动满意度、教育程度满意度四个分项满意度与总体生活满意度的相关系数都呈下降趋势,而只有医疗保障满意度与总体生活满意度的相关系数是上升的,这说明医疗保障领域的感受和评价对农民总体主观生活质量的感受和评价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二)农民总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变化情况
1.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4和表5分别呈现了2013年和2019年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信息。第一,在2013年的样本中,一半以上的样本的人均家庭收入处于均值以下水平,而在2019年的样本中,一半以上的样本的人均家庭收入处于均值以上水平。第二,与2013年相比,我国农民在2019年的人均家庭收入和个人收入的均值是有明显提高的,这说明我国农民的整体收入情况有明显改善。第三,农民平均受教育水平和党员比例在2019年也有少许提升。第四,农民生活满意度的均值从6.79上升到7.36,中位数从7上升到8,表明农民生活满意度有明显上升。第五,农民职业变量的均值从2.72下降到2.59,表明从2013年到2019年,更多的农民从事非农工作或以非农工作为主。第六,农民对环境评价、公平评价、政府工作评价均上升,表明我国在环境保护、社会公平公正、政府工作效率等方面有很大改善。
2.农民总体生活满意度与其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在本研究所采用的调查数据中,因变量农民总体生活满意度是有序离散变量,所以我们采用了Ordered Logit方法进行回归分析,同时,作为对照,我们也用OLS方法做了回归分析,最后发现这两种方法的回归分析结果在显著性水平和相关性上基本一致,我们的报告采用的是基于Ordered Logit方法的回归分析结果。
基于研究需要,我们共设计了8个回归模型,模型1是人口学特征模型,模型2是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特征模型,模型3~模型7是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特征+社会环境单变量模型,模型8 是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特征+社会环境全变量模型。表6和表7分别是2013年和2019年农民总体生活满意度与其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
第一,从人口学特征来看(模型1),首先,就年龄而言,在2013年,60岁以上的老年农民的总体生活满意度是显著高于青年农民的,而38~59岁的中年农民的总体生活满意度是显著低于青年农民的,这可能与中年农民“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压力有关。而在2019年,中年农民和青年农民的总体生活满意度差异不显著,但是60岁以上的老年农民的总体生活满意度依然显著高于青年农民,这与李越、崔红志和叶闽慎的研究结论一致,其原因可能是因为老年人社会比较的倾向较弱,他们仅仅与过去的生活做比较,较少与富裕的同村人或城里人做对比,所以尽管老年农民客观生活质量不太好,但是他们依然感觉相对更满意。其次,在2013年,“在婚”状态下的农民的生活满意度是显著高于“非在婚”农民的,但在2019年,婚姻状况对农民总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变得不显著,说明农民的婚姻观念在发生变化,结婚不一定会更幸福,不结婚也不一定不幸福。最后,性别对农民总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在2013年和2019年都不显著。gzslib202204012038第二,从个体社会经济特征(模型2)来看,2013年与2019年差异比较大。一是,在2013年,无论是人均家庭收入还是个人收入,与农民的总体生活满意度的相关性都不显著,而在2019年,人均家庭收入与总体生活满意度显著正相关,即随着农民人均家庭收入的增加,农民的总体生活满意度会随之提升。之所以收入对农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在2013年不显著,而在2019年变得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在2013年,农民的收入水平普遍较低,大家的生活条件都差不多,所以收入本身就不会对个人的生活满意度产生太大影响,而在2019年,农民的收入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而且收入差距逐渐拉大,收入带来的幸福效应就逐渐显现出来。二是,在2013年,是否是党员与农民的总体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相关关系,但在2019年,是否是党员这个因素与总体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结合精准扶贫期间,共产党员的先锋带头作用,可以推测党员这个身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个人的社会地位,从而有助于提升个体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三是,相比于2013年,在2019年,教育程度对个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变得不显著。具体来讲,在2013年,教育程度与农民总体生活满意度显著正相关,大专以上学历的农民生活满意度最高,其次是初高中(高职)学历的农民,小学教育程度的农民的生活满意度最低,而在2019年,教育程度的差异对个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变得不显著了,说明教育对农民带来的效用在减弱,这也验证了为什么近几年在农村会流行“读书无用论”的观点。四是,在2013年,农民的职业与其总体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相关关系,而在2019年,以务农为主同时也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民的总体生活满意度显著低于全职务农的农民,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以务农为主同时也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民,他们的工作性质是半工半农,既在农村务农,也在城市或城镇打工,相对来说比较辛苦,而且还会经常与生活条件较好的城里人进行比较,出现“比上不足”的心态,以致于生活满意度较低;而全职务农的农民,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圈都在农村,比较的对象也多是在村里务农的人,大家生活条件都差不多,所以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反而较高。
第三,从社会环境因素(模型3~模型8)来看,在2019年,公平评价、信任评价、政府工作评价对农民总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效应都大于2013年。具体来讲,2013年,在控制了人口学特征变量和个体社会经济特征变量后,5个环境因素变量都与农民总体生活满意度显著正相关。如果把所有社会环境因素变量都放在一起比较(模型8),可以看出,影响系数从大到小依次是环境评价、社会公平评价、社会安全评价、政府工作评价和信任评价。在2019年,安全评价与农民总体生活满意度相关性变得不显著了,其他四个因素的影响系数从大到小依次是公平评价、信任评价、政府工作评价和环境评价。也就是说,在2013年,环境评价的影响效应最大,而在2019年,社会公平因素的影响效应最大,从中可以反映出,经过多年的精准扶贫工作,农村整体生活环境得到了改善,同时,也从一定程度上解釋了为什么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转型的深入推进,民众对社会公平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因为社会公平本身以及人们对社会公平的感受和评价会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和生活质量,在“不患贫”的年代,如何摆脱“患不均”的困境,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3.各维度影响因素的Shapley分解结果
本文根据 Shorrocks(2013)提出的基于回归的 Shapley 分解方法,将各维度影响因素对总体生活满意度的贡献进行分解,以求得各个维度影响因素的相对贡献度。我们分别基于Ordered Logit回归方法和OLS回归方法做了Shapley 分解,发现结果是一致的,本文仅列出基于Ordered Logit回归方法的Shapley 分解结果。
从表8中可以看出,一方面,与2013年相比,在2019年人口学特征因素和个体社会经济因素对农民总体生活满意度的相对贡献度都是下降的,而社会环境因素的相对贡献度是上升的。这一变化的可能原因:一是人口学特征因素、个体社会经济因素、社会环境因素等均会影响农民主观生活满意度,但是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开放程度的增加,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婚姻状况的个体之间差异不断缩小,甚至趋同,因此个体特征因素对农民的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程度会下降。二是个体社会经济因素与社会环境因素在农民的福利或效用函数中是互补的,随着农民收入水平的普遍提升和生活条件的普遍改善,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个体社会经济环境因素带来的边际效用会下降,从而个体社会经济因素对主观生活质量的贡献程度下降。三是由于十八大以来农村扶贫和乡村振兴等政策的实施,政府各种资金和资源的投入对农民的经济收入、生活条件、福利状况的影响越来越大,农民对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大,期望也越来越高,相应地,他们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质量、政策实施的公平程度、基层政府工作的开展情况这些问题的关注度就越来越高,从而使得社会环境因素对农民的主观生活质量的贡献上升。另一方面,无论在2013年还是2019年,在三类影响因素当中,社会环境因素对农民总体生活满意度的贡献度都是最高的,远远超过个体社会经济因素和人口学特征因素,说明整体社会公平程度、信任水平、生态环境、公共服务、政府质量等这些社会环境因素对农民总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作用大大超过了性别、年龄、婚姻、收入、教育、职业等变量,也说明政府质量、公共服务、社会公平与社会信任等宏观社会环境在中国转型经济中提升国民主观生活质量的重要性。
五、结论及政策含义解读
本文基于CSS2013和CSS2019两期调查数据,通过实证分析,深入考察了十八大以来,在全面脱贫攻坚战役的大背景下,我国农民的主观生活质量在2013年到2019年这七年期间的变化情况。实证分析结果发现:(1)总体上看,与2013年相比,我国农民的总体生活满意度在2019年呈现显著上升的趋势,从分项满意度指标来看,2019年,我国农民在家庭经济状况、家庭关系、养老保障三个方面的满意度都比2013年有显著提升,而在休闲娱乐、社交生活、医疗保障三个方面的满意度有所下降。(2)从人口学特征来看,在2013年,婚姻状况显著影响农民总体生活满意度,而在2019年,两者的相关性变得不显著;从个体社会经济特征来看,在2013年,收入、党员身份、职业对农民总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效应都不显著,只有教育程度对农民总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效应是显著的,而在2019年,家庭人均收入和党员身份与农民总体生活满意度显著正相关,而教育程度对农民总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效应变得不显著。从社会环境维度来看,在2013年,农民对社会公平、生态环境、社会信任、社会安全和政府工作方面的评价与农民总体生活满意度显著正相关,而在2019年,社会安全评价对农民总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效应变得不显著,其他四个因素的影响效应依然显著。(3)无论在2013年还是2019年,社会环境因素对农民总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效应都是最大的,远远超过个体社会经济因素和人口学特征因素。gzslib202204012038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四个方面的政策启示。
第一,总体上看,十八大以来开展的一系列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工作在提高我国农民主观生活质量方面是卓有成效的,它不仅惠及了贫困农民,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全国农民幸福水平的提高。
第二,我国农民在休闲娱乐、社交生活、医疗保障领域的满意度在2019年有所下降,且休闲娱乐、社交生活领域的满意度与总体生活满意度相关性非常大,这意味着,未来在制定相关三农政策时,需要将这三个领域给予重点考虑,相关政策建议如:增加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为农民,特别是“半工半农”的农民创造休闲娱乐条件;完善农村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制度,控制医疗费用,降低报销门槛,提高异地报销的便利性等。
第三,在推进乡村振兴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要重视宏观社会环境对农民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相关政策建议如:通过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生活污水治理、厕所革命等措施改善农村地区人居环境;通过“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等政策措施进一步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促进收入分配公平;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解决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安家、子女入学等问题,让农民有更多社会流动和阶层流动的渠道和机会,促进教育公平和机会公平;通过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严厉打击市场主体和个人的不诚信行为,降低信任风险,尤其要发挥公权力在营建社会信任机制方面的核心作用,摆脱信任困境,重建社会信任。
第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等农村工作和农村政策的最根本目的是提高农民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因此应将农民的主观生活质量纳入到农村工作和农村政策的效果评估中去。比如,可将本文中农民总体生活满意以及家庭经济状况满意度、社交生活满意度、休闲娱乐活动满意度、教育程度满意度、家庭关系满意度、医疗保障满意度、养老保障满意度等分领域生活满意度等指标纳入农村政策效果的评估体系中去,以切实提高农民的生活满意度、幸福感和获得感。
参考文献:
[1] 白描、吴国宝,2017:《农民主观福祉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5省10县农户调查资料》,《中国农村观察》第1期。
[2] 曹大宇,2011:《环境质量与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实证分析》,《统计与决策》第21期。
[3] 陈刚、李树,2012:《政府如何能够让人幸福?——政府质量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第8期。
[4] 何文盛、张馨文、张瑞菊,2019:《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农民满意度影响因素及其政策优化:一个基于L市的案例分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1期。
[5] 胡荣华、陈琰,2012:《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统计研究》第5期。
[6] 霍灵光、陈媛媛,2017: 《“新农合”:农民获得幸福感了吗?》,《上海财经大学学报》第2期。
[7] 李路路、王鹏,2018:《转型中国的社会态度变迁(2005-2015)》,《社會学研究》第3期。
[8] 李路路、石磊,2017:《经济增长与幸福感——解析伊斯特林悖论的形成机制》,《社会学研究》第3期。
[9] 李越、崔红志,2013:《农村老年人口主观生活质量与客观生活质量差异及形成机理的实证分析——基于对江苏省姜堰市坡岭村农户问卷调查的数据》,《农村经济》第12期。
[10] 廖永松,2014:《“小富即安”的农民:一个幸福经济学的视角》,《中国农村经济》第9期。
[11] 林南、王玲、潘允康、袁国华,1987:《生活质量的结构与指标——1985年天津千户户卷调查资料分析》,《社会学研究》第6期。
[12] 林南、卢汉龙,1989:《社会指标与生活质量的结构模型探讨——关于上海城市居民生活的一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13] 刘军强、熊谋林、苏阳,2012:《经济增长时期的国民幸福感——基于CGSS数据的追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12期。
[14] 苏钟萍、张应良,2021:《收入水平、社会公平认知与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统计与决策》第9期。
[15] 谭旭运、董洪杰等,2020:《获得感的概念内涵、结构及其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社会学研究》第5期。
[16] 唐倩, 2020:《中国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影响因素比较研究——基于CFPS2016数据的分析》,云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7] 王鹏,2011:《收入差距对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分析》,《中国人口科学》第3期。
[18] 王雅婷、张刚旭、万里虹,2018:《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发展状况的横断历史研究:1994-2017》,《保险研究》第1期。
[19] 谢舜、魏万青、周少君,2012:《宏观税负、公共支出结构与个人主观幸福感兼论“政府转型”》,《社会》第6期。
[20] 邢占军,2006:《城乡居民主观生活质量比较研究初探》,《社会》第1期。
[21] 邢占军,2011:《我国居民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社会学研究》第1期。
[22] 叶闽慎, 2017:《主客观生活质量相互作用机制研究——基于可行能力理论视角》,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3] 易松国、风笑天,1997:《城市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研究——武汉、北京、西安三地调查资料的比较分析》,《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3期。
[24] 苑鹏、白描,2013:《社会联系对农户生活幸福状况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山东、河南、陕西三省六县487户农户问卷调研》,《学习与实践》第7期。
[25] 约翰·奈特、宋丽娜等,2014:《中国农村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决定因素》,《国外理论动态》第6期。gzslib202204012038[26] 周长城、蔡静诚,2004:《生活质量主观指标的发展及其研究》,《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
[27] 周绍杰、王洪川、苏杨,2015:《中国人如何能有更高水平的幸福感——基于中国民生指数调查》,《管理世界》第6期。
[28] Bukenya,J. O., 2001, An Analysis of Quality of Life,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West Virginia, Morgantown: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29] Campbell, A., 1981, The Sense of Well-being in America: Recent Patterns and Trends, New York: Mcgraw-Hill.
[30] Day R. L. 1987, Relationships between Life Satisfaction and Consumer Satisfaction. in Coskun Samli A. (ed.), Marketing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Interface, New York: Quorum Books.
[31] Easterlin, R.A., 1974,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in Paul A.David and Melvin W.Reder (eds.),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32] Schuessler, K.F. and Fisher G.A, 1985, Quality of Life Research and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11:129-149.
[33] Shorrocks, A.F., 2013, Decomposition Procedures for Distributional Analysis: A Unified Framework Based on the Shapley Value, 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 11: 1-28.
[34] Wu,Xiaogang and Jun Li, 2013, Economic Growth, Income Inequalit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Evidence from China, PSC Research Report,7:13-796.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Changes of PeasantsSubjective Quality of Life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2013-2019)
Zhou Changcheng and Wang Miao
(School of Sociology,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China has mobilized the whole society to comprehensively combat poverty in rural areas, and achieved major victories that have attracted worldwide attention.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CSS2013 and CSS2019, this paper deeply investigates the changes of Chinese peasants subjective quality of life from 2013 to 2019.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2013, Chinese peasants overall life satisfaction and satisfaction in the fields of family economic situation, family relationship and pension security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2019, while their satisfaction in the fields of leisure and entertainment, social life and medical security decreased somewhat. Through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peasants overall life satisfact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t is found that both in 2013 and 2019, peasants perception and evaluation of social justice, social trus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government work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ir subjective quality of life. Its influence effect is far more than individual socio-economic factors such as income, occupation and education and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gender, age and marriage.
Key Words:subjective quality of life;life satisfaction;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rural revital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