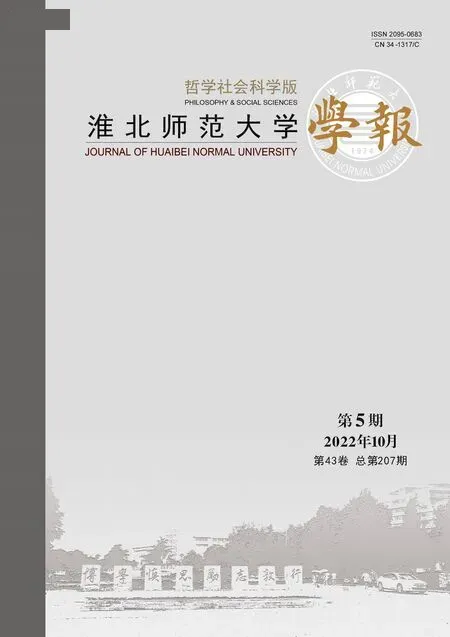输粟赎罪制度在明代荒政中的运作
郭学勤
(淮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输粟赎罪制度,也称赎刑,是指触犯国家法律的人可以通过输粟来免于或减轻科罚的制度。这一制度起源甚早,《尚书·尧典》中即有“金作赎刑”的记载。至明朝,输粟赎罪则十分常见。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制定明代的输粟赎罪制度,“自洪武中年已三下令,准赎及杂犯死罪以下矣”。[1]2293输粟赎罪并不局限于救荒时才运用,但每当灾荒之时,救荒过程中的粮食需求陡然增加,于是,救荒中的输粟赎罪便成为一种常态。特别是明朝中后期,在预备仓等官仓仓储粮食不足以救活灾民的情况下,朝廷对罪犯施行输粟赎罪,拓宽了筹集粮食的渠道。终明之世,此项制度一直在贯彻。关于明代输粟赎罪的研究,学界取得一定的成果①关于明代赎刑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胡建中、江宪《明代赎刑制度初探》(载《学术月刊》1982 年第7 期);张光辉《明代赎刑的运作》(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日本陶安Ando(A.H.Hafner)《中国刑罚史上的明代赎法》(载日本东洋史研究会:《东洋史研究》1998年第57 卷第4号。)以及陶安《律与例之间:通过明代赎法看旧中国法的一斑》(载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999年第138册)。这些成果主要考证明代赎刑的制度性规定、运作以及其在中国法制史中的作用和地位。,但在灾荒背景下此项制度的实施、演化和它发挥的实际使用,目前尚未有学者对此专门讨论。有鉴于此,本文即试图对这一重要制度研究作一补充。
一、朝廷有关荒政中输粟赎罪制度的规定
输粟赎罪是一项延续了千年的制度,明代从建国之初,就继承了这项制度,但最初,国家未必就将此项制度与拯救饥民联系到一起。洪武二十三年(1390),令罪囚运米赎罪,“除十恶并杀人者论死,余死罪运米北边。力不及者,或二人并力运纳”[2]卷176《五刑赎罪》。据此可知,明太祖制定赎刑制度最初是为了北部军事防御,巩固边防。准赎范围也非常广泛,除十恶罪不赦等危及到明朝廷统治以外,杂犯死罪以下的笞、杖、徒、流乃至绞、斩,都可以赎,这些罪犯只要向国家交纳财物即可赎罪免死,但前提是:这些罪行都没有危害封建统治的根基。洪武三十年制定罪囚运米赎罪的数额标准,让这一制度更加完善:“死罪一百石。徒流递减”。如果经济实力不足以赎罪,还可以用有限的米来减轻刑罚等级,“其力不及者,死罪自备米三十石,徒流罪十五石,俱运赴甘州威虏地方上纳,就彼充军。”[2]卷176《五刑赎罪》这样,输纳一部分米即可将死、徒、流等罪减轻为充军。表面上看,洪武年间的输粟赎罪制度似乎并未与救荒相关联,但这些输粟措施为后来的灾后筹粮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明代输粟赎罪被用于救荒的制度至少在明永乐年间已形成,“永乐初制,郡邑各置预备仓,官出金籴粟;若民赎罪入粟,收贮备赈贷。”[3]卷上《人主》在此,已经是明确规定了赎罪粮是预备仓储粮的重要来源之一,而预备仓唯一的作用,就是用于灾后赈济。明成祖永乐年间,输粟赎罪制度进一步细密化,永乐三年(1405)规定,“杂犯死罪纳米一百一十石;流罪三等八十石,加役者九十石;徒罪三年者六十石,二年半五十石,二年并迁徙者四十五石,一年半三十五石,一年三十石;杖罪九十、一百俱二十五石,六十至八十二十石;笞罪十石。”[2]卷176《五刑赎罪》从这些规定来看,囚犯赎罪所输纳的粮食数额较洪武时有所增加。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预备仓管理上出现了诸多问题,仓粮不能满足赈灾的需要。正统年间,大学士杨士奇和杨溥这样记载当时预备仓的状况:“是以一遇水旱饥荒,民无所赖,官无所措,公私交窘,只如去冬今春,畿内郡县艰难,可见沉闻。今南方官仓储谷十处九空,甚者谷既全无,仓亦无存。”[4]卷下即便是正统皇帝也不得不承认,“比年所用州县匪人,不知保民,坠废成法。凡遇饥荒,民无仰给。”[5]卷1《诏谕》预备仓救治灾荒的功能与作用在正统和洪武两个时期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天顺年间,右副都御史项忠任陕西巡抚,此时,关中的官仓中粮食被赈济殆尽。天顺七年(1463)二月癸酉,他上了输粟赎罪的奏疏:“请令各郡邑论断罪囚,俱纳米自赎,储以待赈。笞一十,纳米五斗,余四等递加五斗;杖六十,纳米三石,余四等亦递加五斗;徒一年,纳米十石,余四等递加五石;流三等,纳米三十五石。杂犯死罪,视流加五石。”这份奏折还是奏请皇上能允准罪犯输粟到预备仓。 明英宗批准了他的请求。[3]卷下《项襄毅公救荒事宜》项忠的奏疏中,五刑赎罪的输粟具体标准和前面又有些不同。这还是随着时代变迁,社会经济发展变化带来的结果。
到了景泰四年(1453),山东、河南、江北、直隶、徐州等地出现自然灾害,然而此时预备仓的空虚,根本发挥不了应对自然灾害的作用,明朝廷对输粟赎罪的制度稍作改变,规定罪犯将赎罪的米谷运往灾区,赈救嗷嗷待赈的灾民。明景帝敕令这些地方问刑衙门:“责有力囚犯于缺食州县仓纳米赈济。杂犯死罪六十石,流徒三年四十石,徒二年半三十五石,徒二年三十石,徒一年半二十五石,徒一年二十石。杖罪每一十一石,笞罪每一十五斗。”[6]卷11《应变章一·赎罪》这些赎罪的粮食被囚犯直接运到缺粮的灾区,拯救了待赈的灾民。这种让罪犯往灾区输粮的做法,让罪犯的赎粮和灾后的饥民更为接近。
尽管明朝廷制定了输粟赎罪的制度,但是有些罪犯明明具备输粟经济能力,却不愿意输粟赎罪。
正德年间,江西巡抚林俊就注意到这一问题:“臣又见,凡问口外为民,边远充军,囚或逃而不去,或去而即逃,徒名治奸,无益事实。”同时他又获悉江西所属预备仓积谷少,“湖口县不及一千石,彭泽县不及六百石,石城县仅两千有奇,泰和大县亦仅八千有奇,其余积蓄俱少。”预备仓粮的不足严重阻碍了地方救荒工作的顺利进行。因此林俊上奏明武宗曰:
乞敕法司计议,除情重外,如扛帮诬告,强盗人命,不实诬告十人以上,因事忿争,执操凶器,误伤傍人,势豪不纳钱粮,原情稍轻,不系巨恶,参审得过之家,愿纳谷一千石,或七八百、五六百石,容其自赎,免拟发遣。其诬告负罪平人致死,律虽不摘,情实犹重。并窝藏强盗,资引逃走,抗拒官府,不服拘捕,本罪之外,量其家道,罚谷自五百石至一百石,以警刁豪。俱又抚按参详,无容司属专滥。[5]卷2《奏议·请复常平疏》
林俊的提议还是有其合理性的,既然流放或充军等罪犯在途中逃跑,没受到应有的惩处,不如让他们拿出粮食帮助国家赈灾,做些有益国家和百姓的事情,这样来抵消他们所犯下的罪行。
当然,为了保证这一制度顺利实施,还要明确罪犯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能力,即罪犯必须是“有力”或“稍有力”。否则,这项制度就可能给罪犯增加沉重的经济负担。如嘉靖时新定条例,“俱以有力、稍有力二科赎罪”。[1]2300甚至有人特别强调这一点,如万历年间,刑部尚书孙丕扬曾提醒官员“勿改无力赎为有力赎”[7]卷264,万历二十一年九月戊午。这应当是孙丕扬作为刑部尚书,长期从事司法实践的经验总结。
综上所述,输粟赎罪这一制度在明初已经开始实行,明朝廷允许罪囚输粟赎罪这一制度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北部边防的军粮问题。至少在明成祖永乐年间,输粟赎罪制度已经被用于救荒,实施之初,可能就是为了灾前备荒。至于不同刑罚等级在输粟赎罪中必须输粟数额,有明一代并没有形成一成不变的量化标准,时多时少。但是这一制度却一直沿用到明代灭亡。罪囚把赎罪的粮食一般是输纳到官府的预备仓,这是一种常态。然而随着预备仓的空虚,也不排除非常时期的特殊规定,官府也曾规定过罪囚将赎罪的米粟直接输送到灾区救灾。
二、地方官对输粟赎罪制度的荒政运作
国家的输粟赎罪制度得到一些地方官的支持,经常被地方官们运用到灾前备赈和灾荒救济。而且,明代朝廷确定的制度在地方官的运作过程中被创造性地完善化和细密化。明代中期以后,有些地方的预备仓粮不足,针对这一现象,有些地方官更是不遗余力地鼓励罪犯输粟赎罪。上文中的萧启和林俊便是实例。
输粟赎罪在地方赈灾中的执行事例颇多,万历四十五年(1617),霍邱县灾荒异常,知县王世荫广开钱粮之源,输粟赎罪便是其中之一,“唯有开赎之例可权”[8《]赈备款议》。万历四十二(1614)、四十三年(1615),霍邱县已经遭遇了水旱叠加,此时的王知县在救荒中并没有施行输粟赎罪,“而卑县独以工赈有助,可不藉此,恐纵奸也”。然而王世荫为何在万历四十五年(1617)的这场灾荒中施行这一政策呢?只是因为“今荒且极矣,非仅四十三年之比也。不可通融乎?乃通之”。据此可知,王世荫认为,只有在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来筹集赈济灾荒的钱粮时才可以使用这一方法。因为,在他看来,让罪犯输粟来赎罪是在纵容作奸犯科之人。王世荫详述了他的辖区内输粟赎罪的具体做法:
不必在已成案者,恐费申转耳。唯于未成案,或成案而尚经驳审者,于此中详其应得罪名,或军、或徒、或杖、或枷号、或加责、或省祭承差吏农经革复役等事,一准如四十三年折米例。其米较贵,量准算折麦。盖此时无一稻也。但不许折银,亦不必上纳到官。即令所定饥民,每人每日麦一升,计一月该三斗,径于某犯名下赴领,给有印信官票。饥民执票赴领,本犯收票陈查,果一人不漏,方得如议减等。则在饥民自必取足而有实惠,在本犯亦不致上纳转费,即奸胥亦不得插入冒破矣。[8]《赈备款议》
这段文字记录了王世荫实施的输粟赎罪的几点原则:其一,王世荫在未审结的或是已经审理完毕但又驳审的案件中实施输粟赎罪。其二,王世荫将罪犯赎罪所应输的米按照一定的比例折成麦子收取。这是非常值得一提的。他充分考虑到灾荒年份得到足够的粮食、救活灾民性命是头等大事,因为米贵而麦贱,所以,他别出心裁地将米折麦收取,这样灾区就可以得到更多的粮食以救活更多灾民。其三,官府给予饥民印信官票,饥民持票到罪犯家领取麦子,而不是罪犯或其亲属将麦子运往灾区。这样饥民可以得到足额的麦子,罪犯也不需辗转运输。更为重要的是,一些奸猾胥吏也没有插手的机会,杜绝了他们中饱私囊的可能性。
更为耐人寻味的是,输粟赎罪的制度还演变成为另一种形态,即富人输粟数量或是救活灾民人数达到一定标准,明朝廷即发给免罪帖。如果此人以后犯罪了,就可以用免罪帖来抵消罪责,这样就为其以后的人生预设了一道安全的保障。而明代很多官员还都肯定了这一做法。万历年间,吏部员外屠隆把给富人免罪帖作为规劝富民捐输赈灾的一种方法,“富民之所最欲得者,给以印信一帖,除重情而外,预免其罪责一次,令得执以为信”。[9]182崇祯朝陈龙正记载,这一做法“在《会典》及累朝诏旨俱有之,有司所当亟行者也”。因此,输粟给与免罪帖在明代是由来已久,难怪这些救荒官员劝募捐输时讲到“或给赏帖,后犯杖罪,拿帖准免,皆所以奖之而不负之”,将之作为奖励帮助朝廷赈灾的“ 尚义之人”的一种手段。[10]卷6《荒政议总纲·次三曰四权》甚至有的地方给与的免罪帖不止一张,所捐输的粮食数量越多,给与的免罪帖越多。万历朝巡按陕西监察御史毕懋康认为应该“优好义之家”,对于好善乐施舍粥救灾民之家,如果费米“二十石者,给与免帖一张,犯笞杖罪名,应的决者免决,应纳赎者免赎;三十石以上者,州县呈该道送牌,仍给免帖一张;五十石以上者,州县呈本院给与冠带,本县送匾,仍令各给免帖二张”。富民施粥救活灾民也可以得到免罪帖。在富民施粥时,官府会派人登记富民被救活灾民的数量,“其所活人数,亦照官簿纪名。将散之前五日,有司官亲至舍场,查簿审(人)。众口称德、或千人以上者,本院亲至其门,仍题请冠带,请入乡饮;仍给免帖五张,子孙犯死罪以下,虽难免罪,不许加刑”。[6]卷16《宏济章三·设粥》还有的地方官尽管没有给捐输粮食的义民免罪帖,但是规定之后其犯罪不会用刑罚惩治。如万历年间的陕西布政汪道亨规定,对于输四百石以上入社仓者,除了给与冠带,优免杂泛差役之外,“ 犯罪不许加刑”。[6]卷18《善后章·推赏》这其实和给与输粟的富民免罪帖无异。
实际上,明朝廷规定的荒年“准赎”并不适合所有的民众。有些地方官注意到有的家庭穷苦,无力输粟,“民反苦之”。[11]其十二他们认为输粟赎罪并不是对所有的罪犯都是很好的选择,对于有些经济贫困即“无力”[1]2300的家庭则不宜使用。但是有的官员却为了中饱私囊而不考虑罪犯家庭的实际经济状况,导致输粟赎罪这一制度在各地具体推行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弊端。万历时期,晋中之民刚愎使气,尽管晋中之地贫穷,室如悬磬,“而犹以睚眦之故争告不息”。但是官府的相关部门却不正确引导民众,“有司者不恤其无知而就死也,方且日是事敲朴,幸赎锾以润囊橐”。晋中人尽管喜好打官司,但是一旦打输了官司却不喜接受笞杖的惩罚,于是,官员随意地给罪犯拟定了输粟赎罪。山西曲沃知县何出光尖锐地批评了这种现象,“不知一赎之金,而数口月余之粮,扼其吭而夺之,非所以戕一家之命乎?”如果罪犯愿意接受官府判决服刑则会得到准许,“愿的决者听”。[11]其十二当然,如果罪犯如果提出输粟来赎罪的请求也会被准许。何出光会根据罪犯家庭的经济状况的不同拟定不同的输粟赎罪的标准,经济状况越好输粟标准越高,反之越低,“今出明示,除上六则人丁准赎外,其下上人丁,每杖一十,罚米一斗;下中人丁,每杖一十,罚米六升;下下人丁,每杖一十,罚米三升。”何出光还提出了“省刑狱以恤灾民”,“今请下明示,凡一词之中,两造不许俱罪;一事不许罪二人。罪人非再三告赎,不许轻拟赎罪;即拟以赎,一概不许注以有力。如此则赎锾可省,而灾眚之民可少苏矣”。[11]其七这种做法对于晋中有效地救荒也是有所裨益的,同时,罪犯的输粟赎罪的诉求得到满足。
自然灾害发生时,在执行输粟赎罪的过程中,明代不少官员特别强调灾荒时赎罪一定要输谷粟等粮食,不能以金钱代替。万历朝刘世教提及这些罪犯要用粟、谷等实物来作为赎资,“赎以粟、以谷,勿以金”。[12]崇祯朝祁彪佳反对灾荒时期缴纳银钱,“此法固不可行,但迩来一经告讦,央求关说,费用差钱,极小之事,何尝不至二三十金?”他认为缴纳银钱过多,地方官应该为民着想,让他们缴纳少量的粮食来赎罪,“今贤父母体恤民瘼,尽除此弊,但令稍输赎罪,亦何患民间之不乐从乎?”[6]卷12《当变章二·节锾》崇祯十五年(1642),户部明确规定:“奉圣谕,据议徒罪杖赎,钱粮征比,俱照时价,酌收本色”。[6]卷10《当机章三·和籴》要求本色输粟赎罪,个中原因并不难理解。万历朝的贺灿然这样分析:“至于赎不以银而以粟,使婪朘不得饱而贫民沾实惠,又不易之论也”。[6]卷11《应变章一·赎罪》崇祯朝的祁彪佳曰:“ 今日之赎锾,以饱私橐者多矣。”[6]卷12《当变章二·节锾》崇祯朝户科给事中戴英上奏:“夫纳银则银适以婪官之蠹,纳米则米仍养枵腹之民。”[6]卷11《应变章一·赎罪》潘游龙曰:“其下罪犯,自流徒以下,许其以谷赎罪。余谓罪谷备赈,此荒政遗意也。乃有司者易粟以镪,囊橐其间,经国者惩其冒也。或收之以济边,诚宜归锾于有司,以备积贮。仍敕自今凡罪赎,一切输谷,毋听折纳,而又严侵渔之禁。”[13]如此看来,输粟便可以救助饥民,而输银则可能中饱私囊,这是当时有识之士的一种共识。这种措施对于罪犯和灾民来说都是有利的,罪犯通过输粟而免于惩处,而灾民则得到了救命的粮食,达到了双赢的结果。这样似乎更能体现出罪犯输出的粮食的价值和意义,向人们表明允许罪犯赎罪是因为他们拿出粮食救活了更多的生命,也会降低人们对这一政策的抵触情绪。
如果说输粟只是为了赎罪,而灾荒时期的犯人家庭也可能并不富足,那么,就有人想到可以减少输粟数额以作权宜之计。万历朝吏部主事贺灿然奏曰:“大荒需赈,宜清狱囚之有力而当赎者,谅减其十分之二,赎锾稍轻则完纳自速。其情重即有力而必决配者,亦以荒故,许其收赎,而特不在减例。其罪本可赎而无力者,则减其十分之五。自非极贫,亦必勉力出赎矣”。贺灿然显然是认为降低了赎罪粮食的数额,罪犯赎罪的完纳速度就会加快,灾区就可以迅速拥有救灾粮食。贺灿然还强调灾荒时罪犯赎罪不能是纳银、纳谷,还应当是纳米,“然赎不必谷,不必镪,而当以米”。贺灿然的理由是:“夫谷取其可久贮也,今且旦暮需之,不若输米便。镪将易米以赈饥者,亦不若即以米准镪之为便也”。[6]卷11《应变章一·赎罪》因为灾荒时急需米粟赈济,如果罪犯输谷,灾民还要把谷加工成米才能食用,处于饥饿状态中的灾民不一定有能力去完成这由谷到米的最后一动。但是输米则可以直接食用了,救济更加及时有效。当然,如果不是处于灾荒之际,罪犯输谷到仓库备赈,那就需要输谷了,因为只有谷才有利于储藏。
尽管救荒时的输粟赎罪制度强调要用粮食赎罪,但如果不是十分急迫,赎罪也可以用银钱代替米谷。万历年间,山东督理荒政御史过庭训上疏明神宗:“除真正人命强盗、重大事情,盖不敢议赎外,中有斗殴杀人,而或系一时过误,据法论遣,而原非永远充军者,该地方官酌量听其出谷免罪;如无谷而愿出银者听,取本地仓库收领缴布政司,以备赈济之用”。[6]卷11《应变章一·赎罪疏》和粮食相比,虽然银两对于救济灾民没有那么及时有效,但是有了银两,明朝廷就可以组织人员从丰收的地区买粟,这对于救济灾民也是大有裨益的。因此,有些官员主张罪犯在无谷可输的情况下也可以折色输银。
三、明代荒政中输粟赎罪运作的时评
输粟赎罪这一制度受到明代人积极的评价。万历朝山东督理荒政御史过庭训即从三个方面论证了实施输粟赎罪这一制度的合理性。首先,他认为如果罪犯被判决死刑或是被发配,在执行前,罪犯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在监狱中度过,比如死刑要统一在秋后问斩等,这样会给监狱带来一定的压力,“然有论死而取决无日者,有论配而发遣无期者,众心之忿未快,而囹圄之累日多。”如果实施输粟赎罪,罪犯输粟后被释放,监狱的压力自然就会减轻。其次,“至军徒发遣,骚扰几遍合邑,中途逃脱,贻累又及他人。”就是说,发配充军等即使发遣了,还会可能产生逃跑等问题,罪犯根本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所拟的徒刑等就没有实在意义了。因此,过庭训说这是他不敢轻易发遣罪犯为军徒的原因,“臣心窃伤之,概不敢轻拟问遣。”最后,过庭训还认为允许罪犯输粟是给其一个做善事的机会,“且五流之法,总以冀其改过迁善耳。若愿输粟,全活数百人,是亦改过迁善之机也”。[6]卷11《应变章一·赎罪》如此说来,罪犯输粟赎罪救活灾民就是做了善事,这一制度存在也就有其合理性了。
过庭训对输粟赎罪制度的称道很有代表性,当时其他人对此评价也大致相似。然而也有些人却认为输粟赎罪是纵容犯罪,这是汉代输粟赎罪制度形成以来一直存在的观点。因为罪犯中难免有因为危害他人生命而犯下死罪的,而罪犯输粟之后即可活命,所以,这一制度会让人感到对于逝去的生命是极为不公平的,“死者冤地下,而彼得偷生,圣明之世,诚失之纵”[6]卷11《应变章一·赎罪》。针对这一观点,万历时期吏部主事贺灿然如此反驳道:
然大都一金可活一人,籍其家的万金或数千金,则可活万人或数千人。以活万人数千人之命,偿一人之死,于救荒无策之时,窃谓一时之权,似亦可者。他如侵冒、舞文、武断诸不法,而罪当流者,彼未尝杀人,而籍其家可活千人,则何难一屈法也?故愚以为荒而赎,赎而仅于其最雄于赀者,似不为纵也。[6]卷11《应变章一·赎罪》
祁彪佳也赞成贺灿然的这一观点:“贺公之议,择最雄于赀者,赎其一二,便可活千万余人,要亦偶为通变者耳。若其可以长常行,使上不费法,下得沾惠者”。[6]卷11《应变章一·赎罪》明代官员持有类似观点的不在少数。万历朝刘世教说:“计一笞赎而所活倍之矣,一杖赎而所活更倍之矣。若鬼薪以上,则所赎一而所活者且十之而百千之矣。于法初无大屈,而于穷民则所济博矣”;[12]崇祯朝礼部主事颜茂猷曰:“国有大荒,动系百万人之命”,允许赎罪的罪犯入粟救赎未尝不可,“盖借一人以生千万人耳”;[6]卷2《举纲章二·今言》长洲令祁承认为,“虽屈法于一人,是实可议活千万人之命也,故《周礼》十二荒政之一端也”;[6]卷11《应变章一·赎罪》户部尚书李待问奏曰:“今灾祲病民,流离死徒之际,宽一人即救数千百人之性命,故诸臣咸议及”;[6]卷11《应变章一·赎罪》明末潘游龙曰:“斯乃藏富郡国之策,即有饥岁,民无捐瘠,亦可以省朝廷蠲济之费矣,于财计又岂无补乎?”[13]卷2《户曹·救荒》正是因为这些明代官员看到了输粟赎罪的积极作用,所以他们非常支持这一制度,如周孔教将“除入粟之罪”视作救荒的“四权”之一。[14]《荒政议总纲》弘治年间,都御使林俊看到“蓄积寡而盗繁”的现象,“乞敕省司招民输赀入粟,补散官及抵罪。 情轻法重者,听人赎,为常平本”。[3]卷上《人主》万历年间,张朝端在《常平仓议》中讲到应该恢复常平仓,仓粮的来源之一便是将“每岁将道府州县所理罪犯纸赎,实将一半籴谷入仓”。[13]卷2《户曹·救荒》从这一意见来看,明中后期,可能已经把赎罪收入的一半用于救荒。
结语
明代统治者群体对输粟赎罪制度给予很高的评价,肯定了其在救荒中所发挥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后人能够想到的输粟赎罪所带来的诸如司法不公、加重负担、中饱私囊等问题,当时人们就有了充分的认识,并作出了积极的防范。由此可以看到,明代从建国之初直到最终灭亡的长达二百多年的历程中,不断完善的一整套荒政制度建设是很有亮点的,也是颇有成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