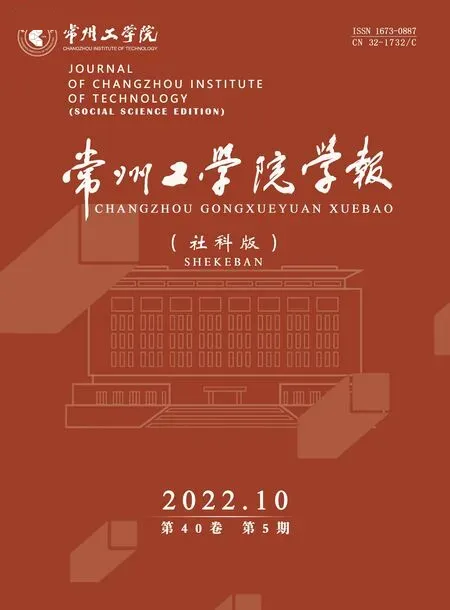论郁达夫小说主体的创生过程与颓废美学的建构
王俊利
(云南工商学院人文艺术学院,云南 昆明 650000)
郁达夫小说中主体最大的特征是身体的疾病、生活的困窘和精神的苦闷。其中,身体疾病指体弱多病和性的烦闷;生活的苦闷主要来自经济的困顿和生计的苦楚;精神的苦闷指绝望悲观的情绪和走向灭亡的颓废姿态。郁达夫的小说更强调人的心理状态和情绪体验,具有主观性和抒情性的特征,他塑造的五四青年知识分子“零余者”形象,均具感伤忧郁、自我憎恨和自我反思的色彩,形成了一种独特忧郁的“病态美”和浪漫抒情的“颓废感伤”情调。这一主体形象从侧面反映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内心的苦闷与焦虑,对五四以后的文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问题的关键是,郁达夫为何要选择“零余者”作为小说叙述的主体?“零余者”的存在空间为何狭窄逼仄且与疾病、爱欲以及颓废关联?这种叙述策略背后暗含着什么样的文化机制,折射出什么样的历史无意识?本文主要借助福柯、柄谷行人和苏珊·桑塔格关于身体美学和疾病美学的分析,结合小说创作的历史语境对文本进行细读,考察郁达夫小说主体存在空间的特点,探究郁达夫小说中主体创生的过程、小说中颓废美学建构的方法以及颓废背后的实质。
一、 逼仄与狭窄:主体的存在空间
郁达夫作品中的“自我”抒情主人公大多生存空间狭窄,常有悲“贫士之无能”的叹息。他们外表柔弱无所依傍,内心愁苦忧郁,精神分裂颓唐,社会地位卑微,经济收入不稳定。他们因国家弱小、生活窘迫、情欲压抑、心理迷惘、内心自卑等产生内心愁苦的飘零之感。体弱多病、生活苦闷、精神忧郁颓废构成了郁达夫小说主体的自然存在、社会存在和精神存在。那么,郁达夫是如何来展现这些自我主体的疾病、苦闷和颓废的?
首先,郁达夫的小说主要用“身体”来展示主体的自然存在,男性自我的身体通常表现为体弱多病和性的“放纵/压抑”两种情况。譬如,《沉沦》《胃病》《茫茫夜》《迷羊》等作品,男主人公经常以病体出现。尤其是在《银灰色的死》中,作者塑造了一位羸弱多病的Y君形象,他体型瘦弱、脸色灰白、眼窝凹陷、颧骨高耸……这位多愁多病的Y君,成为了郁达夫御用的人物形象,他以各种姓名、身份出现在郁达夫的小说中,身患各种恶疾,如肺病、肝炎、胃病、脑病、结核病等。相应地,生病与养病也成为了郁达夫小说中的常见桥段,医院、疗养院与自然风景区就成为了主人公养病的胜地。某种程度上,小说人物生理上的疾病与孱弱不仅构成了主人公的自然生理存在,为小说审美层面营造了一种阴柔美和萎靡感伤之美,而且暗含着一个新主体的创生,表征着一种现代人的生存困境。
在对普通男性生理欲望的呈现方面,郁达夫小说描绘了一系列畸形、病态的男性自我主体形象,他们对性的态度呈现为放纵沉溺或者压抑克制两种态度,展示了知识分子腐朽与压抑的一面。在《沉沦》中,主人公因“性苦闷”而4次偷窥;《迷羊》中王介成因性欲的亢进而导致灵魂的痛苦;《她是一个弱女子》中,身体疾病直接导致吴一粟降低了欲望的需求。这些作品将生理的苦闷与生活的苦闷和精神的苦闷缝合,折射出混乱时代下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人生理想是为政为道、匡济天下,但是动荡不安的生存环境给予他们沉重一击,他们发现自身的力量是如此渺小和无力,竟然报国无门、无家可归。
其次,郁达夫小说主要以生活的苦闷来展示主体的社会存在,他多从职业的缺失和婚姻的失落两个方面展开叙述。郁达夫小说中主人公的职业生涯可用《还乡记》中的“浮浪”二字来概括,他们由于没有稳定的工作而过着一种困窘的生活。从郁达夫创作的第一篇小说《银灰色的死》开始,主人公几乎都面临着职业生涯的危机,如《清冷的午后》中一落千丈、濒临破产的聚芳号的老板,《茫茫夜》中近于失业的教师。郁达夫擅长在艰难的环境中展示社会“边缘人”困窘、苦闷的生活状态,展现主体逼仄、狭窄的生存空间,他们没有显赫的政治地位,没有稳定的职业收入和经济保障,他们多徘徊于旅馆、医院、妓院和家庭之间,呈现出一种无所依傍的柔弱感和迷惘感,如于质夫、王介成、“我”、“他”等。
郁达夫小说中主人公的婚姻生活则是短暂、凄冷的,自我主体因贫弱不堪而丧失了婚姻家庭的温暖,是一个孤独的“零余者”形象。一般而言,家庭是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男性通常在家庭中承担着顶门立户、养家糊口的责任。在郁达夫的小说中,男主人公大多缺乏稳定的职业和收入,经济的困窘也间接导致了婚姻秩序的紊乱和婚姻生活的凄惨。在《迷羊》中,王介成辞职后与谢月英过着风花雪月、坐吃山空的同居生活。一年后,谢月英离弃了王介成。通过小说的情节可以推测,谢月英若不离开王介成,二人的结局恐怕也只有两条:同归于尽或者劳燕分飞。在《她是一个弱女子》中,吴一粟的妻子郑秀月在其穷困潦倒之际投奔了旧情人张康,当吴一粟发现妻子背叛他时,并未表现出暴怒,而是泪眼婆娑、吞吞吐吐地请求张先生不要毒打郑秀月,埋怨自己因失业无法养活妻子。在《银灰色的死》中,男人迫于生计奔波在外,内心觉得愧对乡下守旧贤惠的妻子;《零余者》中,主人公面对家庭产生无用感和无力感;《茑萝行》中,“我”因曾经虐待妻子而产生忏悔之情;《在寒风里》中,主人公无家可归,产生卑微的心境;《青烟》中,主人公在走投无路之际以投河自尽了却残生。在经济困顿、生计苦楚的挤压下,郁达夫笔下的男性主体难以承载家庭的重负,婚姻的纽带也难以维系,这是生活支柱倾塌连带的家庭生活悲剧,也是生活困窘带来的心酸和无奈。社会身份的低微,家庭生活的缺失,使郁达夫小说中的主体形象笼罩着苦闷感、无奈感和羞辱感。
最后,郁达夫主要从人物内心的悲伤、绝望和颓废来展示主体的精神存在。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的弱化,导致郁达夫笔下的自我主体精神层面崩溃,他们往往意志薄弱,经不起诱惑。面对生理的苦闷、生活的困窘,他们并不顽强抵抗,积极进取,而是用哭泣、疯狂或者死亡等方式来应对这无奈的人生。与传统叙述中刚毅、强壮的男性形象不同,哭泣的主人公是郁达夫小说中常见的人物群像,他们有眼睛里“浮着两泓清泪”者、“盈盈落泪”者、“放声痛哭”者、泪如瀑布者等。尽管这些人物也认为眼泪的倾泻是一种情感脆弱的表现,是一种丢人的行为,但是他们依然无法控制泪水的流淌。可以说,眼泪既展现了主人公无力反抗生活中的挫折、无法坦然接受这个世界的事实,又展示了主体为自我辩护的功能,在哭泣中,主人公内心的不满和狂热暂时得以宣泄。
忧郁的心情、悲泣的眼泪和病态的人格精神使郁达夫笔下的主体显示出一种柔弱、忧郁、低迷的“颓废美”。他们对社会、人生的反抗显示出一种苍白感和无力感,譬如,《茑萝行》中,主人公想要反抗生活却无能为力地叹息:“怯弱的我们,没有能力的我们,教我们从何处反抗起呢?”①于是有了《茫茫夜》中自虐、自苦的怪异行为,《沉沦》中偷窥、自杀的变态行为等。在极度的压抑和失落中,郁达夫小说中的主体呈现出一种绝望、颓废的情绪,一种退缩的姿态,这种自卑和懦弱的性格致使他们走向疯狂和死亡。在郁达夫的小说中,男主人公有自杀、自虐倾向的有7个,心如死灰、看破红尘皈依佛门或上帝的有2个,精神失常、疯癫的有2个。此外,还有一些人物濒临死亡,或者想要自杀,或者身患抑郁症,抑或极度自卑与极度偏执。
郁达夫小说主体的存在空间可以用逼仄狭窄来概括,他们的自然空间“畸形”,社会空间凄苦,精神空间烦闷。小说中的主体形象映射了作家对知识分子生活、生命的思考,折射出作家对生活的认知和感受。
二、 东方与西方:主体的“萌生”与颓废美学的构筑
郁达夫善于从病理学、主体的灵肉冲突和精神苦闷的角度来展示现代感性自我主体的诞生过程,他借助结核病、忧郁症和颓废美学使“现代人”在出世伊始就自带性的苦闷与灵肉矛盾。如,在《沉沦》《茫茫夜》《秋柳》等系列作品中,当文弱清瘦的主人公形象与结核病、忧郁症、精神萎靡搭配组合时,一种新的夹杂着灵肉冲突的现代感性自我形象便创生了。郁达夫为何要选择忧郁症患者和颓废美学来构筑小说中的抒情主体呢?这与郁达夫留学日本时期的经历和个人的美学趣味相关。日本迷乱的思想环境和文坛氛围既催发了郁达夫的颓废感伤情绪,又使他以严肃的态度正视“性”这一问题。当时,日本的思想界处于一种纵横错乱的状态,人们急切地想要打破旧传统的束缚,但是新的使人安身立命的东西却并未建构起来。这种新旧思想杂糅的文化氛围,使部分青年坠入了虚无、迷惘、颓废甚至轻生的困境。郁达夫《敝帚集·序孙译〈出家及其弟子〉》一文曾记录,日本高一学生,每年自杀和沉湎于酒色事件的有数起。这种迷乱的思想环境间接熏染着郁达夫的文学创作,使他作品中的主人公多了几分颓废、迷惘与伤感的气质,也使他的小说从正面描写普通男性的“灵肉冲突”。
明治维新后,西方思潮对日本的旧礼教和封建观念形成了猛烈冲击,尤其是两性解放思想在知识阶层、学生群体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两性解放的观念对郁达夫的人生观、道德观及恋爱观都产生了不容小觑的影响,使他以锋芒毕露的笔调书写普通人“性”的苦闷。尽管从“灵肉冲突”角度强调人的天性和社会问题具有一定的狭隘性和副作用,也使他的作品被诟病为具有“颓废”与“色情”的特点,然而强调人的天性也可视为郁达夫挑战传统礼教、封建桎梏的一种策略性尝试,使他小说中的主体创生初始就具备了现代人“两性解放”的性格特征。
日本“私小说”对郁达夫小说的体裁、技巧、情调与笔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郁达夫比较推崇和敬佩的两位“私小说”作家是佐藤春夫和葛西善藏,他们的作品更加关注个体敏感纤细的感触和孤独忧郁的情绪,解剖同情个体的病态畸形的心理,诗意升华个体的灵肉冲突。他曾在《海上通信》中表示出对佐藤《病了的蔷薇》的推崇,有想模仿却“画虎不成”的经历,也曾在《日记九种》中夸赞葛西善藏小说“实在做的很好”。在《沉沦》中,郁达夫有意识地借鉴了《病了的蔷薇》中“叙述心境”的手法、主人公有着忧郁症的特征和引用外国诗歌的桥段。这种用自我意识解析人们内心世界的笔法,使《沉沦》在对人生的孤独、疲倦和忧郁的解析中,流露出一种世纪末的美。那么,为何这一时期日本的文学界会推崇“私小说”呢?
这一时期日本文学界比较热衷于西方颓废主义思潮,且将与颓废主义有关的文学术语视为“先锋”与“现代”的同义语。日本学者伊藤虎丸也指出:“郁达夫留学时候的日本是把像‘病的’啦,‘忧郁’啦或者‘颓废’啦等字眼儿当作‘现代的’的代词来原封不动地使用的时代。郁达夫当时把‘病的’、‘忧郁’等看作‘现代人的苦闷 ’。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他是直接地在佐藤春夫,或者说是在更广泛的大正时期的、特别是新浪漫派的文学影响下,开始迈出了作为小说家的第一步吧!”②由此可见,“颓废”和“疾病”对郁达夫以及日本作家来说是一种现代性的感受,一种现代性的代名词。从小说文本中可以发现,当郁达夫使用“忧郁症”这一概念时,会同时附上它的英文。也就是说,西方医学知识和西方现代性共同参与了郁达夫的小说创作,并且形成了一种现代性的隐喻,表征着一种具有“新的态度”的现代自我主体的诞生。
另一方面,从郁达夫的美学趣味来看,他更钟情于文学作品中的感伤主义和“颓废色彩”,偏爱在悲伤的情感、忧郁的情绪、怪诞的心理中提炼美感。例如:在《感伤的旅行》中,他尝试用诚挚的感伤姿态来容纳社会意识;在《沉沦》中,主人公借华兹华斯的诗歌来感慨异国现实的“荒淫残酷”;在《春风沉醉的晚上》的结尾,他使用了波德莱尔式的意象,将空中的薄云比作“腐烂的尸体”;在《空虚》中,他描写了主人公阅读魏尔伦作品的画面,也叙述了主人公阅读古尔蒙的论文集《颓废论》的片段;在《戏剧论》中,他盛赞了魏德金德用象征手法揭露青年生理需求与道德戒律之间的矛盾。
“颓废”在象征派思潮中指集心理、疾病与美学为一体的概念。卡林内斯库曾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用颓废心理学、心理病理学、颓废美学3个概念来指称于斯曼的小说。郁达夫的小说同样具有一种颓废美,他不仅描绘人物心理—病理学意义上的颓废,而且在描写环境和风景时也写出了颓废的美感。在小说《过去》中,他对“M港市”的感受是“一种衰颓的美感”,一种可以在安居中自然“消沉下去的美感”。他的散文中也经常可见这种对颓废美的观赏,如《苏州烟雨记》中,作者认为苏州的美可以用近代语“颓废美”3个字来概括。《钓台的春昼》中,他称西台的景色可以代表“东方民族性的颓废荒凉的美”。需要注意的是,郁达夫眼中的“东方颓废荒凉美”的源头是西方图画中的风景,是“威廉退尔的祠堂”和“珂罗版色彩”等参照物。这一对比在无意识中暴露出郁达夫是戴着西方颓废美的有色眼镜来观看中国的风景的,他描摹的具有“东方民族性”的荒凉颓废美的风景是以西方为他者的。
应该说,留日生涯间接影响了郁达夫的小说创作,他曾在日本留学10年之久,日本的政治、社会、文化对他的文学生涯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熏陶着他的气质,影响了他的思想和创作。个人的美学趣味直接影响了郁达夫小说中主体的“萌生”和颓废美学的构筑,他更青睐于探析个体内心的病态情感,观察世间的病态美感,借助对主体内心的怅惘、苦闷、荒诞来展示一代青年的普遍忧郁。值得一提的是,郁达夫小说中的忧郁美、感伤美和颓废美融合了东方与西方的美学情趣,既有中国传统文化古典美的影响,又有中国士大夫文化中清高和放浪形骸的烙印,更有西方现代性的影响。
三、 疾病与死亡:主体与民族国家的并置
疾病与死亡是郁达夫小说中常见的意象,作者通过个体对生命的感悟、身体对爱欲的沉溺或压抑以及颓废美学等维度来展开叙事,尝试构建一种新的抒情主体形象。譬如,在1921年出版的小说集《沉沦》中,《银灰色的死》中主人公死于脑溢血,《沉沦》的主人公患忧郁症,最后跳海自杀,《南迁》中的伊人因发烧而患肺炎。那么,郁达夫为何青睐于书写疾病和死亡?这样的叙事策略产生了何种效果?
从社会根源上来看,对疾病与死亡意象的选取,源自郁达夫对时代、民族和社会的失望。郁达夫出生于1896年,恰逢国家极度衰败的时期。1913年至1922年留学日本的经历,使他看清了中国在世界版图中的位置,体验到了弱国子民置身异土时被侮辱、被歧视的切肤之痛。回国以后,面对尖锐的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的政治动乱以及“国民性格的劣根性”,他再度陷入了彷徨、苦闷与失望之中。也就是说,郁达夫陷入了三重失望和痛苦之中,即资本主义列强的残暴和丑恶、国内政局的腐败黑暗以及民族劣根性的顽固。这三重痛苦与失望使郁达夫开始正视黑暗严峻的现实,他将矛头指向了导致“国民性”堕落的封建道德,在作品中将个人的情欲、病态的心理与复杂的社会问题嫁接,创作出“民族+性”的文学样式。
从主观因素来看,郁达夫的性格、气质以及生活状态使他更偏爱疾病、死亡等灰色调的意象。郁达夫天生性格柔弱、情感纤敏,他借作品人物反复表达这一性格特点,小说中的主人公总是以“弱者”的形象出现,拥有一张贫血的脸、一颗胆怯的心,是一个怀才不遇而又带点病态心理的孤独青年。这种纤细、敏锐又柔弱的情感,常常使他放大生活中的一些挫折、愁苦和不公正,从而产生痛苦、压抑和激愤的情绪。在残酷的现实中,他看清了封建制度与封建礼教对国人灵魂的毒害和腐蚀,目睹了国人倾陷争夺、损人利己的社会现象,看到了他所追求的革命阵营内部也会滋生黑暗、腐败。这些现象沉重地打击了他柔弱纤敏的神经,动摇了他的反抗精神和革命信念,加重了他的悲观情绪,也使他小说中的主体多了几分自伤自悼、自艾自怜的病态美。除了情感纤细、内向的一面,郁达夫的气质中还有真率、外露的一面。真率的气质使他在创作中坦然地暴露自己内心的苦闷和灵魂中的丑陋。他欣赏阮籍、刘伶等名士的洒脱不羁,敬佩卢梭“回归自然”的精神和正视“畸形”的勇气。
郁达夫的性格融合了中国传统文人的孤傲清高和“放浪形骸”,他一方面保持着诚实、勤勉和忠贞的信念,另一方面又挑战传统礼教的桎梏,追求人的尊严和情感的自由。这种真率与忧郁兼具的双重性格,是影响郁达夫审美选择的内因,使他将个人的“忧郁”与社会的“苦难”相结合,加工处理为具有时代意识和家国情怀的现代新人,并引申出“个人/民族”的阐释空间。
小说《沉沦》已经浮现出现代觉醒自我主体的双重危机,即“个人/民族”危机的并置。这种危机的抒发是以两性交往为载体的,当小说主人公想到要在一位日本少女面前自称“我是支那人”时,不自觉地萌生了一种自卑情绪。女强男弱的两性交往在叙述中被转换为“外强中弱”的民族主义情绪,并发出“中国要强大”的呼喊。尤其是小说结尾主人公跳海前向“祖国”宣泄内心情绪时的一段独白,巧妙地将个体的崩溃与民族国家建立了联系,将自我的柔弱与民族国家的弱小对接。在《蜃楼》中,郁达夫也运用了并置爱欲本能与民族意识的“个人/民族”叙述模式,小说借主人公在异国他乡的苦恼、挫折和对异国女性的情感体验来展示一种弱者对强者的社会或民族的反抗。当男主人公受到美国少女冶妮的诱惑时,他联想到的是祖国的弱小和欧美列强的强大这种双方不对等的关系,想到的是亨利·詹姆斯笔下喜欢玩弄男子、性格难以捉摸的美国妇女形象。
这种将爱欲和民族意识并置的创伤性体验曾出现在他的著述中,他写道:“是在日本,我早就觉悟到了今后中国的运命,与夫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不得不受的炼狱的历程。而国际地位不平等的反应,弱国民族所受的侮辱与欺凌,感觉得最深切而亦最难忍受的地方,是在男女两性,正中了爱神毒箭的一刹那。支那或支那人的这一个名词,在东邻的日本民族,尤其是妙年少女的口里被说出的时候,听取者的脑里心里,会起怎么样的一种被侮辱,绝望,悲愤,隐痛的混合作用,是没有到过日本的中国同胞,绝对地想象不出来的。”③可以说,身处异国的屈辱感、绝望感和悲愤感使郁达夫特别关注中国未来命运的发展,并且将男女两性之间的交往与民族被侮辱、被欺凌的不平等待遇嫁接,创造出“民族+性”的叙事模式。诚如齐泽克所言,“国家、民族身份只有在其存在受到威胁的经验的促使下才得以成型;在这种经验出现之前,什么国家啦,民族身份啦,统统不存在”④。从这个层面来看,郁达夫小说中塑造的现代觉醒主体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是意识形态“质询”的结果。
疾病与死亡构成了郁达夫小说主体的关键特征,这种审美选择客观上来源于郁达夫对时代、民族、社会的悲观绝望情绪,主观上取决于他柔弱又洒脱的性格、忧郁又真率的气质、纤敏又复杂的思想情感。从郁达夫的生存环境和个人性格特征考察郁达夫小说主体多疾病与死亡的审美选择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其一,郁达夫本质上是热爱生命而非厌弃人生的。他敏锐地体察着世间的百态,真诚地追求着正义和美,并以文学的方式将个体与民族、国家并置,探讨社会人生问题。其二,死亡和疾病意象外壳之下隐伏着反思和反抗的因素。面对复杂的社会动乱和艰难的人生,他用一支铁笔抨击社会人心,倾泻个人哀愁,抒发爱国激情。
四、 放纵与压抑:主体的爱欲叙事
中国传统文学中,爱和欲的叙述经常是分离的,尤其是涉及欲望这一范畴时,欲望总是摇摆于禁欲和纵欲的两极,呈现为有欲无爱或者是压制欲望。在现代文学中,郁达夫较早涉及“爱欲”这一领域,且用自己的方式巧妙地处理了这一题材。需要思考的是,郁达夫在何种意义上将“性”作为问题提出?他又是如何对“性”进行话语建构的?
翻阅郁达夫的小说,可以发现,郁达夫对“性”问题的探讨既有别于明清色情文学,也有别于纵欲文学,它是一种爱和欲联结、情与性的融合,是统筹现代人本主义理论、生命觉醒意识理论以及现代精神分析学理论的独特创造。在他的小说中,主人公的爱和欲逐渐趋于统一,既有泛爱的品格,又具备现代人的感性和欲望。性的需求和灵与肉的冲突使郁达夫笔下的主人公在反思和忏悔之后依然沦陷在欲望的漩涡中,也使小说主人公面临“沉迷欲望—反思忏悔—沉迷欲望—反思忏悔”的恶性循环。应该说,郁达夫在性的苦闷中展示了现代人生活的困境和焦虑,企图用自省和忏悔的药方来救赎自我的灵魂。譬如,小说《迷羊》就包含了这种自我救赎的意味。“迷羊”出自基督教用语,指上帝迷途的羔羊。小说借“迷羊”这一意象,从感性的沉溺、放纵与失途的困惑、惘然入手,讲述了王介成和谢月英的情感生活,表达了人在爱欲之途上的迷失这一主题,揭示出没有生存远景和目标的卿卿我我注定不会长久。郁达夫小说中的人物多呈现一种压制欲望的状态,他们要么是欲望匮乏者,要么是欲望对象难以企及。问题是郁达夫为何要选择“爱欲的压抑者”作为小说的主人公?
实际上,借助压抑主体爱欲这一话语装置,郁达夫的小说叙述在无形中与现代性机制相对接,并且在中国现代文坛构建了“爱欲—压抑爱欲”和“爱欲—净化爱欲”的叙述模式。福柯指出:“在漫长的两个世纪里,性的历史就是一部日趋严厉的压抑史。”⑤郁达夫的小说可以看作是伴随着“现代历史和现代机制”形成的关于压抑的文学样本。关于压抑和匮乏这两个概念,福柯、贝西尔和柄谷行人等都做过相关研究。福柯关注权力对身体的规训与压抑,他指出权力并非只压抑性,它以“推论的方式塑造出‘性’和有着性欲的主体来”⑥。贝西尔认为匮乏与主体性的诞生密切相关,是主体性得以生成的条件。柄谷行人则认为,“主体(主观)”是在“肉体”的压抑之下才得到确认的。而郁达夫小说中充满爱欲的主体正是在压抑的话语之下建立的,压抑不仅成为了构建主体的机制,而且使郁达夫发现了欲望,并且以悖论的情境呈现,最终转化为人“内面(主观)”的一部分。问题的关键是,对欲望的压抑除了导致欲望的放纵外,是否能够将压抑内化呢?
实践证明,人的意志是可以重塑的,压抑机制也可以将欲望内化。在中国,传统儒家将人的欲望与“仁义”“修身”“礼仪”等词对立起来,期望通过修身养性来节制情感泛滥。在西方,基督教教义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以忏悔的方式将压抑内化。据《马太福音》记录,耶稣认为,不可奸淫,看见妇女动淫念属于心里犯奸淫,这一教条尝试将忏悔与自省内化为人的自觉行为,将压抑的欲望转换为情感的净化与升华。
郁达夫小说的另一种经典叙述模式是:身体被压抑以及在压抑中完成净化与升华的过程。从郁达夫的作品来看,促使郁达夫小说中自我情感净化与升华的重要因素是宗教与风景。例如,在《蜃楼》中,作者在面对“清新纯洁的田园朝景”时,如同进入了“本来无物的菩提妙境”,内心的“爱欲情愁”和“小我”在顷刻间得到释然。在《迟桂花》中,风景同样参与了救赎人物心灵的过程。“我”与好友的妹妹在爬山时,竟产生了“一念邪心”,后来在优美的自然风景中,在妹妹单纯、天然的言行中,“我”的欲念消退,并萌生了愧疚感和羞耻感。这种没有牧师的忏悔表征着人的自觉意识的生成,预示着压抑的内化以及主人公在压抑欲望后情感的净化与升华。在此,爱欲和压抑的叙述呈现一种“颠倒”的关系:爱欲的满足并不依靠情感的沉溺与放纵,相反,压抑欲望后反而会获得内心的宁静与升华。这一点与柄谷行人对主体性生成问题的研究相似。柄谷行人从人的“内面”与“自白”制度入手,认为“现代文学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内在主体性的人之诞生,这个主体性的人是以自白的方式出现在小说等文学样式中,逐渐占据了核心的地位”。他通过考察明治时期基督教与文学之间关系,发现“自白(表现方法)这一文学制度起源于基督教的忏悔制度中”,是“自白这一制度的确立促成了主体性的人之诞生”⑦。此外,柄谷行人还进一步确证了“性”“隐私”等概念与基督教自白制度的关系。隐私其实是在自白制度中产生的,正是由于基督徒的自白和忏悔,才确认了隐私这一概念的存在。相应地,性因为具有私密性,所以成为了自白的权威性题材,也使人们从自白制度中发现了性。同样,在郁达夫的小说叙述中,疾病和自叙传在前,现代主体的诞生与觉醒在后。小说《迷羊》可以视为一份融合自叙传小说、基督教自白、忏悔制度的文学样本,故事采用了“后叙”的方式,以作者得到某人手稿的模式,讲述主人公“我”在一位美国牧师的感召下写出了一篇自我忏悔录,牧师将忏悔录交给了好友达夫,达夫用《迷羊》作为题目发表后,落款“达夫”的故事。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郁达夫小说中现代自我的创生是以“自叙传”的形式呈现的,这种自叙传与基督教中的自白、忏悔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种对“自我”和个人主体性的大力宣扬,实质上是一种对现代主体性的探索性的尝试,只是这种现代主体是以西方审美为参照系的。
虽然郁达夫的小说经常涉及爱欲和颓废美,但是他的小说与那些追求感官刺激和市场需求的色情文学、纵欲文学有着本质的区别。他小说中的“身体”是经过历史和现代性规训的身体,是历史事件的载体,承载着灵与肉的冲突,折射着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检索郁达夫对身体的书写痕迹,我们可以追溯到他留日期间的文化语境,得知他笔下的疾病、身体以及压抑背后的文化装置是一种带有西方审美色彩的现代性机制。从现代性的生成这一层面解读郁达夫的小说,探究郁达夫小说创作与现代性装置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可以发现现代性装置催发了现代小说的创生,并促使现代小说区别于色情文学和纵欲文学;另一方面,现代小说又是现代性以及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重要媒介,郁达夫对现代主体的现代感、身体性、颓废美的书写,无意识间参与了现代性和民族国家的构建。
五、结语
郁达夫对疾病和颓废美学的征用,折射出20世纪20年代某些知识青年生活的困窘、身体的漂泊、精神的迷惘。疾病的存在使主体意识到身体性的存在,也使现代小说在萌生之始就与身体建立了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郁达夫采用身体与民族、国家并置的叙述策略,以压抑身体的方式诠释了身体的感性和觉醒过程。这个压抑的身体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民族、国家的权力机制规范和召唤,它将弱小民族体验和性道德内化为一种自觉意识的审美化主体。
人的身体实际上处于社会之网中,受到自然、社会、历史等诸种因素的规约。有趣的是,人们常常更关注精神和思想的自由程度,忽略了国家和社会对身体的束缚。身体受制于国家权力,是以被规训的形式存在的。现代社会试图借助美学来探讨身体性问题,它将肉体的观念与国家、阶级矛盾和生产方式等概念衔接起来。城市流浪者之所以被排除于都市文明之外,是因为他们的身体不符合现代社会重新建构身体的要求。现代社会需要身体具备多方面的素质,如消费的身体、技术化的身体、美学建构的身体等。
审美主要以人类感性领域为对象,指向人的感性层面。康德、马克思等哲学家都认为审美是人与生俱来的本领,而柄谷行人却论证了内面、感性也有在颠倒中被异化的风险。现代性的历史趋势是理性收编感性的过程,也是将审美政治化的过程。也就是说,审美现代性是一个矛盾且意义双关的概念,它既饰演了解放力量的角色,又预示着一种“内化的压抑”。一方面,审美现代性保留着主体统一的特性,无需借助法律制度,每一个主体在维持社会协调有序的同时,又不失独特的个性;另一方面,审美现代性也会将压抑内化,将社会统治根植于被征服者的肉体中,从而卓有成效地发挥其政治领导权的作用。郁达夫小说中的自我暴露、自我宣泄的情绪,往往被人们视为一种个体的非理性和感性的觉醒。实质上,支配这种非理性的依然是理性,在颠倒的状态中,身体被唤醒。当主人公的感伤颓废气质与疾病主题相关联时,主体的“出走”便具有了一种漂泊感和离散感。他们的一生仿佛一场“感伤的旅行”,他们的精神则呈现出个体、爱欲与家国之间的分裂感。诚如伊格尔顿所言,身体美学具有双重性,他“一方面是文明社会中主体的‘感性的、个体的和直接性的存在’;另一方面是国家政治方面‘抽象的、非自由的人和寓言化、伦理化的人’”⑧。
注释:
① 郁达夫:《茑萝行》,萧枫编:《郁达夫作品集(一)》,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36页。
② 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中日近现代比较文学初探》,孙猛、徐江、李冬木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70页。
③ 郁达夫:《雪夜》,《郁达夫文集》(第4卷),花城出版社,1983年,第93-95页。
④ 齐泽克:《如何令身体陷入僵局?》,汪民安、陈永国编: 《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2页。
⑤ 米歇尔·福柯:《福柯集》,杜小真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第290页。
⑥ 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序言》,余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页。
⑦ 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267-268页。
⑧ 特里·伊格尔顿:《审美的意识形态·导言》,王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