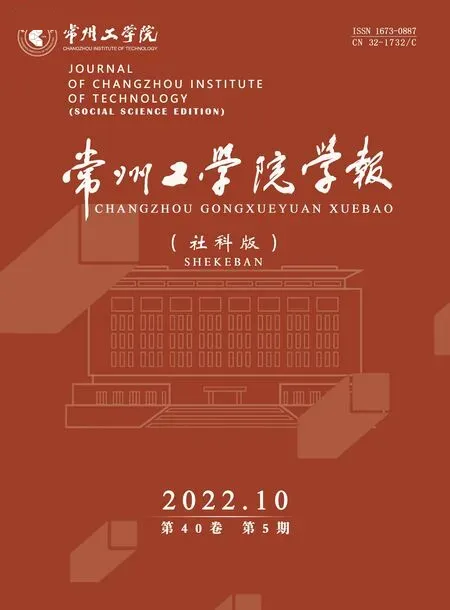身体空间与社会秩序
——解读张洁的转型之作《他有什么病》
何满英,邹璐
(大连外国语大学汉学院,辽宁 大连 116000)
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从森林来的孩子》步入文坛起到如今,张洁作品颇丰,但学界对其关注的重心一直集中在其早期的作品《沉重的翅膀》《方舟》《祖母绿》以及为其二度摘下茅盾文学奖的《无字》上,对其后期的作品以及中期的一些短篇小说一直缺少关注。发表于1986年的《病》(以下简称《病》)更是关注者寥寥,只有在分析其作品序列的时候,稍稍提及这部作品是张洁审美意识和写作姿态转变的标志,如王绯曾说,从《病》开始,张洁就因为对世界的彻底失望而背叛了早期那种成熟的严谨,以及正统又有分寸的对社会的把握和对文学的观照[1]。目前对这部作品的专门评论只有两篇论文:一篇是黄书泉写于1987年的《从现代意识到现代审美意识——谈张洁近作〈他有什么病〉》,论述的重点依然是从文本看张洁审美意识的转变[2]。另一篇是许文郁写于1988年的《两种荒谬感——谈张洁的〈他有什么病〉和王安忆的〈锦绣谷之恋〉》,她认为张洁在《病》中透露出来的荒谬感是一种社会荒谬感,它来源于内在的疯狂和社会的稳定,这是作者从历史反思中得出来的;而《锦绣谷之恋》中的荒谬感是因为认识到过去意识的虚妄不可信,体现了人自我意识的觉醒[3]。两篇文章发表的时间久远,近些年也没有学者从新的视角对《病》作出阐释。
《病》中有大量身体意象的存在和身体空间的营造,并暴露了不同身体空间的紧张关系。而在张洁之前的作品中也存在大量的身体描写,只是随着她审美意识和对社会认知的转变,“身体”变得愈加抽象和符号化。
一、 物质性的身体意象
学界对张洁的研究视角是多样化的,女性主义文学、比较文学、叙事学、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等角度的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其作品频繁出现的身体意象却鲜有人关注。比如在《沉重的翅膀》中,通过叶知秋的眼睛看夏竹筠的身体:“她腕上的皮肤是细腻的,雪白的,细细的金表链勒在手腕上显得紧了,她已经开始发胖。”[4]57通过陈咏明看老吕头的身体:“绿色面料灰色兔毛的衬里,耷拉着两个耳扇子。一走一扇忽,身上那件棉大衣,油腻腻的,胳膊肘,前襟和下摆的边缘都已经不过如此了,就连每个扣眼儿,也都重新锁过了。”[4]90在《方舟》中,通过荆华看白复山:“银灰色的夏装,白色镂空的皮鞋,头发留得不像嬉皮士那样长,也不像那么短……琴拉得不怎么样,派头却做得十足。”[5]36白复山看梁倩:“袜套上有一个不小的破洞,顺着这短袜一路看上去,上面是麻秆一样的细腿。再往上是窄小的胯,再往上是干瘪的胸……”[5]51随后的《上火》《只有一个太阳》《她抽的烟是薄荷味的》《无字》等作品更是大量出现身体描写。
在这些作品中,身体是实实在在的生物意义上的肉身,作者通过看和被看描写人物的肖像、身材和穿着,而且极善于“不怀好意”地对某个细节进行放大,以突出人物性格特征和社会阶级地位,并寄托自身对人物的厌恶或悲悯之情。到晚期创作阶段,张洁更注重在作品中表达某种魔幻色彩和神秘气质,“身体”才大规模地退出她的文本。
在《病》中,类似的身体细描有所减少,只有4处:第一处是开头胡立川在机场打量候机的人群。第二处是描写躺在大槐树下睡觉的汉子:“汉子大张着嘴,仰面朝天地睡着。屁股肥大的苍蝇,在他的嘴里爬来爬去。”[6]232“躺在老槐树下睡觉的汉子这时又醒了,还倚坐在老槐树下,可他的眼神、他浑身的肉却紧了起来。”[6]234第三处是对黄老头在烧人民币为病危的孙子祈福时的紧张神态描写。最后一处是描写“喂”的丑陋面貌,以及他的疯女人和傻女儿同样丑陋但对他有诱惑力的肉体。这时身体出现的作用不再是描写意义上的,而更多有情节上的补充作用和隐喻色彩。比如在老槐树下睡觉的汉子,在丁老汉烧棉花前后出现两次,他每隔半袋烟的功夫,就朝天“嗷”的一声嚎。作者形容他的叫声“又敞亮又嘶哑,又鲜活又死气,又欢畅又凄怆,又暖和又苍凉……似有发泄不完的精力,又似耗尽最后的力气”[6]234。在某种程度上,他象征着文本所有的人物,以及文本诞生年代的所有人物,看似忙忙碌碌,实则毫无意义,貌似精力旺盛,实则精神空间压抑逼仄,胸中有一团莫名的躁动需要发泄出来,但又找不到具体的发泄对象。
写实的身体细描减少,但却充斥着大量零碎的身体部件以及和身体相关的感知,外界破坏性的施虐,人与人之间的倾轧,都集中在身体上“烙印”出痕迹。比如丁小丽的处女膜,文学教授的讲座名叫“肛门与蔷薇”,研究生业余作家的书名叫“天涯满大腿”,木匠在宿舍做木工的噪音对候玉峰造成的影响,像是在“回锯他的骨头,凿他的脑壳,打磨他的神经,刨他的肌肉”[6]236。一方面,作者赋予人体器官负面色彩,以达到戏谑和讽刺效果;另一方面在有意营造一种身体感知上的紧张性,类似于曹禺在《雷雨》中反复写到的恶劣天气,而每个人就处于这种神经紧绷的状态中,等待着一场爆发。只是张洁营造这种紧张性,并不是通过天气,而是通过身体空间的对立和反抗。外显的夸张手法和内在神经性的感知相结合,使得物质性的身体有了内部的空间层次,它得以容纳主体在现实社会中所接触到的情绪,并对这些触感作出精细的反应。
二、 被建构的身体空间
美国学者戴维·哈维站在地理学和政治社会学的交叉口,富有洞见地指出了资本在空间生产上的特殊策略:“空间生产是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动态的一个基本环节……资本有粉粹、分割及区分的能力,制造空间差异,进行地缘政治的能力。”[7]即资本在消除阻碍流通的空间障碍的同时,也基于各地文化、语言、宗教信仰等其他因素的不同来制造不同的地理景观,它们制造异质和分裂,分解同质和团结,从而使得抵抗资本主义的方式无法确定。
尽管《病》始终是围绕医院这个具体的地点书写,并不涉及大的地理空间的差异,但在文本中,没有中心人物,在叙事模式上采用的是一种片段拼接的结构。因而其空间差异的展示窗口不再是地理位置意义上的政治文化等等,而是个体的身体。身体本身代表了空间,不同个体身体空间的差异由市场化经济实行之后日渐悬殊的贫富不均造成,而不是根据个体的受教育程度和道德素养的高低,这种评判标准的外化和物化本身就是经济制度转型的后果之一。
在文本中,侯玉峰作为医生,经济实力比不上用公家材料做私活的木匠;心脏插管的导管国外用完一次就扔掉,国内医院则消毒之后再反复利用;黄老汉在用烧人民币的方式企图挽救孙子的性命;在太平间工作的“喂”因为相貌丑陋失去性繁殖的机会,而深陷和傻女儿乱伦的罪恶感中;人民教师患病却无钱医治,妻子无法,只好去卖血;外贸公司经理因为答应为医院购买设备获得了最好的治疗待遇;来华访问的国外医学专家住的是金碧辉煌的五星级酒店,而负责接待的胡立川医生却只能在8平米的房子里蜗居,曾经的护士同事离职后去酒店当服务员,随手点的咖啡蛋糕就是自己大半个月的工资……对比是多方面的,因为经济条件这一个要素的不同,导致身体空间千差万别,这个空间中包含了医疗服务水平、繁殖后代的机会、住房条件、饮食健康等等内容。种种不合理的差别真实地被作者通过身体这一媒介暴露了出来。
不同个体带着自己鲜活的身体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后,身体被当作机器根据生产能力的不同被制造出了消费空间的差异,这些通过生活方式、生活标准、资源运用方式等多种途径表现的差异,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艰难甚至不可能。于是侯玉峰和小木匠最终大打出手;胡立川日渐封闭,只能在日记中彷徨失措;陈莲生感觉自己像奶油蛋糕正在被不同的人吃掉……在这种足够小的地理空间中展示出个体生存状态的千差万别,充分体现了资本在空间生产上的出色能力。
这一过程也论证了福柯所说的话:“我们时代的焦虑与空间有着根本的关系,比之时间的关系更甚。”[8]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出了身体是“知识权力与权利干预的领域”[9]的结论,并可视化地描绘了权利、知识和道德等机制对身体的规训。在《病》中,张洁对身体被规训过程的书写也随处可见:某领导的司机在医院的叫号中插队,胡立川让他按次序就诊,司机拿着鸡毛当令箭,把自己和领导、和国家大事串联起来,认为耽误他的时间就是在耽误国事,他就以这一套不成逻辑的逻辑说服了医院党支部书记,获得了“照顾”;患有精神病的医生当选为省科协主席,一名女内科大夫提出异议,从此医院里开始流传内科大夫精神不正常的传闻;侯玉峰受木匠的噪音影响,而领导因为要留住木匠为医院服务,拒绝为侯玉峰解决问题,因长期睡眠不足,侯玉峰两只眼睛“越来越邪乎地发出热而乱的光”[6]237。80年代,市场经济实行,社会看似更加开放多元,但其实每个人都“被按照一种完整的关于力量与肉体的技术而小心地编织在社会秩序中”[10],论证着一个保证社会正常运行的包含着悖论的真理:没有个体自由的社会反而是自由的[11]150。
文中出现了3次“神经病”这一现代的“骂人术语”:一次是前文说到的女内科大夫因为提出合理质疑被传成神经病;一次是陈幺妹表达了对来学校演讲的国外作家的不满之后,被校领导称为“神经不正常”;第三次是医院主任陈莲生在公交车上睡着了,因为梦到病人出了状态说了梦话,口水打湿了买来的二手西装,和邻座的时髦女郎比起来,格外地不体面,被售票员称为“神经病”。当社会规范和纪律形成并启动,任何与其相左的行为都被认作失常,人的主体性被逐步消解,自我身份不通过道德或学识勾连,而更多靠消费能力和物质条件来彰显,不正常的到底是社会还是个人?“神经病”这种本身就是由于压抑导致的疾病或许就已给出了答案。
三、局部的身体反抗
随着不同身体空间的互相对立,个体的异化加剧,资本和市场经济利用身体空间的同时,也在生产着矛盾和对立,于是身体正式成了抵抗的场所。因为“商业主义和福利权利在成功诱使人们向它表示臣服时,它从来都不会兑现其美好生活的新世界”[11]138。正如爱德华·W·索亚所说,这种空间的生产“在表达和执行资产阶级利益,贯彻国家权力,包括性别控制和家庭生活的形成; 从这些社会进程中产生的空间形式也变成了被剥削阶级、受压迫的主体、被控制妇女反抗的焦点; 这些反抗的社团不时成为强大的社会运动,他们挑战空间结构意义并试图重组城市空间以支持新的功能、形式、利益、工程、反抗和梦想”[12]124。
在《病》中,身体的反抗恰好来自爱德华所提到的3个对象。第一次反抗来自被剥削阶级丁大爷,他拉着一车上好的棉花去收购站,一路都想着棉花能挣回多少钱,可到了收购站,发现工作人员对棉花质量等级的评定全靠收了对方多重的礼,于是丁大爷一把火把棉花烧了,烧完之后他心里想着自己没吃亏,他的便宜没被别人占去,心里踏实又痛快。无论是对这充满权力压迫和纪律规训的社会的不满,还是内心对性欲的压抑,都在这一把火中释放了出来。第二次反抗来自被控制的妇女丁小丽,和医学研究生丈夫过完新婚之夜后,她被怀疑不是处女而被起诉离婚。在医院接受各项检查后,显示她即使在新婚之夜后,处女膜依然完好,于是她从“淫妇”变成了“烈女”,丈夫想要和她重归于好,但丁小丽认识到他爱的只是一张处女膜,于是她成了要坚持离婚的一方。第三次是受压迫的主体侯玉峰终于不堪其扰和木匠打了起来,感受到鲜血从额头上流了出来,他感觉“他们家传了一辈又一辈的窝囊气,似乎都随着这血流出来了”[6]239。
他们开始去争取尊严以及与自身奉献相匹配的权利。在他们反抗的那瞬间,由文明压抑的不满引发了破坏欲的溢出,进攻型本能得到了暂时的满足。尽管这些反抗都是局部的,但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最终他们依然要承担棉花被烧的损失,离婚的坏名声,还有损伤的肉体,然后重新被编入严密的社会组织和秩序之中。但小的爆发毕竟能换来短暂的平静,更多其他的人,如学医7年并留美归来的但挣得还没服务员多的胡立川,被病逝家属打的女大夫,高学历却只能在实验室照顾小白鼠的小曹……他们只能装着满肚子的邪火,感受着内心的失衡,承受着无形的暴力,精疲力竭。
在消费主义无孔不入、社会风气急剧下滑、社会内部的黏合力持续减弱的年代,是否存在个体能得以安生的空间?作者给出了两个选项:太平间和澡堂,前者没有活人审视的眼光,后者可以脱下一切伪装的“面具”。这两个空间因为被建构出的身体空间的消失,得以回归本质上的肉体,而使人短暂性地恢复肉体本身原有的松弛感。
“当一切压抑似乎合理而又必要,以致让你感到承受不了,只有发疯才是唯一出路的时候,你可万万不能疯,你不需要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还需要你呢。”[6]272文中这句话直白地说出了当下人类的生存现状:世界需要人体的肉体和空间,保持压抑而不发疯,成了群体共同的基本生存法则。
四、身体与社会的隐喻
“一切语种里大部分涉及无生命的食物的表达方式都是用人体及其各部分以及用人的感觉和情欲的隐喻来形成的。”①维科在《新科学》中体现的一个观点是:人类在最初认知有限的情况下,只能根据自身唯一熟知的身体去衡量其他所有事物,所以身体成了社会的隐喻,而疾病则代表了社会的混乱和无序。张洁通过《病》这部短篇小说,想表达的一个很明显的主题就是:社会病了,生活在其中的人也都多多少少有病。
社会理论学家们把社会的秩序建立在4个维度的基础上:时间上人口的繁衍、空间上人口的约束、身体内部对欲望的限制、身体表面的空间再现[13]162。在《病》中的世界,这4个维度都处于紊乱无序的状态。人口繁衍和欲望限制问题上,“喂”在情欲的冲动下,和傻女人发生关系生下智力低下的女儿,并与之发生乱伦关系;上到大领导下到小职员根本不顾国家的计生政策,都在超生,新生人口的数量和质量都和预想中的秩序相背离。空间人口约束上,不同阶级和工种的人都挤进城市,人与人之间经济依赖性增强,这种肤浅的亲密关系反而引起了社会性的减弱,因为城市化和稠密的人口削弱了道德凝聚力和个体的尊严[13]179。作者安排木匠和医生这两个完全不同工种的人同居一室,他们之间不和谐的关系就以小见大地凸显了这一显著的社会问题。而在身体的空间再现上,自我的呈现和个体地位不再依赖阶级或等级的象征物,而是依赖以金钱为基础的风格和时尚,“城市空间成了以商业化时尚和生活方式为基础的互不相让、竞相呈现的大赛场”[13]184。在《病》中,接受教育多年、辛勤工作的医生教师等需要专业知识和技术的人群在物质上只能在温饱线上挣扎,在精神上也得不到本该有的社会尊重,始终无法实现自洽,而投身市场经济浪潮的人衣着光鲜,出手阔绰,金钱为其占据着各种优质社会资源。在社会政治和经济处于不稳定状态时,文中出现的所有知识分子一如既往地被赋予“无用”和“缺少灵活性”的标签。
张洁在80年代书写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说,虽然讽刺意味突出,荒谬感十足,她像恶毒的女巫似的拿着一把刀子,总找社会溃烂得最严重的地方扎下去,看着鲜血冒出来再予以哂笑。但作品的内在质地无一不是一片浓厚的自怜色彩,有时自怜于作为一名女性的艰辛,有时自怜于作为知识分子对社会颓势挽救的无力。说到底,她就是一个维护社会的纯净不得而在唱挽歌的人。
王蒙曾评价她说:她无法和现实生活和解,对社会的堕落和不满她做不到随波逐流,也做不到王朔式的自嘲自慰[14]。这段话形容张洁太贴切了,作为一名在共和国的庇护下成长成名的写作者,她不能忘记对社会的责任感,忽视不了生活在现代化社会的不适感,以及对这种不适感的充满怒意的表达欲。
苏珊·桑塔纳说:“现代疾病隐喻使一个健全社会的理想变得明确,它被类比为身体健康,该理想经常具有反政治的色彩,但同时又是对一种新的政治秩序的呼吁。”[15]张洁在《病》中貌似并无心呼吁理想的社会秩序,更多的是一种深切的失望。多条故事线以医院为中心辐射开,有病的不仅仅是住院部里的病人,连同负责医治别人的医生和整个医院系统都病态十足,根本没有治愈的可能性。更悲观的是,用后现代的身体理论来看,医院的存在本身就是“通过一种维修服务来剥夺人的自我应付能力,从而使人能更好地服务于工业系统”[12]128。这种病态,是人类迈向现代文明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没有退路,没有反抗可言,人们能做的,就是将自我收缩,提高自身对病态的耐受力,做一个秩序所认可的“正常人”。
五、结语
张洁是一位对现实社会状态保持着高度敏感的作家,也极善于从西方文学理论和作品中汲取营养,不断对过去的自己进行超越,因而在数十载的写作生涯中,她的创作过程有明显的分期。《病》这部作品之所以被认为是她跨进“写作更年期”阶段的标志,并不仅仅是因为她由审美走向了审丑,叙事模式由整体变成了碎片化,更多的是她审视现实的眼光有了新的层次感而且变得锐利,她看到了人的身体和心理的新空间,同时也为自己的文学领地开拓了新的空间。在这一阶段,她的作品外在虽然显示出了浓厚的现代主义荒谬感,但内在仍没有摆脱她从步入文坛就始终携带着的对现实社会深切关注的目光,关心着人类的命运与前途。她曾在散文中明确表示,因为自己是从普通人中走出来的,所以在写作当中总是想着中国的百姓。一位作家的变与不变,初心和韧性,在她身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20世纪70年代,“全球化”和“身体”成了政治文化领域的高频词,全球化的发展使得边界感消失,人类不得不重新回归到身体以便在纷繁复杂的后现代语境中找到可观察和思考的场所。在某种程度上,《病》作为转型之作,是张洁作为一个有社会担当和求变激情的作家对这股文化潮流的回应。
注释:
① 出自维科的《新科学》,转引自奥尼尔的《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