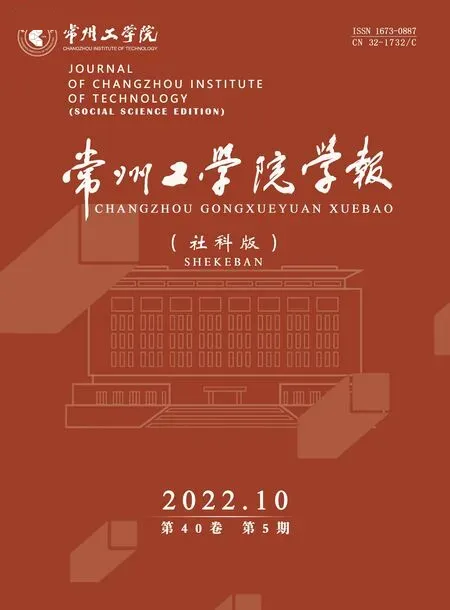道不尽的家庭情感与社会历史
——评阿摩司·奥兹的《乡村生活图景》
宋敏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阿摩司·奥兹是以色列最负盛名和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也是作品被译介到中国数量最多的以色列作家之一。他将关注点集中在神秘丰富的家庭生活,通过描绘当代以色列家庭的生活状况来表现以色列人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同时,他对家庭生活的描绘又能映现以色列的政治历史和社会风貌。因此,他的作品既因着眼于家庭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而显得细腻绵密,又因对社会历史的隐晦呈现而透露着一抹厚重。创作于2002年,2007年被译介到我国的长篇自传体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被视为最能体现奥兹创作风格的代表之作,而其创作于2007年,2016年才被译介到我国的《乡村生活图景》作为他继《爱与黑暗的故事》之后“最优秀的作品”,还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关注。《乡村生活图景》是一部短篇小说集,共收入《继承人》《亲属》等8个短篇小说。它延续了奥兹一贯的写作风格,表现出新鲜的内容与形式。对这部作品作深入的研究,有利于把握奥兹的创作特色,体味以色列文学的特质。
一、对家庭情感的持续关注
奥兹将笔触深入神秘丰富的家庭生活中,淋漓尽致地展现犹太家庭生活中的问题和矛盾,展现个人情感上的困惑以及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具有普遍性意义。他笔下的家庭生活往往并不尽如人意,正如他本人对自己作品主题的概括,“假如你一定要我用一个词形容我书中所有的故事,我会说:家庭。要是你允许我用两个词形容,我会说:不幸的家庭”[1]1。从《我的米海尔》中的汉娜与米海尔,到《了解女人》中的约珥与伊芙瑞娅,再到《爱与黑暗的故事》中的范妮娅与阿里耶,爱情逐渐被琐碎的日常生活冲淡,夫妻之间因缺乏沟通交流而貌合神离,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乡村生活图景》延续了奥兹对家庭生活和个人情感的书写,他所描写的依旧是不幸的家庭和难以实现的情感,但与前作相比,《乡村生活图景》中还增添了温暖和光明的底色。
奥兹选择继续言说爱情这一永恒话题,但他不是要表现充满隔阂与矛盾的情人或夫妻关系,而是致力于表现丰富独特的个体情感状态。在《乡村生活图景》中,作者塑造了几个执着的爱的追寻者形象,他们受家庭伦理或道德规约约束,爱而不得,不得不悲凉收场。《亲属》讲述的是医生吉莉·斯提纳等待外甥吉戴恩·盖特来访却未等到的故事。她对外甥的爱近乎偏执,已然超越了亲情的界限。吉莉·斯提纳在公交汽车站等待外甥未果,却不愿相信外甥没来的事实,她先是猜测他可能在大巴车后座上睡着了,于是便在干冷的冬日执拗地步行前往司机米尔金家中寻觅。确认外甥没有被锁在大巴车内之后,她又猜想外甥可能上错了车,但已经设法抵达并坐在前门台阶上等她。最后,一切猜想都被现实推翻,但她还是不死心地等待着,备好晚饭并精心为外甥布置了房间。她突然想到外甥没来可能是因为有女朋友了,“这一想法让她内心充满近乎难以忍受的痛苦。仿佛她已经被完全掏空,只有枯萎的空壳依然作痛”[1]40。实际上,外甥并没有答应她一定会来,吉莉·斯提纳对外甥的寻找只是为着一点可能性。她对外甥的寻找过程实际上也是她对爱情的寻觅过程,寻找的无果预示着这一不符合家庭伦理的感情注定没有结果。《亲属》体现了奥兹对处于边缘地带的个体情感的关注和思考。
《陌路》讲述的也是爱而不得的故事,呈现的则是懵懂少年面对年龄鸿沟依然主动出击的爱情渴求。考比·爱兹拉,一个17岁的少年,不可救药地爱上了30多岁的离婚女子阿达·达瓦什,他绞尽脑汁地思考合适的谈论话题,专门等她从邮局下班然后一路陪她走到图书馆,积极制造二人相处的机会。阿达·达瓦什猜到了考比的心意,以非常谨慎的态度回应他的感情,以图在不误导他的同时又能不伤害他。因此,面对考比的性冲动,她没有激烈地苛责,反而采取一种包容的态度,这让考比感到懊悔和羞愧。考比深刻地认识到:“我的所作所为什么也改变不了,因为结果从开始就已经注定。”[1]167奥兹写出了一个青春期男孩面对不合时宜的爱情时的纠结与欲望,以及他在主动靠近之后找到的最终答案——不可能。《陌路》是奥兹对如何表达和释放难以实现的情感所作出的回答。
《乡村生活图景》还表现了犹太家庭在遭受重大情感创伤后主动自我疗愈的积极心态。《歌》中的主人公亚伯拉罕和达莉娅夫妇经历丧子之痛后,没有沉湎于悲伤,一蹶不振,而是通过积极参与和组织各类活动来自我疗愈。独子亚尼夫自杀后,夫妻二人给唱歌的学生设立了一个小型奖学金,因为亚尼夫有时在村合唱队唱歌,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来释放对儿子的思念之情。母亲达莉娅努力让自己的生活充实起来,除了参加图书馆委员会、冥想团体、合唱晚会的活动之外,她还参加学习日活动、会议、讲座等。父亲亚伯拉罕每天下班回家后则通过在花园中劳作,喂猫和金鱼,看书,听音乐以及长途漫步等方式来排遣内心的忧思。《歌》一文描绘的主要场景是亚伯拉罕和达莉娅夫妇举办的合唱晚会,同样经历丧子之痛的以色列诗人纳坦·约纳坦创作的富有感伤色彩的诗歌《河岸有时在思念一条河》《歌声再度唱起,岁月再次哭泣》成为他们寄托对儿子思念之情的载体,《世上的一切转瞬即逝》《风儿吹拂的晚上》等合唱曲目在忧伤之外显露出一丝从容与豁达。
此外,奥兹还敏锐地捕捉到女性追求解放和实现个人价值这一时代主题,着意表现女性挣脱家庭牢笼束缚时的坚决和果断。《等待》中的娜娃经历了对婚姻的失望后选择决绝地挣脱家庭藩篱,这对犹太女性而言尤其难能可贵。在犹太传统的社会分工之中,女性应以家庭为重,履行好贤妻良母的责任。娜娃每天中午下班后会准备好午餐等丈夫本尼回家,平时还担负着陪伴和教导女儿的重任。在多数情况下,本尼与娜娃都相敬如宾,但二人早已貌合神离,娜娃怨恨本尼将政治公务带回家中,本尼也不喜欢娜娃对雕塑的艺术热情。实际上,他们的感情在恋爱时就已出现裂痕,当娜娃意外怀孕不得不终止妊娠时,本尼并没有对她表示应有的关心,“他在街对面的一家咖啡馆等她。他看了两份报纸,甚至连体育版增刊都看了”[1]133-134。那时的冷漠与无情就已预示了二人最终分开的结局。娜娃在做好一名贤妻良母的同时,还积极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不顾丈夫反对发展个人兴趣爱好,她所雕塑的怪兽以及断了鼻梁骨的拳击手也能映射出她内心深处的反抗精神。因此,当她对婚姻和家庭生活失望以后,她选择以离开的方式进行突围。“娜娃的出走让‘等待’的相处模式发生了对调,妻子不再等待丈夫回家吃饭,丈夫开始体味等待妻子归来的滋味。”[2]奥兹写出了犹太女性在面对家庭牢笼之时的勇敢与决绝,他“通过描述处于边缘地位的现代犹太女性的生存感受表达了自己对犹太人个体生命体验与群体生存状况的思考”[3]。
二、对传统乡村裂变的呈现
《乡村生活图景》以虚构的小村庄特里宜兰为故事背景展开叙述,展现了这个村庄的发展变迁历程以及村中人的生存状态,将之放在现代化的社会背景之下考量,奥兹的书写就有了反思乡村发展模式的意义。作者曾提到:“我的新作品《乡村生活图景》实际上基于很多年前我做的一个梦。梦中,我当时正走过以色列最古老的犹太村庄之一……这本书应该是关于失去和得到、搜索和藏匿。”[4]《乡村生活图景》呈现出以色列传统乡村的裂变,这不仅指乡村发展方式的变化,还包括人在现代化裹挟之下的异变。
《乡村生活图景》将现代化浪潮冲击之下以色列传统乡村的内部裂变呈现了出来,表达了作者对美好乡村逝去的惋惜之情,同时也写出了乡村发展变迁的必然性。特里宜兰是一个拥有百年历史的先驱者村庄,风景优美,树木繁茂,散落着块块农田。《挖掘》中的阿拉伯学生阿迪勒十分喜爱特里宜兰,他认为“这里是如此宁静。比我们村宁静多了。我们村已经开发得不再像个村庄了,而是一个小镇,到处是商店、加油站和满是灰尘的停车场”[1]63。然而,古老的特里宜兰也逃脱不了城市经济的侵袭,不少农田被改为商店,农庄建筑被改建为艺术画廊。周末城里的游客都会开着轿车鱼贯而入,城里的富人还到特里宜兰购买老式单层住宅,将其夷为平地后建起别墅。现代文明使得乡村的传统建筑逐渐消失,传统生活方式也逐渐解体。然而,奥兹在表现城市文明对乡村的冲击之外,也书写了乡村现代化发展的必然性。《乡村生活图景》的不少篇章都展现了特里宜兰颓败、破落的面貌,比如《继承人》《等待》《挖掘》《迷失》等都描写过几近废弃的场院。在此意义上,都市发展模式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改变乡村凋敝和落后的面貌,为乡村发展注入新动力。
奥兹所描写的乡村样态的变化具有普遍性意义,他笔下以农耕为主的乡村逐渐被城市化侵袭而失去其本来面目,这与当下中国乡村的发展变迁形成了某种对应关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不乏对城市文明入侵乡村生态的描写,如沈从文的《长河》、贾平凹的《秦腔》、梁鸿的《中国在梁庄》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在乡村生态遭到破坏的同时,乡村中人的精神生态往往也随着现代文明的侵袭而逐渐陷落,奥兹的《乡村生活图景》将人在现代化浪潮冲击之下的异变生动地展现了出来。
人的异变主要表现为在经济利益面前的唯利是图和人性的脆弱。《继承人》讲述的是律师沃尔夫·马夫茨尔试图说服阿里耶·蔡尔尼克将母亲的老宅改建为疗养院的故事。马夫茨尔出场的形象饶有趣味:“他淡黄色的头发稀稀拉拉的,一脖子赘肉,两只水汪汪的眼睛转来转去,似乎在寻觅着什么,黑猩猩般的长臂下垂着。”[1]4这段肖像描写已然透露出作者对他的鄙夷和讽刺态度。面对阿里耶的一再推辞,马夫茨尔不仅没有离开,反而紧随阿里耶进门,还暧昧地运用“我们”一词将自己设定为阿里耶的亲戚和合作伙伴,甚至将自己加入了老宅房主罗萨莉亚监护人的行列。“也许证明我们是她的法定监护人会更容易些?那样,我们无须征得她的同意。”[1]13阿里耶犹豫之后选择与马夫茨尔一同躺在老母亲身边则表示他同意了这位陌生人的建议。如此,年迈体弱的罗萨莉亚就在陌生人马夫茨尔和儿子阿里耶的共谋之下丧失了其房产的所有权。小说的希伯来文题目“继承人”使用的是复数形式,因此,尽管小说并没有明确交代阿里耶的态度,但读者能从题目中预见故事的结局。阿里耶原先挣扎在情与理的矛盾之中,一方面担心母亲的身体状况,另一方面又期待着母亲离世后的种种好处,但他最终还是接受了马夫茨尔的提议。与其说是马夫茨尔说服了他,不如说是利益的诱惑和内心的欲望驱使他做出了这样的选择。阿里耶这个人物形象生动地展现出了经济利益和欲望面前人性的复杂一面。
《迷失》中的主人公“我”是一名房地产经纪商,意图购买最后一座由基奠者建造的老宅“废墟”,将其拆除后建造现代别墅从中获利。“我”喜欢“废墟”这座建筑,很清楚它的文化和历史价值,但“我”也认为重新修复这座老宅已无太大意义,因此,即使听到“废墟”的主人想要留存它的原始面貌,即使对拆毁它也心存遗憾,“我”还是下定决心要将其夷为平地。尽管小说以“我”被雅德娜关在“废墟”的地窖中沉睡结束,但可以预见的是,“废墟”终究还是逃不过被拆毁的命运。在奥兹的小说中,房地产代理人仿佛成为了破坏乡村生态者的代名词,他们拆毁传统老宅建造现代别墅映射的是现代物质观念对乡村原始生态的侵袭。在此意义上,奥兹在《乡村生活图景》中所描绘的小村庄以及村中人就具有了代表性意义,它们“象征着在以色列的城市化进程中,当年拓荒者所追求的人生理想和拜金主义、追求物质享受等现代观念发生矛盾”[5]。
三、对社会历史的隐喻和象征
奥兹在《乡村生活图景》中虽然将笔墨集中在描写村庄中的人与事中,但能在日常细微的描写中映射出对国家、社会、历史的隐喻和象征。奥兹在对乡村日常生活的书写中渗透了以色列人对本国政治的认识,以此传达他们在特定环境下的生活态度。奥兹还关注到以色列人对本国历史的遗忘,表现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式微,同时也通过描绘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相处细节挖掘潜藏在人们心中的民族记忆。此外,奥兹还在《乡村生活图景》中用极富荒诞和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笔法写出了以色列的乡村现实。
《乡村生活图景》专注日常书写,并不追求宏大叙事,因此小说并没有对政治背景作清楚的交代,但却在细微描写之中营造了浓厚的政治氛围。《歌》描绘的是列文夫妇在家中举办合唱晚会的情景,其中的政治氛围营造是通过合唱晚会中大家的交谈和争论表现出来的,如收音机广播对战况的报道。大家对时事政治进行争论反映了他们对未知的恐惧与迷茫,但是大家仍能和谐相处,用歌唱代替政治争论。这群普通人无法左右政治局势,因此他们选择暂时遗忘,以一种积极乐观的心态去面对生活、享受生活。《歌》所传达的实际上是奥兹对乱世中的人们如何面对生活的看法与态度。
每个人心中都存留着特定时段内关于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记忆,如果这段记忆为很多人共有,则可以作为集体记忆。《乡村生活图景》写出了犹太人对战乱这一集体记忆的回避和淡忘。《迷失》中的作家爱勒达德·鲁宾多创作了大屠杀题材的小说,风格沉重忧郁。然而时过境迁,他的作品被逐渐淡忘甚至忽视,人们更喜欢阅读报纸、政治书和侦探小说,就连他的女儿也无法忍受其作品沉重压抑的风格。因此,鲁宾去世后,他的笔记、卡片索引等创作资料通通被送进了作家协会档案馆。这一现象的背后,是以色列人对大屠杀记忆的逃避和刻意遗忘,他们不愿再触碰那段充满伤痛的记忆。此外,对以色列建国有重要贡献的基奠者也逐渐被忘却,基奠者街前,纪念在战斗中遇害的基奠者的雕塑周围长满黄草,就连基奠者最初建造的房屋也被一一拆毁。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历史中关于战乱与痛苦的集体记忆的遗忘或许是一种必然,而这正如作者奥兹所说,“生活有巨大的惯性,无论经历了大屠杀还是战乱,地震或者海啸,人都要过日子”[6]。
在以色列人的民族记忆中,阿拉伯人始终是一个敏感的存在。以色列建国以前,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发生过数次流血冲突,这种冲突直到以色列建国后还在持续。《挖掘》通过佩萨赫对阿拉伯学生阿迪勒的态度表现出“犹太复国主义者占领阿拉伯人土地、杀戮阿拉伯人的忏悔心理及焦虑情绪”[7]。佩萨赫是犹太复国主义党内颇具影响力的人物,他晚年与女儿拉海尔以及阿拉伯学生阿迪勒居住在一起,半夜时经常听到奇怪的敲击声、抓挠声和挖掘声。考虑到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矛盾冲突,佩萨赫怀疑阿迪勒是个反犹主义者,并怀疑夜晚的挖掘声是由他发出的,为的是抢夺回属于阿拉伯人的土地。他深深地意识到:“他们岂能不恨我们呢?我要是处在他们的位置,也会恨我们……你要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来观察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只配得到憎恨和蔑视。也许还会得到一点同情。但是那同情不会来自阿拉伯人。阿拉伯人自己就需要世界上所有的同情。”[1]65-66佩萨赫这位犹太复国主义者深刻地认识到阿以冲突的核心问题——土地所有权,阿迪勒这位阿拉伯人的到来引发了佩萨赫的恐惧与焦虑情绪,只通过挖掘声就将他潜意识中对土地所有权的焦虑和对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民族仇恨的忏悔激发了出来。奥兹倾向于“把笔触放到普通人的身上,以以色列普通人的存在状态,来折射出整个社会、国家、民族和人性的状态”[8]。作者这种一贯的创作风格在《挖掘》中同样也得到生动的展现。莫言曾对奥兹的写作姿态赞赏不已,他表示,奥兹“没有站在犹太人的民族观点和利益上来写作,没有为犹太人的不幸而向全社会发出一种控诉。我觉得他站在高于犹太人的人类的角度来写作”[9]。
《彼时一个遥远的地方》在《乡村生活图景》的8个篇章中属于特殊的存在。前7个篇章都是同一时间发生在同一个村庄且彼此有联系的故事,而到了末篇《彼时一个遥远的地方》,作者突然变换叙事手法,运用极为荒诞、具有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笔法,呈现了一个不知名村庄地狱般的图景,仿佛是对特里宜兰村庄的异托邦隐喻。异托邦是“空间的两极,一方面它创造出一个虚幻的空间,另一方面,这个虚幻的空间却揭示出真实的空间”[10]。《彼时一个遥远的村庄》正是以虚幻的描写表现了特里宜兰村庄的某种真实。在这篇小说中,村子里弥漫着腐烂的味道,沼泽地里飘散着毒气,霉菌腐蚀着墙壁,蚊虫纷飞,就连土壤也汩汩冒泡,到处都是荒凉与衰败的景象。村子里的人们很多都有身体缺陷,而这源于近亲交媾的荒淫无道和道德风气的堕落。反观其他篇章中描绘的特里宜兰村庄,花园逐渐变成无人打理的废墟,屋舍和农田逐渐被侵蚀,村子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留下的尽是鳏寡孤独,与《彼时一个遥远的村庄》中那个荒凉衰败的村庄如出一辙。面对村庄发展,特里宜兰村的人们流露出的不是欢快,而是无奈与担忧,同时现代化变革也导致了人们对利益的追逐和对道德的忽视,这与《彼时一个遥远的村庄》中人们的道德堕落具有相似性。在此意义上,《乡村生活图景》可以说是奥兹为以色列传统社会的逝去所吟唱的一曲挽歌。
四、结语
奥兹的《乡村生活图景》继承了其一贯的创作风格,有大量关于家庭的描画,但其中又穿插着对社会历史的表现,由此,家庭的悲欢离合以及社会历史的复杂、沉重在他冷峻、细腻的笔触中缓缓流淌出来。《乡村生活图景》生动地呈现出一个当代犹太作家的细腻情感与理性思考,作者将多个层面的问题融入对日常生活的描述之中,在对特里宜兰这个虚构村庄的叙述中构筑了完整的世界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