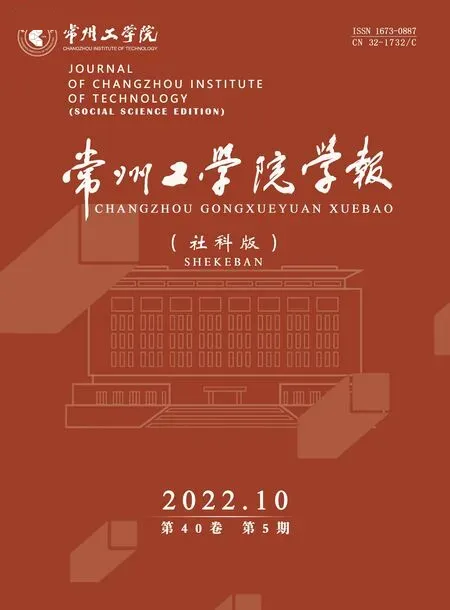歇后语中微型喜剧艺术的建构
梁德群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喜剧作为戏剧的一种类型,常被大家解作笑剧或笑片,同时,它也能作为一种要素,依托其他艺术存在机制,隐秘地存在于人民的生活实践中,其中较为典型的是歇后语。歇后语主要由“引语+停顿+说明语”组成,短小精简却蕴含强劲的艺术生命力。歇后语以其戏剧性的艺术手段和戏谑性的语言风格,包蕴着典型的喜剧审美特性。彭吉象曾言:“人们常把剧本、演员、观众称作戏剧艺术的三要素。”[1]207因此,本文拟从喜剧视域出发,观照歇后语中的剧本、演员和观众三要素,解读歇后语的喜剧艺术魅力和文化审美意蕴。
一、剧本
许肇本在《新编歇后语大全》中曾言:“歇后语也是一种独特的微型文学或称‘一句话的文学’。它以特殊的语言形式,显示修辞的审美特色,它是以精短的语言结构,生动形象的(包括现实的和历史的、社会生活的和自然界形态的)物质材料作为基础创作出来的文学样式。”[2]歇后语作为一种微型文学,虽短小精简,但其内容风格符合喜剧剧本的创作要求,情节幽默,人物情境妙趣横生,角色动作浮夸可笑,具有典型的喜剧风格。
(一)戏剧布局
亚里士多德认为,在喜剧艺术中,“一桩不可能发生而可能成为可信的事,比一桩可能发生而不能成为可信的事更为可取”,“因为可能有许多事违反可能律而发生”[3]。对于喜剧作品来说,在情节选材上,无论是可能性还是必然性,都是对表现对象内在必然性的揭示。内在的必然性和可能性,都比已然发生的事实现象重要得多。歇后语在情节安排中,依据现实生活进行想象,将可能性与必然性的戏剧布局应用自如。
所谓可能性与必然性交织缠绕,即戏剧在情节安排上多以事情发展过程展开,但为使审美主体或审美对象获取别样的审美体验,会让具有可能性或偶然性的情节参与进来,它们共同构筑云谲波诡、别开生面的戏剧艺术。歇后语在情节安排上呈现3种布局,在这3种布局中,歇后语会将现实与虚拟交织,将可能与必然融合,在现实存在的生活中穿插虚拟幻想的可能性题材,使戏剧情节不蔓不枝,愈加有趣。
一是先夸张后揭示。这类歇后语的引语大多安排了夸张性的情节,再通过后面的说明语揭示出来,使得欣赏主体先是惊愕,惊叹过后又哗然大笑,更显歇后语整体布局的喜剧化色彩。例如:
(1)80岁老头嘴叼90斤烟袋——口劲不小
(2)盘子里面扎猛子——不知深浅
(3)迫击炮打蚊子——小题大做
例(1)中,80岁老头可以叼烟袋,但是要叼起90斤烟袋,太过夸张。例(2)中,日常生活中的盘子主要用来盛装食物或其他物品,如果人要想在里面扎猛子,难以实现。例(3)中的迫击炮是军事武器,主要用来歼灭有生力量或清除大型障碍物,用来攻打体积微小的蚊子,显然不可行。
二是先逆境再反转。这类歇后语的引语会先营造悲惨氛围,然后说明语借助谐音的效果,以戏剧化的反转来展现好转的境况,于意料之外更添滑稽风趣。例如:
(4)叫花子住庙——穷人落到佛(福)窝里了
(5)公鸡掉到米囤里——走食(时)运了
(6)汉朝的苏武——久居番邦(酒足饭饱)
叫花子大多以凄惨落魄的形象出现,他们居无定所,有时只能住到庙中,例(4)中后半部分借“佛”与“福”近音相谐,指出叫花子的落魄境况转变。例(5)中,公鸡掉进囤里被困住本是一件坏事,但是它掉进了米囤,米囤中储藏了大量的粮食,它即使长时间困在米囤里,也不会饿死。例(6)中,苏武奉命以中郎将持节出使匈奴,后被长久扣留在番邦,于北海牧羊,饥寒交加,歇后语借谐音将他“久居番邦”的苦难经历转变成“酒足饭饱”的美好生活,令人不可思议,惊叹连连。
三是先设悬念后扑空。这类歇后语的引语部分常以难以实现的事件来设置悬念,引人遐想,然后在说明语部分再将这种矛盾冲突下的结果揭示出来,令人啼笑皆非。例如:
(7)河里捞月亮——白费劲
(8)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心高妄想
(9)老鼠掉到饭甑里——焖(闷)死了
例(7)中,“白费劲”直接将不可能实现的结果揭示出来。例(8)中,丑陋的癞蛤蟆想要吃天空中优雅飞翔的白天鹅,后半部分的“心高妄想”指明其期望破灭。例(9)中,老鼠掉到饭甑中,本以为可以饱腹,却被饭甑焖死了。这些都凸显了预期动机与现实效果的悖反,在矛盾冲突中形成了戏谑的艺术效果。
(二)戏剧环境
歇后语营造戏剧环境的关键,是处理好纪实性和假定性这一对矛盾。所谓纪实性,就是以真实的社会生活为基础,追求还原现实、贴近自然。法国著名哲学家丹纳曾说:“似乎艺术家应当全神贯注地看着现实世界,才能尽量逼真地模仿,而整个艺术就在于正确与完全的模仿。”[4]歇后语中对现实世界的摹仿与再现就是戏剧纪实性的最好体现。所谓假定性,就是以虚假作为存在状态与外在表现,依托人们的联想与想象,营造超脱的虚幻氛围。歇后语创作者不仅要从生活实践中发掘歇后语,也需要依靠想象编造故事,融纪实性与虚拟性于一体,使得故事在接近生活的同时,充满想象性和象征性。例如:
(10)屎蜣螂钻进驴槽里——假充大黑豆
(11)做梦吃星星——永远没那一天
(12)棺材里伸手——死要钱
(13)小巴狗咬月亮——不知高低
例(10)中,“屎蜣螂钻进驴槽里”是现实社会生活中真实存在的现象,但说明语给予它虚拟的感情色彩,将“屎蜣螂”放在“假冒大黑豆”的语义环境中,喜剧画面油然而生。例(11)中,“做梦”是生活常事,但“吃星星”这一行为十分虚幻,因而“做梦吃星星——永远没那一天”戏剧氛围跌宕起伏。例(12)和例(13)中“棺材里伸手”“小巴狗咬月亮”也是借虚与实、真与假来表达戏谑性意图。歇后语能将现实与想象巧妙衔接,在情节的推动下,当真实与虚幻相互转换时,如拙劣的手段可以冒充成高明的技法,丑恶的私欲能够假装成无私的情愫,幼稚的想法可以充当智慧的哲思,喜剧性便产生。歇后语凭借引语和说明语的前呼后应,逐步揭开面纱,高明变成了拙劣,无私变成了丑恶,智慧变成了愚蠢。
纪实性和假定性手法的运用,浓缩了现实生活的点点滴滴,打破了现实与虚拟的界限制约,拓宽了戏剧环境的展现界域。而这种对生活的提炼和对想象的扩展,也以时间颠倒和时空错位的艺术手法来增强戏剧环境的艺术效果,冲击审美主体的心灵。例如:
(14)十二月卖扇子——不识时务
(15)米盆里洗澡——糊涂得很
(16)睡梦里作演讲——胡说八道
歇后语的引语常观照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十二月”与“卖扇子”的时间完全相悖,“米盆”与“洗澡”的场所不同,“作演讲”与“睡觉”场合也不同。歇后语正是通过时间颠倒、空间错位的假定情境,变场景于须臾之间,后面的说明语揭示结果,悬念愈大,嘲弄讽刺的意味愈强烈。
歇后语通过颇具可能性与必然性的戏剧布局、具有纪实性与假定性的戏剧环境异化审美对象,制造矛盾与冲突,造成情节上的不协调,从而引人发笑。歇后语将现实与理想、真实与想象直接展现在人们眼前,把可能性与必然性进行融合,把纪实性与假定性进行对比,给予人们心理震撼。
二、演员
彭吉象曾言:“戏剧艺术作为二度创作的艺术,包括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作为舞台表演基础的戏剧文学和演员创造舞台形象的表演艺术。”[1]205喜剧演员作为审美主体,将作家的喜剧意识对象化,将客观现实意象化,将酸甜苦辣、褒贬爱恨展现出来。歇后语是一种微型喜剧,其创作主体将审美理想渗透其中。歇后语的审美主体具有以下特点。
(一)多变性与低俗性
审美主体具有多变性与低俗性。喜剧作为一门舞台表演艺术,多变性是其突出的审美特性。所谓多变性,就是审美主体依据创作主体规定的情境和特定的情感进行二度创作,运用语言、动作创造不同形象。歇后语作为微型喜剧,亦能体现象征性审美主体的多变性,同一角色不拘于单一的形象,而是在多变的形象中呈现喜剧性的艺术画面。例如:
(17)老虎吃蚊子——枉张空口
(18)老虎打架——劝不得
(19)老虎戴数珠——假充善人
(20)老虎念经——假正经
例(17)到例(20),审美主体皆为“老虎”,但在多变的语境中,老虎本体带有了褒义、贬义、中性等感情色彩,森林之王老虎形象也转变为与人们以往经验所不同的“吃蚊子的老虎”“打架的老虎”“戴数珠的老虎”“念经的老虎”。这几则歇后语造就了性格各异、栩栩如生的审美形象。在歇后语中,审美主体的表演性艺术达到了自我与角色、生活与艺术、现实与想象的融合。可以说,多变性在一定程度上浓缩了喜剧的故事情节,冲破了喜剧的人物限制,给予喜剧的审美主体以新鲜多变的活力。
此外,喜剧审美主体作为模仿对象,多带有“较差”“丑”“可笑”等低俗化特性。亚里士多德认为:“喜剧的摹仿对象是比一般人较差的人物。所谓‘较差’,并非指一般意义的‘坏’,而是指具有丑的一种形式,即可笑性(或滑稽)。可笑的东西是一种对旁人无伤,不至引起痛感的丑陋或乖讹。……喜剧人物是‘较差’而不是坏,‘丑’而不有害旁人,‘可笑’而不引起痛感。”[5]11歇后语中的审美主体大多出现在引语中,包括人物、动物、植物、器物等,它们也有低俗和可笑的特性,如“矮人”“瞎子”“歪嘴和尚”“蛤蟆”“猢狲”“懒驴”“屁股”“狗屎”等等。因为“中国人一向认为利用这类亵渎性语言骂人、羞辱对方最能毁坏对方的心灵和肉体。所以人们在骂架时常使用这类不堪入耳的字眼发动攻击”[6]。所以绝大多数歇后语都是以轻蔑、嘲讽等意味来谐谑、嘲笑他人,在引人发笑的同时显露出强烈的讽刺意味,予人笑里藏刀、绵里藏针之感。此外,歇后语和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充满朴实浓郁的生活气息,并富有浓烈的口语色彩,如“棒槌”“蚕姑姑”“尥蹶子”“转圈圈”“粪叉子”等。歇后语低俗化的艺术魅力,体现出强劲的喜剧艺术生命力和深厚的社会基础。
(二)夸张性与荒诞性
审美主体的动作具有夸张性与荒诞性的特点。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认为戏剧演员通过动作来模仿人的行动,再现行动中的人。在戏剧演出中,演员凭借动作表演来传情达意是戏剧艺术的基本手段。戏剧动作在戏剧中体现人物真实可感的情感,是情节矛盾冲突的导火索,体现了创造主体、审美主体以及欣赏主体对人物角色和剧本本身的诠释。歇后语中出现的动作具有鲜明的夸张性和荒诞性,富有独特的喜剧意蕴。例如:
(21)攀着根铁丝当梯子——硬撑(逞)能
(22)火柴盒做棺材——盛(成)不了人
(23)一顿能吃3升米——肚(度)量大
例(21)中,梯子是帮助别人攀爬高处的工具,而用一根铁丝来做梯子太过夸张。例(22)中,把细小的火柴盒当作棺材拿来装人,夸张至极。例(23)中的人一顿就能吃3升米,这是对人物的食量进行夸张。这些歇后语的人物动作大多是对人民生活行为的模仿,它与戏剧情境、矛盾冲突和情感交流等元素结合,共同揭示人物动作的夸张性特点。总之,歇后语中夸张的动作可帮助寻找剧情的发展线索,预示剧情的发展轨迹,揭示戏谑性的喜剧思想。
荒诞性是喜剧动作的重要特征,而歇后语的动作就糅入了荒诞性成分。在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相互牵制的矛盾斗争过程中,歇后语以视觉反差、经验相悖等审美手段营造意料之外的荒诞性喜剧艺术效果。例如:
(24)耗子给猫捋胡子——溜须不要命
(25)獾狼下耗子——一辈儿不如一辈儿
(26)黄鼠狼看鸡——越看越稀
“耗子”与“猫”,“獾狼”与“耗子”,“黄鼠狼”与“鸡”在歇后语的引语中被安排在一起,产生斗争的火花,这些动作在后面的说明语的揭示下,更显荒诞讽刺意味。
在审美过程中,演员做出了夸张性与荒诞性动作,以对比的潜在形式交代了内在联系。“戏剧表现对象和表现者本身的内在对比性,决定了戏剧本身的内在对比性。这还不仅仅是因为戏剧来自于表现对象和表现者,更重要的是,只有内在对比才会产生戏剧意味。”[5]275这种“内在对比性”鲜明地体现了夸张性和荒诞性,它不失为一种使歇后语矛盾化、反差化、戏剧化的喜剧技巧,使得歇后语富有喜剧幽默。
三、观众
喜剧不能离开观众而存在,观众作为欣赏主体,其接受程度和反应是一出喜剧演出的关键。“如西塞罗所说,喜剧是一面反映生活的镜子,但照亚里斯多德的原意来说,则是对公共的或私人的、能使人高兴愉悦的事件的摹仿。”[5]96诚然,喜剧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是对人性恶习的讽刺,它借幽默使人弃恶从善、扬长避短。歇后语同喜剧较为相似,它主要是使欣赏主体以诙谐幽默的方式理解言外之义,进而幡然醒悟。歇后语之所以能逗乐观众,是因为它本身具备展演性,它将创作主体、审美主体和欣赏主体裹挟于紧张有趣的互动之中,使观众在喜剧化、娱乐化的气氛中,实现了从个人到集体、从生活到艺术的超越与升华。观众在欣赏歇后语后出现的笑就是喜剧意识的直观化显现, 而判别歇后语是否具有喜剧性的关键性因素就是反响热烈与否。
(一)雅俗共赏
歇后语作为游艺民俗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十分注重个人享受与自我满足的紧密结合。“游艺民俗不仅是区域社会内权力系统、评价机制、群体心理等的形象载体,而且以其强大的历史惯性与精神张力,在社区文化建设中担当了某种动力源的作用。”[7]游艺民俗背后反映的是人们的群体意识,人们通过民间信仰形成共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歇后语的出现,就是要打破人们盲目满足于低层次的享受而放弃思想进步的僵局,以辛辣的语言提升人们的思想层次。这就决定了歇后语不是精英艺术,而是口口相传、雅俗共赏的大众艺术。
歇后语产生于民间,不仅具有民俗性,也颇具风雅。歇后语向来与民间信仰、生活节庆、人生仪礼等有着密切联系,渗透到民间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也带有广泛的群体参与性,故能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民间信仰活动的产生与存在促进了歇后语的发展,歇后语常会借助通俗易懂的比喻、拟人、夸张等修辞手法讽刺批判一些现象,因此不管是文人墨客还是乡间农夫,都能领略歇后语背后所隐含的妙义与谐趣。此外,歇后语中大量出现的幽默性题材,皆来源于生活。歇后语看似平平无奇,实则大有文章,它以朴实自然见长,往往通过前后两部分的引注关系来表意,具有风雅有趣的艺术风格,因此古今文人墨客在文学著作中多次引用歇后语。如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曾巧妙地运用了大量的歇后语。孔子也曾提出“兴观群怨”说,作为民俗艺术的歇后语就是“群”的生动体现。歇后语不同于凸显个体精神的精英文化,它营造了公共领域中最容易引起共鸣的以喜剧风格为主的文化氛围,达到了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
(二)喜中有泪
欣赏主体在解读和欣赏歇后语时,多是在嬉笑之后进行思忖并接受规劝,而喜剧的目的正是这种自我超越的实现,人在思忖中保持头脑清醒与精神自由。人们在欣赏歇后语时,有的可以直接理解其义,有的则需要通过想象、联想等多种心理活动来领悟题中之义。
柏拉图在《斐利布斯篇》中言:“就是看喜剧时心里也是悲喜交集”,“照这样看,我们笑朋友的愚蠢时,快感是和妒忌相联的。我们已承认妒忌在心理上是一种痛感,然则拿朋友的愚蠢作笑柄时,我们一方面有妒忌所伴的痛感,一方面也有笑所伴的快感了”[8]。这种放声大笑的狂欢背后是严肃端庄的悲泪。“可笑、有趣是喜剧的艺术特征而不是喜剧的全部目的。当人们一旦从笑声中获取任何社会性收益的时候,这种笑声里就难免包藏着对丑恶事物的些许刺激,闪动着几根使有些人产生痛感的芒刺。”[5]12歇后语常通过字面取巧的文字游戏来获得一种“倾向的诙谐”,当戏谑嘲讽、中伤轻视这些隐意识的欲望得到满足时,人们会产生同情心或伤感。歇后语引人发笑的背后,是欣赏主体对愚笨、丑恶、低浅的摆脱与超越,对情趣、理想和价值的向往与追寻。
歇后语反映了人们对丑陋的不屑与对理想的渴求和欣赏主体对自然、社会与人生问题的深沉叩问。如“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石灰点眼——自找难看”“竹竿勾月亮——差得远”等等,这些歇后语不只是描绘出了五彩斑斓、有趣可笑的世俗生活,更是在探讨世俗人性,明晰人生哲理。歇后语将一般喜剧意义上的好与坏、美与丑消解,滑稽却悲痛,讽刺且同情,营造一种喜中有泪、悲喜交加的审美效果。
四、结语
中国人喜剧理论的形成时间相比西方喜剧虽然稍晚,但是中国人拥有自己独特的幽默形式,歇后语正是中国人喜剧意识的生动体现。喜剧最直接的目的就是引人发笑,它是为“笑”服务的,歇后语能从剧本、演员、观众3个维度与喜剧的旨趣相呼应,建构微型喜剧的艺术范式,展现喜剧诙谐幽默的本质,显现出一个文明古国高超的语言艺术造诣和戏谑化的喜剧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