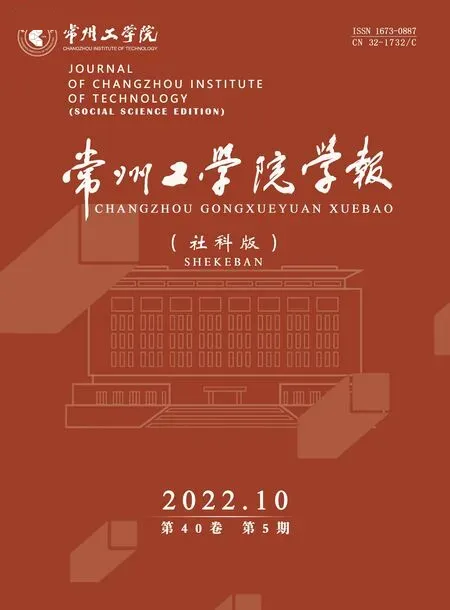论间接正犯的扩张与实质支配的回归
陈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3)
我国刑法学中的间接正犯概念舶来于德日刑法理论,一般是指幕后者利用他人实现自己犯罪的情形。虽无实定法的根基,却早已在司法实践中蔚然成林:辩护人运用间接正犯避免自己的当事人为他人的犯罪行为所波及①,法院和检察院运用间接正犯为造成了严重法益侵害的行为寻找适格的处罚对象②。因此对于被利用者而言,间接正犯的成立意味着出罪;反之对于利用者就意味着入罪。究其原因,在典型的间接正犯构造中,被利用的他人往往被视作工具,而缺乏故意犯罪的可罚性③,适用到三阶层或四要件的犯罪论体系中,表现为只要被利用的人欠缺任一阶层的任一要素或任一要件要素,不问被利用的程度如何,利用者都成立间接正犯,承担全部罪责。在这个意义上,司法实践中的间接正犯理论虚化为了单独正犯的空壳,而失去了以犯罪支配为核心的实质正犯的内涵。
基于此,本文试图回望间接正犯的历史形象,勾勒出其从责任层面向违法性层面和构成要件层面的扩张与泛化之路,主张这一趋势应当以罪刑均衡的间接正犯的当代价值内涵为指引,重新回归到以实质支配为中心的间接正犯发展道路上来。
一、间接正犯的历史形塑
(一)构成要件理论与限制的正犯概念
19世纪以来,伴随着三大自然科学的大发现[1],人类文明进入了狂飙突进的时代,自然科学成为了新的造物主,在供给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无形中塑造了人类全新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精确、严谨而客观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征服了不同学科,成为其争相引进的研究范式。实证主义提倡科学论证只可以根据客观事实,而不应涉及个人的价值评判,即所谓“价值无涉”[2];反对先验的思辨,力图将其自身限定在经验材料的范围之内;反对玄虚的精神,把学术工作限制在“给定事实”的范围之内[3]126-127。由此科学家们摆脱了以往的先验困境与宗教束缚,发现了一个客观真实的世界。当时的法学研究也受其影响,将“仔细观察经验事实与感觉材料”奉为圭臬,形成了法律实证主义,体现为透过法律文本建构的概念与逻辑规则去构建一个封闭的理论体系[4]51-75,即概念法学的逻辑演绎。刑法理论中的“绝对(机械式)的罪刑法定、毫无例外的禁止类推、无价值色彩的构成要件概念、法秩序一体性、法概念一致性以及形式违法性等”[4]54都是这一研究范式的结晶,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要属“构成要件”。
构成要件是由诉讼法概念演化而来的实体概念。德国刑法学家贝林于1906年出版的《犯罪论》是现代构成要件学说创立的标志,由此以构成要件概念为核心的古典犯罪三阶层理论体系建立起来,犯罪论开启了“古典时期”。李斯特在贝林之前就树立了不法与责任区分的意识,因此该体系也被称为“李斯特—贝林体系”[5]91-107。在贝林那里,构成要件是价值无涉的、客观的,是犯罪的指导形象,来源于实定刑法对犯罪成立的明文规定。这种以法定的构成要件为核心的观点成为刑法理论中诸多“形式说”或“客观说”的滥觞。例如犯罪预备与犯罪未遂的界分于着手,依据形式说则以行为人开始实施分则规定的构成要件行为为着手标准;在原因自由行为中,对于将“责任与行为同时存在”中的行为形式化理解为构成要件行为,是理论分歧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二元制犯罪参与体系下,法定构成要件又成为了正犯与共犯的区分所在,并据此提出了限制的正犯概念。
限制的正犯概念发源于德国,除少数如意大利、瑞士等国采用单一的正犯体系外,大陆法系的其他国家刑法中的犯罪参与体系理论莫不受其影响。究其原因,限制的正犯概念认为,只有亲自实施构成要件的才是正犯,故刑法分则明文规制对象是实行构成要件行为的人,但是没有亲自实施构成要件行为只实施了教唆、帮助行为的人,对构成要件行为的产生与完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具有应罚性,因此作为刑法处罚的例外,以“刑罚扩张事由”将教唆犯和帮助犯作为共犯纳入了处罚范围。在犯罪认定层面上将判断核心锁定为构成要件成为限制正犯概念的突出特征,能够合理地圈定刑罚范围,限制国家刑罚权的恣意性,但是过于明确与客观往往导致僵化。限制的正犯概念的正犯仅限于直接正犯,而对没有亲自实施构成要件行为,却在犯罪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又仅非教唆或帮助所能评价的人则无法做到正确认定,影响量刑均衡。
(二)古典犯罪论体系与严格从属性
古典犯罪论体系遵循主客观绝对分离的思路,认为一项犯罪的成立要依次经过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和有责性的重重检验。构成要件是价值中立的犯罪指导形象,起着为违法性与有责性的判断提供对象的功能,而违法性与有责性则分别对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进行客观违法性与主观违法性的检验。与彼时的心理学研究相呼应,刑法理论将有责性的核心——责任的本质——看作一种行为人所具有的心理事实,“在现实中以对犯罪事实有认识并且有意去做为要素的”视为故意,与之相对,“以有这种认识和有意去做的可能性为要素的”为过失[6]442。同时考虑到行为人遵守刑法规范的前提是具有对规范的接收与理解能力,因此责任能力也作为责任要素,纳入了有责性阶层进行考察。心理责任论由此形成:在具备责任能力的基础上,又存在故意或者过失心理的,便充足了有责性。
当时的德国刑法学界大多数学者认为,只有教唆、帮助一个“故意的”正犯行为才成立共犯,若该正犯行为并非故意为之,教唆者或帮助者均不能成立共犯,而是能否成立间接正犯的问题[4]52。当今德国刑法典第26条、27条仍隐约可见当时面貌:教唆犯是指“故意教唆他人实施故意违法行为”,帮助犯是指“对他人故意实施的违法行为故意予以帮助”之人[6]661。在古典犯罪论体系中,故意、过失等主观责任要素要等到行为该当构成要件且缺乏违法阻却事由时才进入检验程序,言下之意即为共犯必须从属于一个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且有责的犯罪行为,方可成立,是为迈耶(Mayer)所言之严格从属性或称极端从属性。当实施正犯行为的人不具有故意时,共犯无从依属,那么当没有除故意外的其他责任要素时,共犯是否成立呢?在古典三阶层体系中,责任要素包括作为责任前提的责任能力和作为责任形态的心理事实——故意和过失。不存在故意的情形既可能是行为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或者因精神疾病等原因而丧失责任能力,也可能是直接缺乏故意的知或欲。除此之外,彼时采严格故意理论的立场,认为违法性认识也是故意内容的一部分,所以当行为人不具有违法性认识时,也是缺乏故意的一种情形。故而在古典犯罪论体系之下,缺乏责任能力、违法性认识和故意的认识要素或意志要素的,都被认为是缺乏故意的情形,从而排除了这些情况下共犯的依附存在。
不得不提的是,责任共犯论也与共犯的严格从属性有着密切关联,甚至可以说,二者是同一事物在不同语境下展现出的不同侧面。前者面向的是没有实施构成要件行为的共犯何以要遭受处罚,即共犯的处罚根据问题;后者则探讨的是共犯对正犯的从属要达到何种程度才能成立。在逻辑上前者以后者为前提,而在事实层面,二者一体共生。在限制的正犯概念看来,共犯属于“刑罚的扩张事由”,是适用刑罚的例外情形,因此正犯与共犯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这反映为处罚根据上的差异。彼时的学者们基于严格从属性,认为共犯的处罚根据在于通过“教唆”“帮助”行为,诱拐正犯人堕入罪责之中,即“正犯是实行了杀人行为,而教唆犯则是制造了杀人犯”[7]。
(三)间接正犯的生成
法定的构成要件理论催生出的限制正犯概念以贯彻罪刑法定、保障人权的旗号获得了广泛认可;而以古典犯罪论体系为基础,严格从属性与责任共犯论也风靡一时,由学理迈入了立法的殿堂④。但是二者的结合却为司法实践带来了不小的难题:当成年人教唆缺乏故意、丧失责任能力或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直接行为人实施不法行为时,即使造成了严重的法益侵害,也囿于理论缺陷而找不到一个应该对此负责的主体。例如,成年人教唆幼儿为其偷盗财物,或者教唆精神病人拦路抢劫等,作为教唆者的成年人没有亲自实施构成要件行为,不符合限制正犯概念,同时幼儿和精神病人都属于责任阙如的主体,教唆者也无法成立共犯。这一刑罚上的明显漏洞限制了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的运行,违背了国民的正义观与法感情,引起了立法者和刑法学家们的重视。早期的间接正犯概念应运而生,借用我国台湾学者韩忠谟教授的定义:“利用无故意或无责任能力人行为,或利用他人无违法性的行为以遂行自己之犯罪者,通常称为间接正犯。”[8]319可以说间接正犯理论最初的使命就是弥补限制正犯概念与严格从属性所带来的处罚漏洞,专门解决利用无责任能力之人的教唆者的责任问题。由于其产生缺乏深厚的理论根基,间接正犯也被李斯特认为是“被虚构出来的正犯”,德国学者耶赛克等也曾评论,“在教义史上,间接正犯原本只扮演了‘替补者’的角色”[9]898。
二、间接正犯概念的扩张与泛化
(一)犯罪论体系的变迁与间接正犯的理论扩张路径
虽然古典的犯罪论体系在犯罪论的演变历史中具有开创性意义,但是实际上,以1906年贝林的《犯罪论》一书出版为起点,到1911年德国学者费舍尔首次发现主观的违法要素和1915年黑格勒最早在构成要件中讨论主观的违法要素为终点,古典犯罪论体系在德国刑法学界占据支配地位的时间不过10年左右[5]92。其后,对古典犯罪论体系加以改造的新古典犯罪论体系、目的行为论犯罪论体系依次登上历史舞台,展现了犯罪论这一刑法领域的经典魅力。
梅兹格尔作为新古典犯罪论体系的集大成者,系统研究了主观的违法要素,在迈尔的“构成要件是征表违法性的认识根据”的基础上,提出了“构成要件乃是违法性的存在根据”,从而将构成要件与违法性共同纳入了不法的判断之中,为目的、意图,乃至故意和过失从有责性阶层前置到构成要件阶层,扫除了框架性障碍。但是此时主观的违法要素并未系统化,例如故意仍仅是在承认未遂犯的可罚性根据上得以例外承认为构成要件要素。也就意味着,早期的间接正犯概念具备了从直接行为人责任要素的阻断蔓延到阻断构成要件符合性以及违法性判断的前提条件,并且在未遂犯的场合,作为罪责要素的故意已经进入了违法性的范畴。
继新古典犯罪论体系之后登场的是目的行为论犯罪体系,其代表人物是目的行为论大师威尔泽尔。威尔泽尔以开放的构成要件论、区分不法意识的主观构成要件论、构成要件错误和禁止错误区分论以及社会相当性理论为主要内容,构建了目的行为论犯罪体系。其中对间接正犯影响深远的莫过于区分不法意识的主观构成要件论和构成要件错误与禁止错误的区分。相比于新古典犯罪论体系在未遂犯的场合才将故意作为主观违法要素,威尔泽尔认为,既然故意在未遂犯的场合能作为违法性要素存在,在既遂犯的场合也应该肯定包括故意在内的整个主观构成要件都属于不法的内容[5]126-127。于是由贝林建立起来的价值中立的、纯客观的构成要件论演变为了客观违法要素和主观违法要素共同组成的范畴,原先作为罪责要素的故意也分裂为对客观构成要件的知与欲和违法性认识可能性两个部分。前者进入了构成要件阶层,成为了主观违法要素,称为构成要件故意;后者仍旧留在有责性阶层中以责任故意存在。至此,间接正犯完成了从有责性阶层到构成要件阶层的扩张,对于是否成立共犯的判断不必再等到责任故意的检验,在构成要件故意中就能做出判断。因为在引起违法性意识的认识上,构成要件故意与责任故意是一个整体[10]165。另外,由于构成要件的故意是对客观构成要件要素的认知与意欲,必然要依附行为、结果、对象等客观构成要件要素而存在,故,若直接行为人缺乏其中任一构成要件要素,自然谈不上故意的存在,遑论幕后者成立共犯。
(二)处罚漏洞的再现与间接正犯的现实扩张路径
如果说犯罪论体系的演变与共犯从属性的更进为间接正犯的扩张指示了理论路径,那么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的处罚漏洞,则为间接正犯原本的替补性底色添上了浓重的一笔。在故意、过失作为主观违法要素成为刑法的重大理论发现、共犯的限制从属性契合了责任主义原理而大行其道的背景下,早初作为“替补角色”的间接正犯概念似乎在当下的司法实践中寿终正寝,以二元犯罪参与体系下的学说史坐标而存在。例如黎宏教授及其合作者姚培培博士就曾明确表示,在行为共同说和限制从属性之下,“间接正犯概念不必存在”[11]。但是这样的观点既忽视了我国刑法第25条对共犯参与采取的犯罪共同说立场,也过于夸大了限制从属性说对处罚漏洞的消除作用。
我国刑法第25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据此,刑法通说理论一般认为我国刑法在共同犯罪的本质问题上采取的是犯罪共同说,进而要求二人以上的犯罪参与人必须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并且在共同犯罪故意之下实施共同犯罪行为[12]。虽然也有学者从行为共同的立场出发,将本条理解为“共同(在)故意犯罪”[13]541,但是这种对刑法文本的添附式解读,存在违背教义学基本立场的嫌疑,也过于偏离国民对法的理性感知,其妥当性需慎重考虑。一方面,在犯罪共同说之下,教唆或帮助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或者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实施犯罪行为的,例如教唆未满14周岁的儿童盗窃,帮助患有严重精神病的青年强奸妇女,虽然对犯罪的完成教唆者和帮助者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由于其没有直接实行犯罪行为,因此不能将教唆者、幕后者视为直接正犯,即使根据刑法第29条对教唆犯处以正犯的刑罚,也总存在教唆犯的共犯角色定位与正犯的刑罚之间的龃龉。而间接正犯这一实质的正犯概念正好可以消除教唆犯、帮助犯的形式共犯定位与实质应处以正犯之罚间的不平衡。另一方面,在行为人利用他人过失行为实现自己犯罪的场合,如果否定间接正犯的概念,将间接正犯的各种情形分流至共同正犯、教唆犯和帮助犯中,就会出现作为犯罪边缘角色的共犯成立故意犯罪,而作为实际主导犯罪过程的直接实行者仅成立过失犯罪的不合理现象[14]。
在限制从属性说之下,共犯的成立以正犯的行为该当构成要件且违法为条件,换言之,正犯行为必须具备不法。在当今结果无价值论与二元的行为无价值论承认构成要件是违法行为类型,是违法性的存在根据,若当正犯行为缺乏构成要件符合性或者存在违法阻却事由,则既不能将正犯行为作为不法行为处理,也不能将利用此类情形的犯罪参与人认定为共犯,处罚漏洞依然存在。例如医生利用无犯罪故意的护士向病人注射谎称是镇定剂而实际上是足以造成病人脏器损害的药物,在行为无价值论者看来,直接行为者缺乏作为主观构成要件的故意,不该当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至多可能成立过失致人伤害罪,因而作为利用者的医生在限制从属性下,也难以被认定为相应的共犯。此外,在利用他人具有违法阻却事由,如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时,基于法益衡量,正犯行为的不法性被排除,利用者亦不能成立相应的共犯。例如,甲编造消息引起了乙对丙的杀害意图,后甲又将乙的杀害意图及计划告知丙,提前做好准备的丙果真在乙实施杀害行为之时反击并杀死了乙。再者,当利用被害人的自我侵害行为时,出于自由主义的考虑,被害人在一定的范围内对自己的权利与法益拥有自我处断,被害人的同意与承诺阻却违法性就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若犯罪参与人唆使或帮助被害人自我损害时,由于被害人自我处分权的存在因而阻却了其自身的法益侵害性,自然犯罪参与者也不能从属于此合法行为而成立共犯。譬如,甲出于嫉妒谎称乙所购买的某天然宝石具有强烈辐射性,唆使乙销毁该宝石,甲不能成立故意毁坏财物罪的教唆犯。
总而言之,即使是当下共犯严格从属性转向为限制从属性,间接正犯的适用范围仍没有如预料之中缩小甚至消失,反而继续存在和扩大。这是因为间接正犯作为实质的正犯概念,其诞生于二元制的犯罪参与体系之下,这种犯罪参与体系认为正犯与共犯具有本质不同,前者为分则明文的规制对象,后者作为刑罚扩张事由,通过共犯制度加以规制。因此正犯概念与共犯无法完美贴合,天然存在着处罚缝隙,并且在理论演进与现实发展的摩擦下越发扩大。间接正犯的弥补性作用非但没有消失,还呈现出泛化的趋势。
三、从补充处罚到罪刑均衡:对间接正犯的类型化检讨
(一)罪刑均衡应当成为当代间接正犯的价值取向
作为“应急性的正犯概念”诞生的间接正犯,一开始就是共犯从属性的主张者为解决限制正犯概念对正犯的认定过于形式的不足而创设的,“弥补性”成为了司法实践为其贴上的第一个标签,并成为一种理论惯性,延伸至当下。但是随着刑法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发展,仅仅将其单纯作为补充性概念的工具的观点已不合时宜,因为当下即使是共犯独立性说的主张者也广泛地使用着“间接正犯”这一概念[15]。在共犯独立性说者那里,共犯的成立不从属于正犯,而在于对法益侵害的间接惹起,因此无论正犯者是缺乏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抑或有责性,都不影响共犯的成立。这充分说明,共犯从属性说主张者们并不是从弥补性的角度理解间接正犯的,而是从其他更为实质的角度赋予间接正犯新的价值内涵。笔者认为,这个新的角度就是罪刑均衡。
理论上一般认为,共犯从属性与区分制犯罪参与体系具有天然亲和性,共犯独立性则亲近于单一性犯罪参与体系。正犯与共犯的区分并不是法学家的理论游戏,而是在一定程度上,透过立法来决定责任的高度、轻重(立法层次的量刑区分),这种模式能够有效地防止司法的恣意与擅断,但却在复杂多变的现实面前丧失了一定的灵活性。而单一性的犯罪参与体系,则不在形式上区分正犯与共犯,只要与法益侵害具有因果关系的都作为正犯,具体的量刑轻重则取决于司法人员对不同参与人作用的判断。可以说,后者是比前者更为实质地看待犯罪参与的理论体系。为了克服区分制犯罪参与体系自身的结构性缺陷,不得不在实质化的路上越走越远。归根结底,这种结构化矛盾源于限制性正犯概念对正犯的认定过于形式,以至于只能将某些在共同犯罪中起到举足轻重作用但没有亲自实施构成要件行为的犯罪参与者,评价为相对不那么重要的共犯,量刑势必无法达到均衡,因此既不能达到论理上的一以贯之,也不能为普通国民所接受。在这种情形下,对正犯概念的实质化改造以达到罪刑均衡就不可避免。
间接正犯“罪刑均衡”的价值取向是在“补充性概念工具”基础上接续发展的理论成果,具有一脉相承的意涵。后者主张用间接正犯概念填补一切限制正犯概念与狭义共犯之间的漏洞,是从无处罚到有处罚的飞跃;而前者则是对后者“一概作为正犯施加处罚”合理性的反思与检讨,是理论发展精细化的必然趋势。那么如何验证认定间接正犯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呢?笔者认为决定因素是行为人对犯罪事实的支配力,亦即罗克辛教授的犯罪事实支配理论是厘定正犯的正确学说。犯罪支配的学说的正当性早已有无数学者进行过论证,作为一个规范概念,“不只是在区分正犯与共犯的问题上有其意义,而是每一个现代法治国刑法的归责基本指导原则”[4]59-60,因此其获得了指示正犯性的功能。直接正犯来源于行为对犯罪事实的支配,而间接正犯则来源于对犯罪事实的意思支配,进一步类型化为通过强制的意思支配、通过错误的意思支配和通过组织的意思支配。但是由于这种类型化过于粗疏,当下更多的是从被利用者的角度进行考虑,即从被利用者缺乏构成要件符合性、具有违法阻却事由和欠缺责任3个层面层层推进。但是这种类型化的潜在前提是,被利用者对其实施的行为不成立犯罪,为了找到一个能为该犯罪行为负责的主体而启用了间接正犯概念,换言之,间接正犯在这种类型中,仍充当的是弥补漏洞的“替补性”角色,因此,有基于罪刑均衡进一步检讨的必要。
(二)间接正犯的类型化检讨:实质支配说的回归
1.利用缺乏如身份等构成要件要素的人
利用有故意但无身份的直接行为人实施构成要件时,利用者是否成立间接正犯,理论上以公务员(甲)指使其不具有公务员身份的妻子(乙)收受贿赂为模型进行讨论,存在诸多争议。第一种观点认为,由于乙具有自由意志、能够应答规范而不能作为单纯的利用工具,所以甲成立受贿罪的教唆犯、乙成立受贿罪的帮助犯;第二种观点认为甲成立受贿罪的直接正犯、乙成立帮助犯。该观点由张明楷教授倡导,认为受贿的构成要件不是单纯地接受财物,而是财物与职务行为的交换性,因此当甲指使乙接受财物时,就是直接支配了对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的侵害,成立直接正犯[13]528-529。更为主流的观点则认为,当身份属于构成要件要素时,利用不具有该身份的行为人实施犯罪相当于利用有故意的工具的一种情形,因此幕后者成立间接正犯。但上述观点都存在不足:
首先,甲成立受贿罪的教唆犯、乙成立帮助犯的观点面临的一个无法回避的批判,就是会导致“没有正犯的共犯”这一现象存在,为二元制犯罪参与体系所不容,而在单一性犯罪参与体系之下,更无此必要。其次,甲成立受贿罪的直接正犯,乙成立帮助犯的观点,虽然坚持了限制的正犯立场,但无疑忽视了“收受财物”对受贿罪成立的重要意义,认为只有具有公务员身份的甲实施的职务与利益交换行为才是构成要件行为,将着手的认定推后至“实施为他人谋取利益”行为的时点,不当缩小了处罚范围。此外,还忽略了无身份者也可以起到与有身份者对等重要的作用而成立共同正犯情形的存在[16]。主流观点的思路仍停留于将间接正犯作为直接正犯的补充处罚的模式,认为受贿罪是身份犯,而乙不具有身份,不能成立本罪的直接正犯,幕后者甲具有公务员身份正是以教唆形式通过乙的行为实现受贿罪法定构成要件的间接正犯。但是利用者是否存在对犯罪事实的支配才是间接正犯成立的实质所在,当直接行为人具有主观故意,不存在被强迫、被欺骗的情形,只欠缺某构成身份时,难以说幕后者对其进行了意志的支配,正如德国学者耶赛克所言,“如果犯罪工具本身未被强制、产生错误或不是无责任能力的话,就很少谈得上幕后操纵者对犯罪工具的意志支配问题”[9]810。此外,有自我意志与行为决定自由的行为人也难以理解为诸如“单枪棍棒”之类的单纯工具。因此,出于实质正犯的视角,既不能将公务员甲认定为直接正犯,也不能轻易将其作为间接正犯。甲乙二人共同成立受贿罪的共同正犯则是值得思考的方向:甲虽然没有分担受贿罪的构成要件行为,但却在接受财物与作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承诺或行为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乙虽不具有公务员的身份,却实际主导了收受财物的行为。二者在共同的犯罪意思之下,互相利用、互相补充各自的行为,实现了犯罪意图,完全充实了受贿罪的所有犯罪成立条件。将二人作为共同正犯,意味着全面评价二人各自在犯罪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在量刑上的罚当其罪。
2.利用具有违法阻却事由(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险)的人
一般认为,利用他人合法行为实现犯罪的,幕后者成立间接正犯,但是刑法理论上所举之例大部分属于利用不知情的第三者的情形,如甲为了非法拘禁乙,谎称乙是现行犯,使警察拘留了他。如果警察明知乙不是现行犯而拘留,甲难以成立非法拘禁罪的间接正犯[13]529。当同时存在被利用者缺乏故意和行为合法两个要素时,难以明确是何者对幕后者成立间接正犯起了决定作用,因此有必要设计只有合法行为起作用的特殊情形:甲为了达到不亲手杀死乙的目的,就以乙儿子的生命为要挟,要求乙在丙晚上回家的路上埋伏杀死丙。同时又暗中告知丙,乙准备杀他的计划。因此丙在乙实施杀人行为时提前做好了准备防卫反击杀死了乙。这被视为典型的利用他人的正当防卫实施故意杀人罪的行为,但是幕后者甲是否成立间接正犯不能一概而论,仍需要进行犯罪支配的实质判断。
首先,从法哲学的角度看,合法行为中不能生出不法,实施正当防卫的行为人虽然直接造成了死亡结果,但其行为因正当防卫而合法化,在未超出防卫限度内不具有法益侵害性,根据“违法连带、责任个别”的原理,不能说一个行为既具有合法性又具有违法性,因此幕后者的利用行为也不能被评价为不法。其次,根据犯罪事实支配理论中的意思支配原理,也难以说幕后者甲将乙的伏击计划告知丙,就对防卫人丙形成了实质的意思支配。因为即使是在告知计划的情况下,乙也并不必然因有防卫的反击而死亡,还存在乙仍旧杀死了丙或者自己被制服的可能性,可见甲在事实上并未完全掌握犯罪过程的动向。最后,“利用行为的非法性与防卫行为的合法性也不具有等价性”[17]。所以从是否形成犯罪支配的角度看,这种利用合法行为的情形应当排除在间接正犯的适用范围之外。那么何种利用合法行为的情形应当作为间接正犯呢?对此,张明楷教授举例道:“A为了使B死亡,以如不听命将杀害B相威胁,迫使B攻击C,同时命令C正当防卫杀害B,后C正当防卫杀害了B。”进言之,即幕后者通过制造利益冲突和操纵利益冲突的处理实现犯罪。但这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利用合法行为。只有附带条件说A希望看到B和C自相残杀,并且无论谁死亡都是A意愿中的结果。A以B的家人相威胁,强制其必须不顾一切向C攻击,而C在无法逃脱的情况下,只能实施正当防卫。如果最终的结果是B死亡,则A成立利用合法行为的间接正犯;如果是C死亡,A则成立强制意思支配的故意杀人罪的间接正犯。简言之,在幕后者利用直接行为人的合法行为完成犯罪时,必须排除直接行为人的其他行为的可能性,并且对于结果呈现概括的接受。
3.利用未达刑事责任年龄或缺乏刑事责任能力的人
我国传统共犯理论认为,成立共同犯罪的前提是犯罪参与人均必须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若其中部分参与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或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则具有这两个条件的参与人就成立间接正犯。这是在四要件构成体系之下采取犯罪共同说和责任共犯论的必然结论[18]。如果单纯将间接正犯作为弥补处罚漏洞的概念工具,则无可厚非,但当罪刑均衡成为当代间接正犯的价值取向后,则存在问题。例如,因盗窃手段高超,行事果决狠辣,甲尚未年满16周岁,就被推举为盗窃团伙的老大。某日甲带领刚入行的成年下属乙共同实施入户盗窃,结果被警察当场抓获。无论是基于盗窃实行行为的分担还是在盗窃中发挥的实际作用大小,都不能径直地将乙认定间接正犯进行处罚,因为甲才是犯罪过程的核心角色,可见在相当的情况下如果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且具备刑事责任能力者并未对整个犯罪过程做到实质性控制与支配,就应当否认其成立间接正犯。即使是成年人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盗窃行为的情形,也应该就该未成年人对盗窃行为是否具有规范意识进行更为实质的考察,而不应该以是否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作为间接正犯的适用标准。刑事责任年龄作为法律拟定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产物,只具有征表意义,针对的是普遍情形,而非充分必要条件。当未成年人由于特殊的成长环境、社会条件以及他人影响等因素对该犯罪行为已经具有规范意识时,就有必要肯定其自由意志和规范认识,而不再一概肯定幕后者的意识支配和控制,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成年人唆使未成年人实施后者具有规范意识的犯罪行为时,不成立间接正犯而成立教唆犯。
注释:
①山西省保德县人民法院(2019)晋0931刑初126号、吉林省东丰县人民法院(2019)吉0421刑初130号、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2017)苏0214刑初528号等判决书。
②甘肃省甘谷县人民法院(2020)甘0523刑初146号、湖南省绥宁县人民法院(2019)湘0527刑初72号、吉林省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吉0191刑初7号等判决书。
③曹波:《中国刑法语境中正犯后正犯理论之消解》,《当代法学》,2018年第6期,第38页。
④德国1871年刑法第48条规定:对于他人以馈赠、期约,或以威胁、滥用其威望、暴力,或者蓄意地造成、促成一个错误,或以他法,故意地令其实行可罚行为者,以教唆犯罚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