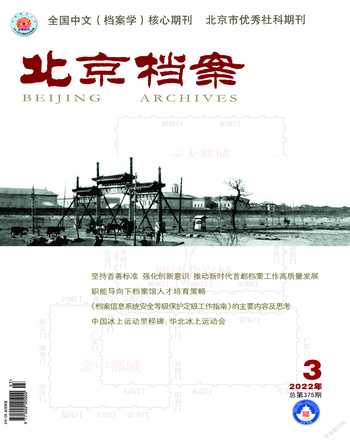民国时期北京照相业同业公会探微
王学斌
行会组织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对于在封建时期卑列于“四民之末”的工商业者来说,传统行会组织如会馆、公所等有着特殊的保障意义。晚清以降,中国经济从传统走向现代,民族民主运动大发展。在很多行业内,不同类型的学会、协会、联合会得以大量成立,许多传统行会组织也逐步向同业公会转化。所谓“人群进化,会社日兴,同舟共济,众志成城,内以谋同仁之利益,外足以御强力之侵凌,凡百皆然,商战尤甚”,[1]就是这一浪潮的真实反映。自19世纪60年代起,北京[2]新兴的照相业诞生,在其日益发展和壮大的进程中,与其他行业相同,也伴随着团体化和组织化。北京的照相业同业组织自20世纪30年代成立以来,先后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公私合营消失。在不同历史时期,它们以其集团性的整体力量,对北京城市社会发展发挥了很大作用。
重農抑商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安定社会和防止民间权势增大的重要手段,清代前期也不例外。但是到清末,清政府迫于内外压力,实行“通商惠工”,支持工商业发展。同时,清政府还颁布一系列法令来规范和引导行业组织的发展。1904年清政府颁布的《商会简明章程》,鼓励各地建立商会,以加强重商团结和官商沟通。1906年,北京商务总会成立后,北京的工商业者为了与外商展开竞争,纷纷成立了同业公会,“维夫诸货之有行也,所以为收发客装;诸行之有会馆也,所以为论评市价”[3]。此时,由于北京的照相业发展尚不成熟,规模较小,因此还没有自觉成立任何行业组织,但在晚清中央政治权威衰落和民间商人自主意识增强的背景下,照相业经营者也逐渐摆脱旧式分散经营的方式,逐渐形成以行业整体为中心的组织力量。
中华民国成立后,民间结社权利在《临时约法》中也得到明确规定,公民拥有集会与结社的自由成为社会共识,这也为照相业同业公会的成立扫除了政治上的障碍。此后,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机关,都颁布了许多关于工商同业公会的章程和法令。1918年,北京政府农商部颁发了《工商同业公会规则》及《工商同业公会规则施行细则》,明确规定了工商同业公会是“以各地方重要各营业为限”的行业组织,其宗旨是“维持同业公共利益,矫正营业上之弊害”,设立在总商会之下,受政府管理部门的监督,[4]首次在法律上认同了同业公会在行业经济管理方面的重要性。由于社会动荡和政府更迭频繁,这一法令并未得到认真执行,但各行业自觉组织同业公会的愿望显著增强。1923年,《工商同业公会规则》进行了修订,均强调同业公会要接受主管官署的领导。政府虽然未强制同业公会加入商会,但是以商会为总属,以同业公会分领行业的建构方式已渐成共识。可以说,在这一时期,已经初步建立起由政府部门到商会到同业公会的行业管理雏形。[5]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出于对加强工商团体管理和控制的考虑,对商会、同业公会等组织加以改组和整顿。1929年,国民政府将原《工商同业公会规则》修改为《工商同业公会法》及实施细则,规定:“各业之公司行号,均得为同业公会之会员,摊派代表出席于公会。”[6]国民政府先后制定的各项准则,均为此后北京照相业同业公会的成立奠定了法律基础。
随着清末照相技术在北京的传播,照相馆数量逐渐增加。据1916年《北京指南》记载,当时技术设备较好、名气较大的照相馆有丰泰、二我、同生、尚友、山本、亨泰、阿东、荣昌、宝记等9家。至1920年,北京照相馆发展到68家。[7]
1928年北京不再作为民国首都后,政治地位衰落,经济萎缩,照相业经营亦受到很大影响,全市中西照相馆下降为48家,约有店员500余人。[8]虽然国都迁移一度阻碍了北京商业的发展,但是“便捷交通,丰富物产之北平,依然保持其一百四十万人口之消费者,……信乎其占有工商业上之深厚基础与优越地位”[9]。此外,各类商人努力去发掘普通大众的各类消费需求,加之近10年的和平环境及“废两改元”等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北京的经济逐渐恢复,并形成了以商业、金融、服务业为主的行业结构。
由于民国初期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同业公会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在政府与手工工厂、店铺之间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大北照相馆成立伊始,其经理赵雁臣即鉴于北京照相馆虽多,但缺乏联络及研究机关,决定于1925年首先组织成立“照相研究公会”,“宗旨在谋技术之精美,及联络同业之感情,俾得互求进步,并颇得本京各照相馆之同意。闻日来加入者甚众,一俟内部组织者就绪,即行开成立大会”[10]。在这种背景下,北京的照相行业为了更好地发展,加之政府不断推动,不同照相商户开始考虑结社自治。到20世纪30年代初,在此前基础上,北京照相业同业公会正式成立,因大北照相馆照相营业规模较大,且业务齐全,经过一致推选,由赵雁臣担任主任委员。
相比于其他行业组织,北京照相业同业公会成立较晚,赵雁臣曾在采访中对照相业同业公会概况介绍道:该公会“迄今尚为全国照像业独一无二之团体,在会者共六十余家,不在会者有十余家,共七十余家”[11]。这些照相馆以东四南城为多,北城较少。其中各家又各分门户,各有专门主顾。它们除照相之外,大都兼营冲洗,唯有多少之别。比较冲洗外业务最多者,为五兴、中原、中华几家,而同生照相馆则开设美术部,营业亦较好。照相业店员人数,不易估计,有三二人开设照相馆,也有多至数十人。顾客中照普通人像者较少,照美术照者居多。
北京照相业同业公会成立后,得到迅速发展。据1936年6月《北平商业调查表》统计,北京市“照相业有87家,资本34975元(法币)”[12]。这些照相从业者大部分都加入了照相业同业公会。在此过程中,照相业同业公会努力维护市场秩序,并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
在照相业市场的经营中,制止恶意竞争是首要任务。在很多城市,因照相业无序发展,同行业之间竞争激烈,“经常出现某某照相馆以开张或成立周年纪念为由,张灯结彩,雇用乐队在店里吹吹打打,或上街游行,散发廉价照相及赠送五彩大像的传单,以广招徕”[13]。一些中小照相馆鉴于力量不足,便数家相互联合,与大户抗争,这种争斗不仅会扰乱照相市场,而且不利于照相业健康发展。由于北京“各照像馆价目所定不一,致有碍照像业发展”,照相业同业公会成立后,为协调非正常的价格竞争,召开成员会议,“商讨划一价目办法”[14]。
除此之外,照相业同业公会为维护本行利益,还会与各照相馆主商议,不断调整行业内的规章制度,以促进该行业的正常经营。1937年2月,北京照相业同业公会“举行二十六年度第一次全体大会,出席四十余人,决议事项如次:(一)改善营业,并防止营业上窒碍案。(二)请求当局减低同业营业税案。(三)执委宋美然拟有整顿业协,实行标准工作,提高工师待遇之信约。(四)规定标准价格,以免同业自相摧残案。(五)恢复公会当年经费办法案”[15]。这些议案经会员全体通过后,被提交于北京总商会,最终由北京政府当局审核处理。
抗战时期,北京照相业同业公会发挥了重要的协调作用,保证了北京照相业市场的稳定运行。抗战爆发后,北京沦陷,在日伪政府的控制下,日本侵略者不仅以暴力手段大肆进行经济掠夺和资源霸占,而且大量倾销日货,使得北京物资奇缺,市场萧条,各类货物价格飞涨。1940年8月6日,日伪《新民报》刊载,当时照相业同业公会有会员110户,从业人员780人。[16]虽然这一时期北京照相从业人员略有增长,但是中国商人在日本侵略者的压榨和排挤之下整体发展十分困难。同时,伪政府为推行“强化治安”,强迫市民办理“良民证”与“居住证”,且粘贴照片。但是抗战时期“本行材料,尽系外货,利权尽属于人,吃亏甚大”,导致沦陷区照相材料匮乏。为应对拍摄大量照片的需求,北京照相业同业公会进一步发挥协调作用,以降低费用,让更多普通民众可以负担。此外,为了应对伪政府额外增加的印花税,照相业同业公会向北京商会致函,“恳请仍援前例,在号簿上倍增印花号单免贴”,以减轻“商人重复之负担”。[17]即使发展艰难,但是为保护本行业,1942年8月,照相业同业公会仍旧“假市商会大礼堂举行改选大会,结果留任董事五人,特选董事六人,宋美然、王泽民、李云清等三人被选为常务董事,王泽民当选为会长”[18],以维持同业组织的运行。
解放战争时期,北京照相业同业公会努力抵御经济萧条,维护了北京照相业的利益。北京照相业同业公会于1946年改组,会址设于外二区甘井胡同28号,经过整顿,照相业得到短暂恢复。但是解放战争爆发后,时局动荡之下,国民党对各行业进行垄断和掠夺,加之后期的恶性通货膨胀,使得北京照相业再次陷入困境。但是照相业同业公会决心“为艺术前途计,为该业信誉计,为商业道德计,为国家颜面计,自亦不宜常此放任如许败类之嚣张也……原照相同业自今年起,一洗过去污点,发扬未来光明才是,果尔,虽不能与突飞猛进之欧美相抵衡,而在艺术本位上,总可问心无亏耳”[19]。因物价飞涨,北京照相业同业公会尽力维持本行业的价格成本。1948年,北京市民政局要求居民换发身份证,但由于照相材料价格上涨,许多照相馆无法盈利,遂统一商议,“请求转呈价格调整加强,使能维持”[20]。到1949年,北京照相业增加到197家,从业人员约1000余人。[21]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北京的照相业同业公会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北京以前的商业行会多是同乡不同行的地方商业组织。近代同业公会是突破了地域界限、以同行为纽带的商业同仁组织。它作为一种社会经济治理机制,对政府和店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照相业同业公会追逐西方、学习西方,将西方的民主思想和管理制度引入内部,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民主原则,能够反映本行业的共同愿望。它通过制定行规行纪,以强制的办法限制行业内部的竞争,同时采取选举和权力制衡原则,加强本行业的现代性,使其在社会转型中更具时代特点。
第二,照相业同业公会以行业自律来保护本行业利益,完善市场经济。它作为工商业者保护自身利益的重要工具,在不同时期的社会环境下,照相业同业公会通过照相馆评级、统一定价防止恶性竞争、改善经营方式等措施,维护同业竞争秩序,团结同业防止共同利益受到侵害,共同抵制外部的压力,并阻挡西方的经济侵略。同时,其通过同行业之间的人员交流,或进行整体培训,提高技能,开办刊物等,促进了照相从业人员整体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和市场秩序的稳定。
*本文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2021年研究生科研立项“照相与民国时期北京社会生活研究(1912—1937)”(项目编号:2021LS02)研究成果。
注释及参考文献:
[1]仝冰雪.中国照相馆史(1859-1956)[M].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16:249.
[2]近代以来,北京先后易名数次,为行文流畅,除史料引用外,本文其他论述皆称北京。
[3]解维汉.中国衙署会馆楹联精选[Z].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257.
[4]彭泽益.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下册)[Z].北京:中华书局,1995:985-986.
[5]魏文享.中间组织: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研究(1918-1949)[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23.
[6]“法规”[N].国民政府公报246号,1929-8-17.
[7][21]北京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商业卷·饮食服务志[Z].北京:北京出版社,2008:291; 294.
[8][9]池泽汇,娄学熙,陈问咸.北平市工商业概况[Z].北平:北平市社会局,1932:593-594; 268.
[10]照相公會之组织[N].晨报,1925-03-23(6).
[11]北平的照像业[N].益世报(天津),1934-07-22(8).
[12][16]孙健,刘娟,李建平,毕惠芳.北京经济史资料:近代北京商业部分[Z].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 464;474.
[13]朱振三.长沙照相业史话)[Z]//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162-170.
[14]全市照像业划一价目[N].北平晚报,1937-02-10(3).
[15]平市照像业请求减低营业税[N].京报(北京),1937-02-04(6).
[17]实业总署工商局、北京市商会、北京市照相馆业同业公会等关于改订征收印花税办法的训令、批、呈、函[Z].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J071-001-00835.
[18]京照相业公会昨午改选[N].晨报,1942-08-29(4).
[19]培雯.一年来的照相业[N].社会画报,1948.
[20]北平市民政局关于换发国民身份证的训令[Z].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J003-001-00304.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以上海茶叶业同业公会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