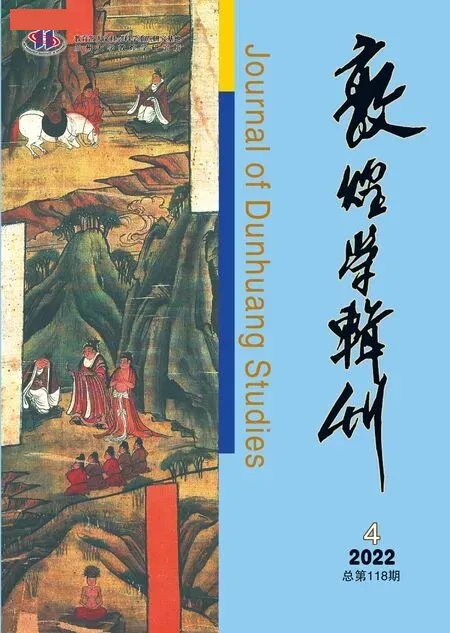构建中国气派敦煌学刍议
胡 潇
(清华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100080)
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和厚重“历史符号”,为人类文明交流互动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近年来,河西走廊地区在华夏文明探源和亚欧文明交流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在新时代背景下建设、传承、创新,发掘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的中国气派敦煌学,将在培育新时代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新文化等方面具有现实意义。
一、敦煌学的发生、发展和壮大历程为继往开来提供了非常好的范例
“敦煌学”原来主要研究藏经洞出土文献资料,以后逐渐扩大到石窟、壁画、汉简乃至周边地域出土的古代文献和文物,成为研究、发掘、整理和保护敦煌地区文物、文献的综合性学科,涉及到敦煌学理论、敦煌学史、敦煌史事、敦煌语言文字、敦煌俗文学、敦煌蒙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与中西交通、敦煌壁画与乐舞、敦煌天文历法等诸多方面。20世纪以来在西学影响下而兴起的敦煌学与吐鲁番学、龟兹学、简牍学、西夏学等都基于新材料的发现,成为“新国学”的有力补充。敦煌学诞生的重要标志是1900年王圆箓道士发现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大量珍贵新材料不但提出许多崭新课题,形成了“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开启了中国敦煌学一个世纪的研究历程。西方学者运用近代考古学、文书学及文化探源和比较文化的方法,因此在敦煌学形成的早期已包含大量“西学”元素。藏经洞出土文献虽然以汉文化写卷为主,但其中有不少其他民族的资料与信息,因而敦煌学超出了“国学”范畴,用新方法、新材料来研求新问题是敦煌学发展的关键所在。王国维用敦煌发现的新资料进行学术研究时,特别注意敦煌新材料与原有旧材料之间的异同、互补和渊源,因此强调“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他对敦煌写本的早期研究,树立了正确处理新材料、新方法、新问题三者关系及中、西学关系的榜样,构建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新视角、新理论、新框架。经过国内外数代学者共同努力,20世纪80年代中国敦煌学研究进入繁荣时期,取得丰硕成果,在敦煌文献整理和利用、敦煌语言文学研究、系列研究著作整理出版、辞典编纂、敦煌艺术研究、敦煌石窟保护等方面成就斐然。
2011年4月,郑炳林主编、法国汉学研究领域杰出学者耿昇翻译“法国汉学研究丛书”之《法国藏学精粹》(全4册)由甘肃人民出版出版,汇集伯希和、韩百诗、石泰安、图齐、古伯察、李盖提等众多法国汉学研究名家的藏学相关文章,涉及地理、考古、语言文字、文学、宗教、自然科学等多方面。2014年12月,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郑炳林、郑阿财主编的《港台敦煌学文库》(100卷),收录港台地区敦煌学领域论文606篇,达1170余万字,基本展现了港台地区近百年来在敦煌学领域重要成果。2015年,敦煌学研究所启动《国际敦煌学百年文库》编撰,得到台湾、日本、法国、英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高校、科研院所及图书馆支持,实现学术数据库共享。“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敦煌讲座》(21册)规模宏大、卷帙浩繁,总字数900万,图片2000余幅,甘肃教育出版社自2013年开始陆续出版,将历史、地理、社会、考古、艺术、文学、文物、文献、经典、写本学等敦煌学研究的主要领域,和以前不为学界所关注的一些极为冷门的偏僻领域进行了全面展现,系统回顾了敦煌学研究的百年历程,从而理清了百年敦煌学发展的脉络和存在的不足,并就敦煌学今后的发展开拓了新视野,提出了新思路和新方法。
二、考古成果大大拓展了“敦煌学”的研究领域
敦煌学诞生的基础是藏经洞出土古代文书资料,敦煌学在发展过程中始终伴随着相关材料的公布、解读,甚至又有新材料被发现,例如,在莫高窟就有两次重要发现。第一次发现是1944年8月30日上午在后园土地祠(该庙为清末中寺主持王喇嘛所修)残塑中发现六朝残经多卷,引起学术界重视。第二次发现是1988年至1995年,敦煌研究院石窟考古研究所对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进行系统发掘,出土了大量汉文、梵文、藏文、西夏文、叙利亚文、古回鹘文以及蒙古文文献,这些13-14世纪蒙古时期的世俗文书、宗教文献,由汉语、波斯语两大语言编纂的史料群,可以更详细地阐明蒙古统治时期的敦煌及河西地方的历史概貌。这些新材料甫一发现,便引起敦煌学界的高度重视,引发学者研究热情。
敦煌地区发现的汉简资料也大大拓宽和丰富了学者的研究范围。1910年代,王国维《简牍检署考》及其与罗振玉合著《流沙坠简》开启了简牍研究先河。王国维与罗振玉共同考释汉晋木简,写作《流沙坠简》之时,运用现代考古学成果,结合《史记》《汉书》等文献史籍资料,对汉代边塞和烽燧的考实、玉门关址、楼兰及海头城位置的确定,西域丝绸之路的探索以及汉代边郡都尉官僚系统的职官制度的排列等汉晋木简所涉及的一系列相关问题,逐一做了详尽的考释,在研究中创立并运用二重证据法,其后又将此方法运用于甲骨文、金文和敦煌文书研究中。1970年代,“简牍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被正式命名,其后该学科的发展日新月异,时至今日已成为当代“显学”。上述敦煌汉简内容多与汉代敦煌、酒泉二郡屯戍活动有关,学术价值极大。从广义上来说也是对敦煌学研究范围的扩展。
近年来,河西走廊地区考古成果卓著。考古发现证实,距今5600-3400年间,在包括南西伯利亚地区、萨彦-阿尔泰-天山地区和蒙古高原地区的欧亚草原东部广泛分布着几个早期青铜文化,如阿凡纳谢沃文化、奥库涅夫文化、切木尔切克文化、赛伊玛-图宾诺文化、安德罗诺沃夫文化等,他们拥有早期青铜冶炼和制作技术,以畜牧和农耕相辅相成的混合类型经济为生产生活方式。这些相同的文化特征说明欧亚草原早期青铜文化之间历来存在着密切联系和交流,并且通过新疆、河西走廊向东传播。河西走廊地区在距今约4100年前就已开始铜冶金活动。敦煌地区新石器文化文化遗址数量较多,玉门市境内10处,瓜州县境内7处,敦煌市境内7处,肃北地区3处,包括新石器时代文化、过渡类型、四坝文化、骟马文化等。(1)段小强、陈亚军《敦煌地区史前文化初步研究》,《敦煌学辑刊》2017年第4期,第112-123页。敦煌南北山脉及河西走廊玉门断裂带玉门、瓜州、肃北、阿克塞等地有数十处铜、金和铅锌矿,这些都为史前金属制造业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敦煌地区史前冶金术受外来文化影响发展较早,且具有明显地域性。敦煌西土沟是最重要遗址之一,考古证明至少距今4000年前敦煌西土沟、古董滩一带就有人从事冶炼铜及相关活动,他们代表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冶炼技术。敦煌地区早期冶铜业变化最为明显,如红铜逐渐向青铜转变,铸造向合金进步,冶金术发展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而发展起来,在相对成熟后也影响着周围的青铜文化。到四坝文化时期,敦煌地区冶炼技术更是炉火纯青。四坝文化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中西部地区,东起山丹,西至瓜州以及新疆东部哈密盆地一带,距今约3900年-3400年。西土沟遗址冶金遗物是较长时段或多个考古学文化所遗留,其中包括四坝文化。
敦煌地区还发现大量贝类及用贝壳加工而成的装饰品,如瓜州鹰窝树遗址出土2件蚌饰均系天然蚌壳制成,发现海贝1件;M3发现海贝3枚;兔葫芦遗址采集到海贝5件。同类海贝在河西走廊民乐东灰山遗址、酒泉干骨崖、永昌西岗、柴湾岗墓地等地区大量发现。研究表明,东灰山遗址发现的海贝来自今辽宁、台湾、广东、海南、西山群岛等地,大多有穿孔,用来佩戴,或死者口含、手握。这些来自东部沿海的文化遗物应该是长距离贸易和文化互动的结果。
四坝文化和中原华夏族同时或稍后即已进入了早期奴隶社会,他们以牧羊业为主,兼营农业、手工业,与外界也已有一定交换关系。大量铜矿、玉矿遗址的发现,表明在包括敦煌地区在内的河西走廊很可能生活着一支或多支在找矿、采矿等方面有着丰富经验的人群,从铜矿寻找开采到玉矿的寻找开采,不同行业在相近领域的知识和经验上有着一定积累、借鉴与传承,这可能促使敦煌地区玉矿资源很早就被开采利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自2011年以来联合多家单位开展“河西走廊早期玉矿遗址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项目,先后发现马鬃山河盐湖径保尔、寒窑子和敦煌旱峡玉矿遗址三处玉矿遗址。敦煌旱峡玉矿遗址早期为西城驿文化和齐家文化遗存,距今约4000-3700年,晚期为骟马文化遗存(2)陈国科、丘志力、蒋超年、王辉、张跃峰、郑彤彤《甘肃敦煌旱峡玉矿遗址考古调查报告》,《考古与文物》2019年第4期,第12-22页。(3)陈国科《河西走廊地区早期玉矿遗址考古调查发掘收获概述》,《丝绸之路》2019年第1期,第38-41页。。科学检测分析显示,“早在距今4000年或者更早,肃北的玉料已经东传进入中原,显示肃北敦煌旱峡古玉矿是潜在的、可能与中国黄河流域早期玉文化关系非常密切的重要的古代玉料产地。”(4)丘志力、张跃峰、杨炯、王辉、陈国科、李银德、宗时珍、郭智勇、杨谊时、谷娴子、叶旭《肃北敦煌旱峡新发现的古玉矿:一个早期古代玉器材料潜在的重要源头》,《宝石和宝石学杂志》2020年第5期,第1-12页。紧邻敦煌的新疆哈密也发现了青铜时代晚期绿松石矿址,开釆历经数百年,从商周时期到战国。黑山岭遗址距离丝绸之路“大海道”仅仅10公里,这条敦煌与哈密、吐鲁番之间最近的古道在敦煌文书中唐代《西州图经》残卷有记载。史料记载“大海道”在西汉时期被开辟出来,实际上它的前身和基础是青铜之路、玉石之路。
甘肃省肃北县马鬃山因其连通新疆东部与内蒙古西部,一直是古代东西交通及游牧民族考古的重要地区,陈靓、任雪杰、凌雪、席琳、文少卿《甘肃省肃北县马鬃山地区先民的生物考古学研究》认为具有东北亚蒙古人种面部特征的马鬃山先民生前经常从事奔跑、骑乘等活动强度较高的活动,食物结构以肉类为主,遗传结构显示与“原匈奴”人群有一定关系,结合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出其绝对年代为1955-1691cal.BC,因此,初步推测其可能是与蒙古高原和外贝加尔地区的人群迁移进入我国北方地区进行人群交流与融合有关,这对探讨我国西北地区早期人群及文化的交流具有重要意义。“马鬃山区域有可能是早期匈奴人进入中国后经常活动的区域,在这里完成了汉化的过程,并发展成为中国北方游牧文化的根基。”(5)陈靓、任雪杰、凌雪、席琳、文少卿《甘肃省肃北县马鬃山地区先民的生物考古学研究》,《第四纪研究》2022年第4期,第1118-1128页。通过前人对马鬃山地区的文化因素分析表明,马鬃山地区的石板墓、石筑墓、组合岩画和石围基址显示出比较明显的游牧文化特色,且与匈奴,月氏有着密切关系。
三、继往开来构建中国气派敦煌学
2021年10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2022年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习近平总书记就文物考古工作作出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科学地回答了事关文物考古事业长远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也为新时代考古学科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
敦煌地区相关考古、研究成果打通了敦煌新石器时代与历史时期,将在华夏文明探源和建立“中国气派敦煌学”中将起到重要作用。玉帛之路的原生性贸易物资是玉石的东输,派生出的才是布匹丝绸的西输。在这同一方向的运输线上,先后接引东来的重要文化要素依次为三大宗:玉、马、佛。而西输的文化要素主要是布匹和丝绸,这条路上的纺织品西输早已终止,只有玉石向内地的东输依然在延续,这是迄今所知最典型的华夏道路,也是伴随中华文明发生发展全程的脚下之路。敦煌旱峡玉矿遗址考古成果将敦煌与中原联系的时间也向前推进了近2000年,证明中华民族对敦煌开发的历史大大提前,可谓“敦煌再发现”,这是自1900年发现敦煌藏经洞和外国学者大量运走敦煌文书以来,由中国本土学者在敦煌独立完成的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探索发现。如果说敦煌藏经洞文献资料催生了敦煌学,不断发现的汉简丰富了敦煌学,那么,以甘肃敦煌旱峡玉矿遗址为基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将为中国气派的“敦煌学”注入新的活力,而新时代中国气派的“敦煌学”必将在向国际社会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讲清楚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和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等方面起到独特作用。同时,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一带一路”经济文化建设的深入,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在考古、文化、历史、教育等领域的交流合作越来越多,跨学科合作研究也是大势所趋。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和大数据共享也为跨国际、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广阔空间。因此,继往开来,建设符合时代潮流的中国气派敦煌学势在必行,也是敦煌学获得飞跃发展的良好机遇。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已经在敦煌学跨国际、跨学科开拓性研究和教育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且已经培养出遍布海内外高素质研究人才团队,必将在中国气派敦煌学建设中发挥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