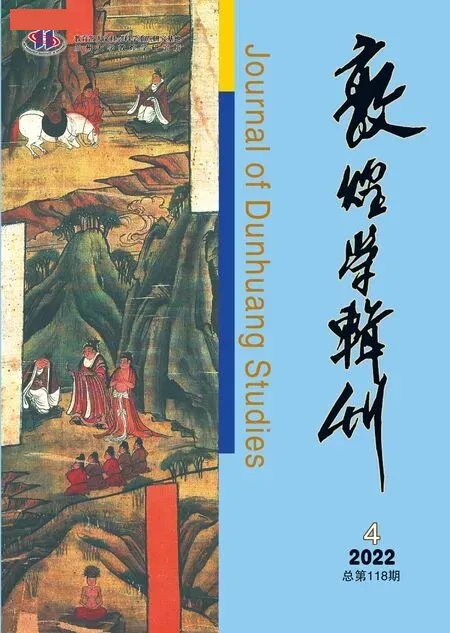敦煌学的珍贵历史记录
——读《敦煌人生:我的父亲段文杰》
刘进宝
(浙江大学 历史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2011年1月21日,父亲吃了早餐后,像往常一样坐在桌前翻看了一会儿书,就说想躺下休息。我把他扶到床上躺下,看他慢慢睡着了。中午饭好了,他说不想吃,继续睡觉。下午阳光很好,葆龄见他醒来就给他理了发,我们像往常一样扶他解手,之后他说累了,要休息一下。到床上不久,我们还没离开就看见他闭上双眼,轻轻呼了一口气,就再没有动静了。葆龄说:‘爸爸走了!’我还不相信,拉着他的手腕,确实没有了脉搏,这才知道他老人家真的去世了。”(段兼善《敦煌人生:我的父亲段文杰》,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年5月,第293-294页。以下凡引本书仅注明页码)一代敦煌人的代表、“大漠隐士”段文杰先生,在95岁高龄时就这样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没有遭受任何的痛苦,简直就是佛的涅槃,这是几世修来的福分!?
一
说到敦煌和敦煌学,常书鸿、段文杰和樊锦诗是无法绕开的,“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和“敦煌的女儿”樊锦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相对而言,被誉为“大漠隐士”的段文杰,知名度则没有常书鸿和樊锦诗高,甚至认为“大漠隐士”的比喻,并不能反映段文杰对敦煌的贡献,应该有一个更加响亮的名称。
对于段文杰,我是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我曾经与段先生有过近距离的接触,在莫高窟与段先生有合影,在兰州的家里拜访过段先生,段先生的回忆录《敦煌之梦》我认真读过。段先生去世后,敦煌研究院于2011年8月23日召开追思会时,我也应邀参加,并作了《敦煌研究院史上的“段文杰时代”》的发言,将段文杰从1980年开始主持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工作到1998年从敦煌研究院院长岗位上退下来的18年,称为敦煌研究院史上的“段文杰时代”,同时还撰写了《段文杰与敦煌研究院》的长文。说陌生,我毕竟与段先生年龄相差比较大,尤其是80年代初我开始涉入敦煌学领域时,段先生已经是大名鼎鼎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我们之间的距离比较远。再加上所从事的专业又不同,段先生的专业是石窟艺术,我是历史文献,没有学术上的交集。所以与段先生虽然相识,但没有个人之间的交往,他的论文我基本上都读过,有些甚至不止一遍。我读段先生的论著,是仰望,是学习,是吸收。
近年来,我关注和研究的重点是敦煌学学术史,敦煌研究院的院史是绕不过去的,段文杰也是我研究的对象,甚至是重点之一。在段文杰先生的公子段兼善老师的支持下,正在整理段文杰的书信,自认为对段先生是比较了解的。但看了段兼善老师的《敦煌人生:我的父亲段文杰》后,仍然很震撼,感觉这是一本了解段文杰、了解敦煌、了解敦煌学的好书,值得推荐和阅读。
现在有许多的传记、回忆录,都会对传主有意或无意地拔高,使传主本人都感觉脸红,同事或知情人看了摇头。拿到本书前我就想,儿子眼中的段文杰会是怎么样的?作者能否客观地描写段文杰的学术与人生?看完本书,知道这是一本冷静客观,以事实为依据,以第一手资料为支撑,能够比较全面反映段文杰与敦煌研究院发展史的好书,真正做到了“自己看了不脸红,别人看了不摇头”,达到了传记的基本要求。
二
段文杰是四川绵阳人,抗战时期的1940年,考入在重庆的国立艺专学习五年,并以人物画为主。1944年,先后看了王子云和张大千在重庆举办的敦煌壁画展览后,受到了感染,认为应该到敦煌去作一番实地的考察与研究。
1945年7月段文杰从国立艺专毕业后,直奔敦煌。到兰州后,时逢抗战胜利,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大多学者复员返乡,又遇到敦煌艺术研究所改隶主管单位,直到1946年中秋节前夕才到达莫高窟。
段文杰先生到莫高窟后,曾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考古组代组长。1950年后,历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美术组组长、代理所长;1980年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第一副所长,主持研究所的工作;1982年4月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升格为敦煌研究院后,为首任院长;1998年以后任名誉院长。
作为管理者的段文杰,他是忙碌又充实的。作为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首先是一位学术领导人和学术组织者,再加上敦煌的国际影响和在丝绸之路上的特殊地位,一些重要活动也在敦煌进行,参观访问的人很多,尤其是许多国际友人和中央相关部门的领导,来敦煌时段文杰都要亲自接待并带领参观和讲解,为此而耗费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如1988年,他既有“频繁的外事交流和接待外宾活动,还要召开院务会议,研究部署各部门工作的同时,挤出时间亲自写书信与有关方面联系。”仅仅是与日本方面的联系,就有很多,如“接洽平山郁夫率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访问敦煌,石川六郎率日本文化保护振兴财团访问考察敦煌,圆城寺次郎、木村佑吉、东山健吾、松本和夫等组团访问敦煌,越智嘉代秋和越智美都江夫妇为其已故女儿越智佳织代捐文物保护款事宜,高田良信率团访问敦煌演出问题,还有安排研究院副院长率团访日进行环境保护科学研究考察事宜等”,都需要段先生亲自致函联络。另外还有许多国内外学者、艺术家和各方面友好人士的来信,涉及到文化交流、援建项目、学术探讨、人才培养、中外友谊等,都需要段文杰认真对待,及时回复。“这些工作烦琐细碎,费时费力,基本都要在业余时间加班加点才能完成。”(第235页)
由于莫高窟于1987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受到了各方面的高度关注。以“保护、研究、弘扬”为己任的敦煌研究院,对外的展览、宣传,也是弘扬敦煌文化艺术的重要举措。仅1988年,研究院就与甘肃、宁夏、内蒙古等省区文博单位联合在日本举办了“中国敦煌、西夏王国展”,段文杰参加了在日本奈良举办的“奈良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段文杰还应日本文化厅、东京艺术大学和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的邀请,前往日本讲学。出席平山郁夫画展并剪彩、致辞;再次与池田大作先生晤谈。拜会日本首相竹下登,并邀请竹下登访问敦煌。同年秋天,陪同竹下登首相参观莫高窟,竹下登宣布日本政府援建项目。
就是在这样忙碌的日子里,作为学者的段文杰,不仅于1988年在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敦煌石窟艺术论集》,而且还发表了《谈敦煌早期壁画的时代风格》《飞天在人间》《敦煌学回归故里》《八十年代的敦煌石窟研究》《莫高窟保护工作进入新阶段》《敦煌石窟保护的历史进程》《解放前后的莫高窟》等学术文章。
段文杰先生将一生献给了敦煌。《敦煌人生:我的父亲段文杰》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段先生在管理、研究方面的贡献。现仅就自己阅读中比较有收获的部分略作阐述。
1.段文杰的临摹实践和成就
段文杰先生到敦煌后,所从事的主要工作首先是临摹。通过初步的观察和实践后,他认识到,“临摹一定要忠于原作,不要随意在临本上改变壁画的造型原貌和色彩。临本是要给别人看的,要让观者看到敦煌壁画的真实状态,看到古人的敦煌画风,而不是让观众看我们进行了加工改造过的所谓的敦煌壁画。”(第28页)
为了学习临摹,段文杰开始时主要临摹一些局部形象,如一尊佛像、一身菩萨、一组舞蹈、几个天宫伎乐、几个力士、几个动物等。这主要是因为局部的构图和形象比较好掌握,一般不容易出错,而整幅壁画内容繁多、场面大,不好把握。而在临摹大型壁画的时候必须要全面了解尺幅、构图、色彩配置关系等一系列画面因素,只有这样,才能成竹在胸,避免失误。也只有多花费一些时间和功夫,反复观察,上下比较,左右对照,反复推敲,才能准确起稿。
为了临摹的作品更加真实,段文杰在实践中认识到,在动笔前,首先要搞清楚古代画师创作的画面形象的思想来源和生活依据。如在临摹“维摩诘经变”时,他先查阅《佛说维摩诘经》中十四品的内容,掌握画面的结构规律。其次要辨别各时代壁画的风格特征。由于时代不同,有些壁画变色严重,有些变色则相对小一些。再次要了解各时代壁画制作的流程和方法。如早期壁画的起稿基本上是用土红作人物大体形象,然后是上色和定型。隋唐时期开始用粉本,从而有了画稿和白画。只有清楚了古代画师的作画程序,临摹时才会心中有数,乃至得心应手。
所谓“粉本”,一种是在厚纸或羊皮上画出形象,用针沿线刺孔,再将羊皮钉上墙壁,用土红色拍打留痕,再以墨笔连点成线,完成了墙壁上的画稿。还有一种“粉本”即小样画稿,也就是“白画”。画师参照白画在墙面自由作画,给墙面白画着色后,稿线会模糊。最后就要用深墨线定型并开脸传神,才算完成。(第32页)
从到莫高窟的1946年,至1957年的十余年,是段先生壁画临摹的黄金时期。他主要的临摹作品如莫高窟第130窟的“都督夫人礼佛图”、158窟的“各国王子举哀图”、第217窟北壁的“观无量寿经变”、榆林窟第25窟的“观无量寿经变”等,都是这一时期完成的,也是青年段文杰留下来的宝贵文化财富。尤其是“都督夫人礼佛图”,更是“临本中的典范之作”,广为世人所推崇。
所谓都督夫人礼佛图,就是莫高窟第130窟进口处甬道南壁的一幅大型唐代壁画,画面高3.12米,宽3.42米。宋或西夏时又在此画上面重新绘画。1942年张大千在敦煌时,无意中将上层壁画剥离,使盛唐时期“朝议大夫使持节都督晋昌郡诸军事守晋昌郡太守兼墨离军使赐金鱼袋上柱国乐廷瓌”的夫人礼佛图显露出来。这幅画场面宏大,人物面相丰腴,体态健壮,服饰艳丽,对复原临摹的要求很高。
在临摹前,段文杰对此画所反映的历史进行了探讨研究,对画面形象不清楚的地方,还力争从其他相似并保存完整的画面中找出根据,再经过反复考证后将其补全。在复原临摹中必须实事求是,要有历史依据,不能随意添补或减少画面内容。
有人曾经问段文杰,“你临摹得最多,速度又快,有什么诀窍?”段文杰是这样回答的:“哪来的什么窍门,只不过是要多花些精力时间去研究琢磨而已。对一幅要临摹的画,首先要把他的主题内容搞明白,还要把握好此画的构图全局。对画面风格的时代特征要做到心中有数,线描运笔要沉稳有力,一气呵成。色彩晕染要丰润雅致,注意层次变化。人物神态的刻画要注意面部表情和身姿动态变化。把握了这些重要的关节点,就容易画好了。”(第60页)这既是段文杰能够成为一代临摹大师的诀窍,也是所有能在某一行干好本职工作、成为某一方面专家的不二法门。
如“都督夫人礼佛图”刚剥出来时,画面比较清楚,色彩绚丽夺目,后来壁画开始脱落,色彩褪变。为了留存这幅有重要价值的壁画,段文杰先生决心将其临摹。“但当时壁画的现状,形象已经看不清楚了,无法临摹。要保存原作,只有复原,把形象和色彩恢复到此画初成的天宝年间的面貌”。段先生就“开始了复原的研究工作,在八平方米斑剥模糊的墙面上去寻找形象”。这幅画共有十二个人物,经过历史的风雨后,有的面相不全,有的衣服层次不清,有的头发残缺,这样就没有了复原的依据。虽然有许多的困难和不便,但段先生没有放弃,他首先“对盛唐供养人和经变中的世俗人物进行调查,掌握了盛唐仕女画的脸面、头饰、帔帛、鞋履等等形状和色彩,把残缺不全的形象完整起来”。然后又“查阅了历史、美术史、服装史、舆服志和唐人诗词”等。正是因为有了“这一切的历史依据,这样就提高了临本的艺术性和科学性。”(1)段文杰《敦煌石窟艺术论集》自序,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页。
段文杰不仅是敦煌壁画临摹事业的开创者,他的临本,技艺纯熟,形神兼备,代表了敦煌壁画临摹的最高水平。他主导并与同事合作完成整窟临摹的莫高窟第285窟、榆林窟第25窟,成为敦煌壁画临摹的标杆。而且还将临摹提升到理论的高度,撰写了《谈临摹敦煌壁画的一点体会》《临摹是一门学问》《谈敦煌壁画临摹中的白描画稿》等学术论文。在这些论文中,段文杰通过自己的临摹实践,对前人不曾留意的“临摹学”进行了探讨,初步呈现了“临摹学”的影迹轮廓。(2)参阅段文杰著,杜琪、赵声良编《陇上学人文存·段文杰卷》编选前言,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8页。当然,“临摹学”的学科建设还任重道远,需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段文杰先生在敦煌壁画临摹艺术实践和理论方面的突出成就,为保存、传播敦煌艺术做出了卓越贡献。”(3)段兼善《敦煌人生:我的父亲段文杰》,第297页。这是时任副省长咸辉在段文杰先生遗体告别仪式上所致悼词中的话。
段先生临摹壁画的原则是:“一要对得起古人,二要对得起观众。他的目的是准确地反映古代匠师的艺术成就,让现代观众感受到传统的精彩。”(第90页)
2.对敦煌艺术来源的思考
敦煌文化的来源,是敦煌艺术工作者值得重视的问题,以前主要流行“西来说”。“一谈敦煌石窟艺术,便是希腊式、罗马式、波斯式、印度式或者犍陀罗式、抹菟罗式。有人认为连石窟形制、制壁方法也都是西方传来的,有人认为佛教艺术从外国传入中国后,不得不沾上一些中国色彩”。段文杰先生指出,敦煌艺术是外来种子在中国土地上开放的花朵,也吸收了外来艺术的营养,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应该清楚,“佛教艺术作为世界性的宗教艺术,同一种籽,播撒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的土壤里,由于不同的雨露阳光的滋润和培养,便开放出艺术上的同形而异质的花朵,形成世界佛教艺术的百花园。如果用中国古典文艺的一种形式作比较,佛教艺术好像曲牌子,同一沁园春、菩萨蛮,不同时代,不同的人填入不同的内容,则表达出不同的思想感情,呈现不同的艺术风格,给人以不同的审美感受。”(4)段文杰《敦煌石窟艺术论集》自序,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页。为此,段文杰先生撰写了《略论敦煌壁画的风格特点和艺术成就》《谈敦煌早期壁画的时代风格》等论文,予以专门探讨。
敦煌石窟是佛教东传的结果,敦煌的壁画、雕塑等,也主要反映的是佛教艺术。敦煌壁画最早的确呈现出印度味很浓的西域风格,但中国汉晋以来的线描造型、以形写神等优秀的艺术手法,很快就和西域传来的印度佛教艺术相融合,“逐步形成了基于敦煌特有的历史文化积淀、时代思潮和审美意趣基础而创造出来的敦煌壁画造型艺术体系。这种体系和流派,其实就是外来艺术的种子,在中国土地上发育生长,接受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阳光雨露的抚育滋养后,开放出来的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民族风格的绚丽花朵。”(第94页)
虽然敦煌艺术的本质是佛教艺术,但古代艺术家在创作敦煌壁画时,为了宣扬佛教,引导人们信佛,就要画出普通百姓看得懂、又喜欢看的画面。“所以佛经故事画均以现实生活中不同时代的各类人物、动物、植物、衣冠、服饰、各种器具用品、各类人工建筑设施和自然生态环境来构成多种多样的社会生活场景。”(第95页)在塑像方面,北魏孝文帝改制后,“中原汉式衣冠风行于北方,南方‘秀骨清像’的艺术风格也一并传入敦煌,因而,敦煌早期彩塑也发生了南方化的改变。”(第104页)
3.提供了莫高窟编号的新材料
说到莫高窟的洞窟编号,此前一般的出版物中都是492个洞窟,莫高窟北区考古中又发现了243个,从而成为现在的735个。实际上,这中间的变化我们并不清楚。最早为莫高窟编号的是伯希和,后来又有甘肃官厅、张大千的编号。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和成立初期的“1943-1944年,史岩和李浴又在张大千编号的基础上编了一次,共计437号”。(第49页)段文杰等到敦煌后,除临摹壁画外,还于1947年下半年到1948年四五月间,进行了洞窟测量和洞窟内容调查工作。在调查中发现,以前对洞窟的编号很不一致,各位编号者多是根据自己的需要编的,其取舍标准不同,如张大千在编号时,有些“耳洞”(大洞里套的小洞)没有单独编号,“其实有些耳洞的内容比较完整,有独成一洞的价值。”“再加上新发现的被沙淹没的洞窟,总数变成469个,这是当时的情况。至60年代,配合崖壁洞窟加固工程进行考古清理时,又发现了一些洞窟,总的编号达到492个。那个时候,给洞窟编号是根据艺术价值和有无文献资料来确定的。在莫高窟的北区还有不少空闲的洞窟,里面没有艺术遗迹和文献资料,于是被判定为过去僧人和画工的居所,所以没有编号。”(第49页)通过本书的记述,我们对莫高窟的编号更加清晰了,尤其是知道了从469个到492个的变化,丰富了敦煌研究院院史的内容。
4.敦煌艺术与新疆石窟的联系
敦煌石窟是佛教东传的产物,而佛教从印度发祥后通过中亚、阿富汗、西域再到敦煌,即敦煌石窟与新疆境内的石窟联系最为密切,段先生一直想探究和比较。1975年,段先生曾与关友惠、马世长、潘玉闪、祁铎等赴吐鲁番、库车考察。1984年,段先生又与关友惠、孙国璋、李云鹤等赴新疆考察,对新疆各处石窟做了比较充分、全面的考察,想“从多角度的比较中来研究敦煌文化艺术”(第234页)。通过考察,段先生认识到,“由于新疆位于古代我国中原、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及希腊这几个重要东、西方的文明中心和文化艺术发祥地之间,自然地就成为这些中心向外扩散、辐射其创造成果的交汇处和集散地。而印度的佛教艺术传播到这里时,也必然要同这些因素混合起来。再加上当地审美追求的影响,就形成了这种新疆高昌、龟兹、焉耆地区特殊的艺术现象。在柏孜克里克、西克辛、雅尔湖等处壁画中可以看出似有敦煌壁画某些痕迹,汉风影响明显。克孜尔石窟和库木吐喇等处虽然也受到汉风的影响,但在人物造型上又有犍陀罗艺术的印痕。”(5)段文杰《敦煌是我生命的全部——段文杰回忆录》,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81-182页。
由此可知,段文杰先生不仅重视敦煌的石窟艺术,还注意与新疆地区的石窟进行比较。正如段先生自己所说,“我在观看新疆壁画时,比较注意与敦煌壁画进行比较,通过比较,对敦煌艺术个性的认识也就更明确而深刻了”(6)段文杰《敦煌是我生命的全部——段文杰回忆录》,第182页。。
5.敦煌石窟与印度佛教艺术的关系
作为敦煌艺术史家的段文杰,不仅重视敦煌与周边新疆石窟的比较,而且非常重视佛教发祥地印度的石窟艺术,尤其是将敦煌石窟艺术与印度佛教艺术的比较研究。他不仅推荐研究院的青年学者赴印度德里大学学习梵文和石窟考古,积极促成敦煌研究院与印度英迪拉·甘地国家艺术中心的合作,联合主办“中印石窟艺术学术讨论会”,还亲赴印度考察。1991年11月考察印度时,段先生为考察印度的佛教艺术,曾游览恒河。因为“恒河是印度文化的诞生之地,释迦传播佛教时讲的许多故事都与恒河有关,九色鹿救溺人的故事据说也是发生在恒河。”他不仅观察恒河两岸的一些古建筑,还注意到“河中有许多印度民众,男男女女在沐浴、洗衣,还看到几个白衣男子在岸边空地上料理荼毗(7)荼毗,音tu pi,佛教用语,指僧人死后火化。,就是佛经上说的香水荼毗,也就是人尸火焚。这块场地后面耸立着一排排高楼,里面都住着上了年纪的老人,意思是等待上天堂。”这一现象引起了段先生的深思,他马上“联想到敦煌壁画中送老人入住墓茔的画面,原来老人等候升天是印度风俗,由此可见佛教对中国艺术影响之深”。(第250页)
鹿野苑是印度笈多王朝晚期的佛教寺院遗址,唐代玄奘到印度取经时曾在此修习过佛典。鹿野苑博物馆不仅藏品丰富,而且最重要的是藏品风格多样,“有早期佛教的本土朴实风格,有受希腊影响的犍陀罗风格,还有笈多王朝的印度民族风格”。(第252页)参观孟买的佛教石窟时,发现这里人物造像的身姿不论男女都呈S形。段先生从而联想到,孟买佛像的“这种动态,对敦煌的佛教雕像和壁画人物体姿有一定影响”。(第252页)由此可知,文化与文明的交流与交融是各民族、各文化都需要的。
阿旃陀石窟是印度最重要的石窟,也是世界佛教艺术上最有影响的石窟。“阿旃陀石窟规模巨大,一个洞窟的大小相当于敦煌石窟的几个大,且石质坚硬,修建不易”,是段文杰先生等赴印度考察的重点。他们用了三个多小时,观览了29个洞窟。(第253页)通过大概的浏览,段先生发现阿旃陀石窟的“壁画里不仅表现了宗教题材,世俗社会生活也是其创作的重要内容”,如宫廷生活、山林田园、风俗小景、战争场面、音乐舞蹈、骑象出行、乘船出海等都有所表现。“所以它不仅有艺术价值,也有历史价值,对东方各国的佛教艺术有重大影响。”(第254页)
作为敦煌石窟艺术研究专家和敦煌研究院的掌门人,段文杰先生特别注意观察阿旃陀石窟和敦煌石窟的联系与区别。段先生在浏览中观察、比较了二者的区别:第一,在石窟形制方面,“阿旃陀多为马蹄形廊柱大殿,而敦煌早期为中心柱窟和多层楼阁或塔,汉式阙形龛,倒斗顶殿窟,窟顶华盖式藻井。唐代设须弥坛、背屏、围栏等,更具宫殿式”。第二,在飞天造型上,“阿旃陀为天歌神、天乐神头顶圆光,身托云彩。敦煌早期为西域式飞天与羽人合成飞仙,头无圆光,继而天宫伎乐与飞仙结合”。第三,在绘画技法方面,“阿旃陀主要用明暗衬托法,而敦煌主要用层次晕染法”。第四,在壁画的裸体表现方面,“阿旃陀人物裸体形象较多,男性肩宽腰壮,强健有力;女性则丰乳大臀,眼大唇厚。敦煌裸体较少,多是裙袍裹体”。第五,在塑像和供养人画像方面,“敦煌石窟中有大量供养人画像,其中不少是等身大像、超身大像”,“而阿旃陀则少有供养人画像和题名”。段文杰先生虽然是走马观花式的观察,但由于其深厚艺术素养和学术功底,将敦煌和阿旃陀两大石窟艺术的相似和不同之处已经比较明显地勾勒了出来。
通过这些具体的分析比较后,段先生还注意到了一个更加重要的不同,即“敦煌是东西文化的交汇点,阿旃陀则不具备此特点”。(第254-255页)
三
为什么本书比较客观、真实?成为一本实事求是,不拔高、不虚美的优秀传记呢?首先,作者段兼善也是一位艺术家,供职于甘肃画院,曾担任甘肃画院副院长。长期与父亲生活在一起,对父亲的工作、生活、交往,乃至喜怒、爱好等比较了解,能够写出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父亲。如1998年,段文杰从敦煌研究院院长的岗位上退下来后,段兼善老师就将父亲接到兰州,与他们一起生活。段文杰虽然离开了敦煌,但他在莫高窟生活、工作了50多年,可以说他将一生都献给了敦煌,所以常常会在睡梦中惊醒。据段兼善记述:“他经常梦见自己置身于三危山下的莫高窟中,半夜醒来就喊着要去看洞窟。怕他夜里起身会摔倒,我在他床前放了一张长沙发,每天夜里我都在沙发上睡觉,这样他有动静我就知道。”(第275页)
其次,段文杰先生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即“他习惯看书时查资料、做卡片,处理公务时留存记录,写日记也是他常年坚持的习惯。”段兼善说:“我每每翻看父亲的日记、资料卡片和工作笔记都敬佩和感动不已。”(第253页)这些卡片、日记成了兼善老师写作的基本素材,所以在阅读本书时,会感到其材料扎实,脉络清晰。
再次,从2001年开始,段文杰先生开始写回忆录,初定书名是《情结敦煌》,并在台北《艺术家》杂志2002年第7期至2003年第2期连载过8期。初稿完成后,都是段兼善帮助整理,并由兼善老师的夫人史葆龄录文。史葆龄也为了照顾段先生的生活并为段先生的回忆录录入文字,提前退休。当20万字的初稿完成后,段兼善“竭力帮父亲查阅日记、笔记、文章和信件……经过修改校对后的第三稿,被父亲定名为《敦煌之梦》。”(第283-284页)本书中的部分内容就是根据段先生的回忆录或根据回忆录改写的。这说明,段兼善的创作是有基础的,有缘由的,有依据的。
另外,为了研究段文杰,我提出从整理段文杰先生的书信开始,并得到了段兼善老师的大力支持。他将段先生所有的信件分类整理后全套复印。我让学生录文后打印出来,再请段兼善老师审阅订正。段兼善老师对已有的段文杰先生的书信、照片等都很清楚,也多次地阅读、思考。
正是因为段兼善老师掌握许多第一手的材料,所从事的专业又与其父一致,尤其是他又有一个常人无法做到的“孝心”,对父亲的工作充分理解和尊重,愿意为父亲、为敦煌、为敦煌学,保留一份珍贵的历史记录,并为此竭尽全力,所以才有了我们能看到的这本《敦煌人生:我的父亲段文杰》。
四
当然,作为一本人物传记,本书还有提高的空间,现将笔者阅读中的问题提出,供段兼善老师修改时参考。
《敦煌人生:我的父亲段文杰》除了段兼善老师的亲历外,主要是根据段先生的日记、笔记和学术论文写成。但有时候计划不如变化,由于段先生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会有许多临时的、甚至意想不到的突发情况而打乱其计划,还有一些临时插进来的会议、接待、出访等,也会改变段先生的安排。如1991年12月下旬,从印度考察后,段先生一行回到国内。“12月31日,父亲和史苇湘返回敦煌途中,在兰州参加了甘肃省敦煌学会成立大会。父亲被推举为会长,名誉会长为吴坚。姚文仓、于中正、樊锦诗、李永宁、齐陈骏、颜廷亮、强宗恕、周丕显为副会长。父亲向与会者汇报了这次访问印度的情况。”(第256页)实际上,甘肃省敦煌学学会成立大会并不是12月31日召开的,而是12月24-25日在兰州召开的,当时段先生还在印度,并未亲自出席会议。笔者曾参加了本次会议并参与了前期的会务工作。会议报道中专门说明,“正在国外访问的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同志也委托有关同志祝贺成立大会的召开。”(8)张先堂《团结协调队伍 开拓深化研究——甘肃敦煌学学会成立大会综述》,《敦煌语言文学研究通讯》1992年第1期,第14页;张先堂《甘肃敦煌学学会成立大会在兰州举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1992年第1期,第32页。会议选举的甘肃敦煌学学会领导名单也与段兼善老师的记述略有差异,正确的名单及排序(均以姓氏笔划为序):顾问:史苇湘、金宝祥、陈绮玲、赵俪生、常书鸿;名誉会长:吴坚;会长:段文杰;第一副会长:姚文仓;副会长:于中正、马文治、齐陈骏、张炳玉、张鸿勋、李永宁、周丕显、康明、颜廷亮。(9)《甘肃省敦煌学学会领导机构名单》,《敦煌语言文学研究通讯》1992年第1期,第12页。甘肃敦煌学学会的领导,除学者外,还有部分相关部门的管理者。吴坚当时任甘肃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敦煌研究院首席顾问,陈琦玲当时任甘肃省人民政府秘书长(随后任甘肃省副省长),姚文仓当时任甘肃省委宣传部部长,于忠正当时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马文治当时任甘肃省文化厅副厅长(分管文物工作,随后成立甘肃省文物局时,又兼任省文物局局长),张炳玉当时任甘肃省文化厅厅长,康明当时任甘肃省社科联副主席。
另如1993年“8月下旬,香港大学主办了‘第34届亚洲及北非国际学术会议’,父亲和孙儒僩、李永宁、施萍婷、谭蝉雪、张学荣,还有西北师范大学的学者刘进宝、马英昌也应邀参会。香港学者饶宗颐主持会议,父亲和各位学者先后发表了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第264页)
1993年8月在香港召开的“第34届亚洲及北非国际学术会议”,段先生原计划是参加的。会议邀请了敦煌研究院段文杰、孙儒僩、李永宁、施萍婷、李正宇、谭蝉雪、张学荣7位学者,当时任教于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笔者和历史系研究世界史的马英昌老师也在邀请之列。在甘肃省外事办公室办理相关手续时,由于西北师范大学的我们两位和敦煌研究院的7位学者是参加同一个会议,所以省外办就编为一个组团参会,并由段文杰先生任团长。段先生向大会提交了《临摹是一门学问》的论文。但段先生在1993年初由于胃癌而做了肿瘤切除手术(第263页),可能是考虑到身体,后来段先生决定不赴香港参会了。当时由于各种原因,在出发前还没有拿到签证,李永宁先生带大家从兰州乘车赴广州,我从兰州去北京办理签证。在北京办签证时很不顺利,在朋友的帮助下,我还给香港大学的会议工作人员打电话,希望给予协助。我报的名单就是段文杰团,工作人员马上说段先生不来了。我拿上签证后直接飞广州,晚上到达广州,入住中山大学,次日由姜伯勤先生带领一起坐火车赴香港。会后,敦煌研究院李永宁先生在会议纪要中说:“我院被邀请与会的段文杰、李永宁、张学荣、孙儒僩、谭蝉雪、李正宇等七位学者,都安排在‘敦煌研究’会,其中除段文杰先生因病未能赴会外,其余六位都在会上宣读了论文。”(10)李永宁《五洲学者聚香江 亚非研究遍寰宇——“第三十四届亚洲及北非研究国际学术会议”简记》,《敦煌研究》1993年第4期,第9页。敦煌研究院专家提交的7篇论文都在《敦煌研究》1993年第4期发表,敦煌组其他的论文由饶宗颐主编为《敦煌文薮》下“第34届亚洲与北非研究国际学术会议敦煌组论文专集”,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于1999年出版。(11)收入本书的文章作者是:姜伯勤、高明士、项楚、郑阿财、张涌泉、荣新江、陈国灿、刘进宝、方广锠。另有未参加会议的唐耕耦、府宪展二位的札记和书评各一篇。饶宗颐先生在“编后记”中说:“由于第34届亚洲与北非研究国际学术会议没有出版全部论文计划,提交本次大会敦煌组的论文,本拟在《九州学刊》发表,并按《学刊》要求补入札记、书评各一篇。由于种种原因,现改以《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丛刊》的形式出版。限于本刊的中文形式,提交大会的英文论文只能割爱;而遗憾的是有些中文论文在我们征稿前已交其它刊物发表,不能再在本丛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