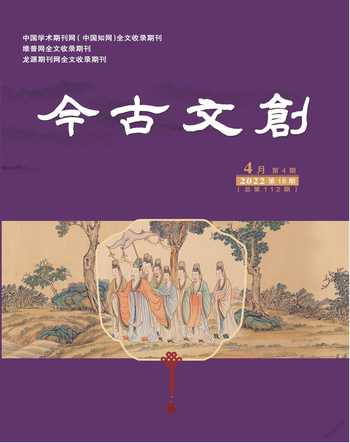论格非农民身份和知识分子立场的交叉写作
【摘要】 格非是一位同时兼具农民身份和知识分子立场的作家,农民生命中真实和充满“重量感”的特质给了格非从“外部进入”的力量,同时人文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精神、强烈的批判意识和深切的社会关怀又促使格非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上通过文学创作向公众传递有价值、有深度的观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特质在格非的身上由矛盾冲突走向交叉融合。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一方面使人们更加准确地理解格非作品的本质,另一方面也促使人们对当代其他拥有农民身份和知识分子立场写作的作家给予更多的关注。
【关键词】 格非;农民身份;知识分子立场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16-0032-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16.010
格非是一位同时兼具农民身份和知识分子立场的作家,这两种特质都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以往对格非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他的知识分子叙事上,而对于格非的农民身份以及这两种特质在他创作中表现出来的矛盾、对立和超越关系却缺少相应的关注。格非也曾在多次采访和演讲中提到过相关问题,他认为自己出生在江南的一个小村庄,而且父母都是农民,所以不可能采取一个纯粹知识分子的立场去思考问题,相反农民特质对于他的创作可能更加重要。可见,格非的创作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叙事,而是农民身份和知识分子立场相互交叉融合的双重写作。那么,格非的农民身份是如何对他的创作产生影响的?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特质在格非的作品中又是如何融合发展的?
一、格非的农民身份
格非1964年出生于江苏省丹徒县,从小生活在农村,父母都是农民,接受的亦是乡村教育,直至上大学才走出农村。格非和众多乡土作家一样,“有农村生活经验,对农村、農民有扯不断的情感记忆和牵挂,出生地的文化作为集体无意识沉淀在他们头脑深处”。①
首先,农民会真实地看待这个世界,不会给一个事物包上“玫瑰”的色彩。格非的农民特质让他对客观世界始终保持提防的态度,能在乌托邦的美好幻想中看到其背后潜藏的危机,能在保持客观冷静的同时又不失为这个世界提供意义的初衷。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以一个家族三代人近一个世纪以来发生的故事为线索,呈现了乌托邦母题在近代乡土中国的传承和变异过程。张季元、秀米、谭功达、郭从年追求的都是类似于大同世界的“桃花源”梦,“天地圆融,四时无碍。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洵然有尧舜之风。就连家家户户所晒到的阳光都一样多”。②但是格非的农民特质让他撕开了理想的面具,直接将赤裸裸的人性拷问呈现在读者面前。“完美的乌托邦成为人性最大的讽刺”,③因为乌托邦本身就不具备现实的土壤,与趋向利己主义的人性天然矛盾;而且想要一个偌大的社会按照既定的轨道运转,并保证社会成员都能自觉遵守最高道德标准,就必须有国家机器和强制措施的力量做保证。而一旦如此,个体的个性和自由便受到了更高意识形态的压制,乌托邦所谓的超越性意义也就丧失殆尽了。格非不同于纯粹的知识分子,他的血液和基因中有着农民纯朴、简单、真实的一面,所以才能在面对看似美好的假象中保持着冷静客观的态度,才会不遗余力地揭开这个世界和人性的伪饰,寻求个体本真存在的超越性意义。
其次,格非的农民身份让他看待城市和知识分子时有一种“外部进入内部”的力量和视角。这也让格非与以“大众、写作者和知识分子的经验,也包括一般的社会、网络和媒体生活”④为代表的公众意识之间拉开了距离。那些始终生活在城市里的纯粹知识分子,因为身陷在城市的包围中,反而看不清城市本身。而格非有过乡村背景,所以他在看待城市和知识分子时便有了距离感和陌生感。这种距离感让他跳出了自己熟悉的圈子,不被城市人和知识分子身份的光环所迷惑,反而自觉地去揭示这些人生存的困境,探索人精神的解放。这种思考集中体现于他1996年创作的《欲望的旗帜》中。这部小说以在上海举办的哲学学术会议为线索,会议云集了全国哲学界的高级知识分子,然而名震国内外的贾兰坡教授在会议前夕跳楼自杀;师兄宋子衿因人格分裂被送去精神病院;就连比较正常的曾山也因长期失眠而变得焦虑郁结,其他各种专家教授更是丑态百出,他们虚伪、丑陋、道貌岸然,却冠之以社会良知。这些代表社会道德规范最高水准的知识分子,似乎早已放弃了对于真理的探求,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利益奔忙,每个人都陷在自己欲望的围城中无法自拔。格非虽然本身就是集教授、学者和作家为一体的典型的学院派知识分子,但农民特质给了他从外部进入的力量,使他不会“当局者迷”,不会沉迷于知识分子和城市人的身份洋洋得意,反而对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对那些被欲望包裹失去灵魂的知识分子、对人的心灵栖息等问题保持高度自觉的思索,并将人“动物化”的极端形态淋漓尽致地揭示了出来,以迫使他们逼近本真的存在。
最后,那些一直在城市中长大的原子化的个人,他们秉持着的是“我就是我,我愿意为自己付出,而不愿意有付出”的观念,生活和存在都变得特别轻,个人化的程度也越来越深。但是在格非的身上可以看到一种农民与生俱来的重量感,这是他过去乡村生活的经验传承,也是整个农村价值文化在他身上的凝聚和投影。格非的童年记忆中充满了暴力、倾轧、欺骗,甚至是死亡,但是他从未放弃对生活和存在的希望,他同样赋予了笔下的人物这样的品质。《望春风》中的主人公赵伯渝从小就失去了母亲,父亲也上吊自尽,孤苦伶仃地在儒里赵村长大,出现在他生命中的光芒少得可怜且转瞬即逝,但是他从未放弃过希望,坚韧地维持着自己的生命。格非塑造了这样一种个体存在的积极意义,就是希望能引起人们对生命厚度的关注。生命的重量是个体存在的支撑,个体存在的后面背负的是更大的责任。活着的信仰、坚韧的性格、抗争苦难的精神、永不停歇地追寻希望的力量才是生命的本质,也是人存在的终极意义。
二、格非的知识分子立场
格非于1981年考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1985年毕业留校工作, 2000年跟钱谷融教授念完博士,同年调往清华大学任教,是集教授、学者、作家为一体的典型的学院派知识分子。高校的环境和氛围不仅让格非奠定了深厚的中外文学研究基础和高超的理论素养,也让他一直处于学术思想交锋的前沿,使他的思考具有了相当的密度和纵深感。
首先,格非的作品贯穿了他对历史问题独立思考的精神。他前期以形式的创新将思考的重点引向了历史的深层结构。
格非后期还将历史与知识分子这两种因素结合到一起,塑造了一批试图创造历史却以失败告终的知识分子“边缘人”群像,展现了知识分子与历史的对话,建构了知识分子永远的精神史诗。格非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始终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努力向下挖掘,破除传统意义上象征着客观、真实和必然性的历史意识形态,形成自己独立的史观并将这种思考传递给大众读者。
其次,格非中后期的作品都始终保持着对现代化强烈的批判意识。格非2016年发表的《望春风》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了儒里赵村在时代变迁中的流变与消失。格非站在知识分子的超越性立场上才能看到现代化带来的种种便利背后的复杂问题。他呼吁现代人退回自身的场域以找到日益衰竭的审美创造力、健康的人格和自然饱满的情感;通过艺术的净化陶冶疲惫的心灵,实现自我的完善。格非并不是提倡阻断现代化的进程,而是站在现代社会审视者的角度,揭露现代化进程给人带来的消极影响,借此为大众敲响警钟并塑造一种超越的理想和参照。
最后,格非对诸多问题的思考和批判都源自于他对社会的深切关怀。格非是一名人文知识分子,他不仅有良好的学术素养和文化底蕴,还有独立的价值观念和深切的社会责任感。格非关怀底层民众的生存困境和知识分子的精神焦虑;关怀农村在现代化冲击下的现状和城市过快生活节奏带来的负面影响;关怀道德和良知的何去何从,也关怀事实和理性的社会效用……面对种种问题,格非认为需要分别具备向前看和往回看的视野。“向前看”即通过展望未来创造新的希望,对乌托邦的寄托也是格非为心灵救赎提出的一剂良药。虽然乌托邦具有虚幻、缥缈的性质,但是它可以启迪并帮助人们重新认识自己的生活,能让人们超越现世的苦难和苍白,带给他们坚韧、永恒、救赎的力量。格非试图通过乌托邦书写来提供一种纯真、美好的生存之境,以期达到人存在的本质。这是格非站在一名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对人的生存困境提出的解答,也是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精英始终在坚守的信念。“往回看”即通过追溯历史了解过往。因为只有通过这种追溯,人们才能了解乡村和城市之间既抗拒又迎合的复杂关系,才能明白现代人在城乡巨变中持有的矛盾心态。格非在《望春风》中通过回顾江南一个小村庄五六十年代至新世纪的流变,表现了对中国当代乡村命运的担忧并提出了“返乡”的主题,并借由精神层面的返乡深入到了乡土中国,进而叩问个体在当下的精神存在。总之,“向前看”帮助人们建立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往回看”让人们了解过去人与自然合一的愉悦状态,两者交相融合,共同构成了格非对社会现状的解决方案。
三、农民身份和知识分子立场的交叉写作
农民和知识分子这两种身份、立场、价值观念在格非身上交叉出现。农民生命中真实和充满“重量感”的特质给了格非从“外部进入”的力量,同时人文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精神、强烈的批判意识和深切的社会关怀又促使格非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向公众传递有价值、有深度的观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特质在格非的身上由矛盾冲突走向交叉融合,并呈现出一种特有的复杂性。
格非农民身份与知识分子立场的关系在他八九十年代的创作初期表现为矛盾与冲突。此时的格非一直处于思想交锋的前沿,他在华东师范大学接受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深受西方现代主义尤其是博尔赫斯的影响,以形式实验去传递哲思。而且格非从农村初到城市,此时的农民身份让他感到尴尬和自卑,所以这一阶段的格非更看重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而农民身份则是隐性的。作者在他前期创作的很多短篇小说中填充了不少乡土元素,却没有真正地去刻画乡土中国,仍以空缺、重复、设疑的先锋形式探索为写作重心,就连小说中的农村和农民也都有一种迷蒙、恍惚、混沌的不真实感。因为他们更多的是作家笔下的人物和工具,没有真正融入作品的灵魂,而且服务于小说整体风格的塑造,始终被压抑于叙事内核的底层。显然,此时格非的农民身份与知识分子立场明显被割裂为两个层次,两者相互抵触,给作品带来一种分离感、陌生感和为实验而实验的稚嫩感。
随着创作的转型,格非开始将先锋的品格和传统的审美经验融合到一起,不仅走出了前期形式实验的牢笼,而且慢慢地发掘到了农民特质对于自己的重要性。虽然这一时期的格非已经有了知识分子精英的身份,而且在城市生活的时间也远远超过了他在农村生活的时间,但是农民特质并没有被稀释消磨,相反变成了他生命中最核心的部分,也是他灵魂深处最坚定的支撑。格非幼时在农村积累的生活经验、立场观念以及他接触过的那些鲜活的人都穿透了时间的磨砺再次回到了作者身边,并幻化为他最重要的精神内核。格非在此基础上创造出了一种农民身份和知识分子立场交叉融合的写作模式,这是理解他作品的关键,也奠定了他在当代文学史上不可忽略的重要地位。这种写作模式在格非后期的小说中屡见不鲜,比方说在《人面桃花》和《山河入梦》中,格非时而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上,表达对那些为实现人类社会大同梦而不懈奋斗的改革者的欣赏以及对乌托邦精神的真切希望;时而农民身上清醒、现实的特质又让他对乌托邦这一命题产生怀疑,并清楚地看到了那些知识分子空想家失败的必然性;与此同时他又忍不住对此产生淡淡的哀伤,对知识分子愿望无数次落空导致的迷茫、困惑、痛苦表示同情;最后农民骨子里那种不轻易妥协的倔强与又屡次支撑他“于绝望中寻找希望”。格非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不遗余力地记录了知识分子在苦難中仍不抛弃希望和理想的信念以及对生命存在意义永恒探寻的宝贵品格。
格非从农村进入城市并成为了一名高级知识分子,他身上既有农民所代表的乡土精神,又有知识分子所象征的都市文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特质在格非身上交叉呈现并表现出了一种特有的复杂性。格非虽然人在都市,却是一名都市里的“乡下人”,他与城市之间始终有一种无法跨越的距离感,相比之下乡村淳朴的感情回忆和残存的人间真情更值得格非懷念留恋,也正是这抹挥之不去的乡土情结成就了他的《望春风》。小说最后“我”和春琴重返儒里赵村的情节,既是作者对那曾经存礼存情的已逝故土的怀恋,也是对现代化冲击下崩盘瓦解的乡村的一次深情的回望,更是拯救现代无根漂泊之人的一味良药。但是格非却无法真正地远离城市回农村做一名农民,一方面是城市生活已经渗透蔓延到了他生活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是格非深知现代化是历史的必然结局,势不可挡,返乡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格非的生命中留存着一抹挥之不去的乡土情结,同时都市文明也已在他体内根深蒂固,二者杂糅在一起,构成了小说创作主体的内在张力,也是格非小说叙述最重要的特质。
总之,格非是一位同时兼具农民身份和知识分子立场的作家。他的视野、思想、理念使他在理性层面上具有了知识分子的素养;同时他的思维、情感、价值观念却更富有农民的品格。而且这种情况并非个案,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一系列作家如李洱、韩少功、叶炜、范小青等等同样如此,他们在面对乡土精神和都市文明时也都表现出了一种犹疑、复杂的精神状态,这是中国社会在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必然结果,也是后现代、后先锋新话语体系复杂性呈现的根源所在。而格非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重大建构意义就在于此,他阐释了对这个世界的深刻理解,给人的存在提供了意义和初衷,建构起了农民与知识分子交叉写作的成功范例,并为人们思考现代社会转型带来的文化效应提供了新的视角,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注释:
①王庆:《现代中国作家社分变化与乡村小说转型》,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页。
②格非:《人面桃花》,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15页。
③刘茉琳:《告别乡土的心灵史——格非小说考》,《当代文坛》2018年第4期。
④格非、林培源:《“文学没有固定反对的对象”——格非长篇小说〈望春风〉访谈》,《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6期。
作者简介:
田馨,女,汉族,山西孝义人,山西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