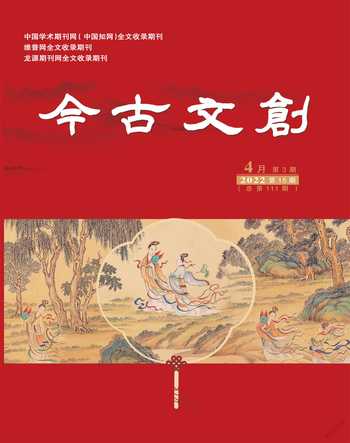救赎与狂欢:晚清至民初的上海中元节图景
任熹
【摘要】中元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各地中元节的习俗各有不同。本文结合各种资料,就晚清至民初的上海中元节图景进行了勾勒,尝试对其中表现出的中国民俗与中国文化关系的意义进行分析。
【关键词】中元节;上海;晚清;民初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15-0052-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15.016
近代以来,社会激荡,民俗变异。上海1843年开埠以后,经济发展迅速,各地移民纷纷涌入,也成为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的一大窗口。在时代激荡之年代,作为中国传统节日之一的中元节在华洋杂处的上海呈现的是怎样的一种面貌,诸种报纸杂志及札记等材料,为人们提供了一些或可深究的蛛丝马迹。由于行文仓促又不便实地考察,本文仅以流通较广的一些常见材料为主,尝试勾勒出晚清至民初的上海中元节图景,并试析其背后的中国民俗与中国文化关系的意义。
一、善堂、公所与药商
明清以来,盂兰盆会这类活动已经成为中元节时各地常见风俗习惯,上海地区亦然。嘉庆二十二年之《松江府志》称:“中元祀先,以素羞往。僧舍设斋,为人荐亡,夜施水灯,曰‘盂兰盆。若月晦值大尽日(俗谓‘地藏开眼),僧人以纸造为白莲船,乡人或以钱米、絮楮少许寄纸船中,祈生西方,夕作梵事而焚之。儿童积瓦甓为塔,至夕亦燃灯,效呗声为戏,或于长衙点放地灯,一行多至数十盏。”[1]3《上海风俗古迹考》盂兰盆会条有曰:“旧时上海于七月十五日各寺举行盂兰盆会,亦名太平公醮,放水陆莲花灯。家祭多以素食,说是祖先亦当去看盂兰盆会之故。祭赛如清明节”,又引倪绳中《南汇县竹枝词》“太平公醮建中元,萧鼓声声水陆喧。到处盂兰盆会盛,新开焰口照孤魂。”[2]
而当时相关祭祀活动,又不仅仅限于寺庙,胡祥翰《上海小志》称“社会旧俗,无论大小各业,每年于七月间举行盂兰盆会,俗称‘打醮。”[3]43善堂为中国传统慈善机构,通常行收养孤儿、赠衣施药及处理无主尸体等善事,在晚清的《申报》上,亦不乏见善堂中元节赈济孤魂之告示,并列举捐款人之姓名。
而上海外来人口众多,多有同乡会组织,如宁波之四明公所,广州府、肇庆府之广肇公所等,这些乡帮公所亦多举行祭祀客死上海的同乡的打醮仪式。[4]而其中最为盛大及引人瞩目的,乃属广肇公所所办的醮会,因其陈设奢华,常见诸报章引为奇事:
山庄盛会
节届中元。粤东诸董事就新闸广肇山庄循例建醮坛,施放瑜伽焰口。十四五六三日复在山庄正厅及侧厢等处陈设古董书画并支搭布棚于甬道之畔。摆列各种戏剧任人游观。第一日观者络绎于途,颇为拥挤,直至深宵露冷,尚有纨扇轻罗。昨日阴云敝天,雨师率驾以致游人绝迹,可以门设雀罗矣。
此处“瑜伽焰口”指的是一种施食饿鬼的一种仪式,上海及周边地区也将中元节所施行的救赎仪式称为“放焰口”。由此则新闻可知,当时广肇山庄之打醮为期三天,除了一般的救赎仪式外还摆设了许多古董字画,并上演戏剧供游人观赏。
除了同乡公所之外,一些行业公所也会举办孟兰盆会,如药业公会:
会设盂兰
南市各药材行向例于中元节前后各筹金资就药业公所建盂兰盆会,并置一切彩色灯景在各处游行。今届仍循襄例。定于本月二十日起招延羽士设坛禳解,并雇令彩匠扎成各色纸灯以备临时之用,想届时一定有一番热闹也。
其事《上海小志》中略有记载:“当时药业中人借醮事以舉赛灯会,游行于南市一带……沪上药行共有十余家,每家必有一起,每一起中间必有龙舟台阁,奇灯异彩,靡不夸富斗丽。”[3]43
无论是广肇公所也好,药业公会也好,所置办的盂兰盆会并非仅仅只有请僧道做法事而已,广肇山庄不仅上演戏剧供游人观赏还布置有古董字画,药业公所也是“借醮事以举赛灯会,游行于南市一带”,这本来是阴气森森的“鬼节”在赛灯斗富的氛围下,染上了不少娱乐色彩,而这一特质,在城隍巡游上,更为明显了。
二、从祭厉到巡会
除了盂兰盆会放灯、打醮及放焰口之外,中元节时上海县的城隍亦会出巡至邑坛祭祀,亦称“三巡会”。所见的材料中,多数把“三巡会”追溯到明初,并多有传说色彩,如1928年的《上海城隍庙》:“明太祖怒杀邑人钱鹤皋,碧血化成白色,尸体如生;太祖怕他变为厉鬼,为防患未然,就下令天下城隍,赈济厉鬼,而册封钱鹤皋为鬼头。惟其钱鹤皋是上海人,所以上海城隍的出巡尤其奉命唯谨。”[5]29此种说法的由来,大概跟当时国家开始制定定期祭祀厉坛的规章有关,《明史》称:
洪武三年定制,京都祭泰厉,设坛玄武湖中,岁以清明及十月朔日遣官致祭。前期七日,檄京都城隍。祭日,设京省城隍神位于坛上,无祀鬼神等位于坛下之东西,羊三,豕三,饭米三石。王国祭国厉,府州祭郡厉,县祭邑厉,皆设坛城北,一年二祭如京师。里社则祭乡厉。后定郡邑厉、乡厉,皆以清明日、七月十五日、十月朔日。[6]
厉坛,即祭祀义冢之地,义冢则为专门安葬无主的尸骨之地,这每年三次的城隍出巡祭祀厉坛以安抚并威慑无主孤魂的行为,其本质上与上述的盂兰盆会和打醮仪式是相似的。只不过通常老百姓清明节和寒衣节一般祭祀自家祖先,只有在中元节才会祭祀无主孤魂。到了同治十年的《上海县志》,才看到“三巡会”的说法:“清明日祭邑厉坛,县牒城隍诣坛赈济各义冢幽魂,名‘祭坛会,舆从骈集,直四五里。亦名‘三巡会,以七月望、十月朔皆有此举也。”[1]7-8
晚清至民初的三巡会的具体情况,在《申报》和《上海城隍庙》中都能找到介绍。出巡之前一般需要进行模拟判案及卜定出巡的路线之活动,称为“排堂”:
在未出巡之前三日,例有排堂之举。那时大殿中支搭临时暖阁一座,中设公案。会首就将城隍抬出,端坐正中,各项书吏,以及马快、皂快、红班、军健等(此项人役,大都为前清县衙署之办事人员及当差)站立两边,一一参拜后,值堂人即将会中犯人名册恭谨呈案,由传事人逐一唱名,解差立在中庭逐一回禀……鸿胪唱罢,城隍便标判某坛派某司赈济,某坛派某司赈济(因出巡时尚有新江司、长人司、高昌司、财帛司等随巡)。最后,就是颁发出巡路由,进某门出某门,其次序以抽签为定。而所经之路,则由会中主事人支配牌示。[5]29
因出巡的节日是临时卜定,所以每年的路线都不会相同,不过从1896年至1902年(1897年《申报》没有刊出巡游路线)5年的路线来看,巡游路线的先后顺序不一定,5年路线都必然经过广福寺、县署、参府署、副府署、海防厅,从(小)南门或东门出城,经过佛阁、紫霞殿及附近的码头,再沿河道或至北而南,或先西后北至西门外的厉坛,祭祀完毕后由西门入城回庙。从这些路线来看,可见除了官署和某些寺庙地位特殊之外,水路,特别是码头和西门至东门的河道尤为重要。
而结合期间《申报》上的报道,亦可大致还原出当时中元节城隍出巡的具体情形,如1899年这一则报道:
中元会景
节会路由已纪昨报。昨日届期虽秋雨霏霏,时落时止,而好事之徒兴致仍复不减。午后钟鸣三下,由邑庙抬偶像出,旗锣伞扇,簇簇生新。更有皇命马、对马、鼓吹马、执事马多至六十余骑。无耻荡妇,复装扮罪犯,招摇过市。此外阴皂隶、十锦牌、大肚刽子手、沿途弹唱之类凡息所奉,奉禁者亦皆明目张胆而为之。以致观者如云,途为之塞。苏松大兵备道宪曾观察曾委县主簿孙少尹率役在邑庙前巡逻,见有年轻艳妇装扮罪犯上无顶小轿者,著即拘拿。然差役咸付之不见不闻,无一拘拿到案者。岂阳世官威,竟不能施之于阴曹木偶吁?上海县王大令保甲总巡□明府则派差沿途照料,以免滋生事端。典史周少尉更命驾至西门外邑厉坛致祭。晚间复进程,香火千家明灯万盏。通街小巷观者仍不减日中。
中元节当日下午三时,城隍神和四司从邑庙抬出,巡游队伍除了常见的旗锣伞扇外,还有扮演不同角色的数十匹马骑,还有扮演阴间皂隶、刽子手者,尤为引人瞩目的是还有年轻女子,浓妆艳抹扮作犯人,在1897年的报道中,更言有俊秀孩童打扮奢华扮作小犯人之类。到了厉坛祭祀完毕之后,巡游队伍晚上再由西门入城。而再参之《上海小志》的说法,当时“盖醮事临了之夕,各业中人例必提灯游行,随以锣鼓,后复舁以无数纸锭,沿途焚化,云以赈济乏祀孤魂”[3]43,加之各处又有赛灯之风,故上文言“香火千家,明灯万盏”。
既是如此热闹场景,“观者如云,途为之塞”也是意料之中,人一多自然容易滋生事端,如以下这一报道所记:
節会肇祸
前日本邑城隍神率同四司循例出巡,神驾诣西门外厉坛赈济无祀孤魂毕。道经万升桥畔,有崇海侯之锣夫陈凤芝在旁伫立,过车牢班之中马执事飞驰而来,陈躲让不及,被撞倒在地,践伤手足。虽经友人剑负而归、多方排忧,恐尚难免饶舌也。又会过小东门时有胡飞云鞋子店伙计某甲在旁观看,以神前所扮之五鬼状貌奇丑,恶言相向,遂尔口角后,因所扮之判官劝散。甲回店后忽发急症,竟至命登鬼录。店主无奈备棺收殓,一面函追尸属来申。惟邻右人等莫不互相传播,以为神灵显赫。殊不知是亦偶逢其□耳。愚民之愚,一何可笑。
巡游之弊端围观者易被巡游之车马所伤则为其一,期间如鞋子店伙计某甲与参加巡游者这般容易产生冲突则为其二。
巡游造成种种混乱,政府想要进行有效的管理却苦无办法,而祭祀厉坛的行为,因为在国家合法的祭祀系统之下,也不能禁止,仍需要派小吏前去致祀;面对县署开坛设醮之旧例,即使发令禁止游行的官员也照常进行。
三、民俗、商业与中国大众文化
1901年,广肇山庄因迫近商业区而被迫搬迁,之后广肇公所也没有再举行中元醮会[7]。而1900年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之时,中元节城隍巡游依然一派歌舞升平之象,即使是慈禧、光绪尚未返京的1901年中元节,似乎也没啥大的变化,无怪当时报人在略述中元会景之后,会有“亦思两宫尚未回銮,三辅更遭饥馑,内忧外患相继而来,我辈臣民正合忧虑警惕,奈何一逢令节,即游玩无度,几于举国狂欢呼”之议。1919年8月10日,《申报》以《三巡会复活》为标题报道民国成立后首次“三巡会”的准备情况。此后,沪城“三巡会”因战争、政治气候等原因时断时续。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各类迎神赛会一度禁止,不久,以城隍庙为首的一系列巡会又死灰复燃,并持续到抗战前[8]。声势浩大的“三巡会”每年举行三次,花费应该不菲,之所以能坚持如此长时间,应该与其背后的组织者和赞助者有关。可惜的是,虽然可见有的研究称三巡会“经费来源一是庙产收入,二是各香会集资,三四信徒募捐” [9],有的称“组织三巡会的经费是向各行各业和同乡公所分派筹集”[10],却都没有给出材料依据。而稍微考察城隍庙的历史不难发现,其日渐繁荣成为游人商人云集之处的过程,也是“三巡会”逐渐走入人们视野的过程。乾隆中叶,豫园从潘允庵处被收购辟为各行业公所,成为城隍庙之“西园”,并自此“游人也渐多,商人竞设店肆,竟然也成为集市了”[11],到1928年,火雪明编著《上海城隍庙》之时,吴灵园在《序二》中称“南市之有城隍庙,犹租界之有永安、先施、新新三公司”[5]21,足以见其商业中心之地位。另外,当时东园还有布业公所、荳米业公所、酒馆公所,而东园则归钱业(即钱庄之行会组织)管理。[5]12-14则城隍庙周边的商户行会公所成为三巡会的经费来源,可能性非常大。
中元节所行之盂兰盆会本应是祭祀先祖亡灵和救赎孤魂的救赎仪式,单就巡游驱鬼、祭祀孤魂的行为而言,在其功能上与当代香港地区打醮时“祭大幽”(俗称“大士出巡”)的仪式十分相似,都可以理解为是保护社区从危险“阴”的处境重新回到“阳”的处境,确认社区和群体界限之仪式。[12]
而这些民俗仪式在晚清之上海却呈现出争奇斗艳、人鬼神同乐的面貌。这样鬼节变佳节之现象,既非上海一地之风俗,更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这样的节日除了给予民众从平日的艰苦谋生中暂时解脱出来的娱乐之外,还意味着什么?或可与近代早期(16至19世纪)在欧洲大量出现的狂欢节现象进行比较。新文化史之领军人物彼得·伯克(Peter Burke)在《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中,以狂欢节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大众文化的结构与社会变化等问题。[13]上海的三巡会与欧洲近代早期的狂欢节一样,都是脱胎于民俗节日,后来成了民众获得娱乐的日子。狂欢节多颠覆日常知识,游行群众化妆成国王、教士、圣人或者普通人[13];三巡会则尝试以现世官府模式模拟城隍审判犯人,除了各种仪仗和小吏跟班之外,处于社会边缘的妓女也加入游行队伍之中,使得巡游更有吸引眼球的因素,因而也难免引起如《申报》撰稿人这样的文人的不快,但显然无论是参与者还是围观者的大多数都不觉得其中有何不妥。
赵世瑜先生在《庙会与明清以来的城乡关系》一文中,列举了清代河南封丘、山东潍城等地的事例。[14]165他认为这类巡游活动带有傩祭的驱鬼驱邪内容,带有原始的狂欢精神,且与等级分明的官方祭祀活动不同,是种打破等级和阶层的全民狂欢。[14]116-144或许,可以更深一步说,晚清至民初上海三巡会的图景,为人们展现了传统民俗与中国文化中的狂欢精神在民众中的契合。
参考文献:
[1]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 上[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
[2]顾炳权.上海风俗古迹[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3]胡祥翰.上海小志·上海乡土志·夷患备尝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4]蔡丰明.上海都市民俗[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
[5]火雪明.上海城隍庙[M].上海:青春文学社,1928.
[6]张廷玉.明史 · 卷五十[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林辉锋.旅沪广帮与近代上海社会文化的多元化[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41.
[8]苏智良,姚霏.庙、信仰与社区——从城隍信仰看近代上海城隍社区[J].社会科学,2007,(1):68.
[9]郑土有,刘巧林.护城兴市:城隍信仰的人类学考察[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10]何益钟.老城厢:晚清上海的一个窗口[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1]上海通社.上海研究資料[M].上海:上海书店影印本,1984.
[12]蔡志祥.打醮——香港的节日与地方社会[M].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0.
[13]彼得·伯克.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M].杨豫,王海良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4]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M].香港:三联书店,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