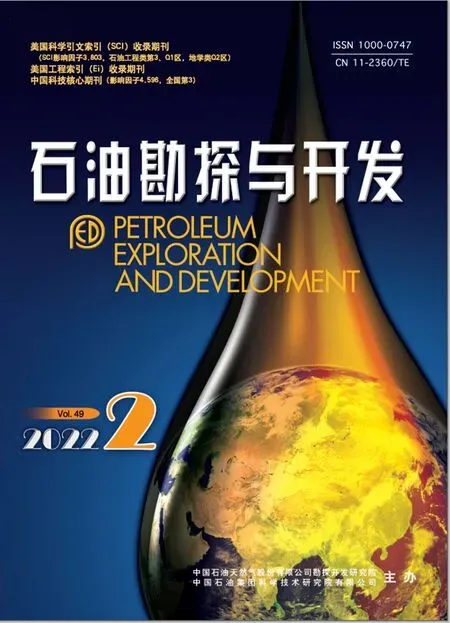不同渗透率砂岩岩心在纳米流体中的渗吸特征
邱润东,顾春元,薛佩雨,徐冬星,谷铭
(1. 上海大学力学和工程科学学院,上海 200072;2. 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上海 200072;3. 上海市能源工程力学重点实验室,上海 200072;4. 苏州纽迈分析仪器股份有限公司,苏州 215163)
0 引言
中国非常规油气资源十分丰富[1],压裂技术是目前低渗、致密、页岩油气开发的主要技术手段:通过压裂施工在储集层中形成缝网,增大井控储量,提高渗流能力。渗吸排油方式在非常规油储集层渗流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影响开采速度和效率的重要因素。
国内外学者在渗吸机理[2-5]、渗吸效果及影响因素[6-9]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如 Cai等采用分形理论研究了渗吸机理[10-11];杨正明等[12]设计了不同尺度岩心渗吸物理模拟实验方法,研究了致密储集层渗吸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并构建了水驱油渗吸作用的定量评价方法;Aghabarari等[13]验证了再渗吸对天然裂缝性储集层的显著影响,提出了再渗吸作用下基质岩块泄油过程的控制方程;Andersen等[14]建立了水、油和岩石相互作用的渗吸流动模型,讨论了黏度对渗吸的影响,黏性耦合有利于动态渗吸,但不利于自发渗吸;Qin等[15]建立了动态多孔介质孔隙网络模型,分析了三角形、正方形和圆形等不同孔隙截面形状对渗吸效率和渗吸速率的影响。王敬等[16]建立了裂缝性储集层渗吸模型,通过模拟发现动态渗吸中岩心下部和缝面附近区域含油饱和度低,与裂缝垂直的两个水平端部含油饱和度最高;Cheng等[17]、Wang等[18]利用倾斜毛细管模型研究了双重介质油藏和气藏的自发渗吸,考虑了重力、动态接触角和裂缝宽度等因素,得到了液体渗吸的最大位移及运移时间。
大量实验表明,表面活性剂能降低界面张力,提高渗吸排油率(岩心排油量占总含油量的百分比)[5,19],但表面张力减小,毛细管力降低,渗吸动力将从毛细管力主导逐步转向重力主导,不利于渗吸。Schechter等[20]提出用逆键数作为判断转向的依据,逆键数大于5,以毛细管力为主导;逆键数小于1,以重力为主导;逆键数为1~5,两者同时发挥作用。
纳米流体提升渗吸排油效果是近年来的重要研究方向[3,21],与表面活性剂体系相比,纳米流体复配体系具有润湿转性与降低表面张力的协同效应[3]。Xu等[3]比较了非离子表面活性剂、纳米SiO2流体与两者复配的纳米流体的渗吸排油效果,在盐水基液中渗吸之后,岩心在 3种体系中的渗吸速率和排油率进一步提高了2%~4%。
采用核磁成像技术研究纳米流体的渗吸排油效果可直观地反应排油动态特征。Zhao等[7]测试了碳纳米流体渗吸的核磁成像图,发现纳米流体的渗吸排油率随时间的延长不断增加,而清水在渗吸达到一定程度后渗吸排油率基本保持不变。Zhou等[22]采用核磁成像记录了致密砂岩岩心中纳米流体和盐水的渗吸过程,结果显示纳米流体中岩心的渗吸可以不断向岩心中心推进,而盐水中岩心的渗吸不具备该能力。
核磁共振成像作为检测渗吸过程中原油分布特征的重要手段,结果更直观、可信,但在相关机理研究方面的应用还较少。本文针对目前渗吸实验岩心移位核磁成像实验存在表面油相损耗与空气吸附,进而影响实验结果精度的问题,改进了实验方法,设计出原位核磁成像渗吸实验方法,采用该方法开展砂岩岩心在纳米流体中的渗吸实验,记录了整个纳米流体渗吸过程中原油的实际运移图像,同时结合砂岩岩心的物性、渗吸过程中的驱动力变化,分析了不同渗透率砂岩岩心在纳米流体中的渗吸特征。
1 实验设计
1.1 原位核磁成像渗吸实验方法
目前渗吸实验岩心核磁成像的基本方法是在渗吸过程中定时将岩心取出,再放入岩心夹持器进行成像测试,测试完成后再放入液体中继续渗吸过程,如此反复完成整个实验。该方法可以得到岩心渗吸图像的变化过程,但岩心移离原渗吸环境后,表面油相的损耗和空气的吸附,都会对渗吸排油效果和渗吸过程中的驱动力变化产生一定的影响,进而影响实验结果的精度。为解决该问题,本文对实验方法进行了改进,设计出原位可视化实验方法,即整个测试过程中,使饱和油岩心始终浸泡在纳米溶液中,并定时对浸泡在纳米溶液中的岩心采集核磁成像数据,整个实验过程中渗吸作用没有中断,也不存在油相损耗和空气吸附现象,故不会对渗吸排油效果和渗吸过程中的驱动力变化产生影响。具体实验流程为:①将饱和油的岩心放入渗吸瓶中;②向渗吸瓶内倒入配制好的SNFQ(上海大学石油中心自制纳米流体)纳米液;③将渗吸瓶放入核磁共振仪的线圈内,启动软件自动定时采集T2(横向弛豫时间)谱和成像数据,同时通过渗吸瓶上部的玻璃管刻度(精度0.05 mL)直接读取排出油体积。
1.2 实验设备与材料
实验设备:包括MesoMR12-060V-I型核磁共振仪、BH-Ⅱ型抽空加压饱和实验装置、SL-2型岩心孔渗联测装置及若干玻璃渗吸瓶。实验中核磁共振仪开口朝上,便于渗吸瓶放置。
液体材料:①普通水配制纳米流体选用SNFQ,主要用于优选纳米流体浓度实验。②重水配制纳米流体,主要用于渗吸核磁实验。实验用重水由北京百灵威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纳米粉体选用亲水粉体NP(上海大学纳米中心生产),粒径范围10~20 nm。在重水中添加纳米粉体,搅拌均匀,配制成粉体质量分数为0.15%~0.30%的纳米液,最后用超声波分散15 min。③油样由新疆克拉玛依油田原油与柴油按1∶4配制而成,密度0.835 mg/L。
实验岩心:①非均质双层岩心由北京石大融智科技有限公司提供;②人工砂岩为实验室自制无磁岩心;③天然岩心取自克拉玛依油田。所有岩心均为亲水或弱亲水,孔隙度 10.20%~36.20%,气测渗透率为(0.013~1 663)×10-3μm2(见表1)。

表1 渗吸岩心的基础参数
1.3 实验内容
根据岩心渗透率的大小,设定不同的实验环境与实验程序,开展3个方面的渗吸实验:①室温(20 ℃)条件下,选用 Y3—Y5号岩心,开展岩心在普通水配制纳米流体中的渗吸实验,重点研究纳米流体浓度对渗吸排油效果的影响,确定合适的纳米流体浓度;②室温(20 ℃)条件下,选用 Y1—Y2和 Y7—Y12号岩心在重水配制纳米流体中浸泡15 h,再升温至80 ℃浸泡5 h,采集不同时间段的排油量、岩心原位核磁成像和T2谱数据;③选用 Y6号岩心在重水配制纳米流体中连续浸泡8 d,间隔4 h采集核磁成像和T2谱数据。
2 纳米流体渗吸排油效果影响因素
2.1 纳米流体浓度
Y3—Y5号岩心弱亲水,渗透率为(1 100~1 250)×10-3μm2,饱和原油后,Y4号岩心首先在清水中浸泡16 h,随后放入质量分数为0.5%的纳米流体中浸泡8 h;Y3和Y5号岩心分别在质量分数为0.2%、0.3%的纳米流体中浸泡16 h,渗吸排油效果如表2所示。

表2 不同浓度纳米流体的渗吸排油效果
实验结果显示,Y4号岩心在清水中的渗吸排油效果很差,仅有少量油花,渗吸排油效率仅1.0%,再放入质量分数为0.5%的纳米流体中后,渗吸排油效率大幅提升至61.1%;Y3号岩心在较低质量分数纳米流体中的渗吸排油效果较差,渗吸排油效率为6.8%,而Y5号岩心在较高质量分数纳米流体中的渗吸排油效果较好,渗吸排油效率达51.4%。
纳米流体能大幅改善渗吸排油效果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其能大幅降低油水界面张力,减小渗吸排油阻力。图1为不同质量分数纳米流体与油水界面张力的关系,可以看到纳米流体质量分数越高,界面张力越低,但当质量分数超过0.3%后,浓度继续增加,界面张力降幅变缓。综合考虑渗吸效率和实验的时间成本,这里取质量分数0.3%为最优值,其余实验均采用该浓度数据。

图1 纳米流体质量分数与界面张力的关系
2.2 岩心渗透率与实验温度
室温(20 ℃)时,在质量分数为 0.3%的纳米流体中,浸泡Y1—Y2和Y7—Y12号岩心15 h,再升温至80 ℃浸泡5 h。图2为部分(5块)岩心渗吸排油率与渗吸时间的关系曲线,可见:①当实验温度为20 ℃,渗吸时间为0~15 h时,渗吸排油率曲线初期(0~4 h)上升较快,随后升幅趋缓。②岩心渗透率越高,孔径越大,渗流阻力越小,渗吸初始排油时间越早。根据实验观察记录,Y1号岩心渗透率为 1 663×10-3μm2,开始排油时间为0.5 h;Y8号岩心渗透率为16.5×10-3μm2,开始排油时间为 1.0 h;Y9、Y11 号岩心渗透率分别为 8.15×10-3,0.08×10-3μm2,排油较慢,开始排油时间为2.0,3.0 h,初始排油时间与渗透率负相关。③当实验温度为 80 ℃,渗吸时间为 15~20 h时,可以看到,温度升高后,原油黏滞阻力和界面张力降低,所有岩心的渗吸排油率均明显提高,温度升高有利于渗吸排油。

图2 原油渗吸排油率与渗吸时间的关系曲线
定义单位时间的渗吸排油率为渗吸速率,图3为原油渗吸速率与渗吸时间的关系曲线:①当实验温度为20 ℃,渗吸时间为0~15 h时,渗吸速率的变化与渗吸排油率有所不同。岩心渗透率越高,渗吸速率上升的时间越短,Y1与Y7号岩心渗吸2.0 h后渗吸速率开始下降,而其他岩心渗吸速率明显开始下降的时间均约为4 h。具体原因为Y1与Y7号岩心渗透率较高,渗吸阻力小,排油速度快,较早达到排油高峰;其他岩心渗透率较低,渗吸阻力大,排油速度较慢,起点晚,达到排油高峰时间长。②当实验温度为80 ℃,渗吸时间为15~20 h时,同样可以看到,温度升高,原油黏滞阻力和界面张力降低,渗吸速率上升,但原油黏滞阻力和界面张力降低后,虽在一定时间内打破了孔喉中油水的受力平衡,促进了原油的排出,但随着时间的延长,孔隙内流体受力重新逐步趋于平衡,渗吸速率下降。

图3 原油渗吸速率与渗吸时间的关系曲线
2.3 岩心孔径
图4为室温条件下,Y1、Y8、Y11号岩心在质量分数为0.3%的纳米流体中不同渗吸时间的T2谱曲线。曲线与横轴之间所包含的面积代表岩心内的含油量,弛豫时间轴代表岩心孔径大小,弛豫时间越长,岩心孔径越大。由图可见:①Y1号岩心T2谱曲线右峰最高,对应弛豫时间为117 ms,岩心储集空间以大孔径孔喉为主,随渗吸时间延长,T2谱曲线仅右边最高峰发生明显下降,说明渗吸排油过程主要在大孔径孔喉内进行。曲线左峰几乎没有变化,说明小孔径孔喉内的油难以动用。②Y8号岩心T2谱的最高峰对应弛豫时间为72 ms,岩心储集空间以中孔径孔喉为主,随渗吸时间延长,T2谱曲线最高峰发生大幅下降,左峰有一定程度的下降,说明渗吸排油过程主要在中孔径孔喉内进行,小孔径孔喉内的油也得到动用,因该类孔喉所占比例较小,故贡献有限。③Y11号岩心T2谱曲线左峰最高,对应弛豫时间为 0.9 ms,岩心储集空间以小孔径孔喉为主,随渗吸时间延长,T2谱曲线仅左边最高峰发生明显下降,渗吸排油过程主要在小孔径孔喉内进行。曲线右峰仅有微小变化,说明岩心中的较大孔径孔喉虽有渗吸排油发生,但不是主要场所,其主要作用为渗流通道。

图4 Y1、Y8、Y11号岩心不同渗吸时间的T2谱曲线
3 不同渗透率岩心渗吸排油特征
3.1 渗吸排油外观特征
图5为室温条件下,Y10、Y3号岩心在质量分数为0.3%的纳米流体中的渗吸排油外观照片,Y10号岩心渗透率 0.71×10-3μm2,Y3 号岩心渗透率 1 250×10-3μm2。可以看到浸泡 0.5 h后,两块岩心的顶端均有油滴出现,侧面未见出油;继续浸泡 80 s,Y3号岩心的油滴渗出,并出现缩颈、断裂现象,而 Y10号岩心液滴无明显变化;继续浸泡128 s,Y10号岩心油滴变化甚微,且仍未排离,而 Y3号岩心在原来位置又有油滴析出。说明岩心渗透率高,排油驱动力强,阻力小,形成了排油通道,为顺向渗吸;岩心渗透率低,排油驱动力弱,阻力大,形成排油通道需要更长的时间。

图5 Y10、Y3号岩心渗吸排油外观照片
3.2 岩心内部原油渗吸运移特征
图6为室温条件下,Y1、Y6、Y8、Y10号岩心在质量分数为0.3%的纳米流体中不同渗吸时间的核磁共振图像。图中纳米流体由重水配制,无核磁信号,表示为蓝色;原油核磁信号表示为红色,颜色越深,含油量越高,信号越强。图中由红色到绿色、浅蓝再到深蓝,表示信号由强变弱,也代表了含油量从高到低的变化过程。

图6 Y1、Y6、Y8、Y10号岩心不同渗吸时间核磁成像图
Y1 号岩心渗透率为 1 663×10-3μm2,Y6 号岩心渗透率为 527×10-3μm2,可以看到,这两块岩心图像变化具有相似的特征,表现为渗吸开始阶段岩心整体图像信号减弱,然后岩心底部核磁信号减弱速度较快,中上部边缘核磁信号减弱速度较慢,说明渗吸时底部原油排出比中上部快。Y1号岩心在1 h开始出现底部信号明显减弱,20 h后呈倒三角状图像,而Y6号岩心在4 h开始底部信号略有减弱,20 h后出现指状图像。说明岩心渗透率越高,该现象越容易发生。这主要是因为岩心渗透率越高,孔径越大,对亲水岩心而言,原油的黏附性弱,孔喉壁面摩擦阻力小,油所受浮力与毛细管力足以克服孔喉壁面摩擦力、重力的影响,驱动油向上运动,油的驱动受浮力与毛细管力共同主导。
Y8号岩心渗透率为16.50×10-3μm2,Y10号岩心渗透率为0.71×10-3μm2,其变化特征与Y1、Y6号岩心不同,表现为岩心四周核磁信号减弱速度快,随后逐步向内部延伸,说明渗吸时岩心四周原油先排出,然后内部原油向四周扩散排出(Y10号岩心下部浅蓝色亮条为渗吸排油仪器在放置岩心过程中残留的胶状物形成,不影响实验结果)。低渗透岩心孔径小,毛细管力相对较大,孔喉壁面摩擦力也较大,油所受浮力与毛细管力不足以克服孔喉壁面摩擦力、重力的影响,难以驱动油整体向上运动。油主要在毛细管力的作用下沿距离最近的岩心壁面排出。
3.3 双层岩心内部原油渗吸运移特征
岩心浸泡于相同的液体环境中,不同孔道中的油滴受力类型相同,但作用力的大小不同,表现出的渗吸特征存在较大差异。为了保证完全相同的渗吸环境,对比不同渗透率岩心的渗吸排油特征,选择双层非均质人造砂岩岩心(Y7号)开展实验。两层岩心采用不同粒径石英砂在相同的条件下制备而成,其润湿性完全相同。双层岩心左半部分渗透率为 300×10-3μm2,右半部分渗透率为 1 500×10-3μm2。
室温条件下,Y7号岩心在质量分数为0.3%的纳米流体中的核磁共振成像如图7示。可以看到,岩心右侧渗透率高,孔隙空间大,含油多、信号强,浸泡过程中,图像信号自上而下由强变弱,表现为原油从岩心上端渗吸排出的特征;岩心左侧渗透率相对较低,孔隙空间相对较小,含油相对较少、信号相对较弱,浸泡过程中,图像信号从岩心四周向内部逐渐由弱变强,表现为岩心四周原油先排出,然后内部原油向四周扩散排出的渗吸特征。

图7 Y7号岩心不同渗吸时间核磁成像图
3.4 长时间连续渗吸排油特征
图8为室温条件下,Y6号岩心(渗透率为 527×10-3μm2)在质量分数为 0.3%的纳米流体中连续浸泡8 d,在不同时间点采集的核磁成像图。可以看到:①渗吸初期(1~3 h),岩心整体图像信号明显减弱,表现为岩心四周原油先排出,然后内部原油向四周扩散排出的渗吸特征;②渗吸中期(3~96 h),3~15 h时底部信号相比顶部开始减弱并逐渐明显,到24 h时出现“指状”特征;同时岩心核磁信号整体减弱,但岩心下边缘更明显,部分油滴具有从下往上运移的特征;③渗吸后期(大于96 h),岩心核磁信号整体进一步减弱,下部减弱程度明显大于上部,油滴自下而上运移特征更明显。可见中等渗透率岩心渗吸特征初期与低渗透岩心类似,中后期与高渗透岩心类似。分析原因认为中等渗透率岩心,经过纳米流体的长时间浸泡,岩心润湿性得到改善,亲水性增强,同时油水界面张力降低,该作用随浸泡时间的延长,不断由岩心表层向岩心内部推进,打破整个岩心的三相界面平衡,进而改变原油渗吸排出的方式。

图8 Y6号岩心长时间连续渗吸排油核磁共振成像图
3.5 纳米流体的渗吸排油机理
纳米流体具有将亲油岩心转变为亲水岩心或进一步增强亲水岩心的亲水性的能力,同时纳米流体具有降低表面张力的作用,能够在三相界面处形成结构分离压力剥离原油[23]。岩心浸泡在纳米流体中,油、纳米液和岩心首先趋于三相界面平衡,纳米流体排出油滴,三相接触线向前移动,并暂时形成动平衡。纳米流体在降低油水界面张力的同时,将亲油孔壁转化为亲水(或增强亲水孔壁的亲水性),从而改变毛细管力的作用方向(或增大毛细管力),另外,在纳米颗粒形成的三相界面处结构分离压力的作用下,界面平衡被打破,三相界面线再次向前移动,形成新的三相平衡,如此反复,逐步将原油排出岩心。可见纳米流体提高渗吸排油效果,是亲油岩心的润湿性反转(或增强亲水岩心的亲水性)、降低界面张力与产生结构分离压力共同作用的协同效应。故岩心浸泡在纳米流体或表面活性剂中,随时间延长,原油渗吸排油率具有缓慢上升特征,而浸泡在清水中时,渗吸容易达到平衡,排油率不再增加[3]。
4 结论
纳米流体能大幅降低油相的界面张力,改善渗吸排油效率,浓度越高,界面张力越低,渗吸排油效率越高,但浓度达到一定值后,渗吸排油效率增幅趋缓;温度升高,有利于降低原油黏滞阻力和界面张力,提高渗吸排油率。
岩心渗透率相对较高,渗吸时底部原油向上运移排出,且岩心渗透率越高,该现象越明显,表现为顶部排油特征;岩心渗透率相对较低,渗吸时岩心四周原油先排出,然后内部原油向四周扩散排出,表现为四周排油特征;中等渗透率岩心渗吸排油特征初期与低渗透岩心类似,中后期趋同于高渗透岩心,但在纳米流体长时间作用下,岩心亲水性不断增强,油水界面张力不断降低,渗吸中后期也会出现顶部排油特征。
——以东营凹陷沙河街组为例
——以双河油田Eh3Ⅳ5-11岩心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