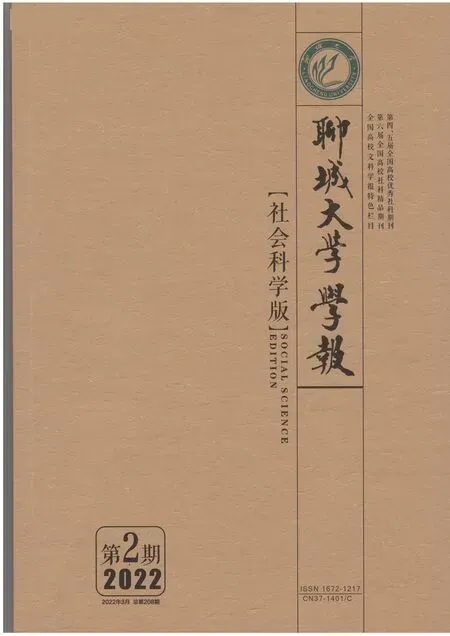张载理学体系探究
——以《正蒙》为中心
李 腾
(聊城大学 哲学系,山东 聊城 252059)
作为北宋五子之一,张载的哲学思想极富创造性和启发性。但如何理解和评判张载的哲学思想一直都是研究者们所面临的一个难题。围绕着张载思想,从宋明以来到近现代,各种争论和分歧一直存在。引发争论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张载文字精炼又晦涩,容易让人产生歧义;另一方面则在于研究者们对张载哲学的理解总是处于某种特定的理论框架之下,这些既定的框架能将张载哲学中的一些隐微之处揭示出来,但也不可避免地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对张载原有之意的遮蔽。
一、研究张载思想的两个既定框架
前人对于张载思想的研究主要有两条进路,一种是程朱理学的“理气论”,以程朱之“理”来考量张载的“太虚”,引发了“太虚是否是理”的讨论;另一种受西方哲学影响,用本体-现象这一范式来分析张载哲学,将张载理学体系定位为“太虚本体论”或“气本体论”。
(一)程朱理气论
宋明以来,学人们受到程朱理学的影响,一般是从程朱理学的视角来看待张载哲学,比如将张载哲学中非常重要的概念“太虚”与程朱之“理”对举。自程颢“自家体贴”①“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参见王孝鱼点校:《传闻杂记》,《河南程氏外书》卷第十二,《二程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24页。出天理之后,经过朱熹的进一步阐发,“理”逐渐发展成为理学的最高范畴:理为形而上者,具有绝对性、普遍性、秩序性等特质。但同时,气是程朱理学的另一重要概念,与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无形迹的形而上之理相比①“理未尝离乎气。然理形而上者,气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岂无先后!理无形,气便粗,有渣滓。”“盖气则能凝结造作,理却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若理,则只是个净洁空阔底世界,无形迹,他却不会造作;气则能酝酿凝聚生物也。”参见黎靖德编:《理气上》,《朱子语类》卷第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页。,“气”属于形而下,气与理之间是倚傍和挂搭的关系。由此可知,在程朱的思想中,理与气是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的关系。在这种理气论的视角之下,程朱对张载的“太虚”多有指摘:理与气分别为形而上者与形而下者,而张载以“太虚”为道体,本应是属于形而上者,但却又与形而下之气浑沦一体,以此程朱认为张载未能分晓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分,对道体的见解也不够深刻②“如以太虚太和为道体,却只是说得形而下者。”参见黎靖德编:《张子书二》,《朱子语类》卷第九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532页。。朱子进一步认为应当以“理”取代太虚,而张载的太虚与理之间的差别还是非常明显的。但在朱子之后,明清很多注家反对程朱以“理”代替张载的“太虚”,而主张“太虚”就是“理”,如明代刘儓注解“太虚无形,气之本体”时直言“太虚,理也”③刘儓:《新刊正蒙解》,引自林乐昌:《正蒙合校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9页。,清代冉觐祖言“太虚,专以理言”④冉觐祖:《正蒙补训》,引自林乐昌:《正蒙合校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4页。。可以说,宋明以来学人们的主要分歧在于“太虚是否是理”。显然这样一种讨论仍是在理气论的框架之下进行。⑤在朱子之后诸家对张载“太虚”的诠释基本都跳不脱朱子的理气论。杨儒宾认为自朱子诠释《正蒙》以来,以理体气用的方式诠释张载气论,是众多服膺程朱理学之儒者的共同见解。明代中晚期兴起反朱子学思想,朱子的理气论成为反对者们对治的目标,但对治者与被对治者却共同形成了包含正反两方面论证的内在论域,使得反对者们也是绕着理气关系展开辩论。参见杨儒宾:《检证气学——理学史脉络下的观点》,载《汉学研究》第25卷,2007年第1期,第247-281页。
(二)本体与现象
近现代以来,由于西方形而上学的影响,很多学者从本体与现象二元的结构来理解张载哲学。例如牟宗三认为太虚为形而上的本体,他主张“太虚神体论”,以形而上的本体与形而下的现象来理解张载太虚与气之间的关系⑥参见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1册,台北:正中书局,1968年。;丁为祥、林乐昌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思、借鉴了牟宗三的思想,丁为祥认为太虚非气,太虚与气是本体与现象的关系⑦丁为祥:《虚气相即——张载哲学体系及其定位》,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4页。;而林乐昌则认为“太虚即气”中的“即”是“合”的意思,根据张载“非有异则无合”而言太虚与气是异质而非同质的关系⑧林乐昌:《张载两层结构的宇宙论哲学探微》,载《中国哲学史》2008年第4期,第78-86页。。总之,他们都主张太虚不是气,注重太虚超越的形上义。而张岱年先生则将张载视作唯物主义者,特别强调张载的“气”为物质,认为张载思想为“唯气论”或“气本论”。⑨张岱年:《张横渠的哲学》,《张载——十一世纪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张岱年文集》第4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77-117页。之后的很多大陆学者都主张张载哲学为“气本论”,他们认为太虚是气,或者认为气自有形上之体与形下之用,或者将气视作形而上的实体。虽然“太虚神体论”与“气本论”的分歧主要聚焦于“太虚是否是气”,但本质上都是从本体论的范式来讨论张载的哲学,而无论太虚是气还是非气,作为主语的太虚都是他们讨论的焦点。
无论是朱子的理气论,还是后来学者的本体与现象二分的框架,都试图从张载哲学中区分出一个超越的本体来,这一本体不同于作为现象的具体世界,而呈现出一种不生不灭、自在完满的静态特征,它不随现象世界的流变而改变自身,否则它就无法体现出本体的功能,换句话说,本体之所以被称为本体,这些都是它必然要具有的规定。这一悬隔的静态意义上的本体是否符合张载哲学的本意,仍然有诸多疑点。而若想真正地解决这个问题、消解疑点,最好的方式莫若回到张载的经典文本,“以张子之说还张子”①王植:《正蒙初义》,引自林乐昌:《正蒙合校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页。,尤其是回到张载的核心著作《正蒙》之中。
二、《正蒙》所展现的太虚-天地-人物三重结构
《正蒙》具有完整而严密的逻辑体系:起首第一篇《太和篇》,以“太虚”作为哲学的起点,给出“太虚之天”的概念,作为其本体论结构的始点;接下来从《参两篇》到《动物篇》论述阴阳交感、天地生物之道,以建立“乾元之天”和“坤元之地”,构成本体论结构的中间环节,而乾坤二元又是万物的直接化生者,由此而形成“太虚-天地-万物”的本体论结构;然后,从《诚明篇》到《王禘篇》分析人道,最后归结于《乾称篇》中的“乾父坤母”、“民胞物与”这一归旨,这是上述本体论结构的最终归宿。通过对《正蒙》结构的梳理,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张载哲学中包含的问题意识:张载为何以太虚始而以乾坤终?这对张载哲学的理解来说是一个具有结构性意义因而也是至关重要的问题。由《正蒙》的篇章结构可知,天人之道,或者更确切地说,天-地-人三才之道在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除了首篇和终篇,其余诸篇的主要内容即是三才之道:天地化生万物,是人与万物的本源,而人则能够贯通天地,与天地并立三才。亦即张载的构思更多地呈现出“太虚-天地-人物”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特征,其中“天地之道”这一环节起到一个重要的枢纽作用,而非简单的本体与现象这种二元结构。换句话说,气一元结构以及太虚与气二元结构都忽视了“天地”这个中间环节,从而只有“太虚”这个张载哲学的起点,无法真正抵达张载哲学的终点②法国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认为“形上学”是张载气论所要避免的,因此他不赞同使用形而上的“本体”来说明张载的思想;德国学者欧阳师主张张载哲学中的“气论”是包含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的双重本体论。可参看Francois Jullien.Procès ou Création.Une introduction à la pensée des lettrés chinois, Seuil, 1989;Wolfgang Ommerborn.Die Einheit der Welt.Die Qi-Theorie des Neokonfuzianers Zhang Zai(1020-1077), Amsterdam/Philadelphia,1996。陈赟也注意到西方本体论的思考范式并不能揭示张载哲学的特色。参看陈赟:《从“太虚即气”到“乾坤父母”:张载本体论思想的结构》,载《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第41-50页;《张载哲学的本体论结构与归宿》,载《江西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第5-12页。。本文认为,对“天地之道”的重视,以及“太虚-天地-人物”这一结构性的构想,才是理解张载哲学的关键,根据这一点,或许才能真正开启理解张载哲学的新路径。
(一)太虚:无法直接化生万物的“气之本体”
在许多先哲(如二程、朱熹、牟宗三等)眼中,太虚是张载哲学体系中最接近于本体概念的,就连张载自己也说过:“太虚无形,气之本体”③章锡琛点校:《正蒙·太和篇》,《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7页,第9页。,但这里的“本体”是否是在本体-现象这一形而上学结构之下来说的,依然存有疑问。因此,如何准确地按照《正蒙》文本来理解“太虚”的原意,就变得极为关键。
就“太虚”这一概念自身的性质来看,它的确很像本体,这一方面主要体现在如下两点:首先,太虚不同于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气化世界,后者触目皆是形形色色的具体事物,可感可见可触,它的实有性不容置疑,而太虚则无形无相,我们之所以知道它的存在,正是由这可见的气化世界逆推而得到,“两不立则一不可见”④章锡琛点校:《正蒙·太和篇》,《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7页,第9页。,换句话说,“今既两体各立,则溯其所从来,太和之有一实,显矣。非有一,则无两也”⑤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1页。,阴阳二气絪緼生化万物,而这个过程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它背后有一个“一”,即太虚。因此,说太虚超越于这个具体的现实世界,而具有更高层次的存在方式似乎也就理所当然;其次,正如第一点已显示的那样,太虚是气化世界之所以得以产生的本源。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太虚作为一个无形的本体来化生万物?倘若如此,就坐实了太虚的本体地位。但是,张载却明确反对这种观点,“若谓虚能生气,则虚无穷,气有限,体用殊绝,入老氏‘有生于无’自然之论,不识所谓有无混一之常”①章锡琛点校:《正蒙·太和篇》,《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8页,第8页,第8页,第7页,第9页,第9页。,如果将太虚与气(或气化世界)视为生与被生、本体与现象之间的关系,则张载的思想与他自己竭力反对的老子的思想就毫无二致,因此,太虚不能被视作为本体,恰恰是张载哲学最重要的特点之一。
与之相反,张载为太虚与气(或气化世界)之间建构了一种独特的关系,“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无之故’。”②章锡琛点校:《正蒙·太和篇》,《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8页,第8页,第8页,第7页,第9页,第9页。他以“幽明之说”来取代“有无之论”,“幽”即目力所不能及的暗处,而“明”即肉眼可见的有形世界,这两个世界如同昼夜、寤寐一样,是一体之两面,有此必然有彼,太虚无形,是气化尚未发生时的状态,但它并非是与气截然不同的超越者,而太虚本就是气,“气坱然太虚”③章锡琛点校:《正蒙·太和篇》,《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8页,第8页,第8页,第7页,第9页,第9页。,人之所以看不到太虚,是因为“人之目力穷于微”④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3页,第17页。,误以为看不到的就一定是“无”。同时,太虚中也保存着气化之理,但这一理并未脱离气而单独分化出来,而是“理气浑沦”的状态,这样一来,“太虚”概念中也就保留了诸多无法被秩序井然的理所消化的非理的一面。
总之,太虚并非是完全不同于气的本体,只是代表着气未化时的一种状态,气化世界并非由它生成。“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⑤章锡琛点校:《正蒙·太和篇》,《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8页,第8页,第8页,第7页,第9页,第9页。未化之太虚内蕴着化之潜能,气“不能不”聚散,意味着气注定要分化为二,即阳与阴,进而才形成了我们生存于其中的气化世界,也就是说,气化世界的直接生成者,并非是处于幽暗处、静态的太虚,而是已分化的阴阳二气,“游气纷扰,合而成质者,生人物之万殊”⑥章锡琛点校:《正蒙·太和篇》,《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8页,第8页,第8页,第7页,第9页,第9页。,游气,即阴阳二气,首先形成的是可以生成万物的天地。
(二)天地:连通太虚与万物的重要枢纽
张载认为,太虚是天地的本原,“虚者天地之祖,天地从虚中来”⑦章锡琛点校:《张子语录·语录中》,《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326页。。但是,“由太虚,有天之名”⑧章锡琛点校:《正蒙·太和篇》,《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8页,第8页,第8页,第7页,第9页,第9页。,既然太虚“有天之名”,为什么还要说天地从虚中来?实际上,在张载思想中,太虚之天与天地之天分属两个层次,太虚之天作为气的本原,它“莫之为而为万物之资始者,于此言之则谓之天”⑨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3页,第17页。。太虚虽名为“万物资始”,但其自身并未直接参与万物生化,所以才说它“莫之为”,其重要的特性就是“一”,即这种意义上的天并没有一个与之相配的地;而天地之天则是与地相配的气化之天,“有地斯有天,若其配然尔”⑩章锡琛点校:《正蒙·参两篇》,《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11页,第10页。。这里的天地,才是化生万物的直接参与者。而天地之所以能够从太虚之中产生,是因为神的作用。张载言“一故神(两在故不测)”[11]章锡琛点校:《正蒙·参两篇》,《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11页,第10页。,太虚虽为未化之气,但内涵不测之神,所以能从“未化之一”变化而为“两体之化”,“天地从太虚中来”正是“神”之变合不测的体现。那么,张载又是在什么意义上言说天地的呢?
1.形体意义上的天地
对于生活在大地上的人来说,头顶上的星空承载着人们无尽的想象。从古到今,这个广袤无垠又深不可测的天空一直吸引着人们不断地观测、探索和追寻。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古人通过观测,对于天体的结构形成了三种说法:盖天说、浑天说、宣夜说,[12]参看陈遵妫:《中国古代天文学简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65-175页。这三种宇宙论中,天地都具有一定的形体或形象,张载也从天象、地形的角度来言说天地。
张载曾言:“人鲜识天,天竟不可方体,姑指日月星辰处,视以为天。”[13]章锡琛点校:《横渠易说·系辞上》,《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177页。于人而言,天无法被轻易地识得,人们通常是将天所成之象视作天。从天象的角度看,天又可分为经星之天与纬星之天。经星,即张载所谓的“恒星”,指二十八星宿,经星之天就是包含二十八星宿及以上之天。日、月、五星则为纬星,五星分别以五行命名: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经星之天与纬星之天不同,区别在于它们与地的关系,张载言:“恒星不动,纯系乎天,与浮阳运旋而不穷者也;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①章锡琛点校:《正蒙·参两篇》,《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10-11页,第11页,第12页。恒星之天在地之外,而日月五星则与地不可分割。日月星辰虽为在天之象,但实际上是“积气”,其中经星及以上是五行之地气所不能触及到的地方,日月五星之天则因为地气所至,而能与地气相互推荡,浑沦为一体之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纬星之天“并包乎地”。因此,真正与地发生关联的是纬星之天,其与地气氤氲相荡而化生万物。在天地气化交感、化生万物的过程中,“道”得以呈现,因此,道即是阴阳两端循环不已的气化运动。这里可以揭示出张载言说天地的另一个角度:以道言说天地。
2.以道言说天地
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存在着以阴阳言说天道的传统,《易传·说卦》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与之相对,以刚柔言说地道:“立地之道,曰柔与刚”②章锡琛点校:《横渠易说·说卦》,《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235页,第235页。。而阴阳之实为气,刚柔之实为质,张载言:“阴阳气也,而谓之天;刚柔质也,而谓之地。”③章锡琛点校:《横渠易说·说卦》,《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235页,第235页。阴阳分立两端,而实为一体之气;刚柔并立两体,但同是一体之质,所以气可谓天道之体,质为地道之体。《正蒙》中,张载总是将气与聚散、攻取、升降、飞扬等动态的词语联系在一起,并且通过《易传》中的“氤氲”、《庄子》中的“野马”来形容气上下周流、肆意盎然、永不止息的状态④“天地之气,虽聚散、攻取百涂,”“气坱然太虚,升降飞扬,未尝止息,《易》所谓‘氤氲’,庄生所谓‘生物以息相吹’、‘野马’者与!”参见章锡琛点校:《正蒙·太和篇》,《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7-8页。,可以说,聚散、升降、屈伸、浮沉等等都是气的存在形式,气始终处于流行不已、聚散变化的过程中;与清通流动的气不同,质则意味着成形的凝聚状态。段玉裁认为“质”的引申义为“朴也,地也”⑤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81页。,说明质与有形之物有关,具有形质的意思。对人来说,有形质的万物皆能被人见闻、感知,地作为“质”的引申义也说明地并非仅仅指塊然有形的凝聚的大地,还包括生活在大地上的万物。总之,如果说气指聚散流动、变化不已的气化过程,那么质正是气化过程中形成的某种结果,本身仍处在整个气化过程之中。张载言“游气纷扰,合而成质者”⑥章锡琛点校:《正蒙·太和篇》,《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9页。,质可以作为气聚合的一种形式,本质上仍然是气,但成质之后的凝聚之气不同于清通纷扰的气。可知,《易传》和张载都以阴阳之气说明天道一气流行,聚散不已,而以刚柔之质呈现地道之殊:因为质本身具有的凝聚状态而形成纷繁复杂、各自不同的森然万物。
张载以阴阳之气言天是为了凸显天道运行不已的气化过程,同时由于天道之体始终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这其中存在着不能被人的理性和规律所掌控的向度,所以有时张载以不测之神来言天,神即是气化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无法被人加以秩序化和理性化的层面。在《正蒙》中,张载分别以神、物/形来对应天道、地道:“地,物也;天,神也。”⑦章锡琛点校:《正蒙·参两篇》,《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10-11页,第11页,第12页。“神与形、天与地之道与!”⑧章锡琛点校:《正蒙·参两篇》,《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10-11页,第11页,第12页。形不仅有名词性的形质之意,还可作为动词,指显形、著见。因为凝聚成质而可以被人感知和把捉的地道之物总是具有地方性、局限性。而天道则因始终处在屈伸聚散的状态中而能够超越形器、地方的限制,张载以神言天道的原因即在于神能够凸显出天道之不可测度,无方而无体的性质。如果说阴阳之气与刚柔之质分别为天道、地道之实,那么神与物或神与形则分别代表天道圆、地道方的本性。
3.乾坤作为天地之用
张载以阴阳之气、刚柔之质分别言天、地,但张载有时也直接以阳对应天,阴对应地①“地纯阴凝聚于中,天浮阳运旋于外”,参见章锡琛点校:《正蒙·参两篇》,《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10页。,并且对阴阳的性质进行阐述:“阴受而阳施”、“阳之德主于遂,阴之德主于闭”、“阴性凝聚,阳性发散”,②章锡琛点校:《正蒙·参两篇》,《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12页。张载以施与受、遂与闭、发散与凝聚来说明阴阳之性或阴阳之德。我们可以通过阴阳之性发现天地如何化生万物,以及它们在万物的生成过程中分别起到的不同功用。
《横渠易说》中,张载进一步分析阳施而阴受的原因:“虚则受,盈则亏,阴阳之义也。……阴虚而阳实,故阳施而阴受;受则益,施则损,盖天地之义也。”③章锡琛点校:《横渠易说·系辞下》,《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224-225页。施受既可作为阴阳之义,同时也是天地之义,这里可以看出张载以阴阳对应天地,天以阳施,而地为阴受,阳始终是充实、丰盈的,所以能不断地进取和施与,而阴则因为虚性而处于接纳、顺受的位分。由此,施受也可以与另外一对词语相互发明:健顺。在《易传·说卦》中,健顺可以作为乾坤的本性:“乾,健也;坤,顺也。”④章锡琛点校:《横渠易说·说卦》,《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236页。乾健坤顺作为天地之德主要体现在天地生物的功用上,《易传·彖·乾》云:“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⑤章锡琛点校:《横渠易说·上经·乾》,《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70页。以元配乾说明乾资万物之始⑥“《彖》明万物资始,故不得不以元配乾”,参见章锡琛点校:《横渠易说·上经·乾》,《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69页。,是万物的开端,而且乾作为“大始”,总是处于施与、创生、开端的过程中,这也意味着虽然乾元可以作为万物的“大始”,但如果只有“乾元”,并不能化育生成可被人感知见闻的万千世界。因此,《易传·彖·坤》中还提出“坤元”:“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⑦章锡琛点校:《横渠易说·上经·坤》,《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81页。与乾元资始相对应,坤元则能资生。乾元只有在坤元的顺承、接纳之后才能完成创始万物的作用。
乾与坤、神与物、气与质都是张载言说天地的不同形式,阴阳之气与刚柔之质是天地之实,而不测之神与形著之物则分别代表着“天圆地方”之性,资始之乾与资生之坤为天地之用。乾坤是天地在化生万物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品质:乾资始,而坤资生;乾主生,而坤主成。天生地养而成就万物。
(三)人物:同出一源但禀性各异
在乾元之天与坤元之地相与作用之下,万物得以生成,张载《西铭》有言:“乾称父,坤称母。”⑧章锡琛点校:《正蒙·乾称篇》,《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62页。从这个意义上说,天地可视为人与万物共同的宇宙之大父母,而人与万物则可视为天地之子。既然人与物皆为天地所生,那么人性与物性也就享有共同的形而上本原,因此性就具有了本原意义上的人物所共具的普遍之性的含义,如张载所言:“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⑨章锡琛点校:《正蒙·诚明篇》,《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21页。但人性与物性之间存在着不可不辩的差异性。虽然并存于天地之间,但人却独为“万物之灵”,《易传》中更是将人作为与天地并立的三才之一。那么,应该如何理解人性与物性之间的差异性?
张载的性论包含两个层面:一源之性与气化之性。一源之性即是“至静无感”的太虚,张载言“至静无感,性之渊源”⑩章锡琛点校:《正蒙·太和篇》,《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7页。林乐昌先生认为“至静无感”的主语为太虚,此句言说太虚的本来状态(“无形”、“至静无感”)。参见林乐昌:《正蒙合校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2页。,至静无感的“太虚”,是性所从出的本原;而气化之性则是阴阳两端之性,张载言“天性,乾坤,阴阳也”①章锡琛点校:《正蒙·乾称篇》,《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63页。,即是从两端分立的气化角度来言性,而“二端故有感”②章锡琛点校:《正蒙·乾称篇》,《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63页。,可知张载又以感言性:“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体。”③章锡琛点校:《正蒙·乾称篇》,《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63页。以感言性则意味着天性属于天用或天道的层面,所以张载才说“合虚与气,有性之名”④章锡琛点校:《正蒙·太和篇》,《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9页。,仅有太虚,性之名不可立,还要有与之相合之气。此处的虚即“由太虚,有天之名”⑤章锡琛点校:《正蒙·太和篇》,《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9页。的太虚,如果说太虚为天之体,那么气可谓天之用,这里的气即“由气化,有道之名”⑥章锡琛点校:《正蒙·太和篇》,《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9页。的气化阶段,其中阴阳两端分立,而相互摩荡。张载以太虚与气化相合而有性之名,意味着性的意涵中,既有作为渊源的太虚,又有阴阳、乾坤之性。对张载而言,太虚之天仅可谓“性之渊源”,由作为天之用的气化所形成的世界,才是万物得以生长收藏的真实境域。
人与万物皆由天地气化而生,所以人与物所禀得的皆是在气化中作为阴阳乾坤相感之“天性”。阴阳两端的变合形式纷繁复杂,因此天性在具体的下落过程中,或者说人与物在对天性的接纳中则存在着多样性。就万物各自气禀来看,每个个体所具有的气质之性都是特殊的,但这样的差异仅仅是从人物各自所禀的气质之具体内容而言的,从内容上看,气质之性代表着个体存在所具有的殊别性内容,而从形式上而言,气质之性则是“人与动物所同具的共性”⑦丁为祥:《虚气相即——张载哲学体系及其定位》,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22页。。而且广义上的气质之性不仅有才性、气性的意义,还包含生物学意义上的生理、欲望、本能等等,可以说张载的气质之性内涵告子“生之谓性”的意义⑧牟宗三先生认为宋儒所说的气质之性综括了自“生之谓性”一路下来而说的气性、才性之类,而西方如康德所说的性脾、性好、性向、人性之特殊构造、人之特殊的自然特征等都是气质之性。气质之性实是心理、生理、生物三串现象之结聚,总之,是“生之谓性”,“性者生也”两语之所示。参见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一册,台北:正中书局,1968年,第508页。。因此,人物之辨就不能仅仅通过“气质之性”来说明,从“生之谓性”的角度看,气质之性为人物所共具,非但不能体现“人之所以为人”的独特性,反而会造成“人与物等”的观念,而这是张载必然不能赞同的,张载认为人物之别主要在于“通蔽开塞”:
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开塞,所以有人物之别,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别。塞者牢不可开,厚者可以开而开之也难,薄者开之也易,开则达于天道,与圣人一。⑨章锡琛点校:《拾遗·性理拾遗》,《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374页。
人与物主要是开与塞的区别。人可开,虽然可开的程度有难易之分,但物则蔽塞不可开。所以说,人这种可开的能力才是人物之间最本质的差异。可开的能力即张载所说的“达于天道”,上达天道并不意味着以阴阳、刚柔的形式回归天地之道,实际上,人不可能完全化为天地之体,也不可能如天地之性那样神妙莫测、无心化物。这一点我们可以诉诸于常识:人何曾能似天地般恒久常存、化生万物?但是,人可以将天地之道的运行方式作为学习效法的对象,即所谓的“修人事即以肖天德”⑩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1页,第17页。,在现实生活的人伦日用中,人通过修习仁义礼智等人道的方式效法天德,进而贯通天道与地道,而这正是人不同于他物的独特性。人“秉太虚和气健顺相涵之实,而合五行之秀以成乎人之秉彝”[11]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1页,第17页。,故而有性有心:性为“成善”提供了可能性,而可感可通的心则是通往善性的途径。这一点是其他种类的动物所没有的,这也是人能够与天地鼎足而立的原因。
三、践行人道:张载理学体系的最终归宿
综上所述,张载在《正蒙》中展现了“太虚-天地-人物”这一三重结构(见下图):其中,太虚是整个气化世界的源头,但它只是气化之前、尚未分化的浑沦一体之气,并不直接生成万物,而是要通过天地达到这一结果;由于“神”的作用,太虚之气分化为代表着阴阳二气的天与地,它们絪緼而生化万物,因此,对于人及其他事物来说,天地才是直接的生成者,在这个意义上后者可被视为一种“大父母”;“万物不得不散而为太虚”,“聚而成形,散而归于太虚,气犹是气也”①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8页,第5页,第5页。,所以张载不言有无,而言幽明,因为万物即使因为死亡而散落成泥,也只不过是回归到太虚本体中,气犹是气,而并不是彻底的消亡。

这一过程是“以天言之”,即追溯人物之所以得以生的来源,而从人自身的角度来看,这三个环节为人展示了人类在两个方向上的关系结构:首先是人与太虚、天地之间的纵向的关系;其次是人与他人、万物之间的生存世界之内部的横向关系。这两个方向上的关系构成了天地之间独特个体的实存处境。
(一)人与太虚、天地之间的关系
由于太虚并不直接参与万物的化生,而是要通过天地这一环节,人类与万物才得以生成,因此,直接礼敬太虚是一种僭越,这种行为只是一种形而上学思维的懒惰,“彼欲直语太虚,不以昼夜、阴阳累其心,则是未始见易,未始见易,则虽欲免阴阳、昼夜之累,末由也已。易且不见,又焉能更语真际!”②章锡琛点校:《正蒙·乾称篇》,《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65页。佛教以空为真,道家崇无黜有,他们都将气化世界以及人间伦常视为人应当逃离或超越的虚幻之物,在现实世界之外寻求超越的意义,而礼敬太虚与佛老的这种思维方式在本质上并无二致。太虚无形无相,是一种静止的、理气浑沦的未化状态,对于它所蕴含的特性,我们只是通过已化的现实世界反推而略知一二,因此,对于它的礼敬也就只能是一种形而上的臆想。在张载的理学体系中,太虚并不能给人类世界提供意义源泉,但它仍然具备一个独一无二的功能:即太虚给气化世界提供一个最初的本源。此外,太虚还能够为人的生死谜题提供一个终极解答。气聚成物,万物散而复归于太虚,“气之聚散,物之死生”③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8页,第5页,第5页。,物之死生就如这气之聚散,聚而复散,散而复聚。因此,死亡并不意味着事物的彻底消失,而是又复为气而回归太虚,这是一个循环过程,这一点恰恰是儒家对待生死的一个独特的态度,所以张载说幽明,说往来,说聚散,而不言生灭。“知死之不亡者,可与言性矣。”④章锡琛点校:《正蒙·太和篇》,《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7页。而且,“天地之气,虽聚散、攻取百涂,然其为理也顺而不妄。”⑤章锡琛点校:《正蒙·太和篇》,《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7页。这意味着气的聚散有其自身的条理,而不会任意混杂或散乱,“故善气恒于善,恶气恒于恶”⑥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8页,第5页,第5页。,这也为君子或圣人之所以修身提供了更深层次的意义:圣人或君子所修习得到的“善气”不会因死去而消亡,而是归入太虚,之后再重回这个世间,“知周万物而仁覆天下”,这样,整个人世间的努力才不会因死亡的存在而陷入虚无,而君子只需“修身以俟命”。张载即使在谈论太虚,他的指向依然是人事,即最终要落实到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具体践行。故而张载并不是执著于形上本体的形而上学家。
既然人不能直接礼敬太虚,那么是否应该礼敬天地?这一点张载在《西铭》中表述得很清楚,“乾称父,坤称母”,意即我们礼敬的应该是乾坤(乾坤是天地之用,它并无自身的形体),而非直接的天地之体。如果直言以天地为父母,可能有人就直接以天地之体为父为母,而忽略自身切近之父母。将乾坤作为父母则能够避免这种舍近求远的情况:乾坤之德可体现在与我们有直接血缘的父母身上,父母生我即是乾坤之德的显现;另外,通过气的思想可知,天地亦是我们的宇宙大父母,乾坤为“天地之用”,所以以乾坤为父母,同时包涵着自家父母与作为大父母的天地。落实到具体实践上,人应该通过孝敬自家之父母的方式来回馈天德。这是人对天地的应有之态度。
(二)人与他人、万物之间的关系
落实到具体的生活世界中,张载在《西铭》中描绘了一幅民胞物与、天地一体的场景,这是张载心目中的理想世界,他基于宇宙万物同此一气,并以“家”为基本意象,构建了一幅天下大同的新宇宙图景:乾称父,坤称母,则整个宇宙是一个大家庭,天地间其他人都是我的兄弟姐妹,其他的事物都是我们的同伴,人只有在这个宇宙的整体中才能成就自我,他人、它物都与我息息相关;君主与家相应善待这个家中的老幼贫弱、鳏寡孤独,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最后落实到每个具体的小家,则应该父慈子孝、兄弟友爱,互相成就。一气流通的思想使得人能够大其心,而破除因自私而人为设定的隔阂,能够让自身的仁爱覆周万物,使得其他存在者都在自身的位置上得到安定。张载的这一理论规划,也充分表明在儒家传统中包含着丰富的关于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资源。
总之,张载在《正蒙》中致力于建构“太虚-天地-人物”这样的一个宇宙一体的动态图景,无论是太虚还是气,都不是一个超越性的本体。而无论在哪个层面,他都明确地指向人类在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伦理实践,这是他哲学体系的最终目的。他非但不是在“本体-现象”这一形而上学思维下进行思考的,反而明确地去反对这种思维,这一点反映在他对佛老的拒斥中,同样地,也贯穿在他整个哲学体系的建构中,因此本文认为,前人以“本体-现象”这样的形而上学框架去理解张载,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对张载思想的遮蔽,而忽略了张载哲学中最有价值的成分。